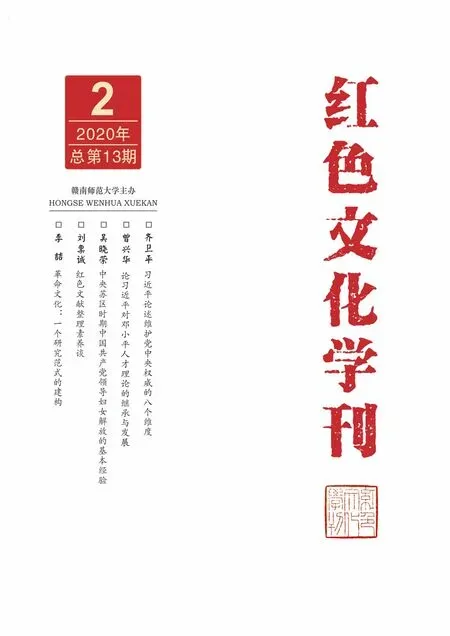红色文献整理素养谈
——以《〈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为例
刘禀诚
由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联合整理,江西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10月出版的《〈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1)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 :《〈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是以中央档案馆影印本《红色中华》(2)中央档案馆 :《红色中华》(影印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为基础,参照其他缺佚文献增补整理而成的。第一次对603.5万字的红色文献《红色中华》进行整理,其辛苦不言而喻,其首创不容置疑,其意义不容小觑。正如该书“编辑说明”所写:“这个文本,填补了《红色中华》馆藏文献的空白,又为《红色中华》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全新的文献史料。”该整理本在如上文本的基础上,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要求,进行了整理校勘,其整理校勘所遵循的体例和原则有11条,主要的有3条:1.繁体字依据《现代汉语词典》改为规范汉字。2.对人名、地名以及译名原则保留原貌,特定翻译尤其是人名的翻译保留原字,但个别国名的译名则统一用今名。人名、地名繁体字能简化的则简化,不能简化的则保留原貌,别字、异体字保留原貌。3.文字保留原有风貌和风格。对十分明显的别字、重字、掉字、倒置字作如下处理:错字改正用“〔〕”标示;漏字用“【】”标示;衍字改正用“〈〉”标注;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字和原件上的缺损字,以“□”代替。这些校勘体例和原则,整理本能大体遵循,但未能一以贯之(详见下文)。尚需说明的是,本文所引例子,均为《红色中华》整理本的照实录入,例子中的下划线则为本文笔者所加,例子最后注明出处(包括《红色中华》期数、版面,整理本所见页码;《红色中华》简称《红》)。对整理本存在的校勘问题,本文拟从五方面论述红色文献整理的必备素养。
一、在思想上,要有红色文化素养,有一颗炽热执着的“红心”
顾名思义,红色文献整理的对象是红色文献。“红色文献”的定义,各有说法。赵莉认为,“红色文献资料主要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起至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之前由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所出版、发行、制作的各种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党的领袖的著作、党组织各类文件及根据地出版的各种书籍和报刊杂志等”(3)赵莉 :《红色文献资料综述》,《丝绸之路》2009年18期。。我们注意到与此相关的“红色文化”的论述,朱桂莲认为,“绝大多数学者在具体研究中,是把中国红色文化理解为一种跟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红色政权密切联系的积极进步的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并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先进文化”(4)朱桂莲 :《近年来我国红色文化研究文献述评》,《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据此,再结合《现代汉语词典》“文献”释义,“红色文献”可定义为“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红色政权密切联系的积极进步的具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它属于红色资源范畴。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南京军区机关时强调指出,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对此,周金堂作了辩证阐释:红色资源承载着红色基因、红色传统;保护利用好红色资源,就能够传承、发扬好红色传统;利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红色传统,就能够优化遗传好红色基因,这是永葆中国共产党红色生命体生机活力的价值所在。(5)周金堂 :《把红色资源红色传统红色基因利用好发扬好传承好》,《党建研究》2017年第5期。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6)习近平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红都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就是兼具“文物”“遗产”“文字”功能并值得利用的重要的红色文献、红色资源。
红色文献整理,首先就要有一颗热爱红色资源的“红心”。毋庸置疑,如果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没有对中国革命光辉历程的真挚情感,没有一颗炽热执着的“红心”,是不可能有《红色中华》整理本的问世。无疑,整理本《红色中华》是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培训”的极好素材,也为广大红色文献爱好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同时,我们不应忽视红色文献整理的两种态度或倾向:一是只要有一颗热爱红色文化的“红心”,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功底,就能把红色文献校勘好,整理好,或者干脆说,从事党史党建研究的就可以胜任了;二是研究语言文字的或者专事文献整理的,则无视红色文献的存在,似乎文献整理中压根就没有“红色文献整理”。这两种态度或倾向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研究党史党建的忽略研究语言文字的,研究语言文字的则排斥红色文化中的语言文字,从而造成红色文献整理的“偏食”现象,以及研究队伍的“短板”现象(唱主角的往往是党史党建、新闻传播方面的专家,几乎没有专业的语言文字研究者参与其中)。
二、在内功上,要有专业知识素养,有一颗辨伪存真的“慧心”
从事红色文献整理,只有“红心”、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扎实的内功,扎实的专业知识素养,主要包括文献素养、语言素养。
(一)文献素养
主要指文献校勘学素养。陈垣首提“校法四例”:“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二为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三为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四为理校法。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鲁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7)陈垣 :《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4—148页。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利用上下文的“本校法”,以及推理校勘的“理校法”。
1.本校法。《红色中华》目前只有一个版本,即中央档案馆所藏原件及其影印本,因此完全可以采用本校法。例如:
(1)鲁黄河于八月初旬,下游之武定县境内角咀老堤决,口丈余将套堤冲决二口,各宽二丈余……(《红》第33期第4版,整理本603页)
据前文“八日晨,汾河陈堤堰又复决口丈余……”,上例中的划线处当作“决口丈余”,逗号当移至其后。这是运用了前后文校勘的本校法,以及推理校勘的理校法。又如:
(2)你们不能从积极上提出实行全线出击,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攻夺取吉、赣、抚南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为当前的中心任务……(《红》第33期第4版,整理本603页。按:“围攻”两字后应有逗号,原文、整理本均失察)
据前文“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攻,夺取吉、赣、抚、南昌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上例中的划线处当作“吉、赣、抚、南”或“吉、赣、抚、南昌”。这是运用了前后文校勘的本校法。再如:
(3)复□二十一日拂晓进攻赖地之万恶靖匪……(《红》第36期第4版,整理本680页)
据前文“又于九月十九日进攻东留”,上例中的缺字□(影印本只有“於”的上半部,较模糊)当作“于”,这也是运用了前后文校勘的本校法。
2.理校法。理校法,就是推理的校勘,是校勘的补充方法。对错误采用推理的方法加以改正(即“定其是非”),主要从语言、体例、史实等方面着手的。例如:
(4)行政院长为臧式毅,司法院长为欣伯,监察院长为张景惠,资源委员会为于冲汉,交通委员为于鑑修……(《红》第9期第7版,整理本143页)
据影印本,下划线处“资源委员会”当作“资源委员长”。整理本“资源委员会为于冲汉”于理无解,因为“资源委员会”是一个机构名称,不是职务或官衔。又如:
(5)戈登路一百八十一号日商同兴纱厂工人,前因愤于厂方无故开除大批工人,任意压迫,加重工作,冠扣工资而罢工……(《红》第9期第6版,整理本140页)
据下一则消息“绢丝工人开会”之“原有赏工,不准克扣”“慰劳金仍照旧章,不得克扣”,“冠扣”当作“克扣”,原文、整理本皆把“克扣”误为“冠扣”,这是因为“克”的异体字“剋”“尅”与“冠”形似而容易混淆。
除了上面校勘方法的使用以外,文献素养还涉及校勘术语的灵活运用。整理本《红色中华》需要校勘的错误疏漏有讹、脱、衍、倒、漏。讹:表现在形近音近而讹误,因上下文而讹误,不懂词义语法而讹误,不知行业术语而误改。脱:文献文字在传写中脱去一字、数字或数句,称脱文。在整理本中主要表现为原文有而整理本脱落的情况。衍:原文本无而传写、刻写、排印误增的文字称衍文,又称羡文、衍字;可分为原文无误而整理本衍文者(整理者臆造的“衍文”)、原文衍文而整理本疏于校勘者。倒:指的是原文并无讹误、缺脱或衍羡,但在传写中文字先后次序被颠倒了。漏:指的是原文有误而整理本疏于校勘。这五种错误疏漏所需语例可参见本文所举例子,此不赘述。
(二)语言素养
既包括古代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的素养,也包括现代语言学的素养,还包括方言文化的素养。由于整理者语言素养的欠缺,整理本大致出现如下失误。
1.文字、词汇素养。这里涉及异体字、形似字、古语词等方面的语言素养。整理者由于不谙异体字字形、古语词用法,因字形相似而导致讹误的情况屡见不鲜。
先看异体字的,例如:
(6)另一种是经过社会民主党而寔〔实〕行法西斯蒂专政,这些都是为了更有力的来镇压国内革命和对付无产阶级的主要工具。(《红》第4期第2版,整理本34页)
据影印本,划线处原文为“寔”,乃“实”之异体字,彼时“寔行”“實行”并行使用,没有校勘之必要,径直转写为“实”即可。又如:
(7)日本向法国借大批军欵〔款〕(《红》第11期第5版标题,整理本187页)
据影印本,划线处原文为“欵”,乃“款”之异体字,彼时官方、民间使用率都很高,并无校勘之必要,径直转写为“款”即可。又如:
(8)夺取吉赣等中心城市,使赣江两峰打成一片,就可以完全实现,望你们努力!奋斗!(《红》第33期第9版,整理本617页)
据影印版,划线处之“峰”为“峯”,“峯”为“峰”之异体字,与“岸”有一定相似性,容易讹误。前文有“赣江西岸”一语,可资佐证,此“赣江两峰”当作“赣江两岸”(即赣江东岸、赣江西岸),否则表示河流的“赣江”何以有“两峰”?“两峰”又焉能“打成一片”?
再看形似字的,例如:
(9)九日上海电:汪精卫时对上海市民声明,国民政府并未对十九路军听其弧军失援,当此时局严重之时,计划未能宣布等语,以掩饰过去企图解除抵抗日军士兵武装阴谋。(《红》第9期第4版,整理本136页)
据影印本,“弧军”当作“孤军”。又如:
(10)建筑工程定于一九三六年完成而铁道经过区域,皆系金厉矿产富饶之地,至铜铁之属,蕴藏尤富云。(《红》第33期第2版,整理本598页)
据影印本,“金厉”之“厉(厲)”当作“属(屬)”。按:整理本“完成”之后当停顿,应加上逗号。又如:
(11)十七日,驻杭城粤敌进攻卢丰区为该区赤卫军迎头痛击,毙敌十余名,伤敌二十余名,敌不支即向安乡退回杭城。(《红》第42期第4版,整理本810页)
这段整理文字,除了标点失察(“驻杭城粤敌进攻庐丰区,为该区赤卫军迎头痛击”“敌不支,即向安乡退回杭城”)以外,还有文字转写失误,即把地名“庐丰”(繁体为“廬豐”)误为“卢丰”(繁体为“盧豐”)。查影印本,先是原文把“庐丰”误为“蘆豐”(简体为“芦丰”),然后整理本又误为“卢丰”。也就是说,原文、整理本,都混淆了“庐”“芦”“卢”,它们的繁体字分别为“廬”“蘆”“盧”。
最后看古语词的,例如:
(12)痘疮预防方法,种牛痘苗,虎列拉预防方法,注虎列拉血清,各种传染病,都可选注射传染病的血清(如白喉,伤寒,鼠疫……),已患着传染病的人,迅速进入医院,若离医院太远,在家调养,必须远居,每天只可指定一人招呼,所用器具,被服,碗者……不能与常人共享,房内注意清洁消毒,用石灰水。(《红》第9期第10版,整理本154页)
据影印本,划线两字皆清晰可见,“选”为“先”之误,“碗者”之“者”乃“箸”之误。“箸”(zhù),“筷子”之义,“碗箸”或“碗筷”并称很常见,而“碗者”并称令人费解(“作者、著者、编者、记者”中的“者”皆为“的人”之义,前一语素皆为动词性)。其实,一直受大家青睐的朱自清《背影》一文最后一段就提到“箸”字:“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客家方言至今还保留了“箸”的古汉语用法,原中央苏区的主流方言即为客家方言。又如:
(13)华军以此战为吴淞之生死关头,竭全力搏击,日军突围几十余次,均不得逞……(《红》第10期第2版,整理本159页)
据影印本,“几”实为“凡”(字迹清晰,赫然在目),有“总共”之义,这是古语词的遗留与继承,也是民国时期词汇“亦文亦白”特征的体现。因此“日军突围几十余次”实为“日军突围凡十余次”之误。又遍查《红色中华》,凡是涉及“几十”“几百”“几千”之义的均用“数十”“数百”“数千”(参例18、例22、例30)表示,无一例外。
2.语法素养。除了语法的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还涉及逻辑关系、标点符号。例如:
(14)一月二十九日上海专电:国民党市政府三十日将抗议:内容谓日总领事所提出四项条件,业经承认答复送达,日总领认为满意。(《红》第8期第2版,整理本102页)
据影印版,下划线部分原为“向日领抗议”,整理本“三十日将抗议”有误:把“向”误为“卅”,把“领”误为“将”,且这一所谓将来时表达根本无法成立。又如:
(15)又电:宝山路之战,国民党军队方面还击甚少(这里士兵反帝坚决表现以及历年国民党出卖中国压迫士兵反帝之积累的一种革命情绪爆发),而日方开枪甚密,但伤病虽中弹犹高呼前进……(《红》第8期第3版,整理本103页)
据影印版,下划线处原文为“是”,无误,整理本有误。括号中内容是新闻点评,应为判断句,而整理本弄成联合结构(两个偏正结构的组合——“这里士兵反帝坚决表现”“历年国民党出卖中国压迫士兵反帝之积累的一种革命情绪爆发”,联合标记是“以及”),况且“这里士兵反帝坚决表现”令人费解。又如:
(16)对于成分和质量要加以详细的检查,不要使阶级异己分子和不积极的,身体不健康的分子,充数送去,要使当红军的工农群众中最健康的最积极的分子,这样才能在质量上去加强红军。(《红》第34期第2版,整理本623页)
据影印版,“要使当红军的工农群众中最健康的最积极的分子”之“当红军的”后脱落了判断动词“是”字,即“要使当红军的是工农群众中最健康的最积极的分子”才是原版中正确无误的表达。
3.音韵素养。在整理本中表现为语音相近而误。例如:
(17)现在西伯利亚铁道,大部分正敷〔辅〕双轨,并建筑新路,新路完全〔成〕以后,两地距离可以减少。(《红》第33期第2版,整理本598页)
整理本认为“敷”乃近音字“辅”之误,非也。在校勘中,确实有语音相近而误的现象,但此例并非如此。查《现代汉语词典》,“敷”除了“搽上、涂上”(敷粉、敷药)、“足、够”(入不敷出)等义项以外,还有“铺开、摆开”(敷设)之义。“大部分正敷双轨”即为“大部分正在敷设(铺设)双轨”之义,而如果按照整理本“大部分正辅双轨”,则“正辅双轨”令人费解。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及反义原则,“正”与“歪、侧、偏、反、副、负”相对,“辅”与“主”相对,“主”与“客、宾、奴、仆、从、辅、副”相对,且“双轨”是不分主次、正副的,是指“有两组轨道的铁路线”。另据考察,江西不少地方把轻唇音(唇齿音)f读成重唇音p,比如“敷药”的“敷”,“扶起”的“扶”,这是古音(古无轻唇音)的遗留现象。据音韵学知识,“敷”“铺”同属滂母虞韵。因此原文无误,语音、语义皆有理据。又如:
(18)代表毫不畏惧,声言“头可杀,上工命令不能下”,工人代表被扣,一时数千人重重叠叠地将军队包围,去抢夺被扣代表,双方冲突,吼声与撕〔厮〕打声混成一遍,于是张木阶睹此情形,卒不得不将代表释放。(《红》二七增刊第1版,1932年2月3日,整理本122页)
据影印本,下划线处“混成一遍”原文、整理本皆误,即原文、整理本把p误成了b,b和p的相同点都是双唇、清、塞音,不同在于前者为不送气音,后者为送气音,应改为“混成一片”。
4.方言文化素养。例如:
(19)本日有一团总开门投降,缴枪五十余支,俘获五六十名,豪绅地主正在清查中,我军毫无伤亡损失。(《红》第40期第2版,整理本752页)
据影印版,“五六十”前脱落了“百”,合起来即为“百五六十”,本期下文有可资佐证之语“总统选举之两院投票时,罗斯福可获三百五十七票,胡佛百十二票”(整理本758页),此为方言的数字表达。但“一”的隐含是有条件的,仅限于一百至二百之间、一千至二千之间的起始数字“一”,比如“英法意派舰赴沪,美亦有十五艘开来,今日到齐,载有陆军千二百名,陆战队四千八百人”(《红》第9期第2版,整理本131页)中的“千二百”。
三、在态度上,要有精益求精精神,有一颗一丝不苟的“匠心”
前面提到在文献素养上,有需要校勘的错误叫做衍文、脱文,指的是原始版本的增字、减字错误,而这里说的是整理者对原始版本文字的不合理增减、替换。
1.有误增的,例如:
(20)现下天气时疫流行,预防之法,十分不注意,这里(福建四都十二军后方总医院)痘疮,痢疾,痳疹,虎列拉……发生者亦颇为惊人,死亡律〔率〕中传染病者占十〈六〉分之六、七,一沾此疫,服药亦甚困难……(《红》第9期第10版,整理本153页)
据影印版,原文并无下划线中的“为”“六”字(整理本认为“六”为衍文,其实是自己臆造的)。又如:
(21)据最近几天,日军屡次进攻,俱遭受失败,死伤甚重,华军阵地线,自吴淞路至江湾一带,均有进展,日军亦在钱家滨,军工路,陆家宅一带,积极备置。(《红》第10期第3版,整理本160页)
据影印版,下划线“受”原文无,实为整理者不细心导致的衍文。按:下划线“备”实乃“布”之误,原文无误。
2.有误减的,例如:
(22)正月四日晚上,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城区群众大会于兴国工农俱乐部,据悉尼港欢送兴国县新战士的欢送会。到有群众数百人,新战士四百三十四人,省苏两级机关的代表,会场空气紧张热烈异常。(《红》第9期第8版,整理本146页)
据影印版,下划线字第一处原文为“二”,第二处后面漏了“召集”二字,第三处原文为“县”,总之以上三处原文皆无误,故整理本第一处第三处都是替换不当(其中第三处属于“理校法”的校勘范畴——因为“省苏”就是“省苏维埃政府”的简称,就是一级政府机关,何来“两级机关”之说?“省县”则是两级,于理说得通),第二处是误减文字。
3.误替的:可分为整理本误校而替换不当的,有校勘标记(如〔〕);也有识别不清而替换不当的,没有校勘标记。前者如:
(23)统一各种纱〔钞〕票,废除正金银行纱〔钞〕票云。(《红》第9期第2版,整理本131页)
据影印版,下划线处原文为“钞票”,无误。后者如:
(24)十四日上午七时上海电:十三日上午十时许,日军藉烟弹之掩护,竟〈被〉偷渡蕴藻滨,在北岸曹家桥上陆,当时情形异常紧张,日军抱必胜信心,努力向华方防线冲击,华方奋勇迎战,并急调后方援军率部参加作战,成大包围形势,日军顽强抵抗不退……(《红》第10期第2版,整理本159页)
据影印版,依稀可辨划线字分别为“之”(“日军抱必胜之心”)、“军”(“华军奋勇迎战”)、“全”(“急调后方援军全部参加作战”)、“取”(“取大包围形势”)。
四、在方法上,要有历史唯物主义,有一颗敬畏历史的“公心”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烙印或特征,语言文字亦然。整理中央苏区时期的红色文献,就应该回归到彼时的时代面貌(尤其是语言文字面貌)上来,了解彼时词语(包括人名地名)的时代特征,否则就会出现“关公战秦琼”式的“移时”或“穿越”。
(一)特有词语的时代特征
(25)土地问题必须实行检查农村阶级斗争要继续深入,对于租佃条例中央尚未颁布,主要原则是消灭地主租田制度,但对于地主承租土地在原则上绝不许可,这是为彻底消灭地主与土地的关系;同时富农在目前不准买入人家的田,只可租借。(《红》第33期第9版,整理本616页)
据影印版,“租田”实为“租佃”之误。按:“实行检查”后应有逗号,“继续深入”后的逗号应为句号。又如:
(26)国民党更是歪在帝国主义怀中才能持得着生命到现在,当然不敢说什么了……这本书是在秘密中写成的,大家都不晓得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红》第36期第68版,整理本685页)
据影印版,两处“什么”皆当作“甚么”,“甚么”有近代汉语、民国语言特色。该期下一篇报道有“所以又受日本军阀的怂恿,宣布甚么海关自主”之语,其中“甚么”没有擅改为“什么”,就是尊重原文,恪守了“体现时代特征”的校勘原则。
(二)单音节词的时代特征
(27)何叔衡通知报告检查江西省苏工作及出席该省工农检查部联系会议之经过情形后,即审□省给中央的工作报告,遂一指出该省最近工作的优点与缺点,议决先给省苏一指示信。随后再派专员指导一切。(《红》第34期第8版,整理本639页)
据影印版,下划线“通知”乃“同志”之误,“遂一”为“逐一”之误,“随后”前面的句号为逗号之误,原文均无误,整理本有误。下划线“□”中的字依稀可见,当“该”无疑,况且前后文均有“该省”(见波浪线)出现,可资佐证。那为何整理者不敢肯定“□”为“该”呢?我以为,“□”前面的“审”让整理者困惑。整理本“编辑说明”交代的第5条整理校勘原则认为,一些使用频率较高的异体字、别字,为体现时代特征,保留原貌不变。这虽然说的是文字处理原则,其实在处理词汇、语法问题时,也可借鉴这一原则:“审”是单音节词,是古汉语的遗留;单音节词普遍使用是民国时期词法的时代特征,是古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型过程中的构词特征。再如“采一致态度”(《红》第8期第4版,整理本107页)、“采一致行动”(《红》第9期第2版,整理本130页)、“采相当举动”(《红》第12期第3版,整理本203页)之“采”,“取一致行动”(《红》第8期第1版,整理本100页)、“取强硬态度”(《红》第9期第6版,整理本140页)之“取”,皆可资佐证。
(三)人名地名的时代特征
(28)少先队代表王盛荣,共产党福建省委代表李明先,共产党江西省委代表刘启耀,及五军团代表等等先后致词(演词从略)。(《红》第9期第8版,整理本146页)
据影印版,所谓“刘启耀”实乃原文“刘启曜”之误。“曜”是“耀”的异体字,不是“耀”的繁体字,因而作人名时不能替代。又如:
(29)罗炳辉,黄苏,赖芹香,郭玉杨,沈德昌等三十五人为福建省苏执行委员【。】(《红》第15期第5版,整理本268页)
据影印版,所谓“黄苏”实乃原文“黄甦”之误。“甦”是“苏”的异体字,不是“苏”的繁体字,“蘇”才是“苏”的繁体字。“甦”用作人名时,不可随意更改。整理本的此处误改,也违背了整理本“编辑说明”中的第二条校勘原则:“人名、地名繁体字能简化的则简化,不能简化的则保留原貌,别字、异体字保留原貌。”人名被篡改了,主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人名有其特定性、符号性。
同理,地名也有其特定性、符号性。中央苏区涉及的变迁地名有“雩都、寻邬、大庾、虔南、新淦”,这些地名因为生僻,1957年国务院宣布分别改为“于都、寻乌、大余、全南、新干”,其实它们不是真正的繁简字关系,而是简易识字原则下的同音字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同音替代,为了“大家称便”,带有较强的人为色彩。整理本忽略了人名地名的特定符号与时代特征,没有还原人名地名的本来面貌,而是以所谓的今字进行转写,这是典型的“以今律古”。
五、红色文献整理的综合素养
请看下例:
(30)十三日晨二时许,华军由蕴藻滨向日陆战队袭击左近之敌军大队根据地,日军忽〔匆〕促应战,迫击炮者甚多,晨五时许,日军以重炮由蕴藻滨左冀向对岸射发烟幕弹,使浓烟密布于对岸,同时陆军在滨上架设浪桥偷渡,至六时日军六七百人,占据曹家桥,华军即乘其尚未渡齐之际,向前冲锋,一时肉搏血战,日军死伤百余人,坠水溺毙者,亦近百人,同时日军另一队数百人,攻击纪家桥,华军应战,日军退却,候〔侯〕家木桥,亦有日军攻击。(《红》第10期第3版,整理本160页)
以上这段文字,共有5处整理失误,这涉及多方面知识素养:(1)文字知识。这里包括异体字、形似字的素养。第一个下划线字“忽”原文为“怱”,是“匆”的异体字,是无须校勘的。问题是整理本把原文“怱”误为“忽”而加以所谓校勘,这是不细心的表现。第三个下划线字“左冀”乃原文“左翼”之误,这是形似字之误。(2)校勘知识。这里指的是理校法。“迫击炮者甚多”实乃原文“被击毙者甚多”之误。“迫击炮者甚多”中有“者”,无从索解。(3)单音节词知识。复合词“冲锋”乃原文“冲战”之误,“冲战”为“冲锋战斗”之义,“冲”“战”皆为单音节词,单音节词较为丰富是民国时期汉语的一个显著特点。(4)姓氏或地名知识。“候家”实乃原文“侯家”之误,“侯”表姓氏,“侯家木桥”是表处所的,今上海仍有“侯家桥”“纪家桥”等地名。又如:
(31)二十四日起二十七日之四日间,在九州岛福冈开动员会议,□□等到会者一百六十余人,九州岛之防备以八幡制铁所为主,研究下列六项:一、以门□、下□等港口为主,研究物质之需要及其供给情形……六、社会治安之维持方法。其中所要实演者为:(一)如何保全熔铁炉;(二)市民之避难方法;(三)□池及其他之矿山须派人实地调查等三项,担任此□工作者为在乡军人,学生等,北九州实行后,推及大阪及东京等地方。(《红》第34期第7版,整理本635页)
据影印本,划线部分除“起”为原文误用、“九州岛”为整理本误增“岛”字以外,其他“□”均为整理者辨识不力(原文有些模糊,但细看能辨识)而导致缺失。特更正如下:
(32)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之四日间,在九州福冈开动员会议,军会等到会者一百六十余人,九州之防备以八幡制铁所为主,研究下列六项:一、以门司、下关等港口为主,研究物质之需要及其供给情形……六、社会治安之维持方法。其中所要实演者为:(一)如何保全熔铁炉;(二)市民之避难方法;(三)三池及其他之矿山须派人实地调查等三项,担任此种工作者为在乡军人,学生等,北九州实行后,推及大阪及东京等地方。
以上这段文字,涉及校勘的综合知识:有语法语义知识(与理校法有关),如“二十四日起二十七日之四日间”就很费解,可改为“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之四日间”或“二十四日起四日内”,前一种改法最接近原貌;有文字知识,如“下关”之“关(關)”,“此种”之“种(種)”;有地名知识,如门司、下关、三池,此处皆表示日本地名(按:云南亦有“下关”)。又如:
(33) 日本帝国主义自从占领东三省以后,更进一步的向热河进攻,并积极的摧毁中国的群众,因此,引起各地群众的坚决反抗……又日陆军决派熊本□岛及姬路二师团,增驻南北满云。(《红》第9期第7版,整理本144页)
据影印本,划线部分“摧毁”为原文“摧残”之误,“又”表示“又有消息”“补充消息”,后应该加上逗号或冒号,“□”原文模糊,但依稀可辨为“广(廣)”,“熊本”“广岛”“姬路”皆为日本地名,因此前两者之间要加顿号,“二师团”应改为“三师团”(“熊本、广岛及姬路三师团”)。此段文字涉及文字知识、地名知识。另外,中央苏区涉及的变迁地名有“雩都、寻邬、大庾、虔南、新淦”,这些地名因为生僻,1957年国务院宣布分别改为“于都、寻乌、大余、全南、新干”,其实它们不是真正的繁简字关系,而是简易识字原则下的同音字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同音替代,为了“大家称便”,带有较强的人为色彩,整理者在整理时务必还原地名的时代特征,不能“以今律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