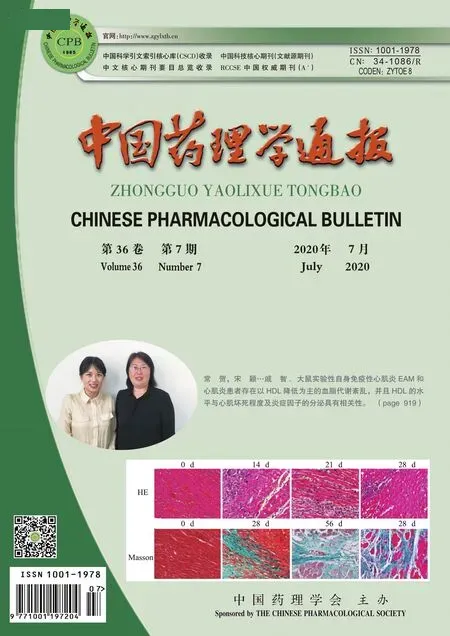植物药抗蛇毒局部毒性效应作用与机制研究进展
董德刚,宋 梅,邓中平,毛文丽,王万春
(1. 江西中医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4;2. 上海中医药大学创新中药研究院,上海 201203;3. 江西中医药大学科技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4;4.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西 南昌 330006)
在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尤其在热带与亚热带地区,毒蛇咬伤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据WHO统计,全世界每年约有500万人被蛇咬伤,其中超过10万人死亡,多达40万人截肢和永久性缺陷[1]。我国南方夏秋季节毒蛇咬伤是常见的急危重症,6~9月是蛇伤事件高发期。我国蛇的种类繁多,现有蛇200余种,毒蛇近50种,剧毒蛇10余种,每年毒蛇咬伤患者达50万余人次,蛇咬伤死亡率为5%~10%,致残率为25%~30%[2]。另外,偏远农村蛇伤患者选择乡村医师或经验方进行治疗的很常见,这些病例鲜有统计。因此,实际病例可能大于报道数据。尽管如此,毒蛇咬伤事件却未受到足够的关注与重视。鉴于此,2017年,蛇毒中毒被WHO再次列为A类被严重忽视热带疾病名录。
毒蛇咬伤病理表现包括全身症状与局部效应,全身症状主要表现为神经毒性、肌毒性、心脏毒性、细胞毒性、溶血、凝血和低血压作用等;局部效应包括出血、水肿、疼痛、肌坏死、皮肤坏死以及继发性感染等[3]。前者致死性强,后者是致残或导致其他二次伤害主要因素。植物药通过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的有效分子群协同作用于蛇毒毒素,尤其在治疗蛇毒局部效应及并发症等方面优势明显。全世界大多数偏远地区的农村和部落居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民间植物药治疗毒蛇咬伤,尤其在我国及印度农村地区极为普遍。本文就药用植物在治疗毒蛇咬伤局部病理中的作用方面作一综述。
1 蛇毒中产生局部毒性效应主要组分
蛇毒是一种具有药理活性的酶和非酶蛋白及肽毒素的复合混合物,是毒蛇在自然界长期进化过程产生具有麻痹、帮助消化猎物及防御功能的一类物质。蛇毒中含有30多种酶,主要包括蛇毒金属蛋白酶(snake venom metalloproteinases,SVMPs)、磷脂酶A2s(phospholipases A2,PLA2s)、蛇毒透明质酸酶(snake venom hyaluronidases,SVHYs)、丝氨酸蛋白酶、乙酰胆碱酯酶、转氨酶、磷酸二酯酶、核苷酸酶、ATP酶和核糖苷酶[4]。其中SVMPs、PLA2、SVHYs是导致局部效应的主要成分,抑制这些酶的活性能明显减轻局部组织损伤。
SVMPs是由一类具有不同结构域组成的锌依赖性蛋白酶。研究表明,SVMPs通过直接作用于毛细血管而引起出血,分裂基底膜组分的关键肽键,从而影响基底膜与内皮细胞的相互作用,这些细胞在体内发生一系列形态学和功能改变,在内皮细胞中形成裂隙,通过裂隙发生血液渗出[5]。SVMPs也参与了皮肤损伤、肌坏死、水肿等局部病变[6],此外,SVMPs也可以通过裂解内源性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s)的前肽而激活,MMPs在细胞外基质的降解和重构中至关重要,并抑制受损骨骼肌的再生[7]。因此,SVMPs在蛇毒诱导的局部组织损伤的发生中起关键作用,是开发新型抗蛇毒药物的重要靶点。
SVHYs是降解细胞外基质及血管、毛细血管、平滑肌周围结缔组织透明质酸的主要酶,能损伤靶器官的结构完整性,促进其他毒素的分布与毒性效应而被称为“传播因子”[8]。SVHYs降解咬伤部位中的透明质酸(HA)是局部组织损伤不断扩散的关键因素,SVHYs不仅损害局部组织,且通过促进PLA2s、蛋白酶等主要蛇毒毒素进入体循环,增加了这些毒素的效力。尽管SVHYs在局部毒理效应中起重要作用,但人们对它的研究较少,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
PLA2s酶水解在甘油骨架的sn-2位的甘油磷脂,释放溶血磷脂和脂肪酸,是所有磷脂酶中研究最多的酶。PLA2s除了具有主要的催化功能外,还可诱导突触前或突触后神经毒性、心脏毒性、肌毒性、血小板聚集抑制、水肿、溶血、抗凝、惊厥和低血压等多种作用[9-10]。PLA2s使磷脂组分的无序排列引起膜结构和功能完整性的改变,导致Ca2+离子流入,肌钙蛋白收缩,激活Ca2+离子依赖的蛋白酶和内源性PLA2s,并使线粒体受损,这些最终致使大量细胞死亡[11]。
2 蛇毒局部效应的治疗策略
抗蛇毒血清是蛇伤唯一特异性药物,能有效减轻蛇毒致死性的全身作用,明显降低了毒蛇咬伤的致死率。然而,抗蛇毒血清已被证明在治疗蛇咬伤引起的局部病理方面是无效的[12]。虽然体外实验证实通过毒液和抗蛇毒血清共孵育,能有效中和局部作用毒素,即抗蛇毒血清中有足够针对局部作用毒素的抗体,但在实际的蛇咬伤中,局部病变发展迅速,蛇毒局部作用的毒理动力学与抗蛇毒血清抗体的药代动力学不匹配[13]。抗蛇毒血清抗体或其片段只有损伤发生后才能够到达受影响组织。因此,蛇伤患者尽管使用了抗蛇毒血清,局部效应仍在继续发展。
抗蛇毒血清还存在如免疫反应风险大、成本高、部分地区难以获得等诸多局限性。因其价格贵、运输不便及存储成本较高等问题,在最需要抗蛇毒血清的农村诊所或乡镇卫生院往往因抗蛇毒血清短缺而延误治疗。另外,抗蛇毒血清作为外源蛋白使易感人群出现超敏反应、“血清病”等不良反应。抗蛇毒血清的不良反应如处理不当,常引起严重后果,甚至威胁生命。
目前,植物药用于毒蛇咬伤的治疗已被广泛报道。植物药治疗蛇伤具有成本低、易获得、室温稳定、无过敏反应等优点。此外,蛇毒液的成分组成随物种的不同而变化,并因大小、性别、生境、食物和季节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应用植物药治疗蛇伤,医生可依据具体情况确定药物的组成及比例,以期达到个体化治疗蛇伤的目的。如今,这些用于民间传统医学的草药解毒剂已受到了世界各地毒理学家的广泛关注。
3 抗蛇毒局部毒理作用的药用植物种类概况
3.1 单味植物药单味植物药抗蛇毒局部毒性效应的基础研究已陆续报道。Molander等[14]将抗蛇咬植物数量较多、代表不同文化、地理和植物区系的国家:中国、巴西、尼加拉瓜、尼泊尔和南非5个国家抗蛇伤的药物植物建立数据库,数据集进行回归分析和二项式分析,发现夹竹桃科、唇形科、茜草科和姜科等为抗蛇毒植物的“热点”科。Giovannini等[15]收集了中美洲260份独立的植物利用报告,用于治疗咬伤的有208种植物,这些种隶属146属,分布于74个植物科。用于治疗中美洲的蛇咬伤有豆科(22种)、胡椒科(18种)、茜草科(13种)、天南星科(8种)、夹竹桃科(7种)、马兜铃科(8种)、菊科(6种)、旋花科(6种)、西番莲科(5种)、蓼科(5种)和茄科(5种)。其中夹竹桃科、茜草科在二文中均有提及。
Alves等[16]研究了远志科植物BredemeyerafloribundaWilld根提取物(BFRE)对巴西矛头蝮(Bothropsjararacussu)毒液(BjuV)引起的局部损伤作用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BFRE对 BjuV诱导的磷脂酶A2和蛋白水解活性均有抑制作用, BFRE (150 mg·kg-1)可抑制BjuV (50 μg每只)诱导的足部水肿,减轻整体水肿。BFRE治疗可明显降低BjuV引起的出血和坏死作用,能有效治疗BjuV诱导的局部毒性作用。Krishnan等[17]将不同浓度的蛇根草根(Ophiorrhizamungos)提取物与圆斑蝰(Daboiarusselii)毒液预孵育30 min后,涂于6日龄的鸡胚卵黄囊膜上,6 h内观察胚胎存活率及出血情况。结果显示,较高浓度的根提取物完全消除了毒蛇毒素引起的出血损伤,认为鸡胚是一种新型的无感动物模型,它减少了高级哺乳动物实验模型的痛苦,对毒液的毒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3.2 植物药复方制剂目前,针对蛇伤的治疗,临床多采用复方药物治疗蛇伤,其中季德胜蛇药片是目前公认的蛇伤特效药,该药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季德胜蛇药片是国家绝密配方,处方公布有重楼、蜈蚣、干蟾皮、地锦草4 味药,具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等功效,可内服与外敷,使用方便,价格低廉,在我国民间已被广泛应用于毒蛇咬伤的治疗。
Chen等[18]通过126例蛇伤患者临床观察评价季德胜蛇药治疗眼镜蛇毒局部损伤作用,对照组外用40%甘油硫酸镁治疗(n=52),治疗组季德胜药湿敷(n=74)。观察皮肤和软组织局部最大坏死面积、消退时间、愈合时间和植皮率。结果显示:治疗组局部皮肤软组织坏死面积最大为(19.9±7.3) cm2,对照组为(23.3±6.4) cm2。治疗组愈合时间短于对照组[(32.1±3.7)vs(34.4±4.5) d],治疗组植皮率低于对照组(10.81%vs25.00%)。对照组与治疗组在皮肤软组织局部最大坏死面积、愈合时间、植皮率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认为季德胜蛇药外用可促进眼镜蛇咬伤所致皮肤软组织坏死创面愈合,降低植皮率。
此外,雷允上药业生产的上海蛇药片,中药方剂犀角地黄汤、蛇黄散、复方三角草片、复方四黄液、双黄蛇药散、三黄散、四妙勇安汤、青龙蛇药片等是目前治疗毒蛇咬伤局部损伤常用经典方或复方成药,以及自制院内制剂或验方如717解毒合剂、蛇肿散、蛇伤外敷散、解毒通腑汤、蛇伤解毒散、抗蝮蛇2号、蝮蛇解毒汤等复方文献证实均有抗蛇毒局部效应。
在诸多的治疗蛇伤复方中,半边莲、白芷、七叶一枝花使用频率较高,其次如甘草、雄黄、野菊花、金银花、虎杖、车前子等中药也常用于蛇伤药配伍组方。这些药物通过多层次、多靶点、多途径发挥药理效应,临床证实对蛇伤患者局部损伤修复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3.3 植物源性单体成分体内、外实验表明,药用植物中的多种生物碱、黄酮类 、多酚类、萜类、皂苷类、甾醇类、苷类等成分能有效治疗蛇毒所致的局部毒性效应[19]。其中以眼镜蛇毒与蝮蛇毒的防治为主。植物药治疗蛇伤方面虽已被广泛研究,但尚未找到植物单体成分可有效治疗蛇伤药物。现有植物抗蛇毒研究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基于在体外实验获得的结果,研究对象主要是与局部组织损伤相关的酶,即SVMPs、PLA2s、SVHYs等。
目前,单宁、马兜铃酸、槲皮素类以及植物源性糖蛋白是目前研究较多的抗蛇毒局部效应的植物药单体。徐淑芬等[20]发现,柿子单宁能抑制磷脂酶A2 酶、L-氨基酸氧化酶和乙酰胆碱酯酶活力,并存在剂量-效应关系。Sachetto等[21]证实,芦丁能减轻局部出血,增加反应性防止了红细胞计数和纤维蛋白原水平的下降,减少了尾部出血并能缩短凝血酶原时间。Machiah等[22]从茄科植物Withaniasomnifera中提取的糖蛋白通过酶谱分析和皮肤组织染色检测,发现该糖蛋白具有明显抑制眼镜蛇(NajaNaja)和蝰蛇(Daboiarusselii)毒液的透明质酸酶活性。
鉴于蛇毒成分与毒效作用的复杂性,单体药物并不适宜抗蛇毒的临床治疗,提示多种植物药或单体复合物是蛇伤临床防治的主要研究思路与方向。
4 植物药抗蛇毒局部效应药理机制
4.1 抗炎作用蛇毒金属蛋白酶、磷脂酶A2s等介导的炎症发生是蛇毒引起局部组织损伤的致病机制,产生水肿,血管通透性增加和白细胞迁移等局部应激性反应。植物药通过抗炎症反应是其实现抗蛇毒主要药理活性形式。铁仔属parvifolia的己烷、二氯甲烷及乙醇提取物均有减轻美洲矛头蝮引起的小鼠爪水肿及血管通透性,减少白细胞数目与迁移,具有潜在的抗炎活性,特别是降低了蛇毒局部损伤作用[23]。李娇等[24]发现人微血管内皮细胞(HMEC)受眼镜蛇毒因子介导的补体旁路激活产物刺激后,引起黏附分子(ICAM-1、VCAM-1、E-selectin)和炎症介质(IL-6、TNF-α)的表达上调,以及NF-κB核内转录活性的上调。不同浓度的川芎嗪对上述炎症反应相关指标的上调均有干预作用,且表现出剂量依赖性。认为川芎嗪对眼镜蛇毒因子引起的补体旁路特异激活HMEC炎症反应有明显的干预作用,其机制可能与抑制NF-κB的核内转录活性有关。
4.2 抗氧化作用黄彬等[25]观察蛇毒清胶囊对眼镜蛇咬伤合并局部组织坏死患者血浆 LPO、SOD、GSH-Px的影响及疗效,治疗7 d后,显示治疗组LPO明显低于对照组,SOD、GSH-Px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认为蛇毒清胶囊能减轻眼镜蛇咬伤引起的氧化性损伤。Gomes等[26]观察从菊科植物PlucheaindicaLess中分离得到的β-谷甾醇和豆甾醇对蝰蛇和眼镜蛇毒的中和作用,动物实验证实活性成分可以明显中和蛇毒诱导的致死,出血,去纤维蛋白原形成,水肿和PLA2活性,并拮抗毒液诱导的脂质过氧化和SOD活性的变化。
4.3 调控免疫应答Shenoy等[27]观察胡椒科植物PiperlongumL乙醇提取物(PLE)和胡椒碱对罗素蝰蛇伤小鼠的免疫应答反应的影响,ELISA和双重免疫扩散试验证实了用PLE和胡椒碱免疫的小鼠血清中存在抗毒液抗体。两种处理均能抑制毒液的致死作用。用胡椒碱处理的小鼠血清与毒液抗原之间存在明显的交叉反应(P<0.01)。认为PLE和胡椒碱对小鼠产生高度的抗体反应,可用于治疗罗素蝰蛇咬伤。可见,除抗蛇毒血清通过高特异性免疫反应对蛇毒起解毒作用之外,植物药也可以通过相似的调控免疫应答反应机制用于蛇伤的临床治疗。
4.4 抗感染作用毒蛇咬伤继发的伤口感染会使局部症状加重,是引起终生残疾或缺陷的重要原因,抗生素显示出较好的疗效,但抗生素耐药、腹泻等副作用,及特殊人群如孕妇等部分患者不适用,植物药是防治蛇伤感染的重要补充或替换药物。樟科植物AnibafragransDucke叶(AEL)和树皮(AEB)的水提物,叶乙醇水提取物(HLE)和叶水蒸馏残留物的提取物(ERHL)能抑制矛头蝮磷脂酶A 2及纤维蛋白溶解活性活性,其中HLE能明显抑制摩氏摩根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11种细菌的生长,这些微生物在毒蛇口腔,以及环境中普遍存在,提示这些提取物可辅助治疗蛇伤继发性感染[28]。
然而,植物药抗蛇伤局部效应机制往往不是孤立的,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黑麦草甲醇根提取物中分离的化合物(2-羟基-4-甲氧基苯甲酸)可能有效减轻蝰蛇毒素引起的白化雄性小鼠炎症反应,减少小鼠肉芽肿,提高SOD活性,减少自由基的含量[29]。总之,植物药通过抗炎、抗氧化、调控免疫以及抗感染等药理作用下,促进了蛇伤局部损伤修复。
5 结语
近年来,针对蛇毒毒素的病理、诊疗,以及蛇毒局部效应酶的特异性和作用方式等方面进行广泛的研究。为了改善实际治疗,提出了两种主要的替代方案:针对大多数组织损伤/免疫原性毒素的合理设计新的特异性抗体; 或寻找能够抑制这些毒素并补充血清疗法的新合成或天然化合物。从民间医学中用于治疗蛇咬伤的植物中分离天然化合物,是寻找蛇伤防治新的先导化合物的良好选择。然而,基于蛇种多样,蛇毒成分随毒蛇年龄、季节、环境及饮食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单一的化学成分很难作为毒蛇咬伤的防治。植物提取物或复方能多层次、多靶点进行特异性治疗,是目前抗蛇毒局部效应与并发症研究的主要方向,这与中药作用不谋而合。因中药成分的复杂性,中医药抗蛇毒机制尚未得到完全阐明,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医药治疗蛇伤有效性的临床观察,少有对抗蛇毒机制的深入研究,尤其对中药防治蛇伤优势即局部效应作用靶点及机制缺乏科学诠释,这极大地局限了中药治疗蛇伤的应用与推广。因此,深入开展中医药防治蛇伤,尤其在减轻蛇伤局部效应机制研究能为蛇伤的有效治疗,以及中药资源开发与利用提供实验依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