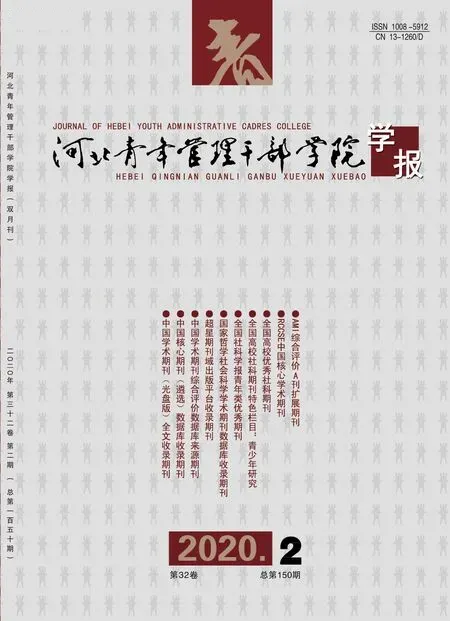《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9条适用问题分析
——从法教义学角度
王 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政法学院, 北京 102401)
与旧法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对涉外民事关系中的“人”的关怀。这不仅表现在整部法律的章节安排中①,更体现在一些冲突规则的内容里②。其中第29条就是一个典型,它鲜明地表达了立法者保护涉外扶养关系之弱势方当事人的立场。若能获司法的贯彻,该条或可成为现代法治与人本追求相得益彰的典范。可惜的是,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法官在适用该条处理涉外扶养纠纷时错误频发,以致立法的人文关怀目的屡屡落空。究其成因,司法本身的不当固难辞其咎,但与此同时立法方面的深层诱因更值得关注。须知所谓司法,本质为对法律之司执,司法效果不佳,若究其源头则不能不反观立法;反之,没有司法的实现,法律只是空洞的文字,必得司法运用之方能发挥定纷止争的实际效果,而观其效,可以为讨论立法之“好”与“坏”提供必要的现实基础。作为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法律的制定有其特殊的技术规范需要遵守,本文将结合《法律适用法》第29条的司法情况,从法教义学角度探究该条款在立法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以求抛砖引玉。
一、司法不当常见类型分析
笔者以北大法律信息网、中国裁判文书网、OpenLaw裁判文书检索网为据,检索了我国法院2011年4月1日至2019年8月1日以《法律适用法》第29条为据审理的案件,并在比较、归纳的基础上认为,目前司法中出现的常见错误有以下两类。
错误类型一:罗列无关的冲突规则。一些争议明为涉外扶养方面的纠纷,本该运用《法律适用法》第29条的规定处理相关法律冲突,但法院却在处理此类争议时,罗列该法规中各种与纠纷无关的冲突规则,并最终选择了错误的准据法。此类错误的典型例证为“韦某与卢某扶养纠纷案”③。该案原告韦某嫁与香港居民卢某为妻,生育一女卢晓欣。韦某与卢某因感情不合,经法院判决离婚,女儿归韦某扶养。后韦某又于2014年向法院请求变更扶养权,将女儿交由前夫卢某扶养。案件判决书中称“本案为涉外扶养权纠纷”④,这一“定性”显然正确。基于此认识,法官理应根据《法律适用法》第29条有关涉外扶养的法律适用规定选择准据法。然而,法院却在援引该条冲突规则的同时,出人意料地罗列了《法律适用法》第25条关于亲子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定,并紧随其后抛出结论:“卢晓欣为中国公民,现居住于中国境内,且被告的经常居住地亦在中国,故本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本案。”⑤此法律适用的结论根本没有遵循第29条的规定,自然谈不上实现其给予被扶养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目的。
错误类型二:乱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一些当事人协商处理包括分担扶养子女义务在内的离婚事项,并约定了发生纠纷时应该适用的法律。法院便因此主张应根据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处理扶养纠纷。此类型的典型案例是“蒋华与切尔西·蒋(Chelsea Jiang)、弗兰克·蒋(Frank Jiang)扶养费纠纷案”⑥。当事人切尔西·蒋与弗兰克·蒋均为未成年人,并以美国为经常居住地。二子之生父为美国公民蒋华,生母则为中国公民黄川。诉讼发生前,黄川与蒋华曾在法院的调解下签订了离婚协议,约定两子均由女方黄川扶养,蒋华须为两子支付扶养费直至分别大学毕业为止,并约定若发生纠纷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后双方因扶养费问题对簿公堂。一审法院适用中国法律作出判决。蒋华不服并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约定无效,应该适用被扶养人本国法——美国法。最终,二审法院作出了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二审判决书中虽提出适用《法律适用法》第29条,但从法律选择的过程与结果来看,判决显然没有根据该条的规定选择对被扶养人有利的法律,而是根据该法规第3条关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规定⑦,适用了蒋华与黄川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与类型二相似,既然第29条都没有得到适用的机会,自然也就无从实现其保护被扶养人的立法目的。
《法律适用法》第29条的司法适用不当并非仅限于以上两类。但此二类却是在司法实践中频频出现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给予被扶养人特殊保护的第29条立法原意也因此屡屡落空。本论姑且不论单纯的司法疏漏问题,而是着重从法教义学角度分析、审视《法律适用法》第29条的规定,以揭示上述立法目的未获司法实现之现象的深层诱因。
二、成因分析:从法教义学视角
《法律适用法》第29条为专门处理涉外扶养法律适用问题的冲突规则。该规则与关于结婚、离婚、亲子关系、监护关系的其他规则同处于第三章“婚姻家庭”;而第三章与第二章民事主体、第四章继承、第五章物权、第六章债权、第七章知识产权共同构成《法律适用法》的分则部分;该部分又与第一章总则以及第八章附则,一并组成整部法规。这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法规构成方式。既然《法律适用法》是这样一个层次分明的法律体系,那么立法者在设置第29条时当然不仅应斟酌其自身内容,还需要考虑该规则与法规中其他规则的协调问题。
(一)与分则第25条的适用范围界域不明
在《法律适用法》第三章婚姻家庭部分,包括第29条在内的所有规则都以婚姻家庭领域的各类关系的法律适用为调整对象,而同领域规则的调整范围往往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因此,第29条须配合其他规则,其他规则的制定也应该充分考虑第29条的内容,以实现既填补立法空白又避免同类规则发生管辖冲突的立法效果,否则就容易造成司法上的混乱。就目前的司法状况来看,第29条与第25条的关系不明已经造成了实务中的困难。具体而言,立法在此方面的疏漏有二。
其一,对第29条“扶养”的内涵缺乏必要的说明。所谓“扶养”,究竟是指狭义的扶养概念,也即平辈亲属之间的相互扶助、供养,还是指广义的“扶养”,也即不仅指平辈还包括不同辈分亲属之间的扶养,例如,长辈对晚辈的抚养和晚辈对长辈的赡养?如果第29条明确地在狭义意义上使用“扶养”概念,则该条与第25条就不存在适用范围上的冲突:当涉及平辈亲属之间的扶养关系时,适用第29条的规定;当涉及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或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时,就适用第25条的规定。如果第29条态度鲜明地宣示在广义上使用“扶养”概念,其与第25条之间的冲突同样也不会发生:在解决父母、子女间扶养权利义务关系时,就以第29条为法律适用的依据;相应地,第25条就限定为处理扶养关系以外的父母子女财产关系。然而,第29条偏偏未就“扶养”的内涵与外延作出任何解释,这就影响了司法者对该条与第25条关系的理解⑧。
其二,《法律适用法》第25条对“父母子女财产关系”缺少必要的解释说明。这一立法缺陷不仅影响该规则本身的正确适用,也对第29条的司法运用造成了不利影响。第25条是规制父母子女间人身、财产关系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则。父母子女之间的人身关系,自然涉及婚生子女身份的获得或认定问题,但父母子女间财产关系的具体所指却难以把握。众所周知,无论是否以父母间合法的婚姻关系作为基础,父母、子女之间的日常财产关系通常指生活中的相互扶持、面对重大疾病或意外时的经济支持或是共同享受生活的消费等。这些都属于天理人伦,一般不会对簿公堂,更不会要求法院通过判决的方式切分父母子女之间的财产。这类要求的提出一般只会出现在较为特殊的情况下,如父母对年幼的子女、成年子女对年迈的父母不愿履行扶养义务,或是父母、子女中一方先亡故需要由另一方当事人继承财产,又或是未成年子女或年迈父母名下的财产需要对方处理等。不论子女为婚生或非婚生,在上述情况下的父母子女间财产分配,第一类问题应该根据扶养,第二类问题应该根据继承,第三类问题应该根据监护规则处理,并无另行考虑父母、子女财产规则的必要。如此,第25条关于父母子女财产关系法律适用的规定究竟应该在何种情况下适用就成为有待权威机关进一步解释、说明的事项⑨。在此之前,一些相关问题——例如当父母子女之间发生扶养方面的财产纠纷时,究竟应适用第25条还是第29条等——就会令司法者感到困惑[1]。可见,第25条所谓“父母子女财产关系”的意涵不明,也会间接影响第29条等与其具有一定关联性规则的范围明确性。
正因第29条本身调整范围不明,且其与第25条的关系亦不甚明了,才会导致出现在前述错误类型一“韦某与卢某扶养纠纷案”判决中的胡乱列举冲突规则的情况。在该案中,法官在处理涉外扶养纠纷的法律适用时,将第25条与第29条之规定并举,并在事实上未遵守其中任何一条规则的情况下贸然抛出适用我国法律的结论。这一明显的司法错误说明,法官对两条规则各自的适用范围不明所以,是以囫囵过关了事。
(二)与总则第3条的关系不清
总则各条款应为整个法规的原则性规定,对分则中的规则具有指导意义。法官在适用分则中具体规则时,须考虑总则规定,不得与总则精神相违背。因此,立法者在制定一部法规的总则规定时,应注意其对分则规则的影响。在处理涉外扶养纠纷时,首当其冲需遵守的便是《法律适用法》第29条,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法规总则部分的规定,如定性、公共秩序保留、直接适用的法、时效等,这些规则都可能对第29条是否适用、如何适用以及适用的结果发生直接作用。结合司法实践情况,在此着重讨论《法律适用法》总则第3条的设置及其对法官适用第29条的影响。
《法律适用法》第3条指出,当事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简单地说,这是对涉外民事关系中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规定。经由16世纪法国学者杜穆林的发展,在选择准据法时尊重当事人意思的冲突法原则逐渐获得国际社会的肯定。如今,这个发端自合同关系的原则早已将疆域扩展至侵权、婚姻家庭、知识产权等其他领域,俨然成为各国广泛使用的极为重要的选法工具。不过,通观各国的立法模式,较常见的是将意思自治融入各分则规定中解决具体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如我国《法律适用法》第3条这般将当事人意思自治规定为整部法规之总体性原则的做法却极为少见[2]。此举缘何而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胜明撰文称,将“当事人的事尽量交给当事人办”是《法律适用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之一[3],作为此思想的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得到了立法者的充分重视。在整部法规中,具体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准据法的规则有13条之多,占全部52个条文的四分之一左右,比重远远超过国际水平。不仅如此,为了明确表达我国对该原则的看重,立法者还特地把允许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选择准据法设置为一条规则放在法规开篇,也即总则部分第3条。
这一做法的确将该原则在整部法规中的纲领性地位表现得一目了然,却也带来了法律适用上的困惑。从立法学的角度来看,但凡出现在总则中的规定,皆为对贯穿于该法规始终的原则的表述,可以指导司法者对分则条文的理解和适用。如此,在总则中规定当事人可以依法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能否理解为本法分则中规定的所有具体法律关系中法律适用问题都可以由当事人意思自治解决?以第29条为例,该条本身并没有授予当事人自行选法的权利,但扶养义务双方是不是可以根据第3条的规定,以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如明示、合意等,为扶养关系择定准据法?
学界早已不乏从此角度质疑第3条之设立意图与作用的论说[4],而本论司法情况分析中的错误类型二也印证了这一怀疑的预见性。在该类型典型案例“蒋华与切尔西·蒋(Chelsea Jiang)、弗兰克·蒋(Frank Jiang)扶养费纠纷案”中,法官虽然将争议定性为扶养费纠纷,却提出根据《法律适用法》第3条的规定适用当事人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法律。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显然有悖第29条的立法意图。事实上,该条排除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并将法律选择的权力交到了法官的手中,如此才能保证最终得到适用的法律对被扶养人真正有利。如果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法,或许可以实现意思自治,但选定的法律却未必是对被扶养人最为有利的法律。从其他分则规则的设立意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6条的规定来看,第3条仅仅是一种立法精神与宗旨的宣示,并不对分则关于法律适用的规定发生直接作用,这种立法方式造成的错觉对司法实践产生了妨碍。
三、结语
《法律适用法》第29条以保护弱者为己任。这一立法目的体现了我国国际私法对人的关怀与爱护,契合法学发展的整体趋势,具有时代先进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实现良好的立法目的,离不开对成熟立法技术的把握与运用,否则便会出现如本论第二部分列举的司法不当。而这些错误的发生,将使立法目的最终落空。要解决《法律适用法》第29条司法适用中的问题,我们不仅要对法官提出要求,更需要对规则进行一定的调整。例如,在建立和谐法律体系方面,立法者应听取专家意见,并根据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在全局观的指导下对法规体系进行有意识的整改。应认识到自身亦是实现个案公正的辅助者,故而在制定法律规则时,必须时时以条文的可操作性、协调性等司法者的现实需要为考量因素,如此才能促使纸面上的公正成为真正关系你、我、他的事实上的公正。
注 释:
① 《法律适用法》在第一章“一般规定”后紧接着设置了“民事主体”“婚姻家庭”与“继承”等与“人”密切相关的章节,而将与人的关系相对更为疏远的“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放在更为后面的章节,可见立法者在法规整体布局方面对“人”的关怀。
② 第25条对亲子关系、第30条对涉外监护、第42条对消费合同、第45条对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规定等皆为此例。
③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4〕穗云法江民初字第563号民事判决书。
④ 我国学界的通说认为,国际私法上的“扶养”概念大致包括民法意义上的“扶养”“抚养”与“赡养”,下文对此将有更为详细的说明。
⑤ 除此之外,类似判决还有“李某某(S甲)诉范某甲(N甲)、范某乙(N乙)抚养费纠纷案”“黎某某与林某某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案”“陈某某与曲某某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案”,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少民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4〕江新法民四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3〕闵少民初字第104号民事判决书等。
⑥ 本案的一审与二审判决书,分别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民初字第94号民事判决书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3〕浙杭民终字第3686号民事判决书。
⑦ 《法律适用法》第3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该条仅为关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性规定。本案即便要适用离婚协议中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也应该以《法律适用法》第26条关于协议离婚准据法的规定为依据,而不应该越过具体规则直接诉及原则性规定。
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89条对于“扶养”曾给出列举式说明。该条司法解释指出“父母子女相互间的扶养、夫妻相互之间的扶养以及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人之间的扶养”皆应依照《民法通则》第148条的规定,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如果可以根据《民通意见》第189条的司法解释理解《法律适用法》第29条的“扶养”,那么显然关系存在于上、下辈与平辈亲属之间,属于广义的扶养范畴。事实上,这也是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和实务界较为通行的理解,也是本论所持的观点。但严格来说,我们可以质疑《法律适用法》生效后《民通意见》有关司法解释是否仍然有效。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基本法律适用原则,在解决2011年后产生的涉外扶养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时自然应该以《法律适用法》第29条为据。既然《民法通则》第148条已经失效,以解释该法条为要旨的司法解释自然也应失效。在此状态下,《民法通则》第189条是否仍然可以视为理解《法律适用法》第29条之“扶养”的依据,或许就需要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⑨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专门为《法律适用法》进行了条文释义,然也未能对第25条“父母子女财产关系”的具体所指给出确实的说明,参见万鄂湘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条文理解与适用》,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