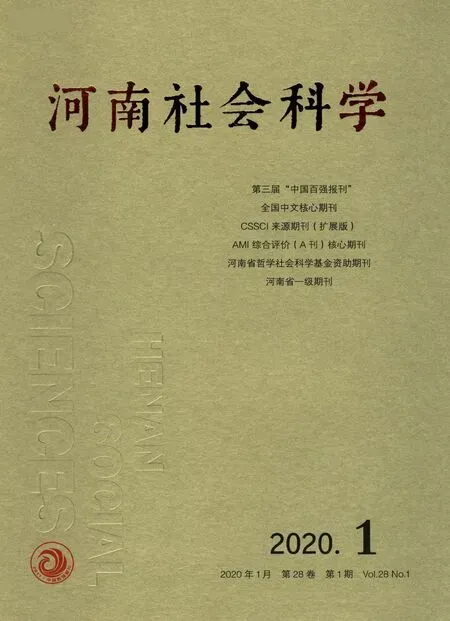从血缘到地缘:论北朝群体造像记的发展演进
——以家庭、宗族、村落和邑义等造像记为中心
李林昊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佛教大盛于北朝,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描绘了当时佛教的盛况:“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1]25从《资治通鉴》存录的文献中亦可窥其大略:“时佛教盛于洛阳,沙门之外,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为之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由是远近承风,无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万三千余寺。”[2]4594
北朝造像记是北方民众积极参与佛事活动的真实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朝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风貌,是研究北朝政治、社会、文化等的重要资料。隋末唐初高僧法琳在《辨正论》中提到,隋文帝时代“开皇之初终于仁寿之末,所度僧尼二十三万人,海内诸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许躯”[3]第52 册,509,可见隋代之前的北朝造像数量之巨。造像记大都是以个体造像或是群体造像的形式展现出来,家庭、宗族、村落和邑义等造像记皆是群体造像记的重要类型。群体造像在发展过程中,由小的空间单位向大的地域单元不断演进,在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与宗教、政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特征。
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群体造像记
根据不同群体造像记的主要形成因素,可将家庭、宗族、村落、寺庙、邑义等不同类型的造像记按照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进行分类,其中家庭、宗族造像记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发展起来的,村落、寺庙、邑义等造像记则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构建的。
家庭、宗族范围内的佛教信众和造像活动以血缘关系为依托,将血缘共同体内的各个成员联结起来,从信众个体、家庭逐步扩散到所在宗族。换言之,宗族造像记是在个体造像记和家庭造像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一)家庭造像记
在论述家庭造像记之前,需要先提及个体造像记。因为个体造像出现时间最早且数量众多,是造像活动中最基本的形式,家庭造像以及后来形成的大规模群体造像大都是以个体造像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
个体造像记往往短小简约,每篇大都只有短短的几十字,仅仅交代造像者、造像对象、造像题材以及进行简单的发愿,不像群体造像记那样长篇大论,对于佛法精妙的赞美与阐释亦多省略。如北魏太和四年(480)《赵明造像记》:
太和四年四月二十日,下博人赵明为亡儿越宝造多宝佛。愿亡儿上生天上,常与佛会。[4]423
这是信众赵明为亡子发愿祈福而作,反映了个体造像记的普遍特征:造像主多为自己或亲人造像,其中为亡故亲人祈福、为现存眷属发愿更是占了半数以上,具有很强的现实黏合度。
与个体造像相比,家庭造像的参与成员更多,造像碑铭篇幅也较长,这些参加者皆为血脉至亲,多是父子两代人共同造像,有的囊括祖孙三代甚至四代人。家庭造像记往往反映了一个家庭整体的宗教信仰和精神风貌。如《刘思祖造像记》:
大齐天保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高城县人刘思祖敬造玉石像一躯。上为国王帝主,下为七世父母现在。刘思祖妻严勾,息男景晕、伯安、伯双、伯丑,愿生生世世,恒值佛。
清信仕女刘男生。孙子刘来宝。[5]173
该则造像记中的参与成员包括祖孙三代人,不单有男性成员,也有女性信众,全家人一起供养佛像。需要说明的是,宗族内部等级森严,故宗族造像的发起者多是宗族内地位高、有威望的男性成员,但家庭造像在此方面并没有严格的限制,北朝时期女性的家庭地位比较高,可以自由组织开展造像活动。如北齐武平三年(572)的《王马居眷属等造像记》有载:
清信佛弟子故人王马居眷属等,敬造观世音菩萨一躯,上为皇帝陛下,七世父母。一切有形,咸同斯福。
像主王马居,夫曹台,息法度,□妻李伏女,□妻麝苑端,□息通达,□子敕奴,□世通妻郭绫,通息子建,女阿瑞,女迎弟,女明月,□女阿肆。[5]279
由造像题名可以看出女性信众王马居是本次造像活动的发起人,其夫曹台只是普通的参与者,这说明家庭内部女性并没有受到太多限制,在宗教活动中可以自由参与,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赵晖等造像记》《侯显妻造像记》《田僧敬造像记》《滑黑奴造像记》等对此均有明确的反映。该类型造像记之所以数量众多,大抵是家庭成员之间既同归于佛教信仰的统摄之下,又通过血缘关系联结得更为紧密,这就为佛事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便捷条件。
(二)宗族造像记
宗族造像是在血缘关系的维系下,个体造像和家庭造像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宗族造像的参与者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在血缘构建的家族网络下组成一个富有凝聚力的佛教信众集体,共襄佛事之举。如《陈氏宗族造像记》:
夫真容虚寂,妙体精绝。湛□恒有,渊廓玄深。……自非建□□岸甯申余等借承汉高左右大丞相户酉侯太□□平晋冲关□□一军□□□长左冯翊太守□六世孙合宗等,信心冲廓,并同玄风,慧机俱发。遂名山采石,远访良规,造四面石像一躯。……
开□光明主威□将军陈映族。加叶主陈思和。开光明主颍川太守陈伯 。……邑子步兵参军陈僧略。邑子陈始和。邑子陈子云。邑子陈冷俊。[4]554-556
遍览整篇造像题名,参与成员皆为陈氏族人,且人数多达几百人。从参与者的身份来看,既有上层官员,如陈伯 官至颍川太守;也有中层官吏,如陈卷生为郡主簿,陈萌□为县令;还有大量的平民族人,像陈始和、陈子云、陈延义等。从上层官员到下层平民,宗族造像通过血缘关系这一纽带,打破阶级、年龄、地位的界限,将全体族人团结为一个强有力的整体,彰显出血缘力量的强大。陈氏族人全体参与,说明佛事活动已经成为宗族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宗族造像记不仅篇幅宏大,还出现了对仗工整、文采华丽的四六句,发愿文中对于佛法的领悟亦很精深,《李显族造像碑记》就是其中的代表:
大魏兴和四年岁次降娄十月甲午朔八日辛丑,李氏合邑造□像碑颂文。
夫旨理虚冲,妙绝于言像之外;凝湛淡泊,超出于燕形之境。所以现应金容,诠言布教者,实由见闻之徒,三千同感。是以大圣降鉴,慈情曲接,影赴麈羁,悲拔昏识,故能托迹净土,抢现元吉,开三为级小之心,演一为接大之则。虚心冥照,理无不统。深是如来处有不有,居无不无者矣。但以众生福尽,不善诸业,百八云张,邪风竞扇,致令灵曜潜晖,迁感异域。自圣去遥延,世华道丧。……[4]586
这篇造像记长达两千字,单是祈愿文就有近七百字,多用四六句对仗,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李氏宗族中有大量的族人出仕,担任的职务种类繁多,文职有太守、中散大夫、太尉府参军、郎中令、县令等,武职有荡寇将军、襄威将军、殿中将军等。此外,还有不少族人是庶民百姓。仔细对照之后发现,该家族文官的数量要远多于武将,甚至有不少族人官位显要,其中官至太守的族人就多达十几人,中下层官吏更是不胜枚举。根据李氏族人更多的是以文官出仕,可以推测该家族当以耕读传家,整个宗族内有着良好的文化氛围,故而造像记中的祈愿文多骈辞俪句也就不足为怪了,同时也说明南朝的骈俪之风亦影响到了北朝文官宗族的造像记撰写领域。而参与成员皆为平民的宗族造像记,因为整体的文化程度较低,祈愿文一般缺乏文采,也不追求对偶,甚至对于佛法的领悟都较少阐述,往往一笔带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宗族造像记中祈愿文内容的书写与宗族整体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
二、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群体造像记
前文提到,村落、寺庙、邑义等造像记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构建的。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类别是按照其主要影响因子划分的,并不意味着这些不同类型的造像记只有单一的影响因素,如宗族、村落和邑义造像既包含了血缘关系又囊括了地缘关系,但宗族造像受血缘关系影响较大,地缘因素只能居于次要地位;而以村落为基础的聚落组织和以邑义为代表的特殊组织形式,因为其部分参与成员不囿于某个村落之内而出现了跨地域的性质,尤其是不同村落的联合造像与跨地域邑义的形成更是直接受制于地缘关系,故本文将村落造像记和邑义造像记归入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群体造像记之中进行讨论。
(一)村落造像记
村落造像与宗族造像有一定的共同点,它在宗族造像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地域性的因素。宗族具有聚居性特征,而一个村落往往包括一个或数个不同姓氏的宗族,因此村落是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叠加之后产生的聚合体。如果说平民信众参加的宗族造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那么其参与的村落造像则是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地缘关系是其形成的主导因素。村落造像规模大,人数众多,且造像记篇幅较长,一般都有几百字,能够将乡村的生活图景、人员构成细致地描摹出来,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北朝的乡里社会。如刻于北魏景明四年(503)的《刘雄头等四百人造像记》:
大魏国景明四年太岁在未三月癸丑朔廿一日,幽州范阳郡涿人刘雄头、高伏德、高道龙合四百人为皇帝造释迦牟尼像一躯。
比丘法崇,比丘道□,智深,道欢……刘□惠隆,高定和,刘恶□,刘造扶,刘灵□。(下缺)高园□,刘天赐,刘□生,□□刘□。(上缺)刘云生,高道显,刘龟,刘伏□□。比丘尼法,尼法珎,尼法幽□。[4]446-447
可将产生于同时期、同地域的《高伏德等造像记》与《刘雄头等四百人造像记》比照参看:
大魏国景明四年,太岁在癸未,四月癸未朔二日,幽州范阳郡涿县当陌村高伏德,像主维那刘雄合三百人为皇帝陛下□□造石像一躯(下缺)记。
高非,高副周,高无讳,刘永得,高卿世,高惠顽,刘黑堆……高宗敬,高 ,高勉兴,刘僧达,高保盖,高法显,刘伏生,李午生,刘原始。……
比丘昙龟,比丘道能,比丘昙绍,比丘智深。[4]447-448
上述两则造像记是关于北魏时期幽州范阳郡涿县当陌村村民共同从事佛事活动的记载,参与者主要为当陌村的高姓与刘姓族人,也有少数其他姓氏的成员和数名比丘、比丘尼参加。两次造像活动实质上当属聚居于同一自然村落内的高刘两姓之合作造像。《刘雄头等四百人造像记》造于景明四年三月,发起人为刘雄头;《高伏德等造像记》的镌刻时间是四月,组织者是高伏德。从其造像题名来看,高伏德、刘雄头、高树、高道德、智深等人在这两次造像活动中都有参与,并可根据题名看出当陌村的人员与姓氏构成:以高、刘两姓族人为主,另有公孙姓、张姓、史姓族人零星分布。《刘雄头等四百人造像记》载录,当陌村有四百余人参加了此次造像活动,一个拥有四百口人以上的村落在人口总数约为三千万的北魏(神龟年间)也算得上较大的自然聚落了。因为共处于同一个自然聚落的民众拥有共同的活动范围,他们或因血缘关系,或因地缘关系,或因村落的共同事务,彼此碰面和接触的机会更多,这就为民众之间的交往互动提供了便利。随着僧尼的宣化与佛教信仰渗透到村落之中,这一特定空间内的信众在宗教信仰的统摄下聚集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血缘观念,不再仅仅以家庭、宗族为单位开展佛事活动,而是通过村落这一更大的空间单元组织信众信佛、奉佛。同时,佛事活动也由单一走向多元,村落内的信众不再仅仅囿于造像之事,讲经、修斋、法会等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一个囊括数个姓氏居民共同生活的村落,宗教活动正是将不同姓氏的族群凝聚在一起的重要因素。
(二)寺庙造像记
寺庙是僧尼和信众举行佛事活动的中心场所,按照佛教礼佛的观念,寺庙中大量的佛像提供了开展仪式和法会的“道场”,为佛事活动的举行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大大方便了僧尼和信众对于佛像的礼拜供养。东魏天平四年(537)的《永宁寺比丘□诸法义等造像记》是以寺庙为依托进行造像的典型:
托经象以□晖范,古今始终共轨。青州永宁寺比丘□诸法义等造释迦牟尼石像一躯。上□帝主,父母师僧,无边众生,亡过现存咸同斯。……比丘昙润。比丘道暹。比丘道善。比丘道双。比丘道稠。清信士□道果。王宝。……比丘尼法光供养时。比丘尼法陵供养时。比丘尼法晖供养时。姜明度,姜成银。郑□王姜□。张鸯,比丘尼昙□。傅敬姜。周男□侍佛时。[4]565
根据造像记题名和“永宁寺比丘□□诸法义等造释迦牟尼石像一躯”,可以看出僧尼和男女信众在永宁寺形成了专门进行佛教活动的佛社,“法义”就是佛社的几种称呼之一。该则造像记实质上是寺庙造像记与邑义造像记的结合,佛教邑义是在永宁寺这一特定空间内形成的。既然是以寺庙为基础开展的佛社造像活动,其组织者和领导者自然是僧尼,但普通信众对于造像亦有经济和劳力上的支持。北魏中晚期以后,庶人及团体造像尤多。据佐藤智水先生考证,东西魏以后,团体中的邑义造像明显增加。由邑义建造的石像、碑像多见于古寺院(如1953 年河北省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出土自北魏到唐朝石像二千尊以上)。与放在家庭佛坛上供奉的金铜像不同,邑义像多安置在寺院。由此可以推测,寺院是地域社会的共同场所[6]70。寺庙造像记反映的是僧尼以寺庙为中心开展的宗教活动,通过僧尼自身和所在寺庙向信众直接施加影响。而以寺庙为中心形成的寺庙邑义,在组织形式和管理结构上更是直接借鉴了寺院的管理形式,如“维那”“都维那”“典坐”等称呼就是源于僧官制度中某些僧尼首领、主事的称号。相比于一般的佛社邑义,寺庙及以寺庙为中心形成的邑义组织,在结构上更加严密,活动类型更加多样,造像记中对于精妙佛法的阐释也更有深度。寺庙造像的发起者主要是僧尼,但也有组织者为信众的情况,如《刘道景造像记》:
北徐州兴福寺居士刘道景邑义等大像之碑。
居士刘道景邑义等今□超海踵像法以恒安……凝神寂寞,晓闻有而难名,知虚无而特妙。□邑义等(下缺)永夜,止火救危,逗川养命,伏外道于四居,降天魔于上界。□眸(下缺)磐资捨著,敬造珍国二丈八大像一躯,并建伽蓝之所,上为皇帝(下缺)决水。不死之药,天下共分;长生之府,门门自至。[5]305-306
本次造像活动是由兴福寺居士刘道景发起的,既属于邑义造像的性质,又带有寺庙造像的色彩。刘道景作为兴福寺的佛教信众,其发起邑义、组织佛事活动当离不开兴福寺及寺内僧众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讲,邑义造像是寺庙造像的拓展和延伸,是僧尼、信众团体在合作造像方面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新的组织形式。
(三)邑义造像记
北朝时期产生了专门进行佛事活动的邑义组织,它的出现意味着拥有共同信仰的广大信众群体可以较为自由地结成佛社,一起组织、参与佛事活动。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社,称为邑、邑义的最多,法义次之。这里的“邑”字,不是地域概念,而是指某一地域内信奉佛教的人结成的宗教团体。郝春文先生认为,“这种由信仰佛教的人组成的邑,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结义性质,‘义’应该就是结义的意思”[7]90-91。日本学者山崎宏指出:“法义是以同样信仰佛教的道义而组合之意,如同义兄系血缘以外结合而成之兄的意思,是以佛法集合的成员。”[8]768
邑义造像种类繁多,规模大小不一,少则有信众几人或十几人,如《赵阿欢造像记》《贾致和等十六人造像记》《邑主孙念堂造像记》;多则有数千参与者,如《法雅与宗那邑一千人造塔碑》《比丘法悦等一千人造像记》《七帝寺造像记》。需要说明的是,个体造像在公元3世纪就已出现,现存最早的是西晋太康三年(282)的《张伯通造像记》。到了4 世纪左右,就已经有大量的个体造像、家庭造像存在了,而邑义造像直到5世纪才出现,其“喷发期”则是在6 世纪前后,两者的“发展成熟期”相距百余年。从个体造像、家庭造像到邑义造像,这是一个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是以血缘关系为主要影响因素的造像活动转向以地缘关系为主导的重要时期。《灵山塔下铭》和《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记》是早期邑义造像的代表:
维大魏太和元年岁次丁巳十二月朔八日壬戌,刘虎子、诸葛洪、方山二百人等敬造灵塔,愿六通三达,世荣资福,合家眷属,慧悟法界,永离苦海,光祚群生,咸同斯庆。
邑主梁英才,维那牟文雍,塔主华智。[4]422
——《灵山塔下铭》
太和七年岁在癸亥八月卅日,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自惟往因不积,生在末代,甘寝昏境,靡由自觉。……弟子等得蒙法润,信心开敷,意欲仰诩洪泽,莫能从□,是以共相劝合,为国兴福,敬造石□□像九十五躯……上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子德合乾坤,威逾转轮,神披四天,国祚永康……又愿同邑诸人,从今以往,道心日隆,成行修洁,明鉴□相,晖扬慧日。[4]423-424
——《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记》
上述两则造像记分别刻于北魏太和元年(477)和太和七年(483)。造像记的文本内容反映的佛事活动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造像、立碑、设斋,而且还有建寺、造塔、法会、讲经等活动。《灵山塔下铭》反映的是二百人的邑义团体建塔题记之事,碑铭提到的邑主是邑义团体的首领,而塔主是建塔的主要出资人。建塔和造像一样都属于积功德之事,佛教对于造塔亦是采取鼓励的态度,《佛说造塔功德经》有言:
欲请如来造塔之法,及塔所生功德之量。唯愿世尊为彼解说,利益一切无量众生。尔时,世尊告观世音菩萨言:“善男子,若此现在诸天众等,及未来世一切众生,随所在方未有塔处,能于其中建立之者,其状高妙出过三界……其人功德如彼梵天,命终之后生于梵世……善男子,如我所说如是之事,是彼塔量功德因缘,汝诸天等应当修学。”[9]第16册,801
由《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记》可知,该邑义团体共建造佛石像95 躯,对于一个仅有54 人的佛社组织而言,其造像数量可谓庞大,经济上也必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信士女是俗家佛教信众的称号,该邑义的参与成员应皆为女性在家信众。
佛社邑义的组织结构不似亲朋故旧仅仅为奉佛而临时开展的合作造像那般松散,反而等级森严、秩序井然。如果说早期的个体造像是自发的,是俗众出于对佛教的虔诚,从为家人、为自己祈福的角度发起的;那么邑义造像就是自觉的,是北朝时期佛教高度发达的产物,是在佛教信仰广泛渗透到北朝民众的日常生活之后,信众有意识结成团体的结果。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作用下,拥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信众有意识地结成群体,催生了佛社这一特定组织。佛社中还出现了许多特有的、与佛事活动相关的职务和称号,主要有邑主、像主、邑师、维那、斋主、邑子等,这些佛社成员在宗教活动中各司其职,分工也日益明确,并逐步走向精细化。
从现存邑义造像记来看,在邑义造像出现的早期,其多以寺庙为中心开展佛事活动,从该角度讲,邑义造像是寺庙造像的另一种呈现形式。大部分邑义组织的邑师、维那由比丘或比丘尼担任,这些僧尼邑师既是邑义的精神领袖,又担负着教化的功能;僧尼维那是邑义的管理者,对于佛事活动的开展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们又都属于寺院的派出人员,寺庙可以通过邑师、维那控制邑义来达到指导、组织、管理信众的目的。待邑义逐渐发展成熟后,其对于寺庙的依附性减弱,信众自主性增强,邑义中的邑师、维那等职务也不再由僧尼垄断,普通信众亦可担任。同时地域因素也逐渐成为邑义发展、壮大的主导因素,宗族、村落、县邑内的佛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三、从血缘到地缘:不同群体造像记的“复合构造”与邑义组织对于北朝社会的多重作用
(一)不同群体造像记的“复合构造”
笔者在研究宗族、村落、寺庙与邑义等造像记时,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宗族、村落、寺庙等不同的造像类型大都或多或少地与邑义造像结合而得以呈现,笔者将此类造像形式称为“复合邑义造像”,它们既具备原有造像类型的性质,又带有邑义造像的色彩。如《李显族造像碑记》就是宗族邑义的典型:“大魏兴和四年岁次降娄十月甲午朔八日辛丑,李氏合邑造□像碑颂文。”至于村落邑义,比较著名的有《高岭诸村邑仪道俗造像记》:“唯大魏武定七年,岁在己巳四月丙戌朔八日癸巳,肆州永安郡定襄县高岭以东诸村邑仪道俗等敬白十方诸佛。”还有北齐河清二年(563)的《阿鹿交村七十人等造像记》:“阿鹿交村七十人等敢天慈降尊……人等深识非常,敬造石室一躯,纵旷东西南北,上下五尺。”通过对北朝佛教造像记的研究梳理,笔者以为,北朝佛教造像记的发展大致遵循这样一个脉络:从个体、家庭造像到宗族、村落造像,再到与宗族、村落相结合的邑义造像,造像的类型经历了从小的空间单位向大的地域单元的演进;影响造像类型发展的主要因素也经历了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再到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共同作用的转变,即从单一因素的影响发展到多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
以往学者在论及邑义造像时,大都认为其主要受地域因素的影响,血缘因素却较少提及。在佛社组织中,血缘关系虽不似地缘关系那样重要,其作用却也不容忽视。如村落邑义造像几乎汇集了整个聚落内的成员,地域成为其形成的主导因素不言自明,而血缘关系影响下的宗族造像在与邑义造像结合时,宗族的血缘关系也在向邑义中不断渗透,宗族邑义内部形成了特定的血缘网络,将邑义成员之间联结得更为紧密。需要说明的是,宗族也生活在村落这一特定区域空间,必然被烙上地域因素的印记;一个村落往往由一个或多个姓氏的宗族组成,血缘的联结在其中亦起到重要作用。邑义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血缘关系与地缘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绝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要之,在研究宗族邑义、村落邑义的复合构造时,要重视这些处于特定空间内的血缘群体、地缘组织是相互联系的。在个体造像、家庭造像发展的早期,是以血缘为纽带将信众聚集起来的;在宗族造像、村落造像发展的阶段,地缘因素成为串联信众的主要因素;到了宗族邑义与村落邑义快速发展的时期,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诸多因素共同催生了复合邑义造像这一高级的合作形式。与此同时,佛教造像的类型也从小的空间单位向大的空间单元不断发展演进。
(二)复合邑义产生的原因
宗族邑义、村落邑义等复合邑义的出现,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造像活动自身的发展来看,与宗族、村落等相结合的邑义造像是合作造像的高级形式,是造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觉结果。从复合邑义造像的内部构成来看,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依托的宗族邑义、村落邑义更容易将信众聚集在一起,处于同一聚落的人群和有血缘关系的群体联系得更为紧密,也就拥有了构成邑义组织的人员基础;邑义成员共同出资、出力进行造像,佛社活动的开展也就有了经济基础。
论及佛教造像的问题,就不得不考虑信众尤其是平民信众的经济条件。北魏孝文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均田制和租调制,其本质是以一夫一妇为单位的家庭生产模式,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其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皆因袭了此种经济生产模式。佛像的铸造、题记的刻写都是要消耗钱财的,而且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可从造像记的载录窥其大略。《宋景妃造像记》有“今且自割钗带之金,仰为亡考妣敬造释迦佛像一躯”之语;《王令猥等造像记》载“以减割妻子衣食之分,为亡息延庆、延明、父母等敬造石铭一区”;《赵阿欢卅五人造像记》云“故各竭家财,造弥勒像一躯”;《邑义一百六十人等造像记》言“有诸邑义一百六十人等,减割资财,造石像一躯”。此类记载比比皆是,造像一躯就需要信众节衣缩食,甚至集全家之财、倾邑义全体成员之力,因此,对于社会上最广大的平民信众来说,造像对他们造成的经济负担是相当沉重的。
《张龙伯兄弟造像记》载:“亡妣康存之日,有牛一头,愿造像,今得成就。”[5]155铁犁牛耕在古代是重要的农业生产方式,官府明确规定民间不得私自杀牛,表明牛的经济价值和生产价值是非常高的,而该则记铭中张龙伯兄弟愿以牛换来钱财以造像,反映出造像有着高昂的成本。
对于个体造像而言,信众单独造像时的费用需要其独自背负。即使是家庭造像,因为参与人数少,开展佛事活动时亦需要承担较大的经济压力。前文提到的《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记》,记录了一个五十四人的邑义信众团体铸造了九十五尊佛像,如果由个人或普通的平民家庭来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团体造像中,造像费用由参与成员共同承担,参加的人越多,个人分摊的钱财就越少,这就大大减轻了信众的经济压力。故而邑义组织积极吸纳信众进入佛社,有的佛社成员多达几百人甚至上千人也就不足为奇了。要之,邑义造像不但能够满足信众对于以造像为核心的佛事活动的需求,亦能通过共同出资的方式减轻个人乃至家庭的经济压力,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邑义、村落邑义,作为合作造像的高级形式,便在此种状况下应运而生。
寺院及僧侣有意识地发展、组织邑义,与封建政权对于邑义的支持、放任态度,促进了邑义组织的发展壮大。佛社邑义是寺庙向世俗社会的拓展和延伸,邑义造像当是从寺庙造像中分离、演变后的新形式。郝春文先生认为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社实际上是佛教寺院的外围组织,佛教寺院与僧人往往通过控制与利用佛社达到控制居民的目的,佛社成员则是佛教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基础[7]98。在邑义出现的早期,邑师大都由比丘或比丘尼担任,他们属于寺院的派出人员,在作为邑义精神领袖的同时,又肩负着寺院赋予的教化信众的重任。邑师通过讲经译经、举办斋会、组织信徒造像等活动,扩大佛教的传播范围与影响力,将俗家信众统摄于佛教信仰之下。寺院、僧尼在获得信众经济布施的同时,又能让信众为自己服劳役。《开化寺邑义三百人造像记》《道充等一百人造像记》《比丘道璸造像记》等记载的邑义团体都是以寺庙为中心建立起来的。
封建统治者重视佛教改造民俗的作用,是故对于佛教的发展采取放任乃至支持的态度。《魏书·释老志》有载:“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10]3292造像记中有大量的祈愿文是为皇帝和国家发愿,直接以皇帝为造像对象的碑铭亦不在少数,这无疑迎合了统治者的心理期待。如《刘雄头等四百人造像记》载“幽州范阳郡涿人刘雄头、高伏德、高道龙合四百人为皇帝造释迦牟尼像一躯”;《雷明香造像记》有言“愿皇帝延祚无穷,下及七世师僧父母、因缘眷属,法界众生,咸同斯庆,等成正觉”;《张祖造像记》云“仰为皇帝陛下,国祚永隆,人同因果,弥勒三会,愿登初首”等。无论是官员贵族,抑或是僧尼、百姓,他们在造像记中大都将皇帝、国家作为造像和发愿的对象,这于无形中增强了民众的国家观念和对最高统治者的认同感,有利于封建国家统治的维系。
(三)邑义组织对于北朝社会的多重作用
北朝时期,佛社的兴起、发展既是佛教高度发展的表现,又是佛教中国化后的产物,亦是统治阶级与广大民众接受佛教的结果。封建政权之所以对于邑义的发展持放任、支持的态度,在于信众造像记中的祈愿迎合封建统治的需要,对于增强国家的认同感、提高皇帝权威有重要作用。同时邑义组织又促进了国家对于基层社会的整合与控制。
信众通过对共同信仰对象的崇奉,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缔结神缘纽带,促进了群体内部的团结。在参与邑义造像的过程中,地方官府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渗入村落,而村落成员亦通过造像这种方式,表达对国家权力的顺服与认同[11]89。《高岭诸村邑仪道俗造像记》对于世俗政权通过邑义整合、控制村落和信众有鲜明的体现,记铭如下:
唯大魏武定七年,岁在己巳四月丙戌朔八日癸巳,肆州永安郡定襄县高岭以东诸村邑仪道俗等敬白十方诸佛……先有愿共相要约,建立法仪造像一躯。平治道路,刊石立碑,以□之功,上为皇帝陛下,渤海大王,延祚无穷。三宝永隆,累级师僧,□世父母,现存眷属,复愿生生之处,遭贤遇圣,值佛闻法,常修善业,□至菩提,誓不退转。愿法界含生,同获此愿,一时成道。 .
州沙门都僧观。梁寺昙高供养。比丘法智,邑子□。比丘昙遥。比丘道略。……
广武将军邢阿平。广武将军李洪宾。……勇士都将镡伏安。王阿宾,马延观。贾社仁,呼延清郎。[4]626-627
一般的村落邑义是以一个村落为主要的空间单位而形成的佛社组织,但本则记铭反映的不是单个村落组织的邑义造像,而是定襄县高岭以东的多个村落居民组成的邑义,这就打破了原本相互隔离的地域单元,从一个村落扩展到周围的聚落,带有强烈的跨地域色彩。《高岭诸村邑仪道俗造像记》中“先有愿共相要约,建立法仪造像一躯”,表明了邑义成员之间对于宗教活动、邑义内部的规则有约定,郝春文先生认为这是类似后世社条一类的规定[7]95。《程宁远造像记》有“遂相约劝率,敦崇邑义”之语;《钳耳世标造像记》云“志标正契,共相将劝,树像一躯”;《普屯康等造像记》载“携接身,敦崇义契,复敬造碑像四佛”。“约”“契”等字眼多次出现,说明邑义团体带有一定的契约性质,佛社组织内部呈现出高度的严密性。
“平治道路,刊石立碑”表明邑义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改善民生的作用。《张操造像记》载“采石冥山,匠尽奇思……置善会寺庭间者”。《李显族造像碑记》云“于是敦契齐心,同发洪愿,即于村中造寺一区。僧房四周,讲堂已就,建塔凌云,灵图岳峻”。邑义组织信众开展的修路、建寺、造塔等活动,都与民生息息相关。平治道路既有利于加强不同地域之间的联系,又使得国家政令的下发更为快捷,便于官府对于基层社会组织的管理。建寺造塔满足了俗众信佛、奉佛的需求,又达到了世俗政权通过僧官制度控制民众精神信仰的目的。有的佛社邑义中出现了“斋主”“八关斋主”等称号,据刘淑芬先生考证,“斋主”是指供参加斋会者饮食的施主,他们可能同时也须负责在斋会后给予僧侣保施……斋会原来系指供养僧侣饮食之意,后来有时也包括对一般俗人饮食的供养[12]530。要之,邑义组织在增加民众福祉的同时又有利于维系社会的稳定,对于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有重要作用。
北周天和五年(570)的《普屯康等造像记》也反映了封建政权以佛驭民的手段:
周国天和五年岁庚寅正月乙酉三日丁亥,新丰令普屯康……即告都督孙详率乡人共崇胜福,聘请邑师僧震三人以别菅会东西六千他步,南北半旬,泛径屯郡,远近云驰,竞忻挹悦,率割珍贿,修庄严克佛像……豪杰延□三百四十他人,携接□身,敦崇义契,复敬造碑像四佛,敕化四方……伏惟皇帝国祚延康,民丰万世……邑师比丘法详,邑主中坚将军槃禾郡守张神覆,邑主征东将军右紫光禄都督张贤。……邑子赵沙陁,邑子张鲁,邑子赵和。[5]88-90
该邑义的参与成员有官员,有僧侣,也有庶民。官员普屯康既是邑义的发起者,也是邑义的管理者;比丘僧震、法详作为邑师,则是该邑义的指导者;平民信众大都只是普通的邑义成员。造像记中的题名往往按照由尊到卑的顺序依次镌写,官员和僧侣的姓名刻在前面,平民的名字写在后面,反映了森严的等级关系。
前文《高岭诸村邑仪道俗造像记》提到的造像者题名中,有“州沙门都僧观”“广武将军邢阿平”“广武将军李洪宾”名列其间,表明官员、僧人和平民共同参加了邑义造像。《普屯康等造像记》与《高岭诸村邑仪道俗造像记》实质上都属于官、僧、民三大群体合作的邑义造像,他们都是邑义组织的重要成员,但身份、地位却大不相同。官、僧是统治阶级,平民信众则处于被统治地位。州沙门都是北朝僧官制度中州郡一级的官职,负责其所在州郡的僧尼、寺院及其所辖庄园、依附户的管理,是封建国家派驻在地方的最高宗教领袖。由该碑文可知,僧官在不同村落之间的联合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僧官不仅仅能管控其所辖区域的僧尼,又能通过宗教信仰影响到广大佛教信众。而僧官的权力是世俗皇权赋予的,其实质是在为国家政权服务,世俗官员与僧官能够较为广泛地参与邑义造像,表明世俗权力已经渗透到民众生活和信仰的方方面面。
在佛教风靡的北朝,封建国家通过僧官体系加强了对于寺院、僧侣的管理,而僧侣又通过游方宣化、佛社邑义、造像活动等对信众施加影响,参与邑义造像的官员、僧尼不仅仅是佛教虔诚的信仰者,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封建国家意识形态的执行者。僧侣在为国家和最高统治者披上神秘的宗教外衣的同时,封建政权的思想观念也通过僧侣这一中介渗透到民众的精神世界。以官员为代表的世俗权力通过宗教来加强对于民众的精神控制,与封建生产关系对于民众的人身控制相互补充。
四、结论
系统研究北朝造像记后发现,造像形式的发展经历了从个体、家庭造像,到宗族、村落、寺庙造像,再到宗族邑义、村落邑义造像,其规模和内部结构是从小的活动单位向大的活动单元不断演进的;造像的维系也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向地缘关系为主要影响因素过渡,最终在血缘、地缘的多重作用下产生复合邑义结构。复合邑义是合作造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级形式,生活在同一聚落内的信众构成了佛社的人员基础,信众共同出资减轻了经济负担,寺院的有意识的发展和封建国家的支持,促进了复合邑义的发展壮大。
邑义的发展对于北朝社会有着多元影响,尤其体现在世俗政权对于基层社会组织的控制与整合,以及增加民众福祉等方面。邑义实现了血缘与地域的共通性,宗族组织和邑义组织的严密性相得益彰,村落则通过自身的地缘优势将不同姓氏的族群连接起来。宗族、村落通过与邑义组织的结合,使得处在同一特定空间内的人群在生产、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联系更为紧密,国家政权通过对于佛教、僧官与邑义首领的管控来达到控制民众精神的目的,邑义造像在一定意义上也带有国家意志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