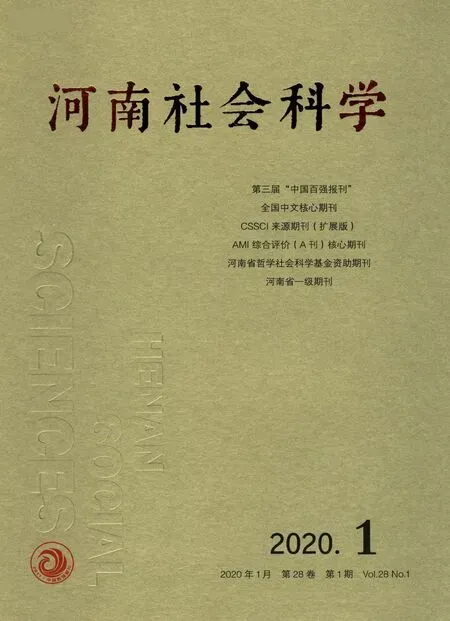比较视域中的马来西亚政党体制转型:执政惰性的理论视角
陈家喜,滕俊飞
(深圳大学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广东 深圳 518061)
为什么看似强大的一党主导体制,最终走向了终结?在马来西亚第14届大选前夕,数百万的海外马来西亚人回国参加投票,造成前往吉隆坡的机场和高速公路严重拥堵,也造就了创纪录的82.32%的高投票率①;马来西亚的年轻人把参与Facebook 和WhatsApp上“拯救我的国家”“拯救马来西亚”等线上讨论作为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抨击政府推行商品和服务税以及取消生活补贴所造成的生活艰难;甚至连担任国民阵线领袖22 年之久的马哈蒂尔也另立政党,与执政党进行公开政治对决。反观执政的巫统(UMNO)及其政治联盟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面对即将来临的政治海啸仍然沉浸在“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之中,试图通过老办法应对新危机,如向公务员、出租车司机大派3000 亿令吉的现金来收买选票,通过主导司法机关和官方媒体掩盖政治领导人的腐败丑闻,出台更严格的法律禁止网络上的政治讨论,重新划分选区以分解反对党的支持力量,等等②。选举结果最终给了巫统及其政治联盟国民阵线一个沉痛的教训:巫统所主导的国民阵线仅获得222个国会议席中的79席,被以马哈蒂尔和安瓦尔领导的“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打败,最终失去了61年的执政地位。
马来西亚曾经是一党主导体制的典型案例。以马来人为主体的巫统,通过联合马华公会、国大党等其他政党组成政治联盟——国民阵线,从1957年至2018年长期执掌马来西亚政权,形成一党主导体制。国民阵线的各个党派分别联系各个族群,巫统执政即是通过主导国民阵线、国民阵线主导国家政权这一方式加以实现的。马来西亚第14 次大选结束之后,相关研究发现,至少有三个因素是导致巫统及国民阵线丢失政权的原因:一是纳吉布的腐败及执政失误。纳吉布任期内政策失误造成生活成本飙升,商品和服务税以及牵涉“一马发展公司”(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1MDB)腐败,直接拖累了执政党巫统在大选中的表现。特别是马来人投票反对纳吉布,转而支持了反对党③。二是马哈蒂尔与纳吉布决裂并加入反对党阵营,给巫统以致命一击。可靠的个性是推动一党主导体制转变的关键因素,而不仅仅是民众对政权的不满④。由于马哈蒂尔长期的领导经验和无人企及的政治威望,他的加入直接提升了反对派的信誉,并给巫统造成了致命性的伤害。三是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及其在马来西亚政治选举中的应用,让反对党找到了数字时代政治动员的新工具,特别是对中产阶级、城市居民和年轻选民尤其如此⑤。
如果从单一选举事件来看,上述解释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从比较政党研究的视角来看,过分强调个人比如马哈蒂尔和纳吉布在政党转型中的作用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巫统一党执政优势的持续衰落可以追溯至2008年的第12届大选。本文通过纵向的历史回溯以及结构主义的分析视角,发现长期执政环境下生成的执政惰性,包括政策调适能力、自我净化能力以及精英整合能力的缺失,是导致长期执政的巫统最终丢失政权的决定性因素。本文也同时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开展以及所取得的执政党建设成绩,从而从另外一个层面印证在一党执政条件下,增强忧患意识,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克服执政惰性,加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一、执政惰性:一党主导体制终结的新解释
作为政党体制的一种典型模式,一党体制具有保持体制稳定的天然优势,它通过整合党内派系、构建法团主义或者庇护体系,包容多元广泛的社会利益;注重意识形态的感召性,适时提出符合民众诉求的纲领;利用公共资源形成选举优势等。亨廷顿将一党体制看作威权政体中的“唯一现代模式”,它相对于个人政体或者军事政体而言稳定性更强,也更有利于国家建设与政治稳定⑥。迪韦尔热则将一党主导体制看作“20 世纪伟大的政治发明……主导党开启了一个时代,可以说,它的纲领、观念、方法、风格与这一时代高度吻合”⑦。阿瑞安和巴内斯认为一党体制虽然设计欠缺,但却由钢铁锻造⑧。一党主导体制的出现适应了二战结束后新兴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于维护国内政局的稳定,弥合不同利益集团的分歧以及坚定地推进现代化发展等都具有积极作用且取得明显的制度绩效。
关于一党体制的终结有四种比较典型的解释:一是政党内部因素,将一党体制的生命衰竭归结为执政党内部的领导、决策、组织、监督、意识形态体系出现衰朽蜕变腐化,无法适应内外变化和执政要求。二是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是政党执政的国内国际环境,包括经济危机加剧,贫富分化加重,青年价值观变化,社交媒体扩散,以及国际强权的和平演变、价值渗透和军事干预,等等。三是结构主义视角,这一视角可以视为政党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结合,突出强调一党体制面临的内外挑战与其执政能力之间的差距,以及由此形成的危机的全局性、整体性和必然性。四是精英主义视角,将一党体制的解体归因于处于权力顶端的政党领袖或精英集团,认为是他们的政治价值偏好、策略选择和博弈互动决定了一党体制的最终命运⑨。
尽管上述解释在分析不同一党制的个案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也难免陷入理论上的混乱。作为政党体制的一种特殊类型,一党制所面临的执政环境、风险挑战、调适方式等与其他政党体制应该存在明显的区分。因此,我们尝试提出执政惰性的概念,作为分析一党体制解体的新框架。所谓的执政惰性,是指一个政党在长期执掌国家政权的过程当中,逐步丧失自我调适、自我革新、自我建设的动力,逐渐失去对外部危机的感知能力、公共政策的调适能力、党内腐败的自愈能力以及根植社会的组织能力,进而导致精英分裂、组织解体、认同流失,并最终丧失执政权力。执政惰性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体现:
其一,一党体制下的执政党缺乏有效的外部竞争,执政危机意识逐步淡薄。许多一党制的形成是与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同步进行的,比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和印度国大党都参与了本国的民族独立战争和建国过程。在争取执政地位的过程中,这些政党具有较强的危机意识和革新意识,把自己锻造得坚强有力且具有政治引领能力。亨廷顿指出,一个政党在争取民族独立和革命斗争中所遭遇的挑战越激烈、越持久,那么随后建立起来的一党制政党制度化程度就越高,执政的稳定性就越大⑩。本杰明·史密斯也有类似发现,一个政党在建党夺权初期遭遇外部势力干预越强,群众型政党的抵制越大,所拥有的资源越匮乏,该党越会注重政党建设、构建政治联盟,有效应对危机,实现长久执政[11]。然而,随着长期执政过程的持续,这些执政党通过运用国家权力游刃有余地化解内外挑战,进而会逐步淡化危机意识,形成权力的傲慢,逐渐失去对社会危机的感知能力和政策调适的主动性。
其二,一党体制下的执政党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容易滋生政治腐败。政治学的一条公理在于,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出现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竞争性的政党体制下,尽管各政党之间的监督往往从各政党私利出发相互倾轧,但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于执政党腐败的有效威慑。研究者发现,一党体制下的执政党拥有显著的资源优势,它们几乎垄断了所有公共财政资源,并将其转换为自身的经济来源,用来构建庇护体系以强化在基层社会的利益纽带,用于选举组织、宣传和动员以形成对反对党的竞选优势[12]。如果这一过程得不到有效的监督,执政党极易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当独大党将公共财政作为本党‘私人银行’的做法,导致日趋明显的腐败以及公众的强烈指责之际,当权者会被迫放弃这一做法,独大党的经济基础和选举根基也随之坍塌。”[13]因此,一党体制下,执政党缺失强有力的外部监督,面临腐败的可能性更大,更需要加强自我监督。
其三,一党体制下的执政党固化政治录用通道,更需要拓宽政治精英选拔和培养渠道。精英录用是政党的核心功能之一,政党只有招募到优秀的政治精英进入政党,才能保证政治上的先进性。在竞争性的政党体制下,政治精英既可以加入执政党,也可以加入反对党,都有获得政治晋升及成长的机会。相对而言,在一党体制下,执政党固化了政治精英进入和成长的通道,任何有政治抱负的优秀人才只有加入执政党才有崭露头角的机会[14]。执政党在掌握了全部政治资源的同时,也形成了政治精英培育的封闭格局。如果未能建立合理的内部人才遴选与培养机制,难免出现卖官鬻爵、吏治腐败,一些政治投机分子浑水摸鱼,形成泥沙俱下的局面。由于缺乏公开的政治竞争机制,围绕党内最高政治权力的争夺导致组织系统分裂,内部派系林立,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
二、政策调适能力缺失,执政党无法有效应对执政危机
政策调适能力是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经济社会形势变动调整政治策略和政策方向,以有效应对挑战和化解危机的能力。对于竞争性政党体制而言,定期举行的全国性大选以及由此带来的政党轮替,让参与选举的政党时刻保持政策灵活性,以便有效抓住选民以争取选举的胜利。对于处在一党体制下的执政党而言,长期执政地位让其逐渐丧失回应外部挑战的主动性,形成对于危机感的钝化反应和政策调适的惰性。
巫统的执政危机集中体现在最近三届大选中连续下滑的选举表现。自从2008年开始,巫统所主导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开始遭遇到来自反对党越来越强烈的挑战,选举优势持续丧失。在2008年举行的马来西亚第12 届大选当中,国民阵线获得140个国会议席,时隔39 年失去在国会中的2/3 绝对多数,也失去了修宪和制定法律的主导权;得票率仅为50.38%,低于上届大选12 个百分点。而反对党不仅赢得了47.79%的得票率,由上届的20 席一跃增至82 席,同时获得了槟城、吉兰丹州等5 个州的地方执政权力。2013年举行的第13届大选当中,国民阵线再次遭遇重创,仅获得47.37%的得票率,时隔44 年再次失去过半选民的支持,获得133 个议席;反对党“民联”获得50.87%的选票和89 个席位。如果不是得益于偏向执政党的选区划分方式,此轮大选国民阵线就会丧失执政地位。2018 年举行的第14 届大选,国民阵线仅获得35.59%的得票率和79 个议席;反对党“希望联盟”获得了54.95%的得票率和121个议席,得票率和议席双双过半,赢得执政地位,终结了巫统长期执政的历史(历年选举结果参见图1)。不难看出,自2008 年大选开始,巫统及其执政联盟国民阵线即面临着反对党强有力的挑战,本该痛定思痛进行执政策略的重大调整,以有效应对执政危机。然而,相反的是,尽管巫统在2008 年和2013 年两次大选中仅仅以微弱优势获胜,在第二届任期中的纳吉布政府依旧陶醉于“高度的自信”当中[15],巫统仍然沿用屡试不爽的竞选老套路,试图通过调整选区划分来瓦解反对党的支持力量,向以马来人为主体的公务员派发现金,以及出台管制网络舆论的法律等,以此延续竞选的优势地位。

图1 国民阵线在历届马来西亚大选中的席位
“协商民主”式的执政联盟失去效力,巫统的政治联盟和执政基础不断流失。在种族、宗教和文化多元分化的背景下,巫统采取“协商民主”的形式进行政治联盟,在大联盟内进行共同利益的协商[16]。具体来看,马来西亚是一个多种族构成的国家,土著(包括马来族和原住民)、华人、印裔人口分别占比为68.1%、23.8%、7.1%,其他种族占1.0%。此外,马来西亚宗教复杂,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印度教、道教等杂陈。为此,自1955年以来,巫统先后吸收马华公会、国大党以及民政党、进步党等十多个政党组成国民阵线,国民阵线内的各个党派分别作为各个族群的代表。这一“协商民主”式的政党联合机制在一定时段内,确保了巫统对国民阵线的主导以及国民阵线对马来西亚国家政权的领导权,同时也确保了各种族、宗教、派别在执政联盟内部的利益表达。然而,随着时势变迁,这一执政联盟也面临着失效的危险,并导致群众基础的流失。首先与巫统站在“同一战线”的马华公会因多年来无法真正表达华人诉求,在华人族群中权威持续衰减,其在众议院议席数从2004 年的31 席直线下跌到2008 年的15 席、2013 年的7 席,以及2018 年的1席。受此影响,巫统可以视为基本失去了全体华人选民的选票。同样,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又是巫统主要支持力量的马来人而言,习惯于享有经济和政治的特权。2008年上台的纳吉布推动的“一个马来西亚”计划,强调民族和谐、民族团结和有效治理,推动不同族群的权益平等。然而,这一计划并没有改变马来西亚种族关系日趋恶化的趋势,反而导致马来人特别是城市居民和中产阶级中的马来人对巫统失去了信任和支持。在2018 年大选当中,在188个马来人占多数的选区,反对党希望联盟获得了58个选区的胜利,而巫统只获得了46个选区的胜利,而这些选区曾经一直被视为执政党的天然票仓[17]。
经济政策失败导致执政绩效不彰,失去选民支持。自2008 年以来,巫统领袖、总理纳吉布连续推出一系列经济政策:推出新经济模式,鼓励知识产业、增加海外投资以增加工人收入,推进向高收入国家的过渡;倡导经济自由化政策,放宽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减少对马来人的商业保护,美国高盛和花旗集团获准扩大在马来西亚的业务;推行商品和服务税以提高政府财税收入;先后投入670 亿令吉实施两轮经济政策计划,以缓解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等等。上述政策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就业并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却没有摆脱“华而不实”的处境。一方面,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生活成本上涨引起选民不满,特别是对于失业率高达12.4%的年轻选民而言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就业人口中的高技能类岗位仅占28%,低工资、低技能、低薪酬和低生产力的结构性矛盾依旧显著。生活成本高涨、引入商品和服务税,以及围绕1MDB管理的问题,成为2018年大选排名前三的选举议题,牵动着选民的神经[18]。
三、自我净化能力缺乏,执政党无法有效清除党内腐败
自我净化能力主要体现为一个政党能够有效根除党内腐败,持续保持廉洁性的能力。相对于竞争性政党体制而言,一党体制下的执政党拥有执政资源优势,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建构国家监督体制、监督司法机关运行、任命执法机构领导人选,以及控制新闻媒体机构。在这一背景下,执政党党内腐败较少受到政党外部的独立监督,而更多地依赖于党内自上而下的垂直监督。执政党精英的腐败,实际上难以受到正常的司法调查和审判。从巫统的个案来看,它并不拥有有效的自我净化能力,党内腐败的蔓延,包括政党领袖出现严重腐败问题,最终造成政党形象在民众心目中的幻灭。
巫统的腐败既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政治领域。巫统长期处于一党主导地位,直接参与金融和组织生产活动,组建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并将其贱卖给马来人而培养了一批“人造资产阶级”,反过来这一批资产阶级与执政党形成密切的利益同盟关系[19]。2011 年马来西亚内阁中有3 名巫统高官受到腐败指控,包括掌管回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贾米尔、巫统妇女组主席阿迪莎·丽扎以及财政部副部长阿旺。贾米尔被控滥用回教义捐支付个人的律师费,阿迪莎·丽扎被指涉及国家养牛中心涉嫌滥用25亿令吉政府低息贷款,阿旺则涉嫌收取商人捐款而卷入贪污丑闻。这些贪腐丑闻不断透支巫统的执政资本,巫统的政治权威像流沙一样不断流失。除了在国家治理层面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经济利益的腐败行为,巫统党内的政治选举也充斥着“金钱政治”,甚至被称为“合理的制度腐败”。巫统党章规定,党主席获选人只有获得191 个区部中的58个提名才有参选资格。因此,在这种少数精英主导的党内选举制度下,金钱政治和暗箱操作现象接连不断。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于2008 年就曾公开披露,一些区部曾向其索要100万—200万令吉不等,作为提名其作为竞选巫统主席职位的“酬金”[20];2018年的大选前夕,又有16 名巫统党员以“两度随意拖延党选”为由向巫统的合法性发出挑战。
然而,对于巫统伤害最大的,莫过于巫统领袖纳吉布所牵涉的马来西亚国家投资基金“一马发展公司”的腐败案件,这也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马发展公司”作为政府经济转型计划的组成部分,于2009 年在总理纳吉布的倡导下成立。然而,该公司在成立仅仅6 年时间内就产生了111 亿美元的债务。2015 年7 月,《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了“一马发展公司”从2013 年3 月至2015 年2 月之间,先后三次将6.81亿美元通过关联企业转入纳吉布的个人账户。事件曝光引起轩然大波,巫统党内成员和反对党人民正义党对“一马发展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彻查。尽管由官方主导的调查显示,转入纳吉布个人账户的金钱来自沙特王室捐款而非“一马发展公司”,但事件还是引发了巫统内部的巨大分裂。马哈蒂尔公开呼吁纳吉布辞职并宣布与其分道扬镳;参与批评1MDB 问题的副总理Muhyiddin Yassin、农村和地区发展部长Shafie Apdal,以及试图独立调查1MDB 问题的总检察长Abdul Gani Patail,相继被免职。此外,纳吉布还要求议会发言人不回应1MDB的问题,并根据《官方保密法》禁止公布审计总报告。在2018年大选后重启的对纳吉布的调查显示,其涉及滥用权力、洗钱等多项罪名,涉及总额达5.6亿美元。
总体而言,掌握执政资源优势的巫统,党内的监督形同虚设,缺乏自我净化能力,导致政党形象一落千丈,执政党内经济腐败、集团腐败、领袖腐败和制度腐败交错纠缠,直接造成执政集团内部的分裂和执政基础的溃散。当担任22 年执政党领袖的马哈蒂尔公开抨击纳吉布的贪腐问题并加入反对党时,当上百万海外马来人在“拯救我的国家”“拯救马来西亚”的口号感召下回国投票时,也直接预示了巫统执政生命即将终结。
四、精英整合能力缺失,执政党代际更替危机频繁
一党主导体制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境是,如何通过制度化来约束政党领袖的权力,推进代际更替的常态化。研究者发现,一党主导体制下的政党领袖,可以将个体化的意志通过制度化的基础权力加以实现,以此来控制反对派的力量以及平息政治改革的要求;这一做法带来的另一难题是难以运用官僚化的“铁笼”来约束政党领袖的“铁拳”[21]。作为政党个体化运行的集中体现,马哈蒂尔自1981 年至2003年期间长期执掌政党权力和国家权力,并且通过包装、操纵和规避的手段来强化其个人对国家制度的影响[22]。然而,由于执政理念的分歧及利益的冲突,个性色彩鲜明的马哈蒂尔先后与四位巫统领袖发生政治冲突,甚至最终以成立反对党来挑战巫统的方式终结冲突。上述巫统内部精英之间的分裂和冲突,不仅导致执政党代际更替的危机,更是将党内分歧演化为党外对立,并直接导致执政权力的旁落(如图2所示)。
从1981 年到2003 年,马哈蒂尔连续22 年担任巫统党主席及国家总理,四次分裂均发生在现任及继任的巫统领袖之间。第一次党内分裂是发生在马哈蒂尔与东姑拉沙里之间。东姑拉沙里曾在马哈蒂尔政府任国际贸易和工业部长及巫统副主席,1987 年他试图挑战马哈蒂尔的巫统主席职位失败之后愤而出走,导致巫统分裂为“新巫统”和“四六精神党”。1987年,在马哈蒂尔的支持下,他选定的潜在继任者之一——安瓦尔加入巫统,并在10年内地位迅速攀升,成为马来西亚副总理。第二次党内分裂出现在马哈蒂尔与安瓦尔之间。1997 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总理马哈蒂尔与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安瓦尔在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上产生严重分歧,双方矛盾激化,马哈蒂尔解除安瓦尔一切职务,并以鸡奸罪判其入狱。这一事件引发了巫统内部的再次分裂,安瓦尔支持者转入新成立的国民公正党,而安瓦尔本人也成为反对阵营的精神领袖。第三次分裂发生在马哈蒂尔与巴达维之间。巴达维是马哈蒂尔指定的接班人,但态度温和的巴达维上任后释放了安瓦尔,并中止了马哈蒂尔执政时期的重点工程,激怒了马哈蒂尔并使两人关系恶化,最终导致巫统内部分裂为以两人各自为核心的派别。马哈蒂尔在巫统内部打压巴达维并转而扶持纳吉布,并最终推动后者于2008年获得总理职位[23]。

图2 国民阵线内部的精英分裂(1982—2018)
第四次分裂发生在马哈蒂尔与纳吉布之间。促使马哈蒂尔与纳吉布分裂的原因在于纳吉布牵涉“一马发展公司”的严重贪腐事件。当纳吉布深陷“一马发展公司”的腐败丑闻时,马哈蒂尔公开抨击纳吉布并要求其尽快下台。而作为回应,纳吉布政府曝光马哈蒂尔过去的执政失误,取消马哈蒂尔作为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顾问和子公司董事长的职位,随后又将马哈蒂尔的儿子穆克里兹(Mukhriz)从吉打州政府首脑和巫统高级领导人行列中开除出去。为了对抗纳吉布,马哈蒂尔先是成立新政党——土著团结党,随后又与曾经的政治对手安瓦尔领导的人民公正党结盟,组成反对党联盟——“希望联盟”,并最终在2018年的选举中击败纳吉布。马哈蒂尔加入反对党联盟给巫统造成了两个严重的伤害:一是让不满纳吉布的巫统精英找到新的政治方向,选择加入马哈蒂尔的阵营。二是让不满纳吉布的马来人和政府公职人员找到了替代性的政治领袖。长期以来反对党所无法攻克的马来西亚土著选民、偏远农村的选民,以及公务员和安全部队的选民,也愿意接受马哈蒂尔的领导,并且相信后者会确保他们既得的特殊利益。这也是反对党愿意摈弃前嫌与马哈蒂尔结盟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马哈蒂尔还是纳吉布,政治强人长时间持续执政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有助于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和维持政局的稳定性。但另一方面,政治强人为维持自身的权威和绝对统治所采取的排挤、打压等手段,却不利于党内精英的代际更新和良性竞争,特别是严重损害党内团结的政治气氛。巫统的每一次分裂都带来不少党内高级干部与党员流向反对党,同时也带走一大批原有的政党支持者。高层的争斗不仅严重削减了执政党组织的领导力和整合性,导致政党分裂与精英出走、变节,而且还给反对党增加实力制造了机会。
五、克服惰性与提升能力:执政党建设的中国经验
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善于学习的政党,还是善于建设与变革的政党。在一党执政情境下,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自身建设问题,强化执政危机意识,持续提升政策调适、自我净化和精英整合能力建设,把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一)强化执政危机意识
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取得政权,其革命时期的危机意识在执政后得到延续和强化。从对“两个务必”到“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强调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执政危机意识的深刻认识存在于各个历史阶段。在取得革命胜利夺取政权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著名的“两个务必”论断,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可以看作执政危机意识的第一次明确表达,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革命成功到全面执掌政权的大好形势下,对于作风建设松弛的高度警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执政危机意识的重视从未淡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执政环境的变化以及由此形成的执政风险。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只有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四大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四种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要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危机意识,是对于不同时期执政环境风险的深刻把握,也是基于领导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执政使命的持续坚守。
(二)提升政策调适能力
政策调适能力体现为一个执政党根据经济社会环境变化而调整政策方向的能力。在领导建设和改革的长期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构建起一套有效的政策调适机制,以适应不同时期的执政环境。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策调适能力集中体现为主动创造环境和被动适应环境,适应于自身推动的社会政治变革[24]。比如,为了修正“文革”错误,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方针路线,开启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历史进程。但是伴随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展开,中国社会结构加速分化和多元化,私营企业主、白领阶层、自由职业者等体制外群体不断成长壮大,进而对于党的组织属性和阶级基础形成冲击。党的十六大适时地提出“两个先锋队”理论,进一步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执政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调适能力的有效性,除了党自身所具有的对于外部环境变化的高度敏感性之外,还在于有一套中国特色的利益表达与聚合机制,包括专家参与国家决策机制、群众意见征集机制,以及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机制,等等[25]。这些机制有助于执政党敏锐地感知到经济社会的变化,并对相关政策进行适时的调整。
(三)突出自我净化能力
相对于竞争性政党体制而言,中国的政党体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非竞争性政党体制。这一体制决定了对于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监督,主要不是来自作为民主党派的监督,而是党对自身的监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26]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都强调必须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其中的“自我净化”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权力监督,净化组织肌体,纯洁党员队伍的各种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波澜壮阔的全面从严治党行动,以雷霆之势开展反腐败行动,从“八项规定”到“四风整治”,从“打虎拍蝇”到“猎狐套狼”,对遏制党内腐败现象形成压倒性优势;持续开展党内系列主题教育,从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持续推动思想建党的进程;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共制定修订140 多部法规,约占220多部现行有效的中央党内法规的60%;此外,中央部委和地方党委也加强党内法规建设,现行有效部委党内法规约240 部,现行有效地方党内法规约3700部[27]。不难看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净化,并且更为突出从纪律、思想和制度三个维度强化党的组织纯洁性和思想坚定性,突出制度反腐的重要性。
(四)加强精英整合能力
中国共产党加强精英整合能力,突出体现在干部选任制度的建设方面。德才兼备、选贤任能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干部选任的重要原则,并且也有力地保障了干部队伍的流动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干部选任得到进一步重视,政治忠诚、做人干净、敢于担当作为干部选任的新标准得到贯彻和执行。而确保党内领导干部有效整合的机制是政治上的要求和组织上的把关。对于领导干部的选拔和考核而言,政治标准被作为首要标准,政治纪律被视为根本纪律。中央先后颁布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党内监督条例、廉洁自律准则、党纪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问责条例等,把理想信念和政治要求作为其中的重要条款,要求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严格遵守。此外,为了确保对党内领导干部队伍的集中统一领导,突出强调党管干部的原则,并且在干部动议、提名、监督等具体环节中加以细化和完善。2014年1月,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党管干部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突出党组织在“动议”环节中的各项权力:提出启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意见,围绕选拔任用的职位、条件、范围、方式、程序等提出初步建议。2016 年年底,中组部修订《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守则》,明确在干部提拔过程中坚持“凡提四必”“三个不上会”“两个不得”“五个不准”等相关程序,突出强化党组织的领导和把关作用[28]。
六、结论
为什么曾经强大的一党主导体制最终走向了终结?对于马来西亚一党主导体制的既有研究,较为关注精英冲突、经济绩效以及信息工具的影响,而本研究认为应当从更为系统宏大的执政惰性视角认识巫统长期执政地位丧失的原因。执政惰性体现在长期执政的主导型政党执政危机意识淡薄、腐败根治能力缺乏以及精英流动固化与冲突等方面。长期主导马来西亚政权的巫统及其政治联盟国民阵线,长期执政的政治优势也导致其逐步丧失了政治危机感,形成系统性腐败并难以自我祛除,政党精英之间的冲突难以通过制度化程序加以化解。这一理论视角超越了就事论事的单因论,如内因论、外因论、结构论和精英论;同时也解构了强大的一党体制走向衰落的深层原因。
执政惰性既有助于解释一党主导体制覆亡的原因,也为长期执政的一党制建设提供了启示。首先是加强组织运行的体制化,特别是精英录用制度和权力交接制度。执政党精英层代表着政党的形象并引领着政党的前进,精英层内部的分歧、矛盾和冲突不仅可能引发党内派系林立以及政党分裂,还可能造成政党精英流失到反对党阵营。要注重加强政党精英录用和权力交接的制度化,将政党精英的冲突用党内民主协商的机制加以规范,避免陷入少数精英之间的路线之争。其次是提升政党适应性,特别是应对民众反映强烈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舆论环境问题,要构建有效的利益综合机制、有针对性的政策回应机制和政策效果反馈机制,力避长期执政条件下形成的权力傲慢。再次是突出权力监督的严密性,坚决反对腐败并强化权力净化。要构建相对独立的党内监督体系,构筑严密的腐败监督体系,强化对于执政党自身的权力监督。要逐步健全资源分配的市场机制,逐步减少政党和政府对于市场的过度干预以及对于经济资源的直接配置,从体制上防范权力寻租和经济腐败现象的发生。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自身建设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开展以及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可以看作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成果。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经验再次说明,在一党长期执政情境下,执政党必须加强执政危机意识,克服执政惰性;必须提升政策调适能力,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增强自我净化能力,不断克服组织腐化风险;加强精英整合能力,防范内部分裂。
注释:
①Khor Yu Leng,Run-Up to GE14:Up to 3.5 million Voters Expected to Be on the Move,see from www.theedgemarkets.com/article/runup-ge14-35-million-voters-expected-be-move.
②Najib Announces BN Manifesto and More BR1M Goodies,see from ww.thesundaily.my/news/2018/04/07 /najib-announces-bn-manifesto-and-morebr1m-goodies; Hanis Zainal,Najib: 67,000 Taxi Drivers Get RM800 Each with 1Malaysia Taxi Welfare Card,see from www.thestar.com.my /news/nation/2018/04/13/67000-taxi-drivers-get-rm800-each-with-1malaysia-taxi-welfare-card. GE14:Najib Confident BN Can Win Big,see from www.thesundaily.my/news/2018/05/06/ge14-najibconfident-bn-can-win-big.
③Serina Rahman,“ Was It a Malay Tsunami?Deconstructing the Malay Vote in Malaysia’s 2018 Election,”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07, No.6, 2018,pp.669-682.
④Walid Jumblatt Abdullah,“The Mahathir effect in Malaysia’s 2018 election: the role of credible personalities in regime transitions,”Democratization,Vol.26,No.3,2019,pp.521-536.
⑤Muhamad M. N. Nadzri,“The 14th General Election, the Fall of Barisan Nasion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1957-2018,”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Vol.37,No.3,2019,139-171.
⑥Samuel P. Huntington & Clement H. Moore,eds.,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New York: Basic Books,1970,pp.3-47.
⑦Maurice Da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London: Methuen,1955,pp.225-592.
⑧ Alan Arian and Samuel H. Barnes,“The Dominant Party System: A Neglected Model of Democratic Stability,” Journal of Politics,Vol.36,No.3,1974,pp.592-614.
⑨陈家喜、黄卫平:《一党体制衰落的制度探源——文献述评与框架建构》,《社会科学》2012 年第7期。
⑩[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7页。
[11][美]本杰明·史密斯:《政党与政权的生命》,严小青、王正旭译,《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
[12] John Ora and Thomas F. Remington,“Dominant Party. Regimes and the Commitment Problem: The Case of United Russia,”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2,No. 4,2009,pp.501-526.
[13]Kenneth F. Green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ingle-Party Dominance,”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3,No.9,2010,pp.1-27.
[14] Kenneth F. Greene,Why Dominant Parties Lose:Mexico’sDemocratizationinComparativePerspectiv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300-301.
[15]GE14: Najib Confident BN Can Win Big,6 May,see from www.thesundaily.my/news/2018/05/06/ge14-najib-confident-bn-can-win-big.
[16]John Funston,ed.,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2001,p.186.
[17] Meikeng Yuen,Felda’s Wave of Support for Pakatan Harapan, see from 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 2018/05/12/ feldas- wave- ofsupport- for - ph - swing-in-rural-areas-majorreason-for-coalitions-big-ge14-win/.
[18] Muhamad M. N. Nadzri,“The 14th General Election, the Fall of Barisan Nasion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1957-2018,”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Vol.37,No.3,2019,pp.139-171.
[19]陈家喜:《一党威权体制的危机与调适——以马来西亚巫统为对象》,《世界政党格局变迁与中国政党制度发展——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政党理论北京研究基地论文集》(第六辑),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政党理论北京研究基地2012年,第294—302页。
[20]哥打峇鲁:《东姑拉沙里:巫统党主席竞选区部索200 万令吉“提名酬金”》,《联合早报》2008 年11月4日。
[21]Dan Slater,“Iron Cage in an Iron Fist: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Power in Malaysi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6,No.1,2003,pp.81-101.
[22]同上。
[23]陈家喜、刘王裔:《马来西亚巫统的执政危机及其根源分析》,《领导科学》2013年第19期。
[24]陈家喜:《中国情境下政党研究的话语建构》,《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25]薛澜、朱旭峰:《中国思想库的社会职能——以政策过程为中心的改革之路》,《管理世界》2009 年第4期。鄢一龙、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中央政府决策模式演变——以五年计划编制为例》,《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26]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第2版。
[27]宋功德:《全方位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2018年9月27日《人民日报》,第7版。
[28]陈家喜、林清新:《新时代执政党干部选任制度的新变化》,《理论探讨》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