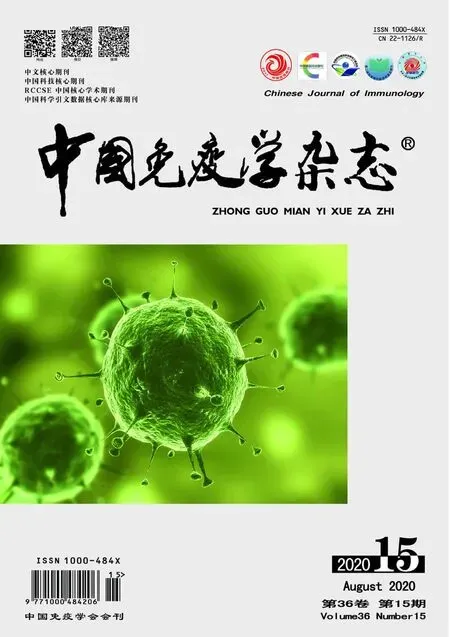肿瘤患者髓源抑制性细胞的免疫抑制及临床应用分析①
陈彦臻 吴 坚 刘沈林
(江苏省中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南京 210029)
髓样细胞是人体主要的造血细胞,由造血干细胞分化而来,研究显示其在肿瘤微环境中具有重要作用,能够调控肿瘤细胞免疫逃逸、肿瘤转移等肿瘤发展的关键环节[1]。髓样细胞是固有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激活适应性免疫反应,对组织内稳态及T细胞免疫反应有重要作用。肿瘤微环境中髓样细胞主要分为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粒细胞、单核细胞、肥大细胞和髓源抑制性细胞(myeloid 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MDSCs是骨髓来源的具有免疫抑制作用异质性的细胞群体,是病理状态下的单核细胞、中性粒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因分化受阻而聚集的一种骨髓前体细胞,这些前体细胞可被肿瘤衍生因子(tumor-derived factors,TDFs)由骨髓募集到外周并活化,是本身不表达MHC-Ⅱ和CD80等活化细胞的共刺激分子,在肿瘤组织中大量存在。
肿瘤主要通过分泌化学信号和细胞因子招募多种髓样细胞至肿瘤部位。研究表明肿瘤微环境中的髓样细胞——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TAMs)在肿瘤转移前被募集,参与肿瘤发生发展、诱导肿瘤血管新生、增强肿瘤浸润、转移并促进肿瘤细胞免疫逃逸等。而MDSCs则是早在TAMs之前发挥骨髓前体细胞作用,发出信号,感应侵袭并发挥免疫抑制作用、到达肿瘤部位,导致肿瘤细胞逃避机体免疫监视和攻击[2,3]。其发生较TAMs更早,目前研究尚在探索阶段。肿瘤微环境中MDSCs除显著抑制免疫反应,还可通过多种途径,从分期、转移和对化疗敏感性等方面促进肿瘤血管生成、参与肿瘤细胞耐药等介导肿瘤的发生发展。
1 人肿瘤来源的MDSCs分型
相较于鼠源MDSCs,人源MDSCs表型分析和分离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由于患者样本难以获取,可用于分析的细胞较少,导致标准的功能测定难以执行。MDSCs的异构性,在人类环境中不存在反映小鼠CD11b-Gr-1这种相对简单统一的标记系统,导致各研究在表型定义上高度分歧。由于人肿瘤MDSCs细胞亚群与嗜中性粒细胞及单核细胞表型特征相似,根据其表型和形态学特征主要可分为粒细胞样-髓源抑制性细胞(G-MDSCs,表型为CD33+Lin-HLA-DR-)和单核细胞样-髓源抑制性细胞(M-MDSCs,表型为 CD14+HLA-DR-)两大亚型,其特征在于单核细胞或巨噬细胞标志物CD11b、单核细胞分化抗原CD14、成熟单核细胞标志物CD15、骨髓谱系标志物CD33和通常在骨髓细胞中表达的HLA-DR。将多形核髓源抑制性细胞(polymorphonucler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PMN-MDSCs)定义为CD11b+CD14-CD15+或CD11b+CD14-CD66b+,M-MDSCs定义为CD11b+CD14+HLA-DR-/lowCD15,早期骨髓源抑制性细胞(early-stage MDSCs,e-MDSCs)定义为Lin-(CD3/14/15/19/56)/HLA-DR-/CD33+[2]。不同肿瘤环境中患者MDSCs表达不同,在黑色素瘤患者中表型为CD14+CD11b+HLA-DRlow/-;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表型为CD11b+CD14-CD15+CD33+;肾细胞癌患者G-MDSCs表型为CD14-CD15+CD11b+CD66b+[4,5]。CD66b可替代CD15,CD33可替代CD11b,由于M-MDSCs高表达CD33,而PMN-MDSC为CD33dim[6]。
2 肿瘤患者MDSCs的免疫抑制
2.1辅助性与调节性T细胞 调节性T细胞( T regulatory cell,Treg ) 与辅助性T细胞Th17 (T helper17 cells,Th17 )均属于CD4+T细胞亚群,Treg表达CD25和转录因子Foxp3(forkhead box protein 3),其主要功能为抑制效应T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及维持机体免疫耐受。Th17表达IL-17与维甲酸相关孤儿受体(retinoic acid-related orphan receptor,ROR)家族中的RORγT,其分泌的IL-17可通过先天性免疫与获得性免疫系统联合的方式促进机体免疫应答,在自身免疫与机体防御反应中具有重要作用。Treg与Th17的动态平衡是维持免疫稳定的重要机制,肿瘤患者外周血中的Treg/Th17升高诱发的肿瘤增殖、逃逸与患者MDSCs高表达密切相关[7]。
2.1.1G-MDSCs与Th17相互调节 目前未有研究指出G-MDSCs与Th17有确切正/负反馈关系,但已明确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调节。IL-17为Th17的标志性细胞因子,有研究表明口腔鳞癌患者外周血MDSCs、Th17细胞增加,IL-17水平升高;乳腺癌患者外周血MDSCs表达上升,低水平的IL-17可抑制STAT3活化,导致乳腺癌患者G-MDSCs增加,提示IL-17介导STAT3信号在乳腺癌细胞中激活[8,9]。在结直肠癌患者中FOLFOX联合贝伐珠单抗靶向治疗可降低G-MDSCs频率,Th17细胞丰度增加可调节Treg/Th17平衡,表明诱导Th17极化在结直肠癌化疗中有重要作用,Th17的早期改变与转移性结直肠癌G-MDSCs频率和疾病不良预后密切相关[10]。炎症相关肠癌患者腹腔巨噬细胞分泌的IL-17可提高粒细胞G-MDSCs存活率并增强其抑制功能,增加Th17比例,促进G-MDSCs积累及炎症相关肠癌发展[11]。
2.1.2M-MDSCs诱导Treg产生 Treg广泛存在于肿瘤患者外周血及浸润组织中,卵巢癌、胰腺导管腺癌、肺癌、胶质母细胞瘤、非霍奇金淋巴瘤、黑色素瘤中Foxp3+Treg的积累将导致患者预后不良[12]。高水平的IL-10可诱导Treg发挥抑制功能,影响T细胞发育。手术诱导的M-MDSCs可显著抑制T细胞增殖,肺癌患者胸腔镜术后表达CD11b+CD33+HLA-DR-CD14+表型的M-MDSCs较术前明显增加,且其积累与Treg增加线性相关[13]。体外与自体T细胞共培养时,胸腔镜术后肺癌患者的M-MDSCs扩增Treg能力更强,提示其作为肺癌患者预后指标优于术前。人结直肠癌中新发现的CD39+γδTreg可通过腺苷介导的途径分泌IL-17A、IL-10、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M-CSF)等细胞因子,可能通过趋化作用吸引M-MDSCs从而建立免疫抑制网络,相比CD4+或CD8+Treg具有更强的免疫抑制活性[14]。41例经多西他赛化疗的前列腺癌患者CD14+HLA-DRlow/-Lin-CD11b+CD33+表型的M-MDSCs明显高于正常组,其频率与Treg水平呈正相关[15]。
2.2降解氨基酸及其关键酶
2.2.1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和精氨酸酶1(arginase 1,ARG1) INOS和ARG1分别是精氨酸代谢和NO产生的关键酶,而与T细胞活化密切联系的L-精氨酸是二者共同的水解底物。T细胞抗原受体和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杀伤受体NKP46、NKP30和FcγRⅢ(CD16)的主要信号亚单位为CD247,CD247下调可导致上述受体功能减退,而MDSCs可通过ARG1摄取、消耗和螯合L-精氨酸,影响CD247表达和T细胞增殖[16]。表达环氧化酶-2的肿瘤高表达前列腺素E2,其可将MDSCs招募到肿瘤部位,诱导免疫抑制功能,如ARG1表达[17]。此外,MDSCs还可通过IFN-γ诱导INOS产生NO阻碍IL-2的释放,从而抑制T细胞增殖[18]。
胃癌患者外周血、卵巢癌患者腹水MDSCs可检出大量ARG1及INOS,加速L-精氨酸水解导致其供给不足,抑制T细胞的增殖与功能[19,20]。卵巢癌患者腹水中STAT3上调可诱导M-MDSCs中ARG1及INOS表达。结外NK/T细胞淋巴瘤患者MDSCs中INOS和ARG1高表达,INOS、ROS抑制剂的使用显著逆转了结外NK/T细胞淋巴瘤患者MDSCs对CD3诱导的T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21]。
2.2.2吲哚胺2,3双加氧酶(indoleamine2,3-dioxygenase,IDO) 色氨酸分解代谢酶IDO表达细胞对色氨酸的消耗和降解限制了T细胞与NK细胞的增殖存活。Caspase募集域包含蛋白9 (Caspase rccruitment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9,CARD9)是一种在髓细胞高表达的适应性蛋白,敲低CARD9可通过NF-κB通路增强MDSCs中IDO表达,减弱肺癌患者MDSCs免疫抑制功能[22]。羟拉米定和苯基咪唑中提取的两种IDO1小分子酶抑制剂在Ⅱ/Ⅲ期人体试验中进展最快,其本身活性有限,但可显著增强免疫原性化疗或免疫检查点药物的活性[23]。
2.3活化高浓度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 在人类肿瘤炎症环境中,MDSCs和其他先天免疫系统产生的高度反应性氧化因子ROS和NO会导致基因组不稳并诱发体细胞突变,如炎性肠病和幽门螺杆菌感染等[16]。MDSCs因此产生的高ROS炎症环境为肿瘤的发生、肿瘤微环境的富集和肿瘤的恶性进展提供了最佳生态。当慢性炎症发展、NO/ROS诱导的MDSCs数量增加时,这些效应会显著增强。MDSCs与活化的T细胞、内皮细胞等相互作用诱导还原型辅酶Ⅱ氧化酶上调并使MDSCs产生ROS,使其能够通过过氧亚硝酸盐的产生抑制抗原特异性T细胞。此外,MDSCs产生的ROS和NO可引起T细胞内多个分子阻滞,原发性肝癌患者中LOX-1+CD15+PMN-MDSCs明显高于对照组及良性组,LOX-1+CD15+PMN-MDSCs升高导致内质网应激诱导的ROS抑制T细胞增殖[24]。提示靶向MDSCs的氧化还原调控在癌症治疗中具有广泛前景。
2.4高表达抑制性细胞因子
2.4.1肿瘤释放趋化因子 趋化因子通常被认为是炎症诱导的调节分子,其参与肿瘤发生发展的各个方面,促进肿瘤细胞生长转移,而肿瘤组织中高水平的趋化因子如CC趋化因子配体-2[chemokin(c-cmotif) lig-and 2,CCL2]、CXC趋化因子配体-2[chemokin ( C-X-C motif ) ligand 2,CXCL2]等可通过募集MDSCs抑制免疫反应。肿瘤细胞通过CXCL2/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macrophage migrationinhibitoryfactor,MIF)-CXC趋化因子受体-2[chemokin ( C-X-C motif ) receptor type 2,CXCR2]信号传导在膀胱癌患者肿瘤微环境中诱导MDSCs积累和扩展,CXCL2或MIF表达与肿瘤浸润性CD33+MDSCs数量呈正相关(P<0.01)[25]。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tumor-associated fibroblasts,TAFs)通过基质细胞衍生因子(stromal cell derived factor,SDF)及其唯一受体组成的SDF-1/CXCR4通路吸引单核细胞,并由IL-6介导的STAT3活化诱导其分化为MDSCs,经TAF处理的单核细胞(T-MDSCs)破坏T细胞增殖,并以STAT3依赖的方式改变T细胞表型和功能。因此肝癌患者中TAFs衍生的细胞因子如IL-6和血清趋化因子SDF-1a,诱导MDSCs产生和激活,损害人类抗肿瘤免疫反应,促进肝癌进展[26]。
2.4.2过表达高水平IL-10 IL-10的过度表达导致Ⅰ型免疫反应的强烈抑制反馈,则MDSCs被Ⅰ型免疫过度激活。在卵巢癌患者外周血和腹水中具有典型的MDSCs单细胞表型CD14+HLA-DR-/low,腹水中检出大量MDSCs,与IL-6、IL-10及其下游的STAT3活化密切相关,其丰度与卵巢癌患者预后不良呈正相关,其中M-MDSCs水平较高的卵巢癌患者生存率较短[27]。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MDSCs中,IL-10产生的B细胞亚群明显升高,其绝对数量与临床分期显著相关[28]。一项随机Ⅱ期临床试验对晚期黑色素瘤患者进行伊匹单抗单药治疗或伊匹单抗联合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检测患者MDSCs循环频率和CD8+T细胞活化情况。结果显示,全反式维甲酸可降低IL-10等免疫抑制基因表达,抑制MDSCs在混合淋巴细胞反应中的免疫抑制作用,患者获益优于伊匹单抗单药治疗[29]。
2.4.3产生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TGF-β) TGF-β是一种免疫抑制效应因子,有助于肿瘤微环境形成,影响免疫治疗。MDSCs生成的TGF-β可更有效地抑制T细胞功能并促进T细胞调控细胞表型[30]。结外NK/T细胞淋巴瘤是非霍奇金淋巴瘤的一种少见类型,其MDSCs抑制IFN-γ和自体CD4+T细胞增殖分泌,促进TGF-β分泌及Foxp3表达,该病患者HLA-DR-CD33+CD11b+MDSCs比例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n=21)[21]。卵巢癌患者血液循环中的Arg/IDO/IL-10表达的M-MDSCs和PMN-MDSCs显著增加,这些亚群在外周血、腹腔液及肿瘤组织等肿瘤免疫微环境中的存在与TGF-β水平呈正相关[31]。
2.5其他
2.5.1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PD-1/CD279)/PD-L1轴 多种肿瘤通过上调肿瘤微环境PD-L1表达,持续激活PD-1/PD-L1信号通路,抑制T细胞功能,而MDSCs在晚期癌症患者中与PD-1/PD-L1信号高度关联[32]。MDSCs衍生的TGF-β介导的PD-1在CD8+T细胞高表达,可抵抗食管癌患者肿瘤微环境中PD-1/PD-L1的阻断[33]。全反式维甲酸降低PD-L1表达,减少晚期黑色素瘤患者MDSCs数量,一定程度地抑制其分化[34]。相对于血液中其他髓细胞,G-MDSCs表达高水平的PD-L1、CD39和CD73且具有较强的免疫抑制活性,可逆转阻断的PD-1/PD-L1轴[10]。有研究表明,恶性胶质瘤患者肿瘤组织中的MDSCs可诱导CD4+效应记忆性T细胞上的PD-1和肿瘤源性MDSCs的PD-L1配体表达上调[35]。
2.5.2高丰度肠道菌群 人体肠道中菌群丰富,多聚于结直肠与口腔。肠道菌群与消化道肿瘤尤其是结肠癌间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而MDSCs是导致肠道真菌群比例失调、肿瘤免疫抑制的关键环节。热带念珠菌培养的骨髓细胞可在右旋糖酐硫酸酯钠诱导的组织炎性损伤后异位到固有层细胞,激活NF-κB、P53等导致肠道功能缺失,肠道菌群负荷增加,诱导MDSCs分化抑制效应T细胞,促进患者结肠癌发展[36]。结肠癌患者肿瘤组织中真菌负荷影响MDSCs数量,两者呈正相关,提示热带念珠菌可诱导MDSCs特性及抑制功能,MDSCs通过人体真菌的高丰度表达与人类肿瘤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结合真菌、细菌的消化道肿瘤患者MDSCs研究已成为近年的发展趋势。
3 MDSCs的肿瘤临床应用
MDSCs广泛存在于肿瘤患者外周血、腹腔液及肿瘤组织,少量存在于脾细胞。卵巢癌肿瘤组织中PMN-MDSCs频率明显高于外周血和腹腔液组;而与腹腔液和健康组相比,外周血中的e-MDSCs水平更高[32]。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ymphocyte-to-monocyte ratio,LMR)越低,结直肠癌患者预后越差,低LMR患者中可观察到高表达的循环MDSCs[37];研究表明肝细胞癌患者外周血MDSCs的相对数量、平均数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宫颈癌患者外周血中Lin-/lowHLA-DR-CD11b+CD33+MDSCs比例显著升高,胃癌患者外周血中CD33+HLA-DR-CD11b+CD15+G-MDSCs和CD33+HLA-DR-/lowCD14+M-MDSCs均显著升高,且晚期胃癌患者MDSCs比例明显高于早期胃癌患者[19,38-40]。
3.1肿瘤免疫疗法的预测标志物 肿瘤患者MDSCs与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和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缩短相关,M-MDSC和PMN-MDSC均与生存结果呈负相关,可作为肿瘤患者临床评价预后的生物标志[1]。病变早期监测Th17和G-MDSCs数量改变对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预后判断有重要影响[10]。T细胞与MDSCs表达水平的平衡使肿瘤向2型免疫倾斜,可能是预测膀胱癌复发的关键因素,影响肌层浸润性癌症患者的死亡率[41]。具有典型CD14+HLA-DRlow/-CD86low/-CD80low/-CD163low/-细胞表面表型的M-MDSCs在乳腺癌中显著增加,并与淋巴结和内脏器官转移及临床分期相关,可作为评估乳腺癌进展及辅助诊断的新标记物[42]。凝集素型氧化LDL受体-1(lectin-type oxidized LDL receptor-1,LOX-1)是PMN-MDSCs独特的表面标记,LOX-1+CD15+PMN-MDSCs显著降低和CD4+、CD8+T细胞增殖可预测并证实肝癌患者PMN-MDSCs的免疫抑制能力[24]。在术前MDSCs水平>1%的总外周血单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s)晚期乳腺癌患者中,术前患者MDSCs水平与IL-6含量呈极显著的正相关,Ⅳ期患者的总体生存期与其他疾病分期相比明显更短,与MDSCs水平<1%患者的总PBMCs相比也显著缩短,提示术前晚期乳腺癌患者MDSCs水平可能作为良好的预后指标[43]。
3.2肿瘤患者的治疗靶点 通过减少MDSCs数量、阻断迁移、诱导MDSCs在人体分化为成熟的骨髓细胞、抑制其免疫活性等皆是以MDSCs为靶点的肿瘤临床治疗的主要思路。ILC2/IL-13轴[41]和CXCL2/MIF-CXCR2轴[25]在MDSCs聚集可抑制M-MDSCs富集,改善膀胱癌的靶向治疗。RUNX1重叠RNA(RUNX1 overlapping RNA,RUNXOR)是一种长链非编码RNA,通过靶向RUNT相关转录因子RUNX1成为髓细胞发育的关键调控因子。肺癌组织MDSCs中RUNXOR的表达高于邻近组织,RUNXOR的敲除可降低MDSCs中ARG1表达;而RUNX1作为RUNXOR的靶基因在肺癌患者MDSCs中表达下调。MDSCs中RUNXOR可作为临床治疗靶点,促使MDSCs分化为成熟细胞,与肺癌患者MDSCs诱导的免疫抑制显著相关[44]。S100A8/A9是由髓源细胞和肿瘤细胞共同产生的促炎异二聚体,阻断S100A8/A9及其受体对胃癌患者MDSCs的作用可使T细胞效应功能丧失,S100A8/A9逆转MDSCs介导的免疫抑制可调节抗肿瘤免疫[45]。已有研究证实,靶向MDSCs能够增强肝癌患者模型索拉非尼、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抗肿瘤功效[46]。
各类激动剂、抑制剂、多聚糖及干预调控因子等治疗方案已逐渐应用于靶向MDSCs的临床诊疗。干扰素调节因子7(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 7,IRF7)可抑制G-MDSCs免疫活性,其表达水平与肺癌患者G-MDSCs的表达频率及肿瘤转移呈负相关[47]。在MDSC/CD8+T细胞共培养体系中,肺鳞状细胞癌患者CD8+T细胞凋亡率随MDSCs比例增加显著升高,肿瘤细胞凋亡率明显下降,高浓度的IFN-γ可显著降低MDSCs含量[48]。MDSCs对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受体2(TNF-related apoptosis-inducing ligand receptor 2,TRAIL-R2)激动剂高度敏感,TRAIL-R2激动剂抗体为DS-8273a。DS-8273a靶向TRAIL-R2可选择性消除MDSCs,在化疗前及化疗中的头颈部肿瘤患者外周血中导致MDSCs下降,且并未影响成熟骨髓或淋巴样细胞[49]。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β-葡聚糖(whole β-glucanparticles,WGP)治疗后可抑制CD14+HLA-DRlow/-CD11b+CD33+MDSCs分化及功能,可能在肺癌治疗起免疫调节作用[50]。采用集落刺激因子-1受体抑制剂PLX3397的前列腺癌患者临床试验中,与单药治疗相比,T细胞过继疗法可增强肿瘤浸润T细胞,降低外周血MDSCs[51]。一项前瞻性Ⅰb期辅助试验表明,在头颈部鳞状细胞癌患者中使用西妥昔单抗加用促炎TLR8 激动剂可导致单核细胞向M1表型倾斜,逆转MDSCs对T细胞体外增殖的抑制,增强细胞抗肿瘤免疫应答[52]。
3.3其他 胃癌患者分泌的肿瘤来源外泌体(tumor-derived exosomes,TDEs)能够将miR-107传递给HLA-DR-CD33+MDSCs,通过靶向DICER1和抑癌基因PTEN可诱导其扩增活化,证实肿瘤患者体内TDEs与MDSCs相关[53]。对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单独实施贝伐单抗治疗结果显示,贝伐单抗治疗期间患者MDSCs 数量仍然相对较低,无显著变化,提示贝伐单抗与患者生存率无关[54]。而同样在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大脑中发现,免疫抑制性MDSCs与自我更新的肿瘤干细胞(cancer stem cells,CSCs)非常接近。高水平CSCs可产生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MIF),MIF的上调以CXCR2依赖性方式增加胶质母细胞瘤患者MDSCs免疫抑制酶ARG1表达,而阻断MIF则降低ARG1[55]。对GSCs与肿瘤患者MDSCs关系的研究,或可成为MDSCs在肿瘤免疫治疗的突破口。
4 结语
MDSCs与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的获得性不同,其主要与炎症及抗原处理密切相关,直接或间接损害CD4+、CD8+T细胞和NK细胞的效应细胞功能。除上述机制外,MDSCs还可能通过分泌高水平的蛋白水解酶如MMPs促进癌细胞侵袭和扩散;头颈部鳞状细胞癌患者组织芯片免疫组化染色分析显示,头颈部鳞状细胞癌患者微血管密度明显增加,其相关通路JAK2/STAT3及血管生成因子与MDSCs密切相关,提示MDSCs可能参与血管生成[56]。各通路、细胞因子间并非绝对独立,亦存在相互介导或上下游诱导所致的MDSCs免疫抑制。
肿瘤周围免疫抑制微环境是肿瘤形成的重要因素,即肿瘤是生长环境选择的产物,而非局限于细胞毒作用,因此考虑患者的免疫状态是抗癌的长久之计。MDSCs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将更全面的反应患者免疫状态,可开发一系列免疫状态标记物作为交叉验证线索,结合遗传和生物肿瘤参数,设计最佳个体化治疗。将目光从肿瘤微环境中的T细胞转移至髓样细胞,通过选择性靶向MDSCs、抑制MDSCs免疫抑制活性、考虑其药理阻断作用、诱导MDSCs在人体分化为成熟的骨髓细胞或许能够进一步壮大肿瘤免疫疗法,将癌前病变炎症环境转变为抗癌环境,克服目前肿瘤治疗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