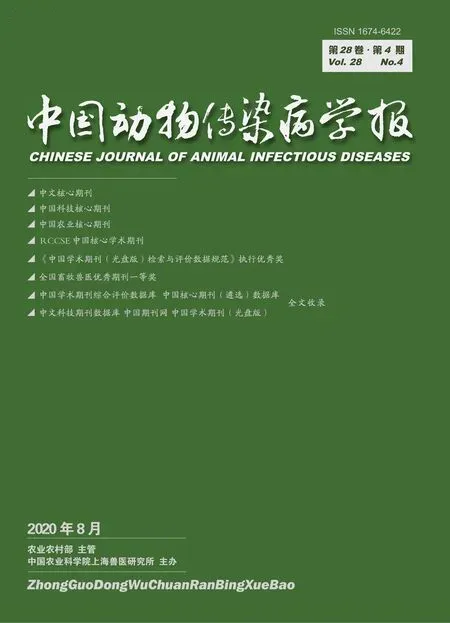蜱与巴贝斯虫之间互作分子的研究进展
姚佳玲,龚海燕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农业农村部动物寄生虫学重点开放实验室,上海200241)
蜱为专性吸血的节肢动物,属于动物界节肢动物门、蛛形纲、蜱螨亚纲、寄螨目、蜱总科。全世界已经发现18属897种,我国已发现10属119种,包括100种硬蜱和10余种软蜱[1]。蜱的发育阶段主要包括卵、幼蜱、若蜱和成蜱,每个发育阶段均需吸血才能完成。蜱的宿主非常广泛,且与人类疾病关系密切,是许多重要病原的传播媒介,可携带和传播病毒、细菌、真菌、立克次氏体、螺旋体及原虫等[2],给人类健康、畜牧业生产及野生动物带来极大危害。
蜱传病中,巴贝斯虫病是由顶复门巴贝斯虫引起的一类血液原虫病,传播媒介为硬蜱,因人兽共患而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关注[3]。根据目前文献记载,硬蜱科的扇头蜱(Rhipicephalus)、硬蜱(Ixodes)、血蜱(Haemaphysalis)、璃眼蜱(Hyalomma)是巴贝斯虫的媒介宿主[4]。巴贝斯虫除少数经输血传播以外,主要通过感染蜱的叮咬传播[5-6]。蜱在吸血过程中大量摄入虫体,但巴贝斯虫随红细胞到达蜱中肠后,大部分将被消灭或者退化,仅少数发育为配子体,随后融合成合子才能穿透蜱中肠围食膜并迁移到血淋巴中的各个器官[7-9]。这些“幸存者”会给媒介宿主带来哪些影响,自身又有哪些变化?本文将对蜱的各个器官和巴贝斯虫中涉及的互作分子进行阐述,以期为阻断巴贝斯虫的传播提供信息和基础。
1 蜱体内互作相关分子
1.1 中肠 防御素和抗菌肽类:中肠不仅是蜱的主要消化器官,而且是营养物质的贮存库,更是多种病原的载体。原虫入侵时,刺激蜱的先天免疫反应,快速合成防御素和蜱抗菌肽(antimicrobial peptides,AMPs),由此构成了重要的体液防御机制。此类分子不仅对原虫有抑制作用,且对细胞内的细菌和真菌同样具有抗性[10-12]。中肠细胞内有一种类防御素蛋白(Longicin),最初发现于长角血蜱(H.longicornis),研究表明重组Longicin在体外可有效抑制裂殖子增殖,且接种该蛋白质使得感染小鼠体内的田鼠巴贝斯虫(B.microti)减少;而Longicin沉默则导致蜱的中肠、卵巢和卵等多个组织中染虫率增加[13]。Longipain也是长角血蜱中分离出来的一种蛋白,属于中肠半胱氨酸蛋白酶,功能与Longicin相似[14]。Microplusin是微小扇头蜱(R.microplus)中富含半胱氨酸的AMPs家族中的一员[15],研究发现具环扇头蜱(R.annulatus)感染双芽巴贝斯虫(B.bigemina)时,Microplusin会过度表达[10]。
蛋白酶和蛋白酶抑制剂类: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cystatin, cyst),可有效抑制木瓜蛋白酶样半胱氨酸蛋白酶。在多种蜱中发现了编码半光氨酸蛋白酶抑制剂的基因[16-17];Hlcyst-2来自于长角血蜱中肠,在吉氏巴贝斯虫(B.gibsoni)感染的幼蜱中表达量比正常幼蜱高1.8倍,其重组蛋白对体外培养的巴贝斯虫表现出明显的生长抑制作用,这些结果表明Hlcyst-2参与蜱的先天免疫[18];镰形扇头蜱(R.haemaphysaloides)的Cystatin分子RHcyst-1和RHcyst-2在感染与未感染巴贝斯虫蜱体内的基因表达量分析表明,在半饱血若蜱阶段,RHcyst-1和RHcyst-2基因显著上调,在饱血若蜱及蜕皮后的成蜱阶段,基因显著下调,体外实验表明蜱的Cystatin可抑制巴贝斯虫的半胱氨酸蛋白酶[19];此外,中肠中还存在其他保护蜱免受病原攻击的蛋白酶和蛋白酶抑制剂[7,10-11,20]。
通道蛋白和受体类:微小扇头蜱中肠中的BmVDAC,线粒体电压依赖性阴离子选择性通道多肽(也称为线粒体孔蛋白),可与双芽巴贝斯虫有性阶段蛋白结合,虫体入侵时,BmVDAC过量表达[21-22]。VDAC被认为位于线粒体外膜中,调节小分子进入线粒体膜间隙的通量,并在细胞代谢和细胞凋亡中起作用[23]。在蚊子中,VDAC在疟原虫入侵中肠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同样,伯氏疏螺旋体(Borrelia burgdorferi)通过蜱中肠的传播可能与VDAC结合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的能力有关[24-25]。此外,在肩突硬蜱(I.scapularis)中肠上皮细胞中鉴定到伯氏疏螺旋体外膜蛋白A的蜱受体(TROSPA),且此蛋白可能控制蜱体内的细菌感染[26-28]。在具环扇头蜱中,TROSPA的直系同源基因在双芽巴贝斯虫感染期间过表达,而基因敲除则使微小扇头蜱和具环扇头蜱中的巴贝斯虫感染率分别降低了70%和83%[10]。用TROSPA免疫接种牛后,双芽巴贝斯虫从牛向蜱的传播概率下降了80%[29]。在具环扇头蜱中,这种受体不仅存在于中肠,还存在于唾液腺(salivary glands,SGs)和卵巢中[30]。在长角血蜱中,还鉴定出富含亮氨酸的重复结构域蛋白(LRR),其重组蛋白对吉氏巴贝斯虫具有生长抑制作用,且效果与传统的抗生素药物相似甚至更好[31]。中肠中还存在其他带有结构域的具有保护作用的分子,如MD-2相关的脂质识别(ML)结构域分子,含有与脂质识别相关的蛋白质[32]。
其他分子:Bm86为膜结合糖蛋白,在微小扇头蜱中肠细胞中首次发现,其可能参与中肠内血液的内吞作用[33-35]。在使用基于Bm86抗原的疫苗Gavac®R的一项研究中,接种疫苗的与未接种的狗相比,接种疫苗的狗体表的若蜱呈现更低水平的犬巴贝斯虫(B.canis)感染。而携带Bm86抗体的牛喂食蜱后,抗体引起蜱中肠消化细胞裂解,进而血液渗漏到蜱淋巴中[36]。由此可以推测,中肠细胞的裂解可能抑制了合子的进入和/或下游动合子的分化,从而损害了若虫对犬巴贝斯虫的获取。但也有研究表明,Bm86的RNA干扰不影响牛巴贝斯虫(B.bovis)经卵传播[34]。Subolesin,最先发现于肩突硬蜱,经鉴定为昆虫和脊椎动物中先天性免疫相关分子Akirin的直系同源基因[37-38],在真核生物包括蜱类高度保守[30,39],是抗蜱和蜱传播病(TTBP)候选抗原中很有潜力的分子之一。Subolesin家族蛋白在转录水平上调节病原体感染反应的细胞通路中的相关蛋白质表达[40-41]。Subolesin沉默引起微小扇头蜱中双芽巴贝斯虫感染水平下降[42],但具环扇头蜱中双芽巴贝斯虫的感染水平降低不显著[10]。Subolesin和含有Subolesin保护性表位(Q38)的嵌合体进行疫苗接种,影响了双芽巴贝斯虫向蜱传播[29],由此表明,Subolesin与巴贝斯虫的感染有一定关系。
蜱中肠是巴贝斯虫穿越媒介宿主,上行到唾液腺的第一道屏障,了解肠上皮细胞和内容物中的蛋白分子与巴贝斯虫的互作,将有助于抗巴贝斯虫疫苗的研发,从而阻断巴贝斯虫在蜱体内的迁移以进一步阻断巴贝斯虫的传播。
1.2 血淋巴与卵巢 巴贝斯虫成功入侵蜱中肠上皮后,其合子在血淋巴的帮助下,通过减数分裂,成为动合子。在淋巴液中,巴贝斯虫经无性繁殖,从而产生多个孢子囊并经卵传播,导致在蜱所有生命阶段及蜱所有器官中都可携带孢子囊[43]。
当蜱被微生物,如巴贝斯虫入侵时,血淋巴细胞增加其循环次数以破坏和控制入侵者,吞噬小颗粒物质和微生物[44-45]。除了吞噬作用外,血淋巴中还通过其他方式保护自身,如形成结节和包囊,或通过血淋巴中存在的分子AMPs、溶菌酶、蛋白酶、蛋白酶抑制剂和凝集素等直接作用于病原体[46-47]。双芽巴贝斯虫在到达血淋巴时表现出运动性并黏附于微小扇头蜱血细胞膜上[48],但蜱是如何在血淋巴水平上控制病原的还不得而知。
几乎所有巴贝斯虫种均可在雌蜱中垂直传播,这是该属的独有特征[8,49],可视为病原为了长期存在于生态系统中而进化出来的适应性[8]。感染巴贝斯虫的蜱卵巢蛋白组学研究鉴定出多个显著差异表达的蛋白质,包括钙网蛋白、谷氨酰胺合成酶和Kunitz型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家族;其次为蜱溶菌酶和一组可能属于AMPs家族的小蛋白质[50]。巴贝斯虫感染可能影响蜱卵巢中参与应激反应、解毒和免疫反应相关的基因[51],这些基因大部分可翻译得到参与卵巢免疫反应的蛋白酶和蛋白酶抑制剂。当蜱卵巢被感染时,发现假定的免疫亲和素(Imnp)和Kunitz型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Spi)基因表达上调[50]。Imnp基因敲除导致子代幼虫感染水平显著上升,表明此分子可能控制原虫入侵蜱卵巢,并影响子代幼虫发育。
蜱的卵黄蛋白原受体(vitellogenin receptor,VgR)与巴贝斯虫的垂直传播有关。VgR沉默后,未能检测到叮咬感染犬的长角血蜱体内的吉氏巴贝斯虫DNA[52],由此可能表明巴贝斯虫分子对蜱VgR具有配体结合活性,从而侵入正在发育的卵母细胞。
卵巢是雌蜱生殖系统中的一个主要结构,包括巴贝斯虫在内的很多病原体可以经卵传播,新孵化的带虫幼蜱可将病原传染给宿主,而卵巢中的一些分子可通过减少卵和胚胎发育,从而降低蜱的繁殖率并阻断蜱媒病原经卵传播,所以卵巢中与病原体相互作用的分子将有望成为疫苗开发的靶标。
1.3 唾液腺 当巴贝斯虫上行到达唾液腺时,经历最后的增殖阶段并产生子孢子,成为具有感染性的虫体。SGs是巴贝斯虫完成媒介中生活史所必须克服的最后一道屏障,且与中肠中所面临的障碍相似[8]。
软蜱和硬蜱的唾液组学研究多有被报道[53-60],其中研究表明AMPs,包括防御素、microplusin/hebraein(一种抗菌肽)、含Kunitz结构域的蛋白、脂质运载蛋白、蛋白酶等分子参与蜱的防御机制。尽管已知唾液腺分子对巴贝斯虫的传播尤为重要,但关于唾液腺分子对巴贝斯虫感染的影响的报道却十分少见。
在帕氏钝缘蜱(Ornithodoros parkeri)的唾液转录组和肩突硬蜱基因组中均发现一种假定的血清淀粉样蛋白A,在脊椎动物中,这种蛋白质在炎症反应的急性期发挥作用[10,53]。在抗蜱感染的牛中发现其血清淀粉样蛋白A表达增加表明其参与由蜱感染产生的应激反应[61]。当具环扇头蜱感染双芽巴贝斯虫时,血清淀粉样蛋白A基因的表达会因感染而上升,基因敲除导致微小扇头蜱和具环扇头蜱中感染水平分别降低66%和86%[10]。
在蜱卵巢、中肠和唾液腺中均存在钙网蛋白(Calreticulin)[10,62],其作用尚不清楚。有些研究表明其在唾液腺和唾液中的存在可能与逃避宿主防御反应有关[61-63],但不具备抗血栓和补体抑制功能[64]。此基因在感染双芽巴贝斯虫的具环扇头蜱中过表达。钙网蛋白下调对微小扇头蜱中的病原体感染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具环扇头蜱感染率影响不显著[10]。据此,认为钙网蛋白参与蜱吸血过程[10,65],且可能在巴贝斯虫感染过程中改变钙的代谢。巴贝斯虫可能和马泰勒虫(T.equi)(以前称为马巴贝斯虫(B.equi)一样,在侵入蜱细胞时需要钙离子。重组钙网蛋白免疫接种牛后,未能减少蜱对巴贝斯虫的感染,这可能是由于蛋白质的免疫原性低所致[65]。钙网蛋白抗血清也不能显著降低微小扇头蜱中的双芽巴贝斯虫感染[62]。其他分子,例如已经讨论过的TROSPA,也存在于蜱唾液腺,其可能是巴贝斯虫的受体。
唾液腺是分泌唾液的主要器官,也是传播巴贝斯虫的主要载体,在病原-载体-宿主相互作用中起到关键性的桥梁作用,因此了解并解析蜱唾液腺分子与巴贝斯虫的互作,将有利于发现或开发有效的药物及疫苗,阻断病原体向宿主的传播。
2 巴贝斯虫体内与蜱的互作分子
巴贝斯虫进入中肠后,由于大多数死亡或者退化,不易分离,因此巴贝斯虫在蜱虫期的分子研究相对困难,报道也较少。在蜱中肠内,仅少数巴贝斯虫发育成配子,进一步以合子形式穿透中肠上皮细胞。目前,已在牛巴贝斯虫基因组中鉴定出10个6-Cys基因(A、B、C、D、E、F、G、H、I、J),其中A、B、E、H、I和J基因在牛巴贝斯虫感染的蜱中肠中转录,并且基因A、B和E也在随后的牛巴贝斯虫动合子期转录,而基因C仅在动合子中转录表达。这些结果表明,巴贝斯虫6-Cys基因在有性阶段与蜱中肠存在一定联系[66]。近年,对牛巴贝斯虫的红细胞期和蜱虫期的细胞表面蛋白的蛋白组学分析和比较,表明有两种蛋白(BBOV_I002220和BBOV_IV006250)在蜱虫期表达量显著增加,且在双芽巴贝斯虫中呈现相似的表达模式[67]。预示这两种蛋白为巴贝斯虫在蜱体内存活所必须,与蜱的互作存在一定关系。此外,双芽巴贝斯虫在有性繁殖期,即蜱虫期特异表达一种转甲基酶(BBBOND_0204030),但在红细胞期无表达,因此,此基因即可作为蜱感染巴贝斯虫的分子标记,也可为蜱-巴贝斯虫互作提供新的信息[68]。此外,研究发现双芽巴贝斯虫的HAP2在体外诱导的有性繁殖阶段及感染的蜱中均有表达,而在红细胞期不表达,并且抗HAP2特异性抗体能够在体外阻断合子的形成,这说明该蛋白可能与蜱存在互作关系[69]。
了解巴贝斯虫在蜱虫期差异表达的分子,可以为解析蜱与巴贝斯虫的互作机制提供前期信息,也为疫苗的研发提供新的信息和潜在的靶点。
3 小结
目前,随着蛋白质组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蜱与病原体的相互作用被发掘出来,但是关于蜱-巴贝斯虫的互作机制信息却相对较少。而阻断蜱载入和传播巴贝斯虫的关键是新疫苗的研发,而新疫苗的研发需要筛选出潜在的候选抗原。本综述收集蜱与巴贝斯虫互作相关分子的相关信息,为后期筛选与鉴定新的候选抗原提供基础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