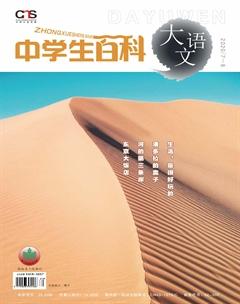我最敬爱的人
周智渊

从小我就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军人,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是国防科技大学第一批科研前线人物;是新中国第一代教授、工程师、专家,是我国第一台YH-F2银河仿真Ⅱ型亿次电子计算机副总设计兼硬件主任设计师。有他一柜子的勋章奖状为证,有他蒙了尘的锁进木柜的绿色军装为证。即使他眉毛花白,布满皱纹,我也是知道的。他是我的爷爷,我敬他,爱他。
从小我就觉得,爷爷是一位迟暮的英雄,喜欢唠叨过去的事情,喜欢一个人在书房一遍遍轻抚泛黄的奖状和老旧的党徽,喜欢天天催我好好学习报效祖国,却又沉默、古板,只会偷偷在战友的葬礼上红了眼眶,擦拭眼角。
我很小的时候,爷爷身体就不好,他的腿疾是几十年来做科研一动不动造成的。他的健忘是几十年高度用脑,脑力衰竭造成的。他的脸色很白,眉毛也很白,皱纹很多,背也很弓。可他走起路来是那么健步如飞,写出的字是那么苍劲有力,他看起来是那么不服老,天天嚷着他没老,他还能再干50年。
他常常教导我要以祖国为荣,好好学习,报效祖国,像每一个望子成龙的长辈,语重心长,满怀厚望。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情是那么肃穆,像在传递什么神圣的职责。以至于现在,我还能清晰地听见,他平缓而有力、铿锵而温和的略沙哑的声音,说到激动处微微上扬的语调;我还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粗糙的大手抚摸过我的发丝留下的余温;我还能清晰地看见,他坐在红木靠椅上,穿着白色的衬衫,扣子被系得整整齐齐,身体前倾,嘴角含着笑,看着我的眼睛,眼神慈祥而认真。
小学的时候,他送我去上学,他温热的大手牵着我的小手。我在操场上做操,他就在操场旁默默地看着。当国歌奏响的时候,红领巾系在我的脖颈上,鲜红的颜色在秋阳的映照下格外神圣明艳,穿着蓝白色校服的我们,腰杆挺直,敬上我们稚嫩生涩的少先队队礼。阳光是初生的希望,我们就像初升的朝阳,有着萧瑟的秋所不具有的蓬勃生气。但我看见操场外,歪脖子的老树旁,萧瑟的秋风里,落叶卷了一地,一位年老的军人也挺直了脊背,颤抖着敬了一个军礼,军礼标准而娴熟,像无数次在梦里反复练习过一般,像在回忆里不断翻腾过一般。他的眼中,是五星红旗在迎风飘扬,是心中不灭的信仰与光,几十年不曾变过。
我曾无数次想过,爷爷年轻时,乌黑齐整的寸头,炯炯有神的目光,一身笔挺的绿色军装,英姿勃发,风华正茂,在祖国的大地上无数次地敬上光荣标准的军礼,像一棵青翠挺拔的松,生长在红旗飘飘的地方,庄重而坚定,神圣而英勇,是怎样地飒爽与豪迈,是怎样的中国好男儿。我多想能亲眼看见这一幕。
可是我不能,我甚至连他仅剩的一点光阴都握不住。他突然倒下了,倒得那么突然,从事一辈子科研工作、知识渊博的学者,大脑重度混沌,连事也记不清楚,连人也认不全,连话也说不出,只能用口型哆嗦地喊着我的小名。我常常躲在爷爷的病房外哭泣,祈求上苍能再施舍给我们一点时间,哪怕是能让爷爷再亲口喊我一声乳名也好。
我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风很轻柔,空气也暖,金黄的阳光斜斜地泻下,照得白色的瓷砖划下极浅极浅的纹路。安静得可怕的病房一下變得那么温暖,一如当年爷爷的书房。爷爷穿着病号服,蓝白衫下是他枯瘦冰凉的手,紧紧地握住我温热的手。他的目光就那么轻轻软软地瞥向我,让我觉得一眨眼爷爷的眼睛就会闭上。我说,我保证,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一定会考上一所优秀的大学,不给爷爷丢脸,不辱没爷爷的名号。他的嘴角一动,艰难地张着双唇,什么都没说,又什么都说不了。我又说,我一定会报效祖国,为国争光。我边说边挤出一个笑容,眼里突然盈满了热泪,因为我看到爷爷颤抖地举起右手,向我敬了一个最漂亮标准的军礼。
至此,葬礼上遥遥地见过一面,这就是爷爷和我的永别了。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是我的爷爷,中国的军人,光荣的共产党员,是无数为祖国默默坚守在科研前列的先辈中的一员。
他是我的爷爷,是我最敬爱的人,我敬他,爱他!
点评
本文看似信马由缰,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我”记忆中的爷爷,然而形散而神不散,爷爷衰老的体魄与过去辉煌的功绩,与他至死方休的爱国热忱,与初升的朝阳一样的“我”,甚至与爷爷年轻时候英姿勃发的模样形成的对比是那样惊心动魄,时光流逝的无情、人类信念的坚定、新旧更迭的传承在这一组组对比中,在“我”对爷爷爱的凝视中被充分展现了出来。文章最后两段情感喷薄而出,就像在枯木上长出的绿芽,让人在伤感中又生出无限的希望,这正是血脉的传递,更是信仰的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