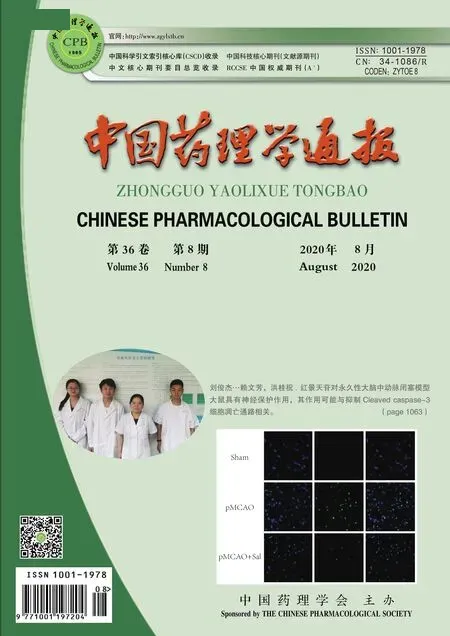肺动脉高压动物模型研究进展
孙姝婵,方莲花,杜冠华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物研究所,北京市药物靶点研究与新药筛选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50)
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hypertension,PH)是指肺动脉压力异常升高的一种血流动力学和病理生理状态。按临床、治疗和病理生理学特点,肺动脉高压分为5类:动脉型PH、左心疾病导致的PH、肺病和/或缺氧导致的PH、肺动脉阻塞导致的PH、未知因素导致的PH[1]。尽管不同亚类PH的病因不同,但都表现出相似的病理变化,包括肺血管内侧肥大、内膜增生和纤维化、外膜增厚伴随中度血管周围炎症细胞浸润、丛状扩张性病变以及原位血栓形成,肺血管不断增生、重构使血管部分闭塞,肺血管阻力增加,导致进行性右心衰竭和功能衰退,甚至死亡[2]。
REVEAL注册研究的数据显示,肺动脉高压新诊断患者生存率为61.2%[3],PH可以是特发性也可以继发于各种病症,有证据表明,PH使各种常见疾病复杂化[1],因此迫切需要探究PH的发病机制和治疗策略。动物模型是实验研究的重要媒介,但目前PH动物模型仍不能全面模拟人体的发病特点,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界定,各种造模方法仍需优化和改进。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外PH动物疾病模型制备方法进行总结,介绍不同模型的原理及制备方法,分析其优缺点以及对临床PH的模拟性。
1 野百合碱诱导模型
野百合碱(monocrotaline,MCT)是从野百合种子中提取的一种吡咯烷生物碱,它能够引起肝毒性和肺动脉高压。
MCT引起PH的机制在于其被肝脏的混合功能氧化酶转化为野百合吡咯,野百合吡咯可以在肺血管内皮细胞中形成DNA和蛋白加合物,从而导致细胞周期停滞,使内皮细胞凋亡,血管内膜剥脱,从而引起肺动脉平滑肌细胞进行性增殖和肺血管重塑[4]。MCT模型的特征在于内皮细胞凋亡和血管周围炎症,这与人肺动脉高压发病的生理病理机制类似。MCT模型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肺血管重塑的过程以及炎症反应在其发病机制的重要作用。大鼠是目前MCT模型的首选物种。
MCT模型主要经颈背部或腹部单次皮下注射1%MCT溶液,极少数采用腹腔注射。MCT诱导的肺动脉高压程度取决于MCT的剂量[5],广泛采用的剂量主要有50 mg·kg-1和60 mg·kg-1,一般2 周后造模成功。通过血流动力学指标判断模型是否成功,主要指标有肺动脉平均压力(mean pulmonary arterial pressure,mPAP)、右心室收缩压(right ventricular systolic pressure,RVSP)、右心室肥厚指数(right ventricular hypertrophy index,RVHI)。有研究表明这两种剂量诱导的PH模型RVSP与死亡率相当,但50 mg·kg-1对肺中、小动脉中膜厚度改变更为明显[6]。
MCT模型具有技术简单、可重复、时间短、稳定性好、低成本等优点。MCT能引起内皮功能障碍,较好模拟临床上炎性相关的PH,但对重度血管增生性PH的模拟有限。另外,MCT诱导的大鼠通常死于MCT诱导的肺毒性、静脉阻塞性肝病和心肌炎,而不是死于肺动脉高压[7]。由于MCT模型形态学变化发展得非常快并且不易通过治疗干预来预防,所以作为临床PH模型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 慢性低氧性模型
低氧性肺动脉高压(hypox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HPH)是临床常见的一类PH,常由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睡眠呼吸暂停、高原病等导致。慢性缺氧(chronic hypoxia,CHP)会引起内皮细胞损伤,以致相关舒缩因子失衡,增加肺血管收缩反应并促进血管重塑,最终发展为肺动脉高压[8]。近年来缺氧性肺血管收缩和肺动脉重塑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内皮素-1、一氧化氮、环氧合酶和腺嘌呤核苷酸途径。
CHP模型需将动物置于低氧舱内,通入N2和O2混合气体,通过控制器将O2浓度控制在(10.0±0.5)%(体积分数),缺氧时长2~8周,喂养期间定期清扫并补充食物和水。大量研究证明,持续缺氧或间断性缺氧(约8 h·d-1)均可发展为PH,并且低压低氧舱或常压低氧舱也均可成功制备模型。
慢性高碳酸血症常见于缺氧性肺病患者,并且根据临床观察,除非同时存在高碳酸血症,否则低氧性肺病很难发展为肺动脉高压,可见二氧化碳分压与肺动脉压力密切相关。因此,吸入低氧伴高二氧化碳混合气体制备PH动物模型更符合临床患者情况。将动物置于常压低氧高二氧化碳氧仓中,仓内氧浓度维持在9%~11%,二氧化碳浓度维持在5%~6%,每天8 h,每周6 d,饲养4周[9]。
通过慢性缺氧诱导肺动脉高压,易于操作,并且牛、鼠、羊、猪都可以建立CHP模型。但慢性缺氧反应在物种间存在差异,即使是同一物种随着年龄、性别的不同,反应也会受到显著影响,最常用的动物是大鼠和小鼠[10]。由于缺氧诱导是可逆的,因此较难模拟临床重症PH,并且不能完全模拟PH的血管损伤情况。此外该方法对设备要求很高,很难同时进行大量动物实验,尽管如此,这两种模型都为体内研究PH发病机制提供重要的疾病模型。
3 栓塞性模型
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是由内源或外源性栓子阻塞肺动脉,引起肺循环和右心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征[11]。慢性血栓栓塞型肺动脉高压(chronic thromboembol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CTEPH)是PH的一种独特形式,是急性肺栓塞或肺动脉原位血栓形成的长期后果,表现为肺动脉增大、内膜受损及周围血管阻塞[12]。
从广义上讲,此模型分为2类:注射血栓或者异物。
血栓模型是从自体或供体(异源)动物获得血液样本在体外凝结成血栓,然后再将其注入实验动物中。注射血栓可较好表现急性肺栓塞的病理生理情况,但是由于离体血凝块的大小和体积均不规则,难以保证肺血管阻塞的程度和持续性,而且自体PE模型还需要进行2次手术,在大鼠、兔或猪中会产生循环休克,操作复杂。
与此相比,很多实验室已采用将惰性材料注入颈静脉的方法来模拟肺栓塞,包括大鼠、兔、狗、羊、猫、猪都可以建立CTEPH模型。其中大鼠模型较为常见,体质量(350~500) g,通过右颈静脉注射聚苯乙烯微球(15~25 μm,130万~195 万个珠/100 g)。该方法可以控制进入肺部的微球数量,较准确地增加肺血管阻力,还避免发生免疫反应、大鼠纤维蛋白溶解率高等问题[13]。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微球是阻塞在肺部毛细血管前小动脉中,而不是临床上通常观察到的阻塞在近端肺动脉。
栓塞性PH模型引起的血流动力学变化与临床一致[13],产生的促凝状态、血栓前变化可作为临床避免血栓栓塞及外科手术等干预机制的实验对象[14]。
4 手术分流模型
肺动脉高压是先天性心脏病的常见并发症,高肺血流量引起的肺血管重构是其重要的病理过程。手术分流可以增加肺部血流量,其中体循环动脉-肺动脉之间的分流和动-静脉之间的分流是较常用的左向右分流型肺动脉高压建模方法。
4.1 体循环动脉-肺动脉之间的分流由于大、中动脉压力高于肺动脉压力,通过压力阶差在两者间建立分流可使体循环血液分流至肺循环,使肺循环血液增多。该方法多采用犬、猪、羊等大型动物。包括诱导主动脉和肺动脉、左颈总动脉和肺动脉、左锁骨下动脉和肺动脉分流等。尽管能更好的模拟临床上慢性心脏病相关的PH,但由于开胸手术难度较大、创伤大、饲养大体积动物困难及成本等问题,因此较难推广和应用。
4.2 动-静脉(A-V)之间的分流利用动静脉间较大的压力差,分流后动脉血流入静脉,使流回右心的血液增加,继而使右心射入肺动脉的血液增多。该方法多采用兔、鼠等小型动物。大鼠多采用主动脉-腔静脉分流;兔多采用颈总动脉-颈静脉分流;有研究首创通过腹主动脉-下腔静脉分流建立小鼠的PH模型[15],小鼠模型为研究PH的分子机制提供了更多机会。与大中动脉-肺动脉间的分流相比,A-V分流具有死亡率低、侵入性低、通畅性较高、成本低等优点。
常见的PH动物模型主要是慢性低氧模型和野百合碱诱导模型,尽管这些模型增加了对PH肺血管重塑机制的理解,但与临床的发病机制和疾病表型不同。随着PH机制研究从单纯的血管收缩转变为血管增生,血液分流的作用被认为在PH的发展中至关重要。
5 遗传修饰模型
由遗传因素导致的肺动脉高压称为遗传性肺动脉高压(heritable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HPAH),主要有家族性肺动脉高压(familial pulmonary artery hypertension,FPAH)和伴基因突变的特发性肺动脉高压(idiopathic pulmonary artery hypertension,IPAH)[16]。在过去的世界肺动脉高压专题讨论会(world symposium on pulmonary hypertension,WSPH)中,科学界不断揭示PH相关基因:BMPR2、ALK1、ENG、SMAD9、SMAD1、CAV1、KCNK3、TBX4、E2F2AK4、GDF2、ATP13A3、AQP1、SOX17[17-18]等,增强了对PH复杂遗传基础的理解。
5.1 基因敲除模型据文献报道,约有70%~80%的FPAH和10%~20%的IPAH病例是由BMPR2突变引起的[19]。有研究证明BMPR2突变类型与PH敏感性之间存在基因型-表型关系[20]。去除外显子4、5的BMPR2基因敲除小鼠(BMPR2△Ex4-5/+)会表现出轻度PH,损害肺血管系统对长时间低氧的重塑能力[21]。还有去除第2个外显子的BMPR2基因敲除小鼠(BMPR2△Ex2/+),这种小鼠对低氧反应性增加[20]。除此之外,有研究采用平滑肌特异性强力霉素诱导BMPR2第899位氨基酸的突变(SM22-rtTA x TetO7-BMPR2R899X),产生了非常接近人类的PH[22]。
除了BMPR2基因敲除模型,还有其他基因敲除模型,如敲除血管活性肠肽的小鼠(VIP-/-)自发形成中度至重度PH;敲除载脂蛋白E的小鼠(ApoE-/-)可自发为PH并伴有肺动脉肌肉化;内皮素受体B(ETB)敲除模型,当内皮素受体表达降低会增加肺内皮素水平,从而促进PH。
5.2 基因过表达模型5-羟色胺转运蛋白(5-hydroxytryptamine transporter,5-HTT)的过度表达是PH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因素。首个5-HTT过表达转基因小鼠模型是通过一个人工染色体对5-HTT的C端血凝素抗原决定簇和内部核糖体进入位点的一个lacZ报告基因进行修饰[23]。之后有研究采用平滑肌启动子SM22建立5-HTT基因过表达模型(SM22-5-HTT+),这种小鼠肺部钾离子通道表达水平降低,并且5-HTT表达增加的水平非常接近于人PH[24]。
常用的还有过表达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的转基因小鼠,对研究IL-6在PH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抗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有研究采用过表达血管生成素1(angiopoietin-1,Ang-1)建立大鼠转基因模型,Ang-1的表达水平与PH的严重程度成正比[25]。研究表明大约5%的S100A4/Mts-1过表达的小鼠发生肺血管重塑,可观察到其他模型没有的丛状病变[26]。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制备PH模型,能从动物整体水平研究目的基因的表达调控规律,加深了我们对PH病理生物学及治疗学的认识,但是该方法存在技术难度大、动物模型品系过少(主要是小鼠)等缺点,仍需进行多方位的改进。
6 混合因素诱导模型
单一因素诱导模型会显示人类PH早期阶段的特征,但与单一因素相比,混合因素诱导的疾病模型与人类重度PH的关联性更好。其中SuH模型最具有代表性,即采用C57BL/6小鼠通过单次皮下注射VEGFR2抑制剂SU5416(20 mg·kg-1)并将其置于常压低氧室(10%FiO2),缺氧3周,若进行长期实验,可每周注射一次SU5416[27]。与单纯低氧诱导相比,该模型出现新内膜增厚和丛状病变,并且对其他器官血管没有影响,避免其他因素干扰。
除了利用低氧联合SU5416造模,也有研究采用低氧联合MCT模拟重症PH,还可观察到血栓性病变[28]。除此之外,切除左肺,使血液仅在右肺循环,手术后1周内注射MCT或SU5416[29],肺血流量增加和内皮功能障碍联合诱导新生内膜形成的重度PH,其局限性是需要一定的手术技能。
多因素干预提高了模型的成功率,但也增加了动物的死亡率。由于临床诊断通常是重症,混合因素诱导模型更有助于发现肺循环血流动力学和结构改变的相关治疗靶点。
7 结论和展望
PH的异质性和治疗难度对动物模型的使用和改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PH动物模型的发展主要经历了2个阶段[30],第1阶段是肺动脉非特异性内膜和外膜增厚,主要包括经典模型(即低氧和MCT);第2阶段是发生丛状病变,血管逐渐闭塞,肺动脉压进行性升高,即手术分流、栓塞模型、遗传修饰以及混合因素诱导造模。本文概述了PH研究中的不同动物模型,同时重点关注它们与PH患者的相关性,有利于科研工作者根据疾病的不同阶段选择合适的动物模型,取得理想的造模效果。同时,也为进一步阐明PH的病理机制、提高PH患者的预后、探索新的治疗靶点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