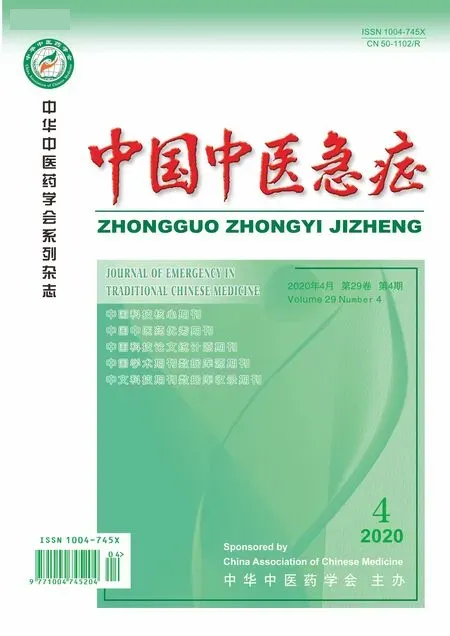叶天士基于“脾体阴用阳”理论论治脾胃病经验探析
姚鹏宇 王建博 赵家有
(1.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 沈阳 110847;2.南昌大学,江西 南昌 330006;3.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 100700)
脏腑体用理论是中医学中重要理论之一,脏腑体用学说是以体用关系阐述脏腑特性、脏腑关系、调治脏腑的内容。叶氏于脏腑体用理论颇有见解,具体如论述并运用“肝体阴而用阳”及“脾体阴而用阳”,然后世对于叶氏论肝之体用有所阐发体会,而于叶氏论脾之体用却少见发挥。研读叶天士医案,可知叶氏于脾脏之生理、病理不乏论述,并以“脾体阴用阳”概况脾脏特性,基于“脾体阴用阳”理论指导组方遣药,用于痰饮、肿胀、脘腹不适等多种疾病。叶氏一生勤于诊务,留世著作多为门人整理,其中以《临证指南医案》最具有代表性。笔者现以《临证指南医案》为参考整理叶氏基于“脾体阴用阳”理论指导临床的经验,以冀发掘叶氏学术思想。
1 理论探析
体用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一般“体”指客观存在的实体,“用”指体的作用和机能[1]。早在《素问·五运行大论》就有关于体用的内容。体用一说与脏腑阴阳结合首见于《景岳全书》[2]。“脾体阴用阳”这一概念首见于清·喻昌《医门法律·中寒门方·论附子理中汤》“人身脾胃之地,总名中土,脾之体阴而用则阳,胃之体阳而用则阴”。这段话简明扼要的概括了脾的病理生理特性,为治疗脾病提供了临床指导思想[3]。脾体阴用阳是将体用理论与阴阳学说相结合,借助体用理论对物质与功能联系性阐述、阴阳的对立统一思维用以诠释脾脏生理特性的理论,既体现了脾脏结构与功能的密切联系,也说明了二者对立统一、互根互用的关系。叶天士立论“肝体阴而用阳”众所周知,然其于脾之体用,亦有论述,独具法眼。清·张璐《张氏医通》言“胃之土,体阳而用阴;脾之土,体阴而用阳”[4],对脾胃体用做了细致论述,而叶天士曾师从张氏学习,其理论源流与此亦有关联。
《临证指南医案·卷六·疟》载“论脾为柔脏,体阴用阳”,叶氏基于“脾体阴用阳”理论于脾病之论治立法组方指导用药之医案颇多。叶氏的脾体阴用阳理论既强调脾脏特点,也关注与其他脏腑关系,其内涵丰富,值得推敲。1)与胃腑鉴别。脾体阴用阳的出现多伴胃体阳用阴。“脏腑分理”学说是在脏腑联系的前提下,对脏腑差异性的强调,脾胃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脾胃分治根源于《黄帝内经》,后经历代医家不断发展完善,至清代叶天士重视胃阴,倡导脾胃分治,使脾胃学说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5]。脾胃者一脏一腑,一阴一阳,叶氏云“凡六腑属阳,以通为用,五脏皆阴,藏蓄为体”,明脏腑二者体用之不同,华岫云言“今观叶氏之书,始知脾胃当分析而论。盖胃属戊土,脾属己土,戊阳己阴,阴阳之性有别也。脏宜藏,腑宜通,脏腑之体用各殊也”,脾胃二者体用有别,可知根据脏主藏的特点,为与腑相鉴别,提出“脾体阴而用阳”“夫胃是阳土,以阴为用”之生理特点。2)指导临床辨证。《灵枢经·本脏》云“五脏者,固有小大,高下,坚脆,端正,偏颇”明确了五脏解剖结构的差异性。中医脏腑内容是建立于直观解剖的基础上,在诠释“体”结构的基础上,涉及了对“用”功能的论述,结构的特异性是为功能表现的特异性服务的[6]。脾体阴用阳,明确了脾实体结构与生理功能的联系性,也执简驭繁的,依据“脾体阴用阳”将脾的辨证分为“体”病、“用”病两大类型,类似于现代医学的器质病变与功能病变。对于脾之功能,形质损伤,精确把握,而各有立法,同时功能病变多见于疾病早期,较为普遍,形成了脾病多病其用,以运化衰惫、生化乏源最为多见的病理特征。3)指导用药。根据脾脏体阴用阳的生理特点,将临床脾脏治法,分为补泻两途、体用两类,共4种,以指导临床用药,叶氏曾云“王道固难速功,揆之体用,不可险药”,临床将治脾药分为“体药”“用药”两大类,又在体用基础上分补泻之法,能将繁杂多样的脾药归于系统。《清史稿》载“(吴瑭)学本于桂”,吴鞠通是叶氏学术经验的继承者,思想理论的践行者,吴鞠通很好地将叶天士散见于医案中的理法方药进行总结整理,《医医病书·五脏六腑体用治法论》中对脾体阴用阳中“体药”用药介绍就是例证。吴氏言“脾为足太阳,主安贞,体本阳也;其用主运行则阳也。补阴者,补其体也,如桂圆、大枣、甘草、白术之类;补阳者,补其用也,如广皮、益智仁、白蔻仁、神曲之类”[7]。叶氏云“脾为柔脏,惟刚药可以宣阳驱浊”,脾体属阴为柔脏,其病多为阴邪所袭,如寒、湿、痰饮、浊毒等,同气相求最易病脾,故以刚治柔,阳以制阴,用病多阳药、体病多阴药。叶氏曾云“胃以喜为补”,这一观点不仅仅适用于胃,包括脾等诸脏腑多如是,脾喜芬芳,恶郁滞。4)其他。“五脏皆具阴阳气血精津液”是中医的重要观点,意指五脏具有相同的物质基础。基于“脾体阴而用阳”结合“五脏皆具阴阳气血精津液”这一观点从脾论治多种疾病,可使临床治疗更具有针对性,如叶氏五行治法中的培土生金法之应用即根据气血阴阳之差异,分为培脾阴养肺阴、补脾气实肺气等多种类型,针对病机不同,而各补不足。气化是脾之功能,血、精、津液则是除脾脏实体外,阴体的重要物质,脾的功能的表达依赖于阴体的物质基础,而阴体的和谐状态又以功能正常为前提,治体与治用是密切联系的,临床在治疗上主次分明的兼顾体用阴阳也是中医整体观的表现。而这一思想在叶天士用药组方中,屡见不鲜。
2 临证经验
2.1 治则治法
治则治法是建立在病因病机的基础上,辨证与方药结合的桥梁,是理法方药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脾体阴用阳”的具体应用必须通过理法方药的一贯性规范,才能更好地用于临床。明确叶天士据理立法的思路内容,才能更好地掌握理法,指导方药实践。
2.1.1 治脾兼胃 《素问·太阴阳明论》“脾与胃以膜相连”从解剖学联系出发,为脾胃一体、脾胃同治奠定了基础。“夫脾胃为病,最详东垣,当升降法中求之”,叶氏于脾胃治法多遵东垣,却又别于东垣,既重视脾胃密切联系,又主张“治胃与脾迥别”,且脾胃分理为叶氏临证特色之一。叶氏治疗脾胃病时指出,脾胃之病,无论是其生理特性、病因病机还是治疗方法等,均须辨证分论,分而治之[8]。《临证指南医案》就有“古称胃气以下行为顺,区区术甘之守,升柴之升,竟是脾药”“夫胃为阳明之土,非阴柔不肯协和,与脾土有别故也”“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叶氏根据脾胃脏腑特点,在脾胃分论、脾胃合论二者之间,寻求契合,多以“运脾疏胃”为治法,既兼顾二者联系,又强调二者差异,此法名医汪逢春于湿温病证治亦多采用。“脾体阴用阳”补益以助脾运化之功达其用、“腑宜通即是补”疏理以复胃腑通畅之性补其体,胃通则脾运无滞,脾旺则胃纳无碍。根据不同的病机特点以运脾、疏胃各为主次,治疗多种疾患。如《临证指南医案·脾胃》载“周四二脉缓弱,脘中痛胀,呕涌清涎,是脾胃阳微。得之积劳,午后病甚,阳不用事也。大凡脾阳宜动则运,温补极是。而守中及腻滞皆非,其通腑阳间佐用之。人参、半夏、茯苓、生益智仁、生姜汁、淡干姜,大便不爽,间用半硫丸”。叶氏明确了温补运脾、疏理通胃主次分明的脏腑结合治法。
2.1.2 治肝培脾 肝脾各自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特点,决定了两者密切密不可分的联系,主要表现为生理功能的相互为用,病理状态的相互传变,临床诊疗过程中的肝脾同治[9]。肝脾生理病理关系密切,为医家之共识,如《黄帝内经》载“土得木而达”,《金匮要略》云“见肝之病知肝传脾”,论述颇丰,叶氏亦有“郁必伤脾”“肝病既久,脾胃必虚,风木郁于土宫”等论述肝脾密切联系之论。治肝培脾为叶氏治疗肝病犯脾之大法,治肝之法又有和肝、制肝、泄肝、疏肝四法。“肝为刚脏,当济之以柔药”的理论亦为叶氏独创学说之重要部分[10],亦是肝病治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和肝培脾适用肝气失调,阻脾之运,以四君培土,佐以炒山楂、炒乌梅、木瓜、生白芍等酸敛柔肝缓急;制肝培脾适用肝之气逆,犯克脾土,多以吴茱萸加芍药治之;泄肝培脾适用肝木火犯脾,以补脾之法,佐以川楝子、黄连、牡丹皮等清热泻火品,少入补脾阴之品;疏肝理脾适用于肝郁脾虚,以四君,佐以陈皮、青皮、柴胡等理气之品。叶氏临证多兼顾脾之体用,杂合四法而治。如《临证指南医案·木乘土》载“朱氏嗔怒动肝,气逆恶心,胸胁闪动,气下坠欲便。是中下二焦损伤不复,约束之司失职。拟进培土泄木法,亦临时之计”以乌梅丸加减治疗,是从泄肝出发以补土。
2.1.3 温肾助脾 叶氏云“夫脏寒生满病,暖水脏之阳,培火生土是法”为脏寒、水肿、胀满等病立益火补土之法。益火补土为临证之大法,其说有以温心阳、温肾阳各说种种,叶氏遵景岳之意,以温肾阳助脾阳为用,提出“自古治肾阳自下涵蒸,脾阳始得运变”“大凡脾阳宜动则运,温补极是”,倡导命门学说,其常用方有金匮肾气丸、四神丸、安神丸等。统计叶天士治疗泻利360则医案将治法加以归纳为十法,其中运用温补脾肾法的就有72则[11]。《临证指南医案·湿》载“庞四四湿久脾阳消乏,中年未育子,肾真亦惫,仿安肾丸法。鹿茸、胡芦巴、附子、韭子、赤石脂、补骨脂、真茅术、茯苓、菟丝子、大茴香”。宗安肾丸意,温肾阳补脾阳,以助运化。脾与肾之间的相互联系包括脾肾先后天互根、精气互生、阴阳相关等多个方面,不拘于补阳助阳一途,然叶氏于温肾阳助脾阳一途应用最广。
2.1.4 温运脾阳 脾阳,指脾的运化功能及在运化活动过程中起温煦作用的阳气,是人体阳气在脾脏功能方面的反映[12]。叶氏云“脾阳式微,不能运布气机,非温通焉能宣达”“论脾乃柔脏,非刚不能苏阳”论述脾阳不足之病机及治法。脾以阳为用,《临证指南医案》于脾阳为病之验案40余则,可见叶氏对脾阳之重视,其治法有温通脾阳、健运脾阳与醒脾阳三法,三法用药皆以刚剂,其中温通脾阳以干姜、半夏、厚朴、附子、白术、桂枝等药组方,姚亦陶云“脾阳衰者,术附必投”;健运脾阳则以平胃散、半夏汤、苓桂术甘汤等方为主,华岫云谓之“若脾阳不运,湿滞中焦者,用术、朴、姜、半之属以温运之,以苓、泽、腹皮、滑石等渗泄之”;醒脾阳一法,多对于湿邪遏脾、脾虽衰而尚有转化之机,叶氏云“草果以醒脾”,陶汉华教授受叶氏启发,而立醒脾法用于脾胃病之证治,疗效颇佳。三法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总以恢复脾脏运化之能为主,助脾阳用为目的。
2.1.5 滋润脾阴 脾阴是脾中水谷精微所化生的营血、津液、脂膏等精微物质,是脾进行生理活动的重要物质[13]。研阅叶氏医案,有“胃阴虚”“胃阳虚”及“脾阳虚”之论述,而唯独缺乏“脾阴”之治。唯一的解说应该是医案资料的阙佚不全[14]。《临证指南医案·嘈》华岫云按语提及“脾阴”,然观叶氏之案脾阴用药亦不乏枚见。具体用治脾阴伤之证,药用最多的为麦冬、竹叶、甘草、沙参、扁豆、石斛等。此类药物皆为性味甘淡、甘缓、甘酸之物,取其甘淡益阴,甘缓和中,甘酸济阴之功[15]。观品味之性,多属叶氏所谓之柔剂,脾阴为脾之津液,滋阴必以配阳,其常佐以通补胃腑、健运脾气之法,而以甘药为主,甘守津还用意。
叶天士于“脾体阴用阳”的应用虽以多用于脾胃病,然在其他疾病中应用亦十分广泛。如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首提“上下交损,当治其中”,开启了虚损证治的新法门,而治中则又分脾胃两途,若从脾论治,多遵循“脾体阴用阳”特点,组方立法,兼顾整体。“脾体阴用阳”理论是对脾脏特点的概括,凡病无论直接或间接涉及脾脏,均须着眼此理。
2.2 代表方剂
复方疗疾,是根据病情病因分析病机,结合理论,依据病机、理论确立治法,再在治法的指导下组成切合病情需要的方剂。中医理论是整个过程的关键,而组方遣药是落实治疗理念的最后步骤。叶氏基于“脾体阴用阳”理论,指导临床,所用方剂颇多,略举数方,浅述如下。
2.2.1 健运脾阳——大半夏汤 叶氏云“阳气健运不息,阴浊痰涎,焉有窃踞之理”,反映了叶氏运用大半夏汤之思想,与“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顺应脏腑特性施治的观点相合。参照叶氏临证应用,方中“非半夏之辛、茯苓之淡,非通剂矣”,半夏、茯苓通浊行滞,白蜜甘寒清养为补益脾胃阴分。叶氏云“宣通补方,如大半夏汤之类”,此方既可宣通阳明,又可健运太阴,体用并理,如《临证指南医案·脾》“朱妪目垂气短,脘痞不食,太阴脾阳不运,气滞痰阻。拟用大半夏汤”。大半夏汤健运脾阳,通浊祛痰,以达脾用为法。
2.2.2 宣补脾气——六君子汤 叶氏云“六君子汤之健脾理痰,多是守剂,不令宣通”“六君子宣补方法”,可知六君子一方是宣补并用,以补为主的方剂,方中陈皮、半夏为宣通之药,其余均是守补之品,以补益脾土,健运脾用为法。如《临证指南医案·木乘土》载“张二九脉小弱,是阳虚体质,由郁勃内动少阳木火。木犯太阴脾土,遂致寝食不适,法当补土泄木”。以六君子加牡丹皮、桑叶。丹桑相配为叶氏常用清泄肝木之药对,二者合用,有清泄少阳火热,轻解少阻之郁及制约肝阳之亢3种功效,清宜兼备,合合血之意,符肝胆之性[16]。
2.2.3 健脾化饮——苓桂术甘汤 叶氏遵仲景立论“外饮治脾”“饮邪当以温药和之”,以苓桂术甘汤从温运脾阳论治痰饮。邹滋九谓之“取仲景之苓桂术甘汤、茯苓饮、肾气、真武等法,以理阳通阳及固下益肾、转旋运脾为主”。方中“术甘之守,竟是脾药”“茯苓通阳”、桂枝温运,方中补通并施,暗合脏腑特性,脾胃兼理,“夫湿属阴晦,必伤阳气”“湿属阴邪,阳不易复”,以阳驱阴。《临证指南医案·痰饮》载“王三二脉沉为痰饮,是阳气不足,浊阴欲蔽,当以理脾为先。俾中阳默运,即仲景外饮治脾之意。苓桂术甘加半夏、陈皮水泛丸”。证属外饮无疑,温运健脾,驱阴化饮。
2.2.4 敛养脾阴——人参乌梅汤 一般认为《伤寒论》中用麻子仁丸治脾约证是脾阴理论的体现。《伤寒论》中顾护津液的思想为脾阴虚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17]。《黄帝内经》“欲令脾实……宜甘宜淡”“酸甘化阴”明确了补脾阴的用药特点。人参乌梅汤系叶氏自拟补脾阴方(人参、山药、乌梅、炙甘草、木瓜、湖莲),治疗痢久阴伤、口渴微渴[18]。亦可加炒山楂、白芍、麦冬等酸甘敛阴之品。《临证指南医案·痢》云“周五十痢后气坠,都主阴伤。但嗔怒不已,木犯土,致病留连。摄阴之中,聊佐和肝”,以熟地黄、茯苓、炒山楂、炒乌梅、木瓜五味养脾阴健脾用,营血津液皆为脾体之阴,久病伤血,故养血滋阴,实其体。
胃苓汤、四兽饮、理中汤等方,亦为叶天士常用方,多用于健运脾阳,消痰散饮,方中稍佐木瓜、芍药等酸甘化阴之品,以柔润兼顾脾阴。
3 验案举隅
《临证指南医案·疟》载祝氏,此劳伤阳气,更感冷热不正之气,身热无汗,肢冷腹热,自利,舌灰白,微呕,显然太阴受病。诊脉小右濡,不饥,入夜昏谵语,但如寐,不加狂躁。论脾为柔脏,体阴用阳,治法虽多,从未及病,当遵前辈冷香、缩脾遗意。方以:人参、益智仁、茯苓、新会陈皮、生浓厚朴、薏苡仁、木瓜、砂仁。又脉右弦,来去不齐,左小弱,舌边红,舌心白黄微绉,鼻冷四肢冷,热时微渴,不饥不思食。前议太阴脾脏受病,疟邪从四末乘中,必脾胃受病。鼻准四肢皆冷,是阳气微弱,因病再伤,竟日不暖。但形肉消铄,不敢刚劫攻邪,以宣通脾胃之阳。在阴伏邪,无发散清热之理。方以:人参、草果、炒半夏、生姜、茯苓、新会陈皮、蒸乌梅肉。二帖后加附子,后又加牡蛎”。
按语:外感内伤合而为病,症见“身热无汗,肢冷腹热,自利,舌灰白,微呕”“不饥,入夜昏谵语,但如寐,不加狂躁”,辨证确属太阴无须赘言,其“脉小右濡”更确病机,可知为脾用不达,虚而不运,兼以体损,叶氏言“论脾为柔脏,体阴用阳”,又谓他法不及病性,自拟成方,方中以益智仁着眼脏腑关系,益火补土,温肾阳助脾运;人参益气健脾,补益脾气;茯苓、薏苡仁宣通阳分,陈皮、厚朴、砂仁运化脾土,性属刚燥,辛甘温药通补脾脏,木瓜一味,酸甘化阴,柔剂充养脾阴;后症变病转,仍遵宣通之法,健运脾脏,脾胃同治。而叶氏同时期名医薛生白于《湿热论》亦有“暑月病初起……湿困太阴之阳。亦仿缩脾饮、冷香饮子”之论述,与叶氏用法组方颇多契合。
4 结语
叶天士以“脾体阴而用阳”立论用以诠释脾脏之特性,虽着眼于脾脏,而不拘于一脏,论脏必及腑,论脾必及肝肾,虽是论述脾脏,却联系脏腑整体。叶天士治脾必明辨脾脏阴阳气血津液之虚实,据脾之生理特性结合病例特点,有针对性地择刚柔通补等法,遣半夏、苓术等方,灵机变通。理法方药,据理立法,依法用方遣药,一以贯之,此叶氏疗疾关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