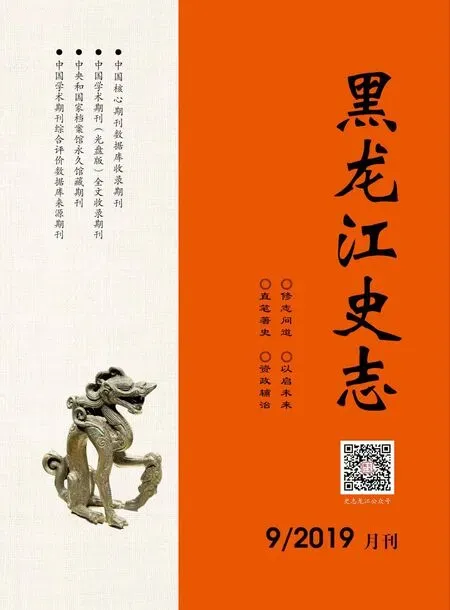修谱仪式的教育学层面分析研究综述
史连祥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把修谱仪式作为一种文化行为进行教育学层面的专门研究的专著和论文至今还没有,这也是本选题可供研究的动因之一。但与本选题某些方面的内容相关或相近的研究则为数不少,这些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修谱、传统教育等两个方面。下面通过综述这两个维度,并使之建构成一个支架,力图最终将这个支架的交点共同指向修谱仪式的教育学层面分析的价值所在,以说明打通民俗学、文化学、历史学、人类学、教育学之间联系的可能性。
一、关于修谱的研究
(一)修谱目的
冯尔康认为明清以来,宗族修谱原因在于修谱能达到敬宗收族的目的,使其族成为大族,并形成族史。[1]而当代修谱的目的带有很强的利益观念,所谓的尊祖是做给在世的人看的;所谓的团结族人,也是为了提高族人的社会竞争力。[2]刘黎明在其著作《祠堂·灵牌·家谱——中国传统血缘亲族习俗》[3]中论说了几个原因:一是维持家族组织,二是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三是实施家长权的依据和保障。《浅析撰修家谱目的》[4]不仅分析了先人撰修家谱目的,即溯源追根、辨析亲疏、凝聚族人、教育后人等,还分析了在新的形势下,今人撰修新家谱的目的:铭流、兴家、育人。渠海燕在《吕梁地区修谱的民俗研究》[5]中认为经济发展和怀旧是修谱的表面原因,而宗族重建则为其根本原因。
(二)修谱体例、内容及特征
冯尔康在《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2]中,对 20世纪上半叶和 20世纪最后 20年的家谱修纂体例与方法做了详述,发现不同时期人们的修谱活动多受家族观念的影响。李现丽的《民国家谱若干问题研究——以浙江地区为中心》[6]以浙江地区的家谱为中心,从家谱的编撰理念、编撰手段和内容的变革展开,剖析了民国家谱变革的原因,是民国家谱研究中较为全面的研究成果。于海燕在《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研究》[7]一文中,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做了一次系统和综合性研究,通过解读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编纂概况,展现了民国时期江苏省的社会生活面貌。王良在《明清徽州谱牒编纂的宗旨、原则和方法》[8]中论述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编纂族谱的目的、基本原则及常见的重要问题。吕春阳的《明代徽州家谱内容与体例研究》[9]以万历时期纂修的《休宁范氏族谱》和崇祯时期纂修的《临溪吴氏宗谱》为例,深入探究这两部家谱中体现出来的明修徽州家谱内容和体例的创新之处。
(三)修谱程序
钱杭和谢维扬共著的《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10],不仅详细描述了20世纪 80年代后江西泰和农村社会的一系列宗族活动,还用一个章节来叙写梅冈王氏族谱的重修历程,从倡议修谱、建立机构,到制定规则、筹款筹物,再到文字编辑、排版印刷,直至最后告成祭祖、分堂收藏,生动地还原了整个重修过程。既呈现了地方性,也展示了当下农村宗族修订族谱的一般模式和特征,指出修谱是宗族重建的重要手段之一,其目的并非为了恢复宗族原有的形态,而是为了强调宗族的存在。陈支平的《福建族谱》[11]对福建族谱编修的历程进行考察,分析出当代社会的许多家族冲破以纯洁血缘传承为核心的修纂原则,不仅没有瓦解家族制度,反而维系了家族与社会的正常运转,使家族制度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经久不衰。蒋国河在《嬗变的传统:赣南闽西重修族谱的过程考察》[12]中,对赣南闽西部分宗族重修族谱活动的组织与筹措过程加以描述,凸出了对重修族谱活动组织过程、特征与机制的考察。
(四)修谱功能、意义
1.对宗族内部整合效用的研究
族谱撰修具有聚族、睦宗的功能。在《仪式与象征的秩序——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力与记忆》[13]中,刘晓春从仪式与权力来分析修谱。作者指出修谱是集家族的综合力量完成的一件神圣大事,不同的家族成员会根据其在家族中的不同地位来体现其作用。家谱的修撰往往是家族力量、也是家族内部各房支力量分化的一次直接展示,强势家族能够通过修谱最大限度地凝聚家族的力量。彭秋婵的《宿松彭氏修谱民俗研究》[14],介绍了宿松彭氏的历史概况、修谱的发起和经过、家谱的内容及变化,并探讨了宿松彭氏修谱活动有着祖先崇拜、加强联系和增强族内的认同、维持族内长幼次序等重要意义。常建华在《晚明华北宗族与族谱的再造——以山东青州<重修邪氏宗谱>为例》[15]一文中,考察了山东青州《重修那氏宗谱》,认为邪氏的修谱行为不仅着眼于睦族,而且由于修谱过程中收录大量宗族制度文献,使得族谱本身成为重要的民间文献。林永雪的《乡村社会的“谱系”与秩序的建构:以小汉镇蓝氏族谱修订为例》[16]从民俗学角度出发,通过对四川省广汉市小汉镇蓝氏家族1992年及其之前的族谱修订行为的个案研究,探究族谱修订行为背后的民俗意义。
族谱撰修还具有兴伦理的功能。葛政委、黄柏权、刘冰清在《权力的再生产——荷叶镇修谱建祠活动的人类学考察》[17]中,通过对荷叶镇葛氏宗族修谱建祠活动的探讨,指出宗族的复兴过程实为宗族话语权力的再生产,是传统伦理和政府的功利化诉求等多种因素相互的结果,修谱则为促使宗族复兴、传统伦理道德的恢复和再现的一种手段。
族谱撰修在传承传统同时,也发生着一些异变。如朱妍、林盼在《宗族修谱活动中的代际分化与青年人的利益诉求》[18]中考察了东南某省郭氏宗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族谱重修活动,通过分析郭氏书信资料,发现宗族成员在修谱过程中的观念呈现明显代际分化。
2.修谱与国家、地方、民众的功能互涉
族谱撰修反映着一定的文化生态背景。濑川昌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读家谱的方法。在《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19]中,他认为人们对家谱内容真实性的考察,还不如去解明家谱修撰者的意识结构有意义。无论家谱所记载的内容是否真实,家谱编修族谱这种活动本身就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反映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进一步说,族谱撰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国家政策对地方的调控以及地方、民众对此做出的回应。赵华鹏的硕士论文《家族行动——镇原慕氏修谱的田野报告》[20]以《镇原慕氏族谱》为切入点,分别从“事件”“过程”“记忆”“仪式与象征”“权力与组织”五个角度分析了镇原慕氏修谱的过程,内容聚焦于慕氏修谱的过程中,挖掘修谱过程中的“人和事”,透过“事”突显出“人”的修谱“行为意义”的多元。指出族谱编修反映了国家和民间权力相互调适的结果,同时也是地方性知识和现代技术推动的结果。《修谱与兴孝:明代家谱修撰目的及实效性研究》[21]中,侯俊琦通过对明代修谱状况、民间社会风尚、家族制度及王朝统治秩序等多层面的考察,不仅分析了修谱与政府兴孝政策紧密结合所产生的成效,同时也为私家谱牒兴盛的原因提供了另一解释路径。
族谱撰修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行为,会呈现出一定的社会价值取向和观念意义。冯尔康在《当代家族谱编修论略》[22],关注了新时代背景下族谱编修的体例,他通过对新旧谱系编修差异的比较,呈现了当代社会族谱编纂行为的价值取向。刘永华在《祭谱与游谱:有关闽西客家族谱相关仪式的笔记》[23]中,将族谱看作一种“物”,探讨其“社会生活”和“象征生活”,通过对族谱的编纂、收藏和使用的社会关系与相关的仪式实践的研究,分析了族谱与社区的密切关系,他认为族谱是一种仪式化的对象和产物,要理解其修纂、收藏等习俗背后的观念意义,还要考虑作为修谱主体的宗族与地域社会的关系。
二、有关传统教育的研究
近年来,许多学者将目光转向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希望从中新获灵感和启示。
(一)对传统教育本身的研究
1.传统教育的内涵
观诸文献,学者们较多地从横向维度对传统教育进行了研究。余世谦的《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探要》[24]、顾冠华的《师道·师责·师谊——中国传统教育中的教师》[25]和《师德与师质:中国传统教育中教师的标准和要求》[26]、杨鑫辉的《中国传统教育的理念探讨》[27]、黄济和郭齐家的《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28]、顾明远的《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29]、严元章的《中国教育思想源流》[30]、汤海燕的《成人之道:中国传统礼仪及其道德教育功能研究》[31]、焦国成的《中国传统教育伦理理念及其主要话语》[31]等著作各从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对象、教学方法、学习方法、教学原则、道德教育、师生观等方面详尽论述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
2.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研究
于述胜、于建福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32]、郭齐家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与全球伦理》[33]和吴亚林、王学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精神气象》[34]均探讨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范畴,但注意点不同。郭齐家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观念和思考教育问题的方式及其教育价值观的透视来进行审视的,而于述胜与吴亚林则侧重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精神气象的研究。于超、于建福在《合“自然”与“当然”为一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35]中从儒、道教育哲学出发,认为二者同源异流,共铸了“自当一体”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并将此融入教育哲学理论建构中,已成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哲学的当然使命。
(二)传统教育的现代审视
1.传统教育与现代化的研究
中国传统教育现代化是中国教育一个世纪以来始终面对的问题。传统教育现代化意味着继承与变革,继承就是传承优秀的华夏传统文化,变革就是改变传统教育中的不合理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的学者对传统教育的现代化提出了应对策略。如裴娣娜在《中国传统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方法论思考》[36]中认为当代中国教育的现代化,首要问题在于方法论的科学化问题,即传统教育的继承改造中需要解决的认识方法、研究方法和思想方法等。王炳照在《二重性·两点论·双重任务——略论中国传统教育与现代化》[37]中指出,要坚持两点论,担负起现代化赋予传统教育研究的双重任务。还有些学者对传统教育变革的现代命运作了探讨。如丁钢的《略论教育传统与变革》[38]、杨东平的《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命运》[39]、胡金平的《教育传统:教育现代化无法割裂的联系》[40]、田正平的《调适与转型:传统教育变革的重构与想象》[41]、杜成宪的《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42]等。
2.传统教育的现代启示意义
学界主要围绕着传统教育的优秀成果进行研究。毕天璋在《右脑开发与中国传统教育》[43]中认为,认真挖掘中国传统教育,是开发右脑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徐秋玲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对现代大学理念的影响研究》[44]指出中国传统教育所具有的教育目标明确、德育第一、强调内省等三个特点对现代大学理念影响深远。郭齐家在《文化自信与中国传统教育》[45]中指出,中国传统教育在今天有重大的安身立命的意义,在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还有学者认为传统教育会对当代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如李文锦和王俊山在《中国传统教育对职业教育的消极影响》[46]一文中便指出,中国传统教育对职业教育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传统教育的人才观、价值取向、人才结构培养体系、传统教育内容等。
三、总结
(一)修谱研究方面。从上面的综述,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修谱研究概况,涉及到修谱目的、修谱体例、修谱程序、修谱功能等四个方面。众多学者对于有关修谱的研究成果众多,研究层面广阔。若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抽丝剥茧、概括总结,便不难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研究内容来看,多是对历史上的族谱编修进行宏观研究。修谱文化、活动仪式的探讨是学界的薄弱环节,成果基本很少,少有的几篇论著也大都进行着静态的描述。尤其是民国《孔子世家谱》撰修仪式的研究,以动态视角在活动仪式过程中深入描述、解释教育文化内涵,几乎尚未得见。
第二,从研究视角来看,从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档案学的角度对修谱进行研究的多。学者多是对修谱进行历史还原、文献解读和档案整理,并描述家族迁移史、家族发展史等。在此视角下,观照到修谱与国家、地方、民众、家族的功能互涉上,继而进行综合性研究。从教育学角度研究,目前仅见一篇学位论文,研究视角更多地放在了族谱的文献解读上。
第三,从研究地域来看,多偏重于华北、华东、华南等宗族聚居地带的研究。另外也有潮汕移民、洪洞县大槐树传说移民成为族谱研究的另一种形式。
第四,从研究取向来看,学者在研究修谱时,往往侧重于概括描述修谱行为的过程,继而将修谱置于历史大背景之中。将族谱从“仪式与象征”方面进行解读的几乎没有。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修谱仪式,本身就需要进行修谱仪式的文化层面解读。开掘修谱仪式中蕴含的丰富、有趣的教育内涵,并对修谱仪式背后的教育基因的深入研究更属空白。
第五,从研究原则来看,就目前所搜集文献,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尚未很好地结合起来,主要集中在客位研究之上。未能运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的原则进行文本的对话和交流,形成对文本的“理解的理解”“解释的解释”。
(二)传统教育研究方面。通过上面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近30年来,中国传统教育一直是教育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学界一直在努力探究、建构传统教育体系,这一过程仍将继续。
从研究内容来看,学界对中国传统教育的研究范围比较广泛,成果颇多。既有从古至今的历史梳理,也有成教育系统的综合分析;既有对传统教育的认同,也有对消极落后的批判;既有对传统教育的回眸,也有对传统教育的现代审视。
然而,从研究领域来看,目前学者多在中国传统教育的本体层面进行考查。从民族心理、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教育的研究仍有待深入。我们不仅需要知道传统教育“是什么”,更应该深入探究传统教育“何以可能”的问题,即努力挖掘传统教育的深层次结构。这才是我们最为需要关怀的“神”和“根”。
以上的分析,从修谱、中国传统教育两个维度出发,力图说明本论文选题的可能性。如同数学二维坐标系一样,这两个维度构成了一个二维坐标系(如图1),二维坐标系的原点便是论文的研究焦点——族谱撰修仪式的教育学意义。在对这两个维度的文献进行梳理、分析时,发现其中尚有亟待完善之处,这正为本研究提供了切入点。

图1 二维坐标系示意图
纵观两个维度的成果综述与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共存特征:缺乏文化、心理、生命、教育深层次结构层面上的观照。族谱撰修仪式的教育学意义作为这个二维坐标系的原点,首先在于打通了民俗学、教育学、文化学之间的联系。将作为一种文化行为的修谱仪式作为研究对象,可以站在文化人类学及文化学的观点和视野下,以“仪式和象征”的角度深入解释族谱撰修仪式背后蕴含的深刻的教育意义结构。其次,在于填补两个维度的空白。族谱撰修仪式的教育文化层面解释,正是实现此目的的意图所在。这对修谱研究来说,将修谱仪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深描仪式空间、仪式内容、仪式程序等典型象征符号,进而解释修谱仪式的教育学意义。对文化研究来说,力图从文化、心理、教育三个层面解读族谱撰修仪式,并将族谱撰修仪式植根于广袤的社会文化生态背景之中,从全新的视角、全新的思路中淬取出有关的地方性知识。对传统教育研究来说,修谱同时又属于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教育基因。我们可以借助教育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体系,努力探寻出族谱撰修仪式的教育基因,以丰富传统教育研究的内容体系,深化对传统教育的认知和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