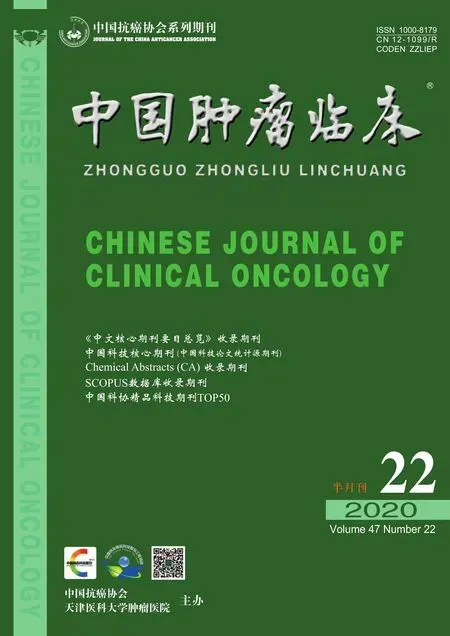抗血管生成治疗之路的瓶颈 对策与方向
李凯
20 世纪Folkman 提出肿瘤依赖血管生长和转移的新理论,阻止血管形成有望“饿死”肿瘤。1997年,针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的抗体-贝伐珠单抗问世,首次提高了结直肠癌[1]和肺癌的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2];之后又在多个瘤种上获得成功,以贝伐珠单抗代表的抗血管治疗也一度被评为手术、化疗和放疗外的“第四模式”。但继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却发现,贝伐珠单抗仅能够延长三阴性乳腺癌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而非OS,这意味其虽可推迟肿瘤复发,却可能随之出现肿瘤耐药、加速生长等问题。据此,FDA 撤回了其乳腺癌适应证的批准。Ranpura 等[3]开展的包括16 个临床试验、10 217例患者的Meta分析表明,含贝伐珠单抗方案的致死性并发症明显高于不含贝伐珠单抗的方案(2.5%vs.1.7%,P=0.01)。上述研究不仅暴露了贝伐珠单抗的缺点,并且可能提示了第一代单靶点抗血管生成药物的天然“短板”,成为阻碍此疗法应用之瓶颈。本文仅就抗血管生成治疗的障碍及相关对策略述浅见,以飨同道。
1 如何有效克服耐药
肿瘤对任何药物均可产生耐药性,但早期(第一代)的抗血管生成药物仅抑制生长环境而非肿瘤细胞,意味着仅依靠其本身难以克服耐药,还需另寻新路。
1.1 耐药之分子基础
第一代抗血管生成治疗药物多通过抑制VEGF通路,阻碍血管生成和供血、供氧,减缓肿瘤生长;但研究发现有效抑制了经典VEGFA通路传导后却往往激活多条代偿性“旁路传导”,如VEGFC[4]、肿瘤生长因子(tumor growth factor,TGF)[5]、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6]等,使肿瘤细胞生物学行为更为恶劣,如侵入周围组织,并“劫留”其中血管据为己用[7],或搭建起类似血管的结构(vasculo⁃genic mimicry,血管拟态)供应血、氧[8],使针对血管内皮细胞的药物再无用处。甚至被认为“基因稳定”的血管内皮细胞中的TGF-endoglin(CD105)通路也代偿性活跃[9],导致血管迁移和形成增加,迅速补充损伤的血管,且新形成的血管渗透性更强,更利于肿瘤细胞侵入周围组织[10]。上述旁路激活可使肿瘤及其血管迅速“反弹生长”,甚至出现治疗后肿瘤侵袭、转移反增之虞[11]。因此,抑制主要血管生成信号通路后肿瘤/血管内皮细胞中的旁路活化已成为诱发耐药的重要原因。
1.2 应对策略
针对靶细胞中的多旁路活化,主要应对策略为:
1.2.1 “A(anti-angiogenesis,抗血管生成)加策略” 即以抗血管生成联合其他药物以覆盖各信号通路,又分为“A+C(化疗)”、“A+E(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和“A+I(免疫药物)”等。在经典的ECOG 4599试验[12]中,化疗联合贝伐珠单抗一线治疗较单纯化疗延长肺癌患者生存(中位OS:12.3个月vs.10.3个月,P=0.003),许多临床试验也大致重复了上述结论[13]。但化疗属毒性很强的“无选择性杀伤”,因此,在有明确治疗靶点(如EGFR)的肿瘤中,“A+E”的尝试也如火如荼。在治疗EGFR敏感型突变非鳞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JO25567研究[14]中,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EGFR-TKI)联合贝伐珠单抗的PFS优于单纯EGFR-TKI(16.4个月vs.9.8个月,P=0.000 5)。在新兴的“A+I”尝试中,联合免疫治疗也有不俗表现[15]。
但关键问题仍是如何确定最佳搭配药物和用药顺序。以抗血管生成的重要效应-血管正常化(vas⁃culature normalization)为例,其可将迂曲、膨胀、渗漏性高的肿瘤血管部分恢复为渗漏性低、血流通畅的“类正常”血管,而使药物更快到达瘤灶,为后续化、放疗增效。但依此设计的先抗血管生成、再化疗的方案却常不奏效;此缘于血管正常化的时间窗短(一般5~7 天)且不固定,故紧随其后的化、放疗常不能落于窗口之中。而寻找灵敏反应正常化时间窗“开关”的标志物[16]带来了新思路,有望使此治疗方案不再盲目,从而取得更佳疗效[17]。
1.2.2 “A 广策略” 尽管“A 加策略”很大程度上覆盖了活化旁路,却仍难达尽善尽美,无论是“A+C”中的AVAiL研究[18]还是“A+T”中的JO25567研究[14],也还会重蹈覆辙-“赢在PFS,输在OS”。甚至在“A+I”中的“豪华”IMpower150研究[19]中,化疗、免疫治疗和贝伐珠单抗四药联合方案的OS与无贝伐珠单抗的三药方案相比亦无优势。这就引发了更多的思考:本该互补长短的药物间真的形成了协同效应?抑或联合用药也并不能有效抑制单通路抗血管生成药物激发的旁路活化?
为应对上述问题,目光又聚焦到多靶点抑制剂上,期望把对多条通路的抑制效应集于一个药物之中,既可减轻不良反应、降低费用,又有望实现多通路抑制作用的紧密协同。但实践中,索拉非尼、阿昔替尼、舒尼替尼等多靶点药物并未显著延长肺癌患者的OS而达成“1+1>2”的效果,甚至令人怀疑疗效还不及单靶点药物,也引发了对其原因的探究。首先,上述药物虽为“多通路抑制剂”,其效应却“偏于一隅”,如阿昔替尼的主要靶点为VEGFR-1、VEGFR-2、VEGFR-3、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β(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R-β)和c-KIT,前四个均针对血管生成,对肿瘤细胞的主要生长靶点并无抑制作用、不能同时顾及生长环境及肿瘤本身。其次,多靶点抑制剂对各靶点通路的作用更多为重合而非互补,如能将其转为“配合”,即有望取得更好的疗效。BEYOND研究[20]分析发现,贝伐珠单抗联合化疗对具有EGFR 基因敏感突变者的远期疗效更好,而EGFR 和VEGF 信号通路间的相互关系也被证明[21]。而新一代抗血管生成药物安罗替尼的靶点包括VEGFR、FGFR和PDGFR等血管生成通路,覆盖c-Kit、EGFR 等肿瘤生长基因[22],实现了“双领域、多靶点”的结合和显著疗效,延长了耐药NSCLC患者的PFS和OS(P<0.000 1),结束了难治性肺癌无药可医的历史[23]。
1.2.3 “A早策略” 肿瘤分期越晚、信号通路活化越多,越不容易被抑制,故抗血管生成新辅助治疗效果亦应更好。一项旨在比较微波消融术(microwave ablation,MWA)联用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与单用MWA治疗Ⅰ期NSCLC的临床试验[24]表明,联合组的PFS明显优于MWA组(30.0个月vs.21.3个月,P<0.001)。类似的研究也提示人血管内皮抑素联合化疗新辅助治疗ⅡB期骨肉瘤的5年无远处转移生存率(distant metastasis free survival,DMFS)明显高于单纯化疗(79%vs.61%,P=0.013)[25]。但也有研究显示[26],与单纯化疗相比,以标准化疗方案联合贝伐珠单抗新辅助治疗(4个周期)并未给ⅠB~ⅢA期NSCLC患者带来更好的OS(HR=0.99,P=0.75)。故针对不同肿瘤,最佳联合用药选择和治疗时间仍需探索。
抗血管生成治疗耐药的重要原因为早期单靶点药物抑制单一通路后诱发多个旁路信号传导活化,以及单靶点药物作用不能全面覆盖肿瘤及其生长环境。克服耐药的关键在于揭示“活化旁路”,并寻求最佳联合模式及“双领域、多靶点”药物,方可能达“1+1>2”之协同效果。探索早期治疗为必然趋势。
2 如何准确评估疗效
血管靶向治疗后肿瘤体积常无明显变化,但瘤体内出现坏死、空洞,依据最大直径变化评价实体瘤疗效的标准(RECIST)并不可靠,精准评估疗效也是亟需解决的难题。因血管生成源于刺激因子,早期研究大多关注它们,但结论却难确定。以VEGF 为例,Calleri 等[27]发现,接受节拍化疗加贝伐珠单抗的乳腺癌有效者治疗2个月后血中VEGF-A显著下降,病情进展时又再度升高(P=0.023),似乎提示其对疗效的预测意义。但在ECOG 4599试验[28]中发现血中VEGF水平不能预测患者OS,其他研究也未发现其与抗血管生成疗效有关。矛盾的结果应该是由于血管生成平衡中促进因子与对抗因子的拮抗作用:一者变化可能引发拮抗反应,难以仅依赖一种因子变化评价疗效。故人们把目光转向了其下游更贴近血管生成本身的指标。
2.1 针对肿瘤诱导新生血管
以活化循环血管内皮细胞(activated circulating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aCECs)为代表,包括源于血管壁的内皮细胞和源于骨髓的内皮祖细胞(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EPCs)。两部分细胞均可经VEGF等激活后进入外周血,趋化至肿瘤周围直接形成新血管[29],因此作为疗效预测指标比上游因子更可靠。虽然对aCECs表型的认定仍存在一定分歧,但越来越多证据证明了其灵敏性与可靠性优于上游的各种刺激因子[30-31]。
2.2 针对非内皮细胞性供血结构
如前所述,除吸引、摄取循环中的内皮细胞外,肿瘤亦可依赖“劫留”血管或搭建“血管拟态”为其供血。aCECs的变化难以提示此类事件,而瘤内血流灌注指标却能准确反映其变化,如血流速度(blood flow,BF)、血容积(blood volume,BV)等。Wang 等[30]发现在抗血管生成治疗时BV 往往早于普通CT 征象1~2 个月产生变化,与aCECs 结合还可提高预测疗效的灵敏性与可靠性。
抗血管生成治疗不同于细胞毒药物,依体积变化判定疗效并不合适,应观察治疗中能反应内皮细胞依赖与非依赖性供血结构变化的指标,构建独特的疗效评估体系,并达到能灵敏预测疗效的目的。
3 如何筛选优势人群
准确筛选优势人群是医生的目标。受EGFRTKI 的启示,最初人们一直探索如EGFR 突变等能事先指示有效人群的靶点。但仅发现VEGF、缺氧诱导因子(hypoxia-inducible factor,HIF)、angiopoietin等[32]靶点与预后有关,但不能确定其对疗效的意义。这是缘于抗血管生成药物既可导致肿瘤休眠和长期稳定,也可导致其激活和快速进展[33],故即使抑制了生长环境中的全部靶点,也并不等同于抑制了肿瘤。一些研究提示肿瘤微血管密度(microvessel density,MVD)[34]、HIF 表达可能提示疗效,但皆因研究例数少、或不易连续取材检查而难以推广。屡次碰壁也引发了反思:既然难以事先确定,何不在治疗中动态观察?在安罗替尼治疗中,经大样本测序和生物信息分析、观察了外周血中的10余项指标动态变化,从中筛选出IDH1 exon 4 基因和肿瘤突变指数(tumor mutation index,TMI)作为灵敏的预测指标[35];另一项研究则从临床表现中筛出了10余项提示优势人群的指标[36],进行了更贴近的临床的探索。
由于其特有的作用靶点及生物效应,目前还很难如EGFR-TKI,通过某种指标事先筛选出抗血管生成治疗的优势人群。除继续探索外,应特别注意治疗初期各指标变化对疗效的提示,转变理念为:既要追求“疗前先知”,也需关注“因治而变”。
4 如何达到最小不良反应
抗血管生成药物不良反应普遍低于化疗药物,但仍可限制其应用,甚至危及患者生命,如出血、血栓、心律失常、高血压危象、肾脏损伤等[37]。上述不良反应多与药物拮抗VEGF、损伤内皮细胞和影响微血管功能有关,故对高龄和有心、肾疾病史患者需谨慎。对于日咯血量多、肿瘤贴近血管或有血栓者则不宜使用。但不同药物对肿瘤和正常血管内皮细胞的毒性也不相同[38],此种差异也令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的心血管不良反应可逆,为其在特殊患者中应用提供了依据[39]。
5 启示与展望
自1997年贝伐珠单抗问世以来,抗血管生成治疗走过了从诞生到壮大,又充满崎岖的23年。随着相关基础研究进展和一代又一代新药问世,其在癌症治疗中已牢牢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了化疗、放疗、免疫治疗甚至外科手术的良好搭档。但我们的认识仍存在诸多盲区,研究结果也多为“某种药物或方案取得了某种疗效”,但疗效的分子基础为何,疗效能持续多长时间?由于我们仅知道一端的几个“D”(药物)和另一端的两个“S”(PFS、OS),对于无法解释疗效的基础生物学效应就成为了横亘在中间的“黑箱”,产生了诸多瓶颈。随着分子生物实验和信息分析科学发展,积极开展紧扣临床需求的基础转化研究,抗血管生成治疗才能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