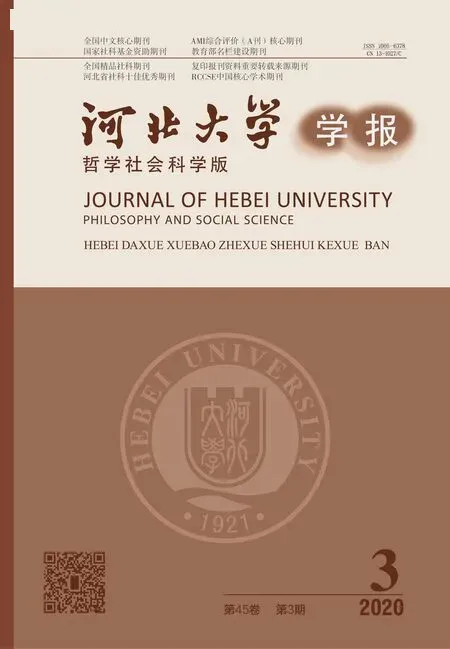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传播路径和影响因素
任淑坤
(河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综观翻译史上的高潮,翻译方向相对单一,通常是由外而内,即由外语译为母语,中西皆同。然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从来不可能是单向的,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深入,文化交流必然呈现双向或多向的特点。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深入人心,学界也在热烈讨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方法、路径。本文将着重探讨中国文学外译的传播路径及影响因素。
一、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历史与现状
(一)翻译主体的多元化
在17—18世纪,中国文学的外译主要由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完成。译出的作品以儒家、道家等的经典作品为主,包括“四书五经”《道德经》《明心宝鉴》等。戏剧《赵氏孤儿》在这一时期最早走出国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除了思想经典外,中国诗歌也在欧美翻译出版,如翟理斯的《中诗英译》。庞德的译作《华夏集》1915年在美国出版,中国诗歌的主题、形式,尤其是意象叠加的手法都成了美国新诗诗人模仿的对象。
以上经典都是通过外国译者之手远渡重洋,中国译者主动向外译介则是随着中外交流和接触机会增多而出现的。1872年,中国派遣的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拉开了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序幕。中日甲午战争后到20世纪初,留学运动出现了热潮。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外的交流和接触已经不可避免。留学运动和国内的外语教育,使得国人对外国文化和语言有所了解,具备了主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必要条件。如萧乾从1931年起就协助美国人威廉·阿兰编辑英文期刊《中国简报》,并在这份刊物上推介了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和沈从文等人的作品。1932年,他翻译了田汉的《湖上的悲剧》、郭沫若的《王昭君》和熊佛西的《艺术家》,发表在当年的《辅仁学报》上[1]。
新中国成立后到60年代末,国内的局势变化和与国际社会关系的磨合,对文化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人们对这一时期产生的文学作品评价不一,有肯定其道德文化意义而奉为经典的,也有因其审美意识的缺失和文学史意义的匮乏而加以否定的[2]。资料的局限和对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否定也直接体现在翻译研究领域对这一时期文学外译的研究不足。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新闻局就以“外文出版社”的名义组织翻译包括古代、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在内的外译。当然,这并不是说官方组织了文学外译,个体译者的翻译就停滞或被取缔,只是说无论是就翻译主体还是就组织形式而言,都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个时期产生的“红色经典”,经由外国译者之手走出国门也并不鲜见。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红色经典是99 岁高龄在中国寿终正寝的沙博理所译DaughtersandSons(《新儿女英雄传》),“这部译作在美国的发行量很小,除几所古老的高校图书馆外,普通高校图书馆均无收藏。即便是我访学的以语言教育和外语翻译著称的高校,这部小说的借阅量也是少之又少”[3]。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访华,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文化交流也出现了新局面。各国的汉学家成为中国文学外译的生力军。如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将《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辛弃疾的许多诗词译为瑞典文;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翻译了老舍、巴金、萧红、莫言、王朔、池莉等多名中国作家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翻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红高粱》《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等;英国汉学家蓝诗玲翻译了《鲁迅小说全集》、张爱玲的《色戒》等;法国汉学家安妮·居里安女士翻译了韩少功的《诱惑》《女女女》等;德国汉学家尹芳夏翻译了《三国演义》;德国汉学家顾彬翻译了《鲁迅选集》、北岛的《太阳城札记》等。
(二)组织形式的不同
官方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级政府和机构积极组织翻译活动,为各类著作走出国门起到了推动作用。“新生的民族国家主动对外翻译介绍本国文学作品,以响应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诉求和召唤,意图在国际社会舞台上实现自我合法形象的塑造”[4]。1951年,在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和文化部的推动下,由回国不久的叶君健筹备、创办了英文版《中国文学》,1964年法文版问世。1981年,《中国文学》新任主编杨宪益倡议,中国外文局支持出版“熊猫丛书”,主要以英法两种语言向欧美等国介绍中国文学。1995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启动“大中华文库”项目。到了21世纪,各种国家级的“项目”“工程”“计划”的启动愈加频繁,其中包括2004年启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9年国家汉办批准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2010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批准设立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年中国作家协会推出的“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2014年启动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等。
从上述“项目”“工程”“计划”的启动和刊物的创建可以看出,国家和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一如既往地重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对外传播,这些努力也已经看到成效。大量的中国图书翻译成外文,从先秦至现代,涉及的领域从思想典籍到文学、历史、哲学、科技、经济等不一而足,中国典籍输出到全球的许多国家。
民间力量: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传递速度越来越快,获取途径越来越多,读者如果需要,可以直接接触到外国文学。懂外语的读者出于兴趣和热爱,自发翻译引发个人阅读热情的作品,虽然译介规模不大,但译介效果却出人意料。引起广泛关注的《射雕英雄传》英译本就是由民间力量自发完成的,并且销售火爆。译者郝玉青在英国长大,有学习中国文学和历史的专业背景。她经过6年的打磨,终于完成英译本《射雕英雄传》第一部《英雄的诞生》,在英国由麦克莱霍斯出版社面向全球出版发行,出版首月即加印6次,美国、西班牙、德国等8个国家也相继买下版权,并被《泰晤士报》《经济学人》《卫报》等知名媒体关注和报道。据“21世纪英语传媒”统计,该书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获得了四星,在中国只有两星。在出版发行最多的英国,有53%的读者打出了五星、35%四星、6%三星以及6%一星,平均打分为四点二星。在出版社的官网上,读者评分则为四星。在美国引起轰动的科幻小说《三体》也是类似的情况。此外,还有译者自发翻译网络小说,建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网站,规模也在增大。如美籍华人赖静平创办的“武侠世界”,日点击量已经破十万。2015年在美国读高三的孔雪松创办了中国网文翻译网站“引力小说”(Gravity Tales),也获得成功。阅文集团旗下的“起点国际”(Webnovel),2017年正式上线,率先实现了网文作品以中英文双语版海内外同时发布、同步连载。美国的艾瑞克·阿布汉森(Eric Abrahamsen)2007年创建的纸托邦(Paper Republic)也成为海外英语世界了解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重要窗口。
(三)现象与问题
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1.与外国文学的译入相比,中国文学的译出仍旧处于“逆差”状态。尽管这些年中国图书外译规模在不断加大,图书进口和出口的差距在缩小,但若要扭转逆差,还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有一组数据能清晰展示这一点:“2008—2012五年间,中国引进美国的图书版权数量依次为:4 011种、4 533种、5 284种、4 553种、4 944种,而 美 国 引 进 中 国 的 图 书 版 权 数 量 则 分 别 为:122 种、267 种、1 147 种、766 种、1 012种。”[5]《中华读书报》也曾报道:“中国著名作家和经典作品在海外至今仍少有人知。据统计,作品被译介的中国当代作家有150多位,只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1.3%。”[6]
2.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外译文本的获取途径仍需拓宽。学者的研究表明,国外图书馆里可以检索到中国文学的译本,尤其在大学图书馆。汉语和中国文学、历史等专业的师生和研究人员可以很方便获取和阅读译本。但也有专家指出,“在美国图书市场上,也就是说主流的连锁书店,基本上不会出现。在美国,相当大部分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的中国文学作品在商业市场是没有销路的”[7]。所以,在做好市场调查和市场培育的基础上,还需要拓宽图书的获取途径。除了图书馆、书店,还可以增加报刊、电子版、电纸书、微博、微信等多种渠道,方便读者的获取。
3.中国文学的外译需要在“忠实”和读者的接受能力之间寻求平衡。为了原汁原味地传达中国文化,我们往往更强调忠实于原文,在文字的完整和对应上更是不敢逾越藩篱。前文提到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国外读者的评分在四星之上,但在中国的得分只有两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母语和外语的敏感度不同,阅读母语文本和英文文本的感受则殊异,读者不自觉地用这种感受作为评价标准。另一方面,更多具有双语能力的读者在比对文字。虽然译者一再强调自己的忠实,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著的中国元素,认为这些元素“不译才是损失”。但读者仍旧源源不断地找出“不忠实”之处。比如黄蓉变成了“黄莲花”,大雕变成了“秃鹫”。这充分说明已经有了原文阅读体验的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阅读能力、阅读感悟和阅读期待的不同。如果译者按照中国读者的能力、感悟和期待去翻译给外国读者看,势必会有译本“遇冷”的状况出现。但不得不承认的现状是,我们常常会在这种情况下做翻译。
二、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传播路径
中国文学“走出去”当然要有好的源本和译本,在满足这个条件的基础上,还需要考虑域外传播的问题。以为只要译成外文,中国的文学典籍自然而然就“走出去”了的观点,“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而没有考虑到译成外文后的作品如何才能在国外传播、被国外的读者接受的问题”[8]。立足于外国文学作品的译入和传播,综合考虑电子技术等对传播的影响,反观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笔者认为可以尝试以下几条传播路径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9]。
(一)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对译作传播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译作通过教育影响人的精神和心灵,另一方面,译作通过教育这一路径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一旦译作进入教学和教育环节,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会受到其影响。比如高尔基的《海燕》、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契诃夫的《变色龙》、安徒生的《丑小鸭》、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等都是因为收入中国的中小学课本而名噪中国。外国文学传入中国是这样,中国文学“走出去”也是同样的道理。外事部门、教育部门和出版机构、译者应通力合作,努力让中国文学的译本能通过学校教育在国外得到普遍传播的机会。
汉语在国外的学习热潮,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做了铺垫,也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契机之一。欧美很多国家开设了中文教学课堂,英国还创办“望子成龙”(Hatching Dragons)中英双语托儿所。中文学习者中不乏特朗普总统的外孙女和美国金融大鳄罗杰斯的女儿这样的名门望族之后。我们可以根据各个层次的中文学习者的需要,以中国文学著作的译本作为学习教材、课外读物或辅助资料,作出不同难度的译本,将语言学习和文学、文化传播结合在一起。比如针对中学生的读本可以是名著中摘录的句子,还可以是配图版;大学生的可以是一些段落或章节,也可以是简易读本;而学习中国文学专业的域外学习者可以用全译本,并辅以导读性质的书籍。我们目前输出的译本多是全译本,文字忠实度高,但对学习者来说难度较大,如果能改进和分流译本,加强针对性,则效果会大不相同。虽然简易读本难以让学习者一时就了解到著作的全貌,但对学习者,尤其是孩童和初级学习者来说,激发兴趣、培养译本阅读习惯,也是一种成功,为了解中国文学的全貌奠定基础。毕竟循序渐进才是学习的常道,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
(二)名家推广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信息的产生和传播速度大大提高,说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并不为过。而译作要在海量信息和数据中脱颖而出,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并不容易,酒香也难抵巷子太深。因而在译作的域外传播过程中,借力也是十分必要的,可以借助名人译者或推介者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推动译作的传播。
五四时期中国大规模引入外国文学作品时,文化名人的作用不容低估。直到今天,虽然翻译语言和环境发生了变化,但名人的译作仍旧在流通。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译作,名人的作品仍旧是最容易获取到的,很多的图书馆都有收藏,很多出版社仍旧密集再版。以我们所熟知的《最后一课》为例:1912年胡适首译为《割地》,后收入《短篇小说集》时改名为《最后一课》。1913—1917年之间,先后还有匪石、“静英女士”、江白痕、梁阴曾的译本产生[10]。胡适的译本并非这些译本中最准确、最完整的,但流传却是最广的。这几个同时期的译本中,目前仍旧流通并广为阅读的,恐怕也只有胡适的译本了。
名人译者和名人推介者自身就是品牌,除了作品本身的魅力外,其影响力及在不同场合的提及、介绍等也在扩大译作的知名度。林语堂能在美国文化界和知识界占据一席之地,除了其作品自身的魅力外,赛珍珠的推荐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
(三)影视剧作
相对于文字的译作,影视剧作有声音和画面辅助,受年龄、国别、文化程度的制约小,具有广泛传播的便利条件。我们熟知的很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并非通过文本的阅读而广为人知,一方面的原因当然是语言限制,并非人人都拥有双语或多语能力。另一方面,在没有特定需求时,并非人人有耐心、有精力、有时间、有心情去阅读大部头的著作。而通过电影、电视剧,既能度过休闲时光,又能了解异域文学和文化,也算是寓教于乐的一种形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几乎都能找到改编的电影,如《基度山伯爵》《奥德赛》《俄狄浦斯王》《挪亚方舟》《圣女贞德》《堂吉诃德》《罗密欧与朱丽叶》《王子复仇记》等等。即便是同一语言同一文化内部,这样的现象也比比皆是。中国的四大名著都曾拍成电视连续剧,吸引了大批观众。尤其是《西游记》,每至假期,成了还不足以阅读原著的小朋友们追看的热剧。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是一个稍显特殊的例子。这部林语堂用外文写就,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小说,经过翻译、改编、拍摄成电视连续剧,在中国广为传播,使得许多观众以为这是林语堂用汉语所写的作品。虽然影视剧作经过改编,受舞台效果、时间等的限制,与原著有出入的地方,但仍旧不失为扩大原著和译作影响力,争取观众和读者的有效方式。中国文学“走出去”也可以尝试同样的路径。
(四)大众传媒
顾名思义,大众传媒的受众数量巨大。在传统的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形式之外,网络传媒因其方便快捷而成为新宠,成为人际交往、信息传播和知识获取的重要途径。正规的学校教育中也在添加网络的元素,比如远程教育、慕课、翻转课堂等。同时,网络因其用户广泛,不受时间、距离的限制,普及性、娱乐性、实时性等特点异军突起。以网络为媒介,通过动画短片、漫画等非正式的方式推广我们的文学作品,变换方式、转变思路,让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另辟蹊径。叶芝的诗《当你老了》经由春晚的舞台、莫文蔚的演唱、网络的传播,以歌曲的形式流行。这首诗因其形式的改变得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化对外译介也是这样,可以不拘一格,采取多种形式。
中国文学“走出去”,网络和网民的力量也不容低估。重视网络小说、网络和网民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力量,并非要忽视传统的经典文学作品,而是为培养国外读者的中国文学作品阅读习惯,也可以说是为中国文学经典的“走出去”做了铺垫[11]。网络文学及其译者,因其自主性、娱乐性、非正式性,翻译所受到的“忠实”压力要小于经典著作的译者,无论是批评家、研究者还是读者,对此类译作的期待会有所不同。这也恰恰给了网络小说翻译更多的自由和生存空间。也许,有些细节还难以准确传达,有些表达陌生感太强引起误解,有些地方不尽如人意,但人类共同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对善良、勇敢、正义等优秀品质的共同追求,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跨越文化障碍得以传播的要素。两种文化碰撞过程的扭曲变形之处,会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逐渐回归正轨。
(五)非翻译方式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作品大量译入中国,除了以翻译的形式引入西方的知识和文化,非翻译或变译的方式也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为读者能顺利接受译作奠定了基础,起到了辅助作用。以五四时期的代表性刊物《新青年》为例,在译作之外,其登载的其他作品也或多或少和外来思想文化的传播有关,涉及西方的制度、军事、法律、宗教、文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新青年》创刊号(时名《青年杂志》)上共有9篇文章,并辅以4个栏目。其中4篇是译作,另外5篇是“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卡内基传”和“新旧问题”,每一篇都和外国文化有关。4个栏目“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通信”和“世界说苑”也是同样的情况。
中国文化向西方的译介中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赛珍珠曾与丈夫一起管理《亚洲》杂志,邀请中国文化名人为《亚洲》“写”稿而非“译”稿,介绍中国各方面的情况[12]。德国汉学家顾彬和妻子张穗子创办德文杂志《袖珍汉学》,介绍中国小说、散文和诗歌各个流派。西方各国汉学家也曾撰写大量的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如葛兰言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卫礼贤的《中国文明简史》《中国精神》等[13]。
这些非翻译的作品,为西方国家的读者打开了一扇窗户,为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可见,在翻译之外,用外文直接写就的著作、综述、游记、新闻报道、介绍性文章等都可以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形式。同时,在西方读者与中国文化之间建立关联的机会越来越多,我们往往会因为一个人而关注一个城市,也会因为一次造访而关注某个国家。随着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国旅游、学生留学、网络交友、跨国婚姻等都可能在中国与外国文学和文化之间架起桥梁。很多汉学家都有位中国妻子,如葛浩文与林丽君、顾彬与张穗子、宇文所安与田晓菲,虽然中国妻子不是成为汉学家的必要条件,但对于增进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培养对中国文化的感情,在两种文化之间起到联结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三、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影响因素
(一)译入语国家对外来信息需求的迫切程度
在教学中发现,学生曾经固执地认为,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中译外一定要直译,为了降低直译带来的陌生感和阅读障碍,就要加注,所以直译加注就是最好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然而,我们忽略了接受者的需求。比如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虽然其中有很多中国特色词汇,但我们很少见到英文译本的报告在后面加很多注释的。这一方面得益于翻译专家团队不拘泥于文字对应这种形式,对西方的阅读习惯和词汇内涵、外延的恰当理解,外国专家对于翻译过程的参与。另一方面,就是译入语国家的需求。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在世界上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中国的社会民生、科技发展、国防事业、财政状况、大政方针等,这就决定了译入语国家收看和阅读政府工作报告的主动性,即便有些表达有陌生感、有中国特色,他们也会花费时间、精力去解决阅读中遇到的困难,甚至会组建包括不同领域的专家团队,去解读报告,只有知己知彼才能更好地交往、合作和竞争。即便其中有带来陌生感的词汇和表达,他们也不会轻易弃读。译入语国家对外来文学和文化信息的需求越强烈,则译出的作品越能顺利传播。
(二)译入语国家对于外来事务的开放心态和敏感程度
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开放心态不一定相同,国与国之间的这个指标值更是有差异。保守、闭塞和不开放的心态往往又与因循守旧、夜郎自大、自我满足和不思进取联系在一起。如果一个国家处于这样的时期,则外来文化的传入,文学译作的推广会面对更多的困难。心态越开放,对外来事务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越强,越能主动调节自身固有的观念和文化,协调处理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越能敏锐地认识到外来文化的价值,以开放的姿态包容、学习、引入带有异域特征的知识、科技和文化。古罗马很善于吸取其他民族的智慧,罗马武力征服了希腊,却被希腊的哲学、文学、戏剧、建筑、科学等方面的成就所折服,大量译介了希腊的作品。从早期实践的直译、模仿、改编、移植、替代到后期的创译、竞赛、超越,与原文文字对应的偏离尺度越来越大,对译文的追求却越来越高,“翻译家的目的是介绍希腊文化,使罗马读者和观众能从翻译或改编的作品和戏剧中得到娱乐消遣”[14]。虽然说,早期对翻译方法的理论探讨几近于无,但翻译家在翻译实践中却“不自觉地采用适合于自己目的的观点和方法”[14]。古希腊的文化遗产就这样通过古罗马人传播延续下去,成就了早期的西方文明。
(三)译入语国家对源语国家信息的熟悉程度
如果译入语国家和源语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关联,对源语国家的文化和相关信息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或者已经激发出一定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则对于相关译本接受的可能性更大、程度更深,译本传播的会更快更广。那些已知信息会帮助读者理解未知信息,消解或降低译本中陌生化信息的难度,接受陌生化异域信息的潜力更大。
中国在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为中国文学外译打造了良好的环境。2017年3月到6月,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与凯度华通明略(Kantar Millward Brown)、Lightspeed合作开展第5次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对全球6个大洲的22个国家发放了11 000个访问样本,经数据分析显示,中国的公信力和整体形象好感度都在上升,“一带一路”倡议赢得普遍好评;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获得更多认可;对中国国民形象的普遍描述是“勤劳敬业、诚实谦虚、热情友善”;中餐、中医药、中国高铁等中国文化与科技元素继续成为国家形象亮点。影响中国文学外译进程的因素包括(1)国际大语境的制约;(2)经济、军事实力等在内的中国硬实力影响,以及包括文化、政治、外交政策等在内的中国软实力影响;(3)国外读者基于自身文化与价值观理念而形成的社会性阅读倾向;(4)作品自身质量释放的阅读行为驱动力[15]。深入交流带来的好感及多种信息,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的阅读倾向,对译入语国家的各种信息的熟悉程度提高,阅读译本的难度减小,阅读兴趣就会提升。
(四)读者的阅读期待
读者阅读译本是为了休闲消遣、提高文学素养,还是为了求学、获取知识、有无考试压力等,都决定了读者对待不同译本的态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分为舒适区、延伸区和恐惧区三个等级。读者若是为了打发时光、休闲娱乐,极有可能选择没有阅读难度的舒适区读物,让身心处于舒适愉悦的状态。但若是为了获取知识,为了求学,则无论是校方的课程设置还是读者的主动选择,延伸区的读物是首选。这个区域的读物,读者阅读时有一定的难度,可能会感到某种程度的不适,但经过一定努力还是可以克服障碍,让知识水平、认识水平和理解力得到提升。而恐惧区的读物,往往是超出能力范围太多,难度过大的读物,阅读时会有较重的不适感,遇到的困难难以克服,让读者失去阅读的兴趣和勇气。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文学翻译的文本,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使其处于延伸区内。读者能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信息去理解未知信息,或者经过咨询、查找资料、触类旁通,克服阅读中的困难,达到了解外国文化和学习外国文学的目的。久而久之,延伸区的读本就会进入舒适区,而恐惧区的读本则进入延伸区。一个译本是处于哪个区域,和前面所讲的三点影响因素也是相互联系的。同样一个译本,在有需求、处于开放时期和已经建立一定关联的国度,可能是延伸区的读本,而在无需求、闭塞和无关联国度则有可能处于恐惧区。对于处在特定时期的特定国家,也许需要输送的不是延伸区而是舒适区的译本,部分过于陌生化的信息需要裹上“糖衣”,让读者能在轻松的状态接受外来文化。这就要求我们的译本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读者需求状态有一定的了解,才有可能有针对性地产出译本,进而顺利传播。
阎连科的作品能在法国得到广泛接受得益于版权代理人陈丰的细致工作,她连译本出版的顺序都作了细致安排,比如短篇的、好看的、容易推广的在先,然后更换口味和篇幅,在有了稳定的读者群后才是大部头的疼痛感强的著作,“这种长短、口味的调整和搭配,如同厨师请客时要做哪些菜,先上哪些菜和后上哪些菜的调整和安排”[16]。
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对外译介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虽然目前销路大好的书还不十分普遍,但每一部成功“走出去”的译作,都会成为一粒酵母,诱发海外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点燃对中国文化的热情。翻译书、推广书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渠道,但不是唯一的。叶嘉莹先生指出:“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不是空谈,不是喊口号,要传播中国文化,是不是知道中国文化美好的品格道德所在,是不是能让它们在身上表现出来。一句话,就是要用言行、用实践来传播中国文化。”[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