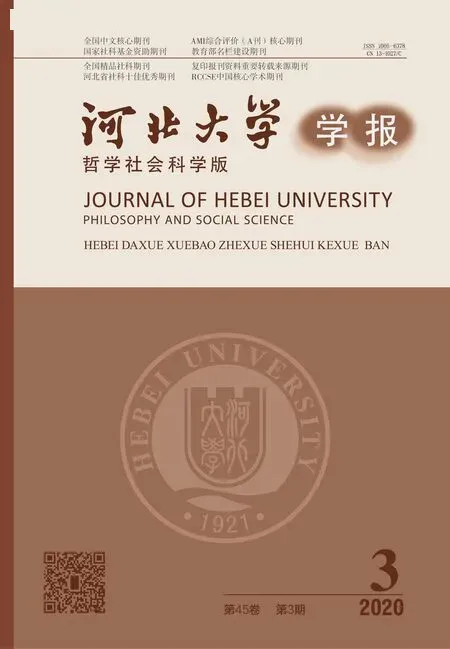蒙古族风格交响乐作品中的审美观
何一波,宋生贵
(1.内蒙古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2.南昌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中国交响乐发展的大背景中,蒙古族风格交响乐创作发展的历程已逾70年。但真正使蒙古族音乐交响化并成为世界乐坛承认的经典交响乐作品,则肇始于辛沪光先生1956年创作的交响诗《嘎达梅林》,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关于蒙古族风格交响乐的唯一作品。20世纪60年代,蒙古族风格交响乐作品为空白。70年代,据不完全统计,蒙古族风格交响乐作品大抵也只有6部左右,且均为单乐章小型作品,但难能可贵的是本土作曲家阿拉腾奥勒先生创作了交响作品《草原音诗》《乌力格尔主题随想》,这也是蒙古族作曲家创作最早的两部交响作品,具有某种程度的里程碑意义。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是蒙古族风格交响乐作品创作的高峰时段。此时段蒙古族风格交响乐作品的创作,除辛沪光和杜兆植等前辈作曲家继续倾情于蒙古族风格交响乐作品创作并力献精品之外,本土本民族的作曲家,特别是永儒布先生和阿拉腾奥勒先生,不仅创作了以《故乡》《第一交响曲》为代表的多乐章鸿篇巨制,使蒙古族风格交响乐创作由单乐章迈向多乐章,同时也为蒙古族音乐的交响化和蒙古族风格交响乐作品走向世界舞台做出了卓著贡献。更为乐见的是,以李世相先生和乌兰图嘎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本土本民族的中青年作曲家积极投身到蒙古族风格交响乐作品的创作大潮中,奉献了一批精品力作。进入21世纪,永儒布先生的大型交响合唱《草原颂》、阿拉腾奥勒先生的音乐史诗《草原组曲》、唐建平先生的大型交响音乐史诗《成吉思汗》、李世相先生的交响序曲《壮美的牧歌》以及叶小纲先生的第四交响乐《草原之歌》等一批优秀作品给蒙古族风格交响乐创作带来了全新的视角、新的生机和希望。
伟大的音乐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听觉上的享受,而更多的是其内部的文化内涵,可以说每一部伟大的音乐作品都有着一种文化作为其支撑,“草原文化是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草原人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1]。蒙古族既是草原文化的奠基者,又是草原文化的最后集大成者。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以自然为主导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草原文化的根本,同时也是蒙古族文化艺术的本源,并且贯穿于新中国成立后至今的所有蒙古族风格交响乐作品中,而其中具体所体现的审美观主要来自对英雄的崇拜、对生命的敬畏、对家园的依恋及对自然的尊崇。
一、对英雄的崇拜
英雄崇拜是蒙古族史诗的基调。以蒙古族先民的英雄史诗肇始,英雄崇拜就一直是蒙古族审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延续至今的蒙古族人的审美标准和蒙古族风格交响乐作品中独特的审美表达。在众多蒙古族风格交响乐作品中,以英雄形象作为主题的作品占很大一部分比例。
如:辛沪光的交响诗《嘎达梅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首部交响乐作品,是蒙古族风格交响乐的奠基之作,是蒙古族风格交响乐的一座丰碑。交响诗《嘎达梅林》,为单乐章奏鸣曲式结构,以同名科尔沁民间叙事诗《嘎达梅林》为蓝本,主题旋律源自科尔沁叙事民歌《嘎达梅林》,该民歌传唱甚广,蕴涵了崇尚自然、崇尚英雄的蒙古族文化的基本特征。
叙事民歌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末,蒙古族英雄嘎达梅林为了蒙古族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生活,与封建王爷和军阀作斗争,最后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表达的是蒙古族人民对嘎达梅林的怀念和歌颂,以及蒙古族人民对争取解放、寻求光明和幸福的坚定意志。作曲家辛沪光以同名科尔沁叙事民歌为主题材料,运用标题音乐的创作手法,以富有戏剧性的单乐章奏鸣曲式为基础,结合叙事民歌故事的发展情节,运用相对自由的结构形式,创作了交响诗《嘎达梅林》。当音乐奏响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叙事民歌《嘎达梅林》中的音调和画面,从而把作曲家的乐思和情感清晰明确地呈现至鉴赏者面前,展现了民族英雄嘎达梅林率领人民与封建势力和军阀斗争的曲折迂回。作曲家将景色描绘与情感刻画相联系,以景衬情,借景抒情,情景交融,音乐形象十分具体,宛如现实生活中的一幕戏剧。整部作品气势磅礴、雄劲豪迈、悲壮沉郁,述说了蒙古族人民心中永远不灭的历史记忆,热情地讴歌了嘎达梅林这位民族英雄。
除《嘎达梅林》外,吴祖强、王燕樵、刘德海等人的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莫尔吉夫的第二交响组曲《成吉思汗》、查干的交响诗《悲壮的东归》、唐建平的大型历史题材交响合唱《成吉思汗》等作品中所体现的也是蒙古族的英雄精神,歌颂的是蒙古族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代表着蒙古族共有的价值观,引领着蒙古族人民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方向。
蒙古族风格交响乐作品中的英雄审美思想与蒙古族的传统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古时期,进入到部落氏族社会的蒙古族先民,由于部落征伐、氏族内部势力的争斗,生产生活的重心从与自然和野兽的抗争转到反对外来氏族侵扰和进攻其他氏族上来,文学也从自然神话中对自然力的神化和摹写转到对英雄人物部落首领的崇拜。在蒙古族民间文学中,大量的中短篇长篇史诗,都描绘了主人公为保卫自己的亲人和家乡而同敌对势力英勇战斗的故事,英雄们的名字虽然不同,但他们所肩负的使命,他们所具有的英雄精神却是相通的。这些英雄形象植根于草原游牧生活的现实土壤中,所体现的正是蒙古族人民刚毅、纯朴和勇敢的性格和力量崇拜的特有民族审美倾向。“草原文化重个体的思想观念,首先表现在全体社会成员都向往英雄、崇拜英雄以及为成为英雄而努力的现实行动上;其次表现在对个体生命价值和个性自由的肯定、践行和追求上。”不论是蒙古族古老宗教里具有英雄形象的保护神、民间文学里中对民族英雄的赞颂,还是对成吉思汗的崇拜,都可看出蒙古族人对英雄的崇拜从未衰减。英雄的精神激励着古代蒙古族人开创了属于自己的英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英雄时代一直是蒙古族人记忆的一部分,即使在历史发生了决定性转折之后,在他们的情感深处仍然保留着有关那个时代的记忆。英雄精神从未在他们的情感中消失,从未在他们的记忆中抹去,并已成为他们所追寻的永恒意义[2]。蒙古族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一直是民间文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以及音乐学等诸多蒙古学领域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江格尔》《格斯尔》以及在科尔沁地区流传着的大型系列史诗——《蟒古思因·乌力格尔》等英雄史诗里,所展现的正是蒙古族先民早在氏族时期的最为淳朴的英雄崇拜情结。
二、对生命的敬畏
蒙古族风格交响乐作品中不乏对蒙古族地区自然风貌的描写,但这样的描写不仅仅是对草原、河流、牛羊的刻意描绘,更多体现的是作曲家对草原“母亲”、河流“母亲”的尊崇,也是对整个蒙古族生命意识的赞叹。
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永儒布先生的《额尔古纳河之歌》,作品中所描绘的是蒙古族的母亲河——额尔古纳河河水的流动过程,隐喻的是民族成长的历程,抒发的是对于生命的敬畏之情。额尔古纳河上源为海拉尔河,发源于大兴安岭西侧吉勒老奇山西坡,西流到新巴尔虎左旗阿巴图附近,后折向东北在额尔古纳市恩和哈达附近同俄罗斯流来的石勒喀河(一般称为黑龙江北源)汇合为黑龙江。额尔古纳河以海拉尔河为上源,右岸为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她不仅是蒙古族等众多游猎民族发祥地,同时也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故乡。
《额尔古纳河之歌》采用呼伦贝尔民歌元素创作而成。呼伦贝尔的民歌种类十分丰富,有巴尔虎长调歌曲、达斡尔民歌、鄂温克民歌和鄂伦春民歌。巴尔虎长调表现了蒙古族巴尔虎人质朴、爽朗及热情豪放的民族性格,体现了草原辽阔、自由、奔放的气势。巴尔虎长调的特点是舒缓、悠长,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怀念故土为主要内容,目前传唱最广的是乌日汀哆。达斡尔民歌、鄂温克民歌和鄂伦春民歌则以抒发对祖国、对蓝天白云、对草原和牛羊的热爱为主要内容,抒发着当地人民崇尚自然的情怀。关于《额尔古纳河之歌》的主题风格,永儒布先生阐释道:该作品的民族创作元素是交织混合在一起的。主题中,音乐旋律流淌着鄂温克风格,同时也渗透出巴尔虎民歌的特点。蒙古族人生活在额尔古纳河流域,额尔古纳河是养育蒙古族人的母亲河。而实际上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生活着多个民族,鄂温克、鄂伦春族在历史上就曾多次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生息繁衍。因此,只采用某一种民族音乐风格不能体现额尔古纳河流域的民族特点。同时,单独使用一首民歌也远远表达不了河流宽广、源远流长的特点。所以在主题风格的选用上,选择了呼伦贝尔地区混合的民族音乐风格特点[3]235。在《额尔古纳河之歌》中,作曲家把“如画”的江山和蒙古族发展的历史足迹以及人生体验相交织,描绘出一种高尚隽美的意境,深情地叙述了一段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话,通过隐喻和象征的手法,表现了大自然的和谐完美与人类历史的壮丽浩荡以及每一个生命主体无限丰富的情感世界,体现了蒙古族“对生命的敬畏”及蒙古族生命观中的“无限与永恒”的审美观。
蒙古族从远古时期就有着敬畏生命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当时更多地体现为生命崇拜。例如《蒙古秘史》当中所提到的“阿迷”(ami)就是“声、生命、性命”的意思。古代蒙古族人信奉“天父地母”,认为“一切生命皆是天神所赋予”,在古代,蒙古族的古老宗教崇尚的是“万物皆有灵”,所有的生命都可视为神灵,都有平等生存的权利。这也是一直以来蒙古族人把一切生命体跟自己的生命同等对待的思想基础。“蒙古族人虽然早已认识到生命的有限性和短暂性,但是他们依然追求‘生命’的无限与永恒,于是形成了‘灵魂不灭’的观念。”[4]因此,蒙古族崇尚“生命”、敬畏“生命”、珍爱“生命”形成了尊重生命,和谐共存的生命意识。
蒙古族对于生命的意识更多的来源于对自然的敬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中所包含的所有内容也都成为蒙古族人所敬畏的对象,母亲在蒙古族人民的心中是最为崇高和伟大的,所以对于孕育生命的载体——自然,便成了所有蒙古族人心中依托的对象,蒙古族地区所常见的自然风貌——草原、河流自然就成了蒙古族人民心中的“母亲”,这样也就有了对所有生命的敬畏之说。
三、对自然的尊崇
在所有的蒙古族风格交响乐作品中,每一部作品中都有着对草原、羊群、马群等蒙古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描绘,这是蒙古族风格交响乐作品区别于其他民族风格作品的标志性特征,也是蒙古族艺术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现。在众多的交响乐作品中,永儒布先生的《蜃潮》更显得独树一帜。
关于标题《蜃潮》,永儒布先生是这样解释的:“蜃潮是草原上的奇景,雨过天晴后,升腾的水蒸气与阳光融合产生水晶般无数的光点闪烁。蒙古包、牛羊,甚至高山从远望去好像在大海中翻腾、忽隐忽显,不知大地还是天空,映出一幅奇幻无比湛蓝缥缈的图画。”[5]作品中最为引人入胜的应该是A 段的最后部分,作曲家加快了各乐器音型的节奏,以渐强的力度将音乐推向至第一个高潮点,将所有在A 段末尾参与演奏的乐器以八分音符的短音突然结束在了B段主调C 徵的主和弦上。但音响并没有完全停止,由潮尔、埙及英国管在八分音符结束音之上同时奏响的新调主音犹如“号角”般的音色从猛烈的音响中显现,就像阳光突然从厚重的云层透射下来,洒向草原,有如天神下凡一般。
蜃景并不多见,只有最幸运的人才能一览其全貌。可想而知,当人们见到蜃景的时候,并不知道眼前的一切到底来自真实的世界还是虚幻的空间,但无论是真实还是虚幻,在这壮丽的景观面前,所有人都会发出感叹,感叹着人类的渺小,感叹着自然的无限,油然而生的是敬仰之情。作曲家将这种感叹交由中提琴、大提琴、贝斯、人声的低音与小提琴以主和弦持续音的方式表现出来。浑厚的低音与飘逸的高音配合,极其形象地代替了他们所要模仿的音色原型——呼麦。
呼麦,亦称“浩林·潮尔”,与潮尔琴一样是蒙古族最古老的艺术之一。演唱者需运用特殊的发声技巧同时发出两个声部的音,两个声部由一个持续的低音及上方可控的旋律泛音组成。“呼麦演唱的最初动因应该是:通过声音来模拟自然界自身的存在,力图表现‘天—地’的广阔空间,以及天地与人的密切关系。”[6]蒙古族呼麦的发展历史与原始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关系。蒙古族古老宗教自然崇拜观念中,以“天—地”“日—月”“山—河”为崇拜对象。然而,这些自然现象均处于对立的模式,但虽彼此对立,又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缺少一种,自然界便无法构成完整与和谐。
作品在B段所表现的看似在描绘草原蜃景的神秘及壮观,但此段音乐的听感却让笔者脑海中很清晰地浮现出“朝圣”两个字。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来自当笔者将听觉集中在具有宗教色彩的呼麦那浑厚的低音及透明的高音上时,它衬托出的上方主题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深远、神秘,而感受更强烈的是其带来的神圣之感,有如神灵现身一般。由于蒙古族传统自然观是蒙古族先民对自然最原始古朴的一种敬畏之情和神化意识,具有鲜明的神话特点,所以,可以叫做神话自然观,也可以叫做游牧文明自然观或草原文明自然观[7]。所以之前对蜃景画面的描述中,笔者并没有提到蜃景中所出现的事物,因为在这幅画面里所包含的并不完全是景物、事物,而更多包含的是对大自然的崇拜,以及对蒙古族的神灵“腾格里”的敬畏。
蒙古族逐水草而居,所追求的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大自然在蒙古族的心里是充满亲情的,是人格与心灵的象征。就像之前所提到的“她”在蒙古族人民的心中是以母亲的形象一直存在着,蒙古高原有着广阔无边的土地、一望无际的草原、奔腾不息的河流,大自然不仅赋予了蒙古族非常美好的生活空间,同时也造就了蒙古族人宽阔的胸怀和特有的个性。因此,蒙古族对自然怀有崇敬之情,有着热爱自然的强烈审美意识。
四、对家园的爱恋
蒙古族风格交响乐作品中,与家园相关的作品最具有代表性的来自永儒布先生的《故乡》。《故乡》由三个独立带有标题性的乐章组成,分别是《荒寺》《雁归》和《奔驰》,从对标题的解析中可以看出作品所要描写的更像是回家之路的经历,但结合永儒布先生的自述,笔者发现作品中真正要表达的其实是对民族精神的解答。
“家园”在美学的定义中是可以真实存在的,也可以是理想中的美好情境。在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中,均不乏对于“家园”的描写及情感的表达。当然,这里的“家园”已不仅仅是生存的居所,而更多的是代表一种精神的依托之所。家园意识两个主要的内容分别是“现实家园”与“理想家园”,字面上的解读就是一个是“不完美”一个是“完美”,“完美”的“理想家园”的实质是个体在自己意识中所建构起来的,其建构的根基一定是“不完美”的“现实家园”,将现实中的“不完美”“完美化”。当个体置身于“不完美”的现实家园,就会产生一种“离家之感“,感受不到“家园”的庇护,从而使人在内心对生存场所产生一种不认同的排斥感,急切地想要回归到自己意识中建构的理想家园。
永儒布先生的《故乡》所描述的正是从“不完美”的“现实家园”到“完美”的“理想家园”这样一个过程,记录的是蒙古族历史中一处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节点,更确切地说是对蒙古族精神回归过程的展示。“过去的民族受到压迫、人民就像生活在孤寺的僧人一样束缚在精神的枷锁中。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严寒己经过去,雪开始融化,人们要像春天一样迎接美好的明天,民族要像春天一样开始发展,一切事物都要像春天一样欣欣向荣。”[8]作曲家将自己化作误闯荒寺的“无助人”、化作北归雁群中的大雁、化作奔驰马群中的骏马,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蒙古族的历史进程,展现了蒙古族的沉睡—唤醒—回归—解放—繁荣的过程,所以作品的第一乐章《荒寺》在对蒙古族历史的那一处节点及对“家园”情感的描写中体现的更多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后续用了两章的内容描绘了整个回归“家园”的过程,让笔者也深刻地体会到回归的幸福之感。所以《故乡》中的“家园”在笔者看来涵盖了故乡、家庭、居所,更主要的是代表了一种对精神的依恋,对蒙古族的精神家园的依恋。
家园与母亲一样,是人们在心理的最后一道防线,最后一道港湾,当我们在探讨自身的家园时,无不会触及心里最为脆弱的一面,所给予的是最深的依恋。“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中,‘乡’始终作为一个底蕴极为丰厚的概念存在着。恋乡、思乡、寻乡、归乡等,是人们深层的心灵指向,也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经久不衰的命题——包括乡愿、乡怨、乡愁在内,都表明人们与‘家园’既生息所依,又灵性所系,是根性的存在,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情结’。”[9]蒙古族的家园意识或者故乡情结,最直观的体现是与本民族自然生态、生产生活方式及因此而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与蒙古族“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大美学背景是完全契合的。而具体来讲蒙古族家园意识有两大核心概念,即“草原”和“母亲”,无论是在文化还是美学的视域中,草原已是自然与人文的重合之处,是由众多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但对于家园的理解并不是完全物化的,它可以是真实存在的,可以是一种思念的表达,同时也可以代表着民族精神的驻地。
蒙古族风格交响乐作品是蒙古族音乐的集大成者和典型缩影,是蒙古族音乐文化的重要标志和载体,也是蒙古族音乐通向世界乐坛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蒙古族风格交响乐作品与蒙古族民间音乐血脉相连,是民族历史和民族精神实质及以自然为主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统领的对英雄的崇拜、生命的敬畏、自然的尊崇及家园的爱恋等蒙古族审美观的审美映射,是蒙古族音乐创作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也反映着这个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和审美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