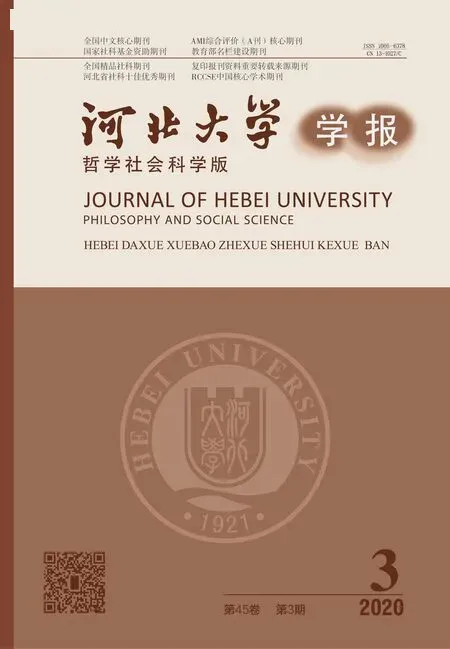北美华文文学的文化反思
——以《芳华》《忠臣逆子》为例
倪学礼,张 琪
(1.中国传媒大学 通识教育中心,北京 100024;2.中国传媒大学 戏剧影视学院,北京 100024)
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相遇、互融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一时代语境下,中国要想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一个自信强大的国家形象,必须要对自身文化有更为清醒和全面的认知。西方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版图中的“他者”,恰如一面可以镜鉴自身的镜子。北美华文文学正是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夹缝处及二者相互融合的交汇地带产生的。相较于其他作家群体,北美华文作家的优势就在于他们既对中国文化有根深蒂固的了解,又对西方社会的生存状态有更为切近的体会;亦即他们同时与中西两种“文化法则”打交道,在两种文化世界中沉浮。对于中国文化,北美华文作家往往既能以身在其中的感性体悟进行把握,又能以跳出其外的冷静视角进行反思,北美华文文学因此便也天然地带有世界公民的视角和文化反思的意味。所以,跨文化与文化研究视角一直是备受北美华文文学研究者青睐的批评、研究方法,学界也积累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是,笔者以为对北美华文文学的“文化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宽泛的文化概念或具体的文化习惯与文化现象上,而是要上升到先验于个体此在,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的哲学高度加以探讨。为此,本文采用现象学存在论的视角,以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袁劲梅的中篇小说《忠臣逆子》为例,力图通过对作品的详尽阐释来揭示北美华文文学关于中西两种不同“文化法则”的根本性思考,以期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
一、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的“文化”的哲学释义
按照现象学存在论的观点,存在不是一个实体性的东西,它不能作为认识对象被我们直接把握,而是一种显现为“无”的最高普遍性,它要么在感性个体的生存方式中显明自身,要么自行隐蔽。在所有存在物(人、日月、石木、观念实在、器具等)中,只有人能显明存在,因为只有人才具有生存方式[1]。“人是这样一种存在物,这种存在物的存在是通过存在的无遮蔽状态的敞开的内在性,从存在出发,在存在之中标志出来的”[2]。人在存在中与存在打交道。那么人如何存在? 海德格尔称为“此在(Daseine)”。“da”这一词缀在德语中为“此时此地”之意,这表明:人既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同时一定有某个“场”供存在显现自身,这“场”乃是人所生活的“世界”。“世界”并非外在于人的一个物理空间,而是与人浑然一体的,人在世界中存在,须臾不可离也,离之,人也不复存在。那存在者究竟是怎样从存在变为存在者的? 这一问题于海德格尔似乎也是不可解的,故曰:“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我们在世之前,世界即以世界的方式存在着,人要想生活得好,必须熟悉、掌握这个世界的“法则”。申言之,人之别于他类“存在者”在于:人不但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存在,还是一种文化的存在。
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观点,人在逻辑层面上有两重“天”——自然之天和文化之天。《易·贲卦·彖传》有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自然之天”为我们提供生存所需的基本养料——阳光、土壤、空气、水诸如此类。刚柔交错、阴阳相生乃自然之道(运行规律),此为“天文”(亦为“地文”);饥欲食、渴欲饮、困欲睡是人存在于自然界所必须遵从的自然法则。“文化之天”是人作为一种文化存在为自己的生活世界建立的意义规范;礼乐典章、文治教化乃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法则,此为“人文”。人生在世既要遵循自然意义上的天道运行规律,又要学习、推广人伦道德等文化世界的活动规律。人总是在“思”中领悟着“在”,“思”之印迹深深浅浅,那些在时间中留下的便形成“文化之道”(文化法则)。因而,“文化之道”虽先验于个体此在,需要作为个体存在者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学习适应,但它毕竟是一个历史性民族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用智慧创造的,其目的在于使人生活得更好。且不同时空环境中的人创造出不同的“文化法则”,比如“仁、义、礼、智、信”“自由、民主、法治”等不一而足。这些不同的“文化法则”均乃人生在世的一种“活法”,究竟哪种“活法”更高明尚未可知。因而,“文化之道”非但不是不容质疑、不可改变的绝对命令,还恰恰需要每一个当下存在的“此在”不断反思、不断突破。因为人生在本质上就是一场对存在的领悟与筹划,故而唯有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永不停歇地开辟着“思”之道路,进行着“思”之“思”,一个民族的“文化之道”才能越来越趋向“幸福”,趋向我们最终想要到达的地方。本文对北美华文文学的文化反思的探讨皆是在上述意义上进行。
二、《芳华》的“白舞鞋”与“黑布鞋”
严歌苓的作品一直蕴含着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反思意识。比如《第九个寡妇》透过主人公王葡萄的人性光芒,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那段“大跃进”、假大空、极左主义的历史进行反思;《陆犯焉识》中男主人公陆焉识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反抗,对特定历史时期精神枷锁的挣脱以及对知识分子自由信念的追求等。201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芳华》更是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了“文化大革命”末期的时代群像。与其说这部作品是作者对青春岁月的半自传式的感性缅怀,不如说是对那个充满了英雄情结与理想主义色彩的特殊历史时代的理性反思。作品通过对刘峰、何小曼两个典型人物的塑造及其与整个历史环境中芸芸众生的冲突与角力,展现了特殊时代环境下人心的基本处境,描画了长久浸润于中国这片“文化之天”下的国人独特的民族心理结构以及埋藏于人性深处的内在灵魂形象。
(一)“白舞鞋”——英雄刘峰的幻灭
小说的主人公刘峰是一个有着不偏不倚的“五刻度”长相的人,没有亮点,也没有缺陷,让你转身就能忘记。在那个穿军装、戴军帽、整齐划一、消灭个体个性、强调集体主义的时代,刘峰不突出的长相可以说是最符合时代标准的范本。他本人也是那个时代不折不扣的道德楷模:挑水、补墙、拆地板、打沙发、堵耗子洞、钉门鼻儿……一切脏活累活他都心甘情愿地干。“找刘峰!”甚至成为文工团的男男女女们遇到困难时脑袋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他是全军学雷锋标兵,甚至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最高美德的化身。如同他的相貌一样,其人品、德性也好得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
他的相貌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没有问题。[4]
作者开篇对刘峰相貌的评价似乎为这个在外貌与内心都堪称完美之人的悲剧式命运埋下了伏笔。“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在那个到处充满学习口号与道德标语,人人钟情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虚假年代,刘峰这颗不掺杂半点私欲的良善之心好得让人们觉得不真实。于是大家在潜意识里都怀着一种期待刘峰暴露人性丑陋面的看戏心理,等待这一英雄形象的崩塌,直到“触摸事件”发生。
“触摸事件”可以说是整部小说的故事内核,也是刘峰命运的转折点。他大概是在一次指导声乐队演员跳舞的形体课上,因为偶然看到林丁丁踢腿时不小心从裤管中发射出的被血泡糟的月经纸而对林丁丁产生了最初的迷恋。一开始,这种迷恋可能是出于一种生物性的生理欲求,但经过刘峰长久的理性压制后,这份迷恋逐渐升华为刘峰灵魂深处滚烫火热且无法抑制的爱,直至爆发。刘峰在情感驱动下对林丁丁的表白与触摸原本是一个对爱充满渴望的年轻人的正常情感表达,但却被林丁丁乃至整个文工团的战友看作是肮脏可耻的,因而遭受保卫科的下流审查以及文工团大会小会的公开批判,刘峰的命运自此彻底转变。
来自人性深处的“触摸事件”无疑撕下了整个时代的虚伪面纱,揭露了在中国特殊“文化法则”的矫饰下,人心的真实面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尤为强调“真诚”的民族。《中庸》有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5]。“诚”乃天道,是天地运行的基本规律;而对“诚”的追求,乃人生在世的根本原则。将《中庸》对诚的解释稍加扩展我们可以推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忍善”等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均乃先于个体生命而存在的“天道”(中国传统文化之天),故其对每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有着本质上的规定——循其道。因而,在根本上,诚信、良善之品质并非人的“可能性”存在,而是对人性的一种“必然”要求,是中国这片特定的“文化之天”所赋予的。诚如《孟子·尽心上》所云: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5]328。故人行天地间贵在反求诸己,对一切美好道德品质的追求都是一个从自我出发又归于自我的向内求取过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处处贴满道德标签、充满理想主义、忠于表彰与批判的年代,表面上人人勤于反思、追求进步,但当刘峰这样一个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符合时代对一个优秀、良善之人的所有要求的“时代精品”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时,人们却在潜意识里持怀疑态度。这恰恰表明,人们从未发自本心地相信、认同自己学习、表彰的道德准则,而是把“英雄”“道德楷模”等一系列被主流价值褒奖的概念看作是与自身实际生活毫无关联的遥远的“称号”。在“触摸事件”发生之前,刘峰就是这样一个远在云端的“道德英雄”,他是画作上的人物、雕塑上的人物,是舞台剧、样板戏中的人物,是飞离了现实大地,被人们当作“圣人”高高供奉的雄伟的“道德图示作品”。人们在潜意识里把一个社会的道德原则推向自身之外,成为用来要求别人的行为规范,而不再是人人都要反求诸己、循其道而行之的根本原则,却成为与自己全然无关的“道德模范”的终身事业。
人们把“道德英雄”推向自身之外,也就否定了道德原则的现实根基。在“触摸事件”发生之前,刘峰作为“道德模范”,甚至从未被大家当作有七情六欲的“正常人”看待。“道德模范”与“人”的分裂是人们将道德原则推向自身之外的必然结果。当人们把“人性”的本质从“英雄”的概念中抽走,“英雄”也就成为挂在天上的“道德宣传画”,失去了实质性的内涵。于是刘峰作为被这个时代所塑造的纯粹外在于“正常人”的“假人”,自然不被允许有半点源出本性的食色之心。而这一记暴露人性的“触摸”恰恰揭露了那个时代人们所追寻的道德理想的虚幻性。
食色之心在那个过分矫作的年代被看作是丑恶的。与此同时,人们也并没有认识到“善”与“恶”、“真诚”与“虚伪”的一体两面性。人之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有“内心”,这“内心”是与“外表”相对的独立私密的精神维度。人的“表情”可以看作是其“内心”情感的外在显现,但“显情”的同时也是一种“隐情”,因为相对于他人,每个人的“内心”都是独立私密的,故人有将其保护起来的权利,这种保护便可理解为是一种“伪装”(“伪”取“人为”之意)。动物没有“伪装”能力(指“有意”而为,其在危险时刻出于自我保护而对环境做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欺骗效应”除外),它们只能单向地承受。因此,一切在表面上对立的道德准则——“善”与“恶”、“诚”与“欺”、“忠”与“奸”等在本质上都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真正的真诚,是在意识到这种真诚有可能是虚伪时才产生的,是对自己的真诚永不满足和随时拷问[6]。同样,真正的行善,是在意识到自己有可能作恶时才产生的。中国文化缺少西方文化的原罪意识,但在原则上,作为中国这片“文化之天”的运行规律的美好道德准则(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对个体之人的“必然”要求是在先验意义上的,它并不能在经验层面保证每个人都不会作恶。所以,我们不能以“天道”来证明自己的“善”,而是要不断反求诸己、自尽己心,用对“善”的不断追求来保证中华文化的“天道”。
文工团的男男女女则是将“是非善恶”全然分裂开,如同刘峰脚上黑白分明的两只鞋:
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右脚穿军队统一发放的战士黑布鞋,样式是老解放区大嫂大娘的设计;左脚穿的是一只肮脏的白色软底练功鞋。后来知道他左腿单腿旋转不灵,一起范儿人就歪,所以他有空就练几圈,练功鞋都现成。[4]6
这是一个极具隐喻色彩的细节设置,“黑布鞋”好比人的人性底色;而那双能跳出优美舞姿的“白舞鞋”则象征着人性可能散发出的道德光芒。刘峰是一个知道自己缺陷——左腿单腿旋转不灵,并勤于苦练、努力弥补的人;同时也是在道德品性上不断锤炼自己,将对良善品德的追求视为同舞蹈一样需要终生修炼的人生事业的人。文工团男男女女的问题在于他们将“英雄”与“常人”、“美德”与“人性”全然割裂,最终导致刘峰那一记出于本心的“触摸”给人们带来的惊怵、幻灭、肮脏与背叛之感,而这只暴露人性的“黑布鞋”彻底粉碎了人们对“英雄”所抱有的美好圣洁的幻想。刘峰自此从神坛跌落,甚至也不配被称为一个“人”,大家带着一种集体宣泄的变态情绪对其进行下流的审查和惨烈的批判。刘峰的命运自此彻底改变。在被下放至伐木连的前一晚,刘峰将装满了优秀标兵证书、奖状、奖品、锦旗的箱子交给了何小曼处理。
一个虚伪的时代所馈赠给人们的一切荣誉都是顷刻间便可被颠覆的虚假幻象。曾经被表扬、被学习的“全军道德模范”刘峰一夜之间就变成人人唾弃的“道德走狗”。表面上人们欺凌践踏的是暴露人性丑恶面的刘峰,实际上却亲手将自己塑造的这一代表人性最高美德的“时代精品”砸得粉碎。于是那个时代所宣扬的一切善良的美德、崇高的信仰都如同印刻在奖品上的“先进模范标兵”的字迹一样,只是一个空洞的标签,那字迹越鲜红耀眼,对自身的讽刺便越犀利尖刻。而埋藏在这些光鲜华丽、虚伪造作的“道德标签”之下的,却是一片荒诞冷漠的现实世界。
后来,刘峰参加越战立功之后谢绝了一切英模会的邀请,他早已在那个夜晚看穿了时代的虚伪:昨天拥戴你的掌声一夜之间便可成为今天痛打你的拳头,而在你“立功”之后这些拳头又在转瞬之间变成把你托至神坛的撑手。拥戴也好,痛打也罢,其背后都是不含任何人性与真情的冷漠与空洞。而那只在战争中失去的触摸过林丁丁的右手,无疑是整个变态的时代对这样一个好人在身体上与精神上的双重阉割。
(二)“黑布鞋”——何小曼的分裂
何小曼也是整个“芳华”时代的悲剧人物。她一出场就是一个穿着两只破旧不堪的“黑布鞋”趔趄踉跄的“丑小鸭”。文人父亲被划做“右倾分子”,服药自杀。改嫁后的母亲对何小曼更是冰冷,甚至连一个拥抱都要通过发烧才换得到。何小曼本以为来到文工团后会迎来崭新的人生,却不曾想,迎接她的依然是一个无爱冰冷的集体。大家对何小曼的捉弄是从揭开她那戴得严严实实的军帽下的秘密开始的。在那个争做“公家的人”、强调集体主义的时代,何小曼那一头带着无数小弯且乌黑浓密的沙发,将她作为异于常人的个体的渺小首次暴露凸显在集体面前,再加上她的家庭出身、特殊的成长经历养成的特殊癖好,以及那个廉价的“丰胸乳罩”的暴露,使她彻底被战友当作一个与公家对立的“异己分子”而肆意欺凌践踏。
何小曼的“丰胸事件”和刘峰的“触摸事件”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暴露了人作为个体存在的“内心”,即人性中那只不假修饰的“黑布鞋”。那个特殊的年代,到处都笼罩着追求纯洁、真诚、“亿万人民一条心”的文化氛围:向党交心、交日记、自我揭发……一切向组织袒露自己内心的行为都在于消除私心。能遮盖个体差异、性别差异的“军装”曾一度成为流行服装流行开来。然而,如上文所述,人之所以为人,人之与动物的本质差别就在于人有“内心”,故对这“亿万人民一条心”的追求越彻底、越纯粹,所产生的结果反而越虚伪、越造作,最终必将走向反人性的极端。
那时我的真话往哪儿都不写。日记上更不写。日记上的假话尤其要编得好,字句要写得漂亮,有人偷看的话,也让人家有个看头。[4]16
一个表面上忠于反思、忠于自我批评的群体却从来不写真话;文工团的成员跳舞可以溜边,唱歌可以充数,这些本职工作做不好都没关系,只要做好了本分之外的事,组织的视野自会巡视到你。由此可见,人们对真诚、袒露本心的追求已经走向了虚伪、包装本心的极端反面。但当时的人们显然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她们仍然终日忙碌于矫饰自己。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人们对自己的行为与内心的矫饰就如同在进行一场技艺精湛的走钢丝表演,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人们当作脱离于集体的对立者恶意攻击。
何小曼就是这样一个没人疼、不怕死、不惜痛,甚至在潜意识里还有求死之心的可怜虫。她是一个不被集体触摸的人,唯有好人刘峰心甘情愿地跳出来与她组成搭档。可是很快,刘峰作为集体一分子所带给她的微薄的暖意就随着“触摸事件”彻底破碎了,刘峰在一夜之间变得比何小曼更遭人唾弃。自刘峰被这个集体抛弃之后,何小曼就已经对这个集体、这个世界彻底失望了。后来在阿坝为即将解散的骑兵团和军马场表演的那场“小战士”的独舞是她人生中唯一一次绽放,她终于被集体捧在手心,做了一回掌上明珠。然而一个虚伪的时代给予一个渺小个体的荣誉毕竟也是虚假的,这场梦很快就破碎了,迎接她的生活是无止境的深渊……
何小曼因为调换体温计、假装高烧被团长下放到野战医院,后来中越前线战事爆发,她作为护理员在前线搀扶受伤男兵步行十多里的路,途中遇上了纪录片摄制组。第二天,何小曼的照片就上了报纸,旁边赫然醒目着一行字——“战地天使何小曼”。是的,一个曾被集体唾弃的可怜虫成为高尚圣洁的“战地天使”了。于是一场场“向何小曼学习”的报告会接踵而至,她每天忙着读政治部主任为她提前写好的稿子,稿子的内容无一例外的都是关于代表人性高尚品质的“白舞鞋”是如何战胜自私贪生等人性底色的“黑布鞋”的心理活动。而在现实中,代表人性底色的“黑布鞋”必须时时被隐藏在“白舞鞋”之下,不允许有一丝暴露。何小曼终于没有从这场突如其来的荣誉的“伏击”中突围出来,她精神分裂了,她是戴着大红花被送进精神病院的。
何小曼的精神分裂是一个时代分裂的标志。在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代,“骂”与“捧”都是冰冷的杀人锋刀。对于何小曼而言,她曾经遭受过的欺辱与痛苦,是如今多少的勋章与荣誉都弥补不了的;相反,她收到的荣誉越多,越是对她曾经遭受过的痛苦的讽刺,越能说明时代的可笑。
刘峰与何小曼都是亲历过这个时代的“两个极端”之人:一个被人从高高在上的神坛拉下又试图将其送上“神位”,另一个被人从低入尘埃的泥坑中拔出,又推上荣誉的云端;一个被时代塑造的道德模范、良善之人却遭受了时代最无耻的唾弃和人性最阴暗的对待,另一个最不被生活善待的人却最懂得识别与珍视这个世界的良善。对一个时代、一种文化的反思必得要深入骨髓才能从根本上加以匡正,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在小说的结尾,严歌苓并没有给现实以光明,而是通过揭示人世间的悲凉底色激发人们更深入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后,在原来文工团的战友都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相继升官发财之时,刘峰却挣扎在社会最底层靠卖盗版书谋生。尽管如此,生性良善的他还经常推荐一些有意义的书给发廊妹看,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感化那些在时代与金钱的诱惑下出卖自己的年轻人。然而如此纯良温厚之人却依然没有被人们记住,甚至于刘峰的亲生女儿在谈及自己的父亲时都是用一种局外人说故事且略带鄙薄的心态讲述的。一生谦让的刘峰连自己的葬礼也是谦让给别人、匆匆举办的。市场经济时代,一切都以金钱和效率为标尺,医院的灵堂也变成按小时出租的赚钱工具。何小曼为刘峰写的悼词终究没来得及读,刘峰的亲人也没来到现场。当年的道德楷模、为保卫国家失去了一只手的战争英雄在如今的时代依然没有被善待,他就像一张泛黄破败的日历纸、一个废旧生锈的螺丝钉一样,被时代欣欣向荣的改革春风撕掉、被社会高速运转的雄伟机器换掉。一个时代的英雄,没有脚注,就这样匆匆消失在下一代人的视野中,其中的精神品质也终于没有得到流传。好像人们只要不再开表彰大会和批斗大会就算改正了时代的错误,然而,“好人”在这个时代却成为一个略带讽刺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词。“刘峰”的悲剧只是换了不同的形式,却依然在上演……
三、《忠臣逆子》的“戏局内”与“戏局外”
袁劲梅是美国克瑞顿大学的哲学教授,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均有深入的研究,她的作品是典型的“以中西文化比较的手法写下去的”。正如她在中篇小说《忠臣逆子》的序言中对文化的解释:“文化不是抹在脸上的粉子,是人性下面的东西。”因而,袁劲梅作品中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与反思绝不是浮于表面的,而是通过对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人性的捕捉来探索潜伏在人性下,对其起着主导作用的文化之根。她作品中探讨的“人性”是区别于“纯人性”的一种作为文化存在的人之“性”,是北美华文作家中着力于文化反思的典型代表。
《忠臣逆子》讲述了戴家四代人的家族变迁史。作者分别用了培根的“四假象说”——“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剧场假象”“部落(种族)假象”①“四假象说”是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观点。他认为:人只能看到事物的假象,原因在于人们常常容易受错误的观念以及认知主体自身幻觉的影响而在认知过程中掺进了很多幻想的成分,并根据虚幻成分的不同,分为“部落(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剧场假象”四种不同的假象。作为导读,串联起小说的四个章节,暗含了人类对世界认知的局限性。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之天”,这片“天”是世世代代的子民在自己栖身的大地上争得的一片生活世界,有着独属于自己的生存法则。因而人的视野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被这片“文化之天”所影响,这影响既包含先天的因素,比如集体无意识、主流意识形态、特定的文化传统等,也包含后天的因素,比如个人所接受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以及特定的生活经历等。关键在于人能否意识到自身视野的局限性,跳出惯常的生活世界,反观自身以突破局限。正如小说中奶奶教“我”看戏时说的一段话:
人年轻的时候都在演戏,演戏的时候,就跳不出那个戏局,到老了就爱看戏,看戏的时候,还是跳不出那个戏局。人在戏局里,好坏都由戏局定了。啥时候人演戏、看戏的时候,都时时知道那不过是个戏局,人就真会看戏了。[7]
(一)戏局中的“辫子”
戴家人无疑是生活在“戏局”中的。戴家大宅院的门楼上有一块写着“英烈五世,忠杰同堂”的大红牌匾。一进门楼,院子当中还有一个刻着红字家训——“洞察天地,唯忠、孝、仁、义、信立于其间”的青石。这块青石上的红字可谓是曾爷爷辈的戏局设定:以传统儒家“忠、孝、仁、义、信”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镇守边疆誓死做大清的忠臣、保卫自己的“辫子”。与此同时曾爷爷的两个儿子——“我”的爷爷和叔爷爷,一个在暗地里娶了个大脚女人;一个抛弃了家里的童养媳,在中年之后做了汪精卫的御医。显然,爷爷们的戏局设定与曾爷爷大有不同,他们代表着推翻封建统治,推动民族解放的崭新力量,而爷爷们要想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必得剪掉曾爷爷的“辫子”,与封建旧势力的产物一刀两断。到了爸爸这一代,青石被搬到了养猪场,戏局便也随之变更,新力量不再是爷爷辈能救国救民的“三民主义”,而是要消灭阶级剥削的“共产主义”。爸爸一辈子都想入党,为了入党甚至坚决与他那被戴了“地主帽子”的妈妈划清界限,然而在这场“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戏局设定中,阶级之间的矛盾似乎是无法消融的,只能通过“一方斗倒另一方”的革命手段予以解决,因此,爸爸终其一生也还是没能成功入党。到了“我”这一代,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青石上的红字变为“只生一个好”。戏局变了,“我”也对爸爸在乎的东西漠然置之,所以在爸爸死后,组织上要对他“追认党员”之际,“我”以一句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掷地有声的话“人都死了,追认管屁用?”坚决拒绝了爸爸追求一生却未能如愿的党员身份。到了“我”的儿子这一代,则变得连汉字都不愿意写了……无疑,戴家的每一代人都是为国为民、死守信仰的大忠臣,却又是实实在在、不敬不孝的衣冠枭獍、忤逆子孙。整篇小说就是在“后一代人不断革前一代人的命”的叙事结构中展开了对主题词“忠”的思考。那么他们所忠之物到底是什么? 又是以怎样的“革命”方式尽忠的? 这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被叔爷爷抛弃的童养媳艳芸无疑是戴家最富有悲剧色彩的人物。自小时候见过丈夫一眼后,她便终日守在戴家的大宅院里数着遥遥无期的日子。作为“忠杰之堂”的童养媳,周围自然有一群七姑八爷们的眼睛盯着她不许失节。然而艳芸还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怀上了别人的孩子,这一所作所为于满口仁义道德的七姑八爷们显然是不可忍的,于是宅院内掀起了一场逼迫艳芸交代奸人的家风整顿运动。面对守口如瓶的艳芸,整顿的手段愈来愈恶劣,从让每家的姑爷们轮番当众打艳芸耳光,到集体给艳芸灌屎灌尿,直至将艳芸整死。在戴家这场戏的戏局设定中,七姑八爷们是守护家风门风的正义派,而艳芸则是那个伤风败俗的忤逆之妇。
现在让我们冷静地看看在这场“交战”中,双方都具体做了什么事:首先,正义派的五姑奶奶与五爷爷的孩子并非五爷爷亲生,而是五姑奶奶与街头药房先生生的。一个与艳芸所作所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风尘妇女竟然是整场保卫家风运动中最积极的带头人;与艳芸竹筒传信、生了两个儿子的五爷爷不但迫于道德舆论的压力不敢承认,而且还和其他爷爷一样当众打了艳芸;而艳芸则是一个没有犯下任何“实质性”错误的普通女人,她与其他女人一样有着对爱情和家庭的期许,却只因一个有名无实的“童养媳”身份,就被剥夺了做“正常女人”的资格,艳芸的孩子不被戴家承认,被当成无法与“忠杰之后”同堂读书的野种。在这场血淋淋的革命中,五姑奶奶用“忠义”的道德外衣为自己残忍的整人手段争得了合法性,“忠义”在五姑奶奶这里不是约束自己的行为准则,而是用来绑架别人的道德枷锁,甚至是杀人武器。而艳芸作为戏局中的“奸逆之妇”却至死都没有说出孩子爸爸的名字,她也许不懂什么“忠孝节义”,但却是实实在在地用生命来捍卫爱情的忠杰之士。
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这出戏,生活中的一切又被“出身”“阶级”所规定。“爸爸”想要加入共产党便与被戴了“地主帽子”的亲生母亲划清界限;“小二爹”“小三爹”跟国民党到了台湾,戴家人就当他们死了;“小二爹”的儿子戴留生因为资产阶级的出身,不能去县中学读书;谈恋爱的方式是先自我批评,后相互肯定的政治恋爱法;“革命婚”更是遍地开花:妈妈的同学嫁给了老区来的工农干部,路遥娶了个撅牙女工农干部,连七老八十的五姑奶奶也赶着这社会风潮与五爷爷离了婚,改嫁给一位年龄相仿的老干部,把自己的成分给改了;婚后生的孩子也要取一个“革命”的名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吐故”“纳新”。
戴家革命戏的最大特点是,每场戏的戏局设定对每代人而言都是不容置疑的绝对命令。比如,在曾爷爷眼里,大清帝国的规矩就是他头顶全部的“天”,一切民主、共和的思想于他而言都是超出他认知能力之外、无可想象的“逆天地之动的邪物”,因而曾爷爷尽忠的办法就是固守住他那上朝的庭步和下跪的姿势,甚至还把那过了时的圣旨用金箔装裱起来以表敬忠。而这种抓住表面形式不放的做法,恰恰是失去本质最明显的标志。到了爷爷辈、父亲辈,虽然戏局的设定陆续换成“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然而戏局本身于他们而言仍然是不可变更的唯一的“天”。“小四爹”因目睹苏联兵在东北强奸中国妇女,揭了“老大哥”的短,便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无疑,所谓的信仰在这代人的戏局中仍然是不容置疑的,信仰非但不可怀疑,甚至连半个污点都不允许往上泼。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向来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提倡正义高于生命的价值理念。妈妈的同屋女友无法接受工农干部粗糙邋遢的生活方式,当“理念”与现实无法和解之时,她并没有选择用离婚的方式在现实中背叛工农干部,背叛自己一直以来深信的“理念”,而是选择继续相信,直至把自己逼上了自杀的绝路,也算是“为义舍生”了。然而,组织并没有看到她的忠贞,反而开除了她的团籍,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她背叛了信仰,而在于在她的死中,“理念”并没有获得胜利,反而如同遭受了侮辱一般显示出自身的可质疑性。
由是可见,曾爷爷供奉的圣旨虽然在形式上被消除了,但仍以思想的方式统治着戴家后代。他们并不知道“否弃和怀疑自己的信仰就是对信仰本身的忠实”[8]。他们就像是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中那些在山洞里终生无法转头的囚徒一样,所见的一切都被身后举着东西走来走去的人们所设定,他们坚定不移地忠于墙上的鬼影,为之生、为之死,他们不知道光在他们背后,更不知道山洞外还有一个更加广阔的真实世界。
(二)戏局外的“黄布”
大脚奶奶是戴家这场“忠逆演义”中唯一的局外人,她一生不卑不亢,明白在戴家的“山洞”外还有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她曾说:
要说老家的那些老房子是个洞,这话儿很对。那大宅院左一条曲径,右一个月门,弯弯绕绕,就跟个山洞一样。一大家子都挤在里面。谁也不敢往洞外看。谁都不知道新疆还有个戈壁滩,站在沙漠上看天看地,看到的可不是什么忠、孝、仁、义、信。看到的是一匹铺天盖地的黄布,那黄布是活的,有生命。那黄布起伏翻动,哪是忠、孝、仁、义、信能镇住的?[7]6
奶奶的一生活成了戈壁滩上那起伏翻飞的黄布,她既置身于戴家一代代“革命”的戏局中,又能跳出局外,看清“革命”的本质,通俗地说:奶奶活得明白。
要弄清“革命”的本质,我们首先需要对“革命”的概念加以阐释:“革命”一词最早见于《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3]429。古代朝代的更替皆是天子奉天命所为,那么何为“天命”? “天命”乃“天道”之意志。上文提及,在逻辑层面,人生在世有两片“天”:一片是提供生存所需基本养料的“自然之天”;一片是在原初自然世界上探索出不同生存方式(活法)的“文化之天”。人是被抛的存在,自然之天显然无法选择,只能适应、顺其势而为,但“文化之天”却是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探索出的能让人们生活得更好的生存法则。故而,“革命”本质上是在旧有的文化法则无法满足当前人们生活需要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变革,改变原来的“天道”,探索新的“道路”(活法),其最终目的是让人生活得更幸福。简言之,革命乃是手段,生活本身才是目的。
戴家的“革命”显然没有触及“天道”,而是在同一片“文化之天”下展开的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换言之,只要“天”不变,“新”与“旧”就不过是各自戏局设定的不同罢了。戴家一代代“革命”革的只是“戏局”的空壳子,生活的本质没有改变,因而,今日斗倒了“旧势力”的“新势力”很快就会被明日更新的“新势力”斗倒。生活的本质在一代代“戏局”的斗争中被掏空,留下的也只是每代人对每代“戏局”形式上的愚忠。
传统家训于七姑八爷们而言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戏局设定,也是他们头顶上永远不可变更的唯一的“天道”。当艳芸怀孕,奶奶提出要更改家训之时,七姑八爷们就如同世界末日将至一般地手足无措,他们无法想象“变了天”的日子该怎么过。艳芸无疑是这场戏局中忤逆“天道”之人,因而在卫道者眼里,她甚至没有资格继续活在这个“忠孝仁义”的世界。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亲戚们把艳芸的死讯报告给她必须为之“守节”的丈夫——住在上海的叔爷爷时,叔爷爷回信说:“他从来没有和这个女人合法结婚。这女人不是他的‘太太’。他不过问此事。”[7]13对上过日本学堂的叔爷爷来说,他个人的戏局设定俨然已经与戴家传统戏局大相径庭。当当事人叔爷爷都不承认艳芸的童养媳身份,不承认他与艳芸子虚乌有的“夫妻”关系,当所守之“节”的实质已经被抽空时,艳芸被要求的“守节”又是在“守”什么呢? 作为“忠孝仁义”的代言人,“忠”字对于七姑八爷们来说完全是一个外在于自我、用以规约别人的形式手段,他们没有反身思考的能力,从来不会思考自己的行为忠不忠,更或者如果自己所“忠”之物本身是错的,那么“忠”的意义又是什么? 甚至与药房先生生了儿子的五姑奶奶并不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比艳芸更甚,只要她满口“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忍善”,她就是传统家训最忠实的捍卫者。然而在她忠实的表面形式下掩藏的却是以非人的手段折磨艳芸致死、试图剥夺无辜孩子上学资格的对生命、对人性的极度冷漠。他们是形式的卫道士,却是生活的反叛者;反之,艳芸虽然是戴家这场戏局中的忤逆之人,却是生活、爱情的忠杰之士。
戴家爸爸辈们的戏局设定是要消灭阶级,然而当这场革命进行至极端之时,革命的手段就变成了目的本身。“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原本只是一个逻辑上的概念,但在父亲一代的戏局中,一定要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斗争实体”:被判定为“资产阶级”成分的爷爷死了,“地主”的帽子不能随之消失,而是转移到一生不争不抢、不悲不喜的奶奶头上;相反,曾经婚内出轨、采用各种非人手段逼死艳芸的五姑奶奶却因为离婚改嫁了老干部,就把自己资产阶级的“成分”给改了。由此可见,这一代人效忠的“成分”与人的内在品质毫无关联,只是通过“改嫁”的方式就能随意改变的、没有实质内涵的“虚名”,它的本质就像一顶可以随便传递的“帽子”,戴到谁的头上谁就被定了性。然而就是这样一顶“帽子”,却主宰了人的亲情、爱情,决定了人的生死祸福。
“革命”本来是要通过对“文化法则”的改变让人生活得更好,戴家每一代人都背负着救国救民的伟大使命,然而生活真的在一代代的“革命”中越革越好了吗? 不论是作为被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后代戴留生,还是作为革命先锋队的无产阶级诗人路遥都在扭曲不安地生活着,他们个体的生命价值均无法得到保障。人成了“革命”的奴隶——一边革上代人的命,一边被下代人革命。其实根本上乃是自己革自己的命。生命的价值、生活的意义终在这一场场“革命”中被遮蔽,作为生活手段的“革命”变成了生活本身、变成了决定人们生死祸福的根本性存在。而人性之本的亲情、爱情均沦为取悦“革命”的奴仆。每一代戴家人都是“革命”的忠臣,却成为“生活”的逆子,忠逆的本质在戴家的“革命”戏局中发生了颠覆性的倒转。
奶奶无疑是懂生活、通人性的局外人,她明白并不是曾爷爷的“辫子”有多好,而是他跟那个辫子过了一生,临终了也应该让曾爷爷带着辫子走,此乃人性。所有的是非对错、争执追逐都是为了生活,生活本身才是人的目的,因而不能过分执着于“辫子”,顽固地“留”和“剪”都是一种舍本逐末的“执”。在这个意义上,“执”就是对所信之物不加反思的无条件坚持。而真正的“忠”乃“德”之正、“心”之正也,是对“天道”的忠,对生活本身的忠。奶奶是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中那个敢于面对真实世界的人,是生活的忠臣,她明白戏局内众人执守的“辫子”不过是生活的假象,而戏局外铺天盖地、活力翻飞的“黄布”才是活生生的生活本身。
于北美华文作家而言,“文化不是移民随身携带的一件行李;它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新的环境不断地进行着自我修正”[9]。我们从《芳华》和《忠臣逆子》中均看到了作者对中国文化所进行的根本性反思。如果说“旅行”是对世界的眺望,是一项专门走近远方的活动,那么“旅居”则是一项亲身操持远方世界的“事业”,北美华文作家正是在进行着这项“操持远方世界”的“事业”,并通过一部部作品不断地对我们固有文化之缺欠进行自我修正,同时更期待、呼吁我们对自身以及他者的文化世界进行更为深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