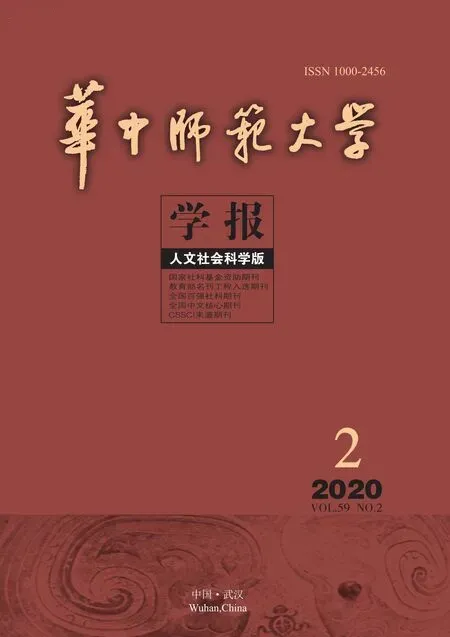一匹“老马”的历史:生态系统概念的科学与文化根源*
唐纳德·沃斯特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2)
2001年,罗伯特·奥尼尔(Robert V. O’Neill)提出了一个醒聩震聋的问题:“是否已是时候埋葬生态系统概念?”在其向美国生态学会发表的罗伯特·麦克阿瑟演讲中,奥尼尔对此概念进行了连珠炮式的批评,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生态系统概念是“人类大脑有限能力下理解真实世界复杂性的产物”。随后,他抱怨道,在试图纠正此概念的不足之处时,“我们正在给一匹老马装上夹板和补丁”。而他的解决办法是让这匹伏枥老骥从痛苦中解脱,转去“购买一匹新的小马驹”①。
生态系统概念一直备受众多生态学家的青睐,被视为其学科提供的关键概念或范式②。另一方面,如奥尼尔等人则对之持沮丧和疑虑的态度。本文并非提议射杀这匹老马,而是试图了解其起源和壮大的过程,并询问它在当今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手中是否还有用武之地。我将重温这匹“老马”的故事——它生自何方,怎样成长,如何逃逸或隐没,而后又是怎样倦马归厩。
一、“老马”的前史
我们知道此马大致的生年——1930年,其诞生之地是一篇无甚名气的论文,该文作者为阿瑟·罗伊·克拉帕姆(Arthur Roy Clapham),此人当时只是牛津大学的研究生,后来成为谢菲尔德大学的植物学教授。我们也知道生态系统一词在哪一年受到关注,并被更广泛地引入科学界——或者它事实上是从研究生克拉帕姆那里剽窃而来,或者委婉地说,在没有给予规范引注的情况下借用而来的?那一年是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阿瑟·坦斯利(Arthur G. Tansley)在一篇文章中运用了生态系统这一概念。我在下文中会讨论这些年代和坦斯利,但让我们在此之前,尝试将生态系统的概念放入更广泛的近代早期西方自然观念演变的历史之中。
今天,“系统”一词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我们泛泛地谈论着人体消化系统,纽约高等教育系统,计算机操作系统,系统分析师和系统构建者。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给了我们“系统皆备(all systems are go)”的流行语。从这些不同的用途中,我们或可得出结论,“系统”是一种非常新潮的、现代的交谈方式。但实际上,早在17世纪,“系统”一词已经开始频繁现身于各类文字当中,在18世纪,所谓的理性时代中,尤其盛行。
《牛津英语词典》为“系统”一词设有七列字体细小的栏目,用以说明其定义并枚举其词义演变的示例。这些例子最早出现在17世纪中后期,并于1700年以后逐渐浩繁。《牛津英语词典》中关于“系统”的第一个、最古老,也是最普遍的定义是,系统指的是一组有组织或相互连接的物体。系统是“相互连接、关联或相互依存的事物的集合或组合,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的整体,根据某种方案或计划,由有序排列的部分组成的整体”。在近代早期,人们随处可见这样的系统。他们看到了组织、联系、整体、方案和计划。举个例子,托马斯·霍布斯在他著名的政治论著《利维坦》(1651)中写道:“在我看来,‘团体’就是不同的人出于同一个目的或利益聚集在一起。”③当一个人放眼整个自然界,无论是尘世的还是天堂的,在社会内部真实的东西在自然界中似乎更为真实。一切自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一个共同的事业,一个共同的经济体系而结合在一起。一切都是制度,一切都是组织,一切都是秩序。
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在该词的核心意涵中屹立着艾萨克·牛顿,这位现代科学之父,同时也是现代系统思维之父。牛顿出生于英国林肯郡的一个小村庄,他在年轻时读过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的大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osopraiduemassimisistemidelmondo或DialogueConcerningtheTwoChiefWorldSystems,1632年首次出版)。此书让他开始思考在天际运行的太阳和行星。牛顿后来因为解释天体运行规律而闻名于世并产生深远影响。这一规律解释了引力如何将天体的轨道从它们正常的、直线的惯性轨道弯曲成巨大的圆形轨道,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行星围绕太阳旋转的系统,且这一系统未曾间断,未受干扰。牛顿警告不要将此系统视为一台纯粹的机器,像一座巨钟或一台当时人发明的新机器。他敦促说不要只看到构造或机理,而要看设计如此系统的伟大思想。他写道:“万有引力解释了行星的运动,但它不能解释是谁使行星运动。上帝掌控万物并知晓一切已经完成或可以完成的事情。”④尽管如此,牛顿的警告常常被忽视。人们开始着迷于构造本身,以至于忽略了它背后的伟大思想。他们被复杂的结构所吸引,为功能的仁慈所蛊惑。隐藏在背后的终极动因可能会遗失在对此构造的歌颂与对自然系统的功用与效率的赞美热潮中。
大约在1710年,乔治·格雷厄姆(George Graham)发明了一种机械装置来演示牛顿所言的太阳系的运转。我们本应该以该机械发明者的名字来称呼它为“格雷厄姆”,但是约翰·罗利(John Rowley)为奥勒里四世伯爵( the fourth Earl of Orrery )做了一个复制品,并谄媚地用伯爵的名字将此装置命名为“奥勒里”。太阳系仪(orrery)是一套复杂的机械装置,由机械臂、机械球和机械齿轮组成,通过精密的发条装置运转,以展现行星及其卫星围绕太阳的运转。在该装置中,地球通常需要10分钟左右才能绕转太阳一圈,因此它很难成为引人入胜的奇观。事实上,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这是一场相当无趣的演出;他们厌倦了等着地球完成它全部的轨道,很快便打道回府。
但是,并非只有太阳系才具有这种有序性和可预测性,地球上构成动植物群落的那一组物体也是如此。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被描述为一个“根据某种方案或计划,由有序排列的部分组成的整体”。这里最有影响的人物是《自然系统》(1735年发表于尼德兰莱顿)的作者卡尔·林奈。该书列出人们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的分类学上的顺序。几年后,林奈在他1749年的论文《自然的经济体系》中,为读者提供了可称之为第一本现代生态(或原始生态proto-ecology)的指南。林奈写道,在自然奇妙的经济体系中,地球上到处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物种,它们都机械般地精密运转着,就像太阳系仪一样。每一个物种都有其独特的食物、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与其他物种的独特互动方式。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态的系统,在其中,一切事物都在物质和能量的巨大循环中运转,其所带来的美好结果是效率、秩序、和谐、宁静、合作的最大化。通过研究这一生态系统,瑞典的自然博物学者林奈暗示我们要学会对自然和自然之上帝心怀敬慕⑤。
对自然进行系统思考的热情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的《自然神学》(1819)就说明了这一点:“宇宙本身是一个系统;每个部分要么依赖于其他部分,要么通过某种共同的运动定律与其他部分相联系。”⑥这种科学与虔诚信仰的结合体现的不仅是佩利,也是1836年之前英国出版的布里奇沃特系列论著(the Bridgewater Treatises)背后的基本时代精神(佩利之作是该系列论著的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一部)。正如林奈所做的那样,所有这些“原始生态学家”都在植物和动物和谐的相互关系中发现了上帝存在的证据。在这个地球的系统背后,耸立着上帝,他是伟大的设计师、技术员和钟表匠。自然所展现的秩序被视为上帝存在的确凿证据。一个人无需通过《启示录》或《圣经》得出上帝存在的结论;通过仔细观察自然界便足以证明。当然,这种对世界系统进行描述和思考的热情是以对数据资料进行高度选择性检验为基础的。从林奈开始,深怀宗教信仰的原始生态学家专注于理解在当时看来最重要的知识:事物如何协同运作,如何保持稳定性,如何体现秩序以及如何展现造物主的理性。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在她的著作《自然之死》中批评了这种世界模式。她称其为“机械论”和“还原论”,指责其抹杀了一种更古老的观点,即自然是整一的有生命的有机体,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个僵死的机械的东西。她认为,古老的、有生命的自然的死亡助长了人们对地球的无情开发,而这也往往被认为与现代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相联系的⑦。
但是,麦茜特所言的情况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结果。一种资源保护哲学可能而且确实出现了,尽管它所产生的时间要晚一些;一直等到19世纪60年代,远离安定有序的英国,在更加混乱的美国,诞生了这种资源保护哲学。第一位伟大的资源保护倡导者是乔治P.马什(George P. Marsh),其大作《人与自然》于1864年出版。马什是在18世纪的自然系统观的影响下长大的。“自然,不受干扰”,他写道,“如此塑造她的领土,使其在形式、轮廓和比例上几乎保持不变”⑧。这又是和牛顿、林奈类似的对一个奇妙系统的想象,这个系统处于长期的平衡状态。相比之下,马什所生活的社会——他的故乡佛蒙特州正处于边疆开发时期——产生了大量的问题,诸如森林滥伐、野生动物的毁灭、水土流失、对溪流的破坏等。那些神圣的和谐正在被邪恶地扰乱。因此,虽然在旧有的系统思维范畴内进行写作,马什却为现代环境保护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查尔斯·达尔文的革命
在大西洋彼岸,则是查尔斯·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革命。如今这是一个为人熟知的故事,尽管人们并不总是以我所采用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简而言之,一位安静、退隐,然而充满智慧的革命者挑战并推翻了早先的以系统诠释自然的方式。达尔文总是谦逊而传统地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博物学家,而非一个科学家,这意味着他沉浸于博物学古老而具地域性的特殊性之中,而非牛顿物理学的现代普遍性。达尔文和马什年龄相仿。他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问世,仅比马什的巨著早五年。二者都周游世界,通过各自的旅行,都意识到19世纪的世界因不断增长的人类活动而发生的剧变,产生了生态上的混乱。强大的力量四处入侵,扰乱地球。对于马什和达尔文这种相当保守的思想家来说,这个世界相比他们祖先定居时已面目全非。然而,与马什不同,达尔文挑战了他那个时代关于自然如何运作的宗教观念。可以肯定的是,他仍然保留了他所处时代的一些观点:他也期望在大自然中找到秩序、平衡和长期的稳定。但是,虽然具有保守主义的倾向,达尔文做出了巨大而深刻的转换——从一个静态的、和谐的宇宙观转向一种历史的或发展的自然观⑨。
除了少数地质学家,任何一位在他之前的伟大科学家——牛顿、林奈——都没有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自然,他们对亘古存在的变化并不敏感⑩。但是,一旦以历史的眼光看待自然,世界开始变得迥然不同:世界并非是一个永久处于平衡状态、完美和谐运作的“系统”,也不是由上帝的理性头脑一劳永逸地设计而来的。相反,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混乱、不确定且尚未完成。达尔文认为,自然是在漫长的时间里演化而来的,这种演化是通过发生在个体生命日常层次上的自然选择而进行的。变异发生在个体生物中,这一过程他无法解释,但他认为这是偶然因素和不可预测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变异为一些个体提供了比其他个体更好的生存和繁衍的条件。这种无休止的竞争过程的累积效应是不断地创造新的变种,然后是新的物种。达尔文继续谈论不同植物和动物“物种”,但是此时物种的概念已经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含义:对他而言,一个物种并不是一种有机物的固定或理想类型,而是一种统计上的平均值。一个物种是钟形曲线上的一组点,在这些点最密集的地方,产生了我们称之为物种的标准。
达尔文自然史的核心强调个体生物为生存而奋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也允许演化既在群体也在个体层面发生——不同的部落或社会为了生存相互竞争,从中产生输家和赢家。
毫无疑问,一个包括许多成员在内的群落,由于他们具有高度的集体主义、忠诚、服从、勇敢和共情精神,他们总是准备互相帮助,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他们将战胜大多数其他群落;这就是自然选择。
但是这些整体是由相同的物种组成的。18世纪所推崇的那种包罗万象的伟大自然系统,并非一种完美的设计或永恒的东西。事实上,达尔文几乎从未使用过系统这个术语。即使他注意到群体或整体,他并非要把它们描述成某种宏大的整体系统。对他而言,自然界总是不完善的,经历着混乱、挑战、竞争和变化。这个过程产生的结果并不是最终的成品,甚至不一定是对已有成果的改进。仅仅只是不同而已。
达尔文所言的不是系统,而是生命之网或生命之树,有着无止尽的分支,总是在生长和变化。用他最生动的话说,自然是“盘根错节的河岸”。盘根错节暗示着一团混乱、纠缠在一起的东西。它似乎需要一个割草机或园丁,或者它可能吸引一个仅仅喜欢观看缠结与多样性的人。让我强调一下,达尔文是一位历史学家:这是了解他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他的自然观是历史性的,而关于系统的思维与历史思维是不相容的。
追随达尔文革命生物学的是他的德国信徒厄恩斯特·赫克尔(Ernst Haeckel),他在1866年首创“生态学”(Oecologie)一词。三年后,赫克尔对这个新科学领域做出了重要定义:“这门学科是关于自然的经济体系的知识……是将对达尔文所指的所有这些复杂的内在联系作为生存竞争的条件所做的研究。”生态学因此与林奈所言的自然的经济体系有关,但显然与“自然系统”无关,在“自然系统”中,所有的生物体都被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一生态学新领域的重点在于为生存而斗争的生物体之间的体现独特个性的竞争关系。
达尔文的世界观与我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所研究的世界是一致的:国家的兴衰、边界的变迁、不断竞争的群体、个人、经济以及不断变化的思想观念。对我而言,历史是达尔文式的,是杂乱无章的、混乱不堪的,充满着偶然性,仅创造出暂时的结构和模式。但我也必须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达尔文主义或任何历史地看待自然或社会的方法,是否遗漏了一些重要的特征?我们历史学家,包括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是否将我们在急速变化与社会激变中的经历解读到我们对过去以及自然的认识当中?就像我们18世纪的前辈一样,我们是否也是有选择性的,只不过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或者,是否还存在着一些并非人类创造的永恒真理,反复出现的模式以及世界秩序?
历史学家已经详细讨论了达尔文主义生态学对世界上人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有时将这些影响视为我们必须要超越的黑暗和邪恶的观念。生态学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前代人所憎恶的:对自然资源的无情掠夺?既然生物界给了我们一个模型,那么现在,我们是否完全有理由去干扰那些业已被干扰并且从未停止被干扰的事物? 或者,恰恰相反,新的达尔文主义生态科学是否鼓励人们对地球上生命的短暂、不确定和脆弱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而这在林奈的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它是否教会了我们更加谨慎地行动,而不是更加残忍无忌?自然界中是否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达尔文主义无法解释的秩序?
三、重寻秩序的尝试与困惑
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70年后,“生态系统”一词首次出现在科学家的词汇中。林奈和牛顿主义所言的“老马”由此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这个名字表达了它的混合血统:孕育自“生态”,受精于“系统”。尽管生态学就总体而言具有达尔文主义的根源,但生态系统的概念却具有非达尔文主义的渊源。在某种程度上,生态系统概念忽视或淡化了自然选择,杂乱无章的演化,那个如此易受随机变化影响的,如此历史性又如此不可测的达尔文式世界。取代达尔文式不确定性的是18世纪自然博学者们探讨的一些共同主题的回归:结构、功能、秩序、周期、平衡、理性和机械般的规律性。
我们通常认为创造生态系统概念的人是阿瑟·G.坦斯利。1913年,他创立了英国生态学会,并成为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生态学家学会的首任主席。他还在《生态学杂志》的编辑任上服务长达21年。在前文提到的1935年的文章《植被概念的使用和滥用》(“The Use and Abuse of Vegetation Concepts”)中,坦斯利继续抨击他认为是蒙蔽此科学领域的无稽之谈的神秘思想。弗洛伊德的神秘主义思想并不在坦斯利的抨击之列,他本人是其信徒。他抨击的是“超级有机体”(super-organism)的神秘思想,这是内布拉斯加州的生态学家弗雷德里克·克莱门茨(Frederick Clements)提出的著名概念。克莱门茨坚持认为,北美大草原不仅是一群自私自利的个体和物种,而且是一个超级有机体,它从如此众多的个体生物中涌现而出。坦斯利不喜欢谈论自然界中的任何超级有机体,他也反对动植物可能构成并生存在其中的“生物群落”的观点。他没有采用诸如有机体和群落之类的隐喻,而是转向极具还原性的物理学来寻找灵感。
尽管查尔斯·达尔文对现代科学有着重要影响,许多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仍然继续探索自然界中非演化的物理系统。例如,热力学(开尔文男爵Lord Kelvin、克劳修斯Clausius)、物理化学(威拉德·吉布斯Willard Gibbs、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亨德森Henderson)所做的工作。他们着迷于看似趋向平衡的物理系统,并且现在他们在一些研究个体生物功能的生理学家中找到了听众。例如,沃尔特·B.坎农(Walter B. Cannon)在1932年出版了《身体的智慧》(TheWisdomofTheBody)一书。在此书中,坎农认为,生命体表现出自我调节的特性,使它保持在一种平衡状态,或者称其为“稳态”(homeostasis)。这种状态类似于在封闭的物理化学系统中发现的平衡状态,但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在坎农看来,作为一个独特的系统,生命体更加复杂,更具流动性。平衡是一种波动状态,时刻变化,又保持相对恒定。身体一直保持在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中。
因此,在坦斯利进行生态研究的时期,大量有说服力的科学书籍和文章问世,描述了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的物理和生物有机体。关于系统的讨论再次流行起来,这些讨论包括展现平衡和稳定的模型,物质和能量的永恒循环以及功能的秩序。坦斯利借用关于系统讨论的观点,开始在生态学家中推广这一观点;为了取代克莱门茨的超级有机体理论,他提出了生态系统理论。他将生态系统定义为“构成我们所言的生物群落环境的所有复杂物理因素的整体——最广义的栖息地因素”。植物和动物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但同样无机的“组成”也是其一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物理学意义上的)整体系统”。坦斯利继续指出,生态系统在所有不同的物理系统中构成了另一个独特的类别,这些物理系统的范围涵盖“从整个宇宙到原子”,他看到了大自然中整体的等级。可以肯定的是,他承认所有这些系统都可能是人类建构的东西,是大脑出于“研究的目的”而分离出来的实体。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创造的”,但“这是我们唯一可行的方法”。
坦斯利的确试图将他的生态系统理论整合到达尔文的自然史和演化论中,从而使自己同18世纪的非历史自然系统概念保持距离。他承认,有时一个生态系统中的各类组成部分(植物,动物,土壤,气候等)不会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稳定的组织;有时生态系统不会出现,有时一个初始的生态系统也会崩溃。“实际上,”他写道,“存在某种初始系统的自然选择,那些能够达到最稳定平衡的系统存活的时间最长”。换言之,生态系统之间可能会相互竞争,获胜者将成为池塘、草地或森林的潜在形态。坦斯利认为生态系统可能是通过自然选择而演化的产物;它并非如牛顿的宇宙一样来自造物主的头脑。但是请注意,如今的演化论并不意味着一个生物体出于养活自己或繁殖的目的而进行的竞争;如今演化也包括相互竞争的生态系统之间的斗争,为的是寻找哪个生态系统可以取得胜利以达到最稳定的平衡。这显然类似于达尔文“群体选择”的概念,但这些群体不再是达尔文所言的群体(由同一物种的个体构成的群体,如蚂蚁或人类)。坦斯利所言的群体指的是生态系统。获胜的生态系统是那些能够建立最长平衡期的生态系统,正如承受住所有挑战的王朝一样。弗雷德里克·克莱门茨把他的“超级有机体”的终点称作“顶级”(climax),但坦斯利更青睐 “平衡”一词。它代表了各组成部分整合的最高状态,它从未被完美地实现,总是围绕着一个平均值波动,总是容易受到入侵或动荡不安。但在生态系统层面上,演化应该产生最大的稳定性和整合性,而这可以在“在给定条件下,伴随可获得的组成部分发展的系统中”实现。
坦斯利认为这种生态系统理论的一个巨大优势是,人类在其中占有可堪夸耀的位置。克莱门茨的“超级有机体”并非如此,它没有给人类留下空间,后者只是作为“干扰者”出现。而在坦斯利看来,“人类活动被视为一种异常强大的生物因素,它日益破坏原有生态系统的平衡,并最终摧毁它们,同时形成性质迥异的新生态系统,人类活动在自然界中找到了恰当的位置”。也就是说,生态系统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为的——一个由人类创造的系统,比如农业生态系统或城市生态系统——人为的生态系统和通过自然选择演化而来的生态系统一样运转良好。人类由此成为生态系统的缔造者。因此,不需要任何伟大的设计师,人类设计师有很多机会创造生态系统,生态学家应该研究这些人类创造的生态系统,就像他们研究通过自然选择演化而来的生态系统一样。
为了获取坦斯利时代前后关于生态系统概念更完整的历史图景,我们还需关注阿尔弗雷德·洛特卡(Alfred Lotka)关于生命世界中能量流的研究,他将热力学纳入对生态系统的研究当中。我们也需要关注伊芙琳·哈钦森(G. Evelyn Hutchinson)在生物地球化学和营养物质(尤其是碳、氮)的循环方面的研究。此外,还应关注哈钦森的学生雷蒙德·林德曼(Raymond Lindeman),他多年来研究了明尼苏达州的雪松湖,根据这项研究他于1942年写作了论文《生态学的营养动力问题》,在论文中他把生态系统模式简化为能量流。我们还必须讨论控制论、信息论和计算机技术所产生的影响,所有这些理论都鼓舞了科学家,令他们头一次期待能够对整个生态系统进行建模,不是以类似于太阳系仪这样简单的机械形式进行,而是在电脑上汇集大量数字化数据的建模。
在结束这次对生态系统概念的考察之前,我们应该简要考察将系统论应用于生态学的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奥德姆兄弟(brothers Odum),即尤金和霍华德·托马斯,美国南部之子,他们对世界各处的现代生态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53年,他们合作编撰了《生态学原理》,这是生态学领域使用最广泛、影响最大的教科书,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出版。1959年该书发行第二版,随后在1971年第三版问世,此时,霍华德·托马斯已经结束了两兄弟的合作关系,独自出版了他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环境、权力与社会》。与坦斯利相比,奥德姆兄弟的共同努力令生态系统成为生态学的核心组织概念。然而,他们对生态系统的定义紧紧追随坦斯利的定义:“任何涵括生物和非生物相互作用以在两者间产生物质交换的自然区域。”生态系统必须是“一个区域”,他们的例子包括一个池塘,一个湖泊,一片森林,甚至一个小水族馆。在一个池塘的情况下,为生态系统设置边界,将该个系统与另一个系统区别开来是相当容易的。而奥德姆兄弟继续辨识着各地的生态系统,使得生态系统的边界变得更加宽泛、随意。他们认为一个分水岭可以成为一个生态系统,令水流成为其决定性因素;他们甚至认为,一架飞往月球的高科技航天器也可能是一个生态系统,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生态系统几乎完全是人工制造的,为宇航员提供了“生命维持系统”。
我们可以原谅公众对于什么是生态系统或什么不是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困惑。这一术语是否仅指任何生物或任何生物群与无机世界之间关系的总和?如同宇航员居住在宇宙飞船这一生态系统,树木或北极熊是否有其居住的生态系统?或者一群野牛如何?一座大学校园或纽约市是否符合这一标准?还是说生态系统不仅是有机体与非有机体之间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关系,而更像是人们在冬天购买并穿着的外套? 它是一个真实的、离散的、物质的实体吗?是一个具有明晰边界的真实事物吗?是某种高于单个生物体、种群、物种或群落水平的“整合水平”吗? 它最终是否与地球一样大——整个地球是一个生态系统吗?
这些本体论问题很难解决,但后来尤金·奥德姆又补充了另一个概念,增加了生态系统在定义上的难度。他指出,每个生态系统都遵循一个共同的“发展战略”。它经历一系列阶段,最终到达终点或目标,即平衡点。“战略”一词通常意味着一种有意识的进攻、运动或行动计划——在战争或政治运动中遵循的战略。二氧化碳、水草、昆虫幼虫和白斑狗鱼如何能聚在一起,制定出任何一种“战略”呢?奥德姆绝非言其生态系统中有任何集体意识,但他确实相信所有的系统都遵循一个共同的模式或计划。该计划旨在实现“在现有能量投入和普遍存在的物质条件所规定的限度内,尽可能庞大和多样化的有机结构”。如果成功的话,生态系统将表现出最大的多样性、效率和稳定性(即他所说的“稳态”,多少类似于沃尔特·坎农所言的人体健康状况)。
奥德姆兄弟讲述了一个后达尔文主义式的故事,有着不同侧重点和结果。他们倾向于忽略搏斗、竞争或流血,同样也倾向于忽略猝然而不可预测的变异,或者充满任意可能的变化。生态系统确实发生了变化,而且每天都在变化,但对奥德姆兄弟来说,这种变化几乎总是周期性的。万事万物都在生态系统中周而复始地循环。诚然,如果一个人回到遥远的地质时代,他会发现一个比现在更加动荡不安的世界。奥德姆兄弟承认,地球经历了巨大的地质和生物革命。但在那些动荡的时代过去之后,平衡执掌一切——一直执掌下去。
唯一严重威胁生态系统稳定的是人类物种,而这是最近才出现的威胁。在这一点上,奥德姆兄弟没有阿瑟·坦斯利乐观,后者在他生活的绿色英国里找到了人类与自然融合的正面范例。对这两位美国人来说,这种人与自然的融合却是遍寻无踪的。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试图无情地推动经济生产,并向敌国或太平洋上偏远的珊瑚环礁投下原子弹,使放射性物质四处扩散。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稳定造成了威胁。奥德姆兄弟开始发出和乔治·帕金斯·马什或弗雷德里克·克莱门茨相似的呼声:人类是一个干扰因素。尤其是尤金·奥德姆成为一名斗志昂扬的环保主义者,他希望保持自然的秩序与稳定,对抗现代人的干扰之手。另一方面,霍华德·奥德姆似乎对利用生态系统知识进行一些系统维护和重组的可能性更为乐观。毕竟他是佛罗里达环境工程学的教授。在彼得·泰勒(Peter Taylor)将这对兄弟的思维形容为“技术统御的乐观主义”时,他想到的主要是霍华德。但两兄弟都对受过生态系统训练的专家抱有相当大的信心,这些专家能够应对所有这些能量流、碳循环和相互作用的有机体。
在美国战后环境保护运动的早期,奥德姆兄弟的生态系统模型对于公众而言极具吸引力。但公众从奥德姆兄弟生态系统模型中带走的只言片语可能显得非常矛盾,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生态系统是我们首先应该识别,然后才能保护其完整和不受干扰的事物吗?或者它是我们可以观察、测量、管理甚至改进的事物吗?产生这种迷惑部分是由于奥德姆兄弟在描述生态系统时所使用的元隐喻。有时这些系统看起来更像是活的有机体,近乎超级有机体,容易受到外界力量的伤害,变得病态或走向死亡。在其他时候,生态系统又类似于一台复杂的机器,如同人们在装配线上制造的新机器(如计算机,通过电流的机器,不断被修补和重新设计的机器)。莎伦·金斯兰(Sharon Kingsland)如此评论奥德姆兄弟思想中的机械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发展生态学这门旨在理解自然的科学,似乎应该通过将‘自然’描绘成人工制造的东西来加以推动,如此迫使自然与其表现出的多样性、不确定性和历史偶然性统统沦落进人造物体的窠臼之中。”
同奥德姆兄弟一道,我们似乎已经渐渐远离了19世纪查尔斯·达尔文的世界观和他那盘根错节的河岸。我们处于20世纪现代物理学,而且是稳定状态的物理学的领域,而非自然史的领域。我们现在谈论的不再是像威廉·佩利所言的由上帝设计规划的世界,然而也不是在谈论一个由随机性、偶发性和偶然性产生的世界,一个在我们眼前不断瓦解与重组的世界。生态学再次宣称,大自然遵循某种计划或设计,或至少是一种策略。秩序、合作、和谐、稳定、优雅的设计再次成为自然的首要品质。科学家再次强调对功能而非对发展的研究。但是这一切有其意义:大约在1950-1970年间,这种对“生态系统”的扩展和重新表述的概念,已经渗透到公众的想象力和日常报纸语言之中。生态系统这一从物理和机械中衍生出来并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比喻,如今已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各种实体的隐喻——场所、个人愿景、企业、政治选区和其他社会组织。生态系统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被教导去感知自然的方式。
生态系统这一术语的不精确性以及它在如此众多不同情况下的应用,使得一些包括罗伯特·奥尼尔在内的科学家试图把它完全抛弃。其他人则反对生态系统思维的静态特性;这些系统,无论它们在何处,似乎在时间上都是如此固定的。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人试图回到达尔文主义并恢复那些演化论的基础,这是一种更为严格的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在这一行动中,生态系统的概念有时被忽视,有时受到傲慢的挑战。
我不会在此冲动下,以简单的拒绝或肯定而结束本文。生态系统概念是否代表着对世界的设计,秩序、合作与和谐的古老诉求?甚至它是否以某种深层次的方式寻找形而上的目的和意义,以确保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计划或设计,可以指导我们前进的世界中?为什么像生态系统这样的概念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最后,在所有这些关于我们应该采用哪一种自然模式的历史辩论中,究竟隐含着怎样的道德关切?
注释
①Robert V. O’Neill, “Is It Time to Bury the Ecosystem Concept? With Full Military Honors of Course!,”Ecology, vol.82, 2001, pp.3275-3284.
②J.M. Cherrett, “Key Concepts: The Results of a Survey of Our Members’ Opinions,” in J.M. Cherrett, ed.,EcologicalConcepts:TheContributionofEcologytoanUnderstandingoftheNaturalWorld, Oxford: Blackwell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1989, pp.1-16.
③“System,”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b. 1651.
④关于牛顿将上帝视为万有引力系统来源的基本观点,参见任何版本的艾萨克·牛顿全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初版于1687年。
⑤参见Donald Worster,Nature’sEconomy:AHistoryofEcologicalIdea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31-39.
⑥William Paley,NaturalTheology,orEvidencesoftheExistenceandAttributesoftheDeityCollectedfromtheAppearancesofNature(1802), https://earlymoderntexts.com / assets/pdfs/paley1802_3.pdf,p.78.
⑦Carolyn Merchant,TheDeathofNature:Women,Ecology,andtheScientificRevolution:AFeministReappraisaloftheScientific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Harper Row, 1980.
⑧George P. Marsh,ManandNature:PhysicalGeographyasModifiedbyHumanAction(1864), Reprint,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29.
⑨参见 Worster,Nature’sEconomy, Part Three.
⑩Stephen Jay Gould,Time’sArrow,Time’sCycle:MythandMetaphorintheDiscoveryofGeologicalTim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