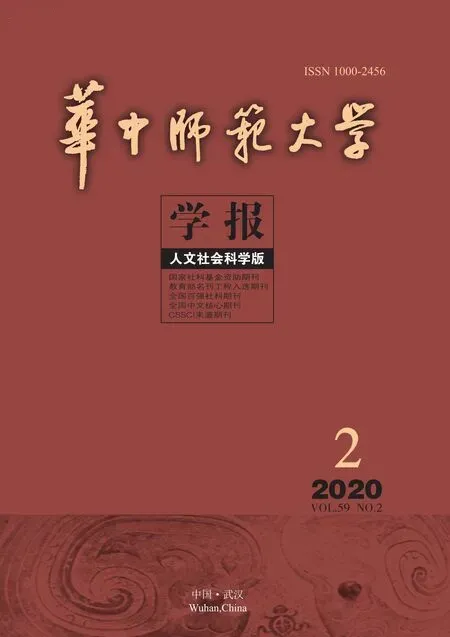叙事技巧的伦理维度
王先霈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 湖北 武汉 430079)
欧洲的小说在18、19世纪达到艺术上的高峰,经过几个世代的积累传承,小说写得越来越精致。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许多后来的作者对于前辈的写作技巧做过细心的揣摩,并且努力继续添加上各自的创新。到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对于小说写作技巧专门的深入的探讨和论述,成为一时的风气,亨利·詹姆斯1884年发表《小说的艺术》,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詹姆斯在谈到小说创作上各种技巧进步的成就背后,必有理论思考作为指导时说过,“但我猜想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成功不曾有过潜在的信念作为其核心的”,他以喜悦的心情预告:对于小说写作技巧的“讨论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已经开始了”①。
相比起来,中国从近代直到20世纪,对于古代叙事技巧的系统的总结和钻研则较为薄弱。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前人在创造出众多叙事杰作的时候,就没有经过理性的谋划,就没有独到的艺术理念作为支撑。亨利·詹姆斯倾力最多的是小说叙述角度的问题,他的追随者珀西·卢伯克在《小说技巧》一书中说,“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角度问题——叙述者所占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调节”②。他的这一论断显然也是来自詹姆斯。而在中国,对于这一问题,从很早起就有人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比亨利·詹姆斯所处时代稍早的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中说:“雅爱左氏叙鄢陵之战,晋之军容,从楚子目中望之,楚之军制,从楚人苗贲皇口中叙之,如两镜对照,实处皆虚,所以为文章鼻祖也。”③这里所谈的是两千年前叙事文本中叙述角度的转换。“文章鼻祖”,在这里说的就是中国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源头,《左传》是中国上古时代最优秀的叙事经典,它已经自如地变换使用多种叙述角度。《左传》开创的对多种叙述角度的灵活运用的经验,在《水浒》《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多个文学名著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并且被金圣叹和二知道人等具体地分析评述。
技巧的创造和运用,归根结底,是出于作者表达内容的需要,是出于描述社会生活和表达对社会生活现象的判断的需要。当初,《左传》的作者是怎样想到可以而且需要运用不同的叙述角度,他为什么要在叙述一个事件的时候变换叙述角度呢?弄清楚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对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的特点的认识和对中西叙事观念的比较,关系到我们对《左传》思想的批判性、战斗性的认识,所以,有必要作一探讨。
《左传》虽然早被列为经典,但它的叙事历来也曾受到文人的质疑。《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记申苍岭讲士人与鬼交谈,纪晓岚听后评论道:“此先生玩世之寓言耳。此语既未亲闻,又旁无闻者,岂此士人为鬼揶揄,尚肯自述耶?”申苍岭“掀髯”反问:“鉏麑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子乃独诘老夫也!”④也就是说,他们要对《左传》叙事的合理性提出诘问。《左传·宣公二年》记晋献公命鉏麑刺杀赵盾,鉏麑潜入赵宅,见赵盾凌晨盛服将朝,不忘恭敬,认为是个好官,刺杀这样的好官是不忠,背弃国君的命令是不信,叹息说,“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申苍岭以及纪晓岚提出,鉏麑自杀前在无人处的内心独白,有谁能够听到,《左传》记述的依据何在呢?钱鐘书在《管锥编》里列举了前人多个同样的质疑之后,解释说,“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戏剧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⑤那么,我们不能不再追问,《左传》和古代许多史书一样,本来就是记事和记言的,作者在这里为什么离开记言改而采用代言呢?为什么由固定的单纯叙事者角度改为无所不知的全知叙事者的角度呢?史家是不是有权用小说、戏剧的代言方式来叙述历史事件,用“想当然”来充当历史事实呢?这在叙事学上是否可以被允许、被承认?
近二十多年来,叙事伦理(narrative ethics)成为文学理论批评著述中一个逐渐热烈起来的话题。叙事伦理的讨论,是文学理论的所谓“伦理转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而是很早就已经或隐或显地出现于古人关于叙事的谈论之中。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之一是高度重视文艺的伦理性质和作用,因此也早就触及这个问题。对于“叙事伦理”这一术语的所指,有关乎叙事内容和关乎叙事技巧的运用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前者意思较为显豁,后者则尚待进一步深入探析⑥。
叙事首要的品格是真实,不同的叙事要求的是不同的真实。在中国古代的漫长时间里,历史叙事相对于文学叙事占有很大的优势地位,历史叙事尤其把真实摆在成败攸关的位置上。历史叙事要求的是本然的真实,文学叙事要求的是应然的真实。早期的最优秀的历史叙事文本,例如《左传》和《史记》,本身常常又带有浓厚的文学性,这就使得它们叙事的真实呈现复杂的情况。
历史必须真实地反映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实,这是从古至今确立的一条根本性的原则。历史叙事既然如此重视和推崇真实,史学理论就把是否忠于事实本身纳入史家职业伦理的核心,中国古代史论家强调的史德,说的就是历史叙事的伦理规范,其中重点就是求真。刘知几《史通·惑经》说,“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提出:“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天,也就是本然的史实;人,是叙事者增饰的推想、猜测。他不赞成把推想、猜测增益到历史叙事之中。为了表明叙事的真实可信,有的史家在叙事文本中对其叙述的依据也即材料来源作出明确交代,预先打消读者可能提出的“谁闻之而谁见之”的质疑。比如,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中,就有很多处这样的说明⑦。修昔底德明确地宣称他的叙述与诗人不同,因为他“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⑧马克思主义从来都强调历史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恩格斯说:历史哲学与自然哲学一样,“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⑨。马克思说:“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⑩他们说的,都是历史叙事伦理中铁的律条,不容许违反也不容许偏离。
《左传》里面有关于历史叙事者坚守叙事真实性原则的记述。“襄公二十五年”《春秋》有“夏五月乙亥,齐崔杼杀其君光”。《左传》具体道出这一条记述载在史册的经过:“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齐国史官记载了这个事件,崔杼不准这样记载,连续杀死三个史官,还是没有能够阻止得了。这样,关于齐庄公被杀,至少就有了两种叙事方案,崔杼所想要的掩盖真相的那一种未能实现。对于同一件历史事件,几种叙述方案、几种叙述文本并存,是常常可能遇到的。希罗多德就说过,“对于居鲁士的死的传说确实是有很多的,但我只叙述了上面的一种,因为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最可信的”。史德,要求历史叙事符合事件的本来实际,文学叙事要求符合生活的客观规律,这是叙事伦理的第一个层次,最基本最重要的层次。
和“襄公二十五年”那一条记述类似,《春秋》在“宣公二年”有“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臯”。同样,《左传》也记述了被叙事者向叙事者提出异议:“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这里也有两个记述方案。在《春秋》的文本中,赵盾所想要的也是未能实现。我们不难看出,与对齐国太史的由衷赞美不同,《左传》的作者深心并不完全同意《春秋》在这里的记述,在晋灵公和赵盾之间,《左传》是同情、赞美赵盾而谴责和抨击晋灵公。对于“赵盾弑其君”被书之史册,心里面存有惋惜之情。但是,由于《春秋》的尊崇地位,由于《春秋》所遵奉的君权至上观念在当时的强大控制力,《左传》能够直接地反驳和颠覆《春秋》的记述吗?显然不能。怎样叙述这一历史事件,就成为《左传》作者必须精心处理的难题。他在这里先是引用了孔子的话:“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用调和的态度,肯定《春秋》采用的记述,又肯定赵盾是好官,错误只在没有逃出国境因而作为卿大夫需要对国君之死负责。然而,《左传》的作者仍不满足,他还要读者知道晋灵公恶行累累,自己走上众叛亲离的绝路,赵盾对灵公的谏劝都是十分正当的。假使《左传》的作者直接出面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不但与君权至上的原则发生冲突,也不但偏离了全书的体例,而且由于其主观色彩,还会缺乏足够的感染力、说服力。在写作前提造成的窘迫情况下,他先是通过无人称的客观叙述,让读者知道晋灵公射行人、杀厨师等种种恶行和赵盾尽力对灵公的阻止。接下来,他觉得客观叙述还不足以表达他对赵盾这个人物的评价,便请出鉏麑作为临时的叙事代言人,把对赵盾的赞扬充分展现。在这个地方,正如美国学者布斯在《小说修辞学》里所说,作者不能直接说话,而“掌握戏剧化的视角,可以高度精确地传达出作者的判断”。这就是《左传》放弃记言而采用代言,或者用布斯的说法,叫做采用“戏剧化视角”的原因所在。变换运用叙述角度对于叙事文本的道德感化效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马克·柯里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中也有论述:“对视角的分析是20世纪文学批评的伟大胜利之一。视角分析的力量部分地来自具有分析力的术语的力量。这些术语描写了叙述声音的微妙变化、出入他人大脑的运动或表现人物话语或思想的各种方式。但对视角的分析不止具有描写力,它是在小说修辞中的一种新探索,小说可以为了某种道德目的给我们定位,驾驭我们的同情,拨动我们的心弦。最为重要的是,对视角的分析使批评家们意识到,对人物的同情不是一个鲜明的道德判断问题,而是由在小说视角中新出现的这些可描述的技巧所制造并控制的。它是一种新的系统性的叙事学的开端,似乎要向人们宣称,故事能以从前人们不懂的方式控制我们,以制造我们的道德人格。……对小说中视角的分析是对作者控制的揭示。”柯里在20世纪末从理论上做出的分析,《左传》的作者早已在叙事实践中做到了,古人早已领悟了叙事技巧的强大的伦理力量。
关于鉏麑自杀前的自白,应该也不是出于作者的虚构,不是一个无来由的凭空想象,那么,这样写的根据在哪里?我们可以推论,赵盾是长期主持朝政的卿大夫,他和晋灵公之间反复发生的矛盾纠葛,是关乎国运民生的大事件,在当时的晋国必然有记载和传闻流传。试看《公羊传》对同一事件的记述:“使勇士某者往杀之,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俯而窥其户,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诚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门,则无人焉;入子之闺,则无人焉;上子之堂,则无人焉——是子之易也。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君将使我杀子,吾不忍杀子也。虽然,吾亦不可复见吾君矣。’遂刎颈而死。”《左传》《国语》《公羊传》三者的记述比较,晋灵公因为赵盾阻碍他的残暴行为而派刺客谋害赵盾,这个刺客没有执行刺杀的命令而是自杀,这两点是相同的,那么,这就应该是当时确实发生的事实;而刺客在赵盾家里看见了什么和怎样自杀,《公羊传》的记述与另两书则有些差异。不同的叙事者根据不同的传闻,在确定发生过的事实的总体框架下,对细节做了各自的选择和推想,他们都不是让作者出面来对赵盾赞扬,而是让鉏麑或者勇士某者出面。这就如同卢伯克所说,“采取另一角度,安排一位新的叙述者,让他首当其冲去跟读者打交道”,“作者便被戏剧化了;他的陈述便赢得了分量”。《左传》和《公羊传》都采用了代言替换记言,目的是在保持对于弑君反对态度的前提下,赞扬赵盾对暴君的抵制和他的忠于职守。新技巧的创造,是为表达作者的伦理观念服务的。
引进鉏麑这个新的叙述者,靠推想写出鉏麑自杀前的心理,究竟是不是合理的呢?这就要看对于历史叙事伦理持怎样的看法了。我们先来看晋国的太史怎样论证他记载“赵盾弑其君”的理由,他并没有提供、甚至没有觉得有必要设法提供赵盾直接参与或者背后指使杀死晋灵公的证据,只是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赵盾听了太史的话竟也觉得难于反驳,而是叹息说,“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不该留恋故土而不离开晋国。“弑其君”的记述虽不合于事实,却被认为合于当时王权下官场的伦理规范。这些人认为,历史的叙事,第一位的并不是忠于事实,而是要符合王道、礼义。《史记》论《春秋》的著述原则说:《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即使是出于善的动机,只要不合于《春秋》之义,也仍然会被谴责为恶。《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都注意到赵盾这个例子:“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簒弑诛死之罪。其实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王道不容许弑君,国君被弑时卿大夫留在国境之内就要对此负全责,哪怕被弑的是个暴君,哪怕这个被指责的人实际上并没有参与。布斯在《小说修辞学》里说的“他们追求的是伦理上的真理”,“迫使我们乐于按照善恶而不是是非标准去判断”,意思也是与此相近的。布斯曾分析文学叙事发生伦理效果的种种情况,他说,“作为艺术要获得成功,必须具有强烈的教育意义,作为一个个人,读者越是感到道德上的无所适从,他作为一种已形成的、富于想象的经验,对于作品的反应就越强烈。卡夫卡的小说说教吗?人们只能这样回答,如果说教就是迫使读者思索他自身道德上的无所适从,那么卡夫卡的小说就是说教的。”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左传》对《春秋》悄无声息的纠正——鉏麑怎样才能既忠又信?做不到!鉏麑无所适从,他于是自杀了。赵盾作为卿大夫对晋灵公的暴虐的行为,是应该阻止还是容忍和迎合?赵盾无所适从,他只有背负“弑君”的罪名。那么,古代的读者读了《左传》这样的记述也可能陷入无所适从,并且随之对没有疆界的君权产生怀疑。《左传》引导读者道德上的无所适从和不由自已的思索,这就是作者创造性地变换叙事角度造成的伦理效果。
尤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布斯提出的“技巧的道德性” (the morality of techniques)问题,值得仔细琢磨和予以引申、展开。叙事技巧在某些情况下具有道德性,技巧可以而且需要从伦理的维度加以审视,对此应该给予专门的研究。叙事者及其叙事行为和作为叙事行为产品的叙事文本,有的是道德的,有的是不道德的。此处所说的道德或不道德,特指作为叙事者应该具有的职业规范,叙事者可以和应该怎样叙事,不可以、不应该怎样叙事;小说叙事可以怎样运用和变换不同的视角,不可以怎样运用和变换视角。技巧的道德是指作为作家道德观念体现的技巧(如叙述角度转换,全知视角的运用)较为隐晦地体现作家的伦理倾向,体现他对人物和事件的伦理评价。作家不动声色地诱使读者同情或嫌弃某个人物。
除了有效催生云南高铁旅游热,对沿线城市的发展也不可小觑。高铁的开通,给高铁沿线城市带来更多发展商机和发展动能,有力刺激城市消费、房地产开发、经济投资等领域加速转型升级,产生一批“同城工作、双城生活、多城消费”的新兴群体。云南以高铁站车为支点的城市圈、生活圈,产业链、经济带正加快形成。
作家在叙事中运用某一技巧,也要受到约束,那就是要看是否合于叙事伦理。拿“赵盾弑其君”来说,这条记载违背了历史叙事的叙事伦理,也就是不道德的。因为,晋灵公不是赵盾杀死的,也不是由赵盾的策划而被杀的,这个记述没有事实的依据。《左传》实际上揭示了《春秋》对此的记述混淆和掩盖了的历史真相,而《左传》的相关记述内容则有很高的伦理正当性。但是,《左传》所记鉏麑的独白却是他人无从知晓的,无法证明其内容的真实,是出于他人的主观揣想,因而在叙事伦理上也是有瑕疵的。
历史叙事者有一种冲动是强化其作品的文学性,无论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或是为了表达某些隐微的思想感情倾向,他都可能要借助于文学性,富有文学才华的历史叙事者很难遏制这样的冲动。《左传》《史记》《汉书》都以其文学性成为久远年代众多读者迷恋的对象。然而,历史不同于历史文学,历史要求从细节到整体完全的真实,严格地拒绝、排斥所有的“想当然”。至于文学叙事,则不但容许而且提倡想象和虚构。布斯提到“艺术中的道德在于‘写好’”,他引用左拉的话,“当你写得糟糕时,你完全该受责备。这是我能承认的文学的唯一罪过。”小说要写得好,就必须虚构。在文学叙事中是优点而产生魅力、放射光芒的虚构,在历史叙事中会成为致命伤。以前面提及的《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例子来说,人们不可以诘问申苍岭讲述的情节何从而闻见之,因为他本来就不是陈述世上发生过的真事,他讲的是“玩世的寓言”;人们却可以诘问《左传》的作者,鉏麑自杀前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介之推和母亲隐遁而死前的对话,你是从哪里知晓的。在某些情况下,“在要显得冷漠和客观,与要使作品的道德基础绝对清楚来提高其他效果的义务之间,有着一种公开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如何选择,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各自服从不同的伦理。每个叙事者都有一个叙事的“权限问题”,历史叙事的性质,决定了他自动放弃了虚构的权力,细节也不应该虚构。古人对于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有时区分不够严格,是一种时代局限。在评价古代历史经典文本的文学性时候,对其中想当然的虚构大加赞扬,是不可取的。
注释
①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亨利·詹姆斯文论选》,朱乃长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4页。
③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85页。二知道人原名蔡家琬,生活在18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
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9页。“浑良夫之躁”见于《左传》“哀公十七年”,卫灵公梦见浑良夫向他大声抗诉,之后占卜,他在占卜时必定要给卜者描述梦境,这和鉏麑死前独语是不同的。《左传》写到浑良夫之躁,没有也不需要转换到全知视角。
⑥参见詹姆斯·费伦:《伦理转向与修辞叙事伦理》,唐伟胜译,《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费伦在文中说, “当前的‘伦理转向’提出了关于技巧和伦理的关系问题,以及我称为讲述的伦理和内容的伦理问题”。讲述的伦理,即运用叙事技巧的伦理规范。又可参见伍茂国:《叙事伦理: 叙事走向伦理的知识合法性基础》,《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 期;江守义:《中西小说叙事伦理研究路径之比较》,《中国文学研究》2019 年第 2 期。
⑦可以参见希罗多德:《历史》,周永强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9、43、77、89、94、103、108、126、132、138页,其他还有很多,例如,其中第77页:巴比伦神殿下,曾经有一座纯金的人像,“我自己没有见过这座像,但我这里是遵照着迦勒底人告诉我的话写的”。
⑧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9-20页。
⑨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1页。
⑩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