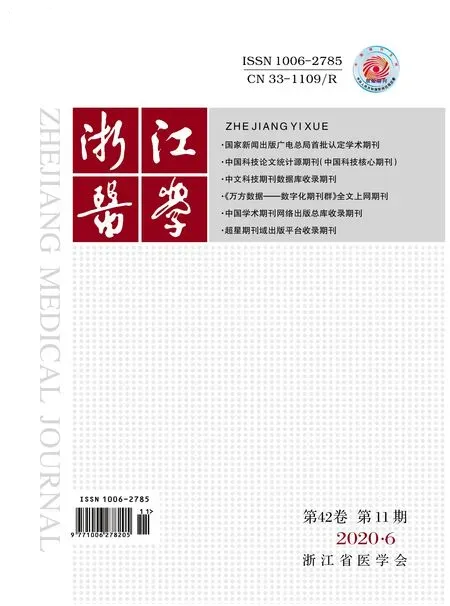Richter综合征1例
应双伟 郭群依 冯长伟 罗文达 张丽
Richter综合征作为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CLL)的一种并发症,首次由Richter于1928年报道CLL并发组织肉瘤而得名,目前定义为CLL转化为更高级别的淋巴瘤,以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DLBCL)最常见,称为经典型 Richter综合征[1]。Richter综合征发病机制不明,治疗方法尚未统一,患者预后往往较差,现将本科收治的1例经典型Richter综合征的诊治经过报道如下,以供同行参考。
患者男,51岁。因“体检发现血白细胞升高1周”于2014年5月入住血液肿瘤内科治疗。查体:两侧颈部、腹股沟多发肿大淋巴结,较大者约3cm×2cm,质地韧,无触痛,活动度欠佳,心、肺听诊无殊,脾肋下2横指可触及。实验室检查:血白细胞37.3×109/L,淋巴细胞绝对值32.5×109/L,血红蛋白、血小板水平正常;乳酸脱氢酶(LDH)192U/L。B超检查示:两侧颈部及腹股沟多发肿大淋巴结,较大约3.6cm×1.7cm,内可见血流;脾大,长径137mm,厚径51mm。骨髓形态学检查示:增生明显活跃,淋巴细胞占88%,成熟型为主,幼稚淋巴细胞3%。外周血免疫分型示:CD5+,CD19+,CD23+,CD20+,CD10-,FMC-,CD34-。外周血TP53基因缺失及CCND1/IGH融合基因的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提示阴性。淋巴结病理学检查示:淋巴结滤泡大小不一,周边小淋巴细胞增生,排列较密集;免疫组化示:CD5+,CD43+,CD23+,BCL2+,CD20+,CD10-,CD3-,CD79a+,CyclinD1-,Ki-67(约 10%)。诊断:CLL(Binet B期,RaiⅡ期)。
根据《中国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诊断与治疗指南》[2],患者无治疗指征,遂门诊随访2年,期间病情稳定,2年后未再随访。直至2017年5月患者因发现右侧睾丸无痛性肿大10余天入住本院泌尿外科治疗。查体:体能状态评分1分,两侧颈部及腹股沟多发肿大淋巴结,较大者约3cm×1.5cm,脾肋下2横指可触及,左侧睾丸无肿大,右侧睾丸肿大,无明显触痛。实验室检查:血白细胞24.8×109/L,淋巴细胞绝对值 21.2×109/L,血红蛋白125g/L,血小板 112×109/L,LDH 541 U/L。B超检查示:右侧睾丸肿大,回声减低不均匀,见丰富血流信号。遂行右侧睾丸根治性切除术,术后睾丸病理学检查示:睾丸正常结构破坏,可见淋巴细胞异型增生,细胞大小较一致,弥漫排列,间质见少量残存的生精小管;免疫组化示:CD20+,CD10-,CD3-,CD5-,CD23-,CD43-,CD79a+,CyclinD1-,Ki-67(60%),Bcl-2+,Bcl-6+,Mum-1+,CD117-。病理学诊断:考虑 DLBCL。骨髓活检及免疫组化未提示DLBCL骨髓浸润。脑脊液流式分析示淋巴瘤颅内浸润。PET/CT示:全身多发淋巴结肿大,标准摄取值(SUV)最高值约8.9;全身多发骨质破坏,SUV最高值为19.9,左侧睾丸及脑实质未见异常。诊断:DLBCL[非生发中心型(non-GCB),国际预后评分(IPI)3分,IVA期]。结合患者既往CLL病史,临床诊断:经典型Richter综合征。
患者因经济原因拒绝使用利妥昔单抗,2017年6月7日至7月23日先后接受3周期标准剂量CHOP方案(环磷酰胺、长春地辛、表柔比星、甲泼尼龙)化疗联合鞘内注射化疗,多次复查脑脊液持续阴性,LDH水平一度下降,但3周期化疗后出现全身骨痛表现,LDH再次上升,考虑疾病进展。患者拒绝接受更高强度化疗,于2017年8月16日起予R-CHOP方案(利妥昔单抗联合CHOP方案)化疗3周期,患者骨痛症状加重,淋巴结较前增大,合并血红蛋白、血小板下降,体能状态不佳,强化疗难以耐受。患者2017年11月15日改R-GDP方案(利妥昔单抗、吉西他滨、顺铂、地塞米松)化疗1次,2017年12月出现双下肢无力,排尿困难。查体:双下肢肌力减退,1~2级,脐水平以下感觉异常,痛觉减退。B超检查示:两肾见散在低回声区,较大者直径约3cm。胸椎MRI示:胸8~10椎体旁多发异常信号,相应水平胸髓受压。复查PET/CT示:部分椎体伴周围软组织密度形成,双肾实质多发团块影,较大约3.8cm×3.7cm,SUV最高值9.59,余淋巴结及骨骼病变较前进展。患者因一般情况差,强化疗不能耐受,选择姑息治疗,2017年12月18日起接受椎体姑息性放疗联合伊布替尼420mg/d治疗,病情出现短暂稳定,但血象下降明显,予加强支持治疗及伊布替尼减量,最终病情进行性恶化,于2018年3月死亡。
讨论约1%~10%CLL在病程中发生Richter综合征转化,年发生率0.5%~1%,转化的中位时间近2年[3]。Parikh等[3]发现近50%CLL患者在达到治疗指征之前发生了Richter综合征转化,本例患者亦是在CLL无治疗指征的随访期间发生了转化。因此,单纯认为Richter综合征是CLL的终末期事件是一个误区。根据DLBCL与CLL两者之间的来源相关性,将Richter综合征分为克隆相关与非相关,前者约占80%,后者约占20%。而如何判定两者的克隆相关性,较为准确的方法是通过测定两者免疫球蛋白重链可变区(IgHV)基因序列的一致性来判定,目前大多医院未能开展,本例患者亦未能行该项检测。
Richter综合征的发生机制尚不明确,目前认为MYC基因的激活、TP53基因缺失、CDKN2A缺失、NOTCH1基因突变是CLL发生转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另外端粒长度、IGHV 无突变,BLC-2、CD38的遗传多态性以及CLL的既往治疗在转化中也起到一定的驱动作用[3-4]。Rossi等[5]认为在CLL的病程中,当患者出现以下表现时需高度警惕Richter综合征转化的可能并建议活检:(1)淋巴结直径>5cm;(2)淋巴结快速增大(倍增时间<3个月);(3)可疑的结外病灶;(4)B症状(发热、盗汗、消瘦);(5)LDH明显升高。本例患者在CLL随访初期疾病稳定,后未再随访,疾病进展期以睾丸肿大为新发症状,PET/CT检查提示全身骨质破坏,而疾病初期无骨痛表现,可以看出一些结外病变的发生较为隐匿,尽管患者初期TP53基因缺失检测阴性。因此,CLL初诊时全面完善相关基因的检测来评估转化的风险以及随访期间患者的依从性至关重要。临床一旦怀疑转化,PET/CT检查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有研究指出SUV>5的淋巴结具有较大的活检价值,其阳性预测值(PPV)为53%,阴性预测值(NPV)为97%,即SUV>5的淋巴结活检阳性率为53%,而SUV在5以下的淋巴结阴性率高达97%[6]。为提升PPV,有学者建议把SUV值为10作为一个截点[7]。本例患者PET/CT检查提示淋巴结、骨骼等病变部位的SUV明显增高,最高近20,符合侵袭性淋巴瘤表现。因此,活检前行PET/CT检查并活检SUV高值的组织有助于提高阳性率。
Richter综合征预后指标较多,其中以转化的DLBCL与基础CLL的克隆之间的相关性最为重要。非克隆相关DLBCL的生物学行为、治疗及预后与原发初治的DLBCL基本一致,中位生存时间(OS)约62个月,而克隆相关的患者仅8~14个月[8]。本例患者起病隐匿,发病迅速,治疗反应不佳,自确诊Richter综合征至死亡仅10个月,推测两者存在克隆相关的可能性大。此外,基于对Richter综合征的临床表现、遗传学改变以及治疗反应的分析,目前已有数个预后评分系统。Tsimberidou等[9]通过一项含148例Richter综合征患者的研究分析中提出5个预后指标,包括(1)体能状态评分>1;(2)血清LDH水平>1.5倍正常值上限;(3)血小板计数<100×109/L;(4)肿块直径>5cm;(5)先前治疗方案>1种。每个指标均计1分,分为低危(0~1分)、低中危(2分)、中高危(3分)、高危(4~5分),中位OS时间分别为13个月、11个月、4个月、1个月。该预后评分系统的有效性在其他研究中也得以证实[10]。另外Rossi等[8]结合Richter综合征的分子学特征及治疗反应,提出了另一个预后评分系统,包括体能状态评分、TP53基因状态、Richter综合征治疗效果3个指标,分为低危(同时符合体能状态评分 ≤1分,无TP53基因缺失,完全缓解),中危(介于两者之间),高危(体能状态评分>1分),因该系统包括Richter综合征的治疗反应,不能作为初始Richter综合征的预后评估。以上的预后评分系统主要基于免疫化疗的背景下,而随着新型药物在CLL和体能状态评分中的开展,预后评分系统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目前Richter综合征的治疗尚未统一,主要分为免疫化疗、放射免疫疗法、造血干细胞移植、新型药物四类,放射免疫疗法因其疗效不佳及不良反应大,目前已不再应用于临床[11]。而传统蒽环类和铂类为基础的化疗的完全缓解率(CRR)<20%,转化后的中位OS<12个月[3]。一项含15例Richter综合征的回顾性研究得出:R-CHOP方案治疗的总反应率(ORR)达到67%,而CRR仅7%,治疗相关死亡率(TRM)为3%,中位OS为27个月[12]。本例患者治疗初期先后接受CHOP、R-CHOP方案化疗,但疾病进展迅速。为取得更好的缓解,在疾病初期是否应该接受更高强度的化疗?既往文献报道高强度蒽环类化疗虽能取得更好的CRR,但同时带来更高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和TRM。在一项应用Hyper-CVXD(环磷酰胺、长春新碱、脂质体阿霉素、地塞米松)方案治疗 29例Richter综合征的回顾性研究中得出:ORR为41%(其中 CRR为38%)、TRM高达14%,中位OS并未延长,仅10个月[13]。也有研究采取Hyper-CVXD联合利妥昔单抗方案,但未取得更好的疗效[14]。遗憾的是,以铂类为基础的方案亦未能取得更好的疗效,Tsimberidou等[15-16]应用OFAR方案(奥沙利铂、氟达拉滨、阿糖胞苷、利妥昔单抗)进行的两项研究结果表明ORR为43%~50%,CRR为6.5%~20%,中位OS分别为6.6和8个月。本例患者对TRM存在较大的顾虑加之体能状态的恶化,病程中始终拒绝更高强度的化疗。
鉴于常规免疫化疗难以持续缓解,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可作为缓解后巩固或挽救治疗一种手段。Tsimberidou等[9]回顾性分析17例行Allo-HSCT的Richter综合征患者后得出:移植前为部分缓解(PR)或CR组的 3年OS为75%,难治组为21%,初治有效未行移植组为27%,表明移植可以降低复发率并延长生存,且初始治疗的效果直接影响移植疗效。另外,Cwynarakl等[17]于 2012年回顾 59例Richter综合征移植患者,Allo-HSCT和Auto-HSCT的3年OS分别为36%和59%,Auto-HSCT组有更好的生存可能归结于该组移植前更高比例的PR和CR。总之,造血干细胞移植能改善Richter综合征的生存已毋庸置疑,但由于患者年龄、体能状态以及疾病缓解程度的影响,仅不到15%的患者有机会接受移植[9]。
由于Richter综合征的难治性及对其发生机制研究的深入促使了新型药物的研发,目前已有包括布鲁顿酪氨酸激酶(BTK)抑制剂、Bcl-2抑制剂、PD-1抑制剂、核输出蛋白抑制剂等在内新药进入临床试验,并初见成效。伊布替尼(Ibrutinib)作为BTK抑制剂,目前已批准用于CLL和套细胞淋巴瘤(MCL)的治疗,而在Richter综合征的治疗中,Tsang等[18]的一项研究中,4例Richter综合征患者接受伊布替尼联合甲泼尼龙治疗,1例取得CR,2例取得PR。本例患者疾病发病初期病变广泛,如初期能进入新药临床试验可能有机会获得更好的疗效,从而赢得骨髓移植机会。Acalabrutinib作为另一种具有高选择性、强效的BTK共价抑制剂,在一项含29例Richter综合征的Ⅰ/Ⅱ期临床试验中取得38%的ORR和14%的CR[12]。Venetoclax作为Bcl-2拮抗剂,在7例Richter综合征治疗的Ⅰ期临床试验中,3例(43%)取得了PR[12]。Pembrolizumab作为PD-1抑制剂,在一项含9例Richter综合征的Ⅱ临床试验中,ORR达到44%(CR11%,PR33%),中位无疾病进展时间(PFS)和OS分别为5.4个月和10.7个月[19]。Selinexor,作为一种选择性核输出蛋白抑制剂,在CLL和Richter综合征中的应用主要基于通过减少TP53的核输出来增加抑制肿瘤活性。一项Ⅰ期临床试验中,6例Richter综合征的ORR为33%,其中无CR患者[20]。可以看出,新药在Richter综合征中的治疗初见成效,但目前尚处初期临床试验阶段,需要更大的临床数据加以证实。
总之,Richter综合征的预后和治疗方案的制定,最重要的因素是DLBCL与CLL是否存在克隆相关性,20%的非克隆相关患者的治疗及预后同原发初治的DLBCL,R-CHOP为一线治疗方案。而80%克隆相关性的患者目前治疗尚未统一,造血干细胞移植及新型药物有望改善预后,治疗目标是尽早达到缓解后联合移植巩固,对于难治复发或者高危的患者争取进行临床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