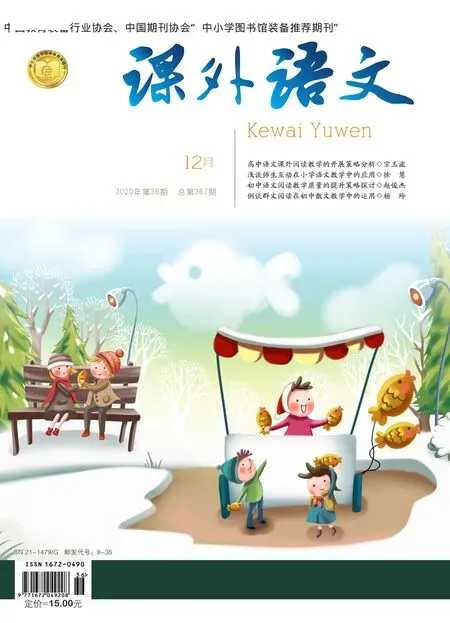培养核心素养,设问需要“看见”
许晋华
(山西省太原市四十八中学校,山西 太原 030000)
一、基础篇——要“看见”文本重点
课堂设问原则:难易适中,提问要有思维度;由浅入深,提问要有递进度;质疑问难,提问要有双向性……在基础阶段,设问首先要解决的是文本问题——教学内容是什么,有什么特点,重难点在哪里,教师要根据具体内容设计问题。
首先,教师要有“整体阅读”的意识,把问题放到整篇、整个单元、整本书里考虑,有的放矢,紧紧围绕重点,针对难点,扣住疑点,体现强烈的目标意识和明确的思维方向。要避免“碎片化”、随意性、盲目性和主观性。
其次,我们也可以用知识形成的建构理论来确定重点和难点,就是知识的最近发展区和知识的未知区。通过提问了解学生的熟练程度,进而确定最近发展区和未知区,然后围绕重难点展开教学,可以提高课堂有效性。
二、进阶篇——要“看见”学生
(一)“看见学生”就是“以学生为本”
虽然我们在问题的设置上分层梯度、有轻重,但是这是技术层面的设计,都不代表真正“看到”了学生。北师大肖川教授认为:“从学科角度讲,要为素养而教(用学科教人)……把教学局限于狭隘的学科本位中,过分地注重本学科的知识与内容,任务和要求,这样将十分不利于培养视野开阔、才思敏捷并具有丰富文化素养和哲学气质的人才。”
设问过分关注或只关注文本,看不见学生——就是无视学习规律。
有的设问大而无当,学生无处着力,不敢吭气;有的设问太小、太碎,没有重点,学生疲于应答,思维混乱;还有的问题设计,看起来“行云流水”,可一实战就“落花流水”,因为不是真的理解,学生得猜答案,猜不着只能放弃,教师只能一个人唱“独角戏”。
(二)看得见学生,设问的调整才有方向
在上《苏东坡突围》这个主题课的时候,我设置了一个主问题“面对困顿,我们应该如何突围?请结合苏东坡的资料,想一想他突围的态度给了你怎样的启示?请有观点、有依据形成一段完整的表述”。虽然课前给学生印发了相关资料,结果看到问题时,学生们仍旧手足无措——说明这个问题的设定是不清晰的,超出了学生的理解处理的范围。
第二次设问,改成了“当人生起伏不定,甚至走向低谷时,苏东坡是如何面对他的困境的?你看到了什么”。设问充分地考虑了学生的实际情况,站在学生的情感体验立场上去问,唤醒了同理心;从苏轼到学生自己,逻辑合理;问得清晰具体,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有话可说,效果很好。
(三)看得见学生,可以在同等情况下让设问更合理,更有效
在学习《深刻与伟大的另一面是平和》时,萧红捕捉了许多鲁迅生活的细节,凸显出一个生活化、人情味儿十足的鲁迅。在此处设问“这篇回忆录是怎么写鲁迅的”或“如何捕捉和描写鲁迅的生活细节”,问题的指向侧重于艺术方法和表达过程,范围大而且对学生基础要求高,学生不容易回答。就不如“回忆录中细节众多,哪几处是你印象最深的?请找出来并谈一谈你的理解或感受”效果好。同样是关注细节,后者从学生的实际感受出发,降低门槛,让人人都有话说,并支持个性化的表述。只要认真研读文本,学生都能有所获:有的同学发现了鲁迅先生“待人大方”和“待己简朴”的差异;有的同学发现抽烟的状态可以代表鲁迅先生健康时和病重时差别;有的同学独辟蹊径,体会出海婴“明朝会”里,孩子的懵懂天真与成人面对生死时的沉重所形成的巨大悲剧效果。这堂课学生是真正在感受、思考、表达。
(四)看得见学生,尊重思维发展的规律,设问才能循序渐进,收放自如
在学《卫风·氓》这一篇叙事诗时,学生容易关注到的是叙事的内容,易忽视的是情感的脉络。学生是先入为主地觉得“弃妇诗,当然会有愤怒和悲伤”,还是从字里行间真正感受到那种伤心和痛苦?这两种学习状态,在情感体验和思维发展的深度上是不一样的。
用深度思维去学习体会,我们便看到了好似十八里相送的“送子涉淇,至于顿丘”中渗透出的依依不舍;看到了“不见复关,泣涕涟涟”和“既见复关,载笑载言”这又哭又笑的矛盾中的“纯真”与“痴情”;看到了“淇则有岸,隰则有泮”里面的痛苦与坚决……
原来可能被同学所忽视的三次关于淇水的描述,便在平铺直叙中突然“不平凡”起来。
教师设问:“‘淇水汤汤,渐车帷裳’这句话该怎么翻译和理解呢?”学生首先会解词“汤汤”是水势浩大的样子。教师继续提问:“第一次叙述送子涉淇,用的是‘涉’字,‘涉’字形就是徒步过河的样子,你感觉水势如何呢?”学生一对比,很快发现,刚开篇淇水水势并不是很大,前后是有差别的。教师追问:“为什么要这样描述,是在表达什么呢?”学生苦思还是不明白。“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现在“启发”的节点出现了,教师提示:“水,是诗歌中的常见意象,关于‘水’诗句,你还知道哪些呢?”这一问,学生思维被激活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教师问:“大家发现‘水’可以表达什么样的感情呢?”学生有了理解“深厚的友情,含蓄深沉的爱情,无法消散的愁绪,一去不返的失落”再读这两句,学生突然理解,“淇水汤汤”,原来是悲愤情感的汹涌与浩大。教师再问:“从这两句中你看到了什么样的画面?”学生又进一步理解,思维跳跃“我看到她在哭!她在擦眼泪”,原因就是“渐车帷裳”学生进行了合理的想象。在解开“水”这个意象密码后,对诗中主人公的情感一下有了“理解”。三次“淇水”的描述,贯穿了全诗,表达情意自然而然,含蓄蕴藉。当学生真的理解了诗句的深层含义时,因有所感悟而不禁自语“这首诗,写得真美……”。
三、升华篇——要“看见”自己
(一)看得见自己的局限
每个人都有自己认知的局限,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设问的时候,认识到自己会陷入认知的局限当中,那就需要有一种高度自觉的意识。
去上海风华中学听课的时候,有一位教师讲《胡同文化》,是汪曾祺先生的一篇散文。课堂的设问关注细节,紧扣文本,在情感态度分析时问:“作者的情感是沉重、悲凉,怀旧、伤感,而结尾句是‘再见吧,胡同。’用的是逗号和句号,表现的是什么情绪呢?胡同文化有什么外在的因素和内在的因素,让作者是这种态度呢?”于无疑处生疑,在课堂上掀起了一个思维的高潮。
这样处理本文,我以前是没有想到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对文本的理解不够深,但仔细去想其实受限于自己的思维的“先入为主”的定式,在备课之初,潜意识就已经认定胡同文化属于传统文化,胡同文化的没落是令人伤感的。这就限制了我想到作者会“平静、果断接受胡同文化没落”的这另一种可能。每一个成长中的教师都有可能陷入这样一种“知”的局限而不自知,“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二)看见自己发展的空间
1.运用主动学习策略,积极跨界,向外寻求设问发展的新空间
耶鲁大学哲学系教授塔玛尔·甘德勒,开设了一门哲学与认知科学通史课,其中包括经典的哲学、文学和心理学,还融入了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的研究结果;在“康德哲学”单元,她会提出:“如果你在驾车回家途中接听手机,但没有发生任何交通事故,是否仍在道德上受到谴责?”让学生耳目一新。
而我们语文课堂也可以用心理学的知识,多一种角度设问,引导学生思考《荷塘月色》朱自清的“淡淡”的情感表达,《氓》里“弃妇”爱情悲剧原因,《离骚》“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里面不被“理解”“信任”的痛苦,《孔雀东南飞》中婆婆赶走刘兰芝的理由……
培养学生思辨性、创新力,需要突破学科壁垒,尝试跨界。只有教师积极学习,扩大自己的视野,提升自己的格局,才能问真正具有启发性的问题。
2.课堂提问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威慑,而是交流;不是教条,而是艺术
而把它从技术上升到艺术,让更多的学生受益,还需要每一个教师进行大量的实践,认真的反思,广泛的学习,积极的行动。让课堂成为学生思维生长的家园吧,我们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