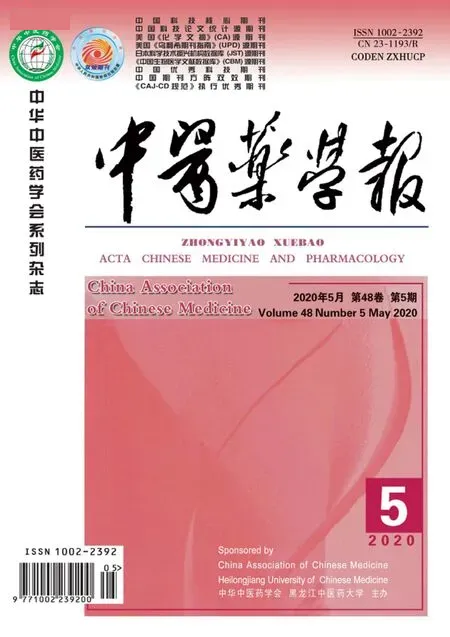基于“湿性疠气致病特点”与“初病即入肺络”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辨治
张福利,李显筑,高恩宇,迟明洋,商春爽,张冠珣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2.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6; 3.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基于武汉地区气候环境潮湿以及发病初、中期多呈舌苔厚腻的证候特点,而从“湿瘟”论治,是一线中医专家们形成的应急性共识。该共识指导下形成的中医药防治方案,疗效显著,令世人瞩目。但临床成就的取得并不意味着理论认识的完结,中医对疾病认识的深化是“辨证求因”“审因论治”和“以方侧证”“以效归因”的开放性互动过程。目前,对新冠肺炎多见“舌苔厚腻却反而干咳”而非咳嗽、痰多的“矛盾性”表现的具体机理,中医界尚缺乏系统的阐释和研讨,这势必影响到对该病之因机证治的全面、系统性认识。本文意在以新冠肺炎“舌苔厚腻却反而干咳”之特征性临床表现为切入点,以明清温病学家的相关理论为依据,以现代医学的认识成果为佐证,形成对该病的因机证治之深化性探讨和推论。
1 学术争鸣中不可忽视的“审证求因”着眼点——舌苔厚腻而反干咳之特殊临床表现
鉴于新冠肺炎初、中期多出现舌苔厚腻,从武汉当地到全国各地包括黑龙江省的病例,均呈现这种共性表现,相关中医专家虽因各人学术底蕴及所诊疗患者证候表现差异等因素,有主张从“寒湿疫”论治或从“湿热疫”辨治之不同,但在“祛除湿疠痰郁”的总治法上已高度共识。如两者都主张可用藿朴夏苓汤治疗该病初、中期,虽然尚存在认为所治之证属于寒湿证或湿热证之分歧[1-2],但从实际证候间距考量,湿热病中的湿重于热之证,和同为温病学范畴的温热病,在因脉证治上相距较远,反到同寒湿证的治法、用药高度趋同,属类证范畴;进而在辨治细节上,又都强调要随机处置因为各种因素导致的“寒湿证”和“湿热证”互相转化问题,更可见并无根本分歧。清代温病大家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论解湿温病时即将湿热证治与寒湿证治并列研讨,供后人互参,其广博胸怀令人景仰。抗疫实践证明,完全基于温病学或单纯从伤寒体系论治,都不能囊括诊治新冠肺炎的各种证候类型及病程发展各个阶段之所需。因此,更需提倡学术争鸣中的包容性。
在此前提下,更值得深入探讨的细节问题是:一方面新冠肺炎发病初、中期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症状表现;而另一方面该阶段患者又多呈白腻或黄腻苔,总体以舌苔厚浊粘腻为舌诊特征。基于通常的“审证求因”推理,舌苔厚腻多标志痰湿为病,但具体应怎样理解痰湿内盛而又出现干咳的“矛盾”征象?一般对干咳症状,大多归因于外感燥邪致病、后期阴伤致病;或从感受湿热而化燥伤阴推求。但从武汉潮湿的气候环境到发病之初就表现为舌苔厚腻且无明显剥落,均不能全面支持外感燥邪致病、外感湿热而化燥伤阴、后期阴伤致病之类的推断。进而从燥湿相混之病因来整体诠解新冠肺炎的特殊发病表现、病情重而死亡率高等诸多问题,亦显牵强而局限。中医“审证求因”的认识方式,不仅仅是只从形式逻辑推断,更要遵从辨证逻辑推理,后者所求之因不仅是外界邪气或者其叠加,更包含体质、病层参与的病机因素。如同对临床常见的外感热病中的“寒包火”之证,从形式逻辑推断可以得出是“同时感受了‘寒’‘热(火)’两种外界邪气所致”,但基于辨证逻辑推理而认为属于“‘内热体质’基础上感受‘外寒’”,其推断才更合理。
那么,舌苔厚腻而咳嗽、痰多与舌苔厚腻却反而干咳、无痰,在总体病机相近的情况下,又有何细节差异?进而在拟订治法、处方用药上又如何更有针对性地处置?显然,这是关系到如何更准确把握新冠肺炎之因机证治的特点而提高临床疗效的关键问题。
2 舌苔厚腻反而干咳属“湿疫性”新冠肺炎“初病即入肺络”之特殊病机的重要征象
笔者基本观点是,新冠肺炎初、中期表现为舌苔厚腻却又干咳,属于感受湿性疫气迅即导致痰湿秽浊阻滞之“初病即入肺络”证而非通常“肺经痰湿证”,前者较后者病情更重,是该病迁延后更易趋向重危症的病因病机基础。仝小林等基于吴又可的“戾气学说”,较早提出新冠肺炎不同于一般六淫导致的普通肺炎,具有发病即“毒袭肺络”的病机特点,因而倡导注重早期“宣通肺络”治法[3],但尚未对“初病即入肺络”之具体机理给予阐明。笔者认为要完成这方面的深化研究,需要将吴又可的疠气学说,同叶天士的温病学说和络病学说以及吴鞠通、薛生白、王孟英等温病学家的相关认识进行汇通性探讨,并参合现代医学角度综合分析,才能取得更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2.1 从叶天士“久病入络”学说到其对外感温热病“初病入络”之因机证治的阐释
《内经》载述经络系统由经脉和络脉构成,是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网络系统。清代温病大家兼络病学说集大成者叶天士阐释“卫表阳络-中层气经-深层阴络”模式的经络系统空间构型,亦是时间流程上疾病从浅入深、从轻到重的进展路径:邪在卫表阳络为病轻浅,邪居气经则病加重,邪入阴络病情危重,为外感热病及内伤杂病之病程进展的一般规律。又认为卫表阳络和中层气经总属“气”之分野,而深层阴络为“脏腑隶下之络”,属“营血”分野;络有阳、阴之分而邪入“阴络”多属疾病后期、重症阶段,所以“由经脉继及络脉”(《临证指南医案·胁痛》)而“久病入络”(指“阴络”,以下同)为“一定之理”。当代学者吴以岭据此界定:“络病,作为络脉系统发生的病变,是广泛存在于多种难治性、危重性疾病中的病机状态”[4],进而对“久病入络”基础上的具体络病病机及分型证治给予了系统总结。
按叶氏“久病入络”论,络病多发生在外感热病的后期、重证阶段,标志着后期和重证的时空一体性,其学说影响深远。实际上叶氏也重视“初病入络”,认为其病位既可在卫表阳络,也可在脏腑阴络。就脏腑阴络证的初病特点而言,认为“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温热论》),心肺在温病包括湿热性疫病方面的受邪、传变及证候表现上均有特殊性:肺居五脏中最表浅之华盖,职司呼吸,其阴络循气道而与外界直通,不同于其它脏腑阴络之处于内隐状态;心肺比邻,同居上焦,气血相关,生理及病理上联系至为密切。所以,他提出“初病入络”之脏腑阴络证以肺、心包之证多见。《临证指南医案·卷五·温热》即曰:“吸入温邪,鼻通肺络,逆传心包络。”详考叶氏著作,所论“初病入络”病证大致有两类:一类是邪犯体表阳络,一般病情较轻;另一类是邪入脏腑阴络,其中,邪入心包络,病情危重;而邪入肺络之病情总体上较前者轻,但无疑较病在体表阳络之证更重,即多属重症范畴。
总之,叶氏虽力倡“久病入络”说,但也阐述了“初病在络”理论,并认为病在体表阳络时病情轻浅,病在脏腑阴络则病情较重。由此阐释了临床上初病即现重证的机理,提出了不同于“初期-经病-轻证”“久病-络病-重证”的一般规律的特殊病机表现。
2.2 吴鞠通、王孟英、薛生白对叶氏湿热性疫病“初病即入肺络”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叶氏之后,其他清代温病大家吴鞠通、薛生白、王孟英,在继承“久病入络”学术思想基础上,又结合对吴又可温疫病学的吸取及各自临证总结,对叶氏“初病入络”的因脉证治给予了补充、发展。但目前中医界对此的挖掘和发挥还有所不足。
明代吴又可《温疫论》开篇即云:“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传有九,此温疫紧要关节。”认为疫病属感“疠气”而致,发病即“邪伏膜原”,基于疠气的不同类型及病家宿病、体质上的差异,可发生不拘于六经程序的多种传变;阐明不同于一般六淫之“疠气”所导致“温疫”,为病凶险,在病机传变、证候表现及治法方药上都有特殊性,创制了治疫名方达原饮。关于膜原,《内经》首先提及,但对其生理、病理并无具体阐述。吴氏始创“邪伏膜原”说,认为膜原居“经、胃交关之所”,为“表里分界”,是众多疾病的介导[5]。虽然吴氏“膜原说”协助其“疠气说”开创了外感热病诊疗的新局面,但后代医家亦有对其膜原界说持异议者。清末医家周学海《读医随笔·伏邪皆在膜原》即云:“人之一身……皮与肉之交际有隙焉,即原也……原者,平野广大之谓也。”提出膜原并非局限胃肠之间,而是广泛分布周身的机体重要调节系统。现代学者更有直指膜原即相当于后世叶天士所言“阴络”[6]。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透过概念表述差异,实质上吴又可已开创了“初病即治阴络”体系。
清代温病大家吴鞠通,既借鉴吴又可的疠气学说、膜原学说,又承接叶天士的温病理论、络病学说,并将它们有机融合,对包含“初病入络”的络病证治进行了新探索。吴氏著作与医案中多处指出六淫、疫邪侵袭均可引起“初病入络”之证,但其病位有阳络、阴络之异,病情有轻重缓急之分[7]。认为由一般六淫导致者病情较轻,其所论感受湿热,邪阻卫表阳络,导致寒热身痛而治用宣痹汤,即属邪犯卫表阳络之轻证;所论感受暑热,邪伤肺络导致干咳而治用清络饮,亦属较轻之证,但病位已在肺内阴络;而所论感受疟邪,传变不循常理而出现“初病入络”之肺络阻滞证,虽病位同为肺内阴络,但已属较重之证;如在此基础上迅速出现邪入心包证,更属危重证候。《温病条辨·上焦篇》第53条自注即云:“心疟者,心不受邪,受邪则死,疟邪始受在肺,逆传心包络。”
较之叶氏,吴鞠通对“初病即入肺络”的因机证治有了更系统总结,但尚未对感受湿疫秽浊致痰湿阻滞肺络之咳嗽的特异表现,给予具体阐述,王孟英进而细化诠解。《王氏医案·卷二》云:“痰在络中,如何自吐……岂可以不见痰面,遂云无痰乎?”“盖由痰能阻气,气不能运痰耳。”阐明素体气虚失于运化加之外感湿浊更伤阳气,迅即导致痰湿阻结肺络,是痰湿内盛而又干咳的根本症结所在。对“初病入络”之痰湿阻结肺络所致咳嗽的临证处置,长于治疗湿温疫病的薛生白,在《湿热病篇》第18条曰:“湿热证,咳嗽昼夜不安,甚则喘不得卧者,暑邪入于肺络,宜葶苈、枇芭叶、六一散等味。”其自注更云:“人但知暑伤肺气则肺虚,而不知暑滞肺络则肺实。葶苈引滑石直泻肺邪,则病自除。”薛氏所论暑邪,当为湿热合邪之暑湿而非暑热,而以葶苈子合滑石清涤肺络的治法,亦显示其发挥仲景葶苈大枣泻肺汤的独到之处。
2.3 舌苔厚腻而反干咳属“湿疫性”新冠肺炎“初病即入肺络”特殊病机的主要征象
清代温病四大家,对“初病入络”尚未如对“久病入络”那样进行纲领性表述,但实际上对前者之因脉证治的总结已较系统,对得出“舌苔厚腻反而干咳属‘湿疫性’新冠肺炎‘初病即入肺络’特殊病机的主要征象”之结论,具有重大指导作用。该结论验之于现代医学也有充分根据。现代医学影像学证实,一般性肺感染的炎症病灶多以大支气管、肺门为中心而分布,随之多表现为咳嗽、有痰之症,进而引发间质性肺炎乃至肺纤维化,为慢性过程;而新冠肺炎和SARS的磨玻璃样炎性病灶,多分布肺体边缘,远离大支气管,以致病灶中的黏液难以排出而表现为干咳,又易急骤发生间质性肺炎进而发生肺纤维化。前者的慢性过程,即属“久病入络”,而后者的特异病理表现及急性过程,则为“初病即入肺络”。
总结上述,叶桂所言“久病入络”是把“从经到络”作为“一定之理”来对待。叶氏之前的吴又可更强调疠气致病,并非从寻常六淫致病特点所能完全推断,而是有其特殊致病表现和传变规律。叶氏之后,吴鞠通、王孟英、薛生白等温病学家在将几种学说有机融合并结合各自临证总结基础上,更系统地形成对“初病即入肺络”之因脉证治的认识。总结上述医家学术思想,结合现代医学对新冠肺炎的认识,笔者进而认为,湿性秽浊较一般湿邪更易重伤阳气、阻滞气化而致发病之初即乘肺气之虚,循气道而入肺络,迅即导致痰湿阻结肺络,是致病外因;现代人膏粱厚味及运动不足的不良生活方式产生的体质上的气虚、湿蕴、络郁,是致病内因,该病的发生及特殊表现,是内、外因相合的结果。如薛生白《湿热病篇》第1条自注所云:“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清代温疫学派医家戴天章曾为吴又可张扬“伤寒下不厌迟,时疫下不厌早”(《广瘟疫论·卷之四·汗法》)之理,发展了仲景通下法的临床应用。现在,我们根据新冠肺炎“初病即入肺络”以及“络体狭小,病邪易入难出”[4]致使病情难愈的病机病程特点,可得出治疗该病亦应“通络不厌早”的推论,以承接温病四大家的“初病入络”而需“新病治络”之论。
3 针对“湿疫性”新冠肺炎“初病即入肺络”之特殊病机而行治络之法的总结、研讨
现代医学对新冠肺炎尚无特效药,主要依靠自身免疫功能恢复而辅以适当支持疗法。对咳嗽症状,认识到是机体自我排毒、调复的有益反应。有证据表明,在该病重、危期的预后方面,有咳嗽表现者较之无咳嗽者,脱离危重症的比例明显增高而死亡率降低[8]。再结合中医总结的湿疫疠气的病因特性,“初病即在肺络”的病机特性,可得出结论:新冠肺炎病情进展上,咳嗽而有痰(痰湿壅盛肺经或兼轻度肺络阻滞)、干咳(痰湿阻结肺络)、咳嗽消失(痰湿夹瘀闭塞肺络),构成了从轻到重的相关序列,随之也说明对该病实施更系统、完善的早期性、全程性、细化性治络的重要性。
3.1 关于针对“湿疫性”新冠肺炎“初病即入肺络”之特殊病机而实施“新病治络”
纵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各省制定的新冠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虽然在初起证候归纳上多未明确界定其络病属性,治则治法上也多未直接提及通养肺络,但笔者认为,其中有中医术语表述习惯差异、中医不同辨治理论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互交叠的问题,如同吴又可膜原界说同叶天士阴络界说,名虽异而实相通一样。细研各方案细节,实际上已在处方用药上针对“初病即入肺络”的特殊病机和证候表现给予了随机应对。善治寒湿秽浊为病的藿香正气制剂,寒湿秽浊和湿热秽浊均能对治、可加减处置的达原饮、藿朴夏苓汤等,都被广泛应用并取得共识。上述三方的共用药厚朴,并非一般行气之品,《本草发挥》言其有“结者散之”之功,可散络中痰湿结聚,且又以芳香之性可治霍乱疫毒。而以厚朴、槟榔、草果为主要组成的达原饮,更是名为“开达膜原”而实属“透解阴络”的治络名方。针对新冠肺炎初、中期的其它处方用药中,通养肺络、调复气化以除痰浊阻滞的药味组合亦应用广泛。以麻黄、草果类温宣肺气而通肺络,葶苈子、陈皮类化痰湿而通肺络,黄芪、茯苓类补益肺气而通养肺络等,成为新冠肺炎初、中期处方用药的一大特点;而具清化瘟邪、宣通肺气之效,能兼治湿热、风热夹湿之证,可先期治络而预防肺纤维化的中成药连花清瘟颗粒,继2003年有效防治SARS之后,在此次疫情中更得到各地普遍应用,疗效较好。
上述包含络病治法、方药的新冠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业已取得良好疗效,进一步反证了该病初、中期就已包含“初病即入肺络”的特殊病机及证候表现。今后,尚需围绕当代络病学科从“久病入络”之因脉证治向“初病入络”的延伸、拓展,实施系列化研究。诸如,对温疫学派、温病学派、伤寒学派的融合;对吴又可膜原学说与叶天士阴络学说的汇通;对吴鞠通、薛生白、王孟英“新病治络”思想的整理与发挥;对“新病治络”之治法的厘定;对“新病治络”方药的细化研究以及中成药开发等等。
3.2 关于针对“湿疫性”新冠肺炎重、危期及一般宿病者日常防护而实施“久病治络”
据不完全统计,新冠肺炎死亡率约2%,黑龙江省等高寒地区较之略高,死亡者以老年而有基础病者为主。根据叶氏“久病入络”之理,该病重、危阶段,中医辨证则以痰湿秽浊夹瘀闭阻肺络为核心而兼及其它,已完全形成共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防治方案中[9],治疗“疫毒闭肺”(“疫毒闭阻肺络”的缩略表示方式)型重症的“化湿败毒方”中,有葶苈子祛痰水而通肺络,黄芪补益肺气而通养肺络;治“气血两燔”型重症的“清瘟败毒饮”加减方中,除葶苈子之外,还有竹叶清涤肺络之气热,牡丹皮、赤芍通散肺络之瘀热。对“内闭外脱”(即心肺之络内闭而阳气欲脱)的重危症,则以人参、附子益气温阳而通养肺络,并合安宫牛黄丸以清解心营之热或合苏合香丸清化湿热痰浊,两者都具透络开窍醒神之功。临床实践证明,将这类通养络脉、调复机体气化功能的救急疗法配合西医急救措施,可一定程度上降低新冠肺炎死亡率[10]。
基于“久病入络”理论,许多学者还认识到,对已患其他类型呼吸系统病而肺功受损者,或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而络脉瘀阻之老年人群而言,一旦患新冠肺炎,其进入“络脉闭塞”之重、危期的几率会剧增。为此,主张防疫期间对上述非新冠肺炎患者,亦应实施“通养络脉、调复气化”之临床干预。《黑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西医结合防治专家共识》即立足黑龙江省气候环境、人群体质、中医证候流行病学等方面的特点而提出:防疫期间,对其他类型呼吸系统病患者,要注意对射干麻黄汤、桑白皮汤等化痰湿、通肺络之方的运用;对脑血管病患者,酌情处以“疏通脑络协定处方”(含地龙、僵蚕、生地黄等通养络脉之品);考虑到“母病及子”,即脾络壅塞更易致肺络阻滞,对糖尿病患者,多考虑用有通脾络、益津气之效的津力达[11]。
因“久病入络”理论更为现代医者熟知,所以对新冠肺炎重、危期施以“通络开闭”治疗,较之对初、中期“初病即入肺络”的“通调络阻”治疗确实更系统。但需注意,新冠肺炎属感湿疠秽浊所致,证候表现有变化难测及隐匿的特点,又有“初病即入肺络”病机基础,易导致“久病入络”时病情更危重。所以对“久病”之“久”需灵活看待,要适当提前应用“通络开闭”之法以期“截断扭转”,不可拘泥于一般疾病的辨治要点俱全而处置,以尽量阻止现代影像检查所见的肺泡被黏液充斥而肺功能衰竭的“大白肺”阶段的到来。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新冠肺炎初、中期多表现舌苔厚腻反而干咳的特殊征象及现代医学对该病的认识,结合吴又可疠气学说,认为该病为感“湿疫秽浊”所致,病机传变上有发病即为较重之症、传变不循常理的特点;结合叶、薛、吴、王温病四大家之络病学术思想的梳理,认为该病具有“初病即入肺络”而“久病”之证更趋危重的特点。由此提出“治络”之法应贯穿该病全程而时时不忘“截断扭转”,即“治络不厌早”:一者,初病即应注重涤除肺络之痰湿秽浊,为此要研讨更精致、准确的治法、处方;二者,对危重期应注重开通肺络之痰湿秽浊瘀闭以救危亡,且应在时限上适当提前而不可拘泥。当然,基于“湿性戾气”隐匿、缠绵、在络中固结难去,以及现代医学认识到的病原体检测再次转阳的特点,对恢复期病人,给予继续通养络脉治疗以防治病情反复及后遗症发生,亦是治疗关键。对此,暂不展开讨论。
最后要说明,中医各家学说、不同辨治方法之间本来就存在广泛交叠;外感热病诊疗中的六经辨治、膜原辨治、卫气营血辨治等方法之间具有广泛的交叉性;络病角度辨治方法本身就已隐含在业已形成共识的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方案之中,成为其取得良好疗效的基础环节之一。本文旨在论证和说明,在此基础上,基于感受“湿性戾气”导致“初病即入肺络”的病因病机特点而推进对络病辨治方法的显化、系统化应用,是深化对新冠肺炎之因机证治的认识进而继续提高临床疗效的重要方面。
——兼与《论流行性感冒与伤寒、温病的关系》一文作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