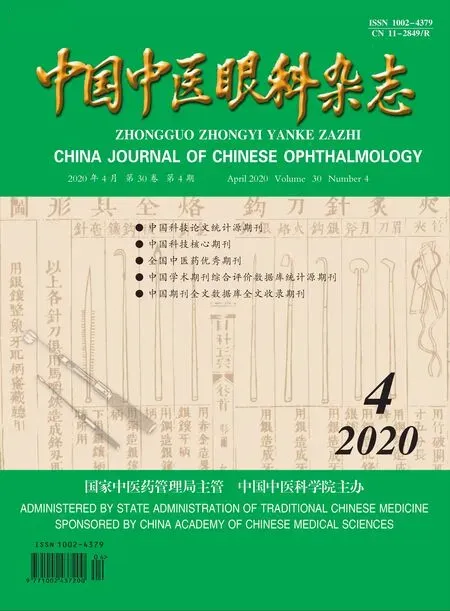中医治疗近视疗效评价指标运用现状
罗晓燕,刘光辉,徐朝阳
近年来,中国近视患病率逐年攀升,且有低龄化、高度数的发展趋势,近视已成为影响国人眼部健康的主要问题之一。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八个部门于近日颁布实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将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上升为国家战略[1]。防治近视,刻不容缓。
中医治疗近视历史悠久,治法繁多,临床亦有较多运用中医疗法有效治疗近视的报道,包括中药内服、中药熏蒸、中药贴敷、针刺、耳穴贴压、揿针、穴位按摩、中药离子导入等多种方法,可有效延缓近视发展、控制眼轴增长、改善调节痉挛及眼底血流[2-9]。但现临床中多单纯运用屈光度、视力等参数评价中医治疗效果,且因所选治疗近视疗效观察指标及疗效评价标准不同,其“有效”所指确切疗效不尽相同。因此,本文拟通过整理分析近10 年临床运用中医疗法治疗近视36 篇[2-37]文献中所选观测指标及疗效评价标准,探析中医治疗近视较为合适的观察指标及疗效评价标准。
1 观察指标
1.1 视力
所选36 篇文献中有34 篇选用视力作为观察指标,其中观察指标为“最佳矫正视力”2 篇,“裸眼视力”21 篇,“最佳矫正视力及裸眼视力”3 篇,未明确说明具体类型,仅表述为“视力”8 篇。视力下降为近视患者最早,也是最主要的症状,且视力为中医“视物模糊”症状的具体量化体现,无论何种治疗方式,视力均应作为近视治疗常规观察指标。临床治疗近视所选研究对象多为单纯性近视患者,已除外病理性近视、合并其他眼部疾病,最佳矫正视力一般可达1.0,故而所选观察指标以裸眼视力为主,最佳矫正视力为辅。若为病理性近视,则应以最佳矫正视力为主,必要时可以近视力为观察指标。
1.2 屈光度
所选36 篇文献中有27 篇选用屈光度作为观察指标,其中21 篇明确说明为散瞳后屈光度,即需经睫状肌麻痹后验光。现临床研究中所采用的近视诊断标准多依据屈光度分类,即轻度近视≤-3.00 D、中度近视-3.25~-6.00 D、高度近视>-6.00 D;部分研究者采用等效球镜进行近视诊断及程度分类,亦是依据屈光度进一步计算所得。研究表明,睫状肌麻痹前后屈光度差值可在1.50~7.50 D 区间波动,年龄越小,其差值波动越大。睫状肌麻痹前屈光状态更偏近视化,睫状肌麻痹后更接近真实的屈光状态[38]。近视的诊断、程度及疗效评估均需依据屈光度,因此,屈光度应作为治疗近视的基础观察指标,以睫状肌麻痹验光结果为依据,以等效球镜为评判标准。
1.3 眼轴长度
大量临床研究已表明,眼轴长度与近视屈光度成正比。一般认为,眼轴每增加1 mm,屈光度约增加-2.50~-3.00 D。眼轴长度为近视,尤其是轴性近视发展的基本评价指标之一。但所选36 篇文献中,仅4 篇选用眼轴作为观察指标,且并未作为主要观察指标,可能为观察期较短,眼轴长度变化不明显,不适合作为近视治疗的短期观察指标。临床研究表明,随着眼轴长度和等效球镜的增加,视觉损伤的患病率增加[39];同时,眼轴长度与近视弧、脉络膜萎缩弧面积、视网膜厚度、神经纤维厚度、脉络膜厚度等均具有相关性[40],除了可评定近视的进展,对于监测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眼轴长度虽无法评价近视治疗的短期疗效,但仍应当作为近视治疗的基本观察指标之一。
1.4 中医证候
所选文献均为运用中医疗法治疗近视的临床研究,但仅8 篇具体将中医证候作为观察指标,主要原因一是近视患者除视物模糊外,多未诉其他明显不适症状;二是近视的诊断及进展评估主要依靠视力、屈光度;三是当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近视中医证候量表,造成了临床运用中医治疗过程中“忽视症状”“无证可辨”“一方通治”等现象。
目前临床研究者多自制中医证候量化表、评分表等,主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 (GB/T16751.2-1997)、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ZY/T001-94)、邓铁涛主编《中医证候规范》、冷方南主编的《中医证候辨治轨范》等,包括了近视患者常见的中医全身证候及眼部局部证候。吴宁玲等[6]纳入气血两虚或肝肾亏虚型高度近视患者,所制《中医证候评分量表》症候包括“目涩少泪、体倦乏力、失眠健忘、腰膝酸软、口燥咽干、抑郁”,依据症候无、轻度、中度、重度,分别为0、1、2、3 分。石梅琴[12]自拟近视《眼局部症状量化表》症状包括“视物不持久、干涩、异物感、眼球酸胀、畏光流泪”,根据“阅读超过1 h 出现、阅读超过30 min 出现、阅读即出现或不阅读也出现”分别评为“轻(1分)、中(2 分)、重(3 分)”。运用中医疗法治疗近视,除了现代医学的检查参数,中医证候的改善亦应作为为最基本的观察指标,更符合评估中医的治疗效果。而此类量化表、评分表,将中医证候量化为具体可评测的数值,从而使中医疗效的评定数据化,具有可行性与简化性,可广泛运用于临床。但眼科专科的量化表、评分表多为研究者自制,在拟定过程中当注意充分结合近视的中医眼部及全身症状特点,才可使评定结果具有准确性与可靠性。
1.5 其他参数
36 篇文献中有4 篇选用除视力、屈光度外的主要观察指标,其中1 篇治疗对象为低度近视患者,主要观察指标为调节功能;3 篇为高度近视的中医治疗,观察指标2 篇选用视野,1 篇选用眼底血流参数。既往研究认为,调节功能为近距离工作与近视之间的关键联动环节[41],改善调节功能可能在延缓近视发展过程中起积极作用。因此,向圣锦[20]通过测定低度近视患者治疗前后调节功能变化情况,以评估治疗效果。高度近视患者视力、屈光度趋向稳定,中短期治疗变化较小,且前期研究已表明随着近视的发展,屈光度、眼轴增加,眼底视网膜、脉络膜血流减缓,部分患者光敏度下降、出现视野缺损。王翠芳[2]、莫亚等[35]选用视野平均光敏度值评估运用中医疗法治疗高度近视后视功能改善情况;吴宁玲[6]则通过对比治疗前后高度近视患者的视网膜中央动脉的血流参数,包括收缩期血流峰值速度、舒张末期血流速度、阻力指数,间接评估治疗效果。此外,研究[42-43]表明,近视屈光度、眼轴长度与视野,脉络膜、视网膜厚度,眼电生理等具有相关性。因此,对于单纯性近视,尤其是调节性近视,可在视力、屈光度的基础上,监测其调节功能;若为高度近视,则可通过监测视野、血流参数、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angiography,OCTA)等以监测组织学变化情况,评估其进展。
2 疗效评价标准
2.1 屈光度+裸眼视力
所选36 篇文献中18 篇选用“屈光度+裸眼视力”的综合评定为疗效评价标准,具体所选用标准不尽相同,但皆为通过评估视力及屈光度改善情况从而评价疗效。吕东[30]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选用评价标准为,“治愈:视力恢复正常,近视屈光度消失;好转:视力提高2 排以上,近视屈光度降低1.00 D;未愈:视力提高小于2 排,屈光度如故”。石梅琴[12]则结合《中华眼科学》拟定近视进展的评价标准,“临床症状加重,远视力降低≥1 行,或散瞳后检影验光近视屈光度明显增加(增加度数≥-0.75 D)”。
19 篇出现“治愈”或“痊愈”的治疗结果,其中1 篇疗效评价依据为“中医症状结合视力”、6 篇为“裸眼视力”、12 篇为“屈光度结合裸眼视力”(其中明确说明为散瞳后屈光度7篇)。临床中虽通过各种治疗手段可使近视患者裸眼视力提高、中医症状改善,但真性近视,尤其是轴性近视,由于眼轴的增长是不可逆的,故除外角膜塑形镜及屈光手术、后巩膜加固术等手术外,屈光度回退、甚至消失有待商榷。究其原因,可能为部分研究未经散瞳麻痹睫状肌验光,所选研究对象为假性近视或混合性近视。临床疗效评价选用屈光度的发展速度更为合理。
2.2 视力
9 篇文献以治疗前后“裸眼视力”为依据进行疗效评价。周珊[29]选用疗效评价标准为,“痊愈:裸眼视力达到1.0 或以上者;显效:裸眼视力提高3 行或3 行以上,但未达到1.0 者;有效:裸眼视力提高1~2 行者;无效:视力提高不到1 行或无增高者”。仅1 篇选“矫正视力”为疗效评价依据,该研究之研究对象为痉挛性近视,且同时分析了治疗前后屈光度、眼轴的变化情况,并非仅以矫正视力作为单一的疗效评价标准。若是初诊最佳矫正视力正常的患者,当以裸眼视力为主要观察评价指标;若是初诊最佳矫正视力差的患者,则可监测最佳矫正视力,同时应注意区别框架眼镜及角膜接触镜之最佳矫正视力。
2.3 中医疗效评价
7 篇文献依据其自拟症状分级表或证候评分表,通过对比前后分级或评分变化情况进行疗效评价。但“证”是对疾病所处一定阶段的病因、病位、病性,正邪关系及病势所作的高度概括,具有阶段性;近视为慢性疾病,运用某一“证”的证候量表作为长期疗效评价欠合理,证候积分量表更适用于中短期疗效评价;若是长期疗效评价,可选用症状分级量表。近年来,“中医状态辨识”理论已逐渐完善,不仅可将中医症状与西医检查结果结合,也包涵了先后天、社会自然环境等因素,有效地将分散的、模糊的机体健康信息转化为较为系统的、客观的状态数据,将中医疗效评定可观化、可测化,同时具有实时性、动态性[44]。近视为长期疾病,发生发展与遗传、环境、发育、体质等关系极为密切[45-46],可运用“中医状态辨识”长期监测并评价中医治近视效果,但其尚未形成完整的眼科专科辨识理论体系,仍待临床研究者进一步探究。
3 小结
现临床中运用中医疗法治疗近视的疗效评价主要依据视力、屈光度、眼轴长度、视野、调节功能等眼科专科检查结果,运用中医证候积分量表或症状分级表等中医疗效评价模式者较少。两种疗效评价模式各有欠缺:一是运用视力、屈光度等现代辅助检查结果虽然可直接反应治疗效果,但并不能具体反应中医证候、病机的疗效;二是证候量表多选用典型症状,部分结合全身症状,而近视患者除“视物模糊”外,临床症状常不典型;且“证”具有阶段性,近视为慢性疾病,运用某一“证”的证候量表作为长期疗效评价欠合理。
当前中医治疗近视的方法多样,对于治疗效果评价缺乏统一的标准,且客观性较差,使中医治疗近视的认可度不高。运用中医疗法治疗近视当中西结合综合评定,西医当以视力、等效球镜、眼轴长度为基础观察指标,具体根据所研究对象选择视力类别,根据研究期限、近视的具体类型选择相关参数;中医方面,可根据研究设计、观察期限选择相应的症状分级表或证候积分量表。“中医状态辨识”可长期、动态观察并评价近视的发展,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眼科专科辨识体系,其具体参数仍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