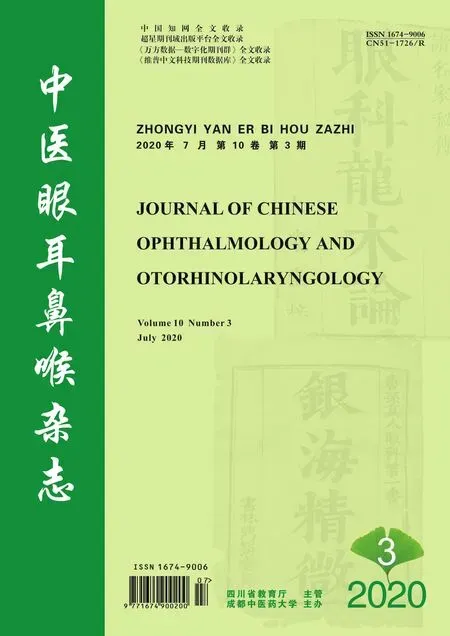扶正祛邪结合情志疏解法治疗鼻鼽经验
李玲娟 张勤修
鼻鼽是鼻科常见难治疾病,多因脏腑虚损、卫表不固所致。典型临床表现为鼻塞、流涕、鼻痒、喷嚏,西医变应性鼻炎、血管运动性鼻炎等均属本病范畴。其发病率高,症状反复发作,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张勤修教授从事中医耳鼻喉科工作多年,临床治疗有着丰富的经验,现将其治疗鼻鼽的经验介绍如下。
1 病因病机
中医学认为本病发生内有脏腑虚损,外有邪气入侵,因正气不足,腠理疏松,卫外功能不固,风寒等邪趁虚入侵。一方面加重脏腑虚损,正气亏虚,鼻失所养;另一方面气血津液运行失调,与邪气搏结,聚于鼻窍,故发而为病。如《诸病源候论》中曰:“肺气通于鼻,其脏有冷,冷随气入乘于鼻,故使津涕不能自收。”又如《景岳全书》言“凡由风寒而鼻塞者,以寒闭腠理,则经络壅塞而多鼽嚏。”[1]张教授指出脏腑虚损为发病之本,邪气入侵为其标,但同时强调情志在鼻鼽发病中的影响。因平素情绪急躁易怒,肝气郁结,气机逆乱,一方面可加重他脏虚损,鼻失所养;另一方面,津液运化失调,聚津为湿,与外邪相合,循经上犯而为病。根据张教授的临证经验,其认为鼻鼽的发生是三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可择一而论。
2 临证治疗
2.1 扶正为主
张勤修教授认为:人之所健,首在正气存内。正气内存,虽世间虚邪长存,邪不可干,唯两虚相逢则病。如《素问》言:“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2]。认为正虚不足是鼻鼽发生的主要原因,而其中又以肺脾肾三脏虚损为主,即肺气虚寒,脾气虚弱,肾阳不足。在治疗时注重辩证论治,不可一概论之。
2.2 补肺扶正
《灵枢》中曰:“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少气”[3],说明肺的生理病理与鼻病的发生联系紧密。肺的生理功能有通调水道和宣发肃降两方面,若肺气虚损,则肺的通调水道和宣发肃降功能失常,无以上输津液,外布卫气,则鼻失濡养,津液停聚为湿。肺虚卫外不固,风寒外邪趁虚而入,搏结于鼻窍,故而发为鼻鼽。表现在鼻鼽症状基础上出现肺气亏虚的临床特征,如畏风,短气不欲言,咳嗽痰稀,舌淡苔白,脉弱等,查见双下鼻甲肿胀,鼻粘膜淡白,或可见鼻腔水样分泌物。治以补肺益气通窍,选方参苓白术散加减。
2.3 健脾扶正
《内科摘要》曰“恶风寒,鼻流清涕,寒禁嚏喷。余日:此脾肺虚不能实腠理”[4],说明脾对鼻病的发生有重要影响。脾的生理功能表现为运化水谷水湿和升清降浊,脾的功能正常则气血生化有源,清升浊降,鼻得濡养,功能正常。若脾虚不足,则气血生化无源,清不升浊不降,水湿无以运化,鼻失濡养,水湿之邪聚于鼻窍而发为鼻鼽。表现为在鼻鼽的症状基础上伴见脾虚失运的临床特征,如面黄消瘦,倦怠无力,纳差腹胀,便溏,舌淡胖,或有齿痕,苔白腻,脉弱等。治以健脾益气,祛湿通窍,选方参苓白术散或补中益气汤加减。
2.4 温肾扶正
《医学入门》中讲到:“凡鼻涕、鼻渊、鼽久甚不愈者,非心血少则肾水少……”[5]。肾藏精,为一身之阴阳,肾的功能正常,则肾精充沛,精气上注,鼻窍得养,肾阳旺盛,卫表得以温煦。若肾阳虚衰,温煦失职,风寒外邪入侵,气化失职,寒水上犯,与外邪搏结发为鼻鼽。表现为在鼻鼽的症状基础上出现肾阳虚衰的特点,如面色苍白,腰膝酸软,形寒肢冷,小便清长,舌淡苔白,脉沉等。治以温肾益气通窍为主。常加用小剂量附子(20克以下),肉桂,淫羊藿,巴戟天等益火之源。
2.5 驱邪为辅
《济生良方》言:“风寒乘之,阳经不利,则为壅塞,或为清涕”[4],说明外邪是鼻鼽发生的重要外因。临床上多数病人因受凉而发病,表现为在鼻鼽症状的基础上伴有鼻塞,流涕,咳嗽,咽痛,头痛,畏寒等不适。治疗时多辅以散寒驱邪。若以正虚为主者,多在参苓白术散或补中益气汤的基础上加用麻黄,桂枝,藿香,石菖蒲,辛夷等。若正气亏虚不显者,则用川芎茶调散加减治疗。
2.6 调畅情志贯穿始终
《素问·举痛论》曰:“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6],说明情志失调与疾病的发生尤为密切。张勤修教授认为天有大周天,人有小周天,天人合一,万物有情,百病之中,情志为先。临床上多数鼻鼽患者表现有情志的异常,或因情志异常而发病,或因病而扰出现情志异常的症状。主要为在鼻鼽症状基础上出现焦虑、抑郁情绪,如对疾病症状过度关注,对病情程度过度评估,对疾病愈合过于悲观等。这些心理因素常会加重患者的病情,而鼻鼽症状长期不得缓解,又会加重情志的异常。故张勤修教授认为,治病万般之法,也不离调畅情志。治疗时常结合理气解郁之法,加用柴胡,郁金,百合,路路通,皂角刺等疏肝之品,同时加强心理疏导,或采用行为疗法,疏解患者心情。
3 典型案例
患者:张某,女,52岁,2019年09月26日初诊。主诉:鼻塞、喷嚏4天。患者诉每到换季时出现鼻痒,喷嚏,已持续多年。4天前因气温骤降而出现鼻塞,流清涕,连续喷嚏等症状,检查见鼻腔粘膜色淡白,下鼻甲水肿,鼻道可见水样分泌物。现除鼻部症状外,伴有倦怠乏力,面色萎黄,头晕困重,纳差,眠差,便溏,舌淡胖,边有齿痕,苔白腻,脉弱。患者就诊过程中,反复讲诉病情,诉曾多次就医而无效,反复询问医生自己所患何病,有无有效治疗方法。中医诊断:鼻鼽(脾虚湿盛证)。治以健脾益气,散寒祛湿。选方参苓白术散加减,具体用药如下:党参15g,黄芪15g,白术20g,白扁豆10g,陈皮15g,莲子10g,山药15g,石菖蒲15g,砂仁10g,茯苓20g,薏仁15g,桔梗10g ,辛夷15g,麻黄10g,藿香10g,柴胡15g,郁金15g,百合10g,炙甘草10g。6剂,每日1剂,3次/日,煎服。同时嘱患者多做事,心情放松,减少对鼻部症状的关注。
2019年10月10日二诊。患者鼻塞,流涕,喷嚏症状较前缓解,检查见双下鼻甲仍肿胀,鼻甲粘膜淡白,鼻道可见少量水样分泌物。头晕困重及倦怠乏力较前缓解,但仍见面色萎黄,纳差,便溏,舌淡胖,边有齿痕,脉弱。上方去麻黄、藿香、桔梗,加建曲10g,山楂10g,6剂。2019年10月17日三诊。患者心情愉悦,鼻部症状较前明显缓解,头晕困重及倦怠乏力较前进一步减轻,食欲较前改善,面色较前有光泽,舌淡胖,腻苔较前变薄,脉弱。前方6剂继续巩固。
4 按语
本例患者因忧思多劳而致脾气亏虚,脾虚失于健运,故纳差;无以运化水谷,气血生化无源,清窍失养,故见倦怠乏力,面色萎黄;脾虚无以运化水湿,则见便溏;脾虚卫外不固,风寒之邪入侵,与水湿搏结于鼻窍,则见鼻塞,清涕,喷嚏等不适。病机在脾气亏虚,水湿内盛,故治疗以健脾益气,散寒祛湿为核心。初诊时选方参苓白术散加减,方中党参,黄芪,茯苓,白术,山药,白扁豆,薏仁等健脾益气,陈皮行气健脾而除湿,莲子补脾而止泻,砂仁醒脾而燥湿,桔梗宣肺载药上行,石菖蒲醒神化湿益智,炙甘草益气而调和诸药。患者因受凉而发病,外邪尚在,故加用麻黄、藿香散寒驱邪,辛夷宣通鼻窍。患者就诊过程中反复讲诉病情,为肝气郁滞之征,故加用柴胡、郁金、百合、路路通疏肝理气解郁。嘱患者多做事,心情放松,减少对鼻部症状的关注,亦为调畅情志之意。
二诊时患者鼻塞,流涕,喷嚏,头晕困重及倦怠乏力较前缓解,但仍见面色萎黄,纳差,便溏等。说明选方用药得当,治疗有效,但此时患者外邪已清,脾虚及情志异常仍在,故在前方基础上去麻黄、藿香、桔梗,加建曲、山楂以消食健运。三诊时患者心情愉悦,鼻部症状较前明显缓解,食欲较前改善,面色较前有光泽,说明脾气得以健运,气血生化有源;头晕困重及倦怠乏力较前进一步减轻,腻苔较前变薄,说明水湿之邪得除。但结合患者舌脉,脾虚之征尚未完全消除,故继续前方巩固。
5 总结
张勤修教授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唯两虚相逢则病。故治疗之法,总在培植正气为主,正气得当,虚邪自除。但百病之中,情志为先,情志异常是疾病诱发和加重的重要因素,故在鼻鼽的治疗过程中强调辨证审因结合情志舒解法,即扶正为主,驱邪为辅,情志调畅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