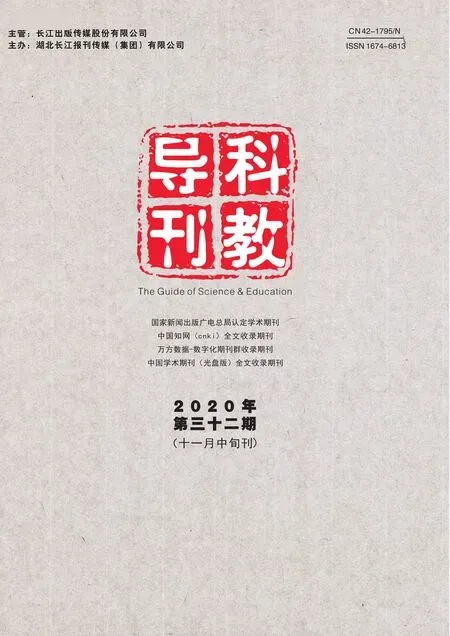试析史书中的游侠形象
——以《史记》《汉书》游侠列传为例
陶嘉伟
(大连大学历史学院 辽宁·大连 116622)
1 混淆的原因
“侠的存在是中国社会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浓厚的文化意蕴。但侠却是一个人们似乎都理解又很难定义的文化名词,而现代人在侠文化研究中的一大误区便是将侠的文学积淀、观念形态混同于侠的历史文化本体。”[1]文学对于人们认识的塑造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而另一重要的原因是史料上的缺乏。《史记》中便说明了这一点:“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而关于侠的记载最早出自韩非《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韩非对游侠的行为进行了总的概括,但并没有对具体行为以及人物进行描写,这使得游侠形象十分的模糊。直到《史记》,《汉书》游侠列传才存在较为详细的记载,但除这两本史学著作之外,后代史书便不再为游侠单独列传。这样的状况极大地影响了对游侠形象的具体认识,在陈夫龙《侠的起源诸学说批判》中提出“侠作为历史的真实存在已经烟消云散,隐退于历史的深处,即如论者所言,侠的本源已经‘丧失’了。因此,作为研究者是不可能确定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侠是什么样子的,也无法确定历史文献上侠的真实面目……”对于侠的起源研究“或多或少都要打上时代的功利要求和主观色彩的印记。”[2]因此,基于上述情况,回归游侠记载较为具体的《史记》,《汉书》总结游侠形像是十分有意义的。
2 《史记》中的游侠特征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游侠却有这样的概括:“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从这段总结出侠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所作所为违背当时的统治秩序,二是存在特殊的行事风格。而他主要记载了朱家,剧孟,郭解三人。
韩云波认为《史记》对游侠的记载存在相当的片面性,带有较重的主观色彩,“即使写现实社会中的侠,司马迁仍与社会的真实存在之间有一定距离,带有相当的理想化因素。《太史公自序》:‘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他只承认‘仁’,‘义’之侠,这就把‘暴豪之徒’和‘盗肠居民间者’排除在外;但他又不能忽视社会上一般人对侠的普遍认识,这就造成他不可摆脱的内在矛盾。”[3]不可否认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述确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在内,英国学者E·H·卡尔曾经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提到“像其他单个的人一样,历史学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他不仅是其所属社会的产物,而且也是那个社会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代言人:他就是以这种身份来接触过去历史的事实。”[4]因此在历史记述中必然包含作者的主观因素,例如将朱家藏匿逃犯叙述成“藏活豪士”,然而从他对游侠的评价以及之后的记载可以看出司马迁并不完全否定游侠是“犯罪分子”,并且司马迁还披露了不少关于游侠作奸犯科的行为,例如郭解“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表现出一定的客观性,在末尾也提到了“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
他对游侠的赞扬,从积极的一面展示了游侠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例如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甚至在国家内乱时,游侠也有相当重要的作为,例如史记中提到的剧孟,在吴楚七国之乱中为周亚夫所看重。“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总之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实际上使游侠这一社会角色更加立体化,而不是在《五蠹》中单纯的反面角色。但仍需说明的是他对游侠的赞扬是以游侠特殊的行事风格为内容的,而不是法律道德上的正义,这种特殊的行事风格除了体现在人物的叙述之中,还体现在游侠列传的叙述方式之上,“司马迁在书写《游侠列传》时,笔墨出入于儒和侠之间,并且儒侠相提时常常‘比权量力’,斟酌下语。”[5]从而跳脱出“拘学”,“咫尺之义”。“司马迁通过为布衣立传及对布衣之义的阐扬,把游侠、刺客、儒者从精神品格上统一起来,试图从中发掘一种民族共同追求的理想人格。”[6]而他们这种特殊的行事风格同时也使他们受到了广大群众,乃至豪强,官员的关注,有大量的少年,豪杰围绕在这些人的周围,例如郭解被迫迁徙至茂陵时,卫青曾为其向汉武帝求情。
综上所述,《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记述的游侠包含以下两种特征,一是所作所为违背当时的统治秩序,二是存在特殊的行事风格。
3 《汉书》中的游侠特征
《汉书》中所记载的游侠前半部分与《史记》游侠列传中主要记载的人物基本相同,另外增加了萭章,楼护,陈遵,原涉等人。《汉书·游侠传》开头叙述了班固对于游侠的看法,“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可以明显地看出班固部分继承了司马迁赞扬游侠的观点,但更多地是对韩非观点的继承发展,“一是强调侠‘作威作惠’的社会活动,二是强调背公死党’的政治倾向。”[7]
袁梅认为,班固较于司马迁有三点进步,一是“对游侠认识的全面性和客观性”,二是“从儒家思想视角看游侠”,三是“班固对游侠、儒士的思考”。[8]但实际上是由于时代的变化,记述时观点不同,以及个人经历的不同,导致了内容上的差异。例如虽然在他的笔下游侠出现了新的特征,游侠开始一定程度与统治阶级合作,例如萭章“与中书令石显相善,亦得显权力,门车常接毂。”又如他笔下的游侠大多接受过统治阶级的封官或成为其幕僚,萭章“为京兆尹门下督,从至殿中,侍中诸侯贵人争欲揖章,莫与京兆尹言者。”楼护:“后护复以荐为广汉太守。”陈遵:“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长子,宣帝微时与有故,相随博弈,数负进。及宣帝即位,用遂,稍迁至太原太守”原涉:“礼毕,扶风谒请为议曹,衣冠慕之辐辏。为大司徒史丹举能治剧,为谷口令,时年二十余。”但实际上类似的行为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就存在的趋势,如条候得剧孟,另外《史记·游侠列传》在前半部分也提到了作为统治阶级一份子,卿相之侠的代表战国四公子,之所以会出现《汉书》所记述的现象与班固记述的时代变化有关,由于统治者对游侠群体的打击,压缩了游侠的生存空间,使得其更需要与统治阶层合作,而所谓儒家思想视角在《史记》中同样也有体现,上文已述,但班固的思想更多体现出儒家的新发展,即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司马迁的个人经历也使得《史记》与《汉书》在记述思想上的不同,他身陷囹圄,又惨受宫刑,使得他深刻地感受到了封建统治的残酷之处,因此将游侠视为打破森严的封建统治的异质力量。[9]而班固出生儒学世家,很早就受受儒家思想影响,而他的人生在因窦宪受株连之前,相对平稳。因此以儒家以及统治阶层视角记述游侠是可以理解的。
由上述可得,《史记》与《汉书》在游侠记述上的不同点可总结为三点,一是对游侠另一面的进一步揭示,二是以正统思想看游侠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三是从时代角度看游侠的兴起,但在游侠特征上其实主要体现的还是《史记》中所表达的,只是趋势与表现的程度不同,《史记》中游侠与上层社会的互动在《汉书》中表现的更多,在违背当时的统治秩序方面,从《史记》所记的“不轨于正义”延伸为“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更为细致也更能体现统治阶层对游侠的看法。在特殊的行事风格方面,《汉书》更为多元,例如陈遵所体现出的潇洒。
4 总结
从司马迁《史记》对游侠的,概述,赞扬,写作方法可以总结出游侠具有两种特征,即所作所为违背当时的统治秩序以及存在特殊的行事风格,之后《汉书》中的记载实际是在《史记》之上,对游侠形象进一步揭示。从两部著作的游侠特征中可以看到,游侠对社会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影响,游侠的个人品质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甚至个人事迹存在着一定瑕疵,但在大多数社会环境下,他们特殊的行事风格,实际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正面作用,甚至成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游侠形象,即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游离于社会的特殊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