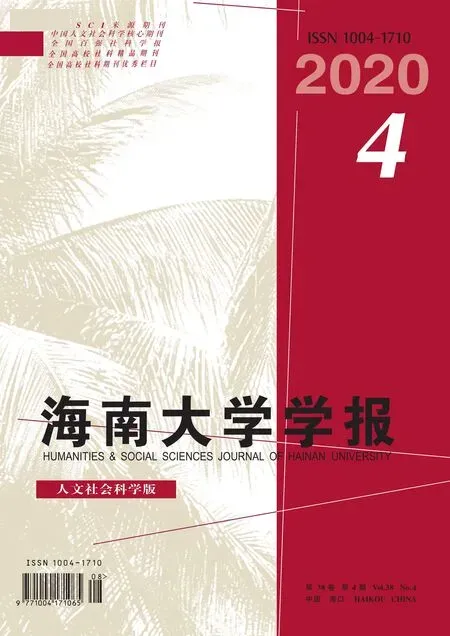韶音令辞:先唐音辞艺术发展探论
王允亮,郑瑞娟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
《世说新语·品藻》有这么一段记载:
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时苟子年十三,倚床边听。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①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83页。
此处的刘尹为刘惔,字真长,东晋人,因为他曾任当时的丹阳尹一职,所以《世说》中多称其为刘尹。王长史为王濛,为刘惔同时人,他曾任司徒左长史一职,故被称为王长史。王苟子为王修,乃王濛之子。刘惔和王濛是东晋清谈之执牛耳者,《世说新语·文学》第五十六载: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己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②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62-263页。
由此可见,刘惔的清谈水平之高,得到时人的公认,而王濛和刘惔的清谈水平则在伯仲之间,《晋书·外戚传》言当时“凡称风流者,举濛、惔为宗焉”③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19页。。由王濛与其子的对话可知,王、刘二者虽同为清谈之宗,风格上却有区别。刘擅长逻辑理论的推演剖析,故能所向披靡,折服对手。王则注重韶音令辞,故以风流文辩映照一时。这也说明,魏晋清谈除了内容上覃精研思,钩深致远之外,作为一种现场式、即兴式的文娱活动,对外在的形式也有讲究,语音的抑扬吞吐,词语的斟酌拣选,同样是清谈的一个重要方面。学界对于玄学清谈的理论内容探讨已多,如言意之辨、养生论、声无哀乐、才性四本等,皆是为人所熟知的清谈议题,但对于其形式的讲究,却注意不多④龚斌《世说新语校释》前言部分曾对此有所论及,惜尚未进行深入探讨,见龚斌《世说新语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4页。唐翼明《魏晋清谈》一书在论述清谈之形式美时,亦注意到清谈过程中对于音辞的追求,提出清谈贵“辞条丰蔚”、“花烂映发”及语音节奏之美,但该书对此仅约略提及,且所言有不够周密处,详细辨析见下文。唐氏观点见其著《魏晋清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58页。。而玄学清谈在传统音辞艺术发展史上,则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故本文拟以魏晋清谈的音辞之辨为切入点,从音制技巧发展的角度,来看唐前传统言说艺术的发展。以此求教于学界诸方家。
一、德先于言:先秦两汉的言说观念
上古时期的文学作品,多有口头文学的记载,如《尚书》中的《甘誓》《秦誓》等,均为公开演说的记录,虽然其间不免经过文字润饰,但也反映出演说者已经有了相当高的言语水平。春秋时期,由于邦国外交的需要,对于言说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出使晋国,因为对方招待不周,就把客馆的围墙拆了,在晋人问罪时,子产通过义正言辞的言说为自己辩解,使得晋人无可奈何。事后,叔向评论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375页。《左传》记载有非常多的外交辞令,如吕相绝秦、烛之武退秦师等,这些辞令显示了非常高的言说水平,因而受到世人的关注被载入史册。《国语》一书因所记多为春秋时期历史,故有“《春秋》外传”之称,由其书名中所含之“语”字,可觇知它以记录人物语辞为主要内容,此书的出现正是春秋时期言说水平高涨的反映。
春秋后期,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对言说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公元前548年,郑国击败邻国陈国,但在向中原霸主晋国献捷时,却受到晋国的责难,认为他们毫无理由侵略小国,陪同郑国国君出使的子产,为郑国行为的正当性进行了有力的辩护,最后使得晋国的主政大臣赵文子无话可说,只能说:“其辞顺,犯顺不祥”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311页。。由此化解了郑国的一场危机。对于子产这番言辞的作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有孔子的评论:
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③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311页。
这段评论体现出孔子对文辞的重视。不仅如此,在《论语·子路》中孔子也有类似观念的表露:“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5446页。对于外交场合的辞令言说,体现出特别的关注。孔子曾根据弟子的特长将他们分为四类,即后来所称的孔门四科,其中专门列有“言语”一门,且仅次于“德行”而居第二,具有极高的地位,这也体现出孔子对言语的重视。
虽然孔子对言语技巧有着正面的肯定,但与此同时,孔子对言说的认可也有一定程度的保留,他曾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5453页。(《论语·宪问》)可见在言和德之间,孔子明显更注重德行。又言:“巧言令色,鲜矣仁”。⑥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5336页。(《论语·学而》)对于巧言令色之人,孔子判定他们缺少仁爱的特质。又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⑦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5487页。(《论语·阳货》)把巧舌利口和郑声、紫色等败坏社会秩序的元素等量齐观。在这些话语中,体现出他对言论文辞的矛盾态度:虽然孔子认可高超的言说水平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相对来说,他更重视言语承载的内容,如果仅仅是形式上的美观悦耳,他反而会比较排斥。
不独孔子如此,当时另一学派的道家学者,对言说也持否定态度,如《庄子·外物》: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⑧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28页。
又《庄子·大宗师》:
子祀子舆子犂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①郭庆藩:《庄子集释》,第235页。
从这些片段可以看出,《庄子》更注重对言语所传内容的心领神会,对于外在的语言形式则不甚在意。除了《庄子》外,道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老子更强调内敛隐忍,从其“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②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1-192页的主张可以看出,他对于谈说更为轻视。
战国末期,人们的言说水平有了非常大的进展,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名家一派的出现。名家注重对概念、逻辑的辨析推演,是中国学术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支,虽然这一学派在后世失传了,但在当时的其他学派著作中屡有记载。名家之外,战国策士纵横往来,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也代表了言说发展的新水平。
鬼谷子曾言及游说之方:
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辩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辩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如此而说不行者,天下未尝闻也。此之谓善说。③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6页。
《荀子·非相》也说:
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欣驩芬芗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④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6页。
这里所抉发的言说技巧,实际上是当日诸子百家,在辩说实践中所积累经验的精要总结,体现出战国末年言说水平的进展。
但在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典籍书写中,名家、纵横家及其他一些善于谈说的人,往往是被批判和抨击的对象,《荀子·儒效》说:“乃始率其群徒,辩其谈话,明其辟称,老身长子,不知恶也”。⑤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24页。《荀子·非相》言:“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⑥王先谦:《荀子集解》,第88页。《荀子·非十二子》又说:“假今之世,饰邪说,交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在者有人矣”。⑦王先谦:《荀子集解》,第89-90页。《荀子》之外,《庄子·天下篇》也有对惠施、公孙龙等为代表的名家学派的批判。总得来看,先秦人更为重视言说所传达的内容,对于言说本身则保持谨慎的认可。
西汉时也有一些人善于言说,《汉书·游侠传》载楼护:“为人短小精辩,论议常依名节,听之者皆竦。与谷永俱为五侯上客,长安号曰:‘谷子云笔札,楼君卿唇舌。’”⑧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707页。《汉书·匡衡传》载:“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庸作以供资用,尤精力过绝人。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语《诗》,解人颐。’”⑨班固:《汉书》,第3331页。刘向《说苑》一书,记载了很多古人的嘉言懿行,中有《善说》一篇,特别强调:“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而说不可不善”。⑩向宗鲁:《说苑校证》,第266页。体现出他对言说的重视。
东汉以来,由于经学辩说的需要,也出现了一些较为著名的人物,如《后汉书·逸民列传》载井丹“通五经,善谈论,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大春’”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64页。,《太平御览》卷六百一十五载戴冯,“正旦朝贺,帝令群臣说经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冯重五十席。京师谚曰‘解经不穷戴侍中’”,丁鸿“少好《尚书》,十六能论难。永平中引见,说《文侯》一篇,赐衣被。章帝会诸儒白虎观,上善鸿难说,号之曰‘殿中无双丁孝公’”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65页。等。对先秦流传下来的言说文献,汉人持有一分为二的态度,《汉书·艺文志》对名家和纵横家如此评价: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鈲鋠析乱而已。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①班固:《汉书》,第1737页。
《汉志》原本于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及《七略》,故对于九流十家的剖判,不仅是班固的个人观点。对以言论谈说为主要特色的名家及纵横家,汉人继承了先秦儒家的立场,首先强调言说内容的正当性,对于外在的技艺形式则相当的警惕,生怕它们脱离内容的羁绊而泛滥无归。
两汉虽有不少善于言说的人。但此时对于言说的态度,则可以扬雄《法言·吾子》的一句话为代表:“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见诸仲尼,说铃也”。②扬雄:《法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当时虽有善谈论者,然少风度仪容之注意,多重视内容是否合理正当,对语言辞藻或许有一定的关切,但于音调韵致等则措意甚少。
二、音辞并兴:魏晋音辞艺术的讲求
汉末以来,随着名士之风兴起,谈说作为彰显名士风采的重要手段开始受人注意。《后汉书·郭太传》载当时之大名士郭太:“善谈论,美音制,乃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③范晔:《后汉书》,第2225页。。对于“音制”一词,清人周寿昌释曰:“音制即音声仪制也”。④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82页。此例足以说明,汉末名士已经开始注重音声仪制等形式上的美感了。这当然与汉末清议之风兴起,名士多注重通过口谈彰显风采有关。汉末清议盛行的现象,典籍中多有记载,《后汉书·郑太传》:“孔公绪清淡高论,嘘枯吹生,并无军旅之才,执锐之干”⑤范晔:《后汉书》,第1812页。,蒋济《万机论》:“许子将褒贬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许文休。刘晔难曰:‘子昭拔自贾竖,年至耳顺,退能守静,进不苟竞。’济答曰:‘子昭诚自幼至长,容貌完洁。然观其插齿牙,树颊颏,吐唇吻,自非文休之敌”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40页。。从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一方面清议是汉末士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清议能力的高低也是人物评价中的标准之一。《后汉书·方术传》论云:“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⑦范晔:《后汉书》,第2724页。所谓“刻情修容,依倚道艺”,点明了汉末名士对外在风采仪表的重视。与谈议成为人物评价的重要标准相应,音声形式作为其外在元素也受到注意,《三国志·崔琰传》即载崔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惮焉”。⑧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69页。崔琰因为形象仪表出众,引起别人的敬重,而“声姿高畅”一语,则说明音声高畅对其形象构成也有加分。这一现象体现出清议之风兴起,给汉末三国人物评价带来的新趋势。
魏晋以后,随着清谈风气的兴盛,除了内容的探析之外,在语辞音制方面的体现也更加明显,下面是《世说新语》中的两段记载: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济每来拜墓,略不过叔,叔亦不候。济脱时过,止寒温而已。后试问近事,答对甚有音辞,出济意外。济极惋愕,仍与语,转造精微。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473页。
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淡。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⑩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60页。
由这两段记载可以看出,王济对王湛(王汝南)之所以由轻视而转为重视,就是因为他“答对甚有音辞”,引起了王济的注意,转而才与他深入交流,并大为改观。道壹道人作为僧人,更是以整饰音辞闻名于时。就所引文字中道壹之言来看,它们不仅六字一句整齐工致,而且韵脚协畅,读来有铿锵磊落之美,与当时流行的赋体韵文一致,算得上经口语润饰的赋体韵文,故在当时名流中独树一帜。
就当时人所重视的音辞来看,仔细剖析的话,又可以分为两大要素,一为音,一为辞,音要动听,辞要绚烂,下面简要举例说明。
一、音之动听
我们来看两段文献,一为《晋书·裴秀传》:
绰子遐善言玄理,音辞清畅,冷然若琴瑟。尝与河南郭象谈论,一坐嗟服。①房玄龄等:《晋书》,第1052页。
二为《世说新语·豪爽》:
桓宣武平蜀,集参僚,置酒于李势殿。巴、蜀搢绅,莫不来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叙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其状磊落,一坐叹赏。既散,诸人追味余言。于时寻阳周馥曰:“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②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63页。
这两者一则是裴遐“音辞清畅,泠然若琴瑟”,突出的是裴遐声调之优美,具有音乐一样的魅力,二则是描写桓温在平蜀后的讲话,不仅具有雄情爽气,还音调英发,慷慨磊落,与所讲成败由人的内容相映衬,使得一座叹服。最有意思的是,在座的浔阳周馥所言“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显然是说王敦也同样具有桓温的特点。这两个例子均说明,魏晋人在谈论时,已经注重音调的优美与铿锵。
魏晋人修饰音调,注重语言的音乐美,与当时佛教对于声韵之美的追求有关。自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随着宣传的需要,僧人们开始重视仪式活动时的语言表达效果,渐渐出现了梵呗新声。梵呗是当时僧人为了宗教活动发展出来的一种说唱艺术,这种艺术起源于三国时期,《高僧传》卷十三曾叙述了南北朝之前梵呗的发展经过:
原夫梵呗之起,亦兆自陈思。始著《太子颂》及《睒颂》等,因为之制声。吐纳抑扬,并法神授,今之皇皇顾惟,盖其风烈也。其后居士支谦,亦传梵呗三契,皆湮没而不存。世有共议一章,恐或谦之余则也。唯康僧会所造泥洹梵呗,于今尚传。即敬谒一契,文出双卷泥洹,故曰泥洹呗也。爰至晋世,有高座法师,初传觅历,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龠公所造六言,即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时有作者。近有西凉州呗,源出关右而流于晋阳,今之面如满月是也。凡此诸曲,并制出名师。后人继作,多所讹漏。③释慧皎:《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08-509页。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梵呗被认为肇始于三国的曹植,这大概是因为曹植文章对于音韵之美有着特殊的讲究④《高僧传》之前,南朝宋刘敬叔之《异苑》卷五已言梵呗起于曹植,然其书又言曹植所传乃道士之“步虚声”,足见曹植乃较早注意文字声韵之美的作家,故佛道二家追论音制发展皆溯源于他。。曹植之后有支道谦、康僧会、高座道人、支昙龠等人。这些人多活动于魏晋时期,与士林清谈风气的兴起同时。清谈技艺的进展,除了受汉末以来名士渐重音制的影响之外,佛教对于音辞艺术的探索与创新,予士林音辞技艺发展以推动也不容忽视。名僧乃清谈的重要力量,《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名僧有支道林、竺法深等人,东晋孙绰曾将当时的名僧七人与竹林七贤相比拟,可见名士与名僧关系之亲密。《世说·言语》第三十九载:“高座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⑤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09页。这个高座道人,就是梵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高僧传》卷一载:
帛尸梨密多罗,此云吉友,西域人,时人呼为高座。……初江东未有呪法,密译出《孔雀王经》,明诸神呪,又授弟子觅历,高声梵呗,传响于今。⑥释慧皎:《高僧传》,第29-30页。
高座与当时名士之间交往颇为频繁,《高僧传》卷十三载他去追悼周顗云:
俄而顗遇害,密往省其孤,对坐作胡呗三契,梵响凌云。次诵呪数千言,声音高畅,颜容不变。既而挥涕收泪,神气自若,其哀乐废兴皆此类也。①释慧皎:《高僧传》,第30页。
足见高座精于梵呗音韵,故不仅可作“胡呗三契,梵响凌云”,又能“诵呪数千言,声音高畅”。晋时名士名僧间往来频繁,清谈乃大家共同喜爱的文娱活动,在这样的现实需求下,僧人擅长的梵呗音韵之技,无疑会被士人吸收到清谈中来,以增加其吐纳抑扬的音韵之美。
二、辞之绚烂
音调的优美铿锵之外,词语的华美精丽,是构成清谈形式美的另一要素,在《世说》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如《文学》第三十六: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②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45-246页。
王羲之本来轻视支道林,结果支道林在论《庄子·逍遥游》时,“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使得“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一下子折服了王羲之,体现出辞藻之美的巨大魅力。
又《世说新语·文学》第五十五: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③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61-262页。
在名士会聚的场合,大家共同就《庄子·渔父》发表意见,“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在此基础上,谢安更加推陈出新,“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在谢安的演说中,一方面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另一方面意气拟托,萧然自得,说明清谈时的才藻和风度,是他折服众人的两大要素。
《世说》又载:
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寺中。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谓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王大惭而退。④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51页。
王濛为了追求清谈的效果,不仅宿构精理,而且撰其才藻,在清谈时“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虽然最后的效果未能如意,但也足以说明辞藻乃清谈的重要追求之一。这三段文字均出现了“才藻”一词,说明与人之才气相关的辞藻,也是时人评价清谈水平的标准。《世说》之外,《晋书》中也有时人擅长辞藻的记载,如《裴頠传》载“乐广尝与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辞论丰博,广笑而不言,时人谓頠为言谈之林薮”,⑤房玄龄等:《晋书》,第1042页。《王济传》载“济善于清言,修饰辞令”⑥房玄龄等:《晋书》,第1205页。等,这些记载说明辞藻乃当时名士清谈的重要元素。
对于音韵动听和辞藻绚烂的关注,有时会让人沉迷于清谈时的感官体验,忽视应有的义理探讨,《世说》即载有相关的例子: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时讲《维摩诘经》,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⑦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50页。
听众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足以说明他们在聆听时,更多注意的是音调辞藻的韵致之美,内容的合理与否已无关紧要。义理内容应有的地位,被语言形式上的美感湮没了①唐翼明《魏晋清谈》一书在论述清谈之形式美时,提出清谈贵“辞条丰蔚”、“花烂映发”及语音节奏之美,正对应本文所言之辞美与音美。唐氏将魏晋清谈家分为简约与丰赡两派,乐广、王濛、刘惔等被归入简约派,以与殷浩、谢安、支遁等为代表的丰赡派对应,然由《世说新语》“文学”第42 条所载“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诸语来看,王濛颇为重视清谈语言的才藻精丽,又《世说》“品藻”第48 载王濛以“韶音令辞”自居,则其清谈风格显然不能仅以“辞约旨达”的简约派目之;另外,唐氏将音美仅归结于语音节奏一方面,亦未免不够全面,如《晋书》载裴遐“善言玄理,音辞清畅,冷然若琴瑟”,此处的音声之美便不仅仅是节奏之美。参唐翼明《魏晋清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58页。。
三、别拓区宇:南北朝音制技艺之进展
南北朝之后,人们对于音辞的追求仍旧没有停止,而且由于社会及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此时对音辞的使用,已经由清谈而扩张到朝会、交聘等相关领域。当时史书中对于时人音辞之美多有记载。如周颙,《南齐书·周颙传》载:
颙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口成句。泛涉百家,长于佛理。著《三宗论》。……每宾友会同,颙虚席晤语,辞韵如流,听者忘倦。兼善《老》《易》,与张融相遇,辄以玄言相滞,弥日不解。……转国子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辩。②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731页。
可见周颙在言谈中辞韵如流,听者忘倦,具有极大的感染力。不惟如此,因其曾任国子博士一职的缘故,还引得太学诸生仿效,影响了一时风气。周颙除了音辞辨丽之外,还精于音韵,撰有《四声谱》一书,此书为永明声律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这是音辞追求影响及文学创作的明证。
与周颙往来密切的张融,也是精通音制之学的人物,《南史·张融传》载:
风止诡越,坐常危膝。行则曳步,翘身仰首,意制甚多,见者惊异,聚观成市,而融了无惭色,随例同行,常稽迟不进。高帝素爱融,为太尉时与融款接。见融常笑曰:“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③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34-835页。
足知张融因为风止意制独树一帜,而引起时人的关注。南朝张氏家族以音辞之学为家学,世代擅长此术,《南史》言“张氏自敷以来,并以理音辞,修仪范为事”④李延寿:《南史》,第843页。,张融之先张敷、张畅并擅音仪,史书有详细记载,先看张敷,《南史·张敷传》:
性整贵,风韵甚高,好读玄言,兼属文论。初,父邵使与高士南阳宗少文谈《系》《象》,往复数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叹曰:“吾道东矣”。于是名价日重。……善持音仪,尽详缓之致,与人别,执手曰:“念相闻”。余响久之不绝。张氏后进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⑤李延寿:《南史》,第826页
张敷擅持音仪,尽详缓之致,与人别所言之“念相闻”,竟可达到余音袅袅的效果,可见他具有非常深厚的造诣,并开张氏一族之独特门风。张敷之外,张畅也以善于音仪著称,史书曾载张畅与北魏李孝伯之疆场对答,双方堪称对手,各展其美,乃当时有名之文化事件,《南史·张畅传》:
孝伯辞辩,亦北土之美,畅随宜应答,吐属如流,音韵详雅,风仪华润。孝伯及左右人并相视叹息。⑥李延寿:《南史》,第831页
除此之外,在内政活动上张畅的音仪之技也曾发挥作用,《南史·张畅传》载:
三十年,元凶弑逆,义宣发哀之日,即便举兵。畅为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荫映当时。举哀毕,改服著黄裤褶,出射堂简人。音姿容止,莫不瞩目,见者皆愿为尽命。⑦李延寿:《南史》,第831页
张畅之名在当时传遍大江南北,《南史·张畅传》载:
后使融接对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顾而言曰:"张融是宋彭城长史张畅子不?"融嚬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达六夷”。①李延寿:《南史》,第836页。
周颙、张融之外,南朝还有很多士人擅长音制之学,如刘绘,《南齐书·刘绘传》载:
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王西邸。绘为后进领袖,机悟多能。时张融、周颙,并有言工。融音旨缓韵,颙辞致绮捷。绘之言吐,又顿挫有风气,时人为之语曰:“刘绘贴宅,别开一门”。言在二家之中也。②萧子显:《南齐书》,第841页。
张融音旨缓韵,周颙辞致绮捷,各有所长,刘绘则兼二家之美,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又《宋书》所载之徐湛之,也以音辞流畅著称史书:
湛之善于尺牍,音辞流畅。贵戚豪家,产业甚厚,室宇园池,贵游莫及。伎乐之妙,冠绝一时。③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44页。
南朝对于音制之学的讲求,与当时佛教声韵之学的进展有密切关系,在声韵学上造诣精深的周颙长于佛理,著《三宗论》;张融在遗命中也要求以小品《法华》陪葬,说明此二人均浸润佛学。南齐文坛的中心是竟陵王萧子良,他热衷佛教信仰,其身边不仅有竟陵八友,也有诸多名僧围绕,这些僧人中不乏有精通音制之人,据《高僧传》载有释僧辩:
少好读经,受业于迁畅二师。初虽祖述其风,晚更措意斟酌。哀婉折衷,独步齐初。尝在新亭刘绍宅斋,辩初夜读经,始得一契,忽有群鹤下集阶前,及辩度卷,一时飞去。由是声振天下,远近知名。后来学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同声发而觉,即起至佛堂中,还如梦中法,更咏古维摩一契。便觉韵声流好,著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龙光普智、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保超胜,及僧辩等,集第作声。④释慧皎:《高僧传》,第503页。
又有释慧忍:
无余行解,止是爱好音声。初受业于安乐辩公,备得其法,而哀婉细妙,特欲过之。齐文宣感梦之后,集诸经师。乃共忍斟酌旧声,诠品新异。制瑞应四十二契,忍所得最长妙。⑤释慧皎:《高僧传》,第505页。
此二人均为僧人中擅长音韵之学者,与萧子良关系密切。当时僧人、士人以萧子良为中心相与游处,士人较易接受僧人音声技法之影响,音制之学因而得到更大的发展。
南朝之外,北朝在音辞领域也有很多突出人物,与张畅相对答的李孝伯亦为一时之秀,《魏书·李孝伯传》载:“孝伯风容闲雅,应答如流,畅及左右甚相嗟叹。世祖大喜,进爵宣城公”。⑥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72页。。赵郡李氏成员之外,北朝音辞出众的还有宋弁,《魏书·宋弁传》载:
高祖曾因朝会之次,历访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对,声姿清亮,进止可观,高祖称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⑦魏收:《魏书》,第1414页。
宋弁因为声姿出众,仪表闲雅还被委任为使者出使南方,《魏书·宋弁传》载:
迁中书侍郎,兼员外常侍使于萧赜。赜司徒萧子良、秘书丞王融等,皆称美之。以为志气謇烈不逮李彪,而体韵和雅,举止闲邃过之。⑧魏收:《魏书》,第1414页。南北朝交聘出使的盛况,《北史·李谐传》曾有描述:“既南北通好,务以俊乂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宴日,齐文襄使左右觇之,宾司一言制胜,文襄为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亲与谈说,甚相爱重”。作为代表国体形象的人物,南北双方对出使的人选均较重视,音声仪制的清美与否,口辩折冲的能力高低,更是遴选使者的首要标准。对于其时出使之要求,详参王允亮《南北朝文学交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6页。由南方流亡北方的琅琊王氏家族成员王肃,也因音制之美著声当时,《魏书·王肃传》:
肃宗崩,灵太后之立幼主也。于时大赦,诵宣读诏书,音制抑扬,风神疎秀,百僚倾属,莫不叹美。①魏收:《魏书》,第1412页。
王诵之外,史书所载尚有多人,略举数例如后,《魏书·刘芳传》所载刘廞:
出帝于显阳殿讲《孝经》,廞为执经,虽酬答论难未能精尽,而风彩音制足有可观。②魏收:《魏书》,第1227-1228页。
《北齐书·杨愔传》之杨愔:
及长,能清言,美音制,风神俊悟,容止可观。人士见之,莫不敬异,有识者多以远大许之。③李百药:《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54页。
《北齐书·李浑传》之李绘:
每罢朝,文武总集,对扬王庭,常令绘先发言端,为群僚之首。音辞辩正,风仪都雅,听者悚然。④李百药:《北齐书》,第395页。
可见擅长音辞在北朝也已为常见现象,讲究音辞的风气遍及大江南北。
与语言清辨著美一时相应,音辞鄙陋则难免遭人耻笑冷落,《北齐书·儒林传》载张景仁:
景仁出自寒微,本无识见。一旦开府,侍中封王,其妻姓奇,莫知氏族所出。容制音辞,事事庸俚,既诏除王妃,与诸公主郡君同在朝谒之列,见者为其惭悚。⑤李百药:《北齐书》,第592页。
又《南史·儒林传》载:
卢广,范阳涿人。自云晋司空从事中郎谌之后也。少明经,有儒术,天监中归梁,位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遍讲五经。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辞鄙拙,唯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仆射徐勉,兼通经术,深相赏好。⑥李延寿:《南史》,第1740页。
足见当时士人对音辞之美的追求。这也充分说明,至南北朝时期,以往仅为清谈所注重的音辞艺术,已经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更多方面,成为士大夫修饰个人形象的必备要素,这是音辞艺术普及的重要体现。
综而论之,语言作为人类交流的工具,随人类的诞生一起出现。但对语言的讲求,则随着时代的进展而不断提升。先秦时期,人们注意到言辞或有左右事情发展的效用,对它有了一定的重视,但此时人们更重视语言的内容,对于音声形式则并没有过多要求,而在言者之言、德二元关系中,德更是处在决定性的位置。过分追求语言的精致、华美,则被视为一种异常现象进行批判。两汉以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士人所持态度与先秦并无太大变化。东汉晚期以来,随着汉王室的衰落,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瓦解,时代新风开始出现。因着清议之风的兴起,名士们开始注重修饰个人形象,言谈风仪作为关键元素,受到时人的重视,音制、声姿之美进入士人视野。两晋以后,随着清谈之风流行于士林,他们音、辞都有了更高的追求,斟酌词句、调畅口吻成为清谈的要务,出现了以此擅场的名士。南北朝以后,随着声律之学的兴起,音制之技更得到了长足发展,不少人以此名家,有些家族甚至将其作为家门特色进行传承。与前代相比,音制之美的讲求,已经走出士人清谈的小圈子,进入政治、宗教、文学的广阔空间,体现出它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影响。唐前音制之学的发展,不仅仅体现于言说技巧的提升,也为文学、音乐等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助力,近体诗的出现即与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