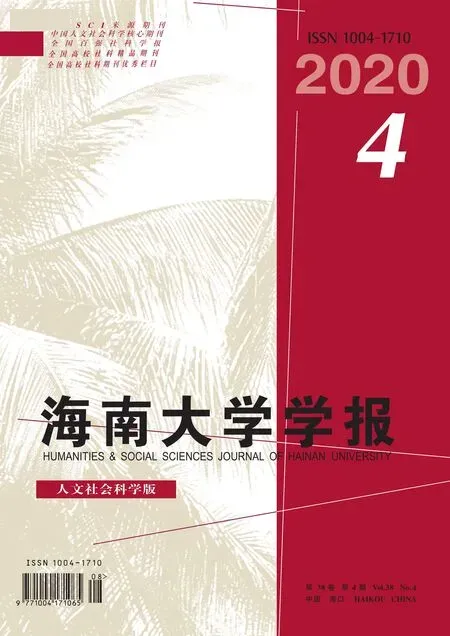欧洲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实践研究及对南海区域合作的启示
郭雨晨
(1.中山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510275;2.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广东 珠海519082)
海洋空间规划是以生态系统方法为基础的,分析、分配人类海洋活动时空分布,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旨在更有效地组织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利用,平衡用海活动之间的关系,平衡海洋开发利用需求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需求之间的关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中提道:“各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因此,合理规划海上人类活动,使其可持续地进行,需要高水平的协调,不仅在国家管辖范围内,有些还要跨越国家管辖的范围。本文所讨论的“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就是指跨国家间行政边界的海洋空间规划①国内学者认为: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包括三个层次内涵——跨行政边界海洋空间规划、跨地理边界海洋空间规划和跨治理边界海洋空间规划。参见马学广,赵彩霞:《融合、嬗变与实现:跨界海洋空间规划方法论》,《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即在至少两个国家管辖海域的共享边界或争议海域进行共同规划的过程。
自2000年以来,跨界海洋空间规划项目已在欧洲各海域,特别是波罗的海海域广泛开展。在世界范围内,跨界海洋空间规划也被积极倡导和推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欧盟委员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UNESCO)于2019年2月12日启动了为期三年的全球海洋空间规划项目(MSP Global),以促进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发展。所以,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已逐渐成为各国海洋领域合作的新趋势,值得关注。鉴于此,本文主要探讨以下三个问题:欧洲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发展现状如何,有何经验启示;在南海开展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的原因是什么;支持南海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的基础都有哪些。
一、欧洲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发展概述与案例研究
海洋空间规划制度在各国的普遍建立是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在欧洲开展的现实基础。截至2019年10月,根据相关数据统计①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官网、欧盟海洋空间规划数据平台,以及赫尔辛基公约委员会官网。,已有26 个欧洲沿海国正在筹划、制定或已经完成了国家级或区域级海洋空间规划。正在筹备或进行规划编制的国家中,大部分是欧盟成员国,所以这些国家的海洋空间规划均预计在2021年3月前完成,以履行欧盟《海洋空间规划指令》(Maritime Spatial Planning Directive)的要求。
目前已完成的欧洲跨界海洋空间规划项目有十余项,分布于北海、波罗的海、地中海以及黑海,波罗的海的项目数量最多。另外,一些跨界项目已经开始了第二轮的合作探索。例如在黑海区域,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MARSPLAN-BS II 项目已于2019年年初启动。该项目在2018年完成的MARSPLAN-BS 项目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完成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跨界海域共同的空间规划战略以及规划编制。在波罗的海海域,Baltic Scope 项目的二期项目——Pan Baltic Scope 也于2019年底完成。
根据规划的目的,这些项目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过程导向型”规划,该类规划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国家间海洋空间规划的协调;加强国家规划机构与海洋利益相关者的合作;确定、商讨跨界问题,提出解决措施;测试规划方法,总结经验教训。典型的规划例如包括瑞典、德国、丹麦等波罗的海六国的“波罗的海项目(Baltic Scope)”。另外一类是“结果导向型”规划,除了完成上述部分或全部“过程任务”的同时还需制定规划文件,但这类规划不会真正实施,因此也被称为试验性规划(pilot plan)。典型的规划例如芬兰与瑞典的“波的尼亚海规划(Plan Bothnia)”。
从各跨界海洋空间规划项目的实践状况来看,项目的过程意义远大于结果意义。并且,这种过程意义并未随着规划项目的结束而终止:通过项目所建立的海洋数据信息共享平台,成立的专门工作组、合作机构,已建立的国家间规划机构的合作关系,以及各海洋部门通过跨界合作所深化的了解和达成的共识都将为今后真正的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和其他海洋领域的合作奠定基础。这些跨界规划项目也同样显示了: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方式没有固定范式,而是根据规划区域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规划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因此,跨界海洋空间规划项目也各具重点和特色,值得其他意图发展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国家参考与借鉴。下文将以三个规划项目为例进行简要说明。
(一)凯尔特海项目(SIM Celt)(2015—2017)
凯尔特海项目是法国、爱尔兰和英国的政府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开展的为期两年的项目,以促进凯尔特海沿海国在海洋空间规划方面的跨界合作。凯尔特海项目注重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编制和实践过程中的实际操作问题。该项目以现有的跨界合作平台为基础,旨在加强合作、减少跨部门冲突、促进参与国海洋空间规划的协调。项目内容主要包括:生态系统方法在海洋空间规划的应用;跨界海洋空间规划机遇与挑战的界定;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实施途径;累积影响评估以及海洋数据平台建设等。
与其他跨界海洋空间规划项目相比,凯尔特海项目的亮点在于:它更加关注如何利用现有的法律政策与合作平台,使其在跨界海洋空间规划中效用最大化。为达到此目的,凯尔特海项目从国际、欧盟、区域(《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体系)和国内四个层级对与凯尔特海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相关的法律、政策、合作机制、机构、海洋信息数据库等内容进行了研究与评估,明确了跨界海洋空间规划面临的现实阻碍。这些阻碍包括法律依据欠缺、规划数据不足、数据标准差异等②Joseph Ansong,Anne Marie O’Hagan and Ellen MacMahon,“Existing Mechanisms for Cooperation on MSP in the Celtic Seas”,EU Project Grant No.: EASME/EMFF/2014/1.2.1.5/3/SI2.719473 MSP Lot 3,University College Cork,2018;Emma Baruah,Rhona Fairgrieve and Lynsay Ross,“Initial Comparison of Requirements of,and Differences between,UK Primary Legislation Pertinent to Marine Planning”,EU Project Grant Agreement No.:EASME/EMFF/2014/1.2.1.5/3/SI2.719473 MSP Lot 3,Marine Scotland,2017.。
以跨界海洋空间规划面临的法律依据不足状况为例:海洋空间规划是全面性、综合性规划,包括对环境、经济和社会要素的多重考量。因此,海洋空间规划的环境与社会经济影响评估是规划编制中的重要环节,跨界情形亦是如此。然而,无论是《跨界背景下环境影响评价公约》下的《战略环境影响评估协定》还是欧盟《战略环境影响评估指令》都要求仅对规划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既不包括对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影响评估,也不包括累积影响评估。虽然,凯尔特海项目报告暗示此问题可以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4 条关于“影响评估(Impact Assessment)”的规定加以解决③Joseph Ansong,Anne Marie O’Hagan and Ellen MacMahon,“Existing Mechanisms for Cooperation on MSP in the Celtic Seas”,EU Project Grant No.:EASME/EMFF/2014/1.2.1.5/3/SI2.719473 MSP Lot 3,University College Cork,2018,pp.55-56.。但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4 条规定适用的阈值是该活动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严重不利影响(significantly affect adversely the biological diversity)”,而跨界海洋空间规划活动并不符合这种情形。因此,关于跨界海洋空间规划中社会经济影响评估和累积影响评估的法律依据完善问题仍待解决。
(二)波的尼亚海规划(Plan Bothnia)(2010—2012)
波的尼亚海位于波罗的海北部,介于芬兰和瑞典之间。波的尼亚海规划是试验性规划,由芬兰和瑞典两国的规划机构、高校科研机构、赫尔辛基公约秘书处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空间规划和发展委员会秘书处等共同完成。项目重点是调研该区域的规划基础并制定规划,由各成员方和利益相关者通过五次会议的商讨推动完成。
最终制定的规划文件展示了芬兰和瑞典两国在波的尼亚海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方面所达成的共识,包含了航行、生态自然保护区、渔业、能源等多领域的规划内容。由于芬兰和瑞典两国的行政结构、海洋规划目标和规划方式很相似,并且在跨界规划方面有很强的合作意愿①Hermanni Backer,Manuel Frias,“Planning the Bothnian Sea-Key Findings of the Plan Bothnia Project”,2013,p.16.。因此,波的尼亚海规划的经验对具有类似情形国家间的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具有较高参考价值。波的尼亚海规划还引起了一些非欧洲国家的关注。2013年,波的尼亚海规划的报告全文由越南规划与投资部(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Investment)下属的越南国家规划机构发展战略研究所(DSI)的研究人员翻译成了越南文版本,以供其国内参考②http://www.helcom.fi/Documents/Action%20areas/Maritime%20spatial%20planning/Plannning%20the%20Bothnian%20Sea%20VIETNAMESE.pdf,2019年9月30日访问。。
关于波的尼亚海规划,一些学者对它的评价更值得关注。也许正是因为两国之间海洋空间规划目标、方式的较高相似性和较高的合作意愿等原因,使得规划文件中并未指明两国跨界规划的根本原因。正如学者Douvere 在点评波的尼亚海规划时所指出的那样:“保持积极主动(地进行跨界海洋空间规划)是一回事,但说明为什么要保持积极主动、共同行动则是另一回事”。③Fanny Douvere,“Annex 4:External Review Commentaries”,Hermanni Backer,Manuel Frias eds.,“Planning the Bothnian Sea-Key Findings of the Plan Bothnia Project”,2013,p.135.应用生态系统方法、实现跨海域综合协调管理是跨界海洋空间规划最为理想化的目标。但在现实实践中,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往往需要参与国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外交成本。因此,清晰、详尽地表明在当下以及未来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必要性,指出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对参与国所带来的直接益处(例如为实现规模效应以降低海洋风电开发成本或保护某种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是跨界海洋空间规划成功的关键所在。
(三)波罗的海项目(Baltic Scope)(2015—2017)
波罗的海项目是由德国、丹麦、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瑞典六国共同完成的跨界规划项目,主要目的是加强波罗的海国家海洋空间规划间的协调,加强海洋跨部门合作,确认跨界问题,提出解决措施。波罗的海项目由两个子项目构成:波罗的海中部项目(Central Baltic Case Study)和波罗的海西南项目(Southwest Baltic Case Study)。中部项目的参与国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与瑞典;西南项目的参与国是丹麦、德国、瑞典和波兰。
基于规划区域的具体情况,两个子项目运用不同的规划方式:中部项目采取以海洋行业为基础的规划模式,关注整个规划区域的不同海洋行业在现阶段和未来的相互影响、联系、冲突和跨界协调问题;西南项目则采用以关键海域为主的规划模式,主要聚焦各国海洋利益重叠的重点跨界区域,通过双边或多边会谈的方式进行利益协调与规划安排。
两个子项目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西南项目。西南项目的规划步骤是:首先收集各参与国在跨界海域已进行的规划项目、已掌握的用海数据和海洋科学数据,确定各国在该区域的用海需求和利益所在;在上一步数据信息收集、互换的基础上,制作各国的利益矩阵,显示各方在跨界海域的利益重叠情况;将利益重叠区域归类为“冲突”“共存”或“竞争”;根据分类情况,组织相关国家举行双边或多边会谈,以商讨潜在的解决方案④Alberto Giacometti,John Moodie,Michael Kull and Andrea Morf,“Coherent Cross-border Maritime Spatial Planning for the Southwest Baltic Sea”,2017.。这种聚焦于具体海域的跨界规划模式,有利于各国通过加深了解、互通各国的重点关切和具体利益所在,将跨界规划将要面对的种种问题聚焦化、具体化。仅由利益相关国参与的双边或多边会晤,也为讨论敏感问题(例如下文将讨论的争议海域的规划问题)提供了对话平台。
西南项目一共确定了八个“跨界重点海域”。在这八个区域中,有一个“灰色区域(Grey Zone)”。这个“灰色区域”随着2018年11月波兰与丹麦海洋边界协议的签署已不存在,但在波罗的海项目进行时,还属于两国在专属经济区的争议海域。海域划界争端的解决已超出了海洋空间规划机构的职权范围。但也正是因为未解决的划界问题,使得声索国海洋空间规划机构的权限在此海域发生重叠。这样的情形既为声索国国内海洋空间规划的工作带来阻碍,也不利于争议海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空间利用的管理。因此,声索国就争议海域的规划问题进行商讨与协调仍旧是有必要的。
关于“灰色区域”规划问题的对话由波兰规划机构向丹麦方提议希望在争议海域寻求临时措施(temporary solutions)而开启。两国的规划人员于2016年1月进行了双边会议,探讨在争议海域“共同规划”的可能性,以作为解决划界问题之前的临时措施①Alberto Giacometti,John Moodie, Michael Kull and Andrea Morf,“Coherent Cross-border Maritime Spatial Planning for the Southwest Baltic Sea”,2017,p.58.。两国的外交部也对这次会议给予了支持。通过讨论,双方同意在该区域适用相似的空间规划方式,因此,两国在该区域更具体和详细的国内规划制定方面具有相似性。在会谈中,两国还互换了本国海洋空间规划制定各阶段的工作安排和时间表,并就下一步会谈内容和双方需要完成的数据准备工作等规划内容进行了安排②Alberto Giacometti,John Moodie,Michael Kull and Andrea Morf,“Coherent Cross-border Maritime Spatial Planning for the Southwest Baltic Sea”,2017,p.58.。波兰与丹麦以其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在争议海域进行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的可能性。
从上述欧洲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案例可以看出:首先,跨界海洋空间规划与海洋划界问题并不冲突,可作为争议海域各方在达成划界协议前的“临时措施”。其次,跨界海洋空间规划没有标准范式,是立足于区域实际或合作方需求的“量体裁衣”的过程。因此,其形式和程度都较为灵活,可以因地制宜、按需设计。在合作形式上,可以从具体的行业部门合作入手,也可以从特定海域入手;在合作程度上,合作基础较好的海域可实现覆盖全方位、多领域的综合性规划;在合作基础欠佳或争议海域也可仅达成宏观的“规划共识”。最后,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过程是对拟规划海域生态资源状况以及开发利用情况的调查,也是对已有治理机制和合作平台进行整合与评估的过程,既能确认国家间需迫切合作的领域以及合作的阻碍因素(例如海洋数据信息标准的差异或法律依据的欠缺),也有利于促进合作国的政府部门、学术研究机构以及涉海行业等多层面的互动交流。当然,跨界海洋空间规划也面临很多现实问题,除了上文提到的法律依据不完善、数据信息标准不同等阻碍外,还存在因治理体系差异而导致规划的目标、程序方面的矛盾与冲突,但这些问题可通过推动政策趋同、建立跨界协调机构等方式得以解决③马学广,赵彩霞:《融合、嬗变与实现:跨界海洋空间规划方法论》,《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以上欧洲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实践对包括南海在内的世界其他海洋区域合作与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学者已从建立海洋环境保护区网络、制定区域性条约、加强南海沿岸国紧密型合作等角度为南海区域一体化的建设建言献策④胡斌:《南海MPAs 区域网络构建:现实需求、法律基础和路径选择》,《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张丽娜,侯丽维:《南海区域合作的法律困境及对策研究》,《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和海洋空间规划交流合作也不失为一个促进南海合作的新思路。
二、南海开展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合理性分析
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岛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指出:“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具体体现,树立了全球海洋治理的理念。“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包括共同的海洋安全、共同的海洋福祉、共建海洋生态文明和共促海上互联互通等多种内涵,强调人类社会在海洋事务方面休戚与共,共同应对全球性海洋挑战①付玉,王芳:《坚持陆海统筹建设海洋强国——我国海洋政策发展历程与方向》,《中国自然资源报》2019年9月26日第3 版。。海洋空间规划是各国海洋开发与保护的宏观布局。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则是在规划层面将各海洋邻国的海洋发展蓝图相互联通,在毗邻海域实现海洋管理对接,对本区域甚至更大范围区域所面临的海洋保护利用以及安全问题开展联合行动,以实现区域海洋的协调治理。因此,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可视为落实“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措施之一。
2017年6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国家海洋局制定并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以进一步与沿线国加强战略对接与共同行动,推动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蓝色伙伴关系,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实现人海和谐、共同发展。跨界海洋空间规划正是我国与沿线各国实现海洋发展战略和规划对接、政策协调,加强国家间涉海部门合作、机构合作和制度合作的措施之一。并且,《“,《“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已明确提出了包括“共同推动制定以促进蓝色增长为目标的跨边界海洋空间规划、实施共同原则与标准规范,分享最佳实践和评估方法,推动建立包括相关利益方的海洋空间规划国际论坛”的要求。所以,我国与其他南海沿岸国进行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合作符合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要求。
另外,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可作为南海“共同开发”的辅助保障。“共同开发”是两国或多国在跨越海洋管辖边界的海域或位于争议区海域以合作形式进行资源勘探或开发的行为②祁怀高:《当前中菲南海共同开发的制约瓶颈与应对思考》,《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3期。。“共同开发”多指具体海洋资源的利用活动,而跨界海洋空间规划是国家间在跨越海洋管辖边界的海域或争议海域进行“共同规划”的行为,它不以单种资源、行业、活动为管理目标,而是对该区域所有海洋开发与保护活动进行综合性、全局性管理。因此,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可以作为“共同开发”的辅助保障,既可以从规划角度支持、推动“共同开发”活动的开展,也可以平衡“共同开发”项目(例如:共同开发油气项目、共同开发渔业项目)与该海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以及与其他用海活动的关系。
三、南海开展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可行性分析
(一)南海开展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法律依据
在全球性条约层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是目前与海洋空间规划最为相关的两部国际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未提及海洋空间规划这个概念,但该公约为沿海国对海洋的开发利用、管理以及保护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一些规定(例如专属经济区的航行自由、领海中的无害通过、海峡的过境通行等)可能会影响到沿海国的海洋空间规划编制,但是总体来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不妨碍沿海国在其管辖范围内进行海洋空间规划的活动③Frank Maes,“The International Legal Framework for Marine Spatial Planning”,Marine Policy,Vol 32,No.5,2008,p.799.。并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3 条也鼓励闭海与半闭海沿岸国就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养护、勘探和开发,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科学研究等方面展开合作;第74 条和第83 条关于“临时安排”的条款也为声索国在未解决海域划界问题的争议海域进行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生物多样性公约》本身也并未对海洋空间规划有具体要求,但是海洋资源可持续性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国家间在上述领域的跨界合作一直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的重点关切。《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对海洋空间规划的关注从海洋保护区问题发展而来。在2012年之前,缔约方大会决议中对海洋空间规划的提及大多与海洋保护区和海洋与海岸带综合管理有关,将海洋空间规划视为推动和完善这两种海洋管理措施的工具之一④参见第八次缔约方大会决议VIII/22。。直至2012年,公约秘书处向公约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SBSTTA)提交了海洋空间规划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的报告⑤Secretariat of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Marine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A Study Carried out in Response to CBD COP 10 Decision X/29”,CBD Technical Series No.68,2012.。在随后召开的第十一次缔约方大会中,海洋空间规划事务作为决议XI/18 的一个独立内容出现。自此以后,作为实施“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2011—2020)”的工具和方法,海洋空间规划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体系下得到了更多关注。
《生物多样性公约》对海洋空间规划最主要的贡献是为海洋空间规划的基础——生态系统方法的应用提供了国际法依据。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对生态系统方法的阐释更加突出人本位的观点,认为自然资源管理的目标是一个社会选择问题①COP,Decision V/6:Ecosystem Approach,2000,UNEP/CBD/COP/5/23,p.104.。但是,以人类中心论来阐释生态系统方法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选择的主观性如何能正确反映生态系统的客观性和不确定性。已有学者指出:“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复原能力,以及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依赖于生态系统的良好状态。但是,健康的生态系统并非是能为人类健康和福祉提供最大限度生态产品和服务(的生态系统)。如果生态系统方法的管理重点由社会所决定,那么生态系统功能和复原力将面临很大的威胁”。②Chris Frid et al.,“Marin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to Maintain Ecosystem Goods and Services”,Sue Kidd,Andy Plater and Chris Frid ed.,“The Ecosystem Approach to Marin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New York:Routledge,2011,p.120.所以,《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的生态系统方法是否可以真正为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还有待商榷。尽管如此,《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还是为海洋空间规划的建立、实施以及跨界合作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
在南海区域性法律文件层面,目前仍以软法文件为主,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规定:在全面和永久解决争议之前,有关各方可在海洋环保、海洋科学研究、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等五大领域探讨或开展合作。这些低敏感合作领域,尤其是海洋科学研究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恰是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建立的基础。
除此之外,现有的南海区域性合作机制,例如东亚海协调机构(COBSEA)和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PEMSEA)也对海洋空间规划的建设提出了相应要求。虽然这两个区域性合作机制并非直接涉及南海,但与南海合作息息相关。在COBSEA 最新制定的《战略指南2018—2022》(COBSEA Strategic Directions 2018—2022)中,海洋陆源污染治理和海洋与海岸带规划建设被列为东亚海区域未来几年的优先发展事项。该指南指出,要在现有最佳科学证据的基础上,提升和强化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与海岸带规划和管理,重点关注海洋保护区(包括海洋保护区网络)以及海洋空间规划在东亚海区域的发展③COBSEA,“COBSEA Strategic Directions 2018—2022”,2018,p.17.。PEMSEA 的《东亚海可持续发展战略执行计划2018—2022》(SES-SEA Implementation Plan 2018—2022)也包含了建立和实施海洋空间规划体系的要求,将海洋空间规划视为实现东亚海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管理目标的重要措施④PEMSEA,“SDS-SEA Implementation Plan 2018—2022”,2018,p.5.。
除了上述文件,《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未来十年南海海岸和海洋环保宣言(2017—2027)》等重要文件的通过也为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在政治安全合作、经济社会发展合作、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科技合作方面提供了战略框架和宏观指导,也可以成为开展南海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相关依据。
(二)我国开展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的外部条件
从目前来看,南海形势总体平稳,围绕“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展顺利,并取得了标志性进展,已提前完成了单一磋商文本草案的第一轮审读。并且,我国与东盟的防卫合作也取得了重要突破。我国与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成熟期⑤外交部:《在2018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620761.shtml,2019年9月30日访问。。近些年我国与南海周边国的高层交往密切,为进一步、更深层次地推进海洋领域的双边合作奠定了基础。例如:我国与菲律宾的关系已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双方认为南海争议不是中菲关系的全部,不应影响双方其他领域互利合作⑥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明》,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452/1207_676464/t1615198.shtml,2019年9月30日访问。,我国与菲律宾的油气合作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和企业间工作组也已宣布成立;我国与文莱的关系已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同意将继续支持两国有关企业在海上油气资源领域开展合作⑦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文莱达鲁萨兰国联合声明》,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004/1207_677016/t1691366.shtml,2019年9月30日访问。;我国与印尼同意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加强双边、地区及国际层面的合作⑧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44/1207_677256/t1557430.shtml,2019年9月30日访问。;我国与越南的关系稳中有进,对话机制运转顺畅,务实合作成果丰硕⑨外交部:《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举行》,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595529.shtml,2019年9月30日访问。。除此之外,21 世纪海洋丝绸之路建设的稳步推进更是为我国与沿线国在海洋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防灾减灾方面的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①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9)》,北京:海洋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因此,我国与周边海洋邻国已建立的有效双边对话渠道,也可以成为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交流的突破点。
(三)我国开展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的内部基础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海洋局发布的《“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共走绿色发展之路,共创依海繁荣之路,共筑安全保障之路,共建智慧创新之路,共谋合作治理之路”的合作重点。作为“共谋合作治理之路”的重点之一,近年来,我国积极与孟加拉国、巴基斯坦、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等沿线国家开展海洋空间规划交流与合作。2019年1月,作为我国首例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编制的海洋空间规划——《柬埔寨海洋空间规划》的编制工作已基本完成②刘川,腾新:《柬埔寨海洋空间规划编制基本完成》,《中国海洋报》2019年1月11日第01B 版。。并且,我国与泰国的海洋空间规划合作也取得了实质性成果③周超:《海洋空间规划:“中国方案”服务“海丝”沿线国家》,《中国海洋报》2018年11月19日第03B 版。。这说明,我国与周边国家就海洋空间规划合作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这样的情形下,除了协助海洋空间规划技术欠发达的国家开展培训、提供技术援助和制定规划外,与海洋邻国开展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也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并且,我国已有与邻国进行跨界自然资源管理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中越北部湾共同渔区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而且,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海洋空间规划研究院已于2018年底成立。研究院除了开展海洋空间规划相关问题研究,为国家海洋空间规划的编制和体系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外,还承担着开展海洋空间规划国际合作、推进海上丝路沿线国家海洋空间规划合作、以及海洋空间规划对外技术援助任务。因此,规划研究院也可充分发挥其国际交流合作的作用,与相关部门一起,作为我国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抓手”。
(四)我国与周边国家海洋空间规划发展概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官网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9月,亚洲大部分沿海国家的海洋空间规划目前都在制定过程中④http://msp.ioc-unesco.org/,2019年09月30日访问。。印尼和泰国已将海洋空间规划的内容纳入其国内法的规定,目前这两国的海洋空间规划活动均在进行之中⑤http://msp.ioc-unesco.org/,2019年09月30日访问。。越南2013年发布的国家海洋战略——《到2020年和面向2030年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与海洋环境保护战略》明确了海洋空间规划的要求⑥李景光,阎季惠:《主要国家和地区海洋战略与政策》,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年版,第182-183页。。并且,海洋空间规划已于2018年被纳入越南国内规划法中⑦http://msp.ioc-unesco.org/,2019年09月30日访问。。在马来西亚,首个海洋空间规划项目——Semporna MSP 于2016年已完成了公众咨询⑧http://www.wwf.org.my/?21925/Malaysias-First-Marine-Spatial-Plan-Proceeds-to-Public-Consultation,2019年09月30日访问。。缅甸的海洋空间规划战略已于2016年完成⑨http://msp.ioc-unesco.org/,2019年09月30日访问。。韩国海洋空间规划示范区工作已经于前些年开展,《韩国海洋空间规划与管理法》也于2018年4月颁布⑩王晶等:《韩国〈海洋空间规划与管理法〉概况及对我国的启示》,《海洋开发与管理》2019年第3期;王泉斌:《韩国京畿湾示范工程海洋空间规划的经验与启示》,《海洋开发与管理》2017年第10期。。综上,大部分亚洲海洋国正在积极进行海洋空间规划的探索与实践。
我国海洋空间管理的实践已超过三十余年,海洋规划技术体系和法规体系已日臻成熟。2019年5月,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进程全面开启。作为新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空间规划体系也面临着调整。因此,我国与部分南海沿岸国目前都处于海洋空间规划的探索和建设时期,对海洋空间规划事务方面有着共同的现实需求,可为海洋空间规划事务的交流与合作提供部分动力。但是,推动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实践的具体动因还需根据合作的国家而确定,在基于对合作国家海洋利用与保护现状,海洋法律政策,海洋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发展目标,以及具体海洋部门发展方向的全面了解、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国家间目前及未来潜在的跨界资源、空间的保护与利用冲突,或确定行业合作协同增效的作用,以达到海洋空间规划合作1+1>2 的目的。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海洋空间规划是当前以及未来海洋管理的新趋势,跨界海洋空间规划也逐渐成为海洋国家合作的新领域。从现有法律基础、目前南海局势、开展跨界合作的国内基础以及我国与其他南海沿岸国建立海洋空间规划体系的现实需求来看,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可以成为促进我国与其他南海沿岸国在海洋领域合作的一种新形式。在南海进行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对落实“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辅助南海“共同开发”项目的顺利开展具有积极意义。
确定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的突破点,既可以从某具体的海洋部门、行业的跨界合作入手,也可以从某焦点海域入手。从现有的状况来看,我国与南海沿岸国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实践可以遵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即从已解决海洋划界的海域(例如北部湾)开始进行尝试,逐渐拓展至进行“共同开发”的海域或各方均承认有争议的海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规划范围或延伸规划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