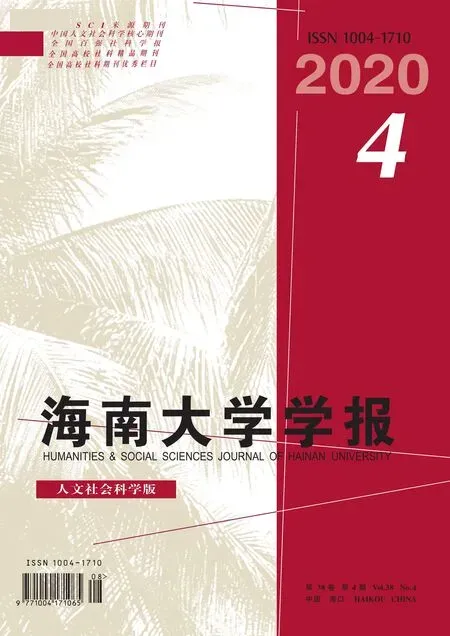市民社会对福斯塔夫骑士主体性的消解
廖金罗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410083)
约翰·福斯塔夫被安德鲁·布拉德雷(Andrew Cecil Bradley,1851—1935)认为是《亨利四世》中“最具魅力的角色”①Andrew Cecil,Bradley,“The Rejection of Falstaff”,New York:Enguin Groups.1988.,被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认为是为莎翁所塑造的“最为复杂的角色之一”②Harold Bloom,“Shakespeare: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New York:Penguin Group.1999,p.275.。福斯塔夫之所以是一个不和谐矛盾的统一体,是因为塑造他的主体性的力量经历着变化。福斯塔夫不得不在现实社会中挣扎,却又无法完全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福斯塔夫在现实生活中获取物质财富的手段和社会对他作为骑士和新教教徒的期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因此,福斯塔夫只能用幽默、俏皮和智慧化解个体和社会以及个体精神世界和社会价值体系之间的对立。作为一个艺术形象,福斯塔夫的魅力就在于他的“复杂性”,这一艺术形象揭示了人的主体性意识和真实生存状况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在历史变革时代人的主体性建构的荒唐性和滑稽性。
一、主体性和生产方式
人是什么?古希腊时期,人被认为是宇宙有机整体的一部分。中世纪时,人被认为是上帝的作品。到十九世纪中期,人开始被认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动物。迄今为止,尽管还存在挑战,查理士·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提出的生物进化论是人类普遍接受的关于人的起源的理论。然而,人的主体性是什么?关于这一个问题,迄今为止,并没有共识。
(一)劳动和人的主体性意识
十七世纪,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开起近代理性主体性的先河。1844年,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认为,被对象性的、自觉的和创造性的劳动从动物界分开之后,人开始有了自己的主体性意识。人的主体性意识在最初阶段仍然带有动物的性质。人作为生命有机体的“自我意识”和人在对象化的、自觉的和创造性的劳动过程中获得的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之间的界线比较模糊。人的对象化劳动已经把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和作为认知对象的人分离开来。就这样,人在把自己的主体性活动作为自己的认知对象来研究时就有了某种自主意识。人和动物之间的不同在于人的主体性意识代替了动物的本能或者说人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的过程中的作用》(The Effects that Labor Produces in Changing Ape to Man)(1876)中阐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观点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表明劳动创造了人。
和其他哲人一样,马克思对人类的理想化的劳动活动做过美好的描述。在批评国民经济学家没有看到异化劳动给人带来的后果时,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在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情况下,人实际上是以全面的、健康的和完整的人为代价换取人的进步的机会,人的异化的劳动不仅导致人和人以及人和劳动的异化,而且导致人自身的异化,即人被分裂为作为生命有机体的人和作为社会建构物的人。与这一异化过程相伴随的是人的意识被分裂为作为生命有机体的“自我意识”以及作为社会建构物的“自我意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的“总和”的意思既包含劳动关系,也包括非劳动关系。社会化的人是人在劳动关系和非劳动关系中的异化物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尽管没有给生产方式下明确的定义,但是,马克思1867年详细探讨了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主体性的作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已经达成共识③赵家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页。。显然,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既指社会整体或者群体获得物质财富的方式,又指个体获取物质财富的方式。
(二)生产方式和人的主体性意识
后现代时期,为了赋予马克思生产方式和主体性理论新的活力,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主导符码的“生产方式是由经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政治、司法、意识形态和文化等要素构成的”④朱彦振:《詹姆逊生产方式理论评析》,《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2期,第46-48页。。显然,他把经典的马克思生产领域的生产方式概念扩展到社会、政治和文化诸领域。詹姆逊的生产方式指社会整体、群体和个体获得物质财富的方式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组织方式、政治管理模式、文化、意识形态和道德体系。生产方式对人的异化作用一是表现为生产方式以及其中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对人的影响,二是表现为人经历了非人性化过程而成为生产方式的媒介,以及作为生命有机体的“自我意识”受到作为“社会建构物”的意识的影响。也就是说,生产方式的异化不仅导致人的分裂(人的生物性存在和社会性存在的分裂)和人的异化(人的生物性存在受到人的社会性存在的支配),而且导致人作为生命有机体的“自我意识”被人作为生产方式媒介的“自我意识”的支配。处于主导性地位的人作为生产方式媒介的“自我意识”成为人的“自我意识”。
在坚持拉康(Jacque Lacan,1901—1981)的“他者”主体性基础上,詹姆逊坚持作为主导符码的生产方式,认为人的主体性就是生命个体与作为“大他者”的生产方式认同的产物,是生产方式以及其中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在人头脑中的反映。主体性建构过程是个体的身躯被想像域中的“镜像自我”窃取以及个体的主体性被象征域中的“小他者II”⑤小他者II,拉康术语,指镜像自我在大他者中的投射。扼杀的过程,是个体把自己在生产过程中对生产方式以及其中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认知内化为个体无意识的过程。作为生产方式的产物,人的主体性必然随着生产方式变化而变化。以阶级替代为特征的生产方式的替代过程必然伴随着以人的主体性重建过程为标志的人的精神历程。如果没有一个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主体性重建过程,前一代的生产力就不可能得到继承,社会政治制度不可能延续,文明成果亦不可能得到传承。
历史的发展绝对不是单纯生产力的自动演进过程,也不是单纯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自然发展过程。一般地说,社会历史的发展一定是由生产力触发的包含生产关系、政治管理模式、意识形态和文化等在内的一系列变革。从这一角度上讲,马克思所提到的每种社会经济形态其实就是一种生产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过程就是生产方式的更替过程。以阶级替代为标志的一种生产方式代替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历史进程必然伴随着以人的主体性重建为标志的人的精神历程。因此,五种生产方式的依次演进过程必然伴随着人们从自在自为主体性到宗教主体性、理性主体性、集体主体性和未来共产主义理想型主体性的精神历程。然而,作为一种生物,人始终具有自身作为生命有机体的需要以及作为生命有机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在任何历史时期始终存在一种根据人的生物性需要思考和行动的生物型主体性。
詹姆逊认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历市场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垄断式资本主义阶段和跨国式资本主义阶段。由此相应产生三种不同的文化,即现实主义文化、现代主义文化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化。三种不同的文化必然孕育三种不同的主体性模式:与资本主义全盛时期相适应的主体性是自由个体主体性;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相适应的主体性是精神分裂式主体性;与未来乌托邦社会相适应的主体性是乌托邦式主体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詹姆逊既没有研究与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笛卡尔式理性主体性,也没有研究与封建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宗教主体性,更没有研究在主要生产方式之下的次级生产方式和人的群体主体性之间的关系。
二、骑士生产方式和骑士主体性特征
由于物质财富获取方式以及与之关联的社会组织方式、政治管理方式、文化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之间的差异,封建生产方式之中存在着不同的次级生产方式。中世纪的欧洲,因为缺乏安全机制,宗教贵族和世俗贵族通过军事采邑制方式把自己的土地分封给部属,而获得土地的部属需要向领主服骑兵役,这些人就是骑士。作为以战争和决斗为职业生涯的武装力量,骑士拥有的嗜血特色和尚武精神却直接挑战了教会在欧洲建立基督教秩序的政治企图。显然,作为军事安全服务的提供者,骑士需要被灌输一种信仰,注入一种思维方式,建构一种行为模式,以确保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不会威胁到教会和世俗贵族的安全。“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1页。作为宗教贵族和世俗贵族的共同信仰,基督教自然被用来塑造骑士的主体性。作为一种次级生产方式,骑士生产方式必然建构群体主体性。符合标准的骑士意味着作为生命有机体的“自我意识”受到作为封建骑士生产方式建构物的“自我意识”的控制。骑士主体性不是骑士肉体的个体性,而是被骑士内化为个体无意识的骑士生产方式以及其中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内在要求,是宗教教会和世俗政权对这支承担一定国家职能和社会职能的武装力量人员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等方面应该具有的价值判断体系和指令体系。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物,骑士主体性的主要特征有:相信上帝,根据基督教教义建构自己的判断体系、指令体系和行为模式;缺乏本能的满足和欲望的实现以及没有个体生命的价值体系;不是铸造自己的生存能力和履行生产职责,而是试图通过文化认同和人身依附关系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社会从封建生产方式向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过渡时期,是骑士生产方式被雇佣军生产方式取代的时期。与这一历史进程相伴随的是人们从宗教主体性向笛卡尔式理性主体性转变的精神历程。
三、约翰·福斯塔夫的主体性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
“福斯塔夫式背景”指“封建关系逐渐解体和资本主义勃兴时期”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或者说,指封建生产方式正在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兴起的阶段。市民社会是以商品交换关系为核心,以平等的私有者在分工前提下自由地交换其私人所有以及采取异化和物象化交往形式为特征的社会组织③韩立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市民社会概念》,《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4期,第40-51页。,是一个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肉体需要而从事使用价值生产,并且从市场上用自己所生产的使用价值换回别人的使用价值从而满足自己肉体需要的社会。因此,市民社会里的人们在生产领域以及生活世界中经历异化。作为生命有机体的个体必然成为社会建构物。这种异化表现为生命个体的社会存在支配生命个体的生物性存在,表现为作为社会建构物的“自我意识”支配作为生命有机体的“自我意识”,表现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物和物之间的交换关系而反映出来。显然,以早期资产阶级取代封建没落贵族为标志的从封建生产方式向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对生命有机体的影响取代封建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对生命有机体的影响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笛卡尔式理性主体性(以人对自然和社会探索以及人和人之间的等价交换为标志)取代宗教主体性(以人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基督教所倡导的“弟兄姊妹”情谊为标志)的精神历程。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物,笛卡尔理性主体性只有在资本主义物质财富生产再生产实践中才能被建构出来。离开了这一生产再生产过程,就不可能建构笛卡尔式理性主体性。中世纪末期,那些从原有的社会秩序中游离出来的人们因为无法进入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文化财富生产再生产过程,无法在新的社会秩序中认证自己,所以无法在新的物质财富生产过程中建构笛卡尔式理性主体性。福斯塔夫之所以无法建构笛卡尔式理性主体性,是因为不具备进入资本主义物质文化财富生产再生产过程的必要因素。然而,作为生命有机体,福斯塔夫需要物质资料和商品满足自己的需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物物交换而实现。也就是说,换取物质资料和商品,福斯塔夫需要金钱。在封建骑士生产方式被雇佣军生产方式取代之后,他既失去了原来的获得物质财富的方式,又无法进入新的社会生产秩序中获取财富。为了弄到金钱,福斯塔夫不得不利用贪污、索贿、偷窃和抢劫等一切机会获取物质财富。这种获取物质财富的非生产性劳动方式必然消解其骑士和新教徒身份以及与此身份相适应的骑士主体性和新教伦理精神。身为新教徒,却在世俗生活中流浪;囊中羞涩,却行为放荡;身为骑士,却坑蒙拐骗、打家劫舍;依附权贵,却招摇撞骗;国难之际,获得重任,却乘招兵买马之机,公然索贿;大战来临时,身为军事指挥官,不是挺身而出拔剑迎战,却是佯死逃生;临阵脱逃,却假冒军功。显然,其最大特征就是不和谐性。也就是说,福斯塔夫是一个不和谐的矛盾统一体。主要根源是:一方面,封建骑士生产方式在其个体心灵深处留下的痕迹仍然左右着他的价值判断体系和指令体系;另一方面,因为无法进入资本主义物质财富生产再生产过程,他只能退化到生活世界,满足单纯的生物性需要,用本能满足和欲望实现的过程来消除自己的骑士主体性。福斯塔夫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后,人们把关注焦点从天国转移到地上,从来生转移到今生,从沉思转移到物质财富的获得和责任承担。人际关系变得非常现实。本能和欲望的实现需要物质财富这一客观事实迫使人们把关注焦点从骑士精神和新教伦理转移到物质财富的获取之上,就这样,物质财富的获取对福斯塔夫思维和行动的影响削弱、取代了骑士精神和新教伦理对其思维与身体的控制力。也就是说,福斯塔夫作为骑士的主体性在现实社会中必然会因自身财富获得方式和市民社会生活状态而消解,由此又会引发主体的价值重构。个体的物质财富获得方式和个体无意识之间的矛盾基本上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基督教宗教哲学与商业实践、商业文明之间的对立矛盾。
(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文化面临“禁欲苦行主义”和“贪婪攫取性”的矛盾①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7页。。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的观点存在分类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从对待财富的态度上讲,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表现为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们对待财富的否定性态度以及注重物质财富获取手段的道德性(由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与后来人们对待财富的“贪婪攫取性”之间的矛盾。从生命意义的角度上讲,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表现为早期的禁欲苦行主义和后来的纵欲主义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资本家的行为特征表现出“禁欲苦行主义”和“注重获取物质财富的手段的道德性”。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却是纵欲主义和“贪婪攫取性”。从福斯塔夫身上,人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早期形式。资本主义文化面临着基督教文化建构的人生价值观和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对物质财富的贪婪态度之间的矛盾,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矛盾。这种矛盾必然导致福斯塔夫现象的出现。方平认为福斯塔夫是“虚伪的行家”,其性格本质就是“虚伪性和欺骗性”②莎士比亚·威廉:《莎士比亚喜剧五种》,方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其作为骑士和新教徒给予人们的文化期待与其作为生命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生存方式之间有着不一致性。福斯塔夫的主体性之所以是分裂的,一是因为作为骑士的福斯塔夫是作为生命个体的福斯塔夫在劳动关系和非劳动关系中的社会建构物,他被期待能够支配作为生命个体的自己。骑士精神是骑士所建构的与他们作为劳动关系和非劳动关系中的社会建构物相适应的异化意识,是领主和骑士之间在土地方面的依赖关系向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延伸。骑士精神反映了宗教统治者和世俗统治者对这支承担一定国家使命的武装力量的价值期待。作为新教徒,福斯塔夫被期待具有新教伦理精神。二是因为没有坚实的肉体,也就没有了维系骑士精神的物质基础。以往的社会都是通过战争、掠夺、没收、征税或其他敲诈勒索的手段来取得财富①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与之相比,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生产来增加物质财富的。然而,在此社会中,财富并非共同占有,而是私有。个人物质财富的分配方式是以货币形式实现的,人和人在物质财富生产再生产过程中由此扮演不同的角色,起着不同的作用。在市民社会中,人们不再从善良、美德或者什么骑士精神的角度判断和衡量他人的价值,而是从他拥有财富的多少以及他在社会物质财富生产再生产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角度判断和衡量。文艺复兴时期,在骑士生产方式被资本主义雇佣军生产方式摧毁之后,福斯塔夫之所以既失去了原有的物质财富获取方式,又无法进入新的社会秩序,适应新的物质财富获取方式,是因为他既没有原始资本积累,无法进入物质财富生产的组织者行列,也不是从事体力劳动的那块料。然而,作为生命有机体,他需要用货币来满足本能以及被唤醒的、不断膨胀的欲望,没有获得物质财富手段的他经历着价值信仰和生存方式之间的矛盾危机。
文艺复兴时期,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再是两个不同实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同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两个方面,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脱节。作为骑士,福斯塔夫具有骑士精神;作为新教徒,福斯塔夫具有新教伦理。只不过,其骑士精神和新教伦理不是表现为通过价值判断阻止作为生命有机体的福斯塔夫对物质财富的欲望,而是表现为对他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估。例如:尽管每一次抢劫前他都会祷告,每一次抢劫后都会忏悔,但只要有人提议抢劫,他什么都干。尽管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属的骑士阶层应该具有的品德体系以及新教徒应该具有的道德标准,但福斯塔夫早已置自己曾经珍视的价值体系、是非标准和道德底线于不顾,不认为自己是什么骑士、新教徒,而“自愿地”消解曾经的自我,在现实生活中建构一个曾经不是的自我。尽管不认同小偷和窃贼,但他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成为这种人。在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之前,人分为公人和私人,宗教只不过是利己主义的遮羞布;而这之后,人过着双重生活——想像中的虚拟的天国生活和没有真实性的尘世生活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正如商人的赌咒发誓,福斯塔夫的忏悔只是个体在市民社会中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分裂之现实的反映。
(二)禁欲主义人生价值观和极端纵欲主义
作为一种彼岸性宗教,基督教基于《圣经》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建构了世人对物质财富和欲望的憎恨态度,对本能和欲望的厌恶感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抵触感。基督教文化鼓励世人从物质财富的追求中,从对欲望的满足中以及对世俗生活的留恋中摆脱出来,致力于一种品德建构和基督教文化认同。中世纪时,人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人的价值是上帝给予的,人在今生今世的唯一任务就是听从上帝的教导,抵制欲望以便死后进入天堂。世人以牺牲本能需要、物质成功和今生今世的个体价值为代价换取文化认同。宗教改革的最大成果就是把彼岸性的基督教变成此岸性的宗教以及人们把物质成功当成宗教救赎的表示。生产和海外贸易所带来的物质财富促进人的欲望的实现。因此,一方面,被唤醒的欲望和本能满足使得人们把关注焦点从天国转移到地上,从来生转移到今生,从精神信仰活动转向生产劳作③闵丽:《论基督新教伦理的思想实质》,《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88-91页。;另一方面,欲望的满足唤醒人的尊严,使人建构起自己的价值体系。与这一趋势相反的是,尽管欲望满足唤醒了福斯塔夫的本能,但却没有唤醒其做人的尊严,反而导致了极端纵欲主义的人生态度。他依靠酒精、食物和女人来满足自己的肉体需要。之所以要不惜一切手段获取物质财富,是因为满足本能的物质需要用货币来换取之。然而,对欲望的过多满足只导致其身体和灵魂的扭曲。
(三)行为方式的矛盾
中世纪时,土地的军事采邑制确保领主和骑士之间的物质分配关系,贵族政治确保领主和骑士之间的统领从属关系,基督教文化确保在物质分配和世俗统属关系基础上的文化认同关系。显然,封建骑士生产方式建构了福斯塔夫的主体性。文艺复兴时期,传统的物质财富生产和分配方式以及世俗统属关系被摧毁。在价值认同方面,人们的注意力从对上帝的“信仰”、对自身“美德”的建构、对“来世”的关注等方面转移到对“今生”的关注、对“现世责任”的追求以及对“理性”的注重上来。经济方式和政治管理方式的变化导致人们不得不消除自己曾经的“信仰”,谪贬从前的“价值”,消解昔日认为最美的东西,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以成为那个自己不愿成为的“自我”。塑造福斯塔夫主体性的力量正在发生变化。他之所以是他,乃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具有肉体欲望的生命有机体,“心甘情愿”地消除自己曾经的主体性,用言语谪贬曾经的那个自我,建构那个曾经不是的“自我”。
在封建生产方式中,生产领域里以土地租赁为基础的依附关系导致人和人在生活领域里的依附关系。尽管其时也存在物物交换关系,但却是次要的,并被基督教的“弟兄姊妹”情谊所掩盖。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希望结交那些在地方事务上起积极作用的经济资源的拥有者。始终看重靠山的福斯塔夫一直认为他和哈里王子的亲密关系会在其登基后给自己带来利益。然而,市民社会中,人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的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0页。。人需要通过转让自己的财富来换取别人的财富以实现自己的需要。人们不再关心别人的情感、文化认同和个人品格,而是关注自己的商品在市场上是否能卖出去以及卖个什么价格,关注自己的价值是否能实现以及他人在自己价值实现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关注货币积累以及通过货币控制他人,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人际交往关系建立在物物交换之上以及人们在物质文化生产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基础之上。小时候,因为比较调皮,哈里王子常常受到大法官的责备,对法官颇有微词。登位前,出于政治考虑,哈里亲王常常和福斯塔夫等小偷们混在一起,登位后却不再按照关系的亲疏程度,而是按照人们在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中所履行的功能进行人事安排。因此他改变了对大法官的态度,对其大加赞赏,相反,福斯塔夫被一种幻想蒙蔽着,一直希望哈里王子在成为国王后能给他带来辉煌前景。登基之后,亨利五世抛弃了福斯塔夫。显然,生活世界受到系统世界的殖民化,人和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友谊被系统世界中的物物交换关系以及功能关系颠覆。在完全掌握政权后,资产阶级颁布一系列法律结束了无政府状态,恢复秩序。于是,福斯塔夫悲惨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四、市民社会和笛卡尔式主体性对福斯塔夫主体性矛盾的消除过程
福斯塔夫所具有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是非观告诉他:抢劫、勒索和欺诈并不符合他从前所属阶级的价值体系和是非曲直观。但他却不得不这样做。也就是说,物质财富对作为生命有机体的他所具有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骑士精神和新教伦理对他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福斯塔夫不得不经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禁欲主义人生观和纵欲主义人生态度以及灵魂和身体的矛盾。一旦选择价值体系、选择灵魂,福斯塔夫就需要经历禁欲主义的人生历程;一旦选择工具理性、本能需要,就需要用本能和欲望的实现来消除骑士主体性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他的内心世界矛盾通过一系列情境呈现出来。
一开始,无论在自己的记忆中,还是在他人的记忆中,福斯塔夫都不是一个很坏的人,反而是既有德行又有情有义。《亨利四世》的第一个情境是亲王和福斯塔夫的对话。作为多年的骑士和新教徒,基督教精神和文化在福斯塔夫心灵深处所留下的痕迹被期待能影响他作为生命有机体的价值选择和身体行为。然而,因为肉体需要,不得不从事非法活动,从而陷入肉体需要和价值需要的冲突之中。尽管不愿意选择价值理性和满足灵魂需要,但价值理性和灵魂需要一直都在。一旦选择肉体需要,他就担心王子做了国王之后会处决所有盗窃犯。他的担心表明他拥有自己的价值体系、是非曲直观和道德观。然而,尽管经历内心世界的矛盾,但一旦有人提议抢劫,他就开始响应。这一情境表明,福斯塔夫的价值体系、是非观和道德观只是对本能需要和欲望实现进行道德评估,而没有能够阻止作为生命有机体的福斯塔夫的实际选择。
第二个情境是盖兹山抢劫之后亲王和福斯塔夫在野猪头酒店相聚。一进门,福斯塔夫就讲述自己的抢劫经历,吆喝着战绩并虚构自己的光辉形象。当破绽被人指出时,他开始赌咒,吹嘘有人已经受伤。他最先说受伤的人数是两个,后改口说四个,又改口说七个,说九个,最后改口说十一个。面对亲王的反驳,福斯塔夫破口大骂。当谎言被揭穿后,他没有感到愤怒和尴尬,而是趁势辩护。显然,传统价值体系又开始起作用了。于是,福斯塔夫提出本能说。为了掩盖自己在现实中的行为,躲避良心的自责,他用刀把宝剑砍成手锯的样子,把鼻子摩擦到流血,把血涂抹在衣服上。这一情境也表明福斯塔夫具有骑士精神和新教伦理精神。只不过其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是分裂的。
第三个情境是福斯塔夫一本正经地、逼真地扮演国王。他逼真的扮演无意中揭示了其内心世界里的基督教精神,或者说,内心深处所残留的基督教文化的痕迹。不过,戏还未演完,警士便到酒店抓人。尽管在亲王掩护下,福斯塔夫逃脱了被捕的局面。然而,他却在帷幕后面睡着了。警士走后,亲王在其衣袋里搜出一堆欠条。这些欠条表明骑士和新教徒也是具有肉体需要的。福斯塔夫一直被这种灵魂需要和肉体需要之间的矛盾折磨着。“我要忏悔,我要赶紧忏悔”。①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III),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版,第65页。不过,忏悔之意被肉体需要麻木了。福斯塔夫和桂嫂之间的交往过程可以说明他堕落的原因。主体性价值的实现受到生命个体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数量的影响。骑士精神需要骑士肉体来包裹,没有骑士肉体包裹的骑士精神是不存在的。只有在骑士肉体的基础上才能孕育骑士精神。
第四个情境是福斯塔夫胡扯自己丢失了价值四十马克的图章戒指。他经常从桂嫂经营的小店里赊欠商品。一次,桂嫂催债,福斯塔夫为了转移话题就胡扯说他在桂嫂店里丢失了一枚图章戒指。面对福斯塔夫的指控,桂嫂引用亲王的话当面揭穿他的谎言。于是,福斯塔夫说他要揍亲王,可亲王出现后又不敢。当谎言被拆穿后,福斯塔夫没有生气,只是辩护,表现得无可奈何。面对这一切,亲王指斥福斯塔夫的胸膛里没有信义、忠诚和正直。亲王的指斥是不正确的。只不过,即使在福斯塔夫的胸膛里存在信义、忠诚和正直,他又能怎样,在肉体需要得不到满足的基础上建立的骑士精神是很难维持的。
第五个情境是尽管被委以重任,但福斯塔夫在国难当头之际仍然利用一切机会谋取利益。他利用公款买酒,滥用征兵命令并用一百五十个兵士换到三百镑钱。临上阵前,他反思生命和荣誉的关系。对于福斯塔夫来说,肉体需要和本能满足已远远超越了作为骑士的精神需要。
第六个情境是哈尔亲王和霍茨波交战的战场。战斗开始后,双方兵士交战。突然出现的道格拉斯严重威胁着为亲王呐喊助威的福斯塔夫的生命安全。于是,福斯塔夫假装倒地,借此逃脱一死。一旦脱险,原来的判断体系和指令体系又开始驱使他思考和行动了。“所以我还是要戳他一剑,免生意外;对了,我要发誓说他是我杀死的”。②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III),朱生豪译,第99页。战斗结束时,福斯塔夫邀功请赏,发誓痛改前非。
第七个情境是伦敦街道。因为过度纵欲,他不仅身体严重变形,健康欠佳,而且负债累累。在伦敦街道,福斯塔夫遇到向他索要债务的大法官。为了躲避大法官,福斯塔夫试图赶快离开。大法官赶上来,希望和他面谈欠债问题。然而,福斯塔夫滔滔不绝,竭力避免和法官谈论欠债一事。
第八个情境还是在伦敦街道上,桂嫂向福斯塔夫索要欠债。这两个情境说明福斯塔夫所面临的不断恶化的经济困境。对于他来说,现实的生存需要远远比骑士精神和新教伦理更重要,更切实际。在市民社会中,物质财富的获取方式必然消解骑士生产方式建构的骑士主体性。
第九个情境是福斯塔夫和桃儿在野猪头酒店的一室里打情骂俏。作为一个单身男人,他依靠小恩小惠和花言巧语来调戏处于社会底层的妓女以满足生理需要。这一情境说明:骑士也是人,有自己的生理需要。
第十个情境是征兵受贿。福斯塔夫抛弃所谓的责任和义务,开始疯狂地追求金钱。
第十一个情境是缺席战斗的福斯塔夫企图凭借俘虏科尔维尔邀功请赏。这两个情境说明了维系社会的法则以及福斯塔夫获得物质财富的企图。
第十二个情境是福斯塔夫在夏禄家的花园谈论战争胜利后的利益分配。战争结束,人们开始享受平静的生活。亨利四世驾崩后,亨利五世继位。消息传来,福斯塔夫异常兴奋,自以为凭借他和哈尔亲王的关系能得到一些好处。
幻想总是会被现实粉碎的。在亨利五世登基庆典上,兴高采烈的福斯塔夫在人群中喊道:“上帝保佑你,我的好孩子!”③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III),朱生豪译,第210页。然而,一听到福斯塔夫的声音,亨利五世就直接拒绝认同福斯塔夫,他的回复直接粉碎了福斯塔夫的幻想。当承诺没有兑现时,夏禄先生就直接向福斯塔夫索要他所欠的一千英镑。这一情境说明,市民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物物交换实现的。最后,福斯塔夫被登基后的亨利五世赶出了宫廷。
伊莉莎白时期是英国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决战时期。以阶级替代为特征的生产方式变化的历史进程伴随着人的以主体性重建为特征的精神历程。一方面,波林勃洛克等统治者在牺牲无数人的生命后实现了自己的帝王梦想。另一方面,普通大众在历史大变革时期经历了人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立。福斯塔夫之所以是福斯塔夫,是因为现实生活的生存法则摧毁了骑士精神对人之本能的控制,趋炎附势取代道德遵循,肉体需要和酒精剌激颠覆了基督教精神的支配性。市民社会的生存需要摧毁了基督教精神对人的本能的控制。
五、市民社会对骑士主体性的消除方式
作为一部历史剧,《亨利四世》一方面通过对庄重、紧张、严肃、充满危机、焦虑和流血的宫廷生活的描写来说明以亨利四世为代表的贵族试图通过流血和战争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的过程;另一方面通过对伦敦东头的野猪头酒店平庸、嬉戏、轻松、琐碎的市井生活和享受物质、释放本能、花天酒地、胡闹和有趣的恶作剧的描写说明以福斯塔夫为首的三教九流如何消解主体性的过程。
尽管拥有自己的价值观、是非观和道德感,但由于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福斯塔夫对传统价值观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行为违背他们那个阶层应该拥有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又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也无法按照他所接受的原则生活。即使不自甘堕落,也没有能力超越生存环境。他试图消除传统价值的影响。在面对战争中的伤亡时,他清楚地知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荣誉的价值,但他如此关注世俗生活和本能需要以至于无法顾及得救和天堂,无法顾及骑士精神和新教伦理。因此,他既通过摆脱社会性存在退返到生物性存在,又不得不通过幽默、智慧和俏皮来化解自己和社会之间的对立。普希金说:“福斯塔夫一点也不笨,他一点也没有什么常规。他像女人一样软弱,他需要强烈的西班牙酒、油腻的饮食和供养自己情妇的金钱。为了获得这些,他什么都干,只要不去碰明摆着的危险”。①普希金:《Table-talk》,见杨周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26-427页。在讲述盖兹山抢劫经过时,福斯塔夫公然撒谎;而当谎言被当众揭穿时,他却没有因此感到尴尬、难过,而是机智地化解了思维和存在、价值和现实之间的矛盾。表面上看,话语有些荒诞不经,有些逻辑荒谬,有些文不对题,然而,荒谬的只是语言层面和逻辑层面。在语言、逻辑和连续的后面隐藏着通过嘲弄、揶揄、幽默、俏皮和智慧化解的个体和社会、个体的精神世界和外部价值体系之间的尖锐对抗以及自己面对这种对抗时的难堪。显然,福斯塔夫表层的荒谬并不是对严峻现实的批判,而是对现实存在的无可奈何的调侃。在《亨利四世》中,福斯塔夫解决矛盾的方法和效果与亨利四世通过战争和暴力解决矛盾的方法和效果形成鲜明对比。尽管亨利四世用打打杀杀来解决自己和周围世界的对立关系,以别人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成功地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那种人,但他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相反,福斯塔夫尽管没有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人,而是成为自己不愿成为的人,尽管也避免不了一死,却通过调侃、捉弄和揶揄化解了自己和社会之间存在的矛盾,给周围环境带来一种难得的压力释放。福斯塔夫这一艺术形象的魅力在于揭示了伴随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的主体性重建以及大变迁时期主体性建构的荒诞性。
六、结 论
尽管后现代这一词语为学者所诟病,但在审视现代社会痼疾及其根源之时,我们又不能不回到各种痼疾的起点,去寻找其起始和经过。福斯塔夫所经历的矛盾不乏对抗性和紧张性。他通过个人智慧和幽默化解了人和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把不和谐的气氛改变成一片节日景象,不至于沦为只有通过刀剑和流血才能化解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因此,读者在观看和欣赏时感到的不是紧张和对抗,而是愉悦和高兴。在喜悦之余,观众又不能不思考一个严肃问题:在特定历史时期,骑士生产方式建构的福斯塔夫主体性是如何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社会形式——市民社会——所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