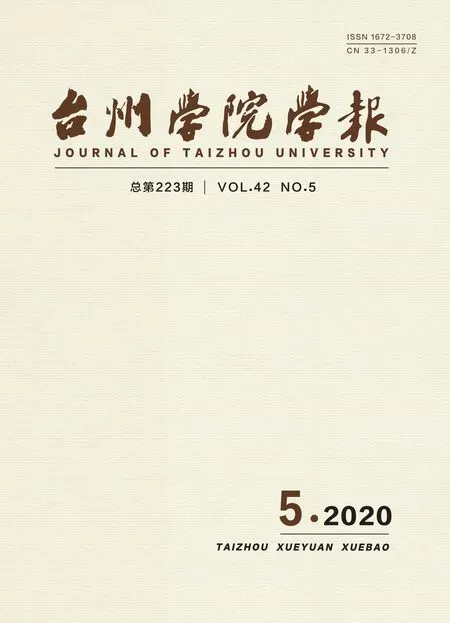辉耀百世的人之诗
——重读邵燕祥
洪 迪
(台州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追思邵燕祥先生的最好方式是重读。重读其人,其文,其诗。邵燕祥先生是辉耀百世的人之诗,是追求人的自由、尊严与美的清新朗健本真的诗,更是本真的人中挺直脊梁诗一样美的人。
一、穿越时代激荡风雷的风雨鸟
从1948年6月30日起,有署名汉野平的陆续在北平《国民新报》上发表《传说》《火的瀑布》《朝阳花赞》等诗作,以《风雨鸟》与《箭楼》最为出色。其《风雨鸟》云:
太阳从瓦解的土地上/敛起了灰白的光辉。/我听到……远方海一样的天空/有呼唤风和雨的鸟在叫,/渐渐近了,渐渐近了,/打个疾速的回旋,唿个信号,/一拍翅占领了天空,/是年青而矫健的水凫、山燕子,/这些风和雨的骠骑兵。//整个天空在变色啊。//鸟们叫来大堆亮灰的云彩,/我和酿雨的云彩赛跑而来。/风雨鸟飞近来了,/云的腿搭下来了,/风的足音雨的脚步杂沓来了!//整个的土地在骚动呵。//灰色的云朵下进行着危险的事情,/像雨激起的漩涡一样滚大。/我们,年青的人们哟,/挺着被日光曝晒的风浇雨打的胸脯/飞奔而来,/震天的雷霆轰然而来,/拔步在泥泞里跑得更快,/绞架在风雨的拳脚下塌了……/感谢呼唤风和雨的鸟![1]7-87月20日刊载的《箭楼》:
箭楼像一滩野鸟的粪便/孤零零地遗落在荒野里/古老的城堞,一堆灰色的砖石//箭楼像搁浅的船只/或受伤的小兽剥秃了毛/蹲伏在旷野里梦着咆哮//千军万马呢?铜钹羯鼓呢?/箭衣褪色在日光的曝晒下了/箭镞锈损在风雨的侵蚀里了//墨色的云追逐于颓圯的箭楼背后/背弓者的心却像拨云见日/不肯在云堆里沉落//我要驰骋在负载我的道路上/把荒野的尸布撕破/把天空的棺盖射穿……[1]10-11这两首诗,即使厕身《预言》或《九叶集》中,亦未见多所逊色,更显自有特色。尤其令人骇异的,是这位崭露头角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新诗人汉野平,竟是15岁早慧诗人邵燕祥当时的笔名。此时的邵燕祥诗兴文兴大发,以诗为主,兼及杂文、散文、小说、故事、书评、短评,频频出现于北平、华北诸多报刊。
然而,《风雨鸟》与《箭楼》二首诗对于诗人邵燕祥的一生,无论其人其诗,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诗中的“风雨鸟”“风和雨的骠骑兵”“呼唤风和雨的鸟”,乃至“我要驰骋在负载我的道路上/把荒野的尸布撕破/把天空的棺盖射穿……”的“背弓者”都是少年诗人的自许和期望着的自传。是的,诗人邵燕祥正好在“志于学”的年龄[2],便立志为本真的诗献身。这种本真的诗必须是诗美含量极高的诗;更应该是战斗的诗,能“一拍翅占领了天空”的诗,能让“绞架在风雨的拳脚下塌了……”的诗,一名“心却像拨云见日/不肯在云堆里沉落”的“背弓者”的诗。两首诗是邵燕祥一生的志向,也是其一生命运自觉不自觉的谶语。
时代在大踏步前进。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易帜。虽然祖籍浙江萧山,邵燕祥却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地道北京人。从1946年春天开始,少年邵燕祥就参加了“自由读书会”“‘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等进步活动。1947年10月,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简称民联)。1948年8月,考取中法大学。1949年3月,考入华北大学。5月底,当与他同一区队的大部分同学随军南下时,只少数学员被调回北平。6月1日,邵燕祥被分派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上班,成为资料编辑科一名见习编辑。此台在开国大典时即改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其后,他曾于1951年10月25日至1952年2月6日参加“西北土改工作团”。不久,被任命为电台的文教组副组长,负责组织每晚半小时的《文化生活》节目。1953年6月18日为中共候补党员。崭新的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朝气蓬勃的新生活,让这位早慧而敏感的青年诗人晃晃然有了“一拍翅占领了天空”的真情实感,更加勉力地用新声放怀高唱。
于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人民画报》《新观察》《人民文学》等各大报刊纷纷发表邵燕祥短诗、长诗、组诗。于是,应《人民文学》编辑部之约,会见诗人严辰。严辰和夫人逯斐、诗人吕剑留饭。又应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诗人袁水拍函邀晤谈。《文艺报》副主编萧殷称赞《歌唱北京城》“有泥土气息”。于是,1951年8月,18岁的诗人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5月,第二本诗集《到远方去》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7月,将上述两本诗集合起来又有所增减的第三本诗集《到远方去》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一时“政治抒情诗人”的赞誉响遍举国上下。不过,这一时期的诗风与此前的诗风相比有着明显的变化。其间内外交合的复杂成因,颇为值得探究。
且重读当年的两首好诗吧。写于1952年的《到远方去》:
收拾停当我的行装,/马上要登程去远方。/心爱的同志送我/告别天安门广场。//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还没有铁路的影子。/在我将去的矿井,/还是一片荒凉。//但是没有的都将会有,/美好的希望都不会落空。/在遥远的荒山僻埌,/将要涌起建设的喧声。//那声音将要传到北京,/跟这里的声音呼应。/广场上英雄碑正在兴建啊,/琢打石块,像清脆的鸟鸣。//心爱的同志你想起了什么?/哦,你想起了刘胡兰。/如果刘胡兰活到今天,/她跟你正是同年。//你要唱她没唱完的歌,/你要走她没走完的路程。/我爱的正是你的雄心,/虽然我也爱你的童心。//让人们把我们叫做/母亲的最好的儿女,/在英雄辈出的祖国,/我们是年轻的接力人。//我们惯于踏上征途,/就像骑兵跨上征鞍,/青年团员走在长征的路上,/几千里路程算得什么遥远。//我将在河西走廊送走除夕,/我将在戈壁荒滩迎来新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想起你,就更要把艰巨的任务担在双肩。//记住,我们要坚守誓言:/谁也不许落后于时间!/那时我们在北京重逢,/或者在远方的工地再见![1]12-14
这显然是一首政治抒情诗,鼓励年轻人“惯于踏上征途”,“青年团员走在长征的路上”,去“河西走廊”,去“戈壁荒滩”,去做“母亲的最好的儿女,/在英雄辈出的祖国,/我们是年轻的接力人”。但是请注意:狡猾的青年诗人隐藏着年轻人喜爱的爱情诗。男的到远方去开发大西北,女的是“活到今天”的刘胡兰,留在北京拼命“要唱完她没唱完的歌”。两人恋恋惜别,“心爱的同志送我/告别天安门广场”。尔后一同牢牢“记住,我们要坚守誓言:/谁也不许落后于时间!/那时我们在北京重逢,/或者在远方的工地再见!”这正是当时年轻人理想的恋爱故事。
再读1954年的《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1]28-30。这首诗开头一节二行:“你可知道祖国的辽阔?/你可曾用脚量过道路?”随后是三节二十一行铺展到处的迫切需求。而紧接着:
你可曾走过这些道路?
你可曾听到道路在呼唤?
它们都通过第一汽车制造厂,
对我们建设者大声地说:
——我们需要汽车!
我们满怀柔情与豪情,
大声地告诉负重的道路:
——我们要让中国用自己的汽车走路,
我们要把中国架上汽车,
开足马力,掌稳方向盘,
一日千里,一日千里地飞奔……
这用上抽象词意象化的现代诗艺的结末四行,即使在新世纪中国的当今,仍然是时代的警句。
尔后,1955年苏联的文学解冻与“干预生活”,1956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邵燕祥诗歌出现了变化,有了不少讽刺诗。例如,在《磨光的五戈比》中[1]54-56,可以读到:“遥想当年,五戈比/乍来到人海浮沉,/就已经自命不凡,/到处都铿锵作声。//把一股逼人的盛气,/充作了满腹经纶,/瞧不起所有的戈比,/卢布也不在眼中。/如今光芒暗淡,面目模糊不清,/仍然爱打转转,/但是头重脚轻。//口袋里的地位不满意,/手心上捧着才称心,/一旦被放到地面,/满怀不平乱跳蹦。//碰到别的戈比,/咬牙切齿响叮叮,/跟这个比大比小,/跟那个较量轻重。”给或一种人画了一幅可鄙的肖像。而在同时,也写了歌颂革命老区的《谒太行》[1]44-46。其后半云:
我登上太行山,朔风怒号,
太行山一夜雪,鬓发斑斑,
太行山,太行山,英雄的母亲啊,
每一条皱纹里是眼泪和血汗。
太行山,太行山沉默不语,
你是否又想起往日的熬煎?
想起了子弟们卧薪尝胆,
想起了难忘的生聚十年?
一层沙,一层雪遮住山路,
当年的脚印早已不见。
怎样一代人将留下新的脚印?
太行山审视着,又慈爱又威严。
思昔抚今,一股英雄的革命正气冲天。不过,总的说来,此时意气风发的青年诗人邵燕祥,其诗观有了新的变化。他认定:“我们的诗应该有助于新人和新事物的成长和胜利。那些阻碍我们前进的旧社会的残余还在发着臭味,我们必须用笔来把它们扫除干净。”[3]发表于1956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的《贾桂香》,便是着重体现其“扫除干净”诗观的力作。
在《贾桂香》[1]317-323诗后,有作者[附白]:“佳木斯园艺示范农场青年女工贾桂香,受不住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的围剿,在7月29日自杀。《黑龙江日报》记者王戈写有调查记,登在10月11日《黑龙江日报》上。读之心怦怦然,因写这首诗呼吁:不许再有贾桂香!”而在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献给历史的情歌》的《后记》中,邵燕祥更说:“我对自己的诗,若说有所偏爱,那就是1956年11月的《贾桂香》。这首诗写得不够深刻,也还有失于天真之处,但确是从我血管中流出的血,真诚的血。”《贾桂香》标志着邵燕祥从此只写尊重人性、珍惜生命的本真的诗,“确是从我血管中流出的血,真诚的血”。纵然因此遭到濒死的长期厄运,仍终生坚持“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4]。
《贾桂香》这个真实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诗的开头是旷朗欢快的:“天上的白云像头巾飘荡,/地上疾走着快活的姑娘,/眼珠儿东望西望,长辫子前晃后晃,/看这儿像不像你的家乡?/菜叶叶翠绿,菜花儿金黄,/掐得出水来,吸收着阳光……/生活比这原野还要辽阔,/幻想比这大路还要宽广!”紧接着是这位“转成了固定工”“担任了生产小队长”,又入了青年团的姑娘,自得到如此自问:“世界上难道还会有烦恼,/还会有不幸吗,贾桂香?”
不,不。太天真了诗人,太天真了贾桂香!大变故竟起于如此平常的生活琐事:
孙大叔老把小贾当成小孩,
一点不像管理员对小队长;
晚上散会,骑车载着她回家,
就跟载着自己的女儿一样。
他爱跟年轻人说说笑笑,
年轻人爱跟他道短说长。
可是只有一句话真讨厌:
“小贾,求不求大叔给找个对象?”
然而,刚解放不久的阳光普照的新中国的湖泊里,会有多恶臭多强烈的沉滓浮起!“哪怕孙大叔生一千张嘴,/再也辩不清小贾的冤枉——/‘小丫头成天跟你在一块,/你们的关系一定不正当……’/流言还只是一阵风,一片云,/会上的批评织成一张网。//这是怎样的一张网呵,/没头没脑罩住贾桂香。”连“年轻的丈夫/体贴”“这夫妻的情分”,竟成了“不爱劳动,不给爱人做饭。”“团支部叫你检查思想”。于是,撤去生产小队长,队长更时时“打击贾桂香”,“所有没有人承担的过错/全归了这个无辜的姑娘”。不得已去找场长,“场长把桌子拍得山响”。终于激愤的诗人如此作结:
我不忍落下这最后一笔,
中国不该有这样的夭亡。
1945年九岁的小嘎,
1949年十三岁的小姑娘,
等待她的该有多少幸福,
多少火热的欢乐的时光!
到底是怎样的一股逆风,
扑灭了刚刚燃点的火焰?
海阔天空任飞翔的地方,
折断了刚刚展开的翅膀!
告诉我,回答我:是怎样的,
怎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
谁知作此呼吁与质问的这只诗的“风雨鸟”,亦正好在“海阔天空任飞翔的地方,/折断了刚刚展开的翅膀!”
二、力争人的尊严自由的诗之火凤凰
犹如晴天霹雳,1958年2月24日,邵燕祥被打“入另册”[5]。直到 1979年1月才接到“改正”的一纸通知。中间是整整21年的苦难。然而邵燕祥这羽诗之火凤凰,纵然在烈火焚身之际,仍然鸣唱不辍。从1958年至1977年20年间,他悄悄写下新诗不下90首。他曾在1962年9月,将此期未结集诗编成一集,投寄上海文艺出版社。翌年初,被退稿,理由为“都是旧稿,比较庞杂,质量不齐”。但在此期间,也有偶尔漏网获得发表的。例如,在《人民文学》1962年3月号发表《夜耕》《灯火》;同年11月10日,在《北京日报》发表《27号岗》。但在未发表的诗稿中,却有新的好东西。比如,写于1959年的《传说——铸钟姑娘》[1]60-61:
……萋萋的芳草化作空中的流萤,/鲛人的泪化作海底的星星,/人间不死的心化作一个酒盅,/倾洒出生死如一的歌声……//五十四声钟,夜深露重,一句句叮咛送你入梦;/五十四声钟,晨光破晓,/打发早行人一路顺风。//钟声里多少次出现她的幻影,/是妻子,是女儿,又是神明。/就是她,铸钟时投入血肉之躯,/古钟斑斓,她却永远地这样年轻。//有人说她是为了老父亲,/有人说铸钟匠里有她的情人……/忠贞的爱情使人赴汤蹈火,/不吝惜一度的生命,不再的青春。//谁追寻古老的传说的岁月,/但相忘我的灵魂永生。/无论什么时候轻叩这座洪钟,/一声声从心坎响透天穹。
这位“铸钟姑娘”是谁?是古代的“忠贞的爱情使人赴汤蹈火”的烈女吗?是的。但我知道,燕祥心底里更是他1957年初刚结婚,不久即因他而受难的贤惠忠贞的妻子谢文秀。“人间不死的心化作了一个酒盅,/倾洒出生死如一的歌声……”可以是超时空的泛指,且更是诗人的自誓。再如,写于1977年的《江边石》。开头是“江边石”的“笑靥——比夕阳更明艳”的苍劲身姿的呈现,然后是深情的结末:
你的心,我的心/曾经为同一理想而发颤。/让万里江山作证,/我们的心永远不变。//是的,你从容地献出了短暂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悠长的思念。/但谁说你已经离我们而去,/我们重逢在长江边。//谁说这只是一块岩石/矗立在奔流的江水南岸?/她的名字叫:青春,/一个五十年代的地质队员。
显然,即使在受难的20年中,诗人邵燕祥根本拒绝将自己打“入另册”。
但是在新世纪初年,邵燕祥却作过深刻的反思。他说:“假如为我那过去的三十年树一座墓碑,应该严肃地铭刻这样两行字: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6]7他说:“战后三十年,陈尸现场/只为了证明真诚之为虚妄/一个游荡的灵魂隐入书里/找来找去,找不到失踪的自己。”[6]314两句话都写在《找灵魂》里,前者为《引言》,后者是《跋》。据此,吴思敬在《苦难中打造的金蔷薇——邵燕祥诗歌研究论集》的《序言》中说:“把这两段文字联系起来,可以说概括了邵燕祥那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独立的思想、因而迷失了灵魂的前半生。”[7]对于吴先生此说,我始尔点头唯唯,继尔沉吟否否。可以说,共和国开创初期邵燕祥这些“政治抒情诗”,在百年新诗史上还是具有一定的价值的,其歌唱者也不是完全的“无谓的牺牲者”。当时的这位热情的青少年诗人,还是保有一定的“自我”“自由”与“独立的思想”;虽然也搀和着一定的轻信、受骗、乃至被“规训”。就在“找灵魂”之后不数年,燕祥先生说:“什么是知识分子,我以为读书人中,只要认为精神价值超过物质追求的,就应该是知识分子。”且更说:“60年的主要感受,应该说是‘言为心声’。写诗第一位是‘心声’,第二位是‘言’。心应当是真心,心声应当是真诚的。”[8]17应当衷心赞同:“历经几十载的社会变迁,岁月轮转,‘秉笔直书’四个字始终是邵燕祥文学生涯的注脚。”[9]
1976年10月,1978年12月,中国政局的高空,频频电闪雷鸣。邵燕祥这羽涅槃中的诗之火凤凰,最为敏锐,抢先冲天而起。他在《诗刊》1978年9月号发表了写于1月的《中国又有了诗歌》。《人民文学》1979年第1期发表了他的《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198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假如生活重新开头》。《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正好跟早年的《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相呼应。且更“与刚刚开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暗合,发表之后有一些影响”[8]18。而在《假如生活重新开头》[1]81-82,复活的诗人宣告:“假如生活重新开头,/我的旅伴,我的朋友——/还要唱那永远唱不完的歌,/在喉管没有被割断的时候。/该欢呼的欢呼,该诅咒的诅咒!”“时间啊,时间不会倒流,/生活却能重新开头。/莫说失去的很多,/我的旅伴,我的朋友——/明天比昨天更长久!”
1978年11月,邵燕祥由广播文工团调入《诗刊》编辑部工作,先任编辑部主任,1981年起任副主编,至1984年秋辞去编务。当时有关于朦胧诗的论争与批判,邵燕祥是力挺朦胧诗的。并在1981年3月号《诗刊》发表了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因而和某副主编“后来合作不愉快,所以在1984年提出辞职”。当回忆这段经历时,他说:“我进入《诗刊》时有两个心愿,一是帮助一些老诗人重新在《诗刊》亮相,经过几年时间大家差不多都亮相了;二是希望牺牲自己的一些创作时间,能够推一些青年诗人出来。这两点在借助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大家一起努力做到了,加上大部分编辑理念与我接近,所以我向文联领导唐达成提出了辞职。”[10]
此后,邵燕祥先生的诗歌创作意气风发地特秀倔强地走着自己的路。“我不属于文学上的什么主义,什么流派,什么诗歌团体。”[11]他的新诗日益从娇丽蔷薇走向高挺青松。他将苦难中最忠贞的友情尤其是爱情化成《空气》[12]25-26:“星光因你而闪烁/波光因你而摇曳/我的质朴到透明的朋友/你无所不在/又难寻踪迹。”这开头一节真将“我的质朴到透明的朋友”写得惟妙惟肖。随后四节历数各种境况而不离不弃,乃有末节:“踪迹难寻又无所不在/厮守身边却默无一语/影子会有离开的时候/你从不离开我,我也不离开你/永不分离,永不分离,到最后一息。”这种诗是决不能用墨汁写成的。燕祥诗的视野宽广。组诗《河西走廊:一次匆匆的旅行》共九首,其中《兰新公路》[12]121-123云:
天地何寥廓!//这是一条古道/又是一条新路//铺路人过去了/架线人过去了/走向天地交接处//天闭着嘴/地闭着嘴//天地何肃穆!/在雪山里彷徨/从野马滩越出//悲壮的西路军/染红祁连山中的白雪/染红黄尘滚滚的沙丘//天也不哭/地也不哭//这里严关鸟不飞/这里平沙不落雁//千里长云横落在/万年的戈壁荒原/等待着一束思想的闪电//天俯着头/地仰着脸//天地何莽莽!//时间无限,空间无限,是谁/曾经补天倾,曾经追赶太阳//不是在前人脚印上踏步/这是需要巨人的时代/这是需要巨人的地方//天又苍苍/地又茫茫
透过这寥廓天地、古道新路、追日补天、时代脚印、无限时空,我们感触到的是诗人胸怀的苍莽与坦荡。诗人写过《美国野花这样说》[12]212-213:
为什么不让我们开七彩的花
到处剪成清一色的绿地
剪成一模一样的平头,像排队的
囚犯,列兵,孤儿院的孩子?
我们羡慕那野生的乔木
一千棵树有一千种身姿
无论凌空擎起油绿的树伞
托起鸟巢,但是捧出一树红叶
都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屹立着
发言,沉默,自由地呼吸
剪平我们,只是为了践踏我们
或者坐着,躺着,打滚,抛球
野餐,并且逗引你们心爱的狗
也在我们的身上跑来跑去
你们相信有权无视我们的权利
就因为你们从来没听过野花的抗议?
而且不承认我们是花
仿佛一千种花都没有自己的名字
你们称我们为草,草坪属于你家或他家
忘记了花是野花,草是野草,我们从来都是野生的
当“草坪属于你家或他家”“到处剪成清一色的绿地”在所不免。
值得大书的是“做一个大写的或者说真正的人,是邵燕祥感应于我们时代的全部诗歌的总主题,且老而弥坚”[13]552。真诗人坚持“从主体的真情实感出发。只有真情作美之升华才是真诗”[13]550。于是,这位追求人的自由、尊严与美的清新朗健的本真诗人再三再四地发问、呼吁。在长诗《长城》中提:“天地间/只是一个问题:/作人/还是作奴隶?”[1]408在小诗《哈姆莱特》说:“是人?是畜类?/这还是一个问题。”[12]142而散文诗《布谷鸟》[1]144则唱:
羽毛被突来的风雨淋湿了……布谷鸟,依然向春天唱着沥血的歌。
假如生活背叛了你,你不要背叛自己。
于是又有了《人》[12]173-174:
让我来回答/这千古疑难的问题:/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原来宇宙只是一个/浑圆的蛋壳/盘古如同一鸡雏/羽毛还未丰满/羽毛逐渐丰满//生命在跃动/他伸开臂膀//挺直膝盖/叉腿站起/他挥臂,他顿足,他要呼吸/打碎蛋壳/擘开这混沌的一团//雷鸣一声/电闪一炬/轻清者上升为天/重浊者下沉为地//蛋壳破裂的一瞬/人的史册/才在宇宙间屹立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14]标志邵燕祥先生一生诗创作高峰的是作于花甲之后的一大组诗与二首长诗。大组诗《五十弦》共55首。有题记两则:“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李商隐”;“忽忆及当年/所有之女子……——曹雪芹”。后来又在一文中说明:“实际上也不全是写爱情的,爱情啊,友情啊,都有,虽然题记里引了曹雪芹的‘忽忆及当年所有之女子……’,但拒绝索隐派。”[8]19这是邵燕祥一生最抒情的诗作了。在情、思、美、诗的交合上,也是最“朦胧”的了。且随机读上几首吧。先看《第二首》:“曾经 少年时/全都不知珍惜/一次回眸 一次凝睇/一阵沉默 一阵笑语/一回欢聚 一回别离/当时说成是插曲//人生如歌/随早潮和晚潮退去/最值得追忆的/是再也听不到的插曲/被风声吹散的断句/被星光点亮的秘密/还有渐行渐远的/被春雪融尽了的足迹。”[1]251这正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15]1354的现代版。再看《第十首》:“不自由的地方才是我的祖国/可恨这古老的咒语/在失去了一切的自由以后/我是幸福的 因为/我还能自由地想你//你的一切不幸/都是我的缘故/我仅有的幸福:/为你祝福。”[1]258这当是为忆及“下放”跟着社员劳动而分离的妻子亦因而受难时所作。其爱情的忠贞、心境之悲凉,几令人不堪卒读。再读《第四十一首》[1]284-285:
那一次/在秋天/草色还是青青的/邂逅清清湖水边/草未凋 湖水照见/你还穿着单薄的衣衫/互道珍重 相约记住/这个秋天 秋天的青草湖边//那个秋天/我们还是少年/初践那青青的草岸/初涉那清清的水湾/我们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天很高地很阔道路很远/天涯何处没有芳草/何处没有湖水清涟//那个秋天/谁也没有想到/纵然异地的春草年年泛青/陌生的流水也有熟悉的涟漪/不会再有同一方青草了/不会再有同一湾湖水了/不会再有那青草湖边/同一个新相知的秋天//水已流逝 草已凋谢/没有重逢的生离就是死别
相信是诗人一次“新相知”香甜偶遇的实录,惜乎留下的是终身的痛憾。
《北纬30°线》[16]这首200多行的长诗,确证邵燕祥先生是“愈老愈发金石之声的诗人”[17]。此诗以“一说北纬30°线/想到的是神秘/更是灾难”开头,结尾是“75岁的邵燕祥/不准备传播可怕的谶言/只是要疾呼 天地间/灾难正在临近//他相信/可以预言的灾难不是灾难//没有预言/而灾难来了//此时此刻/诗已没有意义”。中间是一些独立成诗的片段。诸如:
哦/新奥尔良!/厄尔尼诺是圣婴的名字/上帝该有许多圣婴/那给新奥尔良带来灾难的/圣婴一定不是/从上海的暴雨中升空的/那一个//究竟是上帝还是魔鬼/命令它带着那一股冥冥中的力量/带着使百慕大三角区扑朔迷离吞噬舟船/使柏拉图描绘的美丽岛国一夕失踪/使自贡成群的恐龙灭绝/使绿洲成为大沙漠/使火山灰埋没生活/使天地颠倒 使木乃伊逃出墓穴/使灾难成为灾难……/的咒语 挟着狂风暴雨如海啸登陆/洪水滔滔 连夜叩门
等等。此诗行文颇具意识流意味,曲折散漫,开阔宏远。其要旨:“只是要疾呼 天地间/灾难正在临近!”而在十余年后的今天,从汶川大地震至当今的全球性的新冠肺炎,在在皆在证实这首激情与沉思交融、抽象艺术与意象艺术并驰的大气而重厚的大诗关戚人类的预言。
《扬子江诗刊》2011年第11期同时重载邵燕祥最佳长诗《最后的独白——剧诗片段,关于斯大林的妻子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之死》[1]441-466,与新发唐晓渡精彩论文《娜佳:最后的绝望和最后的救赎——读邵燕祥长诗〈最后的独白〉》[18]。当我们面对这两个文本,实际上是面对着斯大林与娜佳、娜佳与邵燕祥、邵燕祥与唐晓渡这三对史与诗的纠缠和阐释。谁在作《最后的独白》?是400行长诗中女主角斯大林的于1932年十月革命节之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里开枪自杀的妻子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是让她在剧诗中永远复活的诗人邵燕祥;也是对此诗作了深切解读的评论家唐晓渡。娜佳说:“我是谁?我是你的妻子?主妇?/朋友?伴侣?抑或只是你麾下的/千百万士兵和所众里的一个?//你曾把耳朵贴在俄罗斯大地上,/连簌簌的草长都能听见,/但我相信你早已/听不见近在身边的/我的心跳的声音。”娜佳说:“不要人们知道我的姓名,/不做奥林匹斯山上的第一夫人;/不是土耳其后宫的女奴,/也不是挂在别人脖子上的女人;/也许能忍受没有爱情的家庭,/但不能做不受尊重的人。”娜佳说:“我终归是丑小鸭,终我一生/唱不出一句天鹅之歌。/我无力埋葬一个时代,/只能是时代埋葬我。”终于到了终场:“你竟敢吆喝:/嗨,你,喝一杯!/我憎恨你/像你憎恨世界。//就是最柔弱的花蕾/也不在粗暴的叱令下开放。”“如果是上帝决定我的命运,你就是上帝。/如果是魔鬼决定我的命运,你就是魔鬼。/无论你是上帝还是魔鬼,/我第一次不再听命运的决定。”“我走了。/我走我自己的路。”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阶级斗争理论是有机整体,因而更为深广地体现着历史的本质本体。鄙视治下一切人为零的暴君同样被历史异化为非人。被异化为“第一夫人”“女奴”的娜佳,则因为人的自由与尊严以死抗争而成真正的人。而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一个不期望历史理解的/三十一岁的俄罗斯女人的魂灵/在人海里发现了寻找她的眼睛”,这双眼睛属于杰出的中国诗人邵燕祥。在这双诗的慧目的观照下,这位为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9]而英勇牺牲的俄罗斯女人复活了,成为诗化的圣女。这是杰出诗人诗美创造的胜利。而评论家唐晓渡亦正是抓住这一点,给出了自己丰富、精彩而独到的论证与阐释。他说:“自由的灵魂——这是娜佳最初的,也是最后的身份。正是这一身份使‘我是谁’的质询同时也是回答,使‘最后的救赎’同时也是,并且只能是自我救赎。据此娜佳通过选择死亡而拒绝了死亡,与此同时也拒绝了虚无。”他更独到地说:“《最后的独白》中诗人对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表现出如此深刻的理解和同情(本义的同情),以至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灵魂而言,或许娜佳正是诗人的前世,而诗人正是娜佳的今生。”诗人在剧诗中创造了本真的自己。
三、追随鲁迅臻于具体而微
邵燕祥先生之所以是百年中国新诗的经典诗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追随鲁迅先生全面而臻于迫近的高度。首先是人格,精神品格;同时是文学创作,新诗、旧诗、杂文、散文,各方面都在学习鲁迅、追随鲁迅。虽尚有间而未至,亦令我辈学习鲁迅先生者赞叹而景仰。实际上,少年邵燕祥一开手便诗歌、散文、杂文、时诗等都写,后来也写过小说、儿童诗、唱词、剧本、诗论,一向是多面手。只是本质上是新诗人。1964年以后,他写旧体诗词多起来了。出过《三家诗》(与杨宪益、黄苗子旧体诗合集)和《邵燕祥诗抄·打油诗》。并被赞为“亦庄亦谐,借古讽今,声东击西,指桑骂槐,再沉重的话题,都举重若轻,别开生面”,并与杨、黄同称“打油大家”[20]。自 1986 年以来,他出了杂文随笔集 46本,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全部诗集20本的一倍多,而且亦曾自叹:“近年来,不止一个朋友对我说:你的杂文比诗好;又说:你的旧体诗比新诗好。我理解这是含蓄地说我的新诗写得不好吧。”[21]其实,这正是燕祥老师追随鲁迅全人升堂入室,无论新诗、旧诗、杂文,尤其是精神品格,皆已臻于“具体而微”[22]。
复出以后的邵燕祥先生,在奋力文学创作的同时,做了一件对于有良心的正直知识分子非常有意义的要事,便是“找灵魂”,切实反思自己幸与不幸的坎坷一生。他在18年中,接连出版了1996年的《沉船》,1997年的《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2004年的《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2004年的《〈找灵魂〉补遗》,2014年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他活生生地解剖了几乎自身的一生及其所处的社会境况,找到了更塑造了自己学习追随鲁迅的崇高灵魂。于是,他写新诗、写旧诗、写杂文、写随笔,皆能得心应手,皆能相互渗透,促发,相得益彰。他的随笔自选集《捕捉那蝴蝶》出版于1993年,他的《杂文自选集》出版于1996年。他的三本诗选:《中国当代诗丛——邵燕祥自选集》出版于1993年;《邵燕祥诗选》出版于1994年;《邵燕祥诗选(1988—2010)》出版于2011年。而作为他新诗的巅峰之作的《最后的独白》则首发于1988年2月的《中国诗人》。
诗人邵燕祥虽谦称自己的旧体诗为“打油”,实则找不到半点“打油”气。他是新、旧诗一体对待的。他说:“我总是比较被动的等待诗来找我。如果找我来的是新诗,我就写新诗,旧体诗来找我的时候,就写旧体诗。”而且“新诗和旧体诗互相间不可替代”[8]20。他认为:“倘写旧体诗,就该是真正的旧体诗,认真遵守在古代汉语基础上形成相当完备精严的格律,以及有关的规范。”[23]但他在古体完备精严的格律中充以新思想、新语言而挥洒自如,十分难得。请看《咏鸡——干校节日聚餐有鸡》:“荡气回肠不自哀,依稀灯火下楼台。岂知今日刀头菜,曾叫千门万户开。”[24]请再读《悼吴祖光》[25]:
满怀忧愤满头霜,大丈夫谁吴祖光。
堪佩立言兼立德,忝居同案胜同窗。
无心旁骛争民主,生正逢时忆国殇。
风雨凄其从此去,令人长忆二流堂。
仅此一绝一律,足显真诗人律严思深而诗味隽永的力作。
邵燕祥先生杂文,鲁迅风甚炽,却充满新时代的气息。在他洋洋40多本杂文随笔集中,以其对于社会人生的深知,以广博学问为基底的沉思,挥洒诗人的彩笔,成就了一位睿智思想家的业绩与造像。有些短章简直是散文诗。例如《成家之路》[26]:
一个猎人,打死了虎豹,却并不因而成为虎豹。
一个渔夫,刺中了鲸鱼,却并不因而成为鲸鱼。
文场中的渔猎手,杀伤了一个以至一群作家或诗人,就会因而成为作家或诗人么?
燕祥的文与诗往往打成一篇。可以将《说“看客心理”》与《“见死不救”考》与《中国多看客》合在一起读。署上“一九八六年九月三十日于爱荷华”的《“说看客心理”》[27]说:“喜欢‘看热闹’,哪里有热闹就凑上去围观,表面上看似乎跟‘一人向隅,满座不欢’的落落寡合不同,其实是比‘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还坏的心理。”“而看热闹,却不仅是置身事外,袖手旁观,还透着某种兴致,某种满足,使鲁迅年轻时不堪忍受,终于弃医从文,以行疗救国民性的病态为己任的一幕,就是他在电影上看到的,中国人被绑赴刑场砍头,周围竟有那么多中国人做看客所表现出来的麻木。”“而围观‘大团圆’的看客们,我以为比阿Q更阿Q,这就是断子绝孙的阿Q终于并未断子绝孙的缘故。”写于1987年1月11日的《中国多看客》[12]216云:
看云。看月。/看灯。看雪。/看花。看叶。/云有散。月有缺。/雪有化。灯有灭。/叶有凋。花有谢。/看蹓鸟。看游街。/看出殡。看出嫁。/看车祸。看打架。/看劁猪宰羊。看杀人流血。/看不尽的风光。看不尽的热闹。/中国多看客。/看客归去也!
写于1987年9月11日的《“见死不救”考》开头说:“成都一个初中女生在游泳场溺水,围观者四五十人,见死不救,直到眼看她灭顶,这件事被称为‘张歆黔事件’,引起议论纷纷。”在作了一些说明与论议之后,便引用上引这首诗。接着是“岂止麻木而已”与“何必厚责于这四五十个围观者”的辨析与议论;最后如是作结:“多有勇敢的、勤劳的、智慧的个体,才形成勇敢、勤劳的、智慧的民族。然而要怎样消除怯懦、懒惰、愚昧的温床呢?怎样才能使关于精神文明话题不致沦为一句空话?”这是一颗激烈跳动着的热爱中华民族及其广大民众的拳拳之心呵!
燕祥老师寿濒九秩的一生,从稚嫩无畏的风雨鸟到涅槃更生的火凤凰,一贯崇敬鲁迅,学习鲁迅,步趋鲁迅,老而弥坚,乃臻于当代鲁迅的具体而微。最令人尊崇的是他高尚坚贞、独立自在的人格。他愈老愈信奉以人为本、人民至上,脊梁梗直为灵魂的本真。他的日益经典化的艺术高超的新旧体诗,广识多智的杂文随笔,正是其本真灵魂自然盛发的花果。
燕祥老师安然恬然走了。留给百代的后来者的悲悼追思,最好是化作对其杰出诗文的重读,重读,永远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