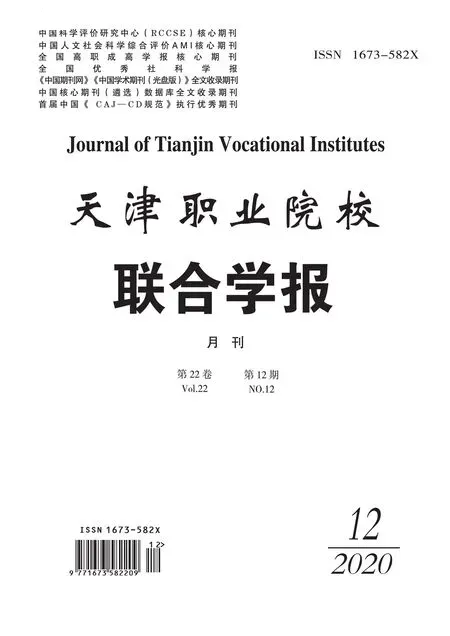论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内涵
张红柳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天津 300350)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是社会的动物,只有在社会共同体之内,人才能真正成为人。实际上,在希腊城邦时代,便有“城邦之外,非神即兽”的说法。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也随之发生着变化,这也表现为社会共同体的形式演变中。近年来,在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中,社会共同体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的词汇,我们首先梳理多学科视角下的“社会共同体”的内涵及其不足,然后通过考察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相关成果,构造一个考察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内涵与意义的理论坐标。
一、多学科视角下的“共同体”内涵及其不足
一般来说,政治学视角中对“社会共同体”的考察,侧重从政治利益出发,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政治学卷”中,对政治共同体是这样规定的:“政治共同体又称政治社区,是西方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指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公认的政治机构和特定的居住区域的人们所构成的社会集合体。政治共同体与其他社会共同体的区别在于,它以共同体成员的政治利益共识为基础,并且拥有共同的政治机构。政治共同体与一般的政治团体的区别主要在于政治共同体的成员通常拥有特定的居住区域。”对共同体的这种规定,特别是对作为一种共同体形式的“国家”的规定,显然是基于经济利益的立场。但事实上,人与人之间除了经济利益关系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关系,如互赠或互酬关系、亲情与友情关系。因此,除了“国家”这种众所共知的共同体形式之外,肯定还存在着其他形式的关系。从这个意义说,政治学视角中的共同体研究还只是以“国家”这种特殊的共同体形式为典范之下的探讨,理论未免狭窄,我们需要拓展共同体研究的视域。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社会共同体首先在于对于社会类型与分层的研究,如区分社会的狩猎与采取的社会、畜牧的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最有名的是滕尼斯对“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区分。在滕尼斯的区分中,前者指的是传统社会,这种社会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后者指的是现代法理社会,亦称为交往社会,指的是人们的行为主要受契约或者法律的约束,因此,社会具有很强的异质性。这个意义对社会共同体的规定与研究视角,具有非常明显的精细与实证特征,但在理论层次上,却有待进一步的提升与抽象。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共同体形式,这些共同体形式有待在更高的的层次上予以抽象,且共同体形式相互之间的演变逻辑,不能停留在社会学意义的材料收集与分析上,而需要哲学意义的构造与提炼。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哲学卷”中对“社会共同体”是这样规定的:“社会共同体是人类历史上形成的由共同生活中某种纽带联结起来的稳定的人群集合体,亦称人群共同体。包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家庭,以共同的经济生活、居住地域、语言和文化心理素质为纽带形成的民族等。”这个规定既揭示了社会共同体是以某种纽带联系起来的人群集合体,同时还揭示了家庭、民族、国家与世界范围内的人群共同体的演变形态。但是,仅仅从生产方式的视角,还是无法全面展示社会共同体的内在特征与丰富内涵,因为就家庭与民族这些共同体形式来说,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或者生产关系的演变,都没有直接关系:在生产力比较低的历史阶段存在,但是在发达的社会形态依然存在。从这个意义说,社会共同体的形式与社会生产方式之间并不存在某种精确的“映射”与刚性的“匹配”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说,需要我们超越既存的关于社会共同体的规定视角,进而重新确立一个研究社会共同体的理论坐标。
二、柄谷行人对“共同体”的区分
日本著名学者柄谷行人在《世界史的构造》中,以“交换样式”为视角,区分了四种社会共同体形式:民族、国家、资本、联合体,并试图通过四种共同体间的关联,以重新构造世界体系,并在此体系中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这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共同体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我们可以参照柄谷行人的区分,按照“社会共同体”中联系纽带的不同,区分五种“社会共同体”的形式:
第一种是以“赠与—回馈”为纽带的互酬类型,主要存在于原始社会的“氏族(民族)”中,这是一种基于友好、互惠关系的交往形式。这种“氏族共同体”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基本的社会单位。但是,自从产生之后,这种共同体形式就没有、也绝不会消失,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柄谷行人认为,“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了从属的关系了。”这个形式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本,也是最具有生命力的交往形式。
第二种是以“强制—服从”为纽带的支配类型。这种共同体形式始于一个共同体对另一个共同体的掠夺。但是强制本身并不能持久,因此便出现了某种相对服从的形式。这便是“国家”的原型。虽然国家通过强制性实现了暴力的垄断,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国家只是基于单纯的暴力,而是说,国家通过禁止国家以外的私人暴力,而使得服从者免受暴力的威胁,从而获得统治的正当性。对于被支配者来说,当服从意味着可以得到安全和稳定的时候,那么,接受这样一个强制型国家的存在便是最有的选择的。柄谷行人对国家共同体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第三种是以“信仰—救赎”为纽带的共同体形式,表现为某种普世宗教的共同体。这种社会共同体集中表现于中世纪的神权政治中。在中世纪时期,宗教这种共同体形式甚至取得了超越世俗国家的地位。因此我们将这种宗教的共同体也视为社会共同体的一种形式。这一点明显与柄谷行人的理解不同。
第四种是以“货币—商品”为纽带的共同体形式。这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共同体形式。而货币便成为了最核心的元素。因为货币持有者不用诉诸暴力的强制,且具有“可以抵换一切”的抵押权,因此,就可以获得他人的生产物(商品)或者他人的劳动。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共同体形式。
第五种是“社会主义—联合体”的形式,即超越“民族”、“国家”与“资本”、“宗教”等共同体的全新的共同体形式。柄谷行人认为,这种形式有点类似于向“赠与—互馈”形式的共同体的回归,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貌似而已。在思想史上,这种形式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同体主义”。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五种共同体形式是从历史上抽象并提炼出来的五种典型形态。如果说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共同体都直接或者间接包含了所有这些样式,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的不同只是在于其中的主导形式的不同:在氏族社会中,互酬性的交换样式占据主导形式,但是绝不意味着国家、战争与商品贸易的不存在;在以国家占据主导的社会形态中,民族、氏族的共同体依然存在;在宗教占据主导的社会形态中,国家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资本占据主导的社会中,民族国家与宗教等依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在社会主义的理想形态中,并不是否认以上四种共同体形式的存在,而是意味着,个体能够摆脱这些共同体的局囿与限制,真正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形式。但问题是,柄谷行人没有给“宗教共同体”这样一种重要的共同体形式予以足够重视,而这种形式在西方社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他将“民族共同体形式”的“回归”当作人类共同体发展的最终目标,错失了马克思所主张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深刻意蕴。正是基于这些缺陷,相对于柄谷行人所提出的“四分法”,我们构造了五种共同体的形式,然后以这五种形式的区分与演进作为理解“社会共同体”的大致框架,进而以此作为揭示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之深刻内涵的基本概念坐标。
三、重新把握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的内涵
如上所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但其他的共同体形式并没有消失,而只是产生了变形。柄谷行人以“资本—民族—国家”这个三位一体的圆环来表征资本主义社会中“共同体”的复合关系。在他看来,三者以“资本”为圆心,结成一个圆环:“资本、民族与国家乃是彼此不同的东西,分别基于相异的原理,但是在这里,它们以相互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缺一不可、环环相扣的连环。”柄谷行人所提出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确立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如果说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宗教、国家与民族被视为相对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按照柄谷行人的区分,三者却取得了与资本同等意义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位置。这是因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国家、民族与宗教类似,都是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同时,一旦出现,便无法消除它们的存在。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集中探讨的,只是商品的生产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而将国家与民族、宗教等视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予以“悬隔”处理。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要实现对资本的超越,就必须将这些被“悬隔”的因素“还原”到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去,即在其中思考国家、民族与宗教与商品生产之间的关系,以在更高的层次上批判这种社会关系,这也是我们所区分的第五种社会共同体形式,即社会主义—联合体的可能形态,并以之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坐标的原因所在。
于是,相对于柄谷行人所区分的“资本—民族—国家”的三位一体的形式,我们可以构造“民族—国家—宗教—资本”的四位一体的形式,作为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所针对的对象,并以此显示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的内涵。根本原因在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以“资本—民族—国家—宗教”的四位一体的圆环予以表征。如果缺乏对“民族-国家-宗教-资本”这些共同体形式的界分及其相互关联方式的规定,那么,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的理论背景及其主张,而会导致思想上的混乱。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四位一体的圆环形式,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所主导下的社会现实,在这种社会现实中,国家、民族、宗教与资本一样,实际上还是同时并存着,并没有根本上消失,只是在资本的主导下改变了存在的形式。因此,我们总结与阐发的四种不同形式的共同体,并不是完全消失在资本的主导场域中,而是在资本的主导下,呈现了不同的形态,并没有否认其存在的独立性。正是由于忽视这个独立性,导致了思想上的很多误区。如有人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集中展开的是“资本”而不是“国家”,认为“国家”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便将“国家”视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实现统治的手段,而根本上就不承认“国家”的相对独立性。在他们看来,如果通过阶级斗争,消解了阶级对立,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也必然会自动消亡。正是因为这样,为了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掌握权力,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上所论,由于“国家”与“民族”、“宗教”一样,作为共同体的形式,是人类生活中的产物,并且一旦产生出来,就不可能迅速消失,而是呈现出一种独立性的存在形式。从这个意义说,重新反思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必然要求从更为宽广的思路展开,而不应该局限在某种单一的视角之内。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氏族(民族)、国家、宗教与资本(市民社会)、社会主义五种社会共同体形式的区分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结成的“资本-民族-宗教-国家”四位一体的圆环,考察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出场路径与可能意义。由于这个圆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成型并且相互扭结,使得四种社会共同体形式之间的差异很难清晰地分辨出来,我们对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的考察,正是建立在对这个圆环中各个社会共同体形式的一般形式及其特殊构造形式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大大地推进了社会研究的视角与方法,至今依然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