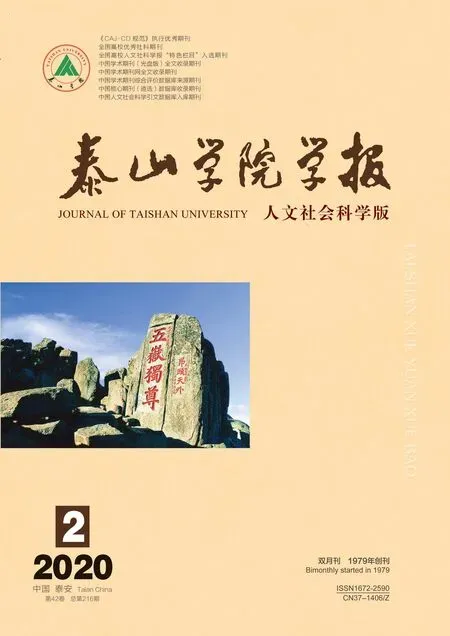在梦与醒的边缘飞翔:范玮小说的审美理念
张 鹏
(泰山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山东 泰安 271021)
一、引言
齐鲁新锐作家范玮在小说中建构了文学的审美理念,他在真实与梦幻、写实与虚构、现实与理想之间飞翔,营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文学空间和想象世界。范玮像一棵乔木立足于丰厚的生活大地并汲取一切现实主义的养分,他又参透了虚实结合的文学秘诀,用想象和梦境弥补了现实生活的粗粝和坚硬。他珍惜生活实感,更知道好的小说是飞翔的现实和舞蹈的想象。他的小说中那种“虚实相生”的叙述空间和人物脸谱是融会贯通的,是“梦幻现实主义”的完美展示,亦真亦幻的遐思迩想和激情憧憬,凸显出他别开生面的智慧、性情和才具。
二、梦与醒的边缘:亦真亦幻的叙述空间
范玮就他的小说中充满梦想与现实的结合时曾自道:“到目前为止,已经由多位评论家指出,我的小说充满梦与现实的结合。我只是觉得小说就应该这样写,这样写比较顺手。梦是愿望的达成,梦是潜意识的信使,有人说人生就是一个梦,只是我们一直在做,无法醒来,还有人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梦,所追逐的一切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幻影,不可控制,无法理解。小说发言的地带,正是由现实通往梦想的这一段儿,我觉得我碰巧走对了路,能不能走远,要看以后的造化”。
范玮绝大多数的小说都建构了一个亦真亦幻的梦境,这与中国当代其他作家相比而言,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精神印记。范玮的小说没有直接来自新闻报道一样的现实土壤,他总是立足于中国当代社会而又能超越现实的桎梏。他的小说总是在梦与醒的边缘追求一种心理现实、精神现实和逻辑现实。这种现实导致他的小说阅读者很难在具体的社会事件和新闻背景中去坐实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
范玮用《刺青》这部短篇小说作为他的短篇小说集的书名,至少说明他自己是把《刺青》作为他的小说的精神浓缩和思维路标的。《刺青》塑造的就是一个亦真亦幻的文学想象空间。虚拟的魔幻的“乌山”如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村、福克纳笔下的杰弗生镇一样,在富有象征意义和地标意味的精神家园里包含着无尽的乡土情怀,活跃其间的人物形象的语言特色、行动路径、思维模式都已经超出了日常生活的墨守成规,而渐渐抵达了梦幻和虚构的世界。著名青年评论家赵月斌说:“从孟村到桃镇,从《像鱼一样飞》到《乡村催眠师》,小说家范玮变得愈来愈可怕,他破茧而出,并没有化蛹为蝶,而是变成了一只会飞的老虎:他吞食着巨大的梦想,在索然的天空下,优雅地,翱翔”。诚哉斯言,范玮小说的化境厚积薄发,如虎添翼,必将再上层楼。
“被那个腰身看起来象苏小耳的漂亮女人一路牵引,蔡小筐迷迷糊糊地跟进了咖啡店,喧嚣的市声被厚厚的玻璃门悄然隔断。……那些光心满意足地躲在薄薄的羊皮里面,柔和地亮着,音乐和光线让咖啡店弥漫出一些辽远和神秘的气息。”[1]《刺青》小说中的主人公蔡小筐就是在这种鬼使神差力量的魅惑下粉墨登场的。咖啡店的音乐和光线所焕发出的是完全陌生的辽远神秘的世界意象。人物所处的空间被写得云山雾罩,如在梦寐中。这种陌生化的环境描写,隔开了日常生活的烟火气和流行色,让人物在自己的精神逻辑中是其所是。
除此之外,范玮还建构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乌托邦般的“乌山”世界。在“乌山”的虚构版图中,每个人物形象都生活在一种不可确定的虚化中。蔡大款、蔡小罗、苏耳等人在苏文医生反反复复建构和编造的美丽流言蜚语和精致谎言中不可自拔,他们终其一生欲罢不能沉迷其间。
乌山不仅有各种各样的传奇人物,如巫婆、游医、风水先生、神汉、疑难杂症、刺青、纹身,就连咖啡馆的女服务生也因失血过多而成为几乎透明的女人,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特异功能和敏锐感官,她能嗅出各种气味、秘密甚至来客的职业、性格和前世今生。苏医生所编织的故事不仅使蔡小筐父子等乌山人深信不疑,就连自己的女儿也沉溺其中乐而忘返。苏医生编撰的大英雄雷大鼓在苏小耳的心灵中根深蒂固:“一股热辣辣的力量突然注入了自己的身体里,她顿时觉得自己的骨骼变硬,内心充满力量。英雄雷大鼓就像种子一样迈进了内心,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种新的力量转化成了向往和爱慕,苏小耳的内心全是雷大鼓,没有留一点地方给其他任何男人。”[2]最终,苏小耳爱慕追随的雷大鼓的劣迹晓白天下,他其实是一个胆小如鼠、偷鸡摸狗的小偷,至此,高大挺拔的英雄形象轰然倒塌。作为故事的始作俑者苏医生自己也遭到报应,他在故事的结尾罹患了一种歇斯底里的怪病,疼痛一旦发作就经常头昏脑涨、头疼欲裂。当树叶子纷纷落下时,苏文医生也不治身亡、溘然长逝了。范玮借苏医生谎言的破灭,揭示了一种精神乌托邦的毁灭,也揭示了“卡利玛斯效应”最终沦为笑谈的祛魅过程。
小说《乡村催眠师》则以小林医生会运用一种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催眠术让文本的迷宫叙述直接进入一个亦真亦幻、变化多端而又不可捉摸的“超级世界”之中,搭建起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迥异的叙事空间。小林医生神奇的催眠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他脱口而出任意言说之后能够仅靠晃动的手指,就能让他的患者迷迷糊糊进入梦境之中,然后患者会情不自禁地把心底的隐私和秘密毫不保留地和盘讲出来。这个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如同一阵风在桃镇荡漾开来,第二天,“沉寂多时的桃镇像桃花沟白色薄冰底下有点发暗的河水蠢蠢欲动起来,桃镇人的耳朵里满是尖利的一夜风声之后苍白空洞的耳鸣,他们手足无措地站在被大风刮得干干净净的大街上,目光飘忽漫无目的,偶尔打量相互像在看着一出哑剧”。[3]
范玮将小说的发生地建立在一个虚构的地名——桃镇,这是范玮的精神血地和成长母本,也是我们的精神“失乐园”,这里没有风起云涌的革命叙事,没有社会运动的波澜起伏,有的只是一地鸡毛、生老病死、春夏秋冬的生活细节和世俗碎片。评论家石华鹏说:“范玮的小说岛与李安影像中的狐獴岛①李安导演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的一个岛屿。有着惊人的相似处:绚烂多姿如梦幻之地,远离现实又处处都是现实,人人神往又惊奇恐惧万分,是人类内心一角的陌生高地。”[4]范玮将这看做是评论家对自己的褒奖,更愿意看做是一种期许,他期望能够写出更多这样的小说来实现自己的文学想象梦想。
三、飞翔的现实:现实主义的飞升与腾跃
范玮是一个思想犀利的小说家,他对现实苦难饱含同情和悲悯。他的小说总是从世道人心中那些微妙的印记入手,以富有警觉意味和飞越现实粗粝表层的叙事,生动地讲述一个“乌山”“桃阵”“孟村”的啼笑皆非的人生戏剧。他所塑造的那些躁动不安的小人物,在艰难维持生存的同时,不约而同地都走向了自闭和寂寥。他关怀这种苦难所导致的生命悲剧,又不断赋予这种悲剧以人性和历史的诠释。
范玮的中篇小说《太平》便是一篇颇能彰显他现实主义理念的代表性小说。小说叙述了一个“我”和自己的女上司小白的故事,伴随着“我俩”故事的是有关太平这个虚构地方的故事。“我”最终因为向小白讲述自己失踪4天的传奇经历而赢得了她的爱情。小白耐心聆听“我”有关太平的故事,这个故事主要讲了“我”的父亲好友于勒的死。“我”像福尔摩斯一样探寻于勒的死因,分别借助了警察、赌徒、六姑、胖老头、疯子青年等人的追忆,完成了这个曲折离奇的故事。没有真相,只有对真相的不断求索,这是范玮持守的真相观。
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的叙述,在不断地恢复往事的真面目,他们分别从自己的感官和心灵,描述消失在历史深处的真相。范玮的小说《东野湖》主题是逃离故乡和家庭。小说分别写了安红、贾丰收对家庭的逃离和司忠之、小莲、小鱼对故乡的逃离。每一个人物的逃离,都是从一座城堡进入另一个城堡,自由却远在天边。这让人想起了《围城》,也想起了卡夫卡的《诉讼》以及《变形记》。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东野湖》暗示了人类的漂泊无根,他们不乏盲目的冲动行为,只是使得自己从一个深坑爬出来继续跳到另一个深坑,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人生行动和言语的碎片化,弥散在小说的叙述经线上,使之迥异于经典现实主义的线性叙述。
短篇小说《孟村的比赛》更是一个关于男性征服女性梦想的隐喻。小说主要写了苏有和孟二起两个男人进行的一场养猪比赛,比赛的结果关乎一个叫麦小小的女人。孟二起以猎物征服这个女性,苏有则拼命养猪克敌制胜。二人的博弈过程堪称“红颜梦”的外化。中篇小说《出故乡记》的开篇是这样的:“本来,故事应该是这样开场的,十一年前,有一个叫李唐的人无缘无故离开故乡。在李武举村人的记忆中,那是一个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的日子,当时日光浓烈,村里的乘凉的人看见李唐走进了白花花的日光下,曾经有一只狗冲着他慢腾腾的背影不耐烦地叫了一声,伴随这声狗叫,李唐消失在日光深处。从此这个叫李唐的人杳无音讯。李唐出走的时候,儿子李敦敦刚刚四岁。这一度让当初目睹李唐离开的人有了错觉,那白花花的日光背面,好像是一望无际的黑暗,李唐的身影就那么晃了一下,消失在了黑暗之中。但,对于这个事件的另一个主角李敦敦本人来说,故事却是十一年之后,他在一个夜晚推开院门开始的”。[5]多重虚拟的故事开首,最终引领我们进入了中国历史上从故乡逃离,去异乡颠沛流离的话语空间。那些无头苍蝇一样在人海中盲流的逃离者,在乡愁萦绕心间的同时,也度过了无数个“几回魂梦与君同”的暗夜。元宝的出走与归来,只是在城市的五光十色的梦乡中陡增了噩梦般的记忆,摆脱不掉记忆的纠葛,最终她选择了自我了断。李唐融入了城市,他用暴力与颟顸与城市这匹恶狼一起载歌载舞。
范玮用一支生花妙笔,写尽了人性的种种变异,既有城乡文化的合力打造与形塑,也有自身身世和情感逻辑的畸变。在高歌猛进的城市化、城镇化进程中,实现由“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的发展转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立足于古老的农耕文明,这使得城市化最终导致了城市与农村更剧烈的撕裂、对立和隔阂。在范玮的中篇小说《出故乡记》中,农村文明融入城市文明的遥遥无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李武举村迄今仍把“不进城”作为祖训,可是,强势的城市文明无孔不入,乡村的溃败在劫难逃。城与乡的夹缝中,是彷徨于无地的“城非城、乡非乡”的过渡时期的国民。有些作家是追求优雅、精致、细腻和纤柔的,范玮显然不属这种,他的风格是饱满粗犷而有表现力的,无论是叙事的复杂性,还是小说人物命运起伏的波澜横生,都能大气沉稳。尤其是他的小说中富有魔幻色彩的心灵岛屿,为他的人物在其中挣扎、呼号、抗争、爱恋和仇恨提供了一个极富妥帖感的背景和舞台。
范玮的小说写作真正超越和深化了现实主义。他善于把潜在的性格冲突转化成叙事动力,把直面原生态经验的勇气解读为自我暗示。他的叙述语言迂回舒展,充满哲思,他对生活的看法跃然纸上,而且能将游戏的精神和想象的快意熔于一炉。他发扬光大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小说写作的魔幻现实主义作风。他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生存的内在悖论,把鸡毛蒜皮的小事写得蔚为大观。他的小说真实地面对了一个城乡结合部及其延伸的飞地丰盛的情感景观、嬉笑怒骂的恣情显露、压抑的内心以及不为人知的嫉妒和暗自发力。他对生活肌理的条分缕析,为这个纷繁芜杂的世界留下了一批毫无修饰的灵魂个案。范玮小说的出现,将有力地开启中国当代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的新局。
四、语言的魅惑与迷津:思维路径及其表达习惯
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实现。小说艺术魅力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是语言。作为一个小说作家,范玮的语言是圆熟、明亮、大气而富有贯穿力的。他的小说语言瓷实浑厚,平中见奇,饱满而到位,融汇了人情美、哲思美和色彩美。他的小说语言,栩栩如生,写人状物惟妙惟肖。他的小说语言具有别开生面的艺术魅力,范玮喜欢用五光十色的色彩语言表达丰富的主观感受。善于打破语言的既定窠臼,自出机轴,耳目一新;范玮的语言叙述风格或诗意勃发,或浓墨重彩,或活色生香,或雅俗共赏,或波澜起伏。
一位作家用哪种文体风格和叙事技巧写作,他就遵循了这种语言内部的语音、词汇、文辞的逻辑结构规律,理所当然地他的表情达意也与语言风格相得益彰,这样就构成了作家的文体风格和思维惯性同他所使用的那种语言内部文理的贯穿性、一致性和相互推出性。同时由于作家的个人履历、人生经验、个性禀赋、心理动因、文学追求以及所处的时代、地域等方面的迥异,自然也会显示出与众不同、独具个性特色的语言惯性风格。
在《会飞的鱼》中,这段文字堪称绝唱:“在波光粼粼的赵牛河上,有一条鱼儿长着翅膀,在水面上飞翔。鱼儿的头是英俊少年黑孩的头像。赵牛河上有两条飞翔的鱼儿,一条是黑孩,一条是伊莲娜。黑孩展开双臂在前头飞,伊莲娜展开双臂在后边跟。美丽的伊莲娜飞翔得那么好看,像一条真正的会飞的鱼。”[6]这样栩栩如生、凌虚蹈空的诗意般的描述,富有奇幻色彩的想像空间,非常符合评论家张丽军教授所谓:“正是在这样一种浪漫主义审美匮乏的时代精神状况中,山东70后作家范玮从最初的文学探索中,逐渐开拓出一种属于自己的魔幻性审美写作,为新世纪山东文学、中国文学的艺术探索与审美创新带来了新的可能性”。[7]
在《老元和老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戏未开始,不省事的孩子,便趴在台边,撩着幕布向里望。有个男孩扭头冲台下说,爹,我看见啦!底下纷纷问看见啥了?男孩说看见老马娘娘的大奶子啦!底下便是一阵笑。老马是队长老田的女人,老田听了也笑,又骂道,你个王八羔子,真操蛋!民兵连长李大海握着一根木棍跑上台去,把那些孩子轰走,棍子指着台下,说,都把孩子看紧了,什么奶子不奶子!底下笑得更响……”[8]这段文字透露出一种土里土气的乡村口语气息,也唯有这样的土得掉渣的俚俗夹杂的语言,方可道出乡村戏场开演前的纷乱和喜气。他的小说文字,是全身心投入进去的,每一个器官仿佛都是敏感而敞开的,所以在范玮的小说中,可以读到很多的声音、颜色、光线、气味,以及各种幻化的肢体感觉,充满勃勃生机,有趣味和喧嚣的声浪并且目之所触色彩斑斓。就感官的丰富性和语言的鲜活性而言,范玮在70后作家中的确是出类拔萃的。我们经常说当代文学的面貌过于单调沉闷,原因就是作家的感官没有进入写作现场。小说若只有情节的建构,而没有声响、色彩、气味,没有日常用度、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致的描写,听不到和看不到鸟语花香就会显得干瘪乏味。
语言既是一种表达工具,也是一种哲学符码。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流派之一就是语言哲学流派,文学最重要的革新和嬗变也是关于语言的革新与嬗变。中篇小说《太平》中有一段文字最见范玮的现场描写功力:“张映红一脚踏进裁缝铺,就看到太平的五六个大男人坐在里面,他们每个人都捧着一个大搪瓷茶杯,坐在裁缝铺里吹牛,消散着男人过剩的精力,两间屋大小的空间被他们搞得热气腾腾,不像个裁缝铺,倒是有点儿像包子铺。太平镇的裁缝,那个叫马莲花的人从里间走了出来,她烫着头,穿着粉红色的旗袍,脚上趿拉着拖鞋,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奇怪的气息,既颓废又张扬,既慵懒又风泼。张映红装作来看布料,马莲花就跟她一一介绍,涤卡、腈纶、锦纶、平绒、的确良、白府绸、乔其纱……布料放在靠墙的一个大橱子里,马莲花来来回回地拿着布料,坐在两条凳子上的男人,就乘其不意地去摸她,马莲花笑得咯咯响,她扭动着柔软的腰肢,灵巧地躲闪着,马莲花在她的裁缝铺穿梭,她走得真像一朵莲花,弄得周围的空气像水一样荡漾”。[9]这段文字把一个裁缝铺的纷乱与喧嚷写得让人如身历其境一般鲜活。各色人等的衣着打扮,店铺内的布料陈设,女性妖艳的腰肢,男人放肆的笑声荡漾眼前,一览无余。范玮的文字细腻纯熟,表面松散,内里紧张,貌似不经意,但风格浑厚鲜明。他所整饬的生活阅历,充满同代人的聚焦和共鸣,那幅沧桑的面孔背后,照见的也是个体面对复杂世相的无力。人生只是不断的偶然和碎片,内心业已粗粝和决绝,生之悲壮与死之凄惨,纯真和污秽,面对这种新的青春记忆,绝望处寻觅归途,向生命的躁动要求洁净的灵魂。
五、结语
范玮有一种写作的终极目标,一种掌控一代人成长和思考的心路历程的自信。他的小说,建基于自我所见所闻,但也不忘反观这代人的心路历程里有多少是被时代和历史的瓶颈所制约和塑造。在这种历史冲突和道德伦理突围里,爱与梦,伤害与顾虑,饶恕与记恨,孤独与温情,美与幻灭,交相呼应,此起彼伏。范玮正带着70年代人的记忆和思索,为一种更壮阔的人生回望做好了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