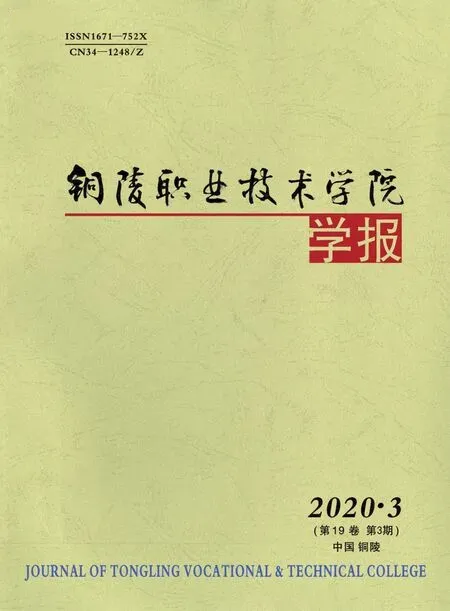文化的符码 审美的意象
——论第五代导演电影视觉意象的运用
朱斌峰
(铜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安徽 铜陵 244000)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社会生活变革带来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意识的嬗变,中国探索电影在银幕上纷纷涌现,一批被称作“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人登上舞台,走出国门,屡屡折桂,形成新潮。他们大多是1982年以后陆续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摄影系、美术系的学生,集结了包括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张军钊、黄建新等艺术群落。他们在电影创作上以崭新的文化观念、审美旨趣、创作风格集体崛起,以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反思,对传统电影观念产生了冲击,可以说是推动了一场电影影像的革命。
从《黄土地》中雄浑凝重的黄土高原,恍若时间老人在诉说着民族的沧桑与新生;到《青春祭》中四季长青的山水,呈现婉丽清新的民族风情,召唤蓬勃的青春意识的觉醒;从《良家妇女》中的石头符码,舒缓地奏响沉朴淡远的女性命运的挽歌;到《一个和八个》中的造型反差,在民族存亡关头唱响撼人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赞歌……第五代导演大多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和审美自觉,以新的观察生活的视角和电影语言,挖掘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呈现出“开风气之先”的影像风貌。他们的作品大多以造型叙事取代情节叙事,具有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赋予了中国电影新的质素,提升了中国电影的文化品格。
从第五代导演起,中国电影开始自觉追求声画表意功能和影像美学,对意象的选择和加工是其重要体现之一。下面,本文将以四部电影作品为例,从情感化表意、符号化象征、仪式化场域、意蕴化隐喻四个层面,对第五代导演视觉意象的运用作一管窥:
一、以视觉的意象实现表意的转换
电影是一门讲故事的艺术,其通过视听进行叙事,塑造人物,讲述故事。同时,电影也是造型艺术,它可以通过视听造型手段,实现表意功能。其中,优秀的电影视觉造型不仅对叙事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能够以表意、象征和隐喻,带给观众以美好的艺术享受,更直接决定了影片的影像风格和风格化艺术风貌。
在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中,从叙事功能向表意功能的转换,是电影视觉语言运用的观念嬗变和手法创新。他们将影像从叙事元素中超拔出来,把叙事元素还原为造型手段,让视觉符号成为一一种艺术符码,不仅对剧作的故事推进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表达和传播着情感、思想、文化信息。正是这种表意功能的强化,以暗示、指代、象征和隐喻的方式,启发观众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获得故事层面之外的情感、认知和审美的满足。其中,视觉意象化,就是其中的一种视觉表意形态。在电影创作中,叙事的纪实性、故事性与表意的深刻性、多义性,似乎是一组此消彼涨的对立元。毛琦在《中国电视电影的叙事规则与文化特征》一文中说:“但这一关系一旦被引入电视电影中就必然做一些调整,如何讲述一段能引人入胜的好故事成为电视电影的新标准,相反影像的象征和隐喻作用则在情节的强化中被相应地淡化甚至是舍弃了”——这即是对这组关系的描述,而影像的象征和隐喻则与视觉意象无不关系[1]。第五代导演注重视觉的意象化,这是他们从传统电影中“突围的利器”,也是形成艺术风格的路径。
意象,在中国传统艺术的绘画、雕刻、戏曲、诗歌中频频出现,它是主观之“意”与客观之“象”的融合,内心情感与外界景象的统一,是中国人审美的传统图式。电影的视觉意象,是通过色彩、影调、镜头及蒙太奇组合技巧,传递情感、精神和文化的内涵,从而达成意境。这种意象造型如夏洐所说,“介于具象造型和抽象造型之间,不脱离描写对象的固有形质,又力图加以超越,以表达主体的主观感受和寄寓主体的意绪为美学原则。”[2]应该说,这种视觉意象是他们电影美感和思想的独特体现。第五代导演正是继承中国美学传统,从诗词歌赋、绘画雕塑、园林艺术中汲取营养,以现代性的电影镜头,找到了一种新的视觉表达方式——这是第五代电影的审美走向之一。
二、以构图的形式营构情感的张力
“形式即内容”,第五代导演在电影视听上往往有着风格化、极致化的表达,他们电影意象具有造型意识,在画面构图、色彩、光影和镜头运动上,以着意渲染或突出夸张乃至近乎变形的处理,传达一种浓烈的情绪基调。张军钊执导的《一个和八个》揭开了第五代导演的序幕,这部作品造型感强,在构图、色彩、画面上力求反差性张力。这是一部根据郭小川长诗改编的电影,演绎的是不同人物在特殊环境下从对峙到凝聚的抗战传奇,故事情节的因果链条并不突显,却以造型思维把诗的意象化为电影的意象。
电影《一个和八个》的主角是一个共产党员和三个土匪、三个逃兵、一个奸细、一个投毒犯,就是“一个正义”和“八个邪恶”的对峙,他们置于同一囚禁的境遇中,在先进与落后、正义与背叛、勇敢与懦弱中泾渭分明地对立着,最后却唱响了共同抗争的强音。为强化这种对立,影片在环境的造型上,呈现出空间的局促感和精神上的挤压感。其内景无论是闭塞的烤烟房,还是铁桶般的砖窑;无论是结实的碾盘,还是封闭的古堡,都呈现出出狭小、黑暗、封闭的压抑感;外景中无论是荒寂的旷野还是横斜的铁路线,无论是村边草垛,还是路外斜坡,都光秃没有半点绿色,给人毫无生机的感觉。内景外景的不完整、不平衡构图,色调简单而纯粹,构成了精神抗争的环境张力。导演张军钊在电影完成台本的摄影注中说:“用版画般的黑白对比,来表现雕塑般的沉重和力度。全片的色彩基调,突出黑、白二字,要力求用最简单的色彩要素做最完善的表现,强调这种力之美……考虑到影片强烈、深沉、浑厚、悲壮的基调,全片以静止的镜头为主。我们企图用强烈有力的静态画面,造成固定与变化、静止与动态、对此与层次的雕塑般的力度美”[3]。这种压缩的空间处理,正是参人物精神层面灵魂的搏斗的可视化表达。
此外,在人物的造型上,剪影式的肖像包含着身份、思想、道德、人性的寓意。电影中,大秃子牺牲的场景即极具造型的冲击力:他半跪在地上,单手挥舞长枪在大笑:“痛快!”一颗炮弹炸响,黑烟弥漫整个画面,可片刻他居然从黑烟中钻了出来,满面是血地站立着仍在高喊。又一颗炮弹咋响,黑烟再次把他吞没。接下来是大全景的静穆画面,没有任何声响,黑烟慢慢飘散,大地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大地无声,情感的抒发被推至大情境。由上可见,本片将意象化的造型作为影片表情达意的元素,从不完整构图到完整构图,从色彩蒙太奇到情绪结构线,实现了情绪结构和情感基调的风格化呈现。
三、以符号的能指传递主旨的内涵
“所指与能指”,第五代导演在电影视听上往往有着符号化的寓指,以视听形象表征传统文化的符号,将中国传统文化具象化,实现了从所指到能指的表达,丰富了作品主旨的内涵。黄健中导演的《良家妇女》符号化特征更是明显,该片叙述的是解放前黔北山区世代相传的“大媳妇、小丈夫”的畸形婚配习俗故事,对传统女性的命运进行了反思。片头浮雕叠印古象形文字“女”字,恍若跪在地上两手扶地的妇女,就是对中国传统妇女命运的观照。而结尾“生育”的浮雕、“裹足”的浮雕、“踩碓”的浮雕、“嫁女”的浮雕、“沉塘”的浮出、“哭丧”的浮雕……更是传统妇女一生具象化的陈述。导演在电影完成本中对“古老原始的求偶、生殖图”是这样注释的:“这一组镜头里古老的崖壁画是求子一场戏同一意念在疯女人和杏仙身上的表现。崖壁画在这里是一种象征。”[3]410而影片中,以石路、石墙、石房子为环境造型主要元素,让人物生活在冰冷的环境中;五娘房里的那张古老而永不停息的织布机,仿佛传统女性命运的流转。而影片设置雾中时隐时现、站在山崖唱歌的疯女人,她曾经因为偷情要被沉潭而发疯。她的多次出现,并没有叙事功能,只具有象征功能——是中国传统妇女受迫害的命运象征,是传统女性异化的符号。
与文化符号的压抑相反,影片中却有着优美自然的风景,那逶迤秀丽的山峦、奔涌飞溅的瀑布、婉曲延伸的山道……似乎每一座山、每一条小溪、每一段山路都有着浓郁的诗意——这为影片染上了一种纯朴柔美的情调。其中,与文化符号基调相反的是来自大自然的视觉符码“飞瀑”。电影中多次出现飞流而下的瀑布,不仅揭示和衬托出人物命运、精神状态和隐秘心理,而且仿佛是一股股清流,对压在传统妇女身上的污垢进行冲击和洗涤;当杏仙给前来拉犁的开炳送饭时,背景中的“飞瀑”,似乎是爱的泉水流淌;当杏仙心爱开炳而不能,得知按照族规男女私通要绑石沉入飞瀑下的深塘时,她心事重重地站在飞瀑下,那“飞瀑”恍若她心底翻滚的波澜。结尾,当觉醒的杏仙离开时,三嫂在飞瀑前痛斥杏仙,却久等杏仙不至。她站在巨大的飞瀑下,身影孤零而渺小,而那“飞瀑”仿佛是时代的潮流飞泻而来,那也是人性和人道的呼唤……《良家妇女》充满大量的象征性视觉符号,以高度凝练而富有潜在的方式来表达影片的意义。影片在文化符号“岩石”和自然符号“飞瀑”的交织下,使得作品主旨不仅得以强化,而且丰富起来。
四、以造型的仪式抵达精神的场域
仪式是集体精神的场域和仪轨。第五代导演往往以色彩、构图等构建仪式感的事件和环境,让饱满的情感和精神的飞扬起来。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讲述了“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九儿的故事。九儿19岁时被许配给十八里坡烧酒作坊的老板,但在回门路上被余占鳌拉人高粱地“野合”。后来烧酒作坊老板被人杀死,九儿和余占鳌撑起了烧酒作坊。当日兵前来青杀口烧杀抢掠时,九儿搬出当年酿的十八里红给伙计们喝,大家斗志昂扬完成了与日寇的殊死搏斗。影片中,高粱地是贯穿全片的符号化意象,前部中迎亲的颠轿、仪式般地释放出被压抑的野性生命力。而片尾在日兵屠杀下,女主人公和酒坊伙计以燃烧高粱的仪式化场面,完成了最后的反抗,彰显出红高粱的子民们狂野的战斗精神。
影片中,九儿与余占鳌的野合场面就很具场域的象征意味。九儿被余占鳌抱着钻入高粱地,两旁急速滑过的高粱,银幕上出现了一片热烈兴奋、疯狂摆动的高粱,在殷红似血的阳光下大幅度摆动。随后,在郁郁葱葱的高粱地里,余占鳌踏倒的高粱形成一片圆形的祭坛。在画面的中间,九儿横卧在圆形的祭坛里,余占鳌跪倒在九儿脚下,被四周风中晃动的高粱掩映着。那种圆形的野合地与传统婚俗“圆房”一样有着仪式感,两人在高天厚土中,在汪洋的高粱地缓缓倒下,谱写出一曲自由狂放的生命颂歌。红高粱的随风狂舞取代了直接的男欢女爱的场面,而九儿的红色衣服象征着热烈狂放的情欲,摇摆着的高粱寓指着原始欲望的爆发。由此,这个场景以象征隐喻的方式,把狂热的激情含蓄地表达出来,也召唤出爱的觉醒和人性的解放。原来“偷情”是伤风败俗的行为,而这种仪式化的处理方式,却是对追求自由奔放的爱情的礼赞。
《红高粱》结尾的“日食”同样具有仪式感:在日兵的侵袭下,大片大片的高粱倒了下去,火红的高粱酒洒落一地,熊熊的大火燃烧了日本军车,落日的余晖和鲜红的高粱地仿佛在燃烧。“我奶奶”九儿死于日兵的炮火中,悲壮地倒在血泊里。此时“日食”不期而至,整个世界变成了红色,染红了御敌战场,染红了高粱地,染红了天地。那血红的高粱酒、满天的火焰、短暂日全食过后火红的太阳、还有那一朵朵鲜血染出的生命之花,呈现出一种壮美的意境,仪式般地唤起了观众心底的悲壮。这种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呼唤中华民族激扬昂奋的民族精神。那红高粱时而肆意跳跃,时而热烈躁动,时而悲愤凝重,并与血红的太阳、血红的天空与漫天飞舞的高粱并置在一起,不仅形成强烈的视觉印象和情感冲击力,而且表现出浓烈的地域文化精神气息,舒展出旺盛的民族生命活力。
五、以影像的隐喻寓指文化的意蕴
“有意味的形式”,第五代导演在电影视听上往往以意象为喻体,指向丰富性、多义性的文化意蕴。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期间,文艺工作者顾青从延安到山区采风,寄宿贫苦农家。此时,农家的女儿翠巧因生活所迫,与一个年龄比她大很多的男人订了娃娃亲。而顾青带来的新生活信息,让翠巧萌发了新的憧憬,最终逃出夫家,夜渡黄河投奔八路军。影片仅把故事当作线索,却通过超时空的视觉意象,以非情节、非人物的造型元素,表现了陕西高原古朴、苍凉、深厚的民风,表达了创作者对民族文化和农民命运的思考。那广阔天垠的黄土地、气势磅礴的黄河,那鼓乐齐鸣的迎亲队伍、烈日炎炎下的腰鼓阵和求雨场面,无不内蕴文化的深意。影片就是以造型和隐喻、抒情和哲理的相融,绘就了以土地、民俗文化与人物的三者统一的隐喻性画面。
影片中,广袤无垠、苍凉沉雄的黄土地是哺育我们民族的高天厚土:那深沟大塬仿佛是中华民族的年轮,在静穆的时光中,成了历史长河中民族文化的表征;那渗透传统重负的祈雨仪式中,一群庄稼汉跪在久旱龟裂的大地上乞求上苍,宛若民族生存的岁月造型;那婚宴上的木鱼、窑洞门上用碗底沾上墨印的黑圈对联,有着贫瘠的苍凉……这些画面和意象有着凝滞感,是中华传统文化厚重、封闭的隐喻式表达。而凝聚民族伟力的腰鼓舞又显示出巨大动能,仿佛是古老大地奔涌出炽热的岩浆,孕育着黄河儿女的憧憬和强盛的生命力。影片中,导演对传统文化的宏观性理解,以某种抽象、变形和象征的色彩,构成了象征性的影像体系。它采用蒙太奇和长镜头的结合、蒙太奇组合和写意性构图的交融,达到了根植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艺术效果。那人格化的黄土高原形象,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情感,浓墨重彩地寓意着中华民族性格的双重性,既有对民族文化中的隐忍、落后、愚昧、自足的揭露,也有对充沛的民族生命力的礼赞。“黄土地”就是传统文化和心理的图式、民族历史和民族精神变迁的仪规,它强烈地表现出世代生活、繁衍在黄土地上的人们的麻木和奋进的交织图景,召唤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生生不已的文化精神。
电影作为跨文化交流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视觉意象传播拓展了跨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第五代导演一度走出国门,冲向世界,成了中国电影人中最值得骄傲的群体,其中中国传统文化意象的表达功不可没。他们的电影在造型意象方面的 “标新立异”,不仅是通过影像讲述故事,更是借助对影像的意象化呈现,让观众感受视觉艺术之美,形成对情感、精神、文化等内容的体察和理解。他们运用各具形态和特色的视听意象,承载时代价值观念、审美新质素和电影功能的新观念,形成了新的艺术风貌,完成了电影美学的拓进,开创了中国电影美学影像美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