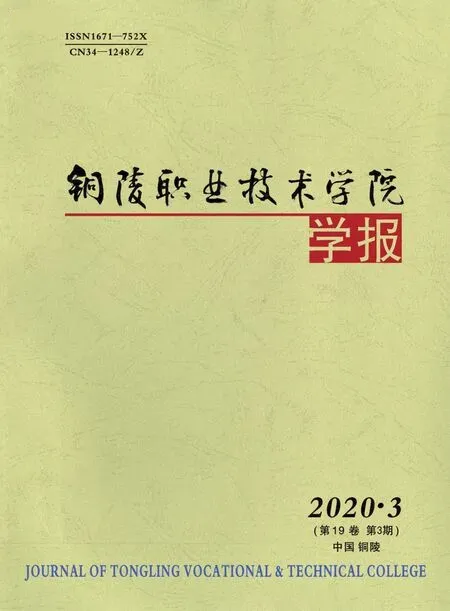清同治增辑本《浮山志》所见法产文书
刘旭冬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志者,史之一体也,国有史,山亦有志。山志之修纂历史可谓久远,中国最早山志可追溯至先秦《山海经》。[1]明清时期是山志修纂的黄金时期,诞生了诸多优秀山志,《浮山志》于此时期多次修纂。浮山,明以前无志可考,山志之修纂肇始于明末,明清两代共修纂山志三次,其分别为明末胡瓒版、清康熙吴道新版以及清同治增辑本山志。由于战乱等原因,前两个版本山志俱佚失,清同治增辑本为明清浮山山志仅存于世之版本。清同治增辑本《浮山志》是桐城地方文人吴康弼等增补辑佚前代山志所出。吴康弼,字仲甫,号樵山,桐城南乡人(今属铜陵市枞阳县)。太平天国时期,兵乱波及桐城,吴康弼避乱浮山十载,得康熙吴道新版《浮山志》之残卷,在此基础上加以增补,并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付梓,是为清同治增辑本《浮山志》。法产文书,即为明清时期浮山山寺合法产业之文书,是历代《浮山志》精华所在,集于清同治增辑本山志之中,流传至今。
一、法产文书概述
《浮山志》,作为方志的一种,据有方志的共性价值。方志是保存社会史料的渊蔽,那里面的丰富记载,是在其他史籍中不能看到的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2]可见清同治增辑本《浮山志》是极具研究价值的珍贵文献资料。《浮山志》承载大量极具价值的法产文书,这些文书围绕浮山山寺法产变化而产生。明清两代所修的三本山志沿袭抄录当时浮山山寺所藏文书,汇集于各版本山志之中,今仅存于清同治增辑本《浮山志》。若按性质划分可分为民间契约文书、地方官府文书。其中民间契约文书包含田契合约22篇,如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华严山老契》、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新置田契》等;另有捐田碑记2篇,即康熙四十年(1701年)《浮山华严寺普同塔院钱氏施田碑记》、雍正元年(1723年)《钱氏捐田碑记》。地方官府文书5篇,其包含审语、执照等,如天启五年(1625年)《张公观音两岩执照》,此皆系地方官府调解纠纷、保境安民之举。
山志所载法产文书所及年代肇始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结束于清雍正元年,法产文书记录了浮山180多年的风土人情,殊为珍贵。由于山志之法产文书是抄录所得,故山志所载文书非第一手史料,此殊为可惜,但山志所载法产文书仍对研究明清时期浮山地区的土地所有权变化、地方民众的经济生活和法制生活、地方治理等方面提供珍贵的研究史料,通过对山志所载法产文书的耙疏整理,亦可对明清时期全国民众的经济生活、法制生活以及政府治理等方面窥见一二。
二、法产文书所见山寺法产变化及地方民众经济生活
不同于西方的土地制度,中国封建时期土地制度下的土地交易发达且历史悠久,土地交易的发展不可避免产生大量相关的土地契约文书。据现存史料,自宋代起已有了土地契约法权的书面形式的存在。[3]明清时期是中国契约文书发展的特殊时期,无论是契约文书的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历代之巅峰,契约文书的规范也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
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契约通常被称为 “质剂”“判书”“书契”“约契”等,而现今各地发现的契约文书,大都以“卖契”“典契”“合同”“分书”“文约”等为名。[4]浮山山寺所藏民间契约文书内容范围广泛,其中包括田契、树契、施贴和合同等。浮山山寺之法产历史悠久远,据山志载:
相传远公说法时,周十余里山场田地俱为浮渡恒产。[5]269
自元迄明,屡遭倾废,雁堂鹿苑,如乌衣燕子,飞人寻常百姓之家。华严寺隶谢氏,圮其址封马鬣矣,会圣隶施氏,金谷隶胡氏。我佛僧伽黎裂作片片水田,供俗人镈笠,残炉断火,仅一二粥饭衲保。金谷石龛,霤滴下即异姓,践则辄呵,何论樵苏瓯脱?祖庭之荡覆,至此极矣![5]1
可以看出,明以前浮山山寺具有一定的法产;自元迄明之时山寺衰落,法产几乎尽失。所以,浮山土地所有权变化主要表现为山寺对原法产的收复与扩大。山志所载民间契约文书最早出现时期为明嘉靖年间,此时期山寺法产之具体范围,今日已不得知,但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明神宗皇帝颁旨,令山民将所侵占山寺之法产皆还于山寺。此时安庆府同知林仰、桐城县正堂徐勘断云:
《志》(此志非山志)载周围五里,东至华严寺前湖边止;南至夹桅石、醉翁岩、芝[之]子[字]冈,直下石塘冈、连云峡;西至棋盘石,横过丹丘岩下人行路止杉木颈;北至天池下茶窊、马鞍窊、纸蓬窊、祈雨坛、抱龙峰、佛子岭止。[5]269又云:
迩来世道凋丧,恒产不多。……仅存田种拾肆担,载亩柒拾叁亩五分,此卖主虚加六担称二十数也,故载亩亦多。[5]269
据此可以管窥明嘉靖年间及此时(万历二十五年)山寺之法产范围,其名义为20担,实则为14担,可见山寺法产不多属实。三年后庚子编审,山寺法产又有新的变动,具体如下:
其田:北至抱龙峰脚;东至牛屎窊山脚;南至胡田,以高茅埂为界;西至鲍家冈、本寺白虎山脚。其山:东从佛子岭分水至胡宅后龙山顶,下清水塘边石墙为界,又从清水塘边石墙(为界),以高松树至牛屎窊胡宅晒场止;南从鲍家冈高树石墙至胡尔秀屋后山脊、本寺茶园止;西从茶园石墙高树(以)起至妙高峰烟墩分水为界;北自烟墩(以起)分水,从如来峰石墙至金谷岩前小塘边引路松,依界石上抱龙峰分水为界,止佛子岭。[5]269-270
对比三年前,可以看出此时(万历二十八年)山寺的法产范围是有很大变化,然其实际差田面积却是怪异地缩小了,此时志云“豁去二十二亩,实当差田五十一亩三分五厘”,即万历二十五年有14担田,约56亩(按1担田换算4亩为计),而二十八年仅存五十一亩。至于为何“豁去二十二亩”,志书并未提及。笔者认为,山志仅记载其差田面积大小,并未言及此时法产包含的林地具体亩数,可能其差田面积变小,而林地面积增大,此亦符合浮山山地之面貌。山寺法产最后一次有明确范围记载是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其具体如下:
华严寺田种二十担,坐落本寺前田屏。……
金谷岩田种九担五斗,坐落华严寺右首。……
会圣岩田种壹十一担肆斗,坐落浮山河东。……
……
醉翁岩田种五斗,坐落上汤庄。……[5]293
此系官方所授山寺法产执照,可信度较高。对比万历年间山寺法产大小,其范围是有所变化的,且明显扩大了。单就田产而言,此时山寺名下约有41担田,即164亩田,比之万历二十五年田产大小,此时山寺田产扩大了近3倍,增加较为明显。
山寺法产面积在明清时期是不断变化的,其法产变化来源较多,笔者根据山志所载法产文书进行归纳,将其变化来源划分为如下三种:
其一,就部分不明地界,山寺与山民协约划分。如顺治九年(1652年)所立《华严金谷山界约》载:
藏之指明,今因彼此山界历年既久互有出人,以致辨论不一,请凭本山诸檀及在山耆旧议定。金谷之右,以如来峰分水,直下石懒墙为界;左以抱龙峰古松直下封墩,至人行路傍株树,并新勒石字为界。……自定之后,各遵各界,以全寺岩体面。倘不如约,无论佛祖不容,即王法亦不宥矣!恐后无凭,立此合同,永远为照。
顺治九年肆月二拾四日立。[5]282
由于年代久远,致使山界渐侵而不清,山寺与有关山民重新议定山界,各遵各界,并立合同为据。
其二,民众施舍与交换田地产。施舍田产如雍正元年所立《钱氏捐田碑记》载:
浮山大华严寺乃桐邑古利也。……先叔讳最仍,……与嫡配吴孺人,随鸿阁皈依三宝信奉维度。因年老艰于嗣息,夫妇发愿,于康熙五十年三月间,将价买王又雍庄田一所,坐落上钱家桥大慈阁地方,计种一十六担,以一半布施常住,凭亲友写立捐契,付方丈宗六师,永作斋僧佛田。……
雍正元年仲秋月谷旦。[5]272
由上可知当地百姓谢氏老夫妇皈依三宝后,捐献田产以供养僧佛,其可见民众信仰之诚心,又见山寺法产之来源。交换田地产如万历二十八年《更换合同》所云:
胡烛同男嘉言、侄嘉临等,今因自己田种一处,载新丈折实亩田、地、塘共八亩六分整,坐落金谷岩、抱龙峰下,四至俱连僧业,系僧面孔之地,烛不便管业。且僧镇晓所买谢宅随田草山,又坐落烛住宅右,系烛肘腋之地,僧亦不便管业。烛同男、侄与晓大众商议,情愿将岩前田种、基地、屋垣,只除宅后已连数坟新立罗围近界不卖外,不遗寸土尺木,厘卧浼中胡遹泽、吴兑屏等,更换僧买草山一片,四至界塅照僧契载,各取便宜管业。……其抱龙峰下,烛旧有在招坟二冢已凭公踏,上以大石顶为界,下以石墙埂为界,东西各以蝉翼沙脊为界。……
万历贰十八年庚子三月初七日立。[5]271
由于山民田产与山寺法产相连,山民与山僧皆不便各管其业,由此山民与山僧更换田产明确界限,使之便宜管业。
其三,山寺购买田地产。如万历二十八年《华严山田契》载:
谢申恩、谢琼选、谢天恩有祭田壹十四担,载亩七十三亩五分,坐落地名浮山。……至万历贰十六年,有僧人镇晓等欲建寺宇,见得基内葬坟兴工不便,彼此状赴抚按。科道批送府县亲临踏勘,见得坟存则寺废、寺建则坟伤,公断将身[谢]祖坟二家俱行迁起另葬,断令镇晓募缘承买,依老契四至管业。当日公议田价纹银贰百两整,其田地、山场、树木、屋宇俱听镇晓照契管业,不与谢人相干。……
万历二十八年二月初七日。[5]270
山僧欲建寺宇,因地基内有山民老坟而不便兴工,山僧诉之于府县,府县令山寺募缘承买山民老坟之地产。立卖后,山民领钱迁坟另葬,山寺照契管业并再建寺宇。其他诸如 《华严老契》、《买界址大枫树契》等民间契约大抵如此产生,此不再一一叙述。此为山寺法产来源之最重要部分,山志所载、山寺所藏民间契约文书多为山寺购买田产所产生。
本文所列民间契约文书仅为浮山山寺与山民土地交易记载的冰山一角,更多的民间契约文书覆灭于历史之长河中,殊为可惜。通过对这些民间契约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可以看出明清时期浮山地区的土地交易是十分发达和完善的,从此亦可管窥明清时期地方的土地制度与地方民众经济生活:其一,明清时期的土地具有私有性质,作为私有财产其所有权是不断变化的,这是大量民间契约文书产生的直接原因;其二,总的来说,土地交易往往使土地集中,买主地产增加而平民田产渐失,这无疑加剧了土地兼并;其三,民间契约文书本身作为一种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具有法权行为,体现了地方民众经济生活中的法律意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契约文书是中国历史变迁最生动的载体,是传统中国社会人们日常经济生活最真实的写照。[6]
三、法产文书所见地方民众法制生活与地方治理
在古代中国,地方民众在参与经济生活中会产生大量的经济纠纷,因此地方民众往往会求助于司法机构(主要是地方官府)来解决问题。由于土地交易中一方的失信和违约,或出于地方官府对民众私有财产的保护,由此出现了大量的围绕民间契约纠纷而产生的地方官方文书。山志所载的地方官方文书可分类为以下两种:
其一,地方官府颁发土地执照,作为对民众私有财产的保护。如天启五年《张公观音两岩执照》载:
具词浮山张公岩僧海洪等,为恳赏执照以便捧据以护道场事。浮山原系远祖香火,后遭居民蚕食,幸蒙诸位老爷护持、众乡尊协赞,于万历三十四年批送本府二太爷林□按临踏看,将张公、观音两岩立有界址分明,赏有执照。……
天启五年八月贰十日告,执照僧海洪、海源。
县批:山既方吴复舍施,人敢有所侵,许僧人执照禀告,依律坐罪。[5]278
由上可知,浮山山民违约侵占山寺土地,致使山寺法产受损,山寺诉之于公堂之上,幸赖地方官府主持正义,划清两岩地界,并颁发官方执照以示司法保护。
其二,土地纠纷打官司,地方官府审案并立下审语判词。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庐江县正堂吴审语》所云:
审得霍之庆乃已故霍赤明即霍可信之侄也,可信年老无子,皈依浮山华严寺山足和尚,于康熙二十二年将自置(产业),坐落本县天光山,田种四担并山场、水塘立契施舍入寺,其契俱载《浮山志》内。……之庆忽将契内山地卖与吕任弘,遂冒称继可信嗣,诬告华严寺僧归六“折[拆]庵毁佛,占茔绝祀”,情词极其迫切,及至庭讯佥供,建庵曾有其说,山足永寂中止。今之草房尚可信旧物,坟墓二处亦岿然无恙。之庆因盗卖惧僧告理,为此先发制人之术。岂知众口难掩听断无私,固不能曲为之庇乎!法应责惩。……吕任弘所执之庆卖契当堂涂抹,之庆已得山价七两差押清完,取吕任弘领状一并附卷存案。
康熙三十七年八月初九日给。[5]275
霍可信年老无子,皈依于浮山华严寺,并将其部分田产施舍与华严寺。其侄霍赤明将已属山寺之田产变卖于他人,并冒充霍可信之子先发诬告于华严寺。地方官府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最终判霍之庆卖契无效,并归还其不当所得。无疑,普通民众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底层,将纠纷诉诸于府衙(即打官司)是其保障自身利益的主要措施,而地方官府对于民间土地官司的协调与裁判也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地方民众的合法权益。
发达的封建地方经济生活必然需要完善的司法作保障,地方官府在此充当了保障人、协约人和执法者角色,地方官府文书是地方民众法制生活的体现。同时,地方官府通过对民间契约的保障和对地方经济纠纷的协调,缓和了地方民众之间矛盾,也表明地方官府一直是积极有为地治理地方,其实质是维护了封建统治。清同治增辑本《浮山志》所载法产文书中的地方官府文书部分恰如其分地展现了这些,为今人研究明清浮山地方乃至全国民众法制生活与地方治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四、结语
中国的文书从古到今基本都是写本,因为文书是实用性文章,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政务活动紧密相联,时效性很强。文书的现实使命完成之后,大部分文书会成为有待查考利用价值的档案被保存下来,成为后人研究历史的真实记录和原始凭证。[7]清同治增辑本《浮山志》所载法产文书,内容丰富且研究意义重大,法产文书是明清时期浮山地区重要的地方史料,是其地方社会生活史的凭证与载体。法产文书包含了民间契约文书和地方官府文书,首先,通过对法产文书中民间契约文书部分的耙梳,足见明清时期浮山地方民众的经济生活。再者,通过法产文书中地方官府文书部分的整理,亦可以了解当时浮山地方民众的法制生活和地方官府的治理工作。最后,浮山作为明清时期帝国疆域的一部分,有其时代的共性,通过对法产文书所反映的浮山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亦可以窥见明清时期整个帝国的普通百姓经济生活、法制生活和地方级别政府的治理工作。由此,山志之法产文书部分研究意义重大,是极其重要的、无比珍贵的地方社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