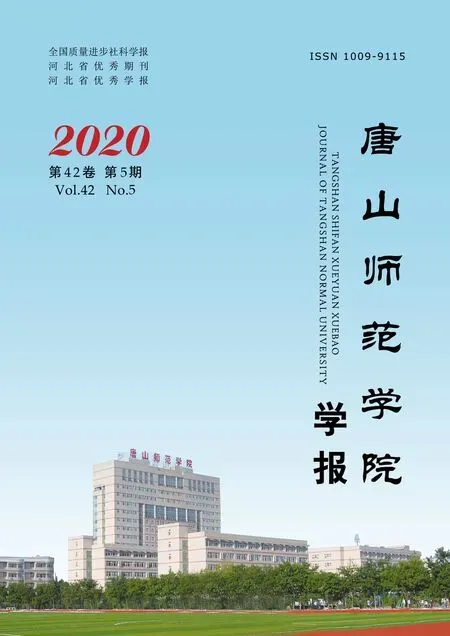《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主人公文化身份嬗变——从巴赫金时空体视角看
曲 涛,黄露娜
《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主人公文化身份嬗变——从巴赫金时空体视角看
曲 涛,黄露娜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基于巴赫金时空体理论,考察裘帕·拉希莉的小说《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中道路时空体、城堡时空体和田园诗时空体三种时空体模式,探讨小说主人公文化身份经历漂泊、碰撞,乃至最终实现多元文化融合的嬗变过程。
裘帕·拉希莉;《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时空体;文化身份;嬗变
一、引言
《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简称《第三块》)是美籍印度裔作家裘帕·拉希莉2000年普利策小说奖获奖作品《疾病解说者》的代表作之一。作品融合印、英、美三国文化元素,以一名印度青年不懈努力改变生存环境为线索,讲述其在印度成长、英国求学、美国成家立业的故事。
这部篇幅不长却寓意深厚的小说受到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有学者指出在男性主人公追求美国梦的显性文本下,隐含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三个女性形象的潜文本,使文本充满张力并具有“东方主义色彩”[1];有学者关注家庭内部陈设,认为印度移民夫妻在新大陆的“共同记忆、探索经历与故事已投射成为家庭壁炉”[2]。大多学者关注文本中的空间内涵,认为作者塑造的不同时空引发读者对“时空维度的好奇”,从而将“世界视为构建而成”探讨“历史性”[3,p112]。其中,“物理和情感距离将人物关联在一起”[4],或运用空间理论,指出主人公作为印裔移民在到达“异托邦”美国后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问题[5]。显然,对东西方文化差异、印度文化传统与跨时空生存空间的研究是以往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将拓宽前人对文本中时空元素与文化内涵关注的范围,运用巴赫金时空体理论,通过建构小说中跨越三块大陆的不同时空体模型,考察小说主人公跨文化生存状态,探讨移民群体自我文化身份的变化历程。
二、道路时空体与文化身份漂泊
西方语境中的“identity”译为“身份”“认同”或“同一性”,起源于拉丁语“idem”,意为“相同”(same)。20世纪以来,随着哲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学等领域的进一步发展,“身份”/“认同”由早期的哲学、人类学研究,逐渐转向“对社会、性别、国家与文化属性的认同探讨”[6]。文化身份或文化认同,体现主体与外界文化认知的同一性。英国著名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提出“文化身份”的两种基本立场。第一种是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文化……反映共有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号”,这种经验和符号给一个民族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7,p209];而第二种立场则认为,“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决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7,p211]。霍尔本人更倾向于第二种立场,即不把文化身份看作“本质”,而视其为变化中所形成的文化“定位”[7,p212],这也是本文研究文化身份的基本立场。
“时空体”(chronotope)这一概念由巴赫金从数学、科学领域引入文学理论之中,并将其界定为“在文学中被艺术地加以掌握的时间和空间的本质性的相互关系”[8,p269]。时空体“总是带有感情和价值的色彩”[8,p436]。在巴赫金看来,小说艺术世界的时间与空间是一个整体。这种整体时空观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依据”[8,p269],以康德哲学理论为哲学基础,并从乌赫托姆斯基关于生物学时空体报告所涉及的美学问题中获得启发[9],对艺术世界时空体的研究有利于反映作品所呈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时空体概念不但能体现作品“世界观”还可以“组织小说的情节”“构成一个功能场”[10]。时间和空间“两者处于一个相互联结的关系链条中”[11],“时间和空间相互结合形成的某种相对稳定的模式”[12]。因此,将时空视为整体,挖掘小说中的时空体模型、探讨人物文化身份变化具有可行性。
道路时空体是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时空体之一。道路时空体中的“时间仿佛注入了空间,并在空间中流动(形成道路)”[8,p437]。通过道路时空体,小说《第三块》成功展现了无名叙述者“我”作为一个普通印度移民,辗转于三块大陆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在道路时空体的起点印度,“我”的母亲因父亲的去世而发疯、失去尊严地生活,这使“我”对印度文化产生怀疑。随着双亲的离世,“我”踏上远走他乡的道路时空体,试图寻求异国文化的滋养。在离开印度时,“我”的“名下只有相当于当时十个美元的财产”[13,p177],没有固定目的地,没有经济来源和保障的异国求学之旅注定艰难。“我”搭乘一艘意大利“货船”,睡在引擎隔壁的船舱里,忍受噪音叨扰,在海上漂航了三个星期之久,穿过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最后抵达英国。随着货船在道路时空体中的移动,“跨越地理边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跨越文化、心理和社会边界”[14],此过程正如货船所代表的道路时空体具有的特征那样漫长艰难。
抵达英国后,“我”在英国“单身汉住所”落脚,经历道路时空体中的“相会情节”。“小说中的相会,往往发生在‘道路’上……在道路中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点上,有许多各色人物的空间路途和时间进程交错相遇。”[8,p437]“单身汉住所”位于“公园附近”“公用唯一一个冰冷的卫生间”,为相会情节提供空间,“身无分文的孟加拉单身汉”在此相聚,“时不时有人结婚搬出去另过”[13,p178]。相会情节中的文化元素具有流动性,使得位于其中的人物难以形成稳定文化身份。这些孟加拉单身汉们聚在一起时而吸英国牌子的香烟,时而又“一锅锅地烧咖喱鸡蛋”“用手抓着吃”,多元交错的文化元素使人感到“挣扎着在海外求学求生”的焦虑[13,p177]。
“我”在以美国为目的地的道路时空体快速转换,体现出对印度文化的刻意疏远和对美国文化的向往。在英国完成学业后,“我”决心奔赴美国工作。由英国飞往美国的途中,“我”在印度仅停留一周用于完成婚事,随即独自赶往美国。如此匆忙的移动使印度包办婚姻下的新婚妻子对“我”而言完全是个“陌路人”[13,p196]。即便她在深夜偷偷哭泣,“我”也不闻不问,只是“就着手电读我的指南,期盼着我的旅行”[13,p185]。妻子是个传统印度女性,恪守印度文化价值观,对待妻子冷淡的态度,间接反映出“我”与印度文化的疏远。与此相反,“我”满怀期待地阅读“《北美就学指南》”以及对美国人登月成功的关注,显示出我对美国文化与生活的崇尚与期待。
尽管如此,美国文化并非“我”想象的那般包容友好,即使身处其中,也仍需不断趋同适应。在“基督教青年会”(“我”到美国后的第一个居住地)的体验反映出我的迷茫。位于剑桥广场的“基督教青年会”“窗户光秃秃的没有窗帘”[13,p179],“我”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公共空间中。房间内,代表基督教文化的木制十字架悬挂在墙面上,让“我”感到陌生与不安。相比于意大利货船上有“甲板可以存身避难”“浮光耀金的大海可以激动我的灵魂”[13,p179],在“伦敦单身汉住所”有来来往往的孟加拉单身汉一起交流,在这里“我实在受不了”,只能“穿着睡衣在昏暗的过道里踱来踱去”。“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声,尖锐刺耳更兼绵长持久”“这股噪声搅得人心烦意乱,有时简直令人无法呼吸”[13,p179]。这种限制实指外在文化差异对主体认知的冲击,在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不适感超越了对印度与英国文化差异的感知。为了能够融入美国,“我”付出巨大努力,在“一间镶嵌玻璃窗的大房间里读《波士顿环球报》”“每篇文章每则广告”都不遗漏[13,p180],以此让自己尽快熟悉、融入美国文化。
对以意大利货船“SS罗马号”、英国“单身汉公寓”与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为节点的道路时空体中主体行为与感受的考察,揭示“我”与印度原文化逐渐疏离和对异国文化的期待。“我”试图改变自身文化身份时所面临的不适与困境,反映移民群体在地理迁移过程中普遍面临的文化身份漂泊状态。
三、城堡时空体与文化身份碰撞
如果说在道路时空体中移动的生活经历体现文化身份移动的任意性,那么,“城堡时空体”展现的则是东西方文化在这一时空体中碰撞从而达成协商的过程。
“克罗夫特夫人家”在“我”看来“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家”[13,p201],对“我”文化身份的重建具有特殊意义。巴赫金在分析18世纪末英国“哥特式”小说时,提出“城堡时空体”概念。在城堡时空体中,历史时间在特定空间中凝固静止,城堡时空体里“充塞了时间,而且是狭义的历史时间,即过去历史的时间”[8,p439],有利于文化价值观念的延续。克罗夫特夫人家“周围是一圈铁丝网围栏”“单家独户”“屋根四周生长着一丛丛乱蓬蓬的连翘”[13,p181],创造现代社会中的城堡时空体。老夫人反复强调“进屋第一件事,就是要锁门”[13,p182],要“将一个她不再理解的世界锁在门外,从而感到安全”[4]。
城堡时空体不仅将历史凝结在城堡的外观表征中,如“泛黄发毛”、旧得“弹不响”的钢琴,更表现在克罗夫特夫人这个“跨越一个世纪”的人物艺术形象中。克罗夫特夫人是被“城堡时空体”时空化的人物形象,代表美国传统价值观。“作为形式兼内容的范畴,时空体还决定着文学中人的形象。这个人的形象,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时空化了的。”[8,p270]在城堡时空体中,克罗夫特夫人代表西方传统文化。这种文化表现在她保守的着装风格、行为准则和对政府的信任上。首先,她的着装保守,“一条黑色长裙,撑起来就像支在地板上的帐篷”“一件白色衬衫,式样古板”,“衣着短到露出脚踝”在她看来“要不得”[13,p190]。其次,她反复对“我”强调“不准带女朋友来”,即便女儿海伦“老得都可以做我妈了”也坚决不允许她和“我”单独交谈[13,p190],恪守男女有别、正派保守的行为准则。最后,克罗夫特夫人十分相信政府,她会在摔倒后第一时间求助于政府,也会反复谈论美国人的登月行为,引以为傲。因此,克罗夫特夫人的住所虽然不是一所真实意义上的中世纪城堡,但它具有城堡时空体特征,延续着西方上世纪之前的文化观念。
城堡时空体营造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属性的封闭时空。“纪律有时需要封闭的空间,规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15]在此时空体中,克罗夫特夫人试图以其上世纪之前的西方价值观规训来自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住客。在她上世纪之前的价值观审视下,哈佛的男子与以前大不一样。她尝试对这些差异进行规训,“虽然我不过在几尺开外,她还是要大声喊叫”,不断强调月亮上那面美国红旗并要求“我”高声称赞“了不起”[13,p183]。这种规训在“我”看来,就像小学时被迫背的乘法表、婚礼时被迫念的梵文诗歌一样,使人感到厌恶。
事实上,东西方文化在城堡时空体中的相遇,除了差别和规训外,也在碰撞中产生对话与共鸣。“我”来到城堡时空体是由于无法完全认同当时的印度社会文化;而克罗夫特夫人选择生活在一个世纪前的老房子中,与外界切断联系,同样反映了她与当时美国社会文化的脱节。“我”与克罗夫特夫人在各自社会中存在的距离与隔阂,成为两种文化协商对话的空间。
令人满意的文化身份协商结果包含被理解、尊重和肯定。“我”开始关注克罗夫特夫人的生活起居,“每天傍晚……我都会和克罗夫特夫人一起,在琴凳上坐上几分钟。我陪她一小会儿,让她放心门锁已检查过了,还告诉她旗帜插到月亮上很了不起”[13,p193],时常在睡觉之前下楼看她是否安全地回卧室,每到星期五准时把房租交到她手上。我的这些行为与东方文化中尊重长者、重视家庭的价值观密不可分。也正因如此,“我”成为在此居住过的学生中,第一个被克罗夫特夫人称之为绅士的人,受到老夫人的尊重。此外,东方女性谦逊与内敛的品质也在城堡时空体中获得认可赞赏。当“我”带着妻子玛拉去见克罗夫特夫人时,老夫人仔细打量玛拉后:“用我十分熟悉的、难以置信却一样欢欣的口吻,扬声宣告道——‘她真是一位完美的女士!’”[13,p200]通过克罗夫特夫人西方文化视角,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城堡时空体中,“我”重新认识妻子玛拉,“对她第一次有了天涯同命的感觉”[13,p199]。“我”对克罗夫特夫人的理解尊重、老夫人对“我”与妻子的肯定以及“我”对妻子态度的转变,体现东西方文化在城堡时空体碰撞中产生的共鸣。
克罗夫特夫人时空化的人物形象代表传统美国文化价值观,她在试图规训“我”的过程中,发现印度文化的闪光点。克罗夫特夫人对印度文化的审视使“我”第一次对妻子产生情感的联结,也使“我”改变对印度文化排斥的态度,承认文化间的相通之处。东西方文化在城堡时空体的碰撞中协商,为形成稳定融合文化身份奠定基础。
四、田园诗时空体与文化身份融合
道路时空体展现了叙述者“我”文化身份漂泊的状态,城堡时空体反映东西方文化身份碰撞与协商,而田园诗时空体,以“家庭”的形式获得归属,实现多元文化融合的身份。
田园诗时空体是巴赫金在分析希腊小说时提出的一种时空体概念。“这是一种规模不大的十分具体和浓缩的叙事抒情时空体”,具有“特有的循环化了的(但不是纯粹循环性的)牧歌时间,它由自然时间(循环性时间)同假定性牧歌生活(部分的广义上说是农业生活)的日常时间结合而成”[8,p289]。
田园诗时空体有利于展现文化身份的融合的状态。“我”在美国的家庭生活,具有田园诗时空体的特征。“生活及其事件对地点的一种固有的附着性、黏合性……它的内容仅仅严格局限于为数不多的基本的生活事实。”[8,p417-418]时间凝结在这一空间之中,获得持续性反复。“爱情、诞生、死亡、结婚、劳动、饮食、年岁——这就是田园诗生活的基本事实。”[8,p418]在田园诗时空体中,“我”“没有再往远处漂泊了”,而将此视为自己最终的归属。从事简单的农业活动,等待“屋后的花园出产西红柿”[13,p201],并以主人的身份在家中招待客人。
田园诗时空体叙述,多用于展现浓郁持久的情感生活。在此时空体中,“我”和妻子培养出浓厚的情感,从“陌生人”到“完全爱上对方”[13,p200]。对于来自印度包办婚姻的妻子玛拉,“我”最初的态度“既没有反对意见,也没有热情向往”[13,p185],仅仅认为这是大家希望“我”应尽的“对每个男人都是如此”[13,p185]的义务。在道路时空体中“我”表现出与妻子同处一个空间的不适感以及对时空移动的迫切渴望,期待早点到美国展开新生活。城堡时空体的出现,让“我”有机会感受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共通之处,克罗夫特夫人对妻子玛拉出乎意料的肯定,使“我”对自身文化身份认知发生改变。在田园诗时空体安定的环境中,“我”与妻子分享“SS罗马号”“芬斯伯里公园”(单身汉公寓)和“基督教青年会”等时空体中的经历以及“琴凳上陪克罗夫特夫人的那些夜晚”[13,p200]。妻子是“我”与原有印度文化连接的桥梁,与妻子关系的复合代表“我”对印度文化偏见的逐渐消解。
在跨越文化边界的游走中,“我们”以家庭的形式建立稳定的田园诗时空体。田园诗时空体的外部环境是美国主流文化,而内部则是印度生活的缩影。虽然“我们都已是美国公民”并“决定终老于此”,但在田园时空体中“我们”仍然吃着印度食物,穿戴印度服饰。
妻子玛拉服饰的变化反映她对异国文化的态度由抗拒到坦然面对的转变。莎丽是印度传统服饰的代表元素,是印度女性“社会身份”和“话语”的“核心符号”[16]。妻子初到美国时羞涩地将莎丽罩在头上[13,p195]。在城堡时空体与克罗夫特夫人相遇时,仍旧头顶罩着莎丽,而在田园诗时空体中,玛拉“不再把莎丽罩在头顶”[13,p201]。玛拉头顶的莎丽作为印度文化的典型象征,反映东西方文化隔阂以及印度女性保守的文化心态。这种文化身份的不确定感在田园时空体循环稳定的时空叙事模式中得到缓和。
第二代移民接受来自田园时空体内外两种不同的文化教养,这种差异在其成长过程中发挥独特价值。“拉希莉的作品通过对二代移民生活经历敏感而富有洞察的描写,展现移民文化和主流美国文化的演变性质。”[17]在田园时空体内,他们深受印度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熏陶,而在美国社会中,他们接受美式精英教育。“我”的儿子在家中和其他孟加拉邦人一样“用手抓饭、说孟加拉语”[13,p201],而他同时在哈佛大学——这所象征美国文化知识最高水平的学府,接受良好教育。二代移民优异的学习表现与其混杂的文化身份相关。异质文化使二代移民更容易感受到差异和危机,激发他们的不懈努力调整自我文化身份的潜力,乃至形成“民族-全球化身份”,这种融合的文化身份“穿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保有民族遗产,同时激发普遍人文关怀”[18]。同时,在田园诗时空体中,父母提供持久稳定的支持,成为他们在异域文化环境中克服身份困惑,努力发挥价值的不竭精神动力。
虽然仍穿梭于两种文化之间,《第三块》中的印度移民家庭已经学会坦然面对文化差异。以“家庭”的形式,在田园诗时空体中找到自我文化的归属,重新形成稳定融合的文化身份。
五、结语
本文以巴赫金时空体为基础的认知模式,考察拉希莉短篇小说《第三块》主人公的移民生活经历,展现其文化身份的嬗变过程。巴赫金的时空体清晰反映了小说世界中时空动态变化的节奏。在道路时空体中,无名叙述者尝试否定原有文化身份,亲近西方文化;在城堡时空体中,东西方文化价值观互相碰撞,达成共识;在田园诗时空体中,叙述者以“家”的形式在新大陆建立混杂文化身份,找到身份归属。
通过深入分析一个印度青年跨越三块大陆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本文认为文化身份在差异与碰撞中存在不断改造和再生产的可能性。在全球文化多元碰撞的当今时代,我们应当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文化差异,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尊重包容他国文化,以此达成文化和谐共存,融合发展。保持文化多元性就像保护生物多样化一样重要,有利于维护人类文化生态平衡和人类精神文明持续健康发展,从而实现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李靓.第三块大陆之下的潜文本[J].外国文学,2012,237 (4):15-21.
[2] Chi-Whi K. Mary. Interior Frontiers in Jhumpa Lahiri’s Interpreter of Maladies[J]. Eureka Studies in Teaching Short Fiction, 2011, 10(1): 85-95.
[3] Moynihan S M. Affect, History, and the Ironies of Com- munity and Solidarity in Jhumpa Lahiri’s Interpreter of Maladies[M]//Naming Jhumpa Lahiri: Canons and Contro- versies, 2012: 97-116.
[4] Caesar, J. American Spaces in the Fiction of Jhumpa Lahiri [J]. ESC: English Studies in Canada, 2005(1): 50- 68.
[5] 李贵苍,黄瑞颖.边缘性的嬗变——论《论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中的空间书写和身份认同[J].当代外国文学,2015,36(3):63-69.
[6] 廖炳惠.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7]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M]//罗刚,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8]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钱中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9] B. H.扎哈罗夫.作为历史诗学问题的时空体[J].高慧,译.俄罗斯文艺,2008(1):32-37.
[10] 薛亘华.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内涵[J].俄罗斯文艺, 2018(4):36-41.
[11] 章小凤.时空体[J].外国文学,2018,271(2):87-96.
[12] 潘月琴.巴赫金时空体理论初探[J].俄罗斯文艺,2005(3): 60-64.
[13] 裘帕·拉希莉.疾病解说者[M].卢肖慧,吴冰青,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14] 云玲.裘帕·拉希莉作品的离散叙事研究[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15] 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李北成,杨远婴,译.第2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6] Amin, Nyna, and Devarakshanam Betty Govinden. Sari Stories: Fragmentary Images of “Indian Woman”[J]. Dress Identity Materiality, 2012(2): 323-340.
[17] Field R E. Writi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Negotiating Cultural Borderlands in Jhumpa Lahiri’s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and The Namesake[J]. South Asian Review, 2004, 25(2): 165-177.
[18] Kraidy M Marwan. Hybridity,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On the Transmut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Protagonist in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khtin’s Chronotope
QU Tao, HUANG Lu-na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Based on Bakhtin’s Chronotope Theory, three chronotope modes were studied in “” by the American Indian writer, Jhumpa Lahiri, namely, the road chronotope, the castle chronotope and the idyllic chronotope. It explore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the protagonist’s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drift, collis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Jhumpa Lahiri; “”; chronotope; cultural identity; transmutation
I106.4
A
1009-9115(2020)05-0041-05
10.3969/j.issn.1009-9115.2020.05.009
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项目(2019JYT11),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2017XJYB08),大连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YJSCX2017-085)
2019-10-05
2020-05-27
曲涛(1970-),男,辽宁大连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英语小说、叙事学理论。
(责任编辑、校对:朱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