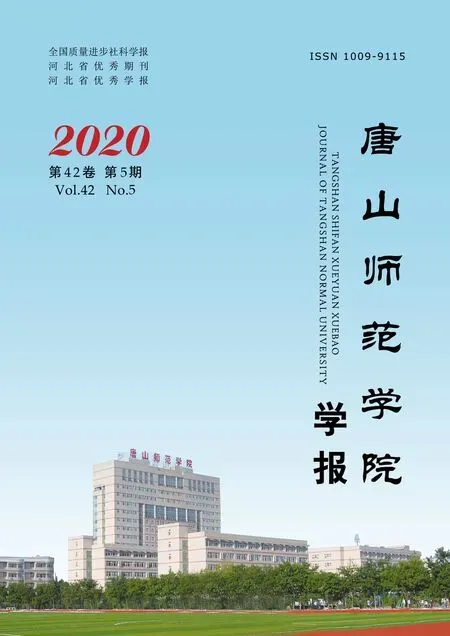法院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原因的实证分析
李五志
法院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原因的实证分析
李五志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法律法规对法院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审查核实作出许多规定,但是实际运行效果究竟如何,就不得而知。通过相关裁判文书分析,揭示法院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审查核实的运行现状,认识不足之处并为实现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制度的立法价值,为解决社会纠纷、推进多元化的纠纷预防机制添砖加瓦。
民事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不予执行
从我国第一个公证处——哈尔滨公证处的建立,到1986年8月全国第一次公证制度研讨会的召开,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以下简称公证法)正式颁布,公证制度历经波折,公证制度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且得到社会的认可[1]。在构建多元化纠纷预防和解决机制中,公证制度赋予公证处以非诉的方式,预先赋予民事与经济交往中当事人之间的正常交往以强制执行效力,后获得法院的执行[2]。因此公证制度在积极预防民事纠纷、节约司法资源、督促债务履行等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3]。
法院的审查决定公证债权文书是否可以进入强制执行。故,法院审查的内容对公证债权文书记载的债权能否得到快速实现就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对于审查的内容与标准做出规定[4]。其次,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以下简称《联合通知》)予以进一步的细化规定,然后,是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15年民事诉讼法解释》)四百八十条再次予以规定[5]。还有2018年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等其他法律法规作出了规定。但是对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并不清晰。有鉴于此,选取2018年和2019年前10个月的相关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希望借此揭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公证债权制度下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一定有益素材。
一、样本基本情况
对公证进行司法监督的法定途径之一是法院对其进行审查,并最终决定是否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不予执行一般是由执行法院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由于全国各地的公证债权文书制度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以及不同公证处出具的公证债权文书的质量差异较大,因此,以某一个公证处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难免会有失偏颇。北大法宝的司法案例数据库为基础,以“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搜索,共检索到将近两千个案例。由于部分案例时间相对久远,不具有参考价值,因此笔者选定2018年案例和2019年截止到10月的案例,共检索到580份案例,排除撤销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申请、发回重审的案例以及无关案例,有效案例共有401份,其中判决书有19份(因为《规定》第二十二条部分内容为通过向执行法院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所以判决书均是在《规定》颁布以后出现的),其他均为裁定书。首先对这401份案例进行简单分析,其中,法院不予执行或者部分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有75个,约占19%,其次,以这75份裁判文书为样本,对法院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原因的现状进行剖析。
另外,为了有明确的参照,这里列出近几年法院对执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收案数量的变化。具体变化如表1所示。

表1 2007-2017全国法院对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收案量①
通过对全国法院2007-2017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收案数量分析,可以得出我国的公证债权文书执行数量呈现曲折式的上升状态,特别是在2015、2016和2017年数量上升相对之前比较明显。需要说明的是,不予执行的数量相对于如此数量的收案量而言显得有些“微不足道”,这说明在总体上公证债权文书的质量是具有保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不予执行公证债权理由的研究没有实际意义,相反通过对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事由的实证研究,可以更加清楚地分析法院是在哪些情况下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以便为之后的公证工作提出建议,在以后的公证工作中避免相关情况的再次出现,使公证债权文书的质量进一步提高,获得法院的执行,提高公证处的公信力。
二、法院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事由的现状考察
根据75份裁判文书,并结合我国《2015年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四百八十条、《联合通知》《公证法》以及《规定》等相关规定,将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事由归结为以下几种:
(一)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
1. 公证债权文书中载明的借款数额与实际发生的借款数额不一致,导致文书记载的内容与事实不符
在民间借贷中因为借贷双方均是非金融机构,规范性相对较差,所以双方经常会在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之后对贷款数额擅自更改。例如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7966号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并且设立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之诉的本意在于完善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程序,对公证债权文书进行司法监督,并充分发挥赋强公证在纠纷预防方面的功能。因此并不能因部分争议而直接认定全部不予执行,而是仅对与事实不符的部分不予执行。但是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8)川01执异1458号案例却表明,在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以后实际履行借款义务导致与事实不符而被裁定全部不予执行。其他案例还有(2018)辽0502执异23号案例、(2018)豫0523执异109号案例和(2018)苏0902执异56号案例。另外,有些甚至是借贷合同中的本金数额争议很大或是不明,导致被认定为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如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18)鄂执复35号案例和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8)粤01执异463号案例。
此外,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2018)京0108执异382号案例中,债权人采用各种隐蔽的方法在本金中预先扣除利息。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借贷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仅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由此被认定为数额不一致,并对公证债权文书不予执行。出现相同情况的还有(2018)最高法执监375号和(2019)京03民终5341号案例。甚至在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的(2018)鄂0105执异3号案例中出现由中介公司收取各种高额的费用,使借款人实际借到金额大为缩减,并在借款后继续偿还公证债权文书确定的利息的情况,并使公证债权文书沦为形式,形成中介公司控制下与出借人共同收取高息高费的工具。在这样的情景下公证债权文书确定的借款数额与实际情况不符,背离了公证的初衷。还有出现本金和利息加在一起作为本金重复计算利息的问题,比如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2019)苏1324执异15号案例。以上情况均被认定为与事实不符。
2. 因公证债权文书与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合同约定不一致,导致公证债权文书与事实不符
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的(2018)京0115执异187号案例中,就因是对相同事实办理的两份不同内容的公证债权文书,最终被法院认定为公证债权文书内容与事实不符。另外,(2018)粤01执异738号和(2018)粤01执异736号案例也是因为公证债权文书与当事人的借贷协议内容不一致而被不予执行。
3. 因日期等事项记载错误被认定与事实不符而被不予执行
特别是涉及数额比较大的案例,法院经常会裁定不予执行。如在(2018)京03执复223号案例中,因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5月10日之内容与事实不符,而被认定银行承兑汇票并非涉案项下之银行承兑汇票,执行证书所确认的债务履行情况与公证债权文书并无直接关联,最终被裁定不予执行。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2018年10月以后,根据《规定》第十二条,对不同的事由予以当事人不同的救济途径,但是(2018)川01执异1458号案例、(2018)粤01执异738号案例和(2018)粤01执异736号案例均是在2018年10月以后做出,并对其事由进行审查核实,仍然采用的之前了运作方式。
(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1. 违反最高利率限制规定
在民间借贷中一般债权人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债权人通常会通过各种名义和手段向债务人收取高额利息,债务人为了获取贷款通常会做出无限的让步。根据《借贷规定》第三十条,借贷的年利率上限规定为24%。在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的(2018)京0116执异144号案例中,因债权人设立利息、罚息、综合费用等名义收取高额利率,最后该法院对于利息、罚息及综合费等之和超出年利率24%的部分不予执行。此类案例还有(2019)沪01执复38号案例、(2018)渝0116执异83号案例、(2016)豫05执异55号案例、(2018)最高法执监375号案例、(2018)沪0115执异388号案例和(2018)京0115执异187号案例。并且还有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5个系列案例也因年利率超过24%被不予执行。在笔者检索到的案例中此原因共出现12次。
2. 是否违反关于法人提供担保的限制性规定
在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8)吉07执异13号中,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公司法》是民事基本法的特别法,其强制性规定可以作为判断合同效力的依据。并且该院认为当事人和公证处有义务审查华宇公司的章程及股东会决议等公司的内部行为。所以法院结合《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以股东会决议存在瑕疵为由对公证债权文书的担保部分不予执行。但是其他法院的判决也有基本相似的案情却是完全相反的结果②。
(三)所记载的给付内容是否明确
1. 公证债权文书对需要进行强制执行的内容是否明确
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发布的《联合通知》第一条明确要求公证债权文书中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同时这也是法院审查核实时重点需要核对的内容之一。如在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执复5号案例中,其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项目及其他应付款项均未明确具体金额或计算方式,特别是实现债权费用中的诉讼费、仲裁费、办案费等以及其他应付款项等,更是缺乏具体指向,并因此而被裁定不予执行。另外,(2019)京0113民初4547号案例、(2019)京03民终7966号案例和(2016)豫05执异55号案例中也出现了实现债权费用以及其他合理的费用等这样类似的情况。
2. 执行证书的给付内容是否明确
执行证书虽然不是执行依据,但却是申请执行人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时所必须提交的材料,因此对于执行证书也要求给付内容明确。执行证书给付内容不明的原因与公证债权文书基本相同,也是因为经常会出现借款利率和支付实现债权所需的所有费用不明等情况。相关案例有(2018)鲁1102执异142号、(2018)鲁1102执异143号、(2018)鲁1102执异144号、(2018)豫0523执异109号以及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3个系列案件。
(四)公证处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审核义务
虽然执行证书不是法律规定的执行依据,但是根据《规定》第三条,当事人在申请执行时必须提交证明履行情况等内容的执行证书。执行证书关乎之后是否可以进入法院的执行,快速实现权利。故,在出具执行证书之前公证处的审查核实义务是否履行到位就显得异常重要。
1. 对催收是否履行核实义务
在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的(2018)鲁1203执异16号案例中,公证处未审查核实催收行为是否属实以及催收方式是否合法,因此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与此相类似的案件有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处理的5个系列案件。
2. 履行审查核实义务时是否遵循程序规定
首先,是法定的核实期间,公证处在发出核实债务履行情况的通知后,应当为债务人留出法定异议期限。在(2018)粤01执异738号案例中,就是因为公证处在异议期间尚未届满之时就已出具执行证书而被裁定不予执行。相同的情况还有(2018)粤01执异736号案例。其次,外出审查核实公证事项的公证员人数规定,在(2018)粤01执异580号和(2018)粤01执异538号案例中,只有一名公证员外出办理,等办理完毕之后回到公证处再由另一名公证员在询问笔录上补签名,形式上造成有两名公证处人员外出核实的表象。最后,公证处审核时形成的询问笔录应经当事人核实。在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2019)湘0381执恢444号案中,公证员口头陈述公证内容后,便让双方当事人在空白的公证文书和公证谈话笔录上签字,所有的公证文书与公证谈话笔录均由公证员回单位后补齐,并因此被不予执行
3. 是否核实债权债务的履行情况
对履行情况的审查核实是一个核实工作中的重点之一。经常会因未核实完毕履行情况而被裁定不予执行。例如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的(2018)京0114执异32号案例,本案的执行证书未能对双方之间债务履行的事实情况作出整体的正确查明,且影响到本案执行标的范围的确定。还有(2018)鲁0203执异152号案例的执行证书中对债权人已经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未尽审查核实的义务。当然如此案例不止这两个,还有(2019)陕08执异20号、(2018)豫0581执异1号、(2018)鲁1203执异34号、(2019)京0105民初10356号、(2018)川0107执异126号、(2018)京0113执异96号等其他案例。
另外,有法院认为债务人自死亡之时起即已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所涉的民事责任主体和诉讼主体应当进行变更。在债务人死亡之后,公证处仍以其为被申请执行人出具执行证书,主体不适合。虽然公证处按照程序向债务人预留地址邮寄了《债务核查通知书》,但客观上已不能送达给债务人,不能完成债务核查程序,如(2018)川01执复159号案例。
(五)办理公证时当事人未在场
在《2015年民事诉讼法解释》的第四百八十条规定,办理公证时要求被执行人或代理人必须在场。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认为并非要求双方必须到“公证处所在地”这个特定场所,而是要求双方亲自或者委托代理人请公证处工作人员办理公证,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双方的知情权,避免出现侵害某一方权利的情况。
在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执异1589号执行裁定书中,裁定书认为虽然汉南公证处作出了(2013)鄂汉南证字第1164号公证债权文书和(2015)鄂汉南证执字第003执行证书,但未依法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现汪红卫以其“未亲自或者委托他人到场进行公证”为由提出不予执行的申请,因汉南公证处无法提供相关公证案卷,无法确定汪红卫是否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参与相关的公证程序,且申请执行人信达湖北分公司亦未能提交汪红卫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参与公证程序的证据。故,认定汪红卫亲自或者未委托代理人到场公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汪红卫提出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请求,予以支持。此种理由裁定不予执行的案件数量还有很多,(2018)鄂01执异1516号、(2018)鄂01执异1517号、(2018)鄂01执异1518号、(2018)陕01执复38号、(2018)鄂01执异1590号等案均以此为由不予执行。
(六)其他不予执行的情况
1. 超过期间
首先,超过申请执行期间。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是两年的申请执行期间,超过两年,便不能申请强制执行,成为自然债务。(2019)辽1403执异2号、(2018)内01执复43号案均是以此为由被裁定不予执行。其次,保证责任期间,也是一个重要的期间,是需要核实时予以关注的重点信息。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0执复5号裁定书因保证责任的期限届满而对保证责任裁定不予执行。
2. 债权债务关系因履行等原因已经消灭
债权债务消灭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效力也随之消灭。因此在(2019)京0102民初17489号、(2019)京02民终8075号案中,就以此为缘由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
3. 其他
对公证债权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必须经过被执行人了解和同意才会产生效力,未经同意不允许未经判决就进入执行。(2019)陕08执异51号、(2018)粤01执异463号以及(2019)京0118执异13号案中,均出现执行证书将未经被执行人同意的债权列入执行标的问题。甚至还出现一方当事人的签名等均是伪造的情况以及一方未收到公证债权文书。另外,还有(2019)鄂0114民初974号和(2019)鄂0114民初975号可能涉及违法犯罪,因为其无法说明资金来源,更无法说明借款的用处,同时因借款时间极短等有悖常理的情况,因此被判决不予执行。
以上就是笔者对75个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事由运行现状考察以及部分分析。其中,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的事由共出现16次,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事由共出现12次且主要是违反关于利息的规定,所记载的给付内容是否明确的事由共出现11次,公证处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审核义务的事由共出现37次,办理公证时当事人未在场的事由共出现11次,其他不予执行的情况的事由共出现11次。
三、实证考察之启示
(一)对法院之启示
首先,法院应当统一法律适用。2018年的《规定》中对于被执行人的救济途径进行细化规定,将实体事项和程序事项予以不同的救济途径。但是通过对2018年10月以后作出不予执行的35份裁定书分析发现,实务执行确实与法律规定有所不同。在35份裁定书中至少有9个案例对实体事项进行了审查。因此,法院需要统一法律的适用,避免出现限制救济或滥用救济的问题。
其次,法院应当明确核实的标准与内容。结合阅读裁判文书和对部分公证员的访谈了解到,经常会因为法律法规的抽象性而出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不同法院会出现不同的标准,例如不同法院针对“公证债权文书未向当事人送达是否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就出现截然相反的判断③。法院作为事后的司法监督部门,对于监督的内容和标准应当予以明确,这会使公证处的事前核实更加具有针对性,符合事后的监督要求,进而提高公证处的公信力。
最后,适当放宽审查。对于公证债权文书形式上出现的瑕疵不应直接裁定不予执行。应当先通知原公证处进行纠正,公证处纠正后若符合规定的标准法院再予以执行,若不予纠正或是纠正后仍不符合再裁定不予执行[6]。
(二)对公证处之启示
1. 落实完善公证处的核实工作
从以上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公证处在进行核实工作时确实没有做好。结合上海等地出现的“套路贷”诈骗,公证处的核实问题存在诸多问题。首先,目前我国公证处多为事业单位,所以对公证员管理机制比较严格,每一个公证员都有相应的编号,并且公证员的准入门槛较高。因此可以构建公证处与民政部门等机关的信息共享平台,并可以采取以编号为账号登录信息共享平台的措施,对公证员的核实工作进行监督。这为解决公证处对于异地当事人信息核实的困难提供了有效途径,并提高了公证处核实信息的效率和准确性。其次,同法院结合出台具有针对性的审核工作细则。例如,针对资金流转和来源情况的查明,应当制定详细规范,特别是民间借贷,要注意审查双方当事人相关背景和资金流转情况。特别需要注意当事人的婚姻状况,以免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或使一方遭受损失[7]。最后,公证处的审核应当恪守底线,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的部分应当坚决不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到,因为违反法律规定,设定的年利率高于法律规定的情况出现11次。因此,公证处在进行赋强公证时应当守住底线,特别防范利用公证获取高额利息的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
2. 全面落实监督体系
在以上的实证分析中可以发现,公证处未完全履行核实义务情况出现37次,是所有不予执行缘由出现次数最多的,因此需要督促公证员在办理赋强公证和出具执行证书过程中更加谨慎。首先,办理赋强公证与出具执行证书应当设定两个不同的部门,最起码要两个不同的公证员分别办理,以加强公证处内部的相互监督。其次,进行恰当的分工。可设定专门负责核实相关信息的部门或者是团队,所有的信息核实均有专门人员进行处理。另外,在进行相关调研中发现已经有部分公证处在采取这样的制度,并且运行良好,例如厦门鹭江公证处。然后,制定一套完整有序的审批制度。将公证文书进行科学划分,设定专门人员对特定类型的文书进行统一审批,把好最后一道关。厦门鹭江公证处就已经采取类似的制度,公证债权文书经过三个不同的人审核,才可以最终办理完毕赋强公证,并且已经实现了部分简单固定的赋强公证可以“批量化”办理。
3. 公证核实方式单一
通过梳理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裁判文书得知公证处主要采取四种方式进行核实信息,分别为询问、信函、电话和约定的方式。但是部分学者认为采用这样传统的审核方式略显乏力,过于单一,难以确保核实内容的客观真实性[8],并且在司法实务中公证员多采取电话的方式进行核实[9]。为促使公证处审核方式多元化,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应当由部分机关主导,构建社会信息共享平台,为公证处核实信息带来便利,提高核实结果的准确性和效率,使社会和公证处享受到因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减轻公证员的负担,实现核实方式多元化。
4. 推动公证处主动与法院沟通
因审查义务履行不恰当导致不予执行的数量如此之多,其中不免会有公证处的核实标准内容与法院审查标准与内容不相协调的情况。公证处处于整个民事司法环节的战略先锋地位(公证—调解—仲裁—审判),是事前的纠纷预防的机构,而法院是事后的审查机关[10]。公证处前面是市场,是办理赋强公证的需求;后面是法院,是执行机关。因此公证处处于中间位置,应当更加主动、积极地同法院进行沟通。可以采取各地法院定期开展关于核实标准与内容的研讨会的方式进行,这样可以缓解因公证处的形式审查与法院的实质审查不一致带来的矛盾,实现赋强公证制度的良性发展。
四、结语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是构建平安中国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社会治理的焦点之一,并且社会治理的“关键一招”与社会矛盾的预防密不可分[11]。而公证制度的研究对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笔者通过对裁判文书的阅读与分析和对部分公证员进行访谈以及对相关数据的整理,提出一些拙见,期望为我国赋强公证事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实证素材和建议,也期待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学者和实务人员对赋强公证的研究与讨论。
①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网.http://gongbao. court.gov.cn/ArticleList.html?serial_no=sftj,2019-10-28.
②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的(2018)鲁1302执异254号、(2018)鲁1302执异250号、(2018)鲁1302执异255号、(2018)鲁1302执异251号、(2018)鲁1302执异252号、(2018)鲁1302执异253号、(2018)鲁1302执异248号、(2018)鲁1302执异256号案件中,也出现相类似的案情。但是该法院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是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因此并不影响法人担保合同的效力。而且该法院认为公司章程系公司的内部自治规范,作为公司内部的行为规范,不具备对世效力,交易相对人不负有审查义务。因此,该法院驳回担保人不予执行的请求。
③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藏03执异2号裁定书认为是程序瑕疵,不应裁定不予执行。而德阳市罗江区人民法院(2018)川0626执异31号裁定书却认为公证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并裁定不予执行。
[1] 鲁坚.加强理论研究为健全和发展我国公证制度而努力——在公证制度研讨会上的讲话[C]//司法部公证律师司.公证制度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1-7.
[2] 杨容元.公证制度基本原理[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220-221.
[3] 邱星美.强制执行公证问题研究[J].政法论坛,2011,33(5): 63-73.
[4] 沈德咏.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42.
[5] 沈德咏.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1274.
[6] 卓萍.公证法学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78.
[7] 马宏俊.公证实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77.
[8]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课题组.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现状调研分析——以厦门法院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裁决审查情况为例[J].中国应用法学,2018,3(1):23-38.
[9] 张海燕.法院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原因及其救济[J].法学家,2017,25(2):150-162,182.
[10] 史凤仪.论公证机关的性质和业务范围[C]//司法部公证律师司.公证制度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7:126-137.
[11] 廖永安.以“共建共享”理念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N].人民法院报,2016-07-05(2).
On the Reasons for Courts Refusal of Enforcement of Notarial Debt Instruments
LI Wu-zhi
(Law School,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Laws and regulations make many provisions on the examin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court’s failure to implement notarized creditor’s rights instruments, but it is not known what the actual operational effect is. Therefo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judicial instruments, the status quo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court’s examin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notarized creditor’s rights instruments is revealed. To recognize the shortcomings and realize the legislative value of the enforcement system of notarized creditor’s rights instruments, it is useful to solve social disputes and promote diversified dispute prevention mechanisms.
notarial debt instruments; enforcing documents; refusal of enforcement
D926.6
A
1009-9115(2020)05-0133-07
10.3969/j.issn.1009-9115.2020.05.025
湘潭大学法学院2019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2019-11-18
2020-05-15
李五志(1994-),男,河南安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
(责任编辑、校对:王学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