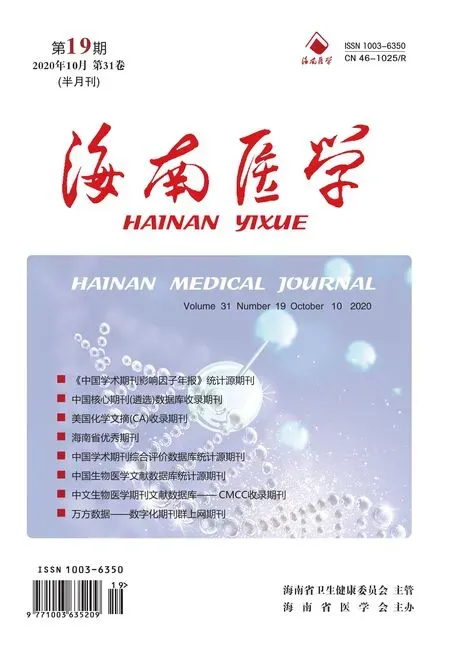肺癌切除术后肺部并发症及其防治进展
王天岚 综述 金健 审校
1.遵义医科大学研究生院,贵州 遵义 653000;
2.成都大学附属医院胸外科,四川 成都 610036
肺癌在我国新发病例中居恶性肿瘤首位,2019年我国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新发肺癌病例约为78.7 万例,因肺癌死亡人数约为63.1 万例[1]。肺癌五年生存率近年在我国提升了约10%,但仍仅有20%~30%[2]。
以解剖型肺切除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是肺癌治疗中的重要一环,但是手术引起的术后肺部并发症引发着临床广泛关注。术后肺部并发症(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PPCs),它指代几乎所有影响呼吸系统而被联系在一起的不同并发症[3]。主要包括肺炎、呼吸衰竭、胸腔积液、肺不张、气胸、支气管痉挛、吸入性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和肺栓塞[4]。在肺部手术中PPCs的发生率约7.4%~20.6%,因PPCs 导致的住院死亡人数约占肺切除术后住院死亡人数的84%[5-8]。了解肺癌患者肺切除术后的常见肺部并发症及应对,可以改善患者术后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时间并显著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1 肺炎
1.1 肺炎的高危因素 肺炎是最常见的肺癌切除术后肺部并发症之一,发病率约2.9%~12%,在高龄或相对晚期的患者中更为常见[7,9-11]。肺癌肺切除术后发生肺炎的高危因素有性别、年龄、既往肺炎、肥胖、酗酒、糖尿病、房颤、1 s 用力呼气容积(FEV1%)、麻醉风险(ASA)评分>3 分、术前活动水平≤400 m、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较低的体质量指数(BMI)、吸烟以及无症状仅在CT 下显示出的肺间质异常或肺气肿等[7,9,12-13]。
1.2 肺炎对肿瘤转移、复发的影响 有报道称术后肺炎会引起癌症的复发,可能是由于术后感染机体的细菌抗原对肿瘤的转移有着直接影响[14]。肺癌切除术后肺炎病原体的识别工作是由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介导的,GOWING 等[15-16]在建立的小鼠模型中,证实了TLR2、TLR4 的激活分别在革兰氏阳性菌肺炎、革兰氏阴性菌肺炎中有促进非小细胞肺癌转移的作用。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等肺炎效应细胞在肿瘤的转移中也起着关键作用[17]:中性粒细胞可以支持癌细胞转移的启动或通过诱导免疫抑制来拮抗CD8+T[18];中性粒细胞能帮助肿瘤细胞克服转移障碍,证据是CTC-中性粒细胞簇的形成与单独存在的CTC相比,前者中CTC转移的潜能增加了[17]。
2 呼吸衰竭
呼吸衰竭也是最常见的肺癌切除术后肺部并发症之一。美国医师学会一项系统评估显示,至少60%关于PPC 的研究都使用肺炎和呼吸衰竭的组合来定义PPC[4]。肺癌术后造成呼吸衰竭的原因除了间质性肺炎急性加重、肺炎、肺不张、肺栓塞、急性肺损伤、多发性肺癌等肺内因素外,肝功能不全、缺血性心脏病和中枢神经紊乱等肺外因素也可导致肺癌术后出现呼吸衰竭。肺活量(VC%)、FEV1%、术前低氧血症等是术后出现呼吸衰竭的患者因素;开胸手术、手术时间、右肺手术则是出现呼吸衰竭的手术因素[19-20]。
3 肺不张
肺不张是较为常见的肺癌切除术后肺部并发症之一[7]。全麻患者中有90%会出现肺不张,但麻醉导致的肺不张普遍较为轻微[21]。肺不张发生的因素有:术前长期吸烟、合并COPD、手术时间过长[22];此外还包括气管插管将口咽部定植菌带入下呼吸道,导致细菌移位;手术损伤导致气道痰液生成堵塞支气管;术后镇痛不足,患者排痰欠佳出现痰液淤积造成阻塞性肺不张。高浓度氧气的吸入则被认为是术后肺不张发生的另一重要原因[23]。
4 肺部并发症的预测
肺切除术后发生肺部并发症具有很大危害,临床对高危患者提前采取预防应对措施、优化护理等就显得极其重要。如何来预测肺部并发症的发生呢?除了发生各并发症的高危因素外,预后营养指数(prognostic nutritional index PNI)可用来预测PPCs 的发生。PNI是根据血清白蛋白水平和外周淋巴细胞计数得出的。目前PIN应用于预测肺部并发症领域的研究还相对欠缺[24]。2018 年的一篇文献[25]以PNI=50 为临界值将患者分为正常组和低PNI组,又将低PNI组以45为界分为轻度减低的PNI组(50>PNI≥45)与重度减低的PNI 组(PNI<45),发现PPCs 在轻度减低组和重度减低组中的发生率均明显高于正常组,重度减低组发病率升高更为明显。
人们也建立了很多预测模型来对PPC进行预测,但大多数预测模型是回顾性的数据研究,而且仅针对某一单一的并发症进行预测。
5 防治措施
5.1 术前措施
5.1.1 口腔护理 一项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口腔护理,术前牙菌斑的存在早已被证实是术后肺炎发生的危险因素[26],进行有效的口腔护理,能够减少口咽部细菌,从而对PPCs 的发生进行预防。IWATA 等[10]进行的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发现对患者采取去除牙结石,去除舌苔,拔除患有严重牙周炎的牙齿可有效降低PPCs的发生率。SEMENKOVICH 等[11]的研究让患者使用洗必泰从术前5 d至术后5 d刷牙,发现术后肺炎的发病率呈下降趋势,患者对这一廉价有效的口腔护理方案依从性非常好。
5.1.2 术前锻炼 随着加速康复外科(ERAS)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减少围术期应激反应及术后并发症的目标成为了广大外科医生所共同追求的。一篇Meta分析显示进行术前锻炼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出现PPCs 的风险降低了67%[27]。术前进行吸气肌训练可以提高吸气肌肉的力量和耐力(术后吸气肌的无力会导致静息肺容量减少,引发气道塌陷,削弱肺复张的能力、引起咳嗽无力等状况,导致肺不张、肺炎等的发生),具体训练方法为术前每周5~7 次训练,每次持续 15~30 min,为期 2 周[3]。上述结果与 GE 等[28]通过Meta 分析得出的每天进行15 min 或更长时间的吸气肌训练增加最大吸气压力可显著降低PPCs 发生的结论相吻合。也有证据表明高强度间歇训练(HIIT)对减少PPCs发生有显著效益,但为期25 d的锻炼计划对肺癌患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癌症发生发展的不确定性、患者的焦虑情绪会使这一锻炼计划在实际运用时遭受巨大阻力[29]。除了减少PPCs的发生外,运动锻炼可能有一项潜在的好处,HIGGINS 等[30]进行的一项动物模型研究表明,运动训练可以上调凋亡介质Bax 和caspase-3的表达促进肿瘤细胞凋亡;也能够明显上调p53蛋白水平,显著减缓肿瘤生长。
5.2 围术期策略
5.2.1 术中通气 由于肺部手术的特殊性,常常需要使病变侧肺塌陷以完成手术。文献报道在单肺通气(one-lung ventilation OLV)期间低 VT 较高 VT 术后ARDS 的发生更低[31],既往的动物与人体研究也指出低VT、低PEEP的组合比高VT不使用PEEP的组合释放的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更低。但也有报道指出,术中高PEEP或低PEEP似乎对患者术后PPCs的发生并没有明显差异[32]。术中的通气最佳策略就目前来看并未达成一致,但术中低VT 及适当PEEP 会降低术后PPCs 发生率已得到多数研究支持,故而LEDERMAN等[33]认为在各参数达成共识以前尽可能术中使用VT 5~7 mL/kg,PEEP 5~7 cmH2O (1 cmH2O=0.098 kPa)的通气策略。
5.2.2 术中低氧血症的应对 因手术操作、体位改变、V/Q 比值失衡等多种因素,术中OLV 期间可能发生低氧血症而增加术后PPCs 的发生。最常用的纠正方法是间歇性恢复双肺通气(two-lung ventilation TLV),但TLV 的实施会显著增加手术时间,影响术者操作,增加手术创伤风险;其次可以提高FiO2纠正低氧血症,但较长时间的高FiO2会引起氧化应激与急性肺损伤;还可选择将PEEP 添加到通气肺和/或向手术肺施加1~2 cmH2O气道正压(CPAP)[33]。最近有文献报道,伊洛前列素可以显著改善患者肺血流动力学,并在很大程度上维持肺换气,当伊洛前列素用作吸入剂使用时,它优先作用于肺血管,降低肺血管阻力[34-35]。单肺通气中使用伊洛前列素雾化吸入可以预防术中低氧血症,吸入适量的伊洛前列素可扩张肺循环,而不会对体循环产生任何严重副作用。吸入性伊洛前列素的最佳剂量,就目前证据而言为一次给药20µg,便可使整个手术过程受益。
5.2.3 围术期液体输入 近年有研究表明,在解型剖肺切除术中,围手术期输液过多会增加术后肺部并发症,一旦术中输液速度超过8 mL/(kg·h),PPCs的发生率将增长的非常快[36],可能是因为术中过多的液体输入会使患者面临酸碱失衡和肺水肿形成的风险,增加毛细血管和肺泡上皮细胞间距,影响气体交换。YANG等[37]的研究则指出术后24 h≥1 500 mL的入量会显著增加PPCs的发生。
5.2.4 术后镇痛 肺癌切除术后的急性疼痛会使患者出现保护性的呼吸浅快,排痰不佳,引发包括但不限于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肺炎、肺不张、呼吸衰竭等并发症,严重者可进展至ARDS 甚至危及生命。目前的镇痛方式有:胸段硬膜外阻滞(TEA)、肋间神经阻滞(ICNB)、自控镇痛(PCA)、椎旁神经阻滞(PVB)、胸壁前外侧筋膜平面阻滞和全身镇痛药物的使用。过去TEA被视为胸部术后镇痛的金标准,并被证实可以降低PPCs的发生率,但硬膜外镇痛会引起诸如不完全阻滞或阻滞失败,以及低血压、心动过缓、尿潴留等副作用问题,近年来有被侵袭性更低的区域镇痛技术逐步取代的趋势[33,38-39]。作为区域阻滞技术的代表PVB被证实与TEA 有类似的镇痛效果[40],赵丽等[41]对七氟烷复合丙泊酚联合椎旁神经阻滞的研究发现,PVB除了有利于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外,还能减轻术后应激反应达,抑制炎性反应。筋膜平面阻滞技术作为胸硬膜外镇痛和胸椎旁阻滞等技术的替代品在胸部手术中应用也日渐增多,包括前锯肌平面阻滞和胸神经阻滞。肺癌切除术后的镇痛应该更多地使用多模式镇痛方案,如非阿片类止痛药与针对性的局部麻醉技术相结合的方案,詹美俊等[42]的研究就显示肋间神经阻滞联合右美托咪定用于肺癌根治术,不仅提供良好的术后镇痛,降低术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还能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
5.3 皮质醇的使用 肺癌切除术后早期使用皮质醇可以减轻术后急性肺损伤,并且早期使用可让患者对其呈现更高的反应性[43]。一项使用地塞米松治疗ARDS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显示早期应用地塞米松可以降低中重度ARDS患者的机械通气时间和总死亡率[44]。但也有报道称皮质醇增多会导致转移部位糖皮质激素受体的激活,增加肿瘤的定植:糖皮质激素受体参与了转移过程中多个步骤的激活和激酶ROR1表达的增加[45]。所以当临床需要使用糖皮质激素来应对肺癌患者PPCs时,需再三的衡量利弊。就目前来说皮质醇在肺癌患者术后的应用仍存在争议。
6 展望
肺癌切除术后发生的肺部并发症是困扰患者及临床医生的重点问题,也是胸外科发展需要攻克的难点问题。近年来随着外科及麻醉技术的发展,肺部并发症的防治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缺陷仍然存在,如上所述,目前大多数的预测模型仅针对单一并发症,但从轻度的肺不张到需要插管的呼吸衰竭有可能在同一患者术后的不同阶段发生,甚至同时发生;多种治疗方式仍未达成统一;保护措施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有着相互的影响,如术中的低氧血症发生会引发急性肺损伤导致PPCs的发生,可以提高术中FiO2来应对,但高FiO2又会引起吸入性肺不张,同样导致PPCs的发生。
近年来临床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如GARUTTI等[46]在动物模型中证实了术中注射艾司洛尔可以减轻肺切除术后的肺炎;对微生物群导向治疗的研究也发现了益生元可以增强抗肿瘤免疫并明显抑制肿瘤生长,合生素(益生元与益生菌结合使用的生物制剂)的使用可以减少术后肺炎的发生,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天数,还可能有助于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和多重耐药[47-48]。随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更优化的方案或许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