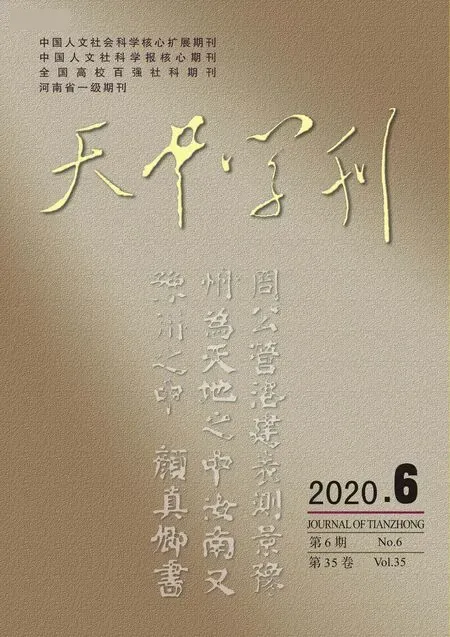明清小说欲望书写的社会表征及其审美演进
康建强,景根喜
明清小说欲望书写的社会表征及其审美演进
康建强,景根喜
(白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吉林 白城 137000)
明清时期,小说的文体概念与范畴边界虽仍未在意识领域明晰,但文本创作的实际表现业已具备鲜明完备的文体特征。作家的创作欲望强化,已普遍具有以小说书写对世界人生认知的鲜明意识。时代与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使得明清小说欲望书写的内容不断拓展并因此表现出显明的阶段性演变特征;作家源于因缘际遇而致的心灵撞击,则是小说欲望书写意涵持续深化的内在因素。这一动态发展的演进历程,充分表明小说业已承担起对世界人生图景进行审美表现的文体使命。
明清小说;欲望书写;社会表征;审美演进
根源于欲望与人以及欲望与社会的内在关联,欲望书写之于小说创作与研究,历来具有既宽泛又缺乏深度聚焦的实际表现。中国古代小说因其特具的非纯文学内涵及特征,自不例外。明清时期,小说虽仍未确立明晰的文体概念,但已在事实上具备并呈现出较为完备的文体特征与表现。基于这一逻辑性错位,其欲望书写的社会表征与审美演进尤具阐释之必要。
一、文体明晰过程中作家创作欲望的强化
在中国古代,小说是一个宽泛的文化学范畴,古人并未能将其视为纯文学文体。今见文献中,《庄子》“外物”篇首次确立了“小说”作为词语的概念内涵,其后《汉书·艺文志》初次确立了“小说”作为文类存在的使用范围,此后,“小说”便长期于二者各自独立或复杂混合的语境中被反复使用。但是在两千余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人们并未确定其明确的文体概念并清晰厘定其文体界限。中国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在文体概念以及范畴边界的非对等性,成为中国古代小说诸多研究问题彻底廓清的天然障碍。考量目下的小说文体,其核心要素有四:叙事、形象塑造、环境描写、审美言语。因此,小说作为作家之于人类存在图景的审美书写,其核心要义在于对人类欲望进行审美表达。基于这一逻辑,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形成与发展其实存在着一个由隐至显的历史过程。
客观考量历代各种小说目录所涵括的唐代以前的文言小说,其实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建设,并无显明意义。像《穆天子传》和秦汉及其之前的各种“虚诞依托”的“小说”以及魏晋南北朝之“发明神道之不诬”“若为赏心而作”的诸多志怪志人“小说”,虽然具备单一或多样的小说质性,但并非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依据古人的“小说”观念将其纳入小说范畴,那么先秦诸子中的部分篇章以及《史记》等诸多历史著作中的大量人物传记与史实叙述,其实亦可被视为小说。究其根由,基本的文体意识及其前提下的创作目的,是衡量小说步入文体建设合理轨道的必要条件。基于这一前提,唐代的部分传奇文才是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意识趋于明确的有益尝试以及文体边界趋于显明的初步标识。如唐代沈既济于《任氏传》篇末所曰“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如若结合其文本书写实际,再与前述所及诸多小说的编创目的及其文本书写表现相比对,即可窥见一斑。“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1]44其实对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确立与规范而言,中晚唐以讫宋末是尤为重要的转捩阶段。俗讲与说话艺术等通俗文艺样式,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日益明晰提供了多样且丰富的艺术经验。鲁迅先生认为,“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二为劝善”[1]66。《小说开辟》亦曾有语曰:
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噇发迹话,使寒士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曰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彻。言无讹舛,遣高士善口赞扬;事有源流,使才人怡神嗟讶。[2]
为争取听众、增加收入,说话艺人竭尽全力巧妙运用各种技巧讲述故事,以期强化讲说效果。虽然这是关于说话实际行为的渲染性评论,但据此亦可估量话本之文本表现形式的大致性状。事实上,与传奇文相较,无论与真实有何种关联,就现存变文、话本等白话通俗小说的实际表现而言,其确实更大程度地剥离了与真实刻意关联的痕迹。总而言之,强烈的讲说欲望、有意且生动的故事架构、鲜活的艺术形象以及多样技法的巧妙运用等艺术要素,使小说具备了较为明晰的体制与机制要素,小说文本的文体形态及其边界亦因此而得以明确。“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3]315探求文学意义上小说文体的确立与演进轨迹,主要应从白话通俗小说的发展演变入手。
因变文与话本现存数量、书写质量以及后人加工改编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客观导致并不能够据以对文体的整体表现,尤其是对作家编创欲望实现全面且充分的考量。小说发展至明清时期,这一问题得以彻底改观。与变文、宋元话本相较,明清时期白话通俗小说文本的文体要素、形态及其边界的现实表现业已明晰。白话通俗小说领域内章回体的出现,其显性价值在于小说容量的扩大与体制的拓展,其隐性意义在于其意味着作家创作视野的宽广度与创作野心的强度均显著加强。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其书“陈叙百年,该括万事”[4],如若再参照明人王圻所曰“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5],以及邱炜萱的“《三国志》以振汉声著”[6]505之评论,即可窥见一斑。其后,这一特征的表现愈加鲜明,如“发愤之所作”[7]的《水浒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8]之《金瓶梅》、“寄托如此,亦足悲矣”[9]的《聊斋志异》等大量小说文本均可作如是观。作家创作欲望的强化,其功用有三:第一,创作动机更为强烈;第二,创作的意图指向更为鲜明;第三,更为广泛深刻的意蕴沉潜。如《水浒后传》作者陈忱明确宣示其“为泄愤之书”[10]。在山河破碎的现实环境下,作家“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11],于是通过生动的故事建构与鲜明的人物塑造,抒发了深沉的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作为典型的文人之作,该书“反映了一个正直的正统儒者的理想意愿,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炽热情感,一种对国土沦丧的悲愤情绪”[12]。
作家创作欲望的强化,与文体发展演进过程中小说形成方式由采录编撰向有为而作的转变亦密切相关。早期小说的形成多因“采”而“录”“编撰”,此后这一编撰方式亦贯穿了直至近代的整个历史进程。虽然魏晋时期的志人小说开始出现“赏心而作”的因素,但是多数仍为或因“粗取”而成“微说”,或为“姑存之以俟博览者广焉”[13],或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14]34等各种基于实用目的而形成的小说样态。采录编撰意味着“言皆琐语,事必丛残”[14]83以及作家主观之意的相对稀薄,客观导致缺乏作家的意识创造与审美创设。有为而作的小说形成方式,自唐传奇文始广大其途。因唐传奇“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15],故而可以驱使作家有意加强创作欲望的投入。鲁迅先生认为:“传奇者流……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1]41宋人洪迈亦曾曰:“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16]据此可以确知,小说形成方式的变化,不但推动了作家创作欲望的强化,而且强化了小说的文体特征并提升了其审美表现。
唐之前的小说,以语体论,均属文言,就形成方式而言,多为采录编撰,创作的成分与程度较少与弱,其文体意识并未自觉,故而此时期小说的文体形态及其边界亦未明确。不能否认唐传奇文之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确立以及演进的重要意义,但相对白话通俗小说的重大贡献而言,唐传奇文委实不属大端。宋元时期的文言小说相对于唐代而言,虽有点滴突出或单一进展,但其整体实无需深论。明清时期,小说虽仍于词语概念与文类概念的复杂交合语境中使用,但是其文体建设已经在事实上逐渐臻于完善之境:文体意识明确,文体要素完备,文体边界清晰,文体的书写表现成熟。这于文言小说领域的实际表现即可得到明确印证,如《剪灯新话》《聊斋志异》,至于以《红楼梦》为典型代表的白话小说更毋庸赘述。
综而言之,白话小说的发展与小说形成方式重心的转移推进了小说文体的发展演进,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作家的创作欲望趋于强化,并因此推动作家的创作意识趋于明确、创作思维以及技法趋于完善,从而为明清小说进行欲望书写奠定了坚实的主体要素。
二、时移世变与欲望书写的内容拓展
“凡世界所有之事,小说中无不备有之;即世界所无事,小说中亦无不包有之。”[17]小说是世界人生图景的审美言语图式,叙事作为文体核心要素与作家表现创作命意的重要介质,是人类欲望的沉潜性凝聚。“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8]675虽然人类欲望的核心要素与主要内涵大体固定,但其具体指向与展示介质却因时代与社会的变化而具有了区别性表现。具体于明清小说的欲望书写,其时代与社会的阶段性演变极具鲜明特征。
元末风雷激荡,反元大起义虽然导致社会动乱,但也使得人们容易突破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而突显时代的现实精神,这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两部章回体白话通俗长篇小说的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章回体与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对百年历史时空中的社会动乱、诸侯争霸与割据作了生动书写,各色人物的现实行为,如挟天子以令诸侯、匡扶汉室、拥兵自重等,其深层的原发性驱动力莫不根源于个体对权力、名望、利益或者生命价值的追求。《水浒传》“以慕自由著”[6]505,尽管文本架构了显性的奸逼民反的因由与起义造反的叙述框架,其实着意描写的是宋江之于生命价值、山野草莽之于自由欲望的快感性实现。二者的欲望书写,可谓创造了令人侧目的突出表现。
明朝定鼎之后,统治者极度加强皇权,施行文化高压政策,强化思想统治,甚至以法律诏令的形式直接干预文艺创作。在此时代与社会背景下,明初的近百年间,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几乎一片空白;文言小说作品数量亦不多,只有《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颦集》三部作品集,但是于欲望书写方面却大有进益。“然此特以泄其暂尔之愤懑,一吐其胸中之新奇,而游戏翰墨云尔。”[19]无论是书写现实生活的沉郁,还是表现理想的寄寓,与之前的文言小说相比,该时期的小说更大程度地着意自我欲望书写,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心绪内转特征。
明代中叶的弘治、正德时期,时代与社会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政治领域,朝政腐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国家统治开始松弛;经济领域,农业、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思想文化领域,王守仁完成了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动摇了程朱理学对人性的束缚。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泰州学派进一步发展了阳明心学中的反道学因素,富于叛逆精神,而李贽及其倡导的“童心说”,更深度触发了人们的欲望觉醒。各种因素综合作用而产生的现实结果,就是人们对欲望追求的显性化,“靡然向奢,以俭为鄙”[20],渴望感性欲求的满足,社会上弥漫着纵情声色、及时享乐的氛围。这在小说领域有鲜明反映,即世态人情与心性描写特具突出表现。如“假托宋朝,实写明事”[21]的《金瓶梅》,对社会各色人物对酒色财气等感性欲望的过度与无耻追求,以及因此而导致的道德堕落与世风败坏,进行了繁富书写;作为“心性之书”的《西游记》,对唐僧师徒四人的欲望追求及其表现、心性磨砺进程作了生动形象的艺术描绘。这两部白话长篇小说实现了对欲望书写内容的显明拓展。此外,“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而不改也”[1]146。这一时期以《觅灯因话》《九龠别集》为代表的文言小说于世态人情的书写方面亦稍有进益。
时至明末的泰昌、天启、崇祯年间,宦官专权,党争不断,朝政腐败不堪,且由于连年灾荒,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动摇了国家统治的根基,再加上后金政权的虎视眈眈而形成的严重民族矛盾,三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在这一背景下,小说领域涌现大量时事小说,如反映魏忠贤祸国殃民的《警世阴阳梦》和反映辽东战事的《辽海丹忠录》,虽然艺术上均非上乘,但于贬斥奸邪误国、感慨民族危亡的欲望书写稍有拓展。白话短篇小说领域,作为拟话本的典范之作,“‘三言’全方位地展示了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中国市民生活五光十色的画卷,真实地描写了生活在那一时代的市井细民的理想、信念、动摇、追求、迷茫、困惑,痛苦与欢乐,爱情与死亡”[22]1174,“‘二拍’全方位地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举凡武侠、官场、佛道、江湖、发迹变泰、男女幽期、家庭伦理、社会习俗都有细腻入微的描述”[22]1192,二者经由对世态人情的全方位描写,对现实人生背景下的欲望与人性内容作了多维展示,可谓欲望内容的全息图景与绚丽画卷。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对各种反清势力进行了残酷镇压,致使一些地区“城无完堞,市遍蓬蒿”[23]。顺治时期,朝廷已开始着手恢复生产,在政治方面,借鉴明代统治经验,实行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在思想文化方面,一面招降纳叛,一面开科取士,笼络知识分子,思想统治尚不严厉。因此,南明以讫顺治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亲历了天崩地坼的亡国之痛,“目击时艰,叹奸恶,真堪泪滴”[24],其生活与心理均受到深刻影响,“君父之仇,天不共戴,国家之事,下不与谋。仇不共戴,则除凶雪耻之心同;下不与谋,则愤时忧世之情郁”[25];另一方面,由于朝代鼎革而又不愿依附新朝,黄粱事业无法继续,“奈何青云未附,彩笔并白头低垂”[26],而不得已借小说寄托感慨,以求得一时的精神安慰。反映于小说领域,具体表现为:时事小说创作的继续推进,如反思南明历史的《樵史通俗演义》,反映李自成起义的《新编剿闯通俗小说》;借名著续作形式抒发遗民心绪的孤愤之作,如《水浒后传》《后水浒传》;才子佳人小说的崛起,如《平山冷燕》等。此外,艳情小说泛滥一时,如《肉蒲团》,“谈牝说牡,动人春兴”[27],不讲人伦道德,缺乏社会意义。
康熙雍正朝时期属清代前期。康熙朝,经济得以恢复,全国实现统一,社会秩序趋于稳定。雍正朝,继续之前强化集权统治的政策,文化思想方面采取高压与怀柔两种手段,怀柔是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28],高压是为消弭异端,使“学者渐惴惴不自保”[29]。这一时期,文人的地位与心态均有所变化。部分遗民在康熙初期虽仍在创作,但格调已发生变化,至康熙后期大都已离世;出生于明清之际的文人,虽曾经历过异代的劫难与沧桑,但由于主要生活在日趋稳定的新朝,尽管偶有民族情绪但故国之情多已淡漠;还有一些文士,对现实社会虽有牢骚,但又惊心文祸,不敢直言。在这一背景下,小说欲望书写的拓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才子佳人小说在之前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直至盛行,但开始流露出比较浓重的归隐情绪,正所谓“宦海微茫,好生珍重,功成名就,及早回头”[30],如《情梦柝》《锦香亭》;第二,艳情小说类型完备而终至泛滥,但无论是纯粹的“纵欲”“宣淫”之作,还是所谓的“诛淫”之作,抑或以“息欲”为名而实则“写淫”的作品,甚或借写淫而别有寓意之作,就整体而言终究缺乏积极的社会价值;第三,代表文言小说高峰的《聊斋志异》出现,此书多数作品是蒲松龄的写心之作,在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文人情爱心理的表现、政治黑暗的鞭挞三个方面表现出长足的进步。
清代中期的乾隆年间,政权稳固,经济与文化亦达至有清一代之极盛,然而至乾隆晚年,又因和珅当权、朝政腐败而内藏危机,衰败之象渐显。“乾隆一朝,为有清极盛时代,亦为一代盛衰之枢纽也。”[31]乾嘉之际的白莲教起义,历时九年,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道光以后,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中国传统社会正酝酿着巨大变革。复杂而又丰富的社会生活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文化与小说艺术的积淀为小说创作的繁荣积累了足资借鉴的经验,小说遂至清中期而达至繁荣状态,“千态万状,竞秀争奇,何止汗牛充栋”[32]。具体于欲望书写的内容拓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通过对士林堕落以及世风败坏的全面书写,表达了对士人对文行出处以及在世方式的精神探求。第二,《红楼梦》以“大旨谈情”为主干,描写了因人性缺陷与利益趋附互相吸附而导致的沉重人生悲剧。第三,《野叟曝言》的弥足珍贵之处在于:“文学史上鲜有作者像夏敬渠一般,把自己现实人生的实际经历,心中追求的理想世界,脑中所编造夸大虚浮的幻想,都透过文学技巧呈现出来。”[33]第四,《歧路灯》“以教育为题材,开创了我国小说描写的新领域”[34],文本“道性情,稗名教”[35],对青少年的欲望滋蔓及其人生救赎作了生动书写。
1840至1911年为清代后期。这一时期清王朝因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逐步走向灭亡,具有四个主要特征:第一,中国社会转型,开启了由近代走向现代的进程;第二,因落后挨打开始向西方学习,欧风美雨西学东渐渐趋深入;第三,有识之士多关心国事,试图变革图强;第四,国人尤其是有识之士的思维转型加剧。由于西方文学思潮的传入、翻译小说的盛行、时代与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体现出由古典趋于现代且二者复杂结合的鲜明特征。具体于欲望书写,其拓展与新变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第一,畸形繁华世界的变态情欲书写,如《品花宝鉴》《花月痕》《海上花列传》《九尾龟》等狭邪小说;第二,揭示官场黑暗与社会丑陋而对现实世界进行深度审丑的社会小说,如《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第三,对未来世界寄寓理想的政治小说,如《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未来世界》;第四,关注女性生存状态寄寓女权主义思想的女性书写,如被称为“当时妇女问题小说的最好作品”的《黄绣球》;第五,“中国向无此种”[36]的科学小说,“独抒奇想……经以科学,纬以人情……间杂讥弹,亦复谭言微中”[37],如《月球殖民地小说》《新法螺先生谭》《乌托邦游记》等。
“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18]694明清小说欲望书写的内容拓展,既是时代与社会生活变化的直接体现,更是作家在时代与社会背景下精神应激的主观结果。欲望内隐于个体,又因生活而外显且趋于复杂性演变,此于上述所及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之于欲望书写的实际表现及其效能区别亦可得到显明印证。
三、生命体验趋进及其欲望书写的深化
小说是世界人生图景的审美言语图式,然而中国古代小说对世界人生图景的全息反映却存在一个渐次浸润的发展过程。相较于之前多“粗陈梗概”的实际表现,唐传奇文“叙述宛转,文辞华艳”,对世界人生图景的审美表现始大张其途。然而,文言的表现力内具天然不足,且小说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意识世界中并非纯文学样式,故而小说并没有成为文人寄寓世界人生认知的重要载体。这一状况,自宋代说书艺术繁荣之后始有明显改观,随着元代文人社会地位的普遍下沉和明代文人群体的壮大,文人处于社会下层的数量大增,另外由于白话小说对世界人生图景进行审美反映的优异表现,使得小说文体日益成为文人书写现实、寄寓理想的重要媒介。明清小说文本数量繁多,现仅以其经典为例对其欲望书写的深化做简要阐述。
《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章回体与历史演义小说的奠基之作,于元末明初率先启动了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文本于“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宏大背景下,对百年时空内的历史走向作了细致书写,其间亦对汉末动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以讫三家归晋等重大事件以及对历史走向发生重要影响的帝王权相、文臣武将作了生动描绘。关于其主题思想,历来众说纷纭。基于阐释学的角度考量,“悲剧说”相对深刻,但亦未中肯綮。“主体,即社会。”[38]百年时空内的社会状态与历史走向,终究是重要人物在欲望驱动下的行为实践综合作用的现实结果。无论是违背道德与是非要求的十常侍、董卓之流,还是“匡扶汉室”“拯救黎庶”的刘、关、张,抑或是追逐权力掌控的各路诸侯,甚至是以诸葛亮为代表的期望实现人生价值的谋士,其行为莫不源于因欲望驱动而生发的现实人间追求。“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也在改造着主观世界;而且也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人们的主观世界才能得到根本改造。”[39]在汉末动乱的时代背景下,各色人等的欲望追求最终被笼扩到社会统一的历史洪流中去。据此可以得出明确结论:《三国志通俗演义》文本以历史为框架,生动展示了个体在权力以及人生价值实现的欲望驱动下绘制的社会动态画卷。
稍后的《水浒传》通过描写一群江湖豪客聚义梁山并最终因为招安而结局悲凉的故事,谱写了一曲自由欲望与生命价值快感的悲歌。文本主要描写了两股对立性力量的博弈:一为梁山群体中的江湖豪客与山野草莽,一为权势群体中的昏庸暗昧之辈与奸邪小人。综合其整体书写,来自权势群体与奸邪小人的压迫与陷害只是显性的外部因由而非绝对的支配因素,因为梁山群体亦不具备全面且绝对的道德与是非优势。二者的核心矛盾与主要冲突在于,前者所代表的现存社会秩序与法则对后者自由欲望与生命价值快感追求的束缚。梁山群体的悲剧根源,亦非当权者的恶意作祟,而是因为以宋江为代表的在既有社会体制内实现生命价值追求的理性选择,笼罩了以武松、鲁智深为代表的追求自由欲望实现的感性选择,即招安是梁山群体悲凉结局的真正原因。相较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宏大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个体对权力以及人生价值追求的生动书写,显然《水浒传》对自由欲望与生命价值快感追求的形象书写与细致表现,价值维度更高,哲性意涵亦更为深刻。
明代中后期先后问世的《西游记》与《金瓶梅》亦是欲望书写与人类心性展示的辉煌巨著。“《西游记》当名遏欲传”[40],主要通过对孙悟空的生命历程探索、天界体系及其设定的取经历程、唐僧取经及其经历的心性考验三个方面的书写,形象展示了人类在世的精神历程。孙悟空的生命历程探索是文本的核心与主干,文本细致描绘了其欲望从无到有、由小至大,终因过度膨胀而招致覆败,其后经由反思而欲望转向并最终心性完善的发展过程。天界体系及其设定的取经历程是文本的叙述背景与宏观框架,文本通过大量否定与消解性书写生动展示了天界的世故及其刻意设计。唐僧取经是文本的叙事主体,反复描绘了玄奘的心性修持。“《西游记》是一部定性书……勘透方有分晓。”[41]如若再结合文本之于取经的普世价值、八戒的欲望揶揄、“心猿”“法性”等大量点缀性书写,可以洞明文本的核心意旨。由此可见,虽然同样写对自由欲望的追求,但是《西游记》较之《水浒传》,在心性修持对生命价值实现的内涵拓展和深度深化方面,均有明显推进。
同期而稍后的《金瓶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通俗长篇小说,其于人类的欲望书写尤有卓异成绩。其突出价值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以近于写实的笔法对“酒色财气”等人类欲望的丑陋表现进行了反复书写;第二,以近于一元化的审丑思维及其表现方法对因无节制追求欲望实现而导致的道德堕落与社会败坏进行了反复描绘;第三,对欲望过度满足的现实恶果进行了原生态的展示。文本“假托宋朝,实写明事”,是对明末社会风俗与人性状态的“非虚构”性书写。“晚明涌动着的人性思潮,当还没有找到新的思想武器冲击传统禁欲主义的时候,人的觉醒往往以人欲放纵的丑陋形式出现,而人欲的放纵和人性的压抑一样,都在毁灭着人的自身价值。”[42]清人张潮曾说:“《金瓶梅》是一部哀书。”[43]《金瓶梅》作为人类世俗欲望的丑陋镜像与肮脏图景,以全息化的书写方式反向激发了读者对欲望的内容、实现方式以及节度等进行合理引控的理性反思。此即为《金瓶梅》对欲望书写推进的关键价值所在。
时至清代,《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不仅在欲望书写的深度方面继续挺进,而且其气质与特色尤具突出表现。《儒林外史》在人类的欲望书写方面,首先架构了一个具有巨大张力的叙述前提,即在预设一个“一代文人有厄”“不讲文行出处”的时代与社会背景的同时,着意塑造了德才兼备却又不为名利所动的王冕作为淡泊欲望的形象符号。其次,文本“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以反复之笔描绘了多种类型的假名士对名利汲汲以求的丑态,进而展示了道德堕落与世风败坏的社会现实。再次,细致描写了讲求文行出处、追求礼乐兵农先儒理想的真名士在现实社会中的困顿、无奈与失败境遇。最后,文本着意架构了不为世俗及欲望所拘而自在于世的四大奇人的象征符号,但亦流露出其于现实社会中实难久长安顿的衰飒之音。层进的文本结构以及意图展示,挤压而生发出文本的核心意涵:在生命理想、行为实践与现实人世的矛盾夹缝中,文人如何调适自我以寻求自在于世的生存方式。这一具有忧郁文人气质的理性探索与诗性迷茫,显然折射了作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如何妥帖地安放自我欲望的现实困境。就此意义而言,《儒林外史》对人类欲望调适路径与方式的诗性思索,较之前作显然更进一步。
“自从《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与写法都打破了。”[3]350对于人类欲望、在世方式、生命状态及其现实路径的审美书写,《红楼梦》可谓达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境。文本首先于超现实层面描写“顽石”因欲而动以及神瑛侍者意欲“经历繁华富贵”,并将之作为叙述的起点与原发性驱动力,其后于现实人间层面主要描写了宝玉的悲剧人生历程:与黛玉的知己之爱却因家族的强制与欺骗而致悲惨结局,个人志趣因不符合家族的现实利益需要而遭蛮横阻碍以致被扼杀,自我生命追求因内在的柔弱与善懦而不能冲决外在之强力禁锢,终致无法踏上光明之阶,故而宝玉之偶尔疯癫、自言自语、多愁善感实为其生命之苦闷状态的象征。此外,文本还细致描绘了源于天然人性缺陷、纠缠于利益冲突、家族与社会弊病而导致的各种女性的缺点与凄凉结局、家族的丑陋及凄惨境遇,而宝玉最后的出走及其身后皑皑白雪上的两行脚印,“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等大量点缀性描写与叙述,最终创设了凄清静寂的浓郁悲剧氛围,即如王国维所言“《红楼梦》是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44]。当然,《红楼梦》对人类欲望、在世方式、生命境界追求及其现实路径的理性思考,其价值并不止于哲性的深邃,其诗性的浓郁其实亦无出其右者,鲁迅先生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1]165之语已切中肯綮,兹不赘述。
其他如《西游补》《歧路灯》等小说文本虽在某些方面亦不乏优长之处,但总体而言与上述六部文本的哲性深度仍有不小差距,故不再细述。
欲望书写的深化,不仅使得小说具备了深邃的理性要素,而且是浓郁诗性形成的基础与内核。总之,欲望书写的深化,不但是作家生命体验驱进的结果,而且意味着小说文体的自觉。就某种角度而言,小说实为形象化的哲学本文。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 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1[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5.
[3] 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 高儒.百川书志[G]//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227.
[5] 王圻.稗史汇编[G]//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229.
[6] 邱炜萱.客云庐小说话[G]//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
[7] 李贽.忠义水浒传序[G]//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171.
[8] 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G]//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176.
[9] 蒲松龄.聊斋自志[G]//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276.
[10] 陈忱.水浒后传论略[G]//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335.
[11] 陈忱.水浒后传序[G]//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335.
[12] 萧相恺.陈忱《水浒后传》杂议[M]//明清小说研究:第1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302.
[13] 毛晋.异苑跋[G]//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60.
[14] 刘知几.史通[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15] 赵彦卫.云麓漫钞[M].北京:中华书局,1996:135.
[16] 洪迈.容斋随笔[G]//黄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64.
[17] 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Z].新世界小说社报,1906(1).
[18] 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9] 刘敬.剪灯余话序[M]//瞿佑,等.剪灯新话(外二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20.
[20] 顾炎武.肇域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889.
[21] 刘辉.《金瓶梅》研究十年[J].中国社会科学,1990(1):216.
[22] 李剑国,陈洪.中国小说通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3]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丙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910.
[24] 李清.梼杌闲评[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403.
[25] 李梦生.中国禁毁小说百话[M].上海:上海书店,2006:161.
[26] 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序[G]//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709.
[27] 佩蘅子.吴江雪[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50.
[28] 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二[M].上海:上海书店,1981:38.
[29] 梁启超.梁启超国学论著二种[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1.
[30] 雪樵主人,等.中国十大禁毁小说文库[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621.
[31] 许子衡.饮流斋说瓷[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12.
[32] 滋林老人.说呼全传序[G]//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166.
[33] 王琼玲.由《浣玉轩集》看夏敬渠生平、著作及创作《野叟曝言》素材、动机:下[J].明清小说研究,1997(1):161.
[34] 杜贵晨.关于《歧路灯》的几个问题[M]//中国古代小说散论.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134.
[35] 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G].郑州: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93.
[36] 饮冰,等.小说丛话[G]//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76.
[37] 鲁迅.《月界旅行》弁辩言[G]//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50.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4.
[39] 吴阶平文集[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971.
[40] 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批[G]//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郑州:中州书画出版社,1983:224.
[41] 吴从先.小窗自纪[G]//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郑州:中州书画出版社,1983:216.
[42]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89.
[43] 张潮.幽梦影[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86.
[44]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静安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73.
The Social Representation and Aesthetic Evolution of Desire Writing in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ANG Jianqiang, JING Genxi
(Baicheng Normal University, Baicheng 137000, Chin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lthough the stylistic concept and the category boundary of novels were not clear in the realm of consciousness, the actual expression of the text creation already had the distinct and complete stylistic features. The writers' creating desire has been strengthened and they had the distinct consciousness of the cognition of the world life.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social life made the content of desire writing in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ntinuously expanded and thus displayed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stage evolution. It is the intrinsic factor that the desire writing connotation of the novel deepens continuously. The evolving process of this dynamic development fully shows that novel has taken the mission of aesthetic expression of the outlook on life.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esire writing; social representation; aesthetic evolution
I207.4
A
1006–5261(2020)06–0109–09
2020-05-29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2019B152)
康建强(1976―),男,山东单县人,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