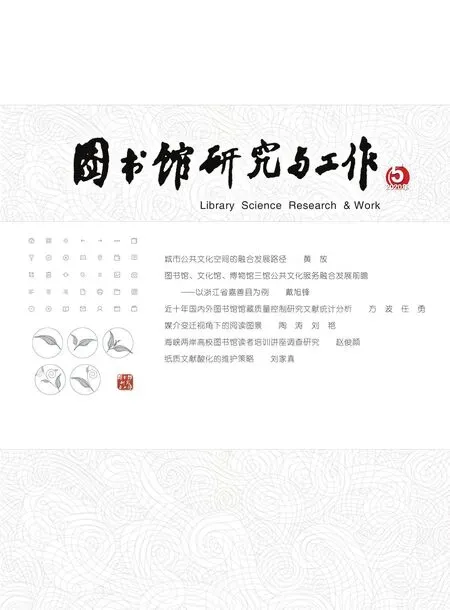媒介变迁视角下的阅读图景*
陶 涛 刘 艳
(江西省图书馆 江西南昌 330077)
1 媒介变迁:阅读从阅听到阅屏
文字载体随着信息媒介的更迭而不断丰富、融合,也改变了人们阅读的样式。长久以来,纸张作为文字的主要载体在文明传承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人们的阅读亦以“阅文”为是;而数千年之前,口耳相授、结绳记事、图腾图案反映了先人以“阅听”“阅图”作为阅读的方式。从知识考古的角度来说,“阅听”“阅图”比“阅文”出现更早。先民时期的阅听,信息是以人的声音为介质进行传播,因此,人的身体作为一种媒介在信息的输出与接收中起主导作用。“阅图”主要是在洞穴壁上赋予图案以输出文化符号与象征意义。象形文字的出现代表着“阅文”时代的来临,从龟甲到青铜再到陶片,从竹简到布帛再到纸张,文字的载体虽几经变革,但“阅文”一直长存于人类阅读的历史长河中,并占据主流地位。然而,随着图片印刷技术、电子音像技术的发展,“阅图”“阅听”开始回归。电视、电影技术的成熟,移动互联、信息技术革命以及智能电子设备的普及使阅读又出现新的变化,从静态的图片到流动的画面,从无声的世界到有声的世界,人类阅读的视界被打开形成新的阅读样式——阅屏。在屏幕中有声音、影像也有文字,是“阅听”、“阅图”(包括动态画面)与“阅文”的融合。本文以“阅屏”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互联网时代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阅读转向,分析由此形成的阅读图景。
2 互联网时代的阅屏
2.1 阅读主体:电子公民
电子公民是现代人在互联网空间中作为阅屏实践主体的化身,表现为一个虚拟的“ID”号、网名或是一段IP地址。现代人在数字信息技术的加持下被集体赋能,在“在线”(虚拟世界)与“在世”(现实世界)之间切换自如[1]。认识“电子公民”这一概念,需要理解“身体”的哲学意义。唐·伊德在其著作《技术中的身体》 中给“身体”做了三个层面的阐释:①身体一,即人生而为人且在世的肉身身体;②身体二,即社会和文化意义层面的身体,是福柯所指的文化构建的身体,是“活着的身体”通过社会、政治、文化等层面构建的身体,是具有思想、理性、精神的身体,身体一是身体二的容器;③身体三,即技术身体,是被技术具化的身体,既穿越身体一也穿越身体二[2]。在互联网空间中,现代人的肉身身体是无法进入电子屏幕与其他电子公民交流、互动,而只有借助技术的身体才能进入虚拟网络世界。存在于网络空间中的不是现代人的肉身,而是他的“网名”,即技术身体。这个“网名”在网络空间中所有的评论、留言、浏览痕迹等构建了这个网络读者的思想、文化特征,成为读者在网络空间的“身体三”,代替现实生活中的肉身阅屏者在网络空间中自由书写、自由传播。现代人足不出户便可通过技术身体购买全球好物,不用去图书馆便可阅读各类图书,不用参与现场读书交流便可与全国读者探讨阅读感想,不用身临现场便可以纵览天下新闻……相比肉身身体而言,电子公民在阅屏实践中完全解除了时空的束缚。现代人可以通过操控技术身体而实现在虚拟世界中的自由行走。这便是与阅屏者在观看“电视”“电影”屏幕时最大的不同。“阅屏”主要分为阅电视、电影屏幕,阅电脑、手机屏幕,鉴于对电子公民的理解,本文将不具有电子公民的阅电视、电影屏幕的实践排除在外,着重于电子公民的阅屏现象,包括在电脑、手机屏上的阅文、阅听与阅图。
2.2 当前变化:阅屏转向
《阅读辞典》认为,“阅读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活动。广义的阅读包括一切对主体上的外部世界及其意义的解读,狭义的阅读是一种从书面语言和其他书面符号中获得意义的社会行为、实践活动和心理过程”[3]。以广义阅读来看,是指在一切形式的信息载体中,如文字、声音、影像、肢体动作、行为痕迹等,获得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与认知[4]。正如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指出,阅读书面上的字母(文字)只是它的诸多面相之一。天文学家可以阅读天空,建筑学家阅读土地,动物学家阅读动物痕迹,音乐家阅读音符,心理学家阅读梦境等[5]。“屏”媒介的出现,使得无论是静态的文字还是动态的声音与影像均可以通过屏幕实现,可以说当前已进入多媒介协同共生的媒介生态情境。相比通过电视屏幕、电影屏幕获得信息的“阅屏”而言,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的“阅屏”具有以下不同。
2.2.1 身体转向
前文阐释了“身体”的三层意义。在电视、电影媒介下,人是肉身的人在真实的物理空间中“阅屏”。此时的人不具有技术的身体,不能够进入到电视、电影中与其他观看者交流,而只能与肉身身体共在同一空间的人交流。但是,在电脑与手机屏幕下的“阅屏”,在物理空间的肉身身体被技术赋能拥有了技术身体,能够进入到网络空间中与全世界的人交流互动,无需肉身身体共在,完全突破时空限制实现无障碍的交流互动。从人类阅读进化史来说,身体在阅读中承担着传播的角色,在口耳相授时期,肉身的身体就是一种信息载体与媒介。而今在网络空间中,技术的身体即电子公民在网络空间中与他人互动,则会在其中留下语言痕迹,这些痕迹不会因为电子公民的离线而销声匿迹,而是永久保留在网络空间中供他人阅读浏览与评论[1]。因此,不论电子公民是否在线,其留下的语言符号都会被其他人阅读或接收,电子公民便是网络空间中作为媒介的、技术的身体实现着信息的传播与扩散。
2.2.2 空间转向
互联网时代的阅屏在空间上的转向,主要体现为两点:①从现实到虚拟。电视、电影的阅屏人还是肉身的人,人还在现实的空间中。电脑、手机的阅屏,人的身体,既有肉身的在场,也有技术身体的在线,既在现实空间中也在虚拟空间中,这一点电视、电影的阅屏不可能同时拥有。②从固定到移动。电视、电影、电脑的阅屏需要肉身身体在固定的空间,而对于手机的阅屏而言则是移动的。移动互联技术、新媒体技术等改变了现代人在看电视、电影、电脑时需要身体在固定空间中阅读的场景。现代人可以在公交上、地铁上,甚至是在走路中、旅途中掏出手机进行阅读、社交或发布信息。
2.2.3 社交转向
在电影、电视的阅屏中,读者无法与屏幕内的人物、内容进行互动,读者无法穿越屏幕,因此,读者与屏幕之间存在鸿沟。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却发生了变化,现代人的肉身身体成为网络空间中自由行走的电子公民,可以借助其技术身体在网络空间中与他人交流。在电脑、手机的阅屏中,读者与屏幕之间的鸿沟通过信息技术得到了弥合与填补。以往传统阅文是读者私密的、个体化的阅读,而阅屏中的阅文基本都带有评论、点赞、阅读圈、交友等功能。另外,微信公众号、微博大V推送的信息也被广泛传播,读者可以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实现信息获取与阅读。社交与阅读的融合使传统阅文转变为社会化阅读,读者可以肉身身体操控其技术身体化成具有信息输出、信息接收媒介作用的电子公民,每个电子公民都是互联网网格中的信息发射塔,同时也是信息接收器,成就互联网中电子公民交流互动狂欢的文化景观。
2.2.4 自由转向
在电视、电影的阅屏中,阅屏者的阅读是线性的阅读,因为读者一旦开启阅屏则无法往回观看,而在电脑、手机的阅屏中,不论是阅读文字、收听音频还是观看视频,阅屏者可以在阅读或观看进行中往回看、从中间看,阅读或观看的顺序可以被打乱,可以跳跃,是一种非线性的阅屏实践。这是因为肉身身体的阅屏者在电视、电影媒介下是不自由的,无法控制屏幕中所呈现内容的快慢与顺序,而只能在阅屏时与屏幕中内容的呈现进度保持一致。然而,在电脑、手机前阅屏时,阅屏者是网络空间中的电子公民,能够跨越读者与屏幕之间的鸿沟,因此,电子公民在阅屏中是自由的。另外,超级链接是互联网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6]。在互联网中阅读,在网页的底端一般会推送与阅读当前网页相似、相关的内容,这就是超级链接,是互联网阅读的特征之一。超级链接的出现使阅屏者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的超级链接自由跳转、转移当前页面,进入下一个内容的阅读。
2.2.5 智慧转向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运用给媒介生态系统带来智慧化的转向,人工智能技术被应用于数据线索的发现、采集、聚合以及内容的生产、分发等环节[7]。超级链接的推送与算法技术密切相关,而算法技术赖以依存的数据源来自于电子公民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痕迹或称数字足迹[1]。算法技术与信息推送相结合是人工智能进入信息输出环节的主要方式之一,主要体现为个性化推荐。例如:阅屏者作为电子公民在网络空间留下的阅读痕迹会被后台算法技术采集信息痕迹,分析出电子公民当前阅读兴趣或方向,并通过超级链接推送与电子公民阅读方向相近、相关的内容,循环往复同质化内容推送以满足电子公民当前阅读需求。因此,电子公民时代的阅屏实现了个人阅读内容的精准化、智慧化推送。
2.2.6 体验转向
传统的阅屏,电视、电影只需阅屏者听觉、视觉器官参与,而在电脑及手机端等移动电子设备上阅屏则需要指尖的触觉,双击标题打开内容链接,观看视频的开始与结束或者快进、慢进都需要手指触觉的配合。在手机阅读APP中电子图书的阅读实现了现实图书阅读翻页一致的效果。2014年万维网的核心语言(HTML)第五次修改完成,被称为H5,H5技术对数字内容的呈现带给阅屏者不一样的体验[8]。在建国70周年国庆大阅兵中就有“虚拟观礼票”,阅屏者只需点击链接就可以直达大阅兵观礼台现场。2012年《成都商报》发布“拍拍动”APP应用,阅读者通过手机扫描报纸内容,手机中展现的内容便会活动起来,还配有表情;扫描报纸上的广告越野车,阅屏者能通过手机360°观看车子外观并能以互动的方式试驾;扫描文娱版出现的明星后手机会播放明星演唱会的歌曲[9]。这是逐渐成熟的VR/AR技术在数字出版中的应用,给阅屏者带来全景视觉、多重感官体验的阅屏体验。
3 阅屏转向带来的阅读图景
3.1 碎片化与浅表式阅读获得现代人青睐
对于碎片化阅读,从虚拟空间来说,阅屏者技术身体的虚拟在场(身体转向)以及自由向度(自由转向)是形成碎片化阅读的原因之一。读者通过技术的身体可以自由选择阅屏内容的观看顺序、快慢、反复等,也可以直接看结尾,也可以跳跃式阅读,超级链接的出现也分解了读者在某一内容上的注意力,此时的阅屏实践是非线性的,断断续续的阅读呈现出碎片化阅读的景象;从实体空间来说,阅读空间的移动化使阅屏者能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内容体量较小的阅读,一段完整的内容可能被分割成几次阅读,呈现出片段化阅读的特征。对于浅表式阅读,①碎片化、片段式的阅读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浅性理解。从时间上说,碎片化的时间本身就无法满足深层理解的要求,因为读者乘地铁、坐公交时要把注意力集中于听站名上,因此无法将沉浸式注意力停留在手机屏幕的内容中,阅读方式往往采取浏览式,或者在选择阅读内容时选取短小、消遣性、娱乐化、不需要深度理解的内容。②巨量级信息体量,迫使读者在阅读时快速地浏览,或者采取抓取关键信息的跳跃式阅读方式,以便以少量的时间成本获得最多的信息[10]。在网络空间中几乎每个网络页面底端都会有超级链接的推送,点击之后下一个超级链接又会出现,如此循环反复,读者应接不暇;电子公民在网络空间中互动交流留下的语言痕迹不会随着电子公民的离线而消失,其他电子公民依然可见,这也是信息量增大的原因,再加上各个媒体的信息发布、推送,如此庞大的信息体量,读者阅屏的时间成本增加,只能以信息速食的方式快速浏览、不假思索的浅表式阅读。
3.2 共享式与互动式阅读重构人际关系链
阅屏的社交转向直接带来社会化阅读样式在互联网空间中的凸显与被广泛实践。社会化阅读是读者将阅读的内容及阅读时产生的想法和创意与别人分享、交流、互动,共同探索思想和理念的阅读方式[11],共享式、互动式是社会化阅读的重要特征。在当前技术环境下,一是在移动阅读APP应用中加入社交板块,二是用户、媒体在社交平台发布、推送信息与内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信息流动的“基础设施”,成为一种“社会化引擎”[12]。社会化阅读是基于内容与关系互动的共享式阅读[13],因此它不仅是图书内容的共享更是人际关系的互动。在网络空间中实践社会化阅读的电子公民因为共享与互动而形成基于互联网的人际关系链条。根据“六度分隔”理论,人们最多通过六个人的介绍就可以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6]。可见,在互动与分享的社会化阅读中构建人际关系链的空间被压缩、时间被缩短,阅屏者可以因为共同的关注焦点、共同阅读爱好或方向而在网络空间中群聚,形成相同志趣的文化交流圈,进一步实现网络群体的重建与网络人际关系链的延伸,这对于实现圈层传播加速信息裂变具有积极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共享式阅读在帮助一部分人知识增值的同时又瓦解一部分人深度参与文本的机会,使其产生思考的惰性而人云亦云,可以说共享式阅读在一定程度上也驱赶了“读者”,他人的审美经验一旦共享,对于其他未阅读的人来说文本、视频里所传达的信息就是前置的,容易不经思索、先入为主地就接受了他人语言符号中所传达的文化内涵与意义,因此,对于某些读者而言,共享式阅读方式成为他们的替代性想象。
3.3 定制式与个性化阅读可链接用户消费
在技术身体的支持下,阅屏者在互联网空间中留下大量的浏览痕迹,各移动阅读平台将算法技术应用于电子公民的浏览痕迹挖掘,从而实现个性化阅读推送。在信息体量巨大的网络时代,内容是吸引读者注意力的重要据点。可以说,各信息推送媒体发布的内容赢得了人气就赢得了关注,各信息平台流量的争夺便是注意力的争夺。好的内容、符合读者阅读需求的内容就能消费用户的注意力,能够粘合用户,甚至实现知识付费。例如,读者在喜马拉雅移动电台APP中反复收听与诗词相关的音频,后台算法便会计算该读者的阅读倾向,从而在“猜你喜欢”中推送与诗词歌赋相类似的音频专辑。音频专辑一般由入驻喜马拉雅移动电台APP的主播自行发布、定期更新,既有付费也有免费。读者通过关注或购买音频专辑即消费了注意力或进行了知识付费,读者实现了内容定制式与个性化阅读,主播则实现了知识变现。在微信阅读中,读者可能通过某一篇推文而关注推送该文的公众号,实现读者阅读内容的个性化订阅,能够消费读者的注意力。另外,快手、抖音、小红书、淘宝等平台,阅屏者可能关注某一主播强烈推荐的物品、用品、图书而产生购买的消费行为。因为在互联网空间中,空间距离对于电子公民而言是趋零的,从阅读内容到购买意愿再到购买,其技术身体可以在互联网空间中任意位移,但是其肉身身体不用位移便可以完成整个流程,技术身体让这一切变得简单便捷,观看内容与消费行为之间的距离只是心理的距离而没有空间的距离,而心理就在于信息接收者对信息内容的订阅、购买与否,是选择消耗注意力还是选择消费行为,因此阅屏者阅读的内容可以链接用户的消费,不论是注意力还是货币。
3.4 感官化与体验式阅读带来临场沉浸感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人们从纸质图书、电视、电影等信息载体中获得知识与信息,纸质图书需要视觉与触觉,电影电视需要视觉和听觉。而随着5H、VR/AR等技术的应用,现代人的阅屏装置得到了重构,彻底改变了内容的呈现方式。内容与受众的关系逐渐演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受众融入虚拟与现实的梦幻交织场景之中[9]。阅屏者感官化与体验式越来越具有十分明显的临场感,因而出现一种新的阅读范式——场景阅读,具有沉浸性、交互性、重感官体验的特征,给予阅读者直观、形象、可感知的阅读体验。这种阅读方式在数字出版、新闻推送、国家重大事件中得到广泛运用。例如:“军装照”体验、“国庆阅兵虚拟观礼”等,阅屏者通过参与这类H5新闻的阅屏实践与体验可以产生情感共鸣。
4 结语
信息技术和科技手段的日新月异推动信息媒介的持续发展与变革,现代人信息的输入与输出亦随之而变,这不仅是信息载体的变革,更是阅读方式的革新。在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中,国民数字化阅读接触的主要内容以阅读新闻、社交和观看视频为主,娱乐化和碎片化特征明显,深度图书阅读行为的占比偏低[14],可以看出,“阅屏”现象相比传统的“阅文”,如今更占据现代人绝大部分的阅读时间,阅屏下的阅文、阅听、阅图又呈现出碎片化、浅表化、社交化、消费性以及场景化的特征,构成了当前时代的阅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