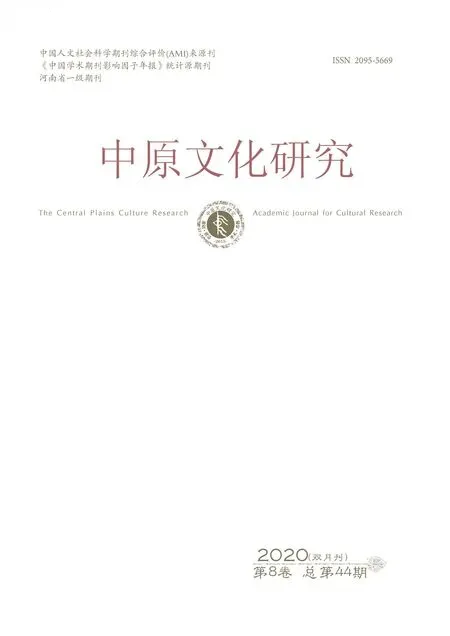张养浩与元代北方学统的建构*
刘成群
一、张养浩对赵孟的疏离与对姚燧的崇尚
现存文集中没有记载,确乎不能说明两人从无交集,如果强行认定,似乎有些“默证”之嫌。然而,这种状况却也能证明一个情况,那便是张养浩并不特别认同赵孟文坛宗盟之地位,否则他不会对赵孟表现出如此明显的疏离姿态。在张养浩的心目中,所谓的文坛宗盟其实另有其人,此人便是前辈文章大家姚燧。张养浩第一次见到姚燧的时间大概是在至元三十年(1293年),当时张养浩只有24 岁,正如其记载:“走年二十四见公于京师,时公直学士院。”[2]110到后来,他正式进入姚门并得到姚燧亲炙,在《送李溉之序》中,张养浩写道:“曩余谢太子文学,数往来今翰长牧庵姚公门,时李君溉之从牧庵学。”[2]113姚燧对张养浩也十分赏识,称其曰“年少而志厉,续学而善文”[3]404。
张养浩在《送姚学士》中称赞姚燧云:“游目当今士,独公文柄操。”[2]42姚燧去世后,张养浩有文祭之,在祭文中,张养浩谓姚燧“斯文之宗伯,旷百祀而一人”[2]201。在《牧庵姚文公文集序》一文中,张养浩赞颂姚燧云:
皇元宅天下百许年,倡明古文,财牧庵姚公一人而已。盖常人之文多剽陈袭故,窘趣弗克振拔。惟公才驱气驾,纵横捭阖,纪律惟意……章成则雄刚古邃,读者或不能句。尤能约要于繁,出奇于腐,江海驶而蛟龙拏,风霆薄而元气溢,森乎其芒寒,皓乎其辉烨。一时名胜,靡不鳃鳃焉自所有,伏避其锋。[2]110
在张养浩的眼中,姚燧系一代文章巨匠,当世文坛之主盟者,其地位固是巍然而不可撼。然而姚燧生前“颇恃才,轻视赵孟、元明善辈”[4]4060,既然姚燧对赵孟有如此成见,则纵使赵孟有再高的成就,恐怕一时也难入张养浩之眼。
二、姚燧对北方学统的建构
姚燧出生在理学家庭,3 岁时生父死,遂由伯父姚枢收养。姚燧在18 岁时正式拜许衡为师,一生以“从鲁斋先生最故且久”[3]67而自豪。姚枢与许衡之学出自赵复,属于南方北上的朱子学形态。但到了姚枢与许衡这一代,则明显加入了金源儒学的特点,譬如许衡对卜筮、历算、医药的青睐,对“治生”的崇尚,就与南方理学传统意义中的淳儒有所不同。然而,许衡去赵复未远,对于南方理学的一些原则性的内容还是极为尊崇的,如许衡就十分维护理学家们“作文害道”的观念,他一直极力倡导“文章之为害,害于道”[6]72之说,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强调“能文之士必蔽”[6]75,甚至不无偏激地说:“文士与优孟何异?”[6]72许衡也曾教育姚燧说:
弓矢为物,以待盗也。使盗得之,亦将待人。文章固发闻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将何以应人之见役者哉?非其人而与之,与非其人而拒之,钧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3]68
姚燧虽然出身于理学,但却对乃师“文章之为害,害于道”的观念不予认同,他认为:“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3]69就是说,文章因为道而轻重,同时道也因为文章而轻重,如此一来,就把“文章”与“道”放在一个完全平等的位置上,查洪德就此评论说:“‘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不承认文对道的从属或依附,文章不一定要传道,特别是程朱之道。这在当时,是很有理论气魄的。”[7]
到了姚燧这一代,北方的学术传承已经与当年的赵复之学颇有不同了。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变化,乃与姚燧对金源儒学的吸收有关。姚燧是杨奂的女婿,曾“婿其家,得观《还山集》者于夫人所”[3]49。杨奂系当时研究韩文的专家,元好问就记载其撰有关于“删集韩文”的专著,并谓是书曰:“划刮尘烂,创为裁制,以蹈袭剽窃为耻。”[8]1452此书即为《韩子》十卷。《元史·姚燧传》记载:“二十四,始读韩退之文,试习为之,人谓有作者风。”[4]4057姚燧自24 岁始读韩文并试习为之,这肯定受到杨奂的影响。
杨奂是从金末文风革新与儒学价值重估思潮中成长起来的人物,他与金末主导文坛的名公巨卿都有交往,如元好问记载曰:“礼部闲闲赵公、平章政事萧国侯公、内翰冯公、屏山李公,皆折行位,与相问遗。御史刘公光辅、编修张公子中诸人,与之年相若,而敬君加等。”[8]1456四库馆臣谓杨奂有“中原文献之遗”[9]1430,良有以也。金亡之后,杨奂与元好问交游最多。元好问赠给杨奂的诗称:“古来知己难,万里犹比邻。”[10]182而杨奂思念元好问云:“短诗聊遣兴,羞向故人传。”[11]249两人深厚友谊可见一斑。金亡后,元好问成为代表金源文化的一代宗工。姚燧对岳父的这位挚友频频提及,在姚燧《注诗音鼓吹序》称:“国初遗山元先生为中州文物冠冕,慨然当精选之笔。”①姚燧又有《三老图三首》,其二曰:“从卧封龙十顷云,闳中肆外溢为文。若非用事多排比,党蔡诸公不足群。”[3]539此诗题中有“三老”,首句有“封龙”,当指“封龙山三老”。《元史·张德辉传》载有张德辉与“元裕、李冶游封龙山,时人号为龙山三老云”[4]3826,元裕当为元好问。《三老图三首》其二则赞美元好问无疑,评价之高溢于言表。
姚燧虽然“有得于许衡,由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为世名儒”[4]4059,但更为明显的是,他经由杨奂、元好问上溯金源,尤其是将金源儒学中“文”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孛术鲁翀赞云:“圣朝牧庵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奋而宗之。”[12]480吴善赞云:“我朝国初,最号多贤、而文章众称一代之宗工者,惟牧庵姚公一人耳。”[3]655又柳贯则赞云:“故大德、至大、皇庆之间,三宗继照,天下乂宁,而公之文章,蔚为宗匠。”[5]699
姚燧为元初文章大家,其“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的观念代表着北方学统的价值追求。姚燧身上的理学素养虽然来自南方,但到了他这一代,已与南方理学学统明显不同,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离道倾向”[13]29。当南方儒士赵孟或带有南方学养的元明善也以文章见称时,南北学统的差异就作为大背景显现了出来。姚燧在世的时候,赵孟在北方的影响远不及后来,虽则如此,姚燧还是显示出一些似嫌狭隘的举措,其中维护北方学统的优先地位或许要大于文人之间的意气之争。
三、元代南北文化的博弈
忽必烈平宋后,元廷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但在国家制度层面,元代的北方与南方长期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在南北差异这一问题上,李治安曾给予了一系列的关注,尤其是《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一文专门探讨元朝统一后国家制度层面“南、北因素的并存博弈”[14]的状况,给人以极大的启发。与国家制度层面相似,元代的文化也存在南北隔膜并相互博弈的现象,这种隔膜与博弈对元代整个文化格局都起到了相当大的形塑作用。
元代文化之南北隔膜可以追溯到靖康以后的南北对峙时期,大抵因为天限南北的政局,从而导致南北文化交流的断绝。很多南人在南宋亡后方才看到北人的著述,正如俞德邻所言:“疆土既同,乃得见遗山元氏之作。”[15]77正是因为对北方了解有限,南方儒士普遍以“斯文在兹”而自居,他们甚至认为:“江南士人曩尝谓淮以北便不识字,间有一诗一文自中州来者,又多为之雌黄,盖南北分裂,耳目偏狭故也。”[16]204当然,北方儒士也在竭力维护着自己的学统,并把上溯金源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在政治层面,他们也以金源为正统,如郝经主张:“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王法。”[17]446如王恽认为:“据亡金泰和初,德运已定,腊名服色因之一新。今国家奄有区夏六十余载,而德运之事未尝议及,其于大一统之道似为阙然。”[18]3489-3490显然都是以元朝接续金源。在合法性的建构层面,政统与学统是相得益彰的。
姚燧出身于理学,但他在《国统离合表序》中对朱熹包含有政统意识与学统意识的《资治通鉴纲目》颇有指摘,饶宗颐就曾指出:“元儒对朱子《纲目》有意见者,如姚燧之《国统离合表》,其著者也。”[19]52姚燧乃杨奂之婿,杨奂晚年曾作《正统书》,有很多意见与朱熹之论相左,而符合北方儒者的价值取向,姚燧指责朱熹之失,当与杨奂的认识一致。
由于所尊崇的政统、学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起码在元初,南北儒士存在着明显的隔膜。南方儒士虽然偏激地认为北方“不识字”“雌黄”,但由于北方儒士在政治上占尽先机,前者较之后者明显处于下风。像赵孟甫入大都时就曾遭到耶律楚材之孙耶律希逸的质疑,议“至元钞法”时又遭到一位杨姓刑部郎中的指责:“昔金人定法,亦与大儒共议,岂遽无如公者!”[20]518不过赵孟得到了忽必烈的垂青,还是留在了元廷。但并不是所有南方儒士都这样的幸运,与赵孟一同北上的大儒吴澄就不得不铩羽而归,临行前向赵孟抱怨说:“吾之学无用也,迂而不可行也。”[20]132
不止是吴澄,发生在吴澄弟子虞集身上的一件事也十分耐人寻味。《元史·元明善传》载:
(元明善)初在江西、金陵,每与虞集剧论,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诸经,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汉以来先儒所尝尽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为文辞,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惊,鬼神之灵变’然后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欢,至京师,乃复不能相下。董士选之自中台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门外,士选曰:“伯生以教导为职,当早还,复初宜更送我。”集还,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选下马入邸舍中,为席,出橐中肴,酌酒同饮,乃举酒属明善曰:“士选以功臣子,出入台省,无补国家,惟求得佳士数人,为朝廷用之,如复初与伯生,他日必皆光显,然恐不免为人构间。复初中原人也,仕必当道;伯生南人,将为复初摧折。今为我饮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酹之。起立,言曰:“诚如公言,无论他日,今隙已开矣。请公再赐一卮,明善终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饮而别。[4]4173
或许在姚燧看来,元明善在南方成名,沾染了很多南方因素,不过就其一贯的表现来看,元明善还是一个标准的北方儒士,譬如他对南方儒士以朱熹之说为宗的取向就颇不认同。虽然朱熹之经说颇有集大成的气象,但也不是全能全善,元明善对虞集的批评可以代表当时很多北方儒士的看法。当然,虞集批评元明善文辞非性情之正,恰恰指向其文气纵横的一面,这也正是北方儒士承袭金源“文”所要追求的效果。
在元初乃至很长一个历史阶段,北方儒士都是稳稳占据上风的,在这种优胜的感觉中,北方儒士有时候也会表现出高风亮节来,他们也会借助仕宦南方的机会,表达对南方文化的某种欣赏,甚至还会模拟南方的某些风格创作,但这些必须建立在没有文化紧张感的前提之上。当北方儒士的地位不再那么稳固,优胜的感觉不再那么明显,则文化上的焦虑就会与之俱来,建立自己学统的合法性便要提上日程了。
东南士聚辇下,如四明公桷、巴西公文原、雍郡公集,有盛名公卿间。既而贡集贤奎章、周待制应极荐之,皆驰骋清途。公(揭傒斯)与清江范梈德机、浦城杨载仲宏继至,翰墨往复,更为倡酬。[21]140
四、张养浩对北方学统的建构
在金代的学术语境里并无太多对理学的推崇,而对古文运动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陈广宏就曾指出,金末时代赵秉文、杨云翼等儒士所主导的“古学复兴风潮”确实“推许其对唐宋古文传统的接续”[22]。金亡后,元好问申明“唐宋文派乃得正传”[8]256-257之义,以金源文化集大成者自居,展现出古文运动的某种遗风。姚燧对“文”的偏好经由杨奂、元好问等人可以追溯到金末儒学价值重估思潮。这一思潮崇尚宏观的“文”,其外表是辞章,其内核包含有丰富的“治道”内容,即这种宏观的“文”乃是“治道”与“文辞”的综合体,“在价值诉求与表现形式等层面更接近于唐宋两代古文运动”[23]。与赵秉文等人相似,姚燧特别推崇具有“文以载道”观念的欧阳修,以之为楷模,如其云:“世复有班孟坚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欧阳子”。[3]69
对于姚燧的这一特点,张养浩看得十分真切,他并不仅仅称颂姚燧“独公文柄操”或“斯文之宗伯”,同时还尤其强调姚燧接续唐宋古文运动的价值与意义。在张养浩那里,常将姚燧与唐宋文章大家并列,如“豪放抗衡于坡老,正大并辔乎昌黎”[2]201,或将姚燧比作韩愈、欧阳修,如其云:“公与二子代虽不同,要皆间气所钟,斯文宗匠,振古之人豪也。”[2]110在张养浩笔下,姚燧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古文运动的意义,在元明善的神道碑铭中,张养浩写道:
夫古文自唐韩、柳后,继者无闻焉。至宋欧阳公出,始起其衰而振之,曾、苏诸公相与左右,然距韩、柳犹有间。金源氏以来,则荡然无复古意矣。天开皇元,由无科举,士多专心古文,而牧庵姚公倡之,骎骎乎与韩、柳抗衡矣。[2]172
接续唐宋古文运动乃是金末以来北方儒士的使命感之所在,姚燧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而张养浩着力强调姚燧的“古文”面相,其目的无疑是以历史依据来建构北方学统的合理性。在建构北方学统的过程中,姚燧虽然是张养浩心目中的标志性人物,但如刘因、王恽极富“文”之追求的北方儒士,张养浩也一并予以礼赞。如在刘因、王恽谢世后,张养浩分别有诗挽曰:
白发山林仅四旬,两朝不肯屈经纶。才名暗折世间寿,气节伟高天下人。康节纵吟无限乐,希夷高卧有余春。一生怀抱谁能识,他日休猜作逸民。[2]54
束发耽经晩益勤,平生精力尽斯文。前朝十老今余几,当代三王独数君。李贺屡烦韩愈驾,羊昙空阻谢安坟。玉堂寥索人何在,落日溪窗满白云。[2]84
邓绍基曾指出:“刘因的论诗见解基本上继承了元好问的论诗主张。”[24]407查洪德认为刘因诗文有“派继中州”[25]的特点。所谓的“中州”,当然指的是通过元好问所汲取的北方文化传统。王恽乃是元好问弟子,常常以“文键亲承謦欬余”[18]1453自豪,或曰“分眀昨夜梦遗山,指授文衡履间”[18]639,甚至以继承元好问而自居,如其云:“党赵正传公固在,阳秋当笔我奚任。”[18]756对于刘因,张养浩并不仅以“逸民”视之,而强调其他人未识之怀抱;对于王恽,张养浩着力渲染其“尽斯文”的一面,显然都是从维护北方学统的角度出发的。
除了刘因、王恽,像许衡与李孟等并非特别长于“文”但在北方儒学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张养浩也十分看重,如评价许衡:“我朝鲁斋许文正公衡,其所陈于世祖皇帝前者,无非尧舜禹汤治天下大经大法,三代以降,皆无所及。”[2]126评价李孟:“辩章秦国公早以儒术事皇上潜邸,从行中外且二十年,格论嘉猷,所以开广天聪、封植国本、阴毗治道、以棐以迪者,靡遗馀力。”[2]123可以看出,张养浩主要从“治道”层面审视许衡、李孟等人,即便是在理学史赫赫有名的许衡,张养浩也不特别阐明其理学意义。总之,在张养浩的笔下,无论是许衡还是李孟,体现的是北方政统与学统同构的特点。
除了姚燧之外,张养浩还特别推崇元明善。张养浩与元明善交游甚多,两人与曹元用并称“三俊”。在张养浩的文集中可以看到不少酬赠元明善的诗文,如谓其“文辞踔厉奇刻,肖其为人”[2]115,显示出明显的推崇之意。元明善去世后,张养浩有挽诗云:“平生碑版天留在,不朽何须借景钟。”[2]65张养浩对元好善的推崇,乃是以其接续姚燧,如其曰:“天开皇元,由无科举,士多专心古文,而牧庵姚公倡之,骎骎乎与韩、柳抗衡矣。其踵牧庵而奋者,惟君一人。”[2]172不过从现有资料来看,元明善对姚燧并未有特别敬礼之意,倒是张养浩自己颇有接续姚燧的想法,张养浩在《祭姚牧庵先生文》中曾提问曰:“今公云亡,孰柄文兮。”[2]202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整篇文章确乎暗含以道自任的主旨。在《牧庵姚文公文集序》中,张养浩接续姚燧之意图则体现得更为明了,如其云:
窃惟韩昌黎文,李汉氏序;欧阳公文,苏轼氏序。公与二子代虽不同,要皆间气所钟,斯文宗匠,振古之人豪也。走何人,敢于焉置喙?辞不获,因纪平昔所尝得诸心目者,姑副所恳。[2]110
姚燧指授过的弟子很多,甚至还形成了一个具有流派性质“姚门文章家群”,“群体的核心成员张养浩、孛术鲁翀、刘致、贯云石、李泂等人”,他们文章的“共同点是古雅刚方、舂容盛大、动荡开合、气势宏壮、时见奇峻,是其峻洁人格的反映。他们也有平易畅达之作,则得之于作者浩然正大之气”[26]。孛术鲁翀是文章家群中影响力仅次于张养浩的人物,曾为张养浩的《归田类稿》作序,也是以张养浩接续姚燧,如其言:“圣朝牧庵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奋而宗之,卓然有成,如云庄张公,其魁杰也。”[12]480这恐怕也代表着时人的普遍看法。
张养浩突出姚燧文章的“古文”意义,乃是为了接续古文运动,以证明北方学统的合理性,并为自己接续北方学统寻找依据。元初,北方儒士由于政治上的优越地位而表现出明显的学统优胜感;但到了元代中期,赵孟等南方儒士在大都的文化影响力与日俱增时,一些北方儒士则明显表现出了文化上的紧张感,张养浩对北方学统的建构与维护就是这种文化紧张感的具体表现。
注释
①在四库馆臣所辑的《牧庵集》中有《唐诗鼓吹注序》一文。此文据陈开林考证,“乃拼接武乙昌序文前半部、姚燧序文后半部而成”。陈开林检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著录的元刊十卷本《注唐诗鼓吹》,得赵孟、武乙昌、姚燧三序。其中姚燧序即为《注诗音鼓吹序》,我们所引即为此篇序言中的部分文句。见陈开林:《四库本〈牧庵集〉所收〈唐诗鼓吹注序〉辨误》,《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4 期,第50—5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