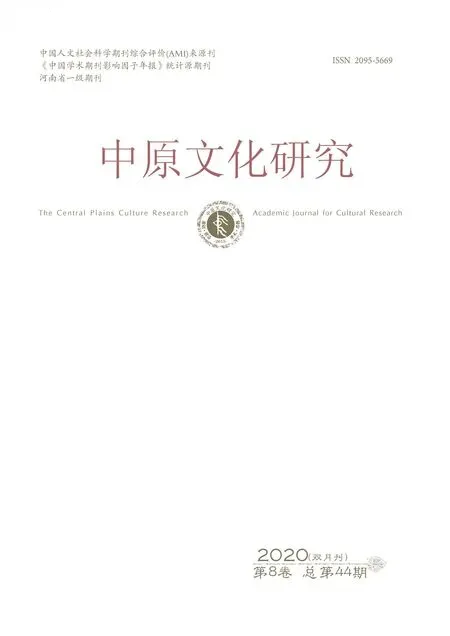试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和同思想
程有为
中国古代,“和”与“同”出现较早。在甲骨文中,即有“龢”字。《说文》曰:“龢,调也。从龠,禾声。读与和同。”卜辞中用作祭名。甲骨文中亦有“同”字,一是祭名,一是“会同”的意思。在《周易》《尚书》和《诗经》中,“和”“同”二字已较为常见。如《周易·乾卦·彖》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1]2《尚书·尧典》言:“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2]2《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云:“四方犹同,王后惟翰。”[3]188“和”的观念已经出现;“同”字多表述“共同”,也有“统一”“齐一”之意。“和”“同”作为两个对应的常用哲学术语,出现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代。和,谓可否相济,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同,谓单一不二,无所差异。这一时期出现了和、同之辨与和同思想。百家争鸣过程中,儒、道、墨诸家对和、同多有论述,形成和发展了玄同、太和、中和、和合、和同、大同等思想观念。墨家倡导“尚同”,儒家则主张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这些思想得到秦汉以降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4]64因此,研究和弘扬中国古代的和同思想,不仅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春秋时期的和同之辨与和同思想
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论述了和与同的区别,从总体上倡导和、同,并将它运用到社会生活,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和同思想。
(一)和、同之辨
含有哲学意义的“和、同”之辨,出现于西周、春秋之际。西周末幽王在位时,朝政日非,诸侯叛贰。在周王室担任司徒的郑桓公姬友心不自安,遂咨询于史伯(周太史):“周其弊乎?”史伯作了肯定回答:
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匿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5]515-516
这段话中将五行作为人类创制物品的五种材料,认为事物存在两个对立面,最早将“和”与“同”联系起来。史伯以味道和乐律为例,解释这两个概念,明确指出两者的区别,继而提出较为完整的和同思想。史伯在这段话中指出,先王务“和同”,其具体做法首先是健康身心,即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其次是“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还要通过生聚教训,使百姓“和乐如一”。而周幽王却反其道而行之,“去和而取同”,遂断言西周王朝必将衰亡。史伯阐述何谓“和”,何谓“同”,两者的不同功能,以及“去和取同”的危害。首先解释什么是“和”,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就是以一种事物去平齐另一种事物。接着说“和”的功用,即“和实生物”,和“能丰长而物归之”;而“同”则是同一种事物的相叠加,只是数量的增长,不能相济,不能产生新事物,终究难以为继,而被抛弃。然后又举例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韦昭注:“和谓可否相济,同谓同欲。”“和”可以包含事物的多样性,所谓“和而不同”;同时“和”又蕴含着发展变化的内在可能与因素,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的事物互相结合才能产生万物,如果事物之上加上相同的事物,不仅不能产生新的事物,而且一切就会变得平淡无奇,没有生机。史伯结合阴阳原理,直接从“天道”角度论证了“生”由“和”成的道理。后人称之为“和生说”。既然和能生物,同无所成,作为统治者就不能“去和而取同”,而应该“务和同”。
春秋末期齐景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22年)十二月,齐景公要到沛地打猎,以弓为信物招虞人(掌山泽之官)陪同,虞人以为不符合制度规定而拒绝前往。及齐景公打猎返回遄台,臣属梁丘据(子猶)未被召见,却骑马疾驰来到行在。此事引发齐相晏婴与齐景公的一段谈话,再次论及“和”与“同”的区别:
公曰:“唯(梁丘)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6]1463-1464
晏婴这段话又明确指出“和”与“同”的区别,他以五味、五声为例说明什么是“和”。总之,“和”根本在于使两种对立面相济,“同”则是单一的东西相叠加。“和”有益于人的身心,“同”则不可。因此,“同”不可取。晏婴又将和、同推广到君臣关系方面,认为君主的意见当肯定的肯定,当否定的否定,如果不辨是非,随声附和,盲目追随,便是“同”。君上必须心平德和,具有包容万有、博采众长的胸怀,臣属应具有君子人格与足够的智慧,能审时度势,提出不同意见,供君主参考、采纳,这才是真正的“和”;反之,君主说可,大臣也说可;君主说不可,大臣也说不可,朝堂实际上成为一言堂,君主决策的错误得不到纠正,这种“同”是要不得的。将不同意见合在一起,得到一个新的统一,这就是和。君臣之间应该和而不是同。但是他也主张“上下同”。晏婴又提倡和平。他说:“寒温节,节则刑政平。平则上下和,和则年谷熟。年充众和而伐之,臣恐罢民弊兵,不成君之意。”[7]内篇杂上,第五他认为阴阳二气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则百姓和乐,国家不可战胜。所谓平就是无过无不及,和就是折中调和。
(二)和同思想
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不仅理清了和、同的区别和各自的功能,而且将和、同思想用于社会政治、军事、民族关系、上下关系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些新观念。
一是兼听谋众,宽猛相济。子产曾担任郑国执政,他发扬民主,将“国小而逼,族大宠多”的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郑国人有游乡校以论执政的习惯,然明对子产说:“毁乡校,如何?”子产说:“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6]1164子产认为,国人发表不同意见是对政事的针砭,对统治者而言是治病的良药。统治者只能忠善以损怨,而不能作威以防怨,对不同的政治见解应予以宣导,社会才会和谐安定。孔子对子产此举予以充分肯定,称子产为“仁”人,又说:“天下有道,则庶人议。”[8]250
子产为政谋划于众,择能而使,在统治集团内部发扬民主,使内部关系和谐协调,形成合力,堪称“和”的典范。子产在弥留之际对子大叔说:“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6]1467子产认为:为政有宽、猛之分,行猛政易,行宽政难。有德者方能以宽服民,其次是猛。这一“宽猛相济”的政治观念既是礼制传统的最高理想,也是从历史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普遍规律。在政治实践中如何处理德与刑、宽与猛的关系,子产在理论上强调以自然为法,在实践上主张以民为本。孔子对子产予以高度评价,指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政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只有宽、猛相济,以求中允,政治才能平和。这就是“中和”之道,即中正平和之道。“中和”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早在周定王八年(公元前599年),刘康公曾对周王说:“宽所以保本也,肃所以济时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5]76主张统治者宽肃宣惠。
二是上下和同,战则能胜。春秋时人认为,在军事上也需要和同,而内部和同是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楚共王十六年(公元前575年),晋国出兵伐郑,楚共王亲自率军救郑。楚军经过申地,司马子反向年老致仕的申叔时咨询此战的前景:
曰:“师其何如?”对曰:“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故诗曰:‘立我烝民,莫非尔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庞,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6]747-748
申叔时以为,战争的胜利依靠的是德、刑、详、义、礼、信。除天时、地利外,更需要“人和”,即“上下和睦”。具体而言,就是“民生敦庞,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国家内部上下和同,民众愿意尽力效死,才能战无不克。而楚国当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必败。后来的战事发展证实了申叔时的预言。
三是和睦邦国,以至戎狄。东周王室重视亲和邦国,朝廷“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9]259。诸国在处理与异族政权之间的关系时,也主张和戎狄,以求互利。春秋时期,立国河东(今山西南部)的晋国处于戎狄的包围之中,如何处理民族关系,成为晋国的一个重要课题。晋悼公四年(公元前569年),山戎无终的君主嘉父派使臣孟乐前往晋国,通过其大夫魏绛向悼公献虎豹之皮,请求晋国与诸戎和好。晋悼公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总结历史经验,言不可再启战端:
(悼)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魏绛)对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君其图之!”公悦,使魏绛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6]818
晋悼公采纳魏绛的建议,外和戎狄,内修民事,终使晋国复霸诸侯。
四是人际关系,和睦同心。周代官制规定:“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协理阴阳。”“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2]199,120朝廷立三公,其职责是治理国政,使自然环境协和。宗伯之职,就是要上下和同。统治者也要和国民。《尚书》中说:“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2]157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8]248行为的和同就是彼此和谐,相互协和。总之,只要上下和同,做到“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5]232,就不患国小民少。
五是礼以和贵,以礼节和。和同也用于礼仪。周定王召士季,曰:“服物昭庸,彩饰显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顺,容貌有崇,威仪有则,五味实气,五色精心,五声昭德,五义纪宜,饮食可飨,和同可观,财用可嘉,则顺而德建。”以和同为处理各种关系的准则。韦昭注“和同”曰:“以可去否曰和,一心不二曰同。和同之道行,而德义可观也。”[5]65,66孔子弟子有若曾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行也。”[8]12礼的作用应该在矛盾调和中表现出来。光是调和不行,还要用礼对于调和加以节制。
六是和为美德,和而不同。春秋时人认为,君子应该具备知、仁、圣、义、忠、和“六德”。《周礼》曰:“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9]156将“和”“睦”作为不可或缺的美德善行。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恭,供养三德为善。”[6]1352“和”作为一种美德与“忠”密切相关,对内对外都要“和”。至春秋末期,孔子又在君子与小人的德行差异方面谈及和与同,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主张“和而不同”,既“群而不党”,又要“和而不流”。揭示出“和”的本质在于统一和协调体内多种因素的差异,而“同”则意味着事物的简单重复相加,或者无原则的复合与统一,缺乏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感共识。孔子“和”的观念意味着主体在面对差异与冲突时的一种理性而自觉的选择,“和”是在主体理性抉择的前提下达致的一种符合目的的理想状态。
二、战国时期的和同思想
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由于各家依据的学术元典都是《周易》《尚书》《诗经》以及《左传》《仪礼》等书,其思想是对春秋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学术的延续与发展,因而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战国时期儒家、道家、墨家以及杂家对和、同思想多有阐述,唯有法家罕有论及,各家的论述多带有自己学派的特点。
一是道家的“和光同尘”。老子对和、同的论述,涉及自然、家族伦理、处世态度等方面。《老子》论述万物生成时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0]175认为事物存在着其对立面,如:“音声相和,前后相随。”[10]10以“和”为发于自然与自然之声的表征。论及家庭伦理关系,说:“六亲不和,有孝慈。”[10]72言婴儿“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10]222,224。老子既强调“知和曰常”,又强调“以中为常”。《老子》第五十六章言:“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10]228“和”即“平”,有掩抑之意;“同”谓齐等而与之不异。“和光同尘”是说镜受尘者不光,凡光者终必暗,故先自掩其光以同乎彼之尘。不欲其光,则也终无暗之时。将“和”与“同”联系起来,并使用了“玄同”这一概念。所谓玄同,就是混同为一。《老子》第二十三章言:“故从事而道者,道德之;同于德者,德德之;同于失者,道失之。”[10]95意思是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从事于德者同于德,从事于失者同于失。
而《庄子》中使用了“太和”“天和”“和理”与“大同”“玄同”等概念。《齐物论》中有:“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11]46庄子又论及是非问题,说:“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谓之两行。”[11]70圣人虽然也跟外界事物相接触,但是其内心总是平静的,这就是“两行”。《德充符》言:“未尝有闻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鲁哀公问孔子哀它何人,孔子以“才全而德不形”回答。鲁哀公又问什么是“才全”,孔子说:“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德者,成和之修也。”[11]206,212,214庄子假孔子之口,以为人苟知性命之固当,则虽生死穷达,千变万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成于庶事和于万物者,非盛德之人不能做到。因而士人须先修身立行,然后方能成事和物。在《人间世》篇,庄子借蘧伯玉之口言:“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11]165士人身形从就,不乖君臣之礼,心智和顺,迹混而事济之。但这样做仍存在患累。因就者形顺,入者遂与同。心智和顺,方便接引,推功储君,不显己能,斯不出也。若遂与同,则是颠危而不扶持,与彼俱亡矣。就是说,士人入仕成为臣属,则会失去自我,还是以出世、遁隐山林为好。庄子亦论及同、玄同、大同。《齐物论》言:“啮缺问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11]91《祛箧》亦言:“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11]353玄同即混同为一。《在宥》言:“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11]390庄子主张绝圣去智,齐是非,反映他在认识上的相对主义与不可知论。晚出的《列子》一书也说:“和者大同于物,物无得伤隔阂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12]57道家所谓大同,指人与物浑然一体。
二是墨家的“尚同”主张。墨子在主张“尚贤”的同时,也主张“尚同”。《墨子》中有《尚同》三篇,对“尚同”思想有较充分的论述。他说:“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垂名于后世者,无他故异物焉,曰: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古者国君诸侯之闻见善与不善也,皆驰驱以告天子,是以赏当贤,罚当暴,不杀不辜,不失有罪,则此尚同之功也。”[13]88,89墨子倡导尚同的社会背景,是人们皆自以为是而“交相非”,不能和合,而导致天下大乱。墨子也主张人际关系的和合。所谓“和合”,就是和睦同心。
社会上成千上万的人“皆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是以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13]91。墨子又讲述义不同的危害是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且上下相贼。“故计上之赏誉,不足于劝善,计其毁罚,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则义不同也。”[13]92如果乡长能壹同乡之义,则乡治;国君能壹同国之义,则国治;天子能壹同天下之义,则天下治。如果“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天子“不上同于天”,天就要降下“飘风苦雨”作为惩罚。因此要想除去灾害,必须“上同于天”。各级正长建立之后,人民必须以正长的是非为是非,“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13]75。即统一是非标准,使大家都能“尚同其上”,上必须明于赏罚,做到赏善罚暴。这样,国家才能治理好。总之,墨子认为家、国、天下之所以治理,其原因都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然而使天下之为寇乱盗贼者,周流天下无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为政善也。”[13]97因此,墨子认为:“尚同为政之本,而治之要也。”“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为仁义,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尚同之说而不可不察。”[13]98
三是儒家论“和”。战国儒家论和同,以《荀子》为多,《礼记》的记载也很丰富,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关于和、同的论述主要是政治方面。当齐王向他谈自己喜欢音乐时,他说爱好音乐是好事,但是要“与民同乐”。“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14]27他又论及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14]86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之间,强调人和的重要性。孟子在国家政治上也主张统一。他回答梁惠王“天下恶乎定?”的问题,说“定于一”,即主张天下归于一统[14]12。
战国末期荀子对诸子百家思想作了总结。在自然观方面,荀子持“天生人成”说,《礼论》篇言:“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15]267重申“和实生物”之说,认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在社会政治方面,荀子更多地谈到“和”:第一,从发展经济角度,谈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关系,说:“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素,啜菽饮水,恶能足之乎!”反之,“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15]127“百姓时和,事业得序者,货之源也。”“时和”,得天之和气,则岁丰。事业得序,即耕稼得其次序,君上不夺农时。“明主必谨养其和”[15]133。第二,从政治角度,谈分、义与和的关系:“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15]109就是说,人在自然界,就体力而言,不能和猛兽竞争,必须组织起来,才能在生存竞争中获得胜利,因而社会应当和谐统一。第三,从战争角度,谈百姓和是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刑政平,百姓和,国俗节,则兵劲城固,敌国案自诎矣。”[15]115第四,从音乐角度谈和:“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15]278,279,281乐与礼的功能不同,乐可合同,礼则别异,两者关乎人心教化。第五,从品性修养角度谈和顺与调和:“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15]16。
《礼记》对战国时期和同思想多有述及,第一,关于乐、礼之和。《乐记》篇说:“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16]658-659“子夏对曰……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16]660“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16]672-673指出音乐在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中有重要作用,通过音乐教育可以实现君臣和敬、父子和亲、万民亲附的社会目标。《乐记》又将乐与礼放在一起,谈乐之和、礼之节与次序功能。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其性),节故祭天祀地。”[16]637,636“礼,交动乎上;乐,交应乎下:和之至也。”[16]408乐与礼交相呼应,就是最大的“和”。第二,家族伦理的和,也称内和。“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仪立。”[16]1047“妇顺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是故妇顺备,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故圣王重之。”强调父子、长幼的亲和与妇顺是家族兴盛的基本条件,也就是“家和万事兴”。“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16]1057,1059从家庭内和扩展到社会国家的和谐。“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地,中取则于人,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尽矣。”[16]1006第三,君臣上下关系的和,也称外和。“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后取其十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匮也,是以上下和亲而不相怨也。和宁,礼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义也。”[16]1088“发号出令而民悦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谓之义。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16]851-852和与仁、义、信都是治国的法宝。第四,人的性情的“中和”。《中庸》篇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6]899喜怒哀乐皆为人的情感活动,其未发是心体流行寂然不动之处,即天命之性的本然状态,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已发动的喜怒哀乐,则体现为人的感性活动,它是心体的流行发用,感性的喜怒哀乐发而合乎中,便谓之和。合于中不仅指符合内在的天理良心,还须符合外在的礼节规范。儒家思想的“中”与“和”相联,“中和”成为一种重要的处事原则。
四是儒家的“大同”理想。《礼记·礼运》篇可能作于阴阳五行思想盛行的战国晚期,重点谈礼的发展演变和运用。全篇假托孔子之口,提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有关“大同”社会的理想,进而说明礼制是“大道既隐”之后的“小康”社会的产物: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16]362-363
与五帝时代的大同社会相对应,夏商周时代则是“小康社会”: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16]364
小康社会是一个现实的阶级社会,要靠政权来维护,靠礼义维持其和谐。此篇所谓的“大道”,据郑玄注是指五帝时期治理天下之道,实际是儒家学者托为五帝时代而表达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就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这里记述孔子论礼、义、仁、顺、教育、音乐及其相互关系,并以达到大顺为治国行政的最高境界,礼对于治理人心和天下国家的重要性,先王如何通过修礼仪以达到天下大顺的局面。儒家仁学的理想就是“天下大同”。大同社会代表了中国古代理想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道家也描述了小国寡民、不乘舟舆、不陈甲兵的理想社会。人们知其文明,守其素朴,不仅是一种理想社会,也是一种精神境界。
五是杂家的和同观念。《吕氏春秋》中也论及和与同,《大乐》谈音乐的起源及其和适的特性,说:“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17]256,255《应同》篇言:“类固(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物之从同,不可为记。子不遮乎亲,臣不遮乎君。君同则来,异则去。故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故曰同气贤于同义,同义贤于同力,同力贤于同居,同居贤于同名。帝者同气,王者同义,霸者同力,勤者同居则薄矣,亡者同名则觕矣。”[17]678总而言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事物从同的例子不胜枚举,有同气、同义、同力、同居、同名诸层次,而以同气为高;帝、王、霸、劳动人民、流亡者诸等级,以帝王为尊,成为是非观念与等级观念的体现。
六是《管子》的和合思想。《管子》对和同也有所阐述,《立政》篇说:“见贤能让,则大臣和同。”“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18]62倡导统治集团内部要和睦同心。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该论著重申了前人的和合思想。两周之际史伯曾对郑桓公说:“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最早使用“和合”二字,五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种美德,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五项原则。此后,《墨子·尚同中》和《荀子·礼论》都用到“和合”。《管子·兵法》篇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18]323可见,崇尚“和合”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
三、后世对先秦和同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古代的和同思想,形成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又有所发展完善。先秦时期的“玄同”“太和”“中和”“和合”“大同”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宇宙观,也成为士人自身修养和处理各种关系的准则,成为一种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这些都为秦汉以降的儒家学派所传承和发展。贾谊所著《新书》中多处谈及和、同。其《道术》篇论及接物,说:“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莫弗亲也。”论及品善之体,说:“刚柔得道谓之和,反和为乖。”[19]302,304对什么是“和”作了新的阐释。《六术》篇谈声音之道,说:“六律和五声之调,以发阴阳、天地、人之清声,而内合六法之道。是故五声宫、商、角、徵、羽,唱和相应而调和,调和而成理谓之音。”[19]317阐述了和在音乐中的重要性。在已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汉代,贾谊将墨子的尚同思想发展到极致,倡导礼制纲常,强调绝对服从,在《五美》篇主张使“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19]67。
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中,继续阐释两周之际史伯“和实生物”的道理。其《循天之道》篇说:“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是故物生皆贵气而迎养之。”“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20]610进而强调中和的重要性:“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20]606将“和”视为最高的德性,它既可用于治国,又可用于养生。同时,董仲舒又发挥了墨子的尚同思想,而倡导大一统。他倡导“同一”“大一统”,就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即“天人感应”。“《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1]2523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核心思想是“大一统”,就是在政治上统一于皇帝,思想上统一于儒学。
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对和同思想多有论述。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以为“万物化生”是由于“二气交感”,这是对史伯“和实生物”的发挥。其《通书》对《中庸》“发而中节谓之和”予以阐释,以为人性有刚柔和善恶,要取其中。所谓中,就是和,就是中节。这是天下之达道,也是圣人之事。邵雍的《观物外篇》谈修养方法,说“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发而中节也”[22]152。就是说,不掺杂私心杂念,不掺杂个人利益的喜怒哀乐,就是中节。又说:“庄子《齐物》,未免乎较量,较量则争,争则不平,不平则不和。”[22]175人得中和之气,性情则不刚不柔。人在处事时则要“至公”。张载曾对先秦时期的“太和”“中和”思想予以解释,《正蒙》有《太和篇》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23]1张载认为,“太和”乃天地间阴阳中和好之气,宇宙演变的整个过程是阴阳矛盾的过程,这个总的过程称为太和。其《经学理窟》又说太和是“和之至”。他又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23]25这四句话反映了他的辩证法思想。
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对和多有论述。《伊川易传》对《周易·乾·彖辞》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又对“中和”作出解释:“中和,若只于人分上言之,则喜怒哀乐未发既发之谓也。若致中和,则是达天理,便见得天尊地卑、万物化育之道,只是致知也。”[24]160他们又言及同,说:“合而听之则圣,公则自同。若有私心便不同,同即是天心。”[24]145认为同是天心,也是“公”,主张“廓然而大公”。二程认为礼就是序,乐就是和,主张安礼而和乐。认为和是天道自然规律,也是道德修养,最终落脚于社会治理。南宋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将《论语》《孟子》和《大学》《中庸》提高到重要地位。《中庸》提出:“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朱熹曾作《中和旧说序》,将自己的认识归纳为“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从而为确定一种适当的修养方法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朱熹讲“理一分殊”,不仅具有形上学的意义,也同样应用于伦理学:“万物粲然,还同不同?曰:理只是这一个,道理则同,气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25]6
明末清初,王夫之的思想中充满了对自然、人类以及人类所构成的社会共同体的辩证而系统的理解。他强调阴阳的和合,《周易外传·大有篇》中说:“阴阳之理,建之者中,中故不竭;行之者和,和故不爽。不爽不竭,以灌输于有生。”[26]37《尚书引义》主张中和为体,礼乐为用。其《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从宇宙观方面论述和。对于张载所谓“太和所谓道”,王夫之注言:“太和,和之至也。道者,天地万物之通理,即所谓太极也。阴阳异撰,而其缊于太虚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浑沦无间,和之至矣。未有形气之先,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故曰太和。”[23]1王夫之又从气化与人之性情两方面,对张载“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作出解释,说:“以在人之性言之,已成形则与物为对,而利于物者损于己,利于己者损于物,必相反而仇;然终不能不取物以自益也,和而解矣。”[23]25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以求和谐(和合)为重要特点,成为其关于人类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具有“天下一体”的社会观念。他认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以“严以治吏”“宽以养民”取代孔子的“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使官吏受约束,人民安居乐业,天下太平无事。
中国近代更多的思想家、政治家论及和与同。康有为倡导变法,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有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小康”社会即升平世,大同社会即太平世。康有为《大同书》说:“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也。”从全世界视域论述太平盛世。孙中山先生倡导“天下为公”,号召开展国民革命,社会各界“同趋于一主义之下”,建立国民平等的“社会的国家”,使家给人足,无一不获其所。总之,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和同思想,经过汉宋诸代的发展,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和、和合、大同思想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弘扬这些思想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