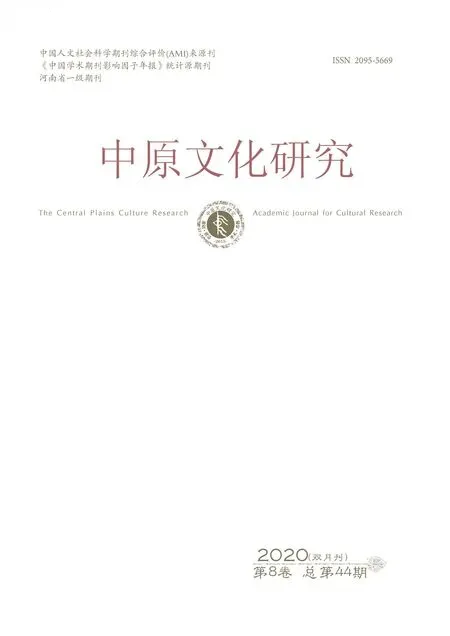图像学视角下妈祖像北传山东的在地化研究*
徐晓慧 张蓓蓓
近年来关于妈祖图像与塑像的研究已积累了不少成果①,除了从宗教学、历史学、人类学等角度对妈祖进行研究外,学者们逐渐开始从图像学的角度研究妈祖,整体呈现出从宏观到微观,由综合性向专门性、地域性的研究趋势。这些研究以不同时代的妈祖图像与塑像作为研究对象,从妈祖图像与塑像的历史学考察、解释、再现意义与象征意义等角度入手,分析不同时代妈祖图像与塑像对不同人群的象征意义。目前国内关于妈祖图像与塑像的研究已经进入了“图像志分析”阶段,但缺少对妈祖图像与塑像在地化发展的研究。本文以山东地区妈祖信俗的在地化现象研究为出发点,对比山东地区与妈祖文化发源地福建地区的妈祖图像与塑像的异同,从图像学研究的角度,为妈祖信俗研究提供更加明晰的显性的文化和信仰符号。
一、妈祖图像的标准化与在地化
(一)妈祖信仰——“神的标准化”
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 L.Wat-son)在20世纪80年代基于华南沿海妈祖信仰的研究,曾经提出“神的标准化”[1]的概念。沃森所言的“神的标准化”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由于国家力量的“鼓励”,导致许多地方神灵逐渐让位于国家所允准的神灵(如妈祖、关帝);二是在此历史过程中,在象征符号与仪式行为一致的表象下,不同的主体(国家、地方精英和普通民众)对该神灵信仰的不同理解和行为差异。无疑,妈祖信俗的广泛传播与国家力量的“鼓励”有直接关系,妈祖所到之处,许多地方神灵都逐渐让位于妈祖,但在山东地区,妈祖信俗并未取代地方神灵,而是与其他神灵共存,如山东当地的龙王信仰、碧霞元君信仰等。沃森所言的“神的标准化”,即看似一致的妈祖信俗的象征符号与仪式行为的表象之下,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陆由于对妈祖信俗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故体现出对于妈祖信俗的不同行为,如口头叙事、称谓、供奉格局、妈祖图像与塑像的制作等都有明显的不同。
作为一种偶像②崇拜,妈祖信俗所涵盖的神格、功能、圣境、仪式、称谓、口述故事等内容无一不体现在对偶像的塑造上。妈祖信俗的“标准化”依赖的是政府的标准化运作,然而其真正深入人心却是依赖信众的口口相传,因此,在传播的过程中,常常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民风民俗、信仰体系等相互融合,呈现出信仰的“在地化”现象。“神的标准化”是詹姆斯·沃森在研究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天后崇拜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很多学者将其作为一个成熟的解释工具用来研究妈祖信俗。然而,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在对妈祖信仰方式的标准化与在地化研究上,包括詹姆斯·沃森本人也是,缺少视觉化角度的标准化与在地化研究。笔者通过研究山东地区的妈祖图像和塑像发现,妈祖信仰方式的标准化与在地化在妈祖图像和塑像的制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和清晰。这是因为,妈祖图像和塑像是替代了妈祖神的“偶像”,是妈祖信仰观念的视觉化呈现,妈祖信俗的在地化现象首先体现在视觉领域,即对妈祖图像与塑像的塑造上。
沃森在证明一个重要观点“像其他中国神灵一样,天后对不同的人代表了不同的内涵”时,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台湾城市官方庙宇和非官方庙宇的双重庙宇模式,一个例子是台湾多用俗名妈祖而广东则多用皇帝封号天后、天妃等[1]。这实际体现了妈祖信俗“非标准化”的两个方面,即官方与民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对“神的标准化”的博弈。这也为本文论点的提出提供了逻辑的可能,即山东地区妈祖信俗作为妈祖信俗之“流”应该存在不同于作为妈祖信俗之“源”的福建地区的妈祖信俗,即使包括山东地区在内的其他北方地区的妈祖信俗,也由于官方的鼓励而存在“标准化”的现象。
沃森还指出:“中国政府对文化整合做法的聪明之处在于:国家强加的是一个结构而不是内容。庙里崇拜活动的实际组织工作交给了地方精英人物,他们有既得利益要与国家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一体系很灵活足以让在社会等级各层次的人都可以建构他们自己对国家允准神灵的看法。换一种说法,国家鼓励的是象征而不是信仰。”[1]以当代再标准化的妈祖信仰为例,20世纪80年代至今,妈祖信仰再度复兴,国家通过非遗认证等形式极力推广妈祖信仰的标准化,其象征符号也由古代封建社会的“加强封建统治”“稳定民心”等转变为“两岸交流”“增强中国民族凝聚力”“弘扬传统文化”。沃森的言外之意是,政府所标准化的是妈祖信仰的结构——象征,而不是妈祖信仰的内容本身,这样各地区各阶层的人就可以建构自己对于妈祖的看法和认知,这些看法和认知是以作为妈祖“神性的隐喻”的信仰内容本身为基础的。
(二)妈祖图像——“神性的隐喻”
上文提到妈祖图像和塑像是“替代”了妈祖神的“偶像”,妈祖“神性的隐喻”就是在这持续的替代过程中实现的,其根本原因是人类感情的“情移”,即从“期望的对象”妈祖神向“合适的替代物”妈祖像的情移[2]15-19。因此,图像志研究阶段的妈祖图像研究只需要对妈祖图像与塑像进行解释,分析其形式和风格,结合地理位置和时代背景,分析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原因。而真正深入的妈祖图像学研究则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妈祖图像与塑像中的某种或某些视觉特质是怎样被经验为妈祖神性的对等物的?即妈祖的“神性的隐喻”,妈祖图像与塑像的象征意义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的问题。换句话说,不仅要回答妈祖形象“是什么”的问题,还要回答“为什么”。
肖海明提出:“清代以来随着妈祖标准化的逐步加强,妈祖图像也逐步走向了标准化,但在‘一统’的表象之下,民间的妈祖图像还是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景象。”[3]但是,妈祖图像标准化的表现要比妈祖信仰标准化的表现复杂很多,如果用视觉艺术“母题”③的概念来解释,妈祖图像的标准化过程即是妈祖图像中独特的支配性的成分逐渐形成的过程。通过对历代妈祖图像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与妈祖有关的文献原典,可以得出妈祖图像母题有“枯槎”“旋舞”“朱衣”“青圭蔽朱旒”几种。
“枯槎”阶段虽尚未出现妈祖人型图像,却是妈祖神性物化的最初“意象”。“槎”作为异象最早出现在东晋王嘉《拾遗记》中:“尧登位三十年,有巨查(即槎)浮于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昼灭。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复始,名曰贯月查,亦谓挂星查,羽人栖息其上。群仙含露以漱,日月之光则如暝矣。虞、夏之季,不复记其出没。游海之人,犹传其神伟也。”[4]23西晋张华编撰《博物志》“八月槎”条记载,旧说“天河与海通”,每年八月有浮槎出现在海边,有“奇志”之人乘浮槎自海赴天河得见牛郎织女。后世又有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张骞“乘槎”溯河之传说,唐宋及以后诗文中也经常出现“浮槎”“乘槎”“星槎”“仙槎”等词,可见“枯槎”因为这些浪漫主义色彩的神话传说而逐渐具有了特殊的神异功能,成为一种成仙意象。由此,“枯槎”成为了妈祖传说中由文本演变为图像的最早的物象符号,是妈祖神性最早的符号隐喻。妈祖“枯槎显圣”的文献记载④乃时人借具有神异功能的“枯槎”物象作为妈祖神性的“意象”载体,目的是彰显妈祖信仰的正统性和可信性,人型妈祖神像出现以后最初多采用木质雕刻便是对妈祖原典所记“枯槎显圣”的呼应。“旋舞”“朱衣”和“青圭蔽朱旒”则是通过服饰、属像⑤、姿势等来表现想要再现的妈祖神的观念和神性。
妈祖“旋舞”之形像出现在文献记载中的时间要早于“朱衣”,应是呼应妈祖最初“里中巫”之身份。“朱衣”最早出现在南宋人楼钥《攻愧集》卷三十四《兴化军莆田县顺济庙灵惠昭应崇福善利夫人封灵惠妃》制诰文:“明神之祠,率以加爵……居白湖而镇鲸海之滨,服朱衣而护鸡林之使。”“朱衣”符号出现之后,“旋舞”之说便不再出现,应是妈祖在封妃荣誉之下完全摆脱了其原本的“里中巫”身份之故。如清代僧照乘等编修《天后显圣录》所言:“急祝天威庇护,见一神女现桅杆,朱衣端坐。”[5]390妈祖封灵惠妃着朱衣与正史记载相符,如《宋史·舆服志三》“后妃之服”条:“后妃之服。一曰袆衣,二曰朱衣,三曰礼衣,四曰鞠衣。”虽与正史部分记载相符,但观历代妈祖造像所见服饰形制与宋至清代《舆服志》中后妃的服制有较大的差异,因此“朱衣”可能有两种意指:一是意指现实中的后妃朱衣,以匹配妈祖封号;二是意指官服或朝服,封号为虚官职为实,目的是为了赋予妈祖更高的神格,此意指的可能性更大,即朱衣仅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而不是现实中后妃服饰的再现。
学界一般认为自妈祖封妃以后,“青圭蔽朱旒”是妈祖图像及塑像走向标准化的代表性形像,然而其形像来源尚不明确。“青圭蔽朱旒”来自刘克庄于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年)拜谒白湖妈祖顺济庙时所作五言诗《白湖庙二十韵》,距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妈祖被封灵惠妃已50余年。这段时间是妈祖塑像母题原型形成的重要阶段,那么妈祖封妃是否是“青圭蔽朱旒”妈祖形像形成的主要原因呢?历代《舆服志》中并没有后妃头戴冕冠的记述,直到明代凤冠类妈祖形像出现,才真正在冠式上与妈祖的封号匹配。肖海明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清代大量出现的凤冠冕板式妈祖图像是“后”与“帝”的完美结合,目的是为了既保留妈祖女性最高神的特性,又具有帝王的身份[3]。与其说是“帝”的隐喻,毋宁说是“双性同体”的隐喻。南宋时期流传至今的神祇造像极少,观之与其同时代的永乐宫三清殿集中唐宋道教绘画精华的壁画《朝元图》,此图虽成于元代,但据耿纪朋考证,此图的绘制是参照了较早的粉本。《朝元图》中玉皇大帝、五岳大帝等地位较高的男性神祇戴旒冕,仅旒数有所区别,地位较高的女性神祇戴凤冠或花冠,并没有戴旒冕的女性神祇的形像出现。
南宋时期妈祖神职进一步扩展,由拯救渔民到护佑苍生,开始具有男性神祇的一些神职功能和外在表现,如刘克庄诗云:“驾风樯浪舶,翻筋斗千秋。既而大神通,血食羊万头。”戴旒冕妈祖形像的出现是妈祖神职扩展和性别模糊的表现,信众为了赋予妈祖更多超越性别的能力,从而更加灵验以实现信众对妈祖的更多期待和诉求。当然,之后随着妈祖的北传,妈祖生育神职凸显,这种“双性同体”的隐喻又发生了以女性特征为主的单体神的复归。因此,“青圭蔽朱旒”是妈祖“双性同体”身份的隐喻,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人类渴望通过两性互补赋予神祇更大能力的内心愿景。
汉学家韩森在研究南宋汉人民间宗教信仰变迁时认为其发展有三个阶段:唯灵是信、金身庙宇和官位封号。妈祖塑像与图像作为妈祖信仰的物化形式,其标准化的过程与韩森认为的三个阶段不谋而合。从最开始将“枯槎”作为妈祖形像的再现,进而金身庙宇、“塑像崇祀”,最后还需要官位封号以体现其身份地位,从而将妈祖的外在形像塑造成古代官员甚至“后”“帝”的形像,这是妈祖图像与塑像逐渐标准化的过程。然而,妈祖形像要成为一种具有持续生命力的信仰符号,又必须满足不同时期政权统治的需要、顺应不同地区民众的信仰需要,从而呈现出多样化、在地化的图像特征。
二、以闽为源、以铜易木:古代妈祖图像的在地化
贡布里希认为:“制像的过程是,先制作后匹配,先创造后指称。”作为一种再现性艺术,妈祖图像和塑像最初的创造过程应该也是如此,工匠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觉制作图像,然后再将其与大家心目中的妈祖女神形像进行匹配,通过不断地“试错”,始终为了创作出最符合妈祖女神形像的图像和塑像而努力。于是,既吸取了基于已有经验的妈祖形像母题,也形成了基于不同知觉的千变万化的妈祖图像和塑像。妈祖信仰中神性的隐喻也就寓于这些千变万化的妈祖图像和塑像中,不同地区地理及文化的差异是这些变化产生的主要原因。
妈祖信俗自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八月妈祖首封之后⑥传入山东以来,在山东沿海及内陆的运河沿岸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据不完全统计,至明清时期山东区域先后出现了52 座妈祖庙,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及运河流域。正如李献璋《妈祖信仰研究》所言:“在明代的内地,妈祖的形象是十分变样的。”这里的变样是指妈祖信仰的象征体系与地方文化和民间信仰融合,发生了在地化现象,这是妈祖信仰得以广泛传播的必要条件。
威海庙岛显应宫和蓬莱天后宫是山东地区历史最悠久的两座妈祖庙。这两座妈祖庙还保存有与妈祖信仰有关的碑刻、铜镜、铜钵、匾额、塑像等文物。尤其是庙岛显应宫保存至今的一尊金身妈祖铜像是研究山东地区古代妈祖像最重要的文物资料。这是一尊妈祖夫人像,与妈祖宋时封号顺济夫人、灵惠夫人等一致,但其手持圭的形象与同时期福建地区的妈祖像有很大的出入。因此,笔者对庙岛显应宫所存金身妈祖铜像的年代定为北宋存疑。对比福建莆田所存鉴定为南宋的两尊妈祖木雕夫人像,虽发髻服饰类似,但这两尊夫人像皆未手持圭。一般认为,手持青圭、蔽膝、朱旒的妈祖形象出现在南宋绍熙初年⑦妈祖封妃以后。莆田市博物馆所藏妈祖木雕神妃像为目前所知最早体现妈祖“青圭蔽朱旒”形像的实物。因此,庙岛所存妈祖夫人铜像的年代最早为南宋及以后是较符合史实的。
福建地区的妈祖造像以木质、石质居多,明清始有瓷质,鲜见妈祖铜质像,尤其明代以前的妈祖像多为木雕。因此,学界普遍认为的庙岛所存妈祖铜像乃闽籍南日岛船民从福建移入庙内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时据刘杰考证,自东汉以来山东地区考古发现的佛教铜造像多达150多尊[6],可见,山东地区自古就有制作铜质宗教神像的技艺传统。考古资料显示,魏晋隋唐时期是佛教铜造像的辉煌时期,宋代以后铜制佛教造像数量极少,元代开始复兴,但大型铜造像以及大规模铜造像的再度出现则是明代[6]。庙岛显应宫妈祖坐像两侧有楹联一副:“救父海中,浑身是铜墙铁壁;警心梦里,夙世有慧业灵根。”这里关于妈祖“浑身是铜墙铁壁”的说法虽是夸张修辞,但与此妈祖像的铜质特点也有呼应。
因此,结合庙岛所存古代妈祖像的服饰特点、材质、楹联等内容,对比作为妈祖信仰与塑像之源的福建地区的妈祖塑像,可以推断庙岛所存妈祖铜质像为明代由山东本地工匠结合妈祖造像传统制作而成。其原因还在于,除立体塑像繁荣发展以外,明代也是平面化妈祖图像发展的高峰期,有版画、水陆画、壁画等⑧,相对于立体塑像,平面化的图像更加有利于妈祖图像的传播,也更有可能成为北方妈祖像的摹本。如《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中的天妃像即与庙岛存妈祖铜像类似的高髻非冕冠形式的特点一致。无独有偶,泰山碧霞祠也供奉有确切纪年为明代的碧霞元君鎏金铜像一座,以及壶天阁北元君殿碧霞元君铜坐像等,可供辅证。目前庙岛显应宫内供奉妈祖像的凤冠和披风都是后来增补的。
除庙岛显应宫外,蓬莱阁天后宫也是山东地区较早建成的大型妈祖庙,天后宫供奉的妈祖像虽为重塑,却是在早期供奉的妈祖塑像基础上的重塑,因此,其形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山东古代妈祖塑像的一些特点。蓬莱阁妈祖像也是铜制,妈祖手持之圭正面刻有北斗七星图案。北斗信仰始于殷商,后为道教吸收,北斗图案成为最明显的道教标识。因此,蓬莱阁妈祖像应是受道教影响较多,据其服饰图案判断其原塑明显晚于显应宫妈祖像,推断为清代完成的妈祖像,其北斗图案所体现的道教色彩则开山东地区近现代妈祖图像与塑像“释道融合、以道为主”之先。
三、释道融合、以道为主:近现代妈祖图像的在地化
除庙岛和登州两座妈祖庙是早在宋元时期建立之外,山东其他的古代妈祖庙大多数建于明清时期,规模大一点的也供奉有妈祖像,但大多已不存,目前山东地区的妈祖庙所供奉的妈祖像和作为公共艺术的妈祖像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新制的。其制作途径一般有四种:一是由本地工匠设计制作,一些小型妈祖庙的妈祖像大多由本地工匠制作;二是由福建地区工匠制作,如台儿庄天后宫用整块香樟木雕刻而成的妈祖像就是福建泉州的工匠制作的;三是从妈祖祖籍福建莆田按祖制开光分灵安座而成,如青岛天后宫妈祖像,庙岛显应宫的“三身”妈祖像;四是由其他地方的工匠制作完成的,如潍坊羊口天妃宫妈祖像就是由是河北石家庄工匠所塑。妈祖像无论是通过哪种途径制作,作为民间信仰的神像制作一定有图可依、有典可循。
妈祖信俗的象征体系是指在妈祖信俗及其包括信俗内容与仪式活动的实践过程中,由经验性象征符号所表达的与妈祖信俗相关的另一类事物的关联意义。妈祖信俗的象征体系首先包括妈祖本身及其在空间构造中被符号化的意义;其次则是以仪式活动为代表的信仰实践中各种经验性象征符号的意义及其整体的象征性。具体包括妈祖塑像与图像的象征性、妈祖庙宇空间的象征性、妈祖信仰仪式的象征性。作为妈祖信仰的物化形式,山东地区妈祖塑像与图像除体现妈祖神像塑造的标准化母题之外,也体现了诸多在地化特征,主要体现在妈祖形像的以下几个方面:
(一)道教色彩
道教对妈祖信仰的渗透在宋代就已经开始了,元代亦有妈祖乃“姑射神人之处子”等记载,明代记述妈祖事迹的典籍《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更是被收入道藏。虽然佛教也一直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对妈祖信仰进行渗透,但山东地区现当代的妈祖信仰还是呈现出更多的道教色彩。山东地区的妈祖庙大多由道教人士参与营造和主持管理,自清代以来山东所见妈祖庙营建碑记中也多次记载妈祖的供奉格局为“左关帝,右龙王,中则天后居焉”。学界一致认为,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妈祖信仰具有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特点,但是据笔者观察,山东地区的妈祖信仰自明代开始直至现代,道教色彩所占比例最大。
明永乐年间的《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对妈祖形像有详细的记述:“(老君)赐珠冠云履,玉佩宝圭,绯衣青绶,龙车凤辇,佩剑持印。”山东潍坊林海宁国寺所供妈祖像与其他妈祖像有明显的不同,该像服饰明显为戎服,头戴饰有花纹带护耳的武胄,上有垂旒冠缨,身着袍服,肩有披膊,如意压领,腰间有带,左手持印,右手持剑。此形像与明永乐年间的《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所记“(老君)赐珠冠云履,玉佩宝圭,绯衣青绶,龙车凤辇,佩剑持印”之“佩剑持印”的记载一致,应是工匠根据此记述塑造而成。除宁国寺妈祖像,潍坊羊口天妃宫妈祖像所戴之冠虽有垂旒,细观之,垂旒所附之冠亦是戎服之武胄,手未持圭,云肩锦衣。
(二)碧霞元君
妈祖信仰传入山东以后的“在地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与本地原有的神祇相互影响和融合,如龙王、关帝、碧霞元君等,由于政府“标准化”的运作以及妈祖封号级别等原因,供奉格局方面,在山东沿海及运河沿岸的海神信仰场所,龙王、关帝等成为妈祖的陪祀。但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女神的碧霞元君信仰却始终没有被妈祖信仰完全取代,甚至有山东地区的妈祖信仰很大一部分就靠附会碧霞元君信仰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民间也有“本元君,南妈祖”的说法。碧霞元君全称为“东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又称“泰山娘娘”“泰山老母”“泰山玉女”,是起源于山东并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山神信仰,其主要神职功能是“生育”。妈祖信仰北传以后其神职功能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在天津、北京、河北等地,其作为生育女神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其原本作为海神的地位,尤其是在女性信众的心中。明代文献曾记载碧霞元君塑像形貌为“塑像如妇人育婴状,备极诸态”,对比山东地区与福建地区的妈祖塑像,山东地区妈祖塑像的母性特征更加明显,更具有亲和力,这是由于妈祖以生育为主导的神职变化对造像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明代庠生王权撰写的《修天妃庙记》记载:“德州旧无天妃庙,庙初立,无文字纪岁月。天顺庚辰、成化辛丑两新之。吾境内,多泰山元君祠,谒天妃庙者,恒以元君视之。”[7]由碑文可知,运河流域的德州明代始建天妃庙,拜谒天妃庙的当地群众将天妃视为泰山碧霞元君。而长山县令叶观海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撰写的《天后阁记》有云:“幸碧霞元君宫前,旧有南厅基址,众商公议,建立高阁五楹,群楼数间,彩楼对列,长廊环卫,刹门僧舍,罔不毕具,为周村辟一名胜。”[7]是说在原碧霞元君宫庙之前建立天后阁。可见,山东地区的妈祖信仰与碧霞元君信仰渊源已久,而且最迟自明代开始山东民众就对两种信仰多有附会[8]。妈祖北传以后,除神职功能、宗教色彩、文学形象的接近以外,妈祖与碧霞元君的视觉形像也比较相近,如:南京高淳地区发现道教神像画中就同时绘有天妃妈祖和碧霞元君像;再如首都博物馆所藏明代绢本《天妃圣母碧霞元君像》,也是将天妃妈祖和碧霞元君并列绘制,形像衣饰也十分接近。
山东地区近现代的妈祖与碧霞元君造像互相影响,似有趋同,但仍然承袭了各自不同的图像母题。张蓓蓓在《妈祖形像考——兼论妈祖服饰及妈祖形像复原实践》一文中说:“如若妈祖形塑的原型是由名工巧匠们所构造的,他们利用手中的画笔或刻刀将信众敬奉的理想神灵形貌描绘于画纸之上或者塑造为一个三维形塑实体,那么工匠们在进行绘画或雕刻创作时必定受到时下久已盛行的宗教信仰、神话故事、文化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并结合当下人神体貌确定一个可参考的形塑模板或摹像。”[9]可见,山东地区的工匠在为妈祖制像时除首先会参考福建地区的妈祖图像与塑像形式外,也会参考山东地区业已存在的女性神像形式,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碧霞元君了。
妈祖宋时先封夫人再封妃,而元君自宋代开始是与夫人并用的称号,不分高低,由此可见,朝廷对妈祖的封号要高于碧霞元君。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作为妈祖图像主题之一的“青圭蔽朱旒”之“朱旒”从未出现在碧霞元君图像与塑像中。由于碧霞元君对妈祖造像的影响,山东地区的妈祖塑像尤其是近现代塑像有相当一部分并未承袭“青圭蔽朱旒”这一图像母题,这是山东地区妈祖塑像与福建地区不同的一个主要方面。
自明清开始山东地区碧霞元君信仰仪式中最重要的是敬献衣物,以红袍为主,这也是人格神信仰“由凡至圣、由圣至凡”的发展规律,认为神也有世俗之人的需求。世俗之衣总有因脏旧冷暖而换新的需要,因此给元君换装也逐渐成为信仰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碧霞元君信仰的献袍换装仪式也对妈祖信仰产生了直接影响,山东地区的妈祖塑像多有红色或金色外袍披风,并根据季节岁时变化举行换装仪式。
(三)持灯妈祖形像
与灯有关的妈祖形像的文献记载始见于元代,神灯、祥光本是妈祖出现时显圣异象和祥瑞异象,清代以前灯元素是作为描述妈祖圣迹的文字形体出现的。持灯妈祖形像最早出现在清人所作《天后显圣故事图轴》中,其中有两幅图刻画了妈祖身后侍女手提灯笼的图像。
北方持灯妈祖图像与塑像明显多于南方,据陈祖芬等统计共有9 处[10]。持灯妈祖塑像中,莆田湄洲岛2 处,天妃故里遗址公园1 处,莆田玉湖公园1 处,其他5 处都集中在北方地区:天津妈祖文化园1 处、辽宁营口西大庙1 处、山东长岛显应宫1 处、山东烟台天后宫1 处,山东荣成成山头风景区1 处。9 处是不完全统计,据笔者走访,山东潍坊羊口公园和荣成石岛天后宫也各有一座名为“海神赐灯”的妈祖持灯雕像。11 处持灯妈祖塑像有5 处集中在山东地区。由此可见,“灯”元素妈祖塑像在山东地区的出现频率和分布都要明显高于福建地区,这与山东地区传统灯俗文化有关。而且以传统元宵节为基础,山东沿海地区还衍生出了一个特有的妈祖节俗活动——渔灯节。
山东多地素有正月十五元宵节将面灯、萝卜灯、豆面灯等送至祖先坟茔,正月十五当天彻夜点燃长明灯,把祭祀用的灯火用来照耳朵照眼睛以求耳聪目明等传统灯俗。沿海地区则有正月十三或十四做渔灯、放海灯,到海边祭拜妈祖、龙王等水神的“渔灯节”。渔灯节的起源传说之一就是妈祖娘娘送灯解救了海上遇难渔民的故事。最终在传统灯俗的进一步强化之下,娘娘送灯的口头叙事和持灯妈祖形像在山东沿海地区人们的心中获得了更高的认同感,并体现在对持灯妈祖形像的塑造中,进一步促进了妈祖信仰以山东为跳板向河北、东北等北方地区的传播。
以山东寿光羊口公园的妈祖塑像为例,这是一尊汉白玉雕刻的妈祖像,其发髻形式与莆田市文峰宫南宋妈祖木雕夫人像十分相似,据肖海明考证,这种髻式为宋人沿袭五代的三丫髻[3]。三丫髻的采用说明工匠在进行妈祖雕像创作的时候参考了部分古代妈祖塑像,以保证对妈祖图像母题的传承。除此之外,此雕像与闽台等地的妈祖露天大型雕像有明显的不同,其整体艺术性与山东青州地区北朝时期的“曹衣出水”式佛像比较类似,体现了青年妈祖的形体魅力和青春活力。妈祖像腰间束带系结后自然垂落,肩部披风随风飘扬,这些服饰特征也明显模仿自佛教造像,体现了山东地区佛教造像技艺在妈祖塑像艺术中的传承。
结 语
在妈祖信仰北传过程中,山东地区起到了中转站的关键作用,作为宋元时代海运的必经之地,胶东半岛的妈祖庙香火很盛,是商客、船工的必拜之地。明清时期妈祖信仰在山东地区大发展,并以山东为跳板传播到了东北地区。与福建地区相比,山东地区的妈祖信仰和妈祖图像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化,这是因为妈祖信仰传播到山东以后,受到当地民风民俗、原有信仰、传统宗教、造像技艺等因素影响,于标准化之外发生了在地化现象。这种在地化现象在祭祀行为、供奉格局、口头叙事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首先体现在视觉化的妈祖图像和塑像形式中。总之,以山东地区妈祖图像与塑像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图像学的角度,对其在地化进行研究,能够为今后妈祖信仰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丰富和扩展妈祖信仰研究的内涵和外延。
注释
①张蓓蓓:《妈祖形像考——兼论妈祖服饰及妈祖形像复原实践》,《民族艺术研究》2017年第3 期;侯杰,王凤:《视觉文化·妈祖信仰·社会性别:以中国传统木版年画为中心》,《宗教学研究》2016年第2 期;侯杰,王凤:《妈祖形象的符号化建构与文学传播》,《妈祖文化研究》2019年第1 期;肖海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院藏清代〈天后圣迹图〉研究》,《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2 期;唐宏杰:《海神妈祖信仰传播与造像艺术探略》,《中国港口博物馆馆刊专辑》2017年增刊第1 期;李丽娟:《妈祖石雕神像蕴含之互动意义解读: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怀化学院学报》2009年第10 期;王英暎:《妈祖图像服饰的隐喻性》,《创意与设计》2012年第3期;王英暎:《浅析现代文化建构中闽台妈祖图像的造像观念》,《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第1 期;刘树老:《芷江天后宫门坊石雕图像的妈祖文化隐喻》,《装饰》2016年第1 期;刘福铸:《元明时代海神天妃画像综考》,《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11年第10 期;肖海明:《宋元明清肖像式妈祖图像的综合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10 期;吕伟涛:《图画中的妈祖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天后圣母事迹图志册〉研究》,《博物院》2019 第2 期;肖海明:《妈祖图像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②Idols:贡布里希艺术理论文集中的一个概念,意指人类崇拜礼仪中神的替代物。③贡布里希将视觉艺术母题的类型分为以下三种:一是指构图中独特的支配性的成分;二是指设计中的一个单元,通过重复这个单元形成一种图案或强调一种主题;三是指艺术作品的主题或题材。④福建仙游人廖鹏飞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所作《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记载:元祐丙寅岁,墩上常有光气夜现,乡人莫知为何祥。有渔者就视,乃枯槎,置其家,翌日自还故处。当夕遍梦墩旁之民曰:“我湄洲神女,其枯槎实所凭,宜馆我于墩上。”⑤属像(attributes)即人物手里拿着的或伴随人物出现以确定人物身份的符号;一些拟人形象也由其属像而得到确定。⑥关于妈祖传入山东的具体时间尚无定论,目前有宋宣和四年(1122年)之后与元代延祐元年(1314年)之后两种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宋宣和五年(1123年)八月妈祖首封之后。⑦关于妈祖首次封妃的时间有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绍熙三年(1192年),绍熙四年(1193年)之说。⑧明代平面妈祖图像有首都博物馆藏明代绢本慈圣太后绘造设色《天妃圣母碧霞元君像》,西来寺水陆画《天妃圣母像》,《太上说天妃救苦灵验经》卷首插图天妃像,《三教搜神大全》天妃像,《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天妃像、荷兰博物馆藏《妈祖圣迹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