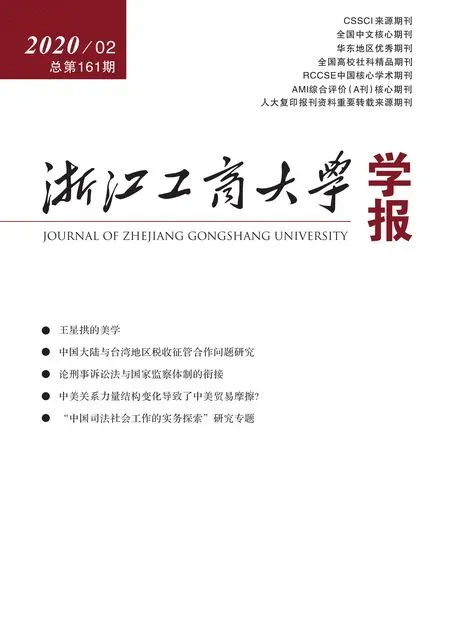从文本注释到文化传播
——由莫言短篇小说的日译本谈起
于海鹏
(浙江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一、 引 言
井口晃1988年翻译的短篇小说《枯河》被认为是日本对莫言作品译介的开始,距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之后经过藤井省三、菱沼彬晁、长堀祐造、吉田富夫、立松升一等人的努力,莫言的作品大量进入日本,并呈现出三个截然不同的时期。1988—1998年是莫言作品日译的初期,这一阶段始于井口晃,盛于藤井省三,莫言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如《秋水》《老枪》《石臼》等在这个阶段被翻译出版;1999—2012年为莫言作品日译的中期,主要表现为吉田富夫对莫言长篇小说,包括《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等作品的翻译;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其作品的日译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即不再集中于某位译者或某部作品,而是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态势。据统计,仅2013年就有四部与莫言相关的作品被翻译出版。2014年吉田富夫翻译的《丰乳肥臀》和立松升一翻译的《瘟神——莫言优秀中短篇作品集》陆续出版,2015年藤井省三还与林敏洁合译出版了《谈论世界的演讲——莫言的思想与文学合集》。
莫言作品在日本的译介虽然始于井口晃,之后又经历了藤井省三、长堀祐造、吉田富夫等译者,但是如果就读者接受度和翻译产量来说的话,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和佛教大学的吉田富夫则远远领先于其他译者。藤井省三是日本境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人,研究范围涉及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鲁迅和莫言等,他对莫言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其鲁迅作品翻译和研究的继承,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极大关注激发和推动了他对莫言作品翻译和研究的进行。与藤井相比,吉田富夫更多的是基于对莫言作品本身的认可与接受,他与莫言之间的个人关系也更加亲密,曾经互相到访过各自的故乡,同时也是唯一一位获得莫言邀请出席诺尔贝文学奖颁奖典礼的日本译者。
可以说,如果没有藤井省三和吉田富夫的译介与研究,莫言作品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就不可能有现在的规模。但是,同样也可以看到,虽然二者在莫言作品的日本译介中做出了极大贡献,但是在翻译策略、译本构建、注释使用等方面呈现出了清晰的差异,同时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日本读者产生了不同的阅读感受和推广意愿,而对于译本来说,读者的接受程度和读后的推广意愿恰恰是评测译本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因此,笔者选取了两位译者都曾翻译过的莫言短篇小说《苍蝇·门牙》的日译本,从它们的注释入手,结合日本读者对这两部译本做出的评价,探究二者采取的翻译策略的不同,进而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思考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翻译工作如何才能达到预设目标,实现译本的有效传播。
二、 注释的功用及其分类
翻译工作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译者通过对自身知识的运用,实现从原来文本(原本)到目标文本(译本)的完整转述过程。但是,在这一转述过程中,由于原本和译本所用语言的结构、内涵乃至语言之外附加的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差异,导致这种转述往往不能彻底地进行。针对这种情况,尤金·奈达提出了功能对等理论,即“不要求译本与原文在文字表面上的死板对应,而是在两种语言之间达到功能上的对等”[1],也就是说要努力实现“译文读者对译文所做出的反应与原文读者所做出的反应基本一致”[2]。奈达认为应该通过在词汇、句法、篇章、文体这四个层面的动态对等,达到在译本中再现原本文化内涵的目的,措辞通顺、表述自然,内容达意、描述传神也因此成了判断是否实现功能对等的标准。为了实现“功能对等”,翻译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了诸多尝试,1997年热奈特提出了“副文本”概念,尝试通过对译本进行内容上的补充,达到与原本功能上的对等,这里所说的“副文本”就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注释。
单就词义而论,注释“亦称注解,对文章中语汇、内容、引文出处等所做的说明,一般用比正文小的字体排印,排印于全篇末尾的称篇末注,排印于书页页脚的称脚注或页末注,穿插排印于正文中间的称夹注”[3]。不过,传统的注释多指对儒学经典的“批注”,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文学交流的越发频繁,翻译注释才逐渐成为主流解释。虽然二者在形式和功用上存在相似之处,但是翻译学中的注释在概念上却有着更加精确的界定:方梦之认为“注释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完整地传达原文语意和风格的一种补偿方法,是为了尽可能地达到翻译等值而采用的辅助性手段”[4]。热奈特则把它定义为“与一段确定的文本相关,或者置于此文本旁的一段长度各异的表述(一个词足已)”[5]。经过林纾的摒弃,严复的借用,如今注释已经正式作为翻译工作的一部分得到承认。吕叔湘认为“必要的注释应该包括在翻译工作之内”[6],孙迎春认为“注释也显示出了译者所下功夫、学样和翻译态度”[7]。胡志挥也认为“我们不能把文学翻译的注释当作一种无足轻重的技术性工作,而应把它看作是一种艺术创造的组成部分”[8],凸显出注释在翻译工作中的重要。
从注释与译本的关系来看,注释可以分为嵌入式注释和分离式注释(又称文本内注释和文本外注释)两种,也有学者认为注释还包括换位注、文内注、译本前言以及附录等(1)参见方梦之:《翻译中的阐释与注释》,载《山东外语教学》1993年第1期;赵小明、王晓燕:《从〈苔丝〉张谷若译本看文学翻译的注释原则》,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本文内容暂不涉及)。嵌入式注释是指注释内容和译文本体相结合,成为译本内容的组成部分,多指传统意义上的夹注或文内注释;与之相对,分离式注释则指注释内容与译文本体相互独立,单独排版印刷,多指脚注和尾注。从功能而论,虽然两者都能够起到解释典源、深化理解和追加内容的作用,但是从阅读效果上来看,嵌入式注释由于和译文本身融为一体,所以便于阅读,不过同样因其和译文结合紧密,故而容易打断读者思路,并占用译文的篇幅。与其相对,分离式注释由于脱离了译文本体,在内容阐释上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充分解释,但是因其与译文脱离,特别是尾注常常位于章节或整篇译文之后,容易造成翻阅困难,影响阅读速度和效果。
关于是否应该加注和如何加注的问题,学界争论已久。支持者认为一个国家的作品除了反映该国特有的社会现实、风俗习惯、典章制度、器物服饰等要素之外,还涉及该国特有的文化内涵,如叙述方式、对仗韵律、文学意象、历史典故、审美心理等,这些在原本作者与读者之间共享的隐性信息,“构成了文本能指之下的未阐明区域”和“文化缺省内容”,因此当这些内容进行跨文化传播并抵达一个全新的文化环境时,往往会成为译本读者理解的障碍,因此需要加注进行解释。反对者则认为“脚注是译者的耻辱”,优秀的译者最应该遵守的准则就是对原本的忠诚,而这里的忠诚不仅包括思想,还包括形式和内容,译者无权添加作者认为没有必要添加的信息。同时,反对者还认为“不能矮化读者,要充分相信读者的能力”,不能替读者做出决定。(2)参见张广法、文军:《汉语古诗英译注释策略研究》,载《外国语文》2018年第6期。
在笔者看来,既然翻译的任务是要把原本中蕴含的思想、审美、情节等信息顺利地从一种语言转述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同时两种语言、文化、读者之间存着差异、空白和阻碍等客观现实,那么采用适当的补充和调整进行信息上的填补无可厚非。而且,译者作为沟通原本作者和译本读者之间的桥梁,不仅需要对译本负责,还需要对译本的读者负责。通过注释这一有效途径,译者既能够帮助作者实现思想传播领域的扩大,又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本的语言文化特色,同时借助必要的注释,帮助读者全面、深入、顺畅地理解原本的主旨和意境,因此,适当、合理、充分的注释十分必要。同时,关于如何加注的问题,在《中国翻译词典》的“两原则”和曹明伦提出的“六原则”的基础上,(3)关于加注两原则参见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曹明伦:《谈谈译文的注释》,载《中国翻译》2005年第1期,其中提到了注释六原则。笔者认为加注应该遵循“最少打扰译文读者原则和与注释对象所在译文兼容原则”,其中,第一个原则应优于第二个原则,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读者阅读感受的目的。
三、 《苍蝇·门牙》日译本的注释
莫言的短篇小说《苍蝇·门牙》创作于1986年,最早发表在文学杂志《解放军文艺》上面,1992年被藤井省三译介到日本,并由白水社出版发行。同时,由于藤井认为“在莫言的全部作品中,只有(这部作品)整篇都极为罕见地洋溢着一种欢乐的气氛”,因此把它收录在了《欢笑的共和国——中国幽默文学优秀作品集》里面。2003年这部作品再次被吉田富夫翻译成日文,收录在《白狗与秋千架——莫言自选短篇作品集》中,并由日本放送株式协会出版发行。抛去这部作品日译本的其他层面不谈,单就注释而论,可以发现藤井省三的译本(下称藤井版)中共出现28个注释,其中脚注4个,文内加注24个;吉田富夫的译本(下称吉田版)中注释共有20个,且均为文内加注。并且,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乌篷船”“赤脚医生”等13项内容的重合。具体注释对象如下:
藤井版:(《苍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小板凳、朝鲜战场、河南焦作、团支部书记、乌篷船、东北靴靴棉鞋、赤脚医生、土洋结合、贫农、豆饼、高中生、敌敌畏。(《门牙》)业务参谋、林华欣、革命委员会、闹洞房、富农、地主、炕、红柳树、龙种等28处。
吉田版:(《苍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乌篷船、东北靴靴棉鞋、赤脚医生、土洋结合、小管、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敌敌畏。(《门牙》)磷化锌、革命委员会、小玩意儿、落汤鸡、“一个倒下去、一千个站起来”、闹洞房、那糖好酸呀、五分硬币等20处。
从上述注释可以看出,两位译者均表现出了对原本内容的解释意愿和深度考察。不过,虽然他们在注释对象的选择上存在重合,却也并非完全一致,比如二者均对作品中具有历史感和中国特有的词汇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革命委员会、闹洞房”等表现出了关注,但是显然藤井表现得更加明显,对此类词汇的注释占到了注释总数的75%。其实,这也是藤井在翻译中国文学时的一贯风格,这种风格在他所翻译的鲁迅作品中也能够清晰地看到,《祝福》《故乡》等作品的翻译也存在着类似现象。如藤井在《祝福》的日译本中同样使用了文中加注和脚注,在这些注释中对中国文化以及具有时代特色词汇的解释也占据了极大比重,在全篇25处脚注中,与文化和时代背景相关的词汇多达20处,占到注释总数的80%,其中如“国子监学生”“一贯铜钱”“炮烙”等均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接下来我们就结合具体的注释,分析二者在各自的译本中对注释的使用。
例1:看到守备四十三团徐团长金黄色的脸,我想他也许想起了1951年在朝鲜战场上趴在战壕里挨轰炸的情景。
藤井版:守備第四三連隊徐連隊長の黄金色の顔が見えた。連隊長は一九五一年の朝鮮の戦場で塹壕にうずくまり爆撃にじっと耐えていた情景を思い出してるのだろうかとぼくは思った。(大韓民国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との間で一九五〇年六月に始まった国際的紛争、アメリカを中心とした国連軍は大韓民国を、ソ連は人民共和国をそれぞれ支援した。五〇年十一月には中国も大量の人民義勇軍を参戦させている。五十三年七月に休戦。(4)文中翻译藤井版均来自藤井省三译《欢笑的共和国——中国幽默文学优秀作品集》,白水社1992年6月第一版,不下另注。)
吉田版:わたしは食卓の足の間に四十三連隊長の亜麻色の顔を見つけたが、ひょっとしたら連隊長、一九五一年の朝鮮戦争で爆撃に遭って塹壕に伏せていたときのことでも思い出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わたしは思った。(5)文中翻译吉田版均来自吉田富夫译《白狗与秋千架——莫言自选短篇作品集》,日本放送株式协会2003年10月第一版,下不另注。
分析:对于原作中出现的“朝鲜战场”,吉田将其直接译成了“朝鮮戦争”(朝鲜战争),而藤井则通过使用页底脚注的方式对朝鲜战争进行了详细描述,不仅指明了参战双方、爆发时间、敌对集团等内容,同时对中国以“人民义勇军”的形式参战,进行抗美援朝做出了说明,而且还特意保留了“战场”一词,在凸显画面性的同时,增强了读者的带入感。相对于吉田的“朝鮮戦争”,藤井的翻译显然更为详尽,凸显出了译者对文本之外内容的关注。
例2:我们坐在小板凳上,呆呆地看着苍蝇。
藤井版:ぼくらは小椅子(風呂場の椅子ほどの大きさ、集会などの際、各自持ち寄る)に掛けたまま、呆然として蠅を見ていた。
吉田版:小さな腰掛けに座ったわたしたちは、ぼんやりと蠅を眺めていた。
分析:对于原本中的“小板凳”,藤井将其直接译为“小椅子”,并对其进行加注,解释为“大小和澡堂里的椅子差不多,人们经常在开会的时候各自带来”,不仅指出了这种“椅子”的尺寸,而且将其在特定场合下的用途进行了说明。与藤井不仅使用汉字将“小板凳”译成“小椅子”并且进行了注释不同,吉田采用了日语式的翻译,直接将其译为“腰掛け”,意为“坐的东西,指台子、长凳、椅子等”。虽然在基本信息的转述上并没有太多缺失,但是显得不够充分和具体。
例3:他跟我是一个县的。
藤井版:徐連隊長はぼくと同県人だった(中国は全国が二千余の県級の行政単位に分かれている。日本の郡に相当)。
吉田版:彼はわたしと同じ県の人間だった。
分析:按照我国现行的行政区划标准,一般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县、县级市)、乡(镇)三个级别。日本的区划则分为都、道、府、县(广域地方公共团体)以及市、町、村、特别区(基础地方公共团体)两级。虽然中日两国均使用“县”来表示行政区划,但是无论是管辖范围,还是人口容量,抑或是经济总额,中国的“县”和日本的“県”都存在着巨大不同。因此,吉田这种直译的方式很有可能会让那些并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日本读者产生理解偏差,误以为二者是相同的行政级别。藤井版则采用了文中加注的方式,对“县”进行了解释,并明确指出相当于日本的“郡”,避免了误解的出现。
例4:后来我才知道“磷化锌”真名林华欣,是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儿子。
藤井版:あとになってからぼくはようやく「リン化亜鉛」の本名は林華欣(「リン化亜鉛」の中国語「磷化锌」と同音)で、天津市革命委員会(文化大革命中に従来の政府機関に替わって成立した権力機構)事務局主任の息子であることを知ったのだ。
吉田版:後から知ったことだが、“燐化锌”「燐化亜鉛」の本名は林華欣(リンホワシン)で、天津市革命委員会「文革中の権力機構。天津は北京、上海とともに中央直轄市」弁工室主任の息子であった。
分析:在藤井和吉田的译本中,均对原本中出现的“林华欣”和“革命委员会”进行了注解。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藤井对于“林华欣”的注释清晰地解释出了“因为在中文里面,林华欣和当时作为灭鼠药的磷化锌发音相同”,为了嘲讽“林华欣”才给他取了“磷化锌”的绰号,吉田版的注释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另外,两者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注释都突出了这一机构在当时作为权力机关的角色,但是藤井还特意点出了“革命委员会”替代“之前的政府机关”行使权力的事实,引导读者去思考当时中国的情况,而吉田的关注点则放在了天津的直辖市身份上。
通过上述对两部译本注释的比较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发现:单就原本和译本的贴合度而论,以及从功能对等的标准来评判的话,毫无疑问藤井的译本显然解释得更为充分,补充了对于众多日本读者来说难以理解的内容,理应得到更多的阅读,受到更大的欢迎。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笔者在筑波大学访学期间,针对日本不同层次的读者就两部译本的“阅读感受”和“宣传意愿”进行了调查,(6)调查对象包括筑波大学人文系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选修日本近代文学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一般民众,以及当地的中文学习者等共计73人。得到了“相对于藤井展示出一段历史,显示出当时中国情况的翻译,吉田的译本则充满了亲和力,较为容易让读者接受”的结论——显示出功能对等与阅读感受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细问之下,受访者认为“藤井的作品虽然做了大量的调查,显示出了对于中国事物的关心和探究,但是作为一名普通的读者,更愿意获得情节和审美上的享受,那些文化和细节方面的研究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工作”,同时“藤井在《苍蝇》中使用了太多脚注,影响了阅读速度和感情流淌”。与之相对,“吉田富夫的作品虽然并不完美,但是译本的翻译比较符合日本读者的阅读习惯,因此阅读起来比较舒服。”——这些回答显示出了中日两国的读者在译本阅读感受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认为的优秀译本日本读者却未必接受,推广意愿也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强烈。那么除了注释以外,藤井和吉田的译本在整体上又存在着什么不同呢?
四、 两部译本的翻译策略
从上文的统计和分析中可以看出,藤井的注释多集中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现象的解释上,而吉田的注释则更多的是关注对该词汇本身的解释,这种趋向在他们翻译的莫言其他作品中也能够得到印证。与《苍蝇·门牙》一起被藤井翻译的还有《透明的萝卜》等作品,它们被一起选编进了莫言的短篇小说集《怀抱鲜花的女人》之中。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部短篇小说集的译本后面附有一篇题名为《从中国农村和军队走出来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访谈,这是藤井根据他1991年2月在北京采访莫言时的谈话整理而成的,从中可以发现藤井提出来的许多问题都是关于莫言的创作动机以及社会背景方面的内容,(7)参见朱芬:《莫言在日本的译介》,载《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4期。因此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出“除了对作品文本的关注之外,藤井对于作品中蕴藏的社会背景、历史要素和文化问题等也充满着求知欲和好奇心。”这样也就容易理解为何他的注释会偏重于历史和文化问题的展现与阐释了。
藤井省三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始于鲁迅,他曾经坦言“研究鲁迅的原因一来是基于中日之间悠久的密切关系,二来是鲁迅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鲁迅文学特有的魅力”[9],由此可以看出,藤井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更多的是聚焦在文学之外的文化层面以及杰出作家的历史意义上,是一种基于文学之上的思想、民族、国情的思考与探视。这种探视的态度藤井并没有掩饰,他在与吕周聚的对谈中也曾说到“对经济持续增长期中的日本学界来说,中国作为‘文化’问题显示出巨大的存在感,解决这一‘文化’问题重要的钥匙就是鲁迅”[9]。从中可以看出,藤井对鲁迅的译介和研究,所关注的并不是文学本身的审美,而是文学背后所蕴藏的内容。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藤井对鲁迅作品的译介“相比竹内译本,藤井译本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更像研究”[10]。而在莫言作品的日译本中,藤井似乎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趋向和特点。
与藤井热衷于关注文本之外的内容相比,吉田似乎更加愿意将作品内容和莫言本人对作品的解读传递给日本读者,例如吉田在《师傅越来越幽默——莫言中短篇自选作品集》日译本里附录的“作品解读”全部译自莫言本人所写的“创作意图说明”,而且还附有莫言写给日本读者的后记,《丰乳肥臀》的日译本里同样也附有莫言“写给日本读者的话”。一般来说,译者后记中对原本所做的解读,要么是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而做的背景介绍,要么是对读者较难理解的部分进行说明,而从上述吉田在译本中附加“作品解读”和“作家赠言”这一行为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吉田的目标读者意识非常强烈,同时格外关注读者的阅读感受。此外,关于“为何会在《丰乳肥臀》日译本的每个章节添加小标题”提问,吉田解释道:“考虑到有的读者可能对现代中国的历史未必熟悉,我与莫言商量之后,添加了作为小说背景的小标题,并辅以简略注释”[11]。显示出了吉田强烈的“读者目的”意识。
其实上述的讨论也可以归结为翻译策略中的“异化”与“归化”之争,这种争论源于翻译本身就是语言之间的转换,但是由于不同语言之间在词汇构成、理解方式、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原本和译本之间的信息缺失,也导致读者对译本这一创造性产物产生了理解偏差。因此,如何在保证审美文化特点的同时,将原本中的信息全面、准确、流畅地转述到译本之中成了关键问题,也由此产生了翻译界关于“异化”和“归化”的讨论。韦努蒂将“异化”和“归化”分别解释为“接受外国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的情景之中”和“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国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带入译入语文化”[12]。从藤井和吉田两人的莫言作品日译本来看,可以发现藤井明显倾向于“异化”翻译,固守原始文本,在更多保留词汇、句段、篇章原始形态的基础上,引导读者探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问题。吉田则更多地使用“归化”翻译,以日式思维和语言表达对莫言的作品进行转述,以利于读者更好地进行阅读,接受译本信息——二者在翻译策略上的不同直接反映在了译本的注释上,也因此带来了不同的读者感受。那么,为了顺利地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国作品的对外译介应该遵循怎样的翻译原则呢?
五、 “读者优先”原则
2016年11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会议强调“要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创新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拓展渠道平台,创新方法手段,增强中华文化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竞争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对弘扬“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出了新的定位,也为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构建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促进国际社会平等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合作与对话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方针指引。不过,想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要重视翻译的作用,因为“中译外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实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汇通融合,完成中国文化‘走出去’时代重大使命的途径之一”[13]。同时,由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本质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因此以文化“走出去”为目的的翻译也不再是简单的语言转述,而是一种与受众和媒介之间充分互动的传播手段,如果只是一味地以我为主,强调本国文化的传播而忽视了译本读者所拥有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接受能力的话,势必会影响翻译的传播效果。
其实在此之前,我国政府也一直在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工作,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中国学术水平、体现中国文化精髓和时代前沿的作品,“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以及兴起于2010年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都是其中具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项目。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良好愿望与现实状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14],“(那些工作)并没有促成我们的中国文学、文化切实有效地‘走出去’”[15]。英国翻译家蓝诗玲在访谈中曾说:“尽管媒体对中国多有关注,尤其是在政治经济方面,但是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对母语为英语的大众来说始终不易被接受。你若是到剑桥这个大学城浏览它最好的学术书店,就会发现中国文学古今所有的书籍也不过是占据了书架的一层而已,其长度还不足一米”[16]。甚至就连被誉为“世界文化交流史上重要里程碑”的由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英文版在西方也受到了冷遇。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学界从译本选择、翻译技巧、出版渠道、读者反馈等层面进行了诸多探讨,其中王榕培认为“收录在《大中华文库》中的译作海外发行总量并不多,原因在于读者接受有一定的偏向,个中缘由至少有二:一为中西译者的思维差异所致,以中国人的方式阐释相对而言不易为西方读者所接受;另一方面,在语言的生动性上,中国译者有可能不及西方译者”[17]。同时,如果我们把翻译看作是一种包含了原本、译者、载体、受众以及翻译效果等层面构成的传播模式的话,那么最应该受到重视的则是译本的传播效果,而这种效果的评测要通过受众即译本的读者才能实现。同时,现代传播学认为“受众利益应该放置在传播活动的首位,无论是信息内容的选择,还是信息产品的制作,都要以受众的根本需要作为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18]。也就是说,如果译本不能得到广泛且精细阅读的话,那么翻译的目的就没有达成,这项翻译活动也就是失败的。然而“阅读”这项活动,最终是要同读者联系起来的,因此翻译活动首先应该遵循的就是“读者优先”原则。
那么“读者优先”原则下的翻译活动应该怎样进行呢?首先在原本的选择环节,许钧认为“对外译介首先要形成一种中国文化价值观,把中华民族最本质、最优秀、最精华、最核心的文化思想与价值观念(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国外受众易于、乐于接受的方式逐步地推介出去”[19]。在坚守这一原则的基础上,我们不妨从选题阶段就开始邀请国外学者、编辑、发行、营销等环节的文化主体参与进来,通过问卷和试投的方式了解对象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选取该国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避免在源头因为缺乏对国外读者的需求分析而导致外译著作失去针对性,保证在基础阶段就能够获得足够的关注和吸引。也就是说,在保证思想正确、价值统一、内容完整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选择对象国读者想要以及愿意去阅读和传播的优秀原本进行翻译。
其次在译者的选择上,之前的翻译活动几乎都是国内译者来推进的,缺少外国学者的参与。许多译者往往是依靠自己掌握的外语知识“用西方概念来裁剪中国社会现实,但是在逻辑和思维上却固守中国的本土规则”[20]。结果必然会造成译者“用他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形式、方法与思维在国外的接受度不够高”[21]。对象国读者的反响自然不会很好。因此,要想顺利实现跨国跨语种的文化传播,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寻求国外译者和中国本土译者的跨境合作。因为虽然国内译者对原本的理解更加透彻,但是由于其自身的知识背景和母语干涉,对目的语的把控仍然缺少先天优势,在表达上也无法像国外译者那么流畅,对象国读者的接受度自然也就不会那么理想。另外,我们也可以委托海外的汉学家进行翻译,蓝诗玲、葛浩文、吉田富夫的成功也充分说明了这种模式在现阶段中国文化外译中具有优越性。
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正如许钧教授所言:“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在西方国家的译介所处的还是一个初级阶段,我们应该容许他们在介绍我们的作品时,考虑到原语与译语的差异后,以读者为依归,进行适时适地的调整,最大限度地吸引西方读者的兴趣。……随着中国作品的不断外译,之后一定会有适应需要的忠实译本的出现”[22]。也就是说,当前阶段在进行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海外传播时,最好以目的语国家的文化习惯、阅读习惯为标尺,构建符合受众需要的翻译内容与翻译模式,由此才能赢得海外读者的欢迎与认可。因为“(这些读者)在阅读时的关注重点,不在乎是否获得了如作者或者译者所期待的文本交际效果,而在乎文字世界里是否有他们寻觅的某种酣畅淋漓与自然流畅的表达方式,从而获得某种阅读快感。”[23]所以,为了更好地使译本获得阅读,实现文化传播的目的,就应该采取“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不应斤斤计较于字面表层的对等,而是应直抵语言的深层含义”[24],从而达到预设的翻译效果。藤井的译本之所以在读者感受上稍逊吉田的译本,在某种层面上也可以归结为他对“异化”翻译的过度坚持。在《红楼梦》的两个主流英译本中,之所以大卫·霍克斯与约翰·闵福德的TheStoryoftheStone能够在认同程度、引用频次、馆藏数量以及读者评价上远超杨宪益、戴乃迭的ADreamofRedMansions,(8)参见江帆:《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汪庆华:《传播学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与翻译策略选择——以〈红楼梦〉英译为例》,载《外语教学》2015年第3期。也是因为采取了合理的归化翻译策略,所以才顺利地实现了文本的传播目的,完成了语言翻译之后的“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任务”。
六、 结 论
翻译工作的进行从根本上来说是以传播过程的实现为标尺的,通过语言的替代、载体的转换、受众的变迁而实现原本中所蕴含或附加的情绪、审美、旨趣的传递。在此基础上,由政府行为所引导的翻译项目想要实现扩大国际影响、增强国民自信、打破文化壁垒、实现文化外传等目标也都是建立在“读者接受”这一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翻译工作首先要遵循的就是“读者优先”原则。为此,我们应当做到选择读者需要的原本,采用读者接受的方式,满足读者阅读的期待,邀请国外译者或汉学家充分参与到外译作品的甄选、翻译策略的制定、具体的翻译活动中来,使中国作品的外译更加符合海外读者的阅读期待。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原本的选择要做到“以我为主”,不能偏离中国文化的精髓;读者的界定应该扩大范围,把听众、观众、网民等其他载体的受众列入翻译传播的对象之中;译者的选择要加强中国译者和国外译者的交流与合作,由中国译者和学者对原本及内涵进行解读,国外译者及汉学家对语言进行加工润色,根据目的国读者的需求做出适应性调整,以顺应海外受众的阅读和理解习惯;在翻译过程中,在保证原本主体内容和文化意象不发生缺失和偏离的情况下,建议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适当使用注释等补充手段,便于读者的接受和阅读,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