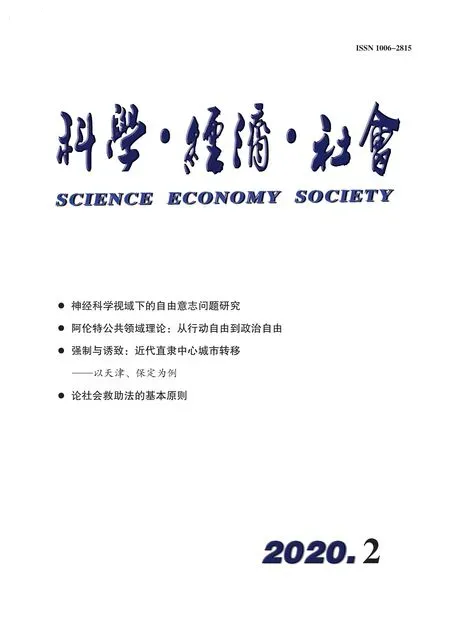强制与诱致:近代直隶中心城市转移
——以天津、保定为例
周 辰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 苏州 215123)
舒尔茨将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经济及政治。[1]中国城市转型的实质是制度变迁,既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契约等正式约束,也包括价值信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约束。林毅夫根据制度变迁的产生原因,将其划分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2]就本文而言,各城市转型动因迥然不同,城市依靠行政干预进行转型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城市受到经济、文化等方面影响自发地产生变化,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
从康熙八年(1669)至民国二年(1913),保定是直隶省会,一度是全省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天津原是卫所,充当北京的军事、经济辅城,清代初期“完成了由封建军事城堡向封建工商业城市的演变。”[3]自1860年天津开埠至19世纪末,天津与保定在不同路径的演进过程中城市地位发生更迭,天津取代保定成为直隶地区的中心城市。本文试以城市转型的动因为视角,探究近代城市发展趋势及其成长动因,以期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借鉴。
一、西方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近代天津在西方国家入侵的压力下被动开放,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天津近代转型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制性地打开了天津市场,使之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同时,列强的通商需求刺激了天津的经济动力,城市发展为区域性的商业中心,是为直隶中心转型的开端与主要原因。
(一)天津在外部压力下被动开放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列强逼迫清政府相继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附加条款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法律的手段谋取侵华特权,打破了天津原有的发展路径,是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列强入侵、开埠通商是天津崛起的前提条件,天津由传统的封建商业城市转型为半殖民半封建的贸易城市,列强在津攫取诸多特权,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开埠通商。根据中英《北京条约》第四款规定,“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贸易均照经准各条所开各口章程比例,画一无别。”[4]该条款规定外国人在津拥有居住、贸易的权力,天津由封闭走向开放,是城市现代化启动的开端。
2. 划占租界。英国援引《天津条约》中“听便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茔等事”[4]的条款,向清政府提出“欲租津地一区,为建造领事官署及英商住房栈房之用,”[5]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天津始有租界。列强在租界内享有自治权和治外法权,设有不受中国政府统辖的行政机构,长期派驻军队,单独设置警察和监狱,任意买卖土地和征收捐税,俨然“国中之国”。[6]租界既是列强侵华的重要据点,也是西方文明传播的输出地,客观上促进了天津近代转型。
3. 协定关税权。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4]中国自此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列强大幅下调了中国的关税税率。据中英《通商章程》规定,普通出入口税则“值百抽五。”[4]“主要进口货物的税率,比1843年的水平又降低13——65%。”[7]《天津条约》还规定了子口税制度,“已在内地买货,欲运赴口下载,或在口有洋货欲进售内地,倘愿一次纳税,免各子口征收纷繁,则准照此一次之课。其内地货,则在路上首经之子口输交,洋货则海口完纳给票,为他子口毫不另征之据。所征若干,综算货价为率,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4]洋商在华进出口商品,只需缴纳一次性2.5%的子口税,中国商品在国内转运,每经过一道关卡,都要缴纳各种税费。关税的调整、子口税制的颁布,使我国进出口贸易处于劣势地位,各开埠口岸沦为了列强在华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的中转站,天津由此发展为北方地区的商贸中心。
4. 海关行政权。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被剿灭后,英美法三国组成税务司管理上海海关,开启了列强参与中国海关行政管理的恶例。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4]中国海关行政权自此开始由外国人所控制。1861年,天津海关成立,首任税务司是英国人克士可士吉。英国人德璀琳曾控制天津海关达22年之久,不仅一手操纵了天津的进出口贸易,而且忠实地执行着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各项侵略政策。德璀琳因此被外国资本家称为洋行“贸易的助手”。[8]中国海关是西方控制进出口贸易的工具,天津海关在近代以来长期被列强所控制,根本起不到保护本国贸易的作用。
(二)西方通商需求推动了天津的现代化启动
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料与市场的需求空前提升,疯狂对外扩张,天津被卷入到世界市场体系之中。列宁曾说过“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9]列强的贸易需求提升了天津的经济地位,并在租借地传播西方文明,天津在20世纪初发展为全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
1. 对外贸易的繁荣提升了天津的经济地位
自清代以降,天津是漕运、海运的交汇处,商品经济颇为发达。“清代中叶,无论从漕运、盐业,还是海运、商业的发达情况来看,天津已明显地成为北方的商业中心。”[8]就其商业地位而言,开埠前的天津被定位为北京的经济辅城,“商品经济还没有发展到有自己直接控制的经济圈,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很弱。”[10]
开埠后天津的经济地位明显提升,19世纪末发展为北方地区的外贸中心,对外贸易甚是繁荣。开埠通商加强了天津与国内、世界市场的联系,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需求激发了城市的经济潜能,天津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1865年为1290万两,1895年则达到了5017余万两,1911年为11654余万两,到1921年达22478余万两,1931年达到350230余万两。[11]天津对外直接贸易进出口比重明显上升,以1867年和1894年为例,进口由1.1%升至2.7%,出口由1.6%升至5.1%。[12]严中平曾对上海、广州、汉口、天津、大连五港口的对外贸易总值所占比重进行统计,天津由1871年由1.8%增长至1935年的11.7%,[7]20世纪20年代以后,天津外贸规模超越汉口、广州,是继上海之后中国第二大商业城市。与此同时,天津的商业腹地也随之扩大。开埠前,它作为中转集散地,将沿海贸易集中在这里,将南方货等销往北京和内地,[13]开埠后其势力范围横亘于黄河左岸以北的本部六省(直隶、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及蒙古、新疆和满洲,[14]逐步摆脱了依附北京的经济地位。
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也推动了天津近代工业、金融业的初步发展。1871年成立的大沽驳船公司是外国资本在津创办的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据统计,20世纪以前,外国资本经营的企业共有16家,资本总额为94.8万两左右,雇佣工人为1300人左右。[15]天津最早的近代银行是1882年设立的英国汇丰银行天津分行,19世纪末俄国道胜、日本横滨等银行相继在津设置分支机构。就发展进程而言,天津的近代工业、金融业在20世纪前处于起步阶段,在民国时期逐步成为北方地区的工业、金融中心。
2. 租界的开辟推动了天津城市近代转型
列强相继在津开辟租界,以西方模式经营管理租界,改变了天津的城市空间结构,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秩序,推动了城市近代转型。
首先,租界区范围的扩大拓展了城市的空间。19世纪60年代以后,英、法、美三国在紫竹林一带开辟租界,形成了天津最早的租界区。租界区原为荒凉之地,英法当局“均在河岸修建了停船码头,转移了天津城市的经济重心,并由此造成了租界的繁荣。”[16]1894年甲午战争结束,日、德开设租界,五国租界连成一片,“很快发展成为天津的对外贸易中心和城市的经济中心。”[16]庚子之变后,天津拥有九国租界,“总面积达23350亩,相当天津旧城的8倍。”[10]天津的经济中心也由老城区转移至租界区。
其次,租界的开辟改变了当地传统的社会秩序。租界作为列强侵华的前沿阵地,将西方文明传入中国,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打破了传统体制的束缚,在管理体制、市政建设、思想文化观念、社会生活等领域推动了当地转型。英国作为当时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最早在津开辟租界,对当地冲击最具典型性。管理体制方面,英国将西方城市自治制度引进中国,英租界的行政管理机构是工部局,董事会是统治主体和决策机构,经选举产生,该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得到了中方的借鉴。经济活动方面,英租界是列强推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设有众多洋行、银行等企业。据统计,在1937年前后,天津有483家洋行(不包括一般中小型日本洋行),其中404家设在英租界。[6]各国集中将银行设立在英租界,维多利亚道外商银行大楼毗邻有“天津华尔街”之称,[6]英国汇丰、美国花旗、俄国道胜、日本横滨正金等银行设立于此。洋行数量的激增促使买办阶层的产生,外国银行业的蓬勃涌现刺激了天津近代金融业的转型与兴盛,改变了天津的社会结构,提升了城市的经济地位。市政建设方面,近代天津公共设施大多发轫于英租界。1887年,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铺设了碎石子公路,此后煤气、自来水、电灯等现代技术相继传入,天津在19世纪末期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社会生活方面,英租界内设有教堂、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建立旅馆、俱乐部、夜总会等娱乐休闲场所,印刷了天津最早的英文报纸《中国时报》与中文报纸《时报》,西方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对当地居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综上所述,20世纪以前的天津在现代化启动中经历了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列强胁迫清政府将天津开埠,并攫取众多特权,打破了城市传统秩序,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西方资本、技术、文化的传入为天津近代转型起到了诱导作用,城市的经济活力被激发,在思想观念、社会结构、市政建设、管理制度等方面均有所变化,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西方国家的外部冲击为天津的崛起提供了主要动力,构成了天津、保定区域地位转换的前提条件。
二、中方改革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直接推动力
天津是北京的东大门与入海口,政治、军事重要性居各通商口岸之首,开埠后是列强“足以威胁京城”的基地与“阴谋的巢穴”。[17]清政府对天津进行了重点经营,推动了天津、保定行政地位的转化,清政府的众多行政干预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
(一)地方行政体制的调整提升了天津政治、军事地位
天津开埠后,清政府于1861年成立总理衙门,下设三口通商大臣,驻扎天津,管理牛庄(后改营口)、天津、登州(后改烟台)三口通商和对外交涉事务,天津政治影响力空前提升,“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16]
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后,清政府再度调整地方行政体制,裁撤三口通商大臣,设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自李鸿章起,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形成惯例。清政府颁布上谕如下:“天津地方紧要,自宜因时变通,三口通商大臣一缺著即行裁撤,所有应办各事宜均著归直隶总督督饬该管道员经理,即由礼部颁给钦差大臣关防,用昭信守;并著该督于每年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倘遇有紧要事件必须回省料理,亦准其酌度情形暂行回省,事竣仍赴津郡,以资兼顾。”[18]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的设立,是直隶行政中心转移的开端。上谕表达了两层含义:第一,直隶总督轮驻天津、保定处理政务,直隶形成了双省会并存的政治格局,直隶政治中心开始由保定向天津转移。第二,天津的重要性高于保定。天津“地方紧要”,是海防、洋务、外交的要地,直隶总督常驻于此,只在冬令封河时期才回到省城保定。在轮驻制度中,总督驻地以天津为主,保定为辅,此后鉴于洋务事宜繁忙,“遂终岁驻此,不复回驻保定。”[19]天津成为直隶地区事实上的政治中心,保定省会地位徒有虚名。同时,清政府认为“天津洋务海防,较之保定省防关系尤重”,[18]把天津作为重点经营的军事要地,保定的军事中心地位也被天津所取代。
(二)洋务运动的开展确立了天津在直隶地区的中心地位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有识之士为拯救民族危亡,主动进行现代化探索,开展洋务运动。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以后,天津是中国北方推行洋务运动的中心地区。
天津作为拱卫京师的重要门户,“遂被选定为清王朝重点布置防御力量的沿海城市,20世纪以前,天津竟成了中国最大的近代化军事基地。”[20]清政府在天津兴办了大量企业,天津机器局和大沽船坞是官办工业的骨干企业。天津机器局筹建于1867年,是天津最早出现的近代企业,规模仅次于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专制外洋各种军火机器。”[21]大沽船坞创建于1880年,是北方最早的船舶修建厂和重要的军工基地。为了解决工业原料及运输问题,李鸿章创办了开平矿务局,采取西方技术采掘煤矿,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运枢铁路——唐胥铁路。为配合北洋水师的建设,洋务派开办了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北洋医学堂等新式学堂,天津成为近代教育的中心。天津还是中国最早设立电报、开通有线电话的城市,一度是“中国邮政的总汇地点”。[8]
洋务运动开启了天津早期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其中官方是主要的推动力量。20世纪以前,近代天津官办和官民合办的企业资本总数,占了当时天津全部近代企业资本94.3%,工人数占当时天津近代产业工人数总额的78%。[16]19世纪末,天津集直隶贸易、工业、军事、教育、通讯、邮政、交通中心于一体,还是总督的常驻之地,是直隶地区的中心城市。
(三)清末新政强化了天津的政治、经济功能
20世纪初,清政府历经庚子之变的劫难,推行新政。“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22]1902年,袁世凯以天津作为其实施新政的核心地区,强化了其政治、经济功能。
就政治而言,天津俨然是全国新政的示范之地,影响力再度提升。袁世凯在津推行巡警制度、提倡兴办实业、兴办新式学校、开发河北新区、重视市政管理、试行地方自治、开展禁烟运动等。天津在城市管理、地方自治、振兴实业和新式教育等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在全国的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3]自1902年以后,袁世凯常驻天津,很少去保定,“直隶总督新署迁至海防公所,天津始为直隶省省会。许多官邸、衙门纷纷迁至境内。”[23]1913年,民国政府将直隶省会迁往天津,正式确认了天津的政治中心地位。
就经济而言,袁世凯倡导兴办实业,开办直隶工艺局,天津“成为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国内的特大城市。”[24]天津的近代企业在新政期间得到迅猛发展,庚子以前,天津的近代企业中民办者仅有五家,资本总额只有100余万元;到1900—1911年间,天津近代工业已有135家,可计算的资本总额为2920万银元。其中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企业资本总额为2200万余元。民营资本厂家共107家,注有资本总额的53家其资本总额为670余万元。[25]但是,民族资本只占资本总额的22.95%,官方是当地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主导者。
综上所述,天津在遭遇西方势力侵入的同时,经历了由清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官方决策推动了直隶政治中心的转移,省会轮驻制度的实行,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开展,使天津跃升为直隶地区的政治中心。此外,清政府兴办了大量近代工业企业、倡导发展实业,亦强化了天津的经济功能。
三、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保定的转型属于清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历经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前的启动阶段,保定失去了直隶中心城市的地位;二是清末十年的快速发展阶段,保定城市功能发生嬗变,由政治中心转型为区域性的军事、文化城市。
(一)20世纪以前,保定在直隶中心区位的丧失。
19世纪70年代,保定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也开启了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近代工业、教育、金融、通讯、邮政、交通等领域初步发展。李鸿章购置西方机器,在保定东门外设军械局并建有八蜡庙子弹制造厂,为保定兴办近代工厂的发端。[26]1870年建直隶官刻印书局,为直隶省较大的印书局。[26]1871年设修志局,重修《畿辅通志》。1885年架设了由天津至保定的电报线路,1887年北洋电报官局在保定设分局。1898年直隶总督王文韶奏准创建“畿辅大学堂”于保定,[27]被视为保定近代教育的开端。同年,中国通商银行在保定设立分行。[28]1899年卢汉铁路卢沟桥至保定段通车,北京邮政总局建保定大清邮政局。此外,基督教、天主教相继在保定城内开设西方的诊所、医院、教堂,城市面貌有所变化,基督教、天主教的引入属于西方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对城市转型影响力甚微。
19世纪末的保定处于近代转型的启动阶段,发展速度极为缓慢。尽管保定在局部领域具备了现代化的特征,城市在社会结构、空间范围、文化观念等方面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仍然是传统封建政治、军事城市,被天津迅速超越,直隶中心城市就此发生转移。
(二)20世纪初,保定市功能的嬗变
20世纪初,保定在清末新政的实施下加快了城市转型的进程。袁世凯对保定进行了系统性的改革,涉及政治、军事、警政、教育、经济等领域,是全国军事、教育改革的示范之地,从传统的政治中心转型为军事、文化重镇。
保定近代文教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袁世凯于1902年在保定设立直隶学校司,是我国最早的省级教育机构,“为通省学务总汇之所”。[29]随着科举制的除和“癸卯学制”的颁布,保定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有学生城的美誉。从类别看,有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和军事教育,从等级看,有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城镇和乡村的各级各类学校总数约300所。[27]其中直隶政法学堂、直隶通省巡警学堂系全国首创,直隶农务学堂、直隶师范学堂系全省首创。教育事业的繁荣,也带动了图书馆业、印刷出版业、新闻报纸等文化产业蓬勃发展。1902年,清廷在保定成立军学编译局,下设武学书局。官府办的报刊有《北洋官报》《农务官报》和《直隶教育》。革命党人创办了《直隶白话报》《地方白话报》。[30]1908年创办的直隶图书馆是当时直隶地区最大的公用图书馆。清末时期,保定的文化事业在全国享有盛名,直隶地区形成了保定、天津双文化中心格局。
保定军事地位显著提升。庚子之变后,列强规定天津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拟由中国国家禁华兵距驻扎天津之军队二十华里内前进或屯扎,”[31]天津军事功能被严重削弱,袁世凯将军事改革转移至保定推行。首先,袁世凯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编练北洋新军。“先令屯扎保定省垣,以便聚处训练。”[29]北洋常备军六镇编成后,常驻保定的兵力保持在两镇以上,先后有二、三、四、六镇。[32]其次,保定还成为军事政治人才培养基地,而且超越直隶省区域性而成为全国性军政人才培养基地。[33]袁世凯在保定创办了十余所军事院校,先后建立将弁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速成武备学堂。在此前后还设立军械学堂、军医学堂、经理学堂、宪兵学堂、军官学堂、北洋陆军师范学堂、马医学堂等。[30]新政以后,直隶军事重心由天津向保定转移,保定发展为全国瞩目的军事重镇。
同期,保定的政治功能再度被弱化。20世纪以前,直隶总督尚且遵循轮驻制度。以李鸿章为例,他于1876年12月(农历)离开天津赴保定,“十二日李伯相离津回保定,”[34]次年3月回到天津,“大约于三月初旬旌节可到津,”[35]在保定停留时间大约3个月,保定不失为直隶政治中心城市之一。1902年,袁世凯移督天津,衙署、官员相继迁出,保定沦为名义上的省城。
综上所述,保定近代转型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行政权力为城市现代化启动提供了主要动力。与天津相比,保定受到官方的支持力度相对不足,政治功能日渐衰微,直隶中心因此转移至天津。清末新政中保定在近代军事、教育改革方面居全国前列,由政治中心转型为区域性的军事、文化重镇。
四、余论
保定与天津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体现了近代中国城市的两种发展路径。“不同的制度安排也演化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路径,并在经济表现和绩效方面产生巨大的反差。”[36]直隶中心城市的转移,是“西方与中方”“经济与政治”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反映了近代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具有特殊性。
首先,经济因素取代政治因素构成了近代中国城市转型的主要动力,这是津兴保衰的根本原因。“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虽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则成为城市一个主要的规律”。[37]天津等沿海、沿江城市在西方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作用下被动开放,客观推动了当地商品贸易的发展,升级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如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等。开埠城市因经济功能的强化而迅猛发展,西方贸易需求所产生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城市成长的根本动力,列强以强制性的手段获得了开埠通商、协定关税等特权,是其崛起的前提条件。保定等传统城市凭借政治权力推动了近代转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主要动力,如北京、保定、开封、太原等。传统区域政治中心是政客聚集之地,城市经济功能以消费为主,生产功能不显著,商品经济缺乏成长动力。即便如此,保定在政治力量的作用下仍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清末新政中是全国军事、教育改革的示范之地,民国初期是直隶军阀大本营所在地,“素称华北第三商埠,”[38]与天津相比却是相对衰落的。近代中国传统城市格局重构,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兴盛是历史的发展趋势,天津的崛起与保定的衰落反应了这种规律。
其次,政府的决策推动了近代直隶政治中心的转移。伴随着沿海、沿江城市的相继开放,各地经济中心大多发生位移,唯独直隶政治中心城市出现更迭,这与天津特殊的区位密切相关。天津与保定均作为北京的门户,在洋务运动、清末新政中得到了较快发展。两城相比,天津区位优势优于保定,天津是距离京师最近的开埠口岸,清政府以天津作为处理外交、海防、洋务、新政的要地,直隶总督由轮驻津保变为移督天津,促使直隶政治中心发生位移。庚子之变后,天津受《辛丑条约》的限制,将军事功能转移至保定,具有一定的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