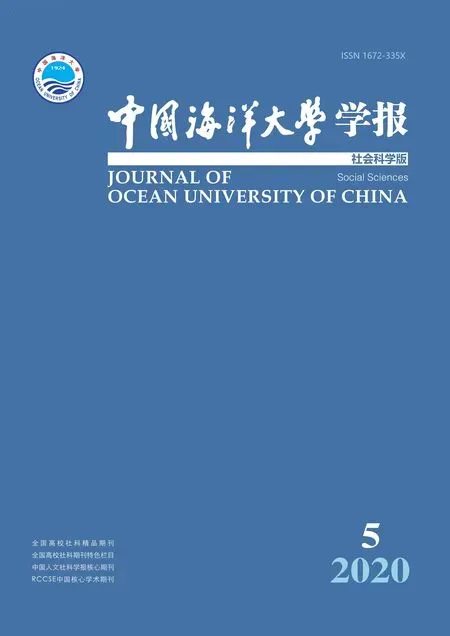中国海洋法制度与若干问题概论*
金永明
(中国海洋大学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本文在时间和内容上,重点分析1949—2020年间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在海洋法制度上的立法进程和相应的重要海洋政策,以及其存在的若干问题,目的是检视中国海洋法制度体系的效果,评估国家海洋治理体系和海洋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更好地推进国家海洋事业、建设海洋强国、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目标做出微薄的学术贡献。(1)中国在海洋法治发展上的历程、特点和作用内容,参见贾宇:《改革开放40年中国海洋法治的发展》,《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4期,第5-33页;马得懿:《新中国涉海法治70年的发展、特点与应然取向》,《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1期,第27-39页;杨泽伟:《新时代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变革:理念与路径》,《法律科学》2019年第6期,第178-188页。
一、中国海洋法制度的发展与成形
(一)海洋法制度的萌芽阶段(1949—1978)
在此阶段,我国的海洋立法数量有限,而且立法层次较低,没有一部法律。(2)例如,1954年《海港管理暂行条例》,1955年《关于渤海、黄海及东海机轮拖网渔业禁渔区的命令》,1958年《进出口船舶联合检查通则》,1964年《外国籍非军用船舶通过琼州海峡管理规则》,1974年《防止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1977年《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实施细则》,等。在此期间,最重要的政策性立场文件是《中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1958)。其核心内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确立了领海的宽度12海里;第二,宣布使用直线基线;第三,一切外国船舶包括军舰进入领海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并遵守中国的有关法令。(3)参见《中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1958年9月4日)第1-3项。其主要特征是确保中国的海洋尤其是海防安全(海上安全)。(4)《中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是在中美苏关系紧张,中国大陆炮击金门岛,并在美国第七舰队加强保护台湾的情况下为保卫海洋安全发布的政策性立场文件。参见[法]Francois Joyaux,《中国的外交》,[日]中嶋嶺雄、渡邊啓貴译,白水社1995年版,第31-33页。
(二)海洋法制度的发展阶段(1979—1990)
此阶段的海洋立法情况有所改观,不仅海洋法规的数量大增,而且立法层次也有所提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第二,在海洋资源利用方面,《中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列》(1982),《中国渔业法》(1986);第三,在航行安全方面,《中国海上交通安全法》(1983)。这些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对于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海洋法制度的成形阶段(1991—2009)
在此阶段的海洋立法业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在制定海洋基本法制方面:《中国领海及毗连区法》(1992),《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决定》(1996),《中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1998)。
2、在完善海洋法制的基础方面:《中国政府关于中国领海基线的声明》(1996)。
3、在制定海洋其他部门法规方面:《中国海域使用管理法》(2001),《中国渔业法》(2000、2004修改),《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修改),《中国涉外海洋科学管理规定》(1996),《中国海岛保护法》(2009)。
4、在履行国际海洋规则和业绩方面: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作出的排除性声明(2006年8月25日),提交东海部分外大陆架初步信息(2009年5月11日),针对日本外大陆架划界案的书面声明(冲之鸟问题,2009年2月6日),针对马来西亚和越南联合外大陆架划界案、越南单独外大陆架划界案的照会(2009年5月7日);缔结《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2年11月4日),《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2000),《中日渔业协定》(1997),《中韩渔业协定》(2000),《中日关于东海问题的原则共识》(2008)等。
上述的法规和声明、以及协定和共识,不仅维护了我国的海洋权益,而且切实地履行了国际责任和义务,保障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初步形成了中国海洋法制度体系。
(四)海洋法制度的充实阶段(2010—2020)
在此期间,与海洋有关的法制,主要为:《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3、2016修订),《中国关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的声明》(2012),《东海部分大陆架外部界限划界案》(2012),《中国关于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声明》和《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航空器识别规则公告》(2013),《中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2016),《关于对赴外国管辖海域开展科学研究进一步加强管理的通知》(2019),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2020)。(5)中国外交部于2019年12月9日发布的《关于对赴外国管辖海域开展科学研究进一步加强管理的通知》内容,参见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5/t1723270.shtml,2019年12月10日访问;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于2020年1月16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内容,参见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1/t20200119_1219275.html,2020年1月19日访问。此外,中国自然资源部、民政部于2020年4月19日发布的《关于公布我国南海部分岛礁和海底地理实体标准名称的公告》内容,参见http://gi.mnr.gov.cn/202004/t20200419_2509115.html,2020年6月24日访问。中国自然资源部于2020年6月23日发布的《关于公布我国东海部分海底地理实体标准名称的公告》内容,参见http://gi.mnr.gov.cn/202006/t20200623_2528802.html,2020年6月24日访问。
其他若干制度和文件,如《中日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四点原则共识》(2014),《中日防卫部门之间的海空联络机制谅解备忘录》(2018)和《中日政府之间的海上合作搜救协定》(2018),以及《中国政府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2014)和《中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2016),等。
在此期间,我国通过修改个别法律、适时公布部分岛屿领土的领海基点和基线声明,以及其他措施,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我国的海洋法制度体系,形成中国海洋法制度治理体系。
二、中国海洋法制度的基本特征及若干问题
(一)基本特征
1、直线基线制度。《中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中宣布的直线基线制度,在《中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得到了确认;并依据直线基线制度宣布了我国大陆领海的部分基线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以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采用直线基线制度的基点和基线。(6)例如,《中国政府关于中国领海基线的声明》(1996年5月15日),《中国关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的声明》(2012年9月10日)。美国于2013年3月7日对我国2012年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划设的直线基线提交了外交照会,认为我国的做法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违反国际法。参见包毅楠:《美国军舰擅闯我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的国际法实证分析》,《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6期,第58页。
2、按照公平(衡平)原则解决海洋划界争端。我国坚持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按照公平(衡平)原则解决海洋划界争端的原则,不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决定》第2条作出了规定,而且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2条第3款得到确认。(7)对于“公平原则”和“衡平原则”的翻译问题,“衡平”相较“公平”而言,除公平、公正之义外,还能表达一种动态因素,即衡量一切因素而取得其公平解决,所以,将英文的“equitable principles”翻译成“衡平原则”是正确的,这也体现了划界原则由“等距离中间线原则”向“衡平原则”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即在海洋划界过程中应考虑一切相关因素,以达成衡平的解决结果。参见傅崐成、崔浩成:《南海U形线的法律性质与历史性权利的内涵》,《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72-73页。这不仅成为我国解决海洋划界争端的重要原则,而且在实践中得到了运用。例如,《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的签署和生效。
3、针对重大海洋权益问题排除司法或仲裁方法。即我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的规定,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书面声明,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第1款(a)、(b)和(c)项所述的任何争端(即涉及海洋划界、领土主权、军事活动等争端),中国政府不接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5部分第2节规定的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程序。(8)《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第2款规定,根据第1款作出声明的缔约国,可随时撤回声明,或同意将该声明所排除的争端提交本公约规定的任何程序。换言之,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关于海洋问题的上述争端不适用司法裁判和仲裁制度,将由相关国家通过协商解决上述争端,即采取政治方法优先协商解决国家之间海洋争端问题的立场。
4、存在多个临时性或政治性质的原则性共识。由于海洋问题尤其是海洋领土主权争议问题,复杂和敏感,并关联历史和国民感情,所以相关国家很难作出实质性的让步,难于最终得到解决。而为维护稳定和正常秩序,缔结临时性的协议或政治性质的共识就成为管控海洋危机的重要方法,这在东海问题上特别明显。[1]
5、存在需要澄清的内容。例如,南海断续线的性质、历史性权利内涵、管辖海域的范围。尽管我国通过不同的方法,如政府声明、白皮书、立场文件等发布了针对海洋问题尤其是南海问题的政策和立场,但对于南海断续线的性质或地位并没有作出清晰的解释,即使在《中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2016年7月12日)中,也没有涉及南海断续线的性质和历史性权利(权原)的内涵。(9)《中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第3条规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包括:第一,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第二,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和毗连区;第三,中国南海诸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第四,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参见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712/c1002-28548370.html,2016年7月12日访问。笔者认为,对于历史性权利(historic rights)和历史性权原(historic title)的关系问题,历史性权利来源于历史性权原,历史性权利是历史性权原的表现形式之一,即如果国家基于历史性证据取得某些既得利益,从而构成历史性权原,则国家拥有取得既得利益的行为或活动的权利。即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如《中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14条的规定一样,依然没有作出权威性的解释。(10)例如,《中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14条规定,本法的规定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历史性权利。可见,我国除依据距离原则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外,还可依历史性权利为基础对不同的海洋地物主张相应的管辖海域。而对于本法中基于历史性权利下的海域地位,存在三种解释。第一,它可能被理解为这一海域不能成为中国的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但应拥有与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相同的法律地位;第二,它可能被理解为体现中国历史性权利的这一海域在200海里界限之外;第三,它可能被理解为体现历史性权利的这一海域虽在200海里界限之内,但可以拥有与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不同的替代的管理制度。参见Zou Keyuan, Historic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 China’s Practice, 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Vol.32, No.2, 2001, pp.149-168.同时,对于在《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和《中国渔业法》第2条规定的中国管辖海域范围及性质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清晰的任务。(11)例如,《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2条第1款规定,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即中国政府应在合适的时机就这些问题的范围及性质做出进一步的阐释。
(二)若干问题
1、西沙群岛的直线基线问题。我国虽然于1996年5月15日公布了在西沙群岛的直线基线,但受到美国的挑战。美国认为这是“过分的海洋权利”主张,包括于1996年6月9日发布了《海洋的界限——中国的直线基线要求》(No.117)报告,以及近年来通过军舰在西沙群岛领海内实施多次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国的法律规范。(12)Se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Ocean Affairs, Limits in the Seas No.117: Straight Baseline Claim: Chin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1996.美国军舰在西沙和南沙海域实施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内容,参见金永明:《南海航行自由与安全的海洋法分析》,中国国际法学会编:《中国国际法年刊(2018)》,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410-438页;金永明:《美国军舰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目的及中国的应对》,《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10-12页。
诚然,各国有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条和第7条的规定,选择适用正常基线和直线基线的权利,但在利用直线基线时受到一些条件性的限制和适用上的限制。(13)沿海国适用直线基线的条件规定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条的第1、3、5-6款;沿海国使用直线基线在适用上的限制规定在第8条第2款。同时,西沙群岛适用直线基线的基点的宣布直接冲击了南海断续线线内水域的地位。即呈现南海断续线内的水域无法成为诸如内水、领海那样的具有历史性水域地位的弊端。
2、军舰在领海内无害通过时的事先许可或事先通知问题。美国主要挑战我国在上述《中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中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决定》中,对外国军舰在领海内的无害通过适用事先许可或事先通知沿海国的做法,认为这些规定违反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坚持军舰在领海内的无害通过无须事先批准或事先通知沿海国的航行自由论的立场和行为。(14)中国针对外国军舰在领海内无害通过的程序性规定内容的差异及观点,参见金永明著:《新时代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研究》,海洋出版社2018年版,第135-137页。此外,对于军舰在领海内的无害通过做出程序性(事先许可或通知)限制的国家有40多个。See J.Ashley Roach and Robert W.Smith, 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Third Edition), Maritimes Nijhoff Publishers, 2012, pp.250-251, pp.258-259.这些国家在国内法上做出军舰在领海内无害通过的限制性规定的法律依据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10条,目的是使该国国内法律和规章同本公约的规定取得协调。
3、毗连区内对安全事项的管辖权问题。美国认为《中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第13条针对毗连区内防止和惩处与安全有关的事项具有管辖权的规定,违反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并主张中国对毗连区内安全事项予以防止和惩处的规定,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规范内容。(15)在国际社会有五个国家(柬埔寨、中国、苏丹、叙利亚和越南)对毗连区内的安全事项主张管辖权。See Raul(Pete)Pedrozo,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ast Asia Focus, The Journal of Island Studies, Vol.7, No.2, March 2018, p.79.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3条毗连区内容承继了1958年《领海与毗连区法》的规定。而在1958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审议毗连区制度的第一委员会提交的案文中,存在“防止侵犯沿海国的安全并予以处罚”的内容,但在全体会议上审议此内容时,因多数国家的反对,在最终案文中删除了与安全有关的内容;与会多数国家反对将安全事项纳入条文的理由是,安全的意思抽象,有把所有的保护法益作扩大解释的可能并存在滥用的风险。[2](P89-92)因此,在《领海与毗连区法》第24条中并未包含对安全有关的事项具有管辖和处罚的内容。
4、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问题的事先同意或许可制/自由使用论问题。在中国的海洋法制度中,并不存在对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如军事测量、谍报侦察活动和联合军事演习)适用事先同意或许可制方面的规定,但在实践中采用了事先同意或许可制的原则,以确保专属经济内的海洋安全利益,所以在中美两国之间呈现了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问题的事先同意或许可制和自由使用论之间的对立问题。
由于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没有关于“军事活动”的定义,所以只能从海洋科学研究和海洋和平利用的视角进行考察。(16)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和海洋科学研究、海洋和平利用之间的关系内容,参见金永明著:《中国海洋法理论研究(增订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31-49页,第259-269页;[日]和仁健太郎:《军事活动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位置——与海洋科学研究的关系》,《阪大法学》第66卷第3-4期(2016年),第613-639页。但遗憾的是,对于海洋科学研究、海洋和平利用的概念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也没有直接的定义,所以,这个问题很难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决,但幸运的是,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或原则性的规定(例如,第59条),为此,中美两国应根据专属经济区的立法宗旨和其特殊的法律地位,结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款(例如,第58条和第59条)进行具体分析和协调,并结合国际社会现存的制度和达成的共识予以处理。[1]在未达成共识前,美国军舰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包括海洋科学研究活动,仍应遵守《中国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规定》(1996)所规定的事先批准制并遵守中国的有关法律和规章。(17)例如,《中国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规定》第4条。对于《中国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规定》的分析内容,参见徐贺云:《我国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实践和对法规修订的思考》,《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4期,第50-60页。
5、南海岛礁海洋地物的地位和性质问题。即针对中国在南海尤其在南沙岛礁进行建设和部署的挑战。美国认为中国在占据的南沙岛礁建设损害了周边海洋环境,尤其是中国在陆域吹填工程结束后在南沙岛礁上的建设工程存在军事化的趋势,严重威胁其他国家的安全尤其是航行自由和安全。同时,美国认为,中国无法依据自己占据的南沙岛礁主张更多的管辖海域,因为在南沙岛礁地位的认定上存在不同而对立的主张。此外,美国国务院不仅于2014年12月5日发布了《海洋的界限——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No.143)报告,并认为中国应更加清晰地界定中国南海断续线的性质及线内水域的法律地位。(18)See Bureau of Ocea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Scientific Affair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Limits in the Seas, China: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ecember 5, 2014.对美国国务院《海洋的界限》报告的批驳内容,参见贾兵兵:《驳美国国务院〈海洋疆界〉第143期有关南海历史性权利论述的谬误》,《法学评论》2016年第4期,第76-82页;关于中国南海断续线的内容,参见高之国、贾兵兵著:《论南海九段线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第1-49页。Also see Zou Keyuan and Liu Xinchang,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U-shaped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Its Legal Implication for Sovereignty, Sovereign Rights and Maritime Jurisdiction,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4, No.1, March 2015, pp.57-77.
6、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拘束力问题。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认为,中国应遵守南海仲裁庭作出的“南海仲裁案最终裁决”(2016年7月12日)内容,认为该裁决对中国具有拘束力,中国必须遵守。(19)对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全面性的批驳内容,参见中国国际法学会著:《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395页。
诚然,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6条及其附件七《仲裁》第11条,仲裁庭作出的裁决对相关方具有拘束力。(20)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仲裁》)第11条规定,除争端各方事前议定某种上诉程序外,裁决应有确定性,不得上诉,争端各方均应遵守裁决。南海仲裁案的问题是,仲裁庭是否对菲方提起的仲裁事项具有管辖权,即其是否是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在广义上是否属于中方排除的仲裁事项?菲方提起强制仲裁的前提条件是否满足?即可受理性问题,以及仲裁庭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是否存在不足和缺陷等方面需要进行评估。(21)中国政府针对南海仲裁案的管辖权内容,参见《中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http://www.gov.cn/xinwen/2014-12/07/content_2787671.htm,2014年12月8日访问。针对南海仲裁案最终裁决的批判性内容,参见中国国际法学会著:《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446页。对于南海仲裁案的内容,也可参见Jin Yongming, The Challenges of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to the Law of the Sea(1)-(2), The Waseda Law Review, Vol.94, No.1(December 2018), pp.355-375 and Vol.94, No.2(March 2019), pp.261-270.[日]田中嘉文:《对南海仲裁案最终裁决的考察——以历史性权利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3款的解释为中心》,《国际法外交杂志》第117卷第2期(2018年8月),第1-29页。针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包括南海仲裁案内容分析,参见贾兵兵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研究:附件七仲裁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8-170页。
三、中国海洋政策及完善海洋法制度的思考
中国海洋法制度的成形和发展,受到一些主要海洋政策和理念的影响,所以,有必要论述相关的海洋政策和理念/倡议。这有利于理解我国的海洋法制度体系和解决海洋问题争议的立场。
(一)中国的海洋政策与倡议
1、“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1984)。对于南海尤其是南沙群岛领土争议问题,邓小平先生于1984年明确提出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方针。(22)一般认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源于邓小平副总理于1978年10月25日在日本记者俱乐部的回答内容。即邓小平副总理指出,“这个问题(钓鱼岛问题)暂时搁置,放它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足,这个问题一谈,不会有结果;下一代一定比我们更聪明,相信其时一定能找到双方均能接受的好方法。”日本记者俱乐部编:《面向未来友好关系》(1978年10月25日),第7页;Also see http://www.jnpc.or.jp/files/opdf/117.pdf,2014年8月12日访问。经过各方努力,我国与东盟国家之间依据该方针取得了一些业绩。(23)例如,对于南海区域中的南海问题,在双边层面上的业绩,主要包括《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中越两国《关于指导解决中国和越南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2011年10月11日),《中越联合声明》(2011年10月15日),《中菲政府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8年11月27日)。在区域层面上的业绩,主要包括中国与菲律宾和越南签署的《在南中国海协议区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2005年3月14日),依据《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国家于2011年7月20日就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指导方针达成一致共识,以及《中国和东盟国家外交部长关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联合声明》(2016年7月25日)。同时,尽管“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具有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但其在南海的适用并未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发展。(24)海上共同开发的理论和实践内容,参见杨泽伟主编:《海上共同开发国际法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306页。其理由主要为:首先,东盟一些国家既难以接受“主权属我”的前提,缺乏实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治意愿,难以启动;其次,无现实利益需要,因为东盟一些国家已大力开发了南海的资源;最后,南海尤其是南沙争议涉及多方,特别是争议海域范围难以达成共识,存在实际操作上的困难,所以,“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在南沙的实施依然存在困境。为此,中国和东盟国家找到并扩大共同利益范围的海洋低敏感领域的合作,是可以努力的方向。[3](P77-79)
2、和谐海洋理念(2009)。我国在200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60周年之际,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海洋形势发展需要,提出了构建“和谐海洋”的倡议或理念,以共同维护海洋持久和平与安全。构建“和谐海洋”理念的提出,也是我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理念以来在海洋领域上的细化和目标具体化,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海洋问题的新认识、新要求,标志着我国对国际海洋法发展的新贡献。(25)我国提出的“和谐海洋”理念内容为:坚持联合国主导,建立公正合理的海洋;坚持平等协商,建设自由有序的海洋;坚持标本兼治,建设和平安宁的海洋;坚持交流合作,建设和谐共处的海洋;坚持敬海爱海,建设天人合一的海洋。参见金永明著:《中国海洋法理论研究(增订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305-306页。
3、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2012)。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自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完整提出以来,经过发展和成形以及深化的过程,已形成新时代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治理体系。其核心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在政治和安全上的目标是不称霸及和平发展;在经济上的目标是发展和壮大海洋经济,具体路径是运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坚持陆海统筹加强区域协调合作;在文化上的目标是构建开放包容互鉴的海洋文化;在生态上的目标是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生态环境。新时代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终极目标和愿景是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4]
4、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推进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路径。“一带一路”倡议获得国际社会的好评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得益于其符合时代发展需要,契合各国发展愿望,在性质和功能上其是一种新型国际和区域合作模式与路径。
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取得如此好的效果,离不开中国政府及时通过发布政策性文件(例如,2015年3月28日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7年5月10日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和中国的贡献》,2017年6月20日发布的《“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以及2019年4月22日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和展望》),以阐释“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和本质及特征以及目标愿景,并通过设立多个重要平台(例如,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进口博览会)和保障性基础制度(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促进了“一带一路”建设进程。此外,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途径中,离不开南海区域,即无法回避南海问题,所以,合理地处理南海问题是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基础。(26)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之本质和南海区域合作内容,参见Jin Yongming, The Essenc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Hiroshima Law Journal, Vol.43, No.2, October 2019, pp.41-70。
5、海洋命运共同体(2019)。2019年4月23日,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青岛集体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从海洋的本质及其地位和作用、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目标、中国参与海洋治理的作用和海军的贡献,以及国家间处理海洋争议的原则等视角,指出了合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7)参见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4/23/c_1124404136.htm,2019年4月23日访问。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一样,需要分阶段、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实施。这是由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属性或法律属性决定的。
不可否认,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推进和实施的主体是人类。这里的“人类”是指全人类,既包括今世的人类,也包括后世的人类,体现了海洋是公共产品、国际利益空间(国际公域)及人类共同继承财产、遵循代际公平原则的本质性要求。而代表人类行动的主体为国家、国际组织及其他重要非政府组织,其中国家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及绝对的主体,起主导及核心作用。这是由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地位或核心地位决定的。
在客体上,海洋命运共同体规范的是海洋的整体,既包括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空间和资源的一切活动或行为,也包括对赋存在海洋中的一切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养护,体现了有效合理使用海洋空间和资源的整体性要求,这是由海洋的本质属性(如公益性、关联性、专业性、流动性、承载力、净化力等)所决定的,也体现了对海洋的规范性和整体性要求,以实现可持续利用和发展目标。(28)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前言”中指出,本公约缔约各国应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以便利国际交通和促进海洋的和平用途,海洋资源的公平而有效的利用,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以及研究、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为此,笔者认为,海洋命运共同体可分为三大类。第一,按海洋区域或空间范围分类,例如,地中海、南海、东海命运共同体;第二,按海洋功能分类,例如,海洋生物资源共同体、海洋环境保护共同体、海洋科学研究共同体,以及海洋技术装备共同体;第三,按海洋领域分类,例如,海洋政治、海洋经济、海洋文化、海洋生态、海洋安全共同体。
在运作方式上,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及其他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采取多维多向合作的方式予以推进,以实现共同管理、共同发展、共同获益、共同进步的目标,体现共同体原理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取向。
(二)中国完善海洋法制度的若干建议
1、军舰在领海内的无害通过程序上的内容修改。如上所述,对于外国军舰在中国领海内的无害通过在国内法中存在不同的规定,例如,《中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第6条针对外国军舰在我国领海内的无害通过规范的是事先许可或事先批准,此内容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决定》的声明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其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领海内无害通过的规定,不妨碍沿海国按其法律规章要求外国军舰通过领海事先得到该国许可或通知该国的权利。
从制定和解释法律(“决定”)的主体看,它们具有同样的地位,因为它们均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和决定的;从法律本身的位阶看,“法律”高于“决定”;从制定或通过的时间看,对于同样的事项,是否应遵守“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那么这就面临需要修改“先法”规定的内容,以协调和统一针对同一事项的具体规范。[3](P136)此外,我国是否需要继续实施事先许可制或事先通知制,也到了须予以讨论和研究的时机了。因为采用此方法的国家毕竟不多,并对我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进程也带来阻碍作用。为此,如何运用构建包容互鉴的海洋文化目标指导海洋法制度的完善,使海洋发挥自由和开放的本质性作用就特别重要。
2、制定海洋基本法的核心是明确海洋机构职权。海洋基本法的制定不仅可以克服和弥补“海洋”用语入宪的难度,而且可以明确地规范海洋机构的职权,以统领海洋事务工作,发挥主导作用。(29)对于中国周边国家存在的诸如“海洋基本法”的内容及启示,参见董跃:《我国周边国家“海洋基本法”的功能分析:比较与启示》,《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4期,第39-49页。
众所周知,我国在进入新时代(2012—)以来,对海洋管理机构作了两次大的机构改革(2013年,重组国家海洋局,设立中国海警局和国家海洋委员会;2018年撤销国家海洋局,其职责由其他部门如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和农业农村部等承担,中国海警局转隶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但国家海洋委员会的具体职责和单位组成、运作方式等内容和程序,迄今没有公开,所以可以在制定海洋基本法时予以明确规定,确保其透明性、正常运作并发挥统筹协调作用。(30)《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指出,为加强海洋事务的统筹规划和综合协调,设立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国家海洋委员会,负责研究制定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统筹协调海洋重大事项;国家海洋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国家海洋局承担。参见http://www.gov/20131h/content_2354443.htm,2013年3月15日访问。
3、制定中国海警局组织法以明确执法职权。在2018年的海洋管理机构改革中,2013年组建的中国海警局已由接受公安部业务指导转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指挥,组建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海警总队,称中国海警局。尽管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2018年6月22日通过的《关于中国海警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定》(2018年7月1日起施行),赋予了中国海警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的范围或任务以及在执行任务时与其他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的内容,从而使中国海警局在隶属中央军委领导和其他行政机关执法之间的职权上得到了协调。[4]但中国海警局与其他行政机关的执法协作机制需要在今后的法律规章中予以规范,包括修改现存有关海洋领域的法律规章,而更重要的是,为行使中国海警局在海洋维权执法中的职权应尽快制定中国海警局组织法,以明确其任务、具体职权,以及适用措施上的程序性规定等内容,包括中国海警局在维权执法过程中未能履行或不可能单独完成其海上维权职责,转为由体制内的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和部署行动时,在何种情形下,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何种程序,启动何种程度的应对措施等内容,需要在今后的相关法规中予以确定。
4、海洋争议解决方法利用再思考。中国在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等重大问题上,一贯坚持由直接有关国家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取得了一定的业绩。主要为:中国同12个陆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处理同邻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以建设性姿态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尽最大努力维护南海、东海及周边和平稳定;[5](P8)中国和越南通过谈判协商划定了两国在北部湾的海上界线和缔结了渔业协定(即《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2014年6月30日生效),维护了北部湾的海上安全,并在渔业合作上取得了双赢的效果。
从我国针对海洋问题的政策和解决海洋争议问题的进程看,我国解决海洋争议问题的路径为以下三个步骤。首先,利用协商谈判的方法,包括“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其次,当利用这些方法无法解决问题时,则通过制定规则、管控危机,达成共识的方法处理争议问题,这样做的目的是实现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目标;最后,通过各方面的海洋领域合作,提升互信,为最终解决海洋争议问题创造基础和条件,实现和谐海洋、海洋命运共同体之目标。
但当运用政治方法确实无法解决或预测不可能最终解决海洋争议问题时,我国面临是否应由政治方法向法律方法(司法或仲裁)转换的困境,即我国面临利用法律方法解决海洋争议问题的政策调整的利弊分析和研究的任务及挑战,以更好地为实现“依法治海”目标做出贡献。
四、结束语
如上所述,我国依据习惯海洋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了国内海洋法制度,并经过长期努力形成了中国海洋法制度体系及其治理体系,但其中的一些内容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所以中国面临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困境。
事实上,中国在海洋法制度体系上的挑战内容,多是国际社会无法达成共识的争议性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如果国际社会无法继续达成共识,则这些对立性问题将依然存在,包括美国在世界各地进行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结果也不能改变其他国家的法律立场,所以,为实现和谐海洋理念、海洋命运共同体目标,“依法治海”是重要的基础和保障。所谓“依法治海”,就是以规则主张权利,以规则维护和使用权利,以规则解决权利争议,维护海洋秩序,实现“依法治海”目标。
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规则”是指国际社会共同参与达成的统一性规则。如果对这些“规则”的内容存在异议或不同的解释,则在他方反对的情况下,就不能运用此“规则”处理海洋争议问题,相反,相关方需要就此“规则”的差异性进行磋商,以补充和完善这些“规则”内涵。
此外,中国应根据国际形势和自身实际地位,对他国反对的国内海洋法制度内容进行重新检视,包括补充和澄清模糊性内容、术语,调整国际社会少数国家的实践性做法,以自觉、自发和大局的角度以及引领海洋秩序的意念进一步完善中国海洋法制度体系,为增进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规则,为实现中国提出的合理海洋倡议和愿景目标做出中国的持续贡献。(31)中国在维护海洋秩序、构筑海洋新规则上的角色转换和定位内容,参见金永明:《现代海洋法体系与中国的实践》,《国际法研究》2018年第6期,第45页;金永明:《新时代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治理体系论纲》,《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29-30页。这是对负责任大国的要求,也是具有多重身份的中国的应有价值取向,更是中国适应海洋特质所须努力的目标。总之,这是多赢合作时代的合理要求和必然产物。(32)金永明:《新时期东海海空安全机制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8-9页。例如,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0年6月20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2020年6月21日起施行)第9条规定,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由内卫部队、机动部队、海警部队和院校、研究机构等组成;第47条规定,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执行海上维权执法任务,由法律另行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