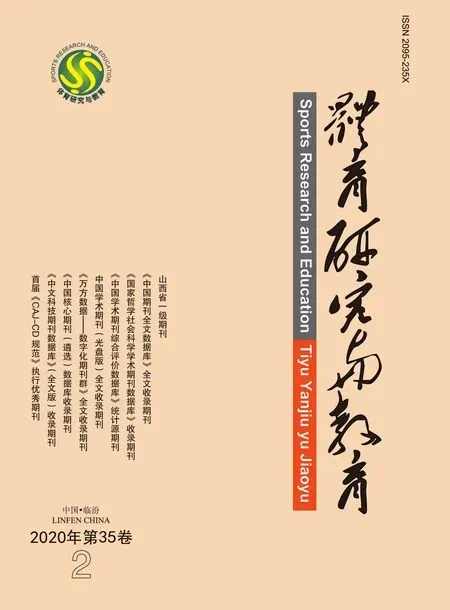民俗体育的发生学分析
——以黄山市为例
郑代义
采用发生学的方法对体育存在进行分析,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发生学的分析方法,最早是现象学的一个分支,强调现象或者具体存在的生成、演化,是从过程的视角展开的考察。发生学概念在历史进程中,其内涵不断变化,正如其概念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存在方式,它本身不会自我演化,但从根本上讲是人的介入才导致概念的迁变。如此一来,发生学就是关于人的历时性的解读。
体育是关于人的体育,其首要条件就是人的存在。具体的体育活动在文献中、在语言交流中,总是以概念的形式呈现。通常情况下,提及一个体育概念,我们面前首先呈现的是一个身体活动的画面,然后具体的场景中呈现出来就是当场景发生了变迁。人的活动也随之变迁,这就是体育本身的历时性,也是发生学考察的范围所在。
民俗体育可以看作是民俗和体育两种文化的亚种。作为古徽州的所在地,黄山市是徽州文化的核心区域。如果从地域的视角来看徽州文化,它包含的范围更广阔,大致在今天的浙西皖南和赣东的区域,且其文化特点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民俗是其文化特征的重要表现。民俗体育作为民俗文化的一个亚类,其形成受限于地理、人文等因素。任何一个民俗体育概念的形成,都是一系列事件的累积,同时也是人这一概念不断发生发展的结果。
从发生学的视角展开对徽州民俗体育的研究,对今天的徽文化的传承和黄山市的体育发展具有双重的考察意义。
1 民俗体育概念及发生
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民俗体育这一判断,包涵了民俗体育的概念,将场景放置在徽州这一文化范畴内,那么民俗体育的形成就有了历史性特征。
民俗体育顾名思义,即是民俗也是体育,既具有民俗的特点又有体育的特征。在体育的分类中,民俗体育可以看作是传统体育的一部分。如果把传统体育的概念狭义化,民俗体育相对传统体育这一大类概念而言,传播的区域范围更小,其形态更加原始,而且具体地域内的民俗体育的稳定性更强。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体育比传统体育更远离现代体育的概念。
中国历史上,传统体育项目的推广有城市和国家行为的因素嵌入其中。城市独有的集中式的休闲娱乐催生了许多民间体育项目。这些体育项目经过长时间的固定,就形成了传统体育项目。古代大型城市都有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活动,文献所呈现的传统体育项目大多与城市有关,所以真正的乡村里的传统体育项目很少。北宋时期汴梁城中各种体育类的结社活动,其载体就是传统体育项目,如蹴鞠、射箭、武术、杂技等项目,其范围之广、组织程度之高,就是在今天也让人叹为观止;另外,传统职业的发展,尤其与身体活动相关的职业,也催生出各种各样的传统体育项目,最典型的就是古代军队的训练。在训练项目上,负重跑步、射箭、举重等军事项目,还有例如蹴鞠、摔跤、相扑等军队内部的娱乐活动,都有沿承。这些都是促进传统体育得以形成的关键因素[1]。
民俗体育有很强的地域性。我们不否认流传度较广的传统体育项目往往在具体地域内流行,但是离开了城市或者大城市,在具体的乡间,大部分传统体育项目就发生了变种,仅仅是大致相同,同时在规则层面也会有不同。如陀螺运动,在全国各地都有开展,通过梳理就会发现,基本上不同区域内,对陀螺比赛的规则是不同的。
民俗体育在更多的情况下扎根乡土,与乡民的生活相结合。它不像大型城市中体育项目那样普及,开展的频次也不高,甚至在项目的表现上,也呈现出规则更加简单,向雏形化发展的倾向。这就使得古代民俗体育在种类上,比城市里的传统体育,在项目的设置上更加多样化,而在形态上,却更加简单。所以二者之间既有交集,更多的却是差异。
另外,体育作为舶来词,也是舶来品,目前流行度较广、形式规则均较完善的体育项目绝大部分来自国外,尤其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篮球、排球等。它们多强调规则的统一,强调绝对的判断标准等,在价值观上,也与西方文化取得了统一。在某种意义上,民俗体育概念的提出,也有用体育的形式来套用民俗的嫌疑。当然从宽泛的视角来看,民俗活动中,确实蕴涵了丰富的体育因素。尽管民俗体育项目规则更加简单,但是都以身体活动能力的提升为目的,与现代体育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融合。
2 民俗体育的发生机制
对民俗体育概念的进一步考察,可以放在其发生机制上。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将体育看作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可发现其形成有自然自发的特征。其最主要的来源就是人类的交流活动。交流活动将体育项目形式固定下来,更加便于流传或推广。广义地看,凡有集会,就会有体育活动发生,二者有极高的相关性,而对徽州所属各地方志的梳理,也会发现这种现象。大多数可以称之为体育的活动,基本上就是在各种集会和仪式中展示出来。
在传统社会里面,集会的发生无非是典礼、节日与集市等三种形式。它们大致可以看作是古人社会交往的主要场合性因素,这也说明了体育的发生,场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集会为民俗体育的传播提供了交流的舞台,同时交流也促进了民俗体育在形式和规则方面的成熟。例如,徽州民间有跳钟馗的传统,也算是巫术的一种。在一些丧事和祭祀场合,会大规模出现。尽管有许多故弄玄虚的行为,但是其动作的训练,有许多身体练习的因素;节日的庆典有记载的很多,游行就是一种,尤其以地域为特征的游行活动,可以作为载体,掺杂许多运动项目。
作为传统体育的亚类,民俗体育的发生,同样有依托于其他职业,成为其他职业形式的一种衍生品的特征。例如,徽州有名的戏班文化中,各种舞戏、打戏的练习,催生了基于曲艺的舞蹈类民俗体育形式;徽州自古有外出经商的传统,商帮出于安全考量,配置武装力量所带来的尚武文化,使得古徽州也是传统武术的重镇,各类拳术在这里融合,使得徽州的武术品类既多又杂[2]。因此,与身体活动相关的职业,基本上都会催生出相关的相对成熟的身体练习方法、考校方法和比试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活动也已经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体育形态。
另外,传统文化具有实用性倾向。古徽州自明清时期,文化氛围浓,社会富裕,在子女教育方面颇为投入。基于身体练习的教育活动门类繁杂,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教育类民俗体育内容。据统计,可以梳理出来的古徽州在各个年龄段的教育中的民俗体育项目大致可以有七大门类一千多种,基本上涵盖了现代体育的主要大类,比如投掷类、竞速类、平衡类等等。流传比较广泛的也有三十多种,大部分都是小范围内因地制宜开发出来的游戏,大致具有了体育的基本形态,可见传统社会在体育资源的开发上,并不像之前我们认为的那样贫乏,而是恰恰相反,这同时也说明了体育项目的发生是基于人的本性需求,而不是单纯地囿于社会因素。
当然,古徽州作为传统文化的重镇,中国古代文化对徽州民俗体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如传统的中和思想,使得修身这一要素占据了重要的比例,在民俗体育中也掺入了礼节和自然教育等。这也说明,传统体育很难像现代体育一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体育的核心特征,更多的是依托于各种文化认知,如徽州的传统武术,其修身养性的要求,往往被排在第一位。
3 古徽州民俗体育的形式特征
从形式方面看,古徽州的民俗体育,类似体育游戏,而非正式的体育项目。其承担的任务也不尽相同。在现代体育中,竞技是一个核心的标准之一,而民俗体育项目,大多竞技性不足。在礼制的约束下,民俗体育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气氛上的和谐互动,以及个体在完善自我方面的表现。如荡秋千与社火表演,即使有比赛,也很少追求一种绝对的标准,更多是表演,而在同时期的城市体育中,荡秋千却有着明确的胜负判定。
但是也应该看到,恰恰因此,民俗体育才具有较强的地域性特征。与现代体育在规则方面的成熟相比较,民俗体育具有很强的随意性。这不仅表现在古徽州民俗体育中,其他地域同样如此。即使是同一项目,在不同的乡间,尽管使用的器械和过程大致相同,但是其规则也不尽相同,甚至在同一乡间同一场所,不同时刻,也会发生规则的迁移。典型的如舞龙灯,在不同的乡间,龙灯的扎制规格不同,评比的依据也不同,以致于古徽州乡间每年都会为龙灯游行专程协商规则。这是民俗体育的又一个特征。
当然,这种情况更多出现在集会的场景下。通常而言,越封闭的环境,规则越稳定,流变的程度越低。一个村子的体育项目可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规则不发生变易,而只要两个村子一起,就有对规则进行统一的必要了。这样一来,民俗体育项目的流变就会发生。这也是传统的民俗体育的一个重要特征[3]。
民俗体育的大部分项目,不会有现代体育那样系统的身体练习要求,不强调动作要符合身体结构,甚至很多有反身体结构的表现。在竞技因素上,竞速、竞力项目很少,而更多的是竞准,更强调节奏与协调性,强调参与者的表现力,类似于舞蹈。即使有对抗,也是点到为止,很少有面对面的伤害事件呈现。
4 正在发生的民俗体育
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民俗体育一直处于不断的流变过程中。运动项目在不断地消亡,也在不断地被创造,规则也是随着地域的改变而改变。换言之,民俗体育总是伴随着具体群体的存在而存在。这就造成了民俗体育不可能像现代体育那样具有稳定的形式。恰好是这种不稳定性,也可以看作是体育创编的随意性,赋予了民俗体育以强大的生命力。
这个现象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体育是人的本能需求,不是被给予的存在形态。而人对体育的需求,不仅仅有身体发展方面的需求,也有社会化方面的需求。只要有人就有体育。民俗体育在流变性方面体现了体育的一个重要的原始形态。
另外,民俗体育的流变性特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它的依附性特性。民俗体育与居民所居住的环境、从事的职业息息相关[4]。现代体育项目因为标准化的运动器械与固定的项目规则,可以无限制地在各地复制传播,得到大范围的推广,民俗体育则不能这样。离开了确定的地域,它的规则就会变形;离开了依附的职业,它可能就会消亡。
因此,民俗体育,可以称之为正在发生的体育形态,换言之,即正在发生的民俗体育。考察民俗体育,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即运动项目的流变、与人自始至终的参与性。如此,民俗体育的意义,就超越了历史。直面活生生的人,直面我们现实的生活。我们在看待民俗体育的时候,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记忆的视角,而是当下的,直接的参与性的活动。
5 创新民俗体育文化
黄山市对民俗体育的保护开发,是在大旅游观中的传统民俗文化的框架下展开的。大力挖掘历史上的民俗体育项目,使其在博物馆中留存,在黄山市的旅游事业中留存,这对历史的印记是一种很好的维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民俗体育的流变性,可以真实地反映黄山文化在历史中的发展,也就是反映不同历史阶段下,居住在黄山市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活,以及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文化。民俗体育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注重人的历时性体验。如果将人生看作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不应该是冷冰冰的概念化存在,而是活生生的实在参与。在参与的过程中体验历史、体验文化,在这种互动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黄山市作为重要的旅游城市,在旅游资源的开拓上,就目前而言,已经接近极致。不再仅仅依靠黄山这个风景资源,徽文化资源正在被大力开发出来,但是表现形式,要么是一种标记性的符号记忆,要么是观看形式的礼仪表演。对于深入到徽州文化的内涵,缺少了参与度的提升。
历史在活动中,活动是参与者的活动,民俗体育无疑具有这样的特征。它的流变性,它的参与度,能够更好地呈现徽文化在不同阶段,人的生活生存状况,以及文化的内涵性表现。所以,黄山市在徽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的开发中,应该在民俗体育方面大做文章,例如与古徽州职业相关的曲艺体育、与集会相关的村社体育、与教育相关的育儿游戏、与徽商相关的武术表演,等等,都是急需开发的资源。如何还原,如何展示,如何吸引游客参与,都是当前黄山市民俗体育的研究重点[5]。
上述是从古徽州文化的留存与旅游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说明民俗体育的发展要求,这本质上是一种狭隘的看法。民俗体育对人的意义不仅限于此。目前,徽州人的生活方式相对于古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民俗体育在乡间的留存,其实少之又少,我们只能从文献记载中还原。从诠释学的视角来看,是现代人眼中的古代民俗体育,毕竟古代的生活环境和规则,我们无法百分之百复制。
从正在发生的民俗体育的视角来看,黄山地区人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相对应的现代的民俗体育也在形成。就目前来看,因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黄山地区的体育形式,还是以国际流行的体育项目为主。现代体育项目与传统体育之间截然不同的就是内容与规则的标准化统一,如篮球项目无论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是执行同一套裁判规则;同时,现代体育并不依附于具体的职业,它本身自成职业。所以,一定意义上,现代体育的开展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传统意义上的民俗体育,传统的民俗体育被挤进了博物馆[6]。
那么黄山地区现在是否有当下的正在发生的民俗体育呢?答案是肯定的。其实在现代体育中,并不能找到徽州文化的痕迹。只有与生活融为一体的民俗体育才是徽州文化的最好呈现。也就是说,关注生活中的体育形式,能够固定下来的就是民俗体育。逐渐筛选出新的适合徽州人生活方式的体育形式。加以引用开发,也会成为新的民俗体育形式,当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种基于文化的大体育观。民俗体育从来未曾消亡,也不会消亡,而目前的任务就是如何使之成为印记,成为文化记忆。同理,徽州的发展,不在于对其他城市的复制,而是,在历史进程中,实现对地方文化的重塑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