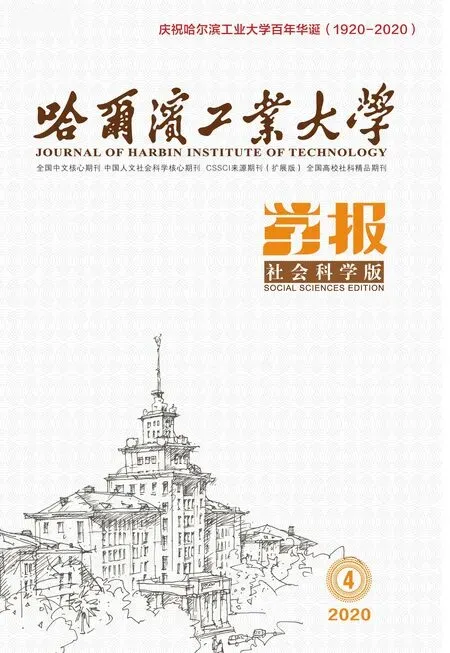汉末魏晋疾疫发生与文学思想转型
王洪军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哈尔滨150080)
东汉中叶以降,频繁发生大规模疾疫,张角以治病为由创建太平道,汉灵帝中平元年在青、徐等八州发动起义,东汉进入了末世的灾祸、战争阶段。疾疫、水旱灾害、战争导致汉末人口大量缩减,每个人都面临死亡的威胁,整个社会笼罩着愁苦悲凉的气息,对于文人的心态、观念、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古诗十九首》表现出来的痛苦、哀怨以及挣扎,就是时代特征的反映。考察汉末魏晋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的转型,在不忽视朝代更迭所造成的士人政治适应、思想转换、人格裂变等大的影响前提下,我们选择了疾疫作为研究重大文学现象发生的切入点,以此分析生命离析之际士人的精神感悟、文学表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学思想的转化。不可否认,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在文学发展史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疾疫的影响是有限的。我们必须明确,中国的传统文学以及文化不是由于疾疫影响才开始发展变化的。然而,在某些历史段限内,疾疫所引发的生命思考是深入的,其文学表现也是让人刻骨铭心的。汉末魏晋的文学深深蕴含着文人峻刻的人生体验、凄切的生命感悟,而深沉凝重的思想情感表达,脱不去时代苦难背景的影响,这苦难就包括疾疫所引发的疾病乃至死亡,以致来自内心深处的恐惧和幻灭,从而引发多元的思考,催生了时代的命题。
一、汉末魏晋疾疫的发生及其传播
纵观中国历史,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汉末魏晋这样频繁和剧烈地发生疫灾,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孙关龙系统地研究了从殷商到清代三千年的疾疫发生状况,以翔实的数据告诉我们,疫情的“第一个活跃期为公元2—3世纪,两个世纪的大疫记录分别为1018条,比以前增加好几倍,在中国历史上每100年大疫发生次数第一次进入到两位数,而且以后的1000多年中,即直到16世纪以前一直没有超过这个记录。另外,这个活跃期的峰值是在公元200—279年,即公元3世纪”[1]。公元2—3世纪恰恰是东汉中叶至西晋中叶,也是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剧烈的发轫期。具有以天下为己任情怀的知识分子主动或是被裹挟着参与到历史变革的进程中来,在时代的潮流中激荡,或者豪情满怀,或者林薮丛聚,然而那个时代的一个副产品——疾疫,却增加了生命的变量,使一切陷入不可知当中,生命之歌从而变调。疾疫影响是普泛化的,无论身份高贵与微贱,也不管居住城郭还是山林,疾疫一旦流行起来,在医疗条件有限的中国古代社会,其爆发力、破坏力是巨大的。史载,汉代桓、灵帝之后,疾疫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趋势。
《后汉书·孝桓帝纪》载:元嘉元年(151)正月,京师疾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延熹四年(161)正月,大疫。延熹九年(166)正月,诏书曰:“比岁不登,民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盗贼征发,南州尤甚。”[2]317又《后汉书·皇甫规传》记,延熹五年(162),皇甫规率领大军征讨陇右,道路阻隔,军中发生大疫,士兵死者十之三四。汉桓帝十五岁即皇帝位,三十六岁病故。在位二十一年里,发生五次疫情。延熹年号共十年,期间发生了三次瘟疫,这已经是相当频繁了,然而无人料到,这是汉末瘟疫大流行的发端。桓帝驾崩后,十二岁的汉灵帝即位,三十四岁薨逝,在位二十二年里,发生疾疫的次数相较于汉桓帝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汉书·孝灵帝纪》载:建宁四年(171)三月,熹平二年(173)正月,光和二年(179)春,光和五年(182)二月,中平二年(185)正月,都发生了相当规模的疫情,即被称为“大疫”。在天人感应学说极度流行的汉代,如此频繁发生大规模的疫病,并不认为是天灾,而是政治问题,其成为诱发汉末政治动荡的因素之一。
光和元年(178)二月发生日蚀,卢植上疏直陈八事,第三事为“御疠”,曰:“御疠者,宋后家属,并以无辜委骸横尸,不得收葬,疫疠之来,皆由于此。”[2]2117宋后即汉灵帝宋皇后,无宠而居高位,被后宫妃嫔及宦官谮毁,捐弃暴室以忧致死,父及兄弟并被诛戮。尸骸无人收葬,导致疾疫发生。这是卢植的观点。很明显这一年又发生了疾疫。汉灵帝时,见诸记载的疾疫已经达到六次之多,平均三年多就要发生一次大的疾疫。以治疗疫病为由而建立的太平道,也是抓住了朝廷忙于“党锢”的契机而发展壮大起来。
汉桓、灵帝时期,疾疫大规模爆发,巨鹿人张角与其弟张梁、张宝趁机自称天医,能够治疗疾病。被治愈者转相炫耀,信众趋之若鹜,从而创建太平道。十余年间,聚集了数十万信徒。中平元年(184)正月,首领张角等聚集三十六万人,同日攻击东汉地方政府以及军队。自此之后,东汉末叶兵连不息,最终导致地分三国,政出三家。黄巾军起兵之后,中常侍吕强对汉灵帝说曰:“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2]2189经过延熹八年(165)桓帝的第一次禁锢、建宁二年(169)灵帝第二次禁锢的“党人”,在黄巾军兵锋所指的高压下,被彻底大赦,重新获得了自由。黄巾军反抗的直接受益者,显然是以忠直著称的东汉末叶的政治清流——具有家国情怀耿介刚直的士大夫。也可以说,“党人”受益于因疾病流行而发展起来道教徒众的起义。
焦培民等人的相关研究认为:“公元151年以后,每隔几年就出现一个疫灾年份,直到公元185年,34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有11个年份发生疫灾,疫灾年份间最长间隔仅6年;公元208—220年,计12年的时间里有5个年份出现疫情,公元 208、215、217、219、220 年是疫发年份。”[3]而公元208—220年间,基本上是汉献帝建安年间,尤其是以赤壁之战的大疫为人所熟知。建安十三年(208)六月,曹操自为丞相,十月曹操伐东吴孙权。十二月,曹操与孙刘联军战于赤壁,军中暴发疾疫,死者大半,不敌孙刘联军进攻,大败而去。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证实了这一点:“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船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4]589赤壁之战后,孙权率众攻合肥,疫病已经流传至此。《蒋济传》曰:“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5]450曹操号称八十万大军,兵锋所指,志在必得。孙刘联军仅有六七万兵马,却能以少胜多,疾疫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争的结果。
《五行志》载:“建安二十二年,大疫。”[2]3351在许昌的陈琳、应玚、刘桢染疫而亡。这一年,在南方攻打孙权的军队也发生了疾疫,丞相主簿司马朗病死军中。四十八岁的徐幹在“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厉疾大命殒颓”[6]。《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建安二十四年(219),大疫。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崩于洛阳。《贾逵传》注引《魏略》曰:“时太子在邺,鄢陵侯未到,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疠,于是军中骚动。”[5]481连续四年持续发生疫情,和军队连年征战是有关系的。曹操也可能感染疾疫,才骤然离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末持续不断发生的疾疫,导致了太平道的兴起、教徒起事,出现了赤壁之战的以弱胜强,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切实地影响了历史进程。
魏蜀吴三国的建立,疾疫并没有消失,依然在持续不断地发生。据《宋书·五行志》[7]载:
魏文帝黄初四年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数。魏明帝青龙二年四月,大疫。青龙三年正月,京都大疫。吴孙权赤乌五年,大疫。吴孙亮建兴二年四月,诸葛恪围新城。大疫,死者太半。吴孙晧凤皇二年,疫。晋武帝太始十年,大疫。吴土亦同。晋武帝咸宁元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万人。晋武帝太康三年春,疫。晋惠帝元康二年十一月,大疫。元康七年五月,秦、雍二州疾疫。晋孝怀帝永嘉四年五月,秦、雍州饥疫至秋。永嘉六年,大疫。晋元帝永昌元年十一月,大疫,死者十二三。河朔亦同。晋成帝咸和五年五月,大饥且疫。晋穆帝永和九年五月,大疫。晋海西太和四年冬,大疫。晋孝武帝太元五年五月,自冬大疫,至于此夏。多绝户者。晋安帝义熙元年十月,大疫,发赤班乃愈。义熙七年春,大疫。
从以上的文献记载来看,魏文帝黄初四年(223)三月、魏明帝青龙三年(235)正月,洛阳发生了疾疫,死亡人数以万记。而孙权的吴国处于南方,夏月暑湿,草木深茂,疾疫时有发生,见诸记载的反而相对较少。到了晋代,咸宁元年(275)十二月,洛阳发生了重大疾疫,死亡人数达到了十万。《晋书·武帝纪》载:“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太半。”[8]65次年正月,晋武帝本人也染疾,因发病而废朝,并且发诏曰:“每念顷遇疫气死亡,为之怆然。 岂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艰邪?”[8]66因为发生疾疫而辍朝,在晋代不止发生过一次,晋穆帝永和末年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晋书·王彪之传》载:“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礼部尚书王彪之上疏曰:“疾疫之年,家无不染。若以之不复入宫,则直侍顿阙,王者宫省空矣。”[8]2009皇室,或者是贵族之家,对于疾疫莫可奈何,而普通百姓于疾疫就是一场生命的浩劫。《晋书·庾衮传》载:“咸宁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复殆,疠气方炽,父母诸弟皆出次于外,衮独留不去。……十有余旬,疫势既歇,家人乃反。”[8]2280这次疫情持续有三个月之久,民众纷纷逃难,又导致疫病的传播,如像王彪之所言“疾疫之年,家无不染”。如此大规模疾疫暴发,其结果就是人口的迅速减少。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冬发生大疫,到了次年五月,多绝户者。《晋书·食货志》记载了西晋末期,也就是八王之乱后,整个社会凄惨的生活情况:“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8]791这是与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极度相似的末世景象,西晋亦亡。
疾疫在何时发生以及发生的规模、流传的范围是不可预测的,但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历史事件的结果,从而改变历史的进程。疾病尤其会对人的情感与生命产生强烈的冲击,这在汉末魏晋文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文人具有兼济天下的胸襟、悲悯苍生的情怀,感情丰富而又充沛,疾病对自身以及大众所造成的伤害与痛苦,婉转低回体现于笔下篇章,成为我们观察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文学发展的镜子。
二、疫情样态下的文人与文学书写
文人是一个时代的歌者,一个时代最强的声音是文人的歌唱。无论处于哪一个时代,外部生活的艰辛和苦难,最能够在人的情感上产生震荡。然而,这种苦难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发出文学的呼唤,也只有文人对于苦难、痛苦、生命的感悟更深刻、更彻底,从而发出震撼心灵的呐喊,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汉末魏晋这段历史时期,是文人开始大规模集中出现的历史时期,文学作品的多样性、文学题材的多元化以及文学思想的丰富性,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关注疾疫频发时代文人的生活以及生命的样态,对于理解鼎革之际的文学创作、文学思想的转型具有积极的意义。
疾疫对于文人的影响,莫过于建安七子的衰落。建安十六年(211)正月,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建安七子,除孔融(建安十三年伐刘表之前被曹操所杀)外,王粲、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已经聚集在曹丕、曹植兄弟身边,尤其是在邺城,日相游宴,文学娱心,创造了邺城文学的佳话。建安二十一年(216),王粲随曹操南征孙权,次年正月二十四日,王粲在返回邺城途中病逝,时年四十一岁。王粲的病故,使生命靡常的恐惧笼罩在文人心间。曹植《王仲宣诔》曰:“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谁不没,达士徇名。生荣死哀,亦孔之荣! 呜呼哀哉!”[9]1155既是诔人,也是自哀。又《说疫气》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9]1152-1153文人细腻而又敏锐的观察真切地反映了疾疫所造成的痛苦以及引发的生命思考。建安二十二年(217)发生的大疫,不仅王粲罹受其祸,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陈琳、阮瑀、应玚也未能幸免。《文选》载曹丕《与吴质书》,该文解题下引《典略》曰:“初徐幹、刘桢、应玚、阮瑀、陈琳、王粲等与质并见友于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诸人多死,故太子与质书。”[4]591诸人更多的是聚集在曹丕的麾下,他的痛苦以及思考则更加深刻和具有时代性。曹丕《典论·论文》对于汉末文学情况进行了总体概括,他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妆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9]1097这就是代表那个时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七个人。曹丕给予了建安七子堪称典型性的评价,最终目的是要给予生命和死亡一个解释,即人如何才能做到不朽,曹丕评价建安文人和文学所取得的成绩,也使文学理论、文学思想达到了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这是曹丕所没有料到的。
建安十三年(208)是疾疫暴发的年度,曹操最钟爱的儿子曹冲在这一年的五月病卒。这件事最大的受益者是曹丕。曹操曾经不无惋惜地对曹丕兄弟说:“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5]580因为曹操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要传位于曹冲,故有此语。曹丕作《曹苍舒诔》曰:“于惟淑弟,懿矣纯良,诞丰令质,荷天之光。……如何昊天,雕斯俊英。呜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促促百年,亹亹行暮,矧尔既夭,十三而卒,何辜于天,景命不遂。”[9]1091-1092可谓情真意切。 曹丕建魏后,黄初二年(221)八月,迁葬曹操高陵,作策曰:“咨尔邓哀侯冲,昔皇天钟美于尔躬,俾聪哲之才,成于弱年。当永享显祚,克成厥终。如何不禄,早世夭昏!……追悼之怀,怆然攸伤。今迁藏于高陵,使使持节兼谒者仆射郎中陈承,追赐号曰邓公,祠以大牢。 魂而有灵,休兹宠荣。 呜呼哀哉!”[5]581无论这是一场政治秀,还是感情真挚的兄弟情义,其中都透露出对于生命无常的哀伤。
或是曹操连年征战传播了疫病,抑或曹氏家族有某种病史,曹冲的死亡并不是个例。从曹丕、曹植的诗文集来看,曹氏家族经常发生童幼殇亡的悲剧。曹丕因为族弟曹文仲年幼而亡作《悼夭赋》:“气纡结以填胸,不知涕之纵横。时徘徊于旧处,睹灵衣之在床。感遗物之如故,痛尔身之独亡。愁端坐而无聊,心戚戚而不宁。步广厦而踟蹰,览萱草于中庭,悲风萧其夜起,秋气憯以厉情。仰瞻天而太息,闻别鸟之哀鸣。”[9]1073曹丕命王粲作了同题之文。王粲作《伤夭赋》:“惟皇天之赋命,实浩荡而不均。或老终以长世,或昏夭而夙泯。物虽存而人亡,心惆怅而长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愬?求魂神之形影,羌幽冥而弗迕。淹低徊以想象,心弥结而纡萦。昼忽忽其若昏,夜炯炯而至明。”[10]二者抒发的情感无别,但是角度和深度却是不同的。这一时期,曹植为哀太子中子殇逝作《仲雍哀辞》,为早逝的子女作《金瓠哀辞》《行女哀辞》等,情难自已,悲伤凄怆,面对死亡无奈痛苦的心情摹写淋漓尽致。
由于文献不可征,疾疫所造成的死亡之烈、影响之大,只能从侧面进行了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给我们提供了一则信息:“哀辞者,诔之流也。崔、苏顺、马融等为之率,以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建安中,文帝与临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刘桢等为之哀辞。哀辞之体,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辞。”[9]1906疾疫流行时代的死亡使文体得以强化,这是哀伤的文学记忆。
赤壁之战后,建安十五年(210),三十六岁的周瑜染病骤然离世。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载,周瑜临死前给孙权的信说,自孙权委以腹心、统御兵马之后,“规定巴蜀,次取襄阳”,“至以不谨,道遇暴疾,昨自医疗,日加无损。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诚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于是荐举鲁肃,如果孙权能够同意,“瑜死不朽矣”[5]1271。 很明显,东吴才俊周瑜也是身染疾疫而亡。在死亡面前,文臣武将都考虑到“不死”的问题。曹丕以立言为不朽,而周瑜则以事功、续功为主体思想。两者虽然有不同,但是依然在周秦以来传统思想文化的框架之内。
魏晋是玄学时代,作为这个时代学术思想的发动者之一的王弼,作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刘孝标注引《弼别传》曰:“少而察惠,十余岁便好《庄》、《老》。通辩能言,为傅嘏所知。吏部尚书何晏甚奇之。……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疠疾亡,时年二十四。”[11]231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了高平陵政变,诛杀了曹爽、何晏、丁谧、毕轨等曹魏的肱股之臣,也是魏晋玄学的倡导者与理论阐释者。王弼被免官,同年秋天,遭疠疾亡。“斯人也而有斯疾也。”[12]梁武帝萧衍感叹“才学迈世”却先患风疽、又染疠疾而左目失明的周兴嗣如是说。这一感慨对于王弼依然适用。王弼不仅得到傅嘏、何晏、司马师赏识,并且与钟会为友。刘陶称赞王弼“天才卓出,当其所得,莫能夺也”[5]795。 天才纵横的王弼,其所注《周易》,孔颖达认为:“独冠古今,江左诸儒并传其。”(《周易正义序》)东晋大将军王敦夸赞卫玠曰:“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当复绝倒。”[8]1067金声之于前,玉振之于后,说明王弼的玄学理论在西晋末叶并未绝响,而是绵传不止。同时,永嘉之末又是一个疾疫频发的历史时段,王弼又是死于疾疫,也有其惋惜之意。
《晋书》载,永和末,多疾疫。历史有记载的,永和六年(350)、永和九年(353),都发生了疾疫。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朋友,都是当时朝廷重要官员、社会名流,聚集在山阴兰亭“修禊”,作诗三十七首,裒为一集,王羲之为之序。在此崇山峻岭,有茂林修竹、激湍清流,足以移人精神,悦人性情。曲水流觞,临风讽咏,畅叙幽情,本来是很快乐的事,但是熏熏然的王羲之序曰:“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8]2099意兴之间忽发生死之悲鸣、人生无常的感慨,这恐怕是当时人面对疾疫、面对生死必须思考的人生主题。
每一个王朝的末世,都会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乱,伴生着多种多样的灾难,只有疾疫是无法躲避又是难以治愈的病痛,死亡也就变得触目惊心。汉末魏晋疾疫所造成的死亡尤其惨重,所以,对于生命飘忽的哀叹,在建安文人中是一种集体趋势,也是这个时代的总体特点。虽然不乏曹操横槊赋诗的慷慨悲歌,也仅仅是一个抑郁时代的一声高亢的歌吟罢了,不会改变整个时代的忧郁气质,也不会改变一个时代文人对于生命的担忧和对死亡的忧虑。正是因为死亡的威胁,魏晋人不得不重新考虑生命安顿的方式,玄学产生是有其深刻内因的,重个体、重情性的文学也就呼之欲出了。
三、汉末魏晋文学思想的转型
东汉社会主体思想依然是儒家学术思想,儒生政治是其不变的主题。东汉中期,太学生已经达到了三万人,在增加社会人口知识阶层含量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矛盾。处士横议,君臣交争,导致两次党锢之祸的发生。地震、水旱灾害等屡有发生,大规模频繁暴发的疾疫,催生了太平道,导致张角起义。汉末割据势力长期交战,最终灭亡了东汉,历史进入三国魏晋时代。汉代桓、灵帝以后,死亡阴影的笼罩使整个社会弥漫着忧郁悲凉的气息,从儒生转化成文人的社会,一部分社会精英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人生与生命的思考,不朽问题屡屡被提及;儒学遭到了玄学的挑战,玄学在魏晋大放异彩。正是对于情感的释放,文学回归本体,“诗缘情”理论挣脱了名教礼制的束缚脱颖而出。一个抑郁悲凉的时代,完成了哲学的突破,塑造了张扬的个性,创造了灿烂的文学及其理论。
(一)汉末魏晋:一个精神忧郁悲凉的时代
汤显祖在《牡丹亭》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就像风起于青萍之末,微细的变化我们毫无察觉,特征显著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种趋势。东汉社会的情绪就是这样,从又见汉官威仪的群情激奋,到洋洋乎永平的雍容典雅,再到章帝时的颂声嘹亮,倏忽四十余年,阴阳易位,社会情绪转而悲伤难抑。《后汉书·周举传》载:汉顺帝永光六年(141)三月上巳,梁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与亲朋故旧酣饮极欢,“酒阑倡罢,继以《薤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涕”[2]2028。 《薤露》是当时的挽歌。注引崔豹《古今注》载曰,《薤露歌》:“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还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2]2028歌词伤感,充满了死生无奈的感叹。 而梁商是汉顺帝皇后的父亲,官拜大将军,作为地位尊贵的皇亲国戚,享受荣华富贵,原本一场兴高采烈的春游宴饮,却以悲歌流涕散场。这不是个案,哀歌作乐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甚至在婚礼上也演奏哀乐。《后汉书·五行志》载,汉灵帝时后宫有服妖,导致天下大乱。刘昭注云:“《风俗通》曰:‘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儡》,酒酣之后,续以挽歌。’《魁儡》,丧家之乐。挽歌,执绋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国家当急殄悴,诸贵乐皆死亡也。自灵帝崩后,京师坏灭,户有兼尸,虫而相食,《魁儡》、挽歌,斯之效乎?”[2]3273不仅有党锢的倾轧,还有天灾的频繁发生。尤其是疾疫的发生,没有任何征兆,倏忽其来,奄忽其过,去就之间死亡不可胜数。仅以疾疫发生来看,《后汉书·五行志》又记载,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延熹四年正月大疫。孝灵建宁四年(171)三月大疫,熹平二年(173)正月大疫,光和二年(179)春大疫,光和五年(182)二月大疫,中平二年(185)正月大疫。汉献帝建安时期疾疫发生的频率有过之而无不及。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全 国 人 口 统 计:16 070 960户,50 066 856人。三国鼎立时,户口统计:1 473 433户,7 672 881人[13]。 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是极其真实而又残酷的历史写照。当然,人口急速缩减,并不仅仅是因疾疫引发死亡而导致的,水旱灾害以及战争也是导致人口递减的原因,尤其是战争,但以上诸因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躲避的。唯有疾疫发生,人则无法逃避,即便逃离,也会成为疾疫流动的传染源,它对生命未知所造成的恐慌是最大的。
东汉桓灵帝以降,社会弥漫哀伤的氛围,历史进入忧郁的时代。《古诗十九首》的痛苦、哀怨、悲伤是整个社会情绪宣泄的表现,直击生命本质的人生思考是深入也是深刻的,“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去者日以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明月皎夜光》),峻刻的生命领悟,在千百代之下犹能获得共鸣。建安末期,整个社会哀伤忧郁而不能自持,以哀歌曲调作乐声已经相当普及,从而变成一种社会时尚。曹操作《薤露》《蒿里行》,诸葛亮好为《梁父吟》,并为哀歌。曹丕、曹植以及建安七子并无乐府丧歌古题的诗文,作的是《长歌行》《短歌行》《七哀诗》。晋人的陆机不仅作短歌,也作长歌。“置酒高堂,悲歌临觞。”(《短歌行》)“兹物苟难停,吾寿安得延。”(《长歌行》)伏无忌《古今注》云:“长歌短歌,言人生寿命,长短定分,不可妄求也。”[14]所以,军旅征战、驰骋疆场的曹操,固有孔武之风的慷雄壮慨,不免有人生譬如朝露、痛哉世人的悲凉。曹操的慷慨是一种悲情的慷慨,人生悲凉引发的慷慨。建安七子已经由儒生蜕变为文人,他们身上有更多的文人的哀感顽艳,建安诗风是笼罩在忧郁悲情时代的文人歌唱。
在疫情以及战争笼罩下的汉末魏晋时代,表现出浓重的忧郁和悲凉,于是生命不朽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文章承担起建设人文情怀、构建生命精神的重要使命。同时,这也是道家学说大放异彩的前提。在哲学上关于人和生命的思考,促使文学走向了玄言、走向了游仙,真情与自我涌动的文学冲破了礼教的禁锢,文学成为人的文学。
(二)“经国之大业”:文学价值的重新体认
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陈琳、应玚、刘桢四人几乎同时病亡,致使建安七子全部凋落。面对来势汹汹的疾疫和无处不在的死亡,承受朋友相继离世的痛苦,曹丕不得不直面生死问题。建安二十四年(219)二月三日,曹丕给自己的好朋友吴质去了封书信,表达自己沉痛的心情以及人生的思考,曹丕想到了昔日游处的快乐时光,黯然兴叹:“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9]1089曹丕回顾了除孔融外建安六子的文学成就,但无论文学创作如何高妙,为时人所倾倒,斯人已经化为粪土,而随着年龄的增大,思虑之多,至于“通夜不瞑”。在二月八日,吴质很快给处于焦虑之中的曹丕寄来一封回信,回忆当年宴处的快乐,不无感触地说:“何意数年之间,死丧略尽。臣独何德,以堪久长。陈、徐、刘、应,才学所著,诚如来命,惜其不遂,可为痛切。”笔锋一转,随即说道:“白发生鬓,所虑日深,实不复若平日之时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过之地,以为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欢,难可再遇;盛年一过,实不可追。”[9]1221曹丕与吴质的书信往来,只是怀念故友,表达深湛之思以及生命老去的愁闷,二人考虑如何让生命不朽的问题。《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云:“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5]88几年间,曹丕在友朋凋零、生命无常的痛苦与思考中找到了人生真谛的答案,即《典论·论文》文学不朽思想的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9]1098
当疾病所带来的死亡涤荡了生命活力,无论高贵贫贱都化成一抔粪土的时候,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直接冲击了文人的思考,让历史以及人们记住的,唯有古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这样才能做到生命的不朽。乱世崇尚武功,文人若能立功,只能采取依附所谓明主的方式来获取。汉末时期,“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就是文人雅士聚集在曹操幕府的主要原因,同时曹操本人也是才华横溢,慷慨悲歌,能够欣赏与理解文人作品歌咏的深刻内涵,由此而增进了一方枭雄和文人之间的情感距离,所以很多文人聚集在曹氏父子周围。汉末文人的主体,也是能够被文学史所铭记的时代的歌者,在曹氏父子的羽翼下,能够相对优雅文艺地生活着,对于曹丕来说,铸成了难以忘怀的快乐时光。但是,曹丕彼时已经成为魏王的太子,自己的建功立业和诸多文士想要或正在采取的方式又自不同,只需要坐稳魏王太子的位置,立功仅在一心之间。曹操去世之后,曹丕很快以禅代的方式取得政权,黄初三年(222)大举南攻孙权,而不是偏安一隅,立功的急迫心情可想而知。
建安文人除了选择明主才能建功外,立德显然又是不现实的。曹操采取了“唯才是举”的政策,只要人才为我所用即可,并没有附加道德的要求,这就使聚集在曹操幕府的文人,在道德上高劣俱存。七子中的刘桢,竟然在曹丕席上平视甄氏,险些被曹操斩杀,王粲初附刘表、陈琳初附袁绍,若以道德论,事二主德行有亏。文人以文章、文采而立,难免风流不羁,不注重细行小节。所以,从在汉末特定的时代以及所采取的招徕人才政策的方式来看,注重立德显然是不现实的。七子中为曹丕所称道的徐幹恬淡自守,被曹丕称为“彬彬君子”,这种道德要求和评价显然要低得多。对于文人来说,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立功、立德不可取,唯有自身以才华、辞藻编织的或精美或沉郁的华彩辞章,更能博得世主、世人的关注。
曹丕指出了建安五子,实际上还有孔融,在依附于曹操之前都已经各自成名,只有部分文章是在依附曹氏父子之后留下来的。所以,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不朽思想,主观上在论人,客观上在论文,人因文而不朽,文因人而永传。曹丕认为,斯七子者所作即为经国之文章,并且各有所胜,都是时代文学的佼佼者,虽然七子已逝,因文章可以不朽。确实如此,因为曹丕不遗余力的表彰,七子已经做到了不朽,后人也因为作品而念念不忘七子。《文心雕龙·才略》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声;徐幹以赋论标美;刘桢情高以会采;应玚学优以得文。”[15]
(三)“文以气为主”:个体文学风格的生成
《说文》曰:“疫,皆民之疾也。”南唐徐锴则做了引申论说,《说文系传》曰:“疫,民皆病曰,从疒,役省声。臣锴曰:‘亦鬼神在其间,若皆应役然也。’”刘熙《释名·释天》:“疫,役也,言有鬼行疫也。”又《释疾病》曰:“疾,病者,客气中人。疾,急也;病,并也,并与正气在肤体中也。”疾疫为鬼神行役所致,是汉代流行的看法。襄楷就认为:“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结,无所归诉,淫厉疾疫,自此而起。”[2]1078显然,曹植是反对这一说法的。《说疫气》曰:“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此方和《礼记·月令》的观点相一致。《礼记·月令》说:“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行秋令,则其民大疫。”为了防止阴阳不调造成疫气,采取的方式是傩礼,即“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郑玄注曰:“此难,难阴气也。明寒至此,不止害将及人,所以及人者阴气右行,此月之中,日行历昴,昴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随而出行,命方相氏帅百吏索室,欧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于四方之神,所以毕止其灾也。”[16]这就是汉代民众采用的清除疫气的方法,当然这种方法是无效的。
疾疫,又称疫气,是鬼神所致,这和东汉襄楷的说法是一致的,民间也是如此流传的。疫气为气,鬼神也是气,《论衡·论死篇》曰:“人死精神升天,骸骨归土,故谓之鬼。鬼者,归也;神者,荒忽无形者也。或说:鬼神,阴阳之名也。阴气逆物而归,故谓之鬼;阳气导物而生,故谓之神。神者,伸也,申复无已,终而复始。人用神气生,其死复归神气。阴阳称鬼神,人死亦称鬼神。”[17]这样的理论与先秦以来的哲学思想是一致的。古人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五行之气生成的,更进一步说,也就是阴阳之气形成的。疾疫,鬼神,以及人,都是气,在哲学层面上有了感染、交流、媾和的可能,所以人感染疾病是有其道理的。然而,同是气,人又有不同。《礼记·礼运》云:“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人是高层次的气,也就具有了能动性,能够感知万物。
人为气所构成的,气有清浊,人就有了各自不同的禀赋;各自不同的禀赋,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文章型态。所以,才有了曹丕所谓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看似在论文,实际上是在论人,是在讨论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选择适合于自己的文体,也就有了各自的文学风格。这就是所说的人各有体的问题。因为曹丕已经分析了七子的所长:“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陈琳阮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社,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时有所善,杨班俦也。”[9]1097然后才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虽然写作同一类文体,或者同一题材,由于个人的气格不同,文章的表现力就不一样。曹丕所谓的文学分体问题,核心是在探讨创作风格问题,而创作风格又是由个体不同的气格所决定的。元人郝经对此理解得非常透彻,他说:“文章以气为主,孔融气体高妙,徐幹时有齐气。文章有大体,无定体,气盛则格高,格高则语妙,以气为主则至论也。呜呼!丕言论固至矣。”[18]鱼豢《典略》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文以气为主”的观点:大鸿胪卿韦仲将云:“仲宣伤于肥戅,休伯都无格检,元瑜病于体弱,孔璋实自粗疏,文蔚性颇忿鸷,如是彼为,非徒以脂烛自煎麋也,其不高蹈,盖有由矣。然君子不责备于一人,譬之朱漆,虽无桢干,其为光泽亦壮观也。”[5]604“仲宣伤于肥戅”“元瑜病于体弱”“孔璋实自粗疏”,曹丕《与吴质书》所谓“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元瑜书记翩翩,孔璋章表殊健”,论文论人,其主旨思想即是“文以气为主”。
(四)“诗缘情而绮靡”:诗歌本体的发现
宗白华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9]177经过魏代的祛弊,越名教而一任自然,竹林七贤成为个性解放、追求自然、对抗礼教的文人典型,充分展露个体天性、情怀,使魏晋进入钟情的时代。
《礼记·乐记》有云:“情深而文眀,气盛而化神。”东汉末《古诗十九首》深情而凄美,而这种肆意的深情为三曹及建安七子所继承,他们的诗歌中张扬了抒情的传统,然而并未脱尽礼乐文化的影响。如曹操《度关山》“兼爱尚同,疏者为戚”,徐幹《西征赋》“登明堂而饮至,铭功烈乎帝裳”,依然有着反情合志的影子。正始玄学兴起之后,人的个性和情感得到了释放,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矫枉过正,所谓僈侮轻狂行为对于社会的冲击,使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行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王戎卿卿我我,痛失爱子的悲不自胜,所谓:“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11]751钟情、尊情、抒情成为魏晋文人的精神骄傲。作为父亲,郗愔爱其子胜过王戎。《世说新语·伤逝》载:“郗嘉宾丧,左右白郗公‘郎丧’,既闻,不悲,因语左右;‘殡时可道’。公往临殡,一恸几绝。”[11]75深受魏晋风度影响的鲁迅,也曾告诉我们“怜子如何不丈夫”,爱子之情正是魏晋人深情的体现。
《世说新语·伤逝》载:顾荣喜好抚琴,及丧,家人置琴灵床上。同乡好友张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11]753。 上床弹琴,临丧不执孝子之手,都是有违礼法的行为,张翰只顾悼念朋友,尽情而去。这样的事情还发生在王献之、王徽之兄弟身上。《晋书·王徽之传》载:王献之卒,“徽之奔丧不哭,直上灵床坐,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呜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顿绝。先有背疾,遂溃裂,月余亦卒”[8]2104。 非是悲不能成调,而是“人琴俱亡”,兄弟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二十四友之首的潘岳,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具有美好的容貌和优雅的风姿。虽然在品行上备受诟病,但是对于亲人的浓郁之情还是备受称道的。夫人杨容姬亡后,作《悼亡诗》三首。其中有云:“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独无李氏灵,髣髴睹尔容。抚衿长叹息,不觉涕沾胸。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潘岳《悼亡诗》其二)潘岳对亡妻的思念之情娓娓道来,令人感同身受。钱基博称赞说:“辞来切情,情往引哀,只就闺房细碎,抒写追慕,情文相生,如闻呜咽,以岳固工于叙哀也。”[20]
正是在钟情、尽情的大时代背景下,文学史上与潘岳并称“潘江陆海”的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超迈前代的诗学命题:“诗缘情而绮靡”。曹植《洛神赋》:“扬轻袿之绮靡兮,翳修袖以延佇。”清人沈自南说:“吕向曰:‘袿,妇人之上服也。’今按:轻袿长带也。修袖,大袖也。长带大袖,卷舒若烟云,盖古美人之服多如此。”[21]依此,陆机所谓的“绮靡”可以理解为多姿多彩,或舒展华美,后衍生出香艳之意。祝尧《古赋辨体》曰:“殊不知辞之所以动人者,以情之能动人也。何待以辞为警策,然后能动人也哉!且独不见古诗所赋乎,出于小夫妇人之手,而后世老师宿傅不能道。夫小夫妇人亦安知有所谓辞哉!特其所赋,出于胸中一时之情不能自己,故形于辞而为风比兴雅颂等义,其辞自深远矣。然指此辞之深远也,情之深远也,至若后世老师宿傅则未有不能辞者。”[22]无疑道出了“诗缘情”的真谛。 这里的情是经过魏晋玄学祛弊之后,不受礼乐文化束缚的人的自然之情感,这种情感,即便不懂文辞之美,如“小夫妇人”的作品也能做到一往情深,从而动人心脾。陆机的“诗缘情”说已经回归到诗歌本体的探寻,“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19]183,魏晋之文人在神情疏朗中,自信地展露才华横溢,演绎着一往情深的文学。
结 论
中国2—3世纪暴发疾疫频次之高、范围之广、死亡之巨对于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剧烈的、持久的,思考也是深入的。发生疾疫虽然是一种自然现象,在当时却附加了士大夫的主观政治意识,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也就有了末世的意味,潜藏着社会变革的信息。疾疫以及日蚀、地震、水旱灾害的相伴发生,持续不断的战争,使整个社会弥漫着末世的哀伤与凄凉,形成了汉末魏晋忧郁的时代气质。当哀歌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音乐,就不仅仅是情感上的苦难,更呈现出精神上的挣扎与黑暗,希冀生命不朽的文人骚客,于是把文学作为延续生命的手段,文章不朽的命题自然被召唤出来赋予时代的意义,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先声。阴阳是先民对于物质世界构成的认识,人与世间万物,也包括疾疫,都是阴阳二气构成的,“气”就成为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钥匙。曹丕“文以气为主”的理论命题不仅有了学理的支持,还有了更深刻的现实考量,个体文学气质的认识也更加深入。人是由气构成的,所以才能养浩然之气,疾病与死亡刺激了“养气”与游仙理念的深入发展,游仙诗、玄言诗脱颖而出。而区别于儒家思想的新的天人关系因时因运而生,思考生命本质的玄学成为魏晋时代哲学的主流,生命安顿方式、个体情感抒发不仅改变了文人的生活方式,喝酒、吃药、恣意享乐,如此的放荡与洒脱促使魏晋文人以及文学更加重情重义,充满了人性的温度。回望历史可以发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正是不可预知的疾疫所造成的死亡,加速了汉末魏晋社会、思想以及文学的主动变革,推动了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促进了文学思想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