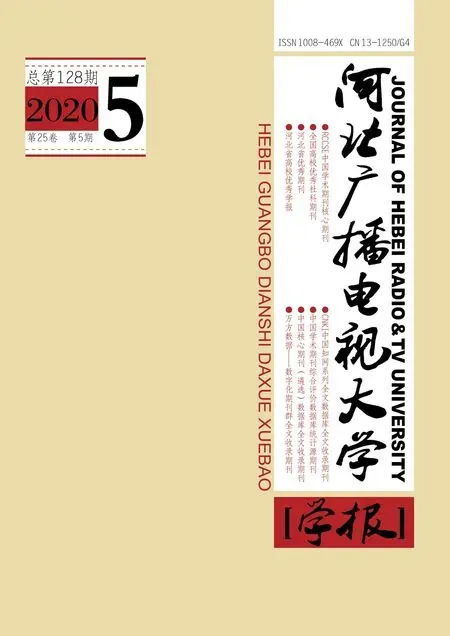“发愤著书”说对“诗可以怨”的继承和发展
武 超
(辽宁大学 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理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命题,他将文学创作的动机及思想性归结为作家内心的“郁结”,从而揭示了作家和作品之间的紧密关系。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孔子的“诗可以怨”,他不仅在“怨”的文学功能上进行了继承,同时又有很大的突破,并且对后世文学理论以及文学实践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发愤著书”说的提出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其《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1]同时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理论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记》草创于太初年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刑下狱。由于切身的实践体验,他对封建统治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从创作的实践中更加体会到古人发愤著书的心情。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 《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2](P4006)他在《报任安书》中也写道:“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P83)他从历代先贤著书经历出发,同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发愤而创作《史记》。
“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义愤愈加强烈,则作品的思想性也就愈为深刻。”[3](P82)司马迁身受腐刑,同时不满当时的现实,于是在《史记》里揭露和抨击周围的黑暗现象,同情被压迫的人民。“发愤著书”说的内在思想和批判现实的文学精神相结合,使得《史记》成为“无韵之离骚”。
二、“发愤著书”说的形成过程
陆游在《澹齐居士诗序》中说:“诗首国风,无非变者,虽周公之《豳》亦变也。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3](P84)可见《诗经》中诗歌的创作多是作者心中有所郁结,所以借助诗歌来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和对社会的不满。“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馋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忧思而作《离骚》。”[2](P2482)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解释了屈原发愤作《离骚》的原因,同时说道:“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2](P2482)此外,屈原在《九章·惜诵》明确说出了“发愤以抒情”[4](P121)。他将辞赋创作作为发泄内心愤懑的方式。从《诗经》中作者有所郁结到《离骚》中屈原“怨生”,司马迁总结前人创作动机,同时结合自己切身体会,提出了“发愤著书”的理论主张。
1.孔子的“诗可以怨”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重要的文论命题,他的产生不仅有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切身体会,而且有深远的理论背景。早在《诗经》时代诗歌中就出现了抒发忧怨的意识,《诗经·园有桃》中写到“心之忧矣,我歌且谣”,[5]就是把内心的忧伤不满以歌谣的形式抒发出来,但这里的抒忧只是一种感性的发泄,没有达到理论的高度,真正形成一种理论认识的是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总结的“诗可以怨”[6]。
什么是怨呢?主要有两种解释:其一,汉代孔安国《论语循解》中注释为“怨刺上政”,即主要看重对政治的怨刺。受因于当时的社会风尚——汉代好以《诗经》作政治功用,但并不很全面,怨的内容在《诗经》中有着广泛的体现,如表现古代妇女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备受压迫和摧残的《氓》;反映从军将士艰辛生活和思归情怀的《采薇》;描写沉重劳动场景,嘲骂剥削者不劳而食的《伐儃》等。春秋后期,政局混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诸侯王对社会的自由言论采取一种压制的态度,因而人们只能通过歌谣的形式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和抒发内心的愤懑。其二,宋代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将“怨”解释为“怨而不怒”,[7]即虽然要借助诗歌实现批判社会的效果,但也并不能走向极端,这也是符合孔子原意的。儒家诗歌以“温柔敦厚”冠名,它对于诗歌创作有一定的约束,无论是过于喜乐还是过于忧愤,都是不提倡的。
正如《诗大序》所阐发的那样,“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3](P63),孔子的“诗可以怨”这种思想集中突出地表现在关于诗歌的社会作用方面:“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3](P63)这种理论更多体现在政治上表达统治阶层对诗歌的要求,同时要求诗歌要“温柔敦厚”,不能太过激烈。
2.屈原的“发愤以抒情”
战国时期,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在《九章·惜诵》一文中写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4](P121)他用“以”字将“发愤”与“抒情”联系起来,揭示了先“发愤”后“抒情”这一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
屈原的“情”突出表现在“愤”上,他的愤是怀王不能听信忠言、明辨是非,被谗言和谄媚之辞蒙蔽了聪明才智的悲愤;是邪恶小人危害公正之人,端方正直的君子不为朝廷所容的义愤;是世人皆醉我独醒,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孤愤。屈原的《离骚》是抒发哀怨愤怒的杰出诗篇,是“发愤以抒情”这一理论在创作中的具体体现。
这里提到的“发愤抒情”跟孔子的“诗可以怨”有一定的区别:其一,更接近于“诗可以怨”的表层含义,即进行文学创作以抒发自己的怨情,从而使“发愤”进入创作动因的层面。其二,儒家虽然提出“诗可以怨”,但“怨”的前提是要止于礼仪,儒家认为诗可以怨刺上政,但必须“主文而谲谏”[3](P63)。屈原作诗以抒愤,充满了批判色彩,显然是在儒家允许的范围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的“诗可以怨”强调社会功能,着重于政治、社会以及教育。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则是侧重于创作主体情感的宣泄、抒发。屈原不是文艺理论家,他对文学创作的看法并不是通过文学评论的形式来阐述的,但不得不说他的“发愤以抒情”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提出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此可见,“发愤著书”说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从孔子的“诗可以怨”到屈原的“发愤以抒情”,两位先贤的理论都直接启发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提出。
三、“发愤著书”说对“诗可以怨”的发展
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思想中一条重要的理论意脉,他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经过屈原“发愤以抒情”,到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提出则是这一理论的重大发展。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提出将研究的聚焦点转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从诗怨内涵来看,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不仅是对“诗可以怨”的继承,更是一种发展,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1.表现范围的个人化
就情感表现范围而言,孔子所提出的“怨”主要来自对上政的不满,还有一些是对感情生活的不称心,对生活艰苦的抑郁不满,以及对不合礼教的言语和行为的愤怒。从内容范围上看,这些“怨”包括两类:因个人遭际而产生的个人哀怨,以及因政治昏暗、民不聊生产生的家国之怨。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从范围上看,虽然不能说没有国愁民忧,但更多的是与黑暗现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个人之怨,范围小。一方面司马迁对自己执掌史官的卑下地位深表不满,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另一方面,对于司马迁来说,在他的人生遭遇中,宫刑之祸可以说是他经历的最大痛苦。司马迁从小学习儒家思想,“儒者可亲不可劫也,可杀而不可辱”的观点深深嵌在他的脑海,宫刑不仅是对他健全体格的摧残,更是对他人格尊严的侮辱和践踏。身体的不完整让他“肠一日而九回”,无颜苟活,以至于想一死了之。但是历史上那些惨遭厄运却自强不息,化悲痛为力量的先辈们的事迹鼓舞了他,父亲在临终前托付他的神圣使命也不允许他有半点退缩。在反复思量下,司马迁痛定思痛,选择继续苟活下去,把一腔怨愤化为创作的动力,终于写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P83)的史学著作。这也正说明了司马迁之怨来自他对黑暗现实、自身遭遇的不满,与家国之怨没有多大关系。
2.情感程度的强烈化
就情感强度而言,孔子所说的《诗经》之“怨”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抱怨、小牢骚,主要体现在一些表现婚姻生活不如意、恋人相思之苦、征人思妇的作品中,例如《鹊巢》 《采薇》等;另一类是由于内心极度愤懑引发的怒,主要体现在对君主发动战争以及由此带来民不聊生现状的讽刺和批评的作品中,例如《小雅·正月》 《伐儃》等。而孔子本人主张不怨不怒,怨是积压在内心的不满情绪,而怒是外表上体现出来的不快。无论怨、怒都有一个度,要做到合情合理,不超出一定的范围。
司马迁在继承孔子“诗可以怨”思想的基础上,摒弃了孔子诗教思想中“温柔敦厚”的中庸一面。他指出“愤”是内心压抑不得伸展的状态,是作家创作的内在心理动力,通过著书来使内心郁结而成的“愤”情得到疏通宣泄,使心理得到平衡。司马迁的“愤”是一种强烈的“怒”,是高于孔子所言的“怨”的。如果说“怨”是一种星星之火,那么“愤”就是燎原烈火。从孔子的“诗可以怨”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文学的情感力量呈现出了飞跃的发展。“发愤著书”不仅仅是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同时也寄予着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种情感力量的变化,使得作品不再局限于“温柔敦厚”的风格特征,而是呈现出强烈的批评精神,当然,对于读者来说也能起到极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
3.情感表达的文学化
从诗怨命题发展史来看,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对文学创作的发展起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撑。
第一,由孔子侧重的社会领域转向了文学艺术领域。春秋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奴隶社会的鼎盛期,众多的劳动人民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身份和平等地位。而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即提倡统治者要施行“仁政”,最终促使整个社会形成“泛爱众而亲仁”的理想局面。但在奴隶社会,这种社会理念显然过于理想化,虽然作为奴隶的劳动者常年辛勤劳动,但常常遭受奴隶主惨无人道的剥削压迫,在广大劳动人民当中弥漫着对统治者的不满和怨恨情绪,所以此时孔子提出的“诗可以怨”这一理论具有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也因此诗歌的批判和讽刺功能具有了普遍性和社会性。由此不难看出,孔子的“诗可以怨”将重点放在了社会领域,更加强调诗歌的社会政治功能。而“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从自身经验和历史上许多先贤都遭受磨难仍自强不息发愤著书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出来的文学创作规律。他更多强调作家个人的命运遭际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向世人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反映现实生活、批判黑暗现实、具有真情实感的优秀作品都是作家内心有所郁结、理想无法实现后的产物。他这一理论更侧重文学艺术领域,同时也对后世作家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由“诗可以怨”中的接受主体转化为创作主体。后人往往根据表达的习惯,把“诗可以怨”理解为“《诗经》可以用来抒发内心的怨愤”。按照这种理解,“怨”的主体便是作者,作者通过创作诗歌来宣泄内心的牢骚不满以及怨愤。孔安国的“怨刺上政”的注释便是从这一角度考虑得出的。但这种解释与孔子是大相径庭的,孔子是以接受者的身份,大量研习、阅读《诗经》,根据《诗经》怨的内容特征提出“诗可以怨”的。所以“诗可以怨”中“怨”的主体是接受者。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在总结前人和自己创作经验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愤”的主体是作者,作者内心郁结,借助著书来疏通自己的情感,使心理得到平衡。当然,“发愤著书”并不意味着作家情感的肆意宣泄,而是将内心的愤懑转化为著述的动力,通过作品来抒发内心的情感。
第三,在更深层次上,与以往孔子主张的“克己”不同,司马迁表现出强烈的个体意识,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生命意识的觉醒。他不再是“不怨不怒”,而是“怨且怒”,把满腔悲愤融入创作中,终于创作出“不虚美,不隐恶”的《史记》。
四、“发愤著书”说对“诗可以怨”突破的原因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提出的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从孔子的“诗可以怨”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司马迁不仅在“怨”的文学功能上进行继承,同时又有很大的突破,这种突破主要是来自于他本人所具有的批判性。至于他所具有的批判性和反抗性,其思想渊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道家思想的影响
司马迁少年时代虽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就学于孔安国和董仲舒,但他的世界观中也有从其父那里继承来的道家思想。在《太史公自序》中他全录了其父的《论六家要旨》就是最好的证明,《论六家要旨》载:“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2](P3289)司马谈对五家学说(阴阳、儒、墨、名、法)肯定中又有批判,但对道家学说却只有肯定,认为其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学说。
道家的思想,特别是庄子带有一种强烈的批判色彩,他愤世嫉俗,大胆地揭露与批判现实中的一切腐朽黑暗,如《庄子·肢篋》篇中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8],尖锐地讽剌统治者假仁假义的丑恶行为。司马迁吸收了道家思想中的这些积极因素,用他那支如椽之笔,写尽天下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刑法、思想等方面,上至残暴不仁的帝王将相,下至酷吏贪官佞臣,他都给予了无情的抨击,真正做到了“实录”精神——“不虚美、不隐恶”。例如,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直接引用了《庄子·肢篋》中的名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来批判统治者所讲的仁义的虚伪性。另外,彭城一战,项羽大败刘邦,刘邦落荒而逃,《史记》载:“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2](P322)这是说刘邦为了逃脱性命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子女都不顾,这就足以让人感到他的不仁,令人心寒。紧接着司马迁又在《史记·项羽本纪》写了另一件事:“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背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2](P327-328)这里写的是刘邦说很想喝一杯用自己父亲的肉煮成的汤,于是一个万人敬仰的汉高祖在司马迁笔下就变成了六亲不认的大流氓。
正是由于司马迁所具有的近于道家庄子的批判精神,我们才能更清楚更真实地看到封建统治者虚伪的真实面目,更加深入地了解封建社会的本质。
2.传习《鲁诗》
司马迁习《诗》传自《鲁诗》,清代著名儒学家陈乔枞在《鲁诗遗说考·卷一》中指出:“《史记》叙传自言‘讲业齐、鲁之都’,子长宜习《鲁诗》。又《儒林传》言‘韩婴为《诗》与齐、鲁间殊’,似不深信韩氏。且子长时《诗》惟鲁立博士,故《史记》所引《诗》皆鲁说也。乔枞谨案,全氏祖望云:‘太史公尝从孔安国问《古文尚书》,安国为《鲁诗》者也。史迁所传,当是《鲁诗》。’乔枞今即以《史记》证之,其传《儒林》,首列申公,叙申公弟子,首数孔安国。此太史公尊其师传,故特先之。据是以断,《史记》所载《诗》,必为鲁说无疑矣。”[9]清末学者王先谦也认为:“太史公从孔安国问业,所习当为鲁诗。”[10]
与《齐诗》 《韩诗》和《毛诗》相比,《鲁诗》更注意《诗经》的讽谏作用,如同样是阐释《鹿鸣》的大旨,齐、韩、毛三家都认为《鹿鸣》之旨,在燕群臣嘉宾方面,但《鲁诗》却认为《鹿鸣》有“刺”的方面。[11]又如东汉时期《鲁诗》的传授者蔡邕在《琴操》中指出:“《鹿鸣》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倾,留心声色,内顾妃后,设旨酒嘉肴,不能厚养贤者,尽礼极欢,形见于色。大臣昭然独见,必知贤士幽隐,小人在位,周道凌迟,必自是始,故弹琴以讽谏,歌以感之,庶几可复歌。……此言禽兽得美甘之食,尚知相呼,伤时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而刺之,故曰《鹿鸣》也。”[12]《鹿鸣》为《小雅》之始,看重“刺”既是《鲁诗》不同于《齐诗》 《韩诗》和《毛诗》的地方,同时也给《诗·小雅》带来了新的解释。
司马迁传习《鲁诗》,接受了《鲁诗》重讽谏的作用,这种讽谏最直接的反映便是在《史记》中对当朝皇帝汉武帝的种种不当行为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如《封禅书》讽刺了汉武帝迷信鬼神的愚蠢行为;《平准书》揭露了汉武帝利用权力,扼杀、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以求解决自身财政危机;《匈奴列传》对汉武帝不停地进行战争,耗费人力财力以及任人失当、不知选贤任能作了辛辣的嘲讽。
3.独特的创作经历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用生命实践的理论主张,在文学史上,创作成就能与司马迁比肩的文学家还有很多,但是能像司马迁这样把理论和实践高度统一、紧密结合进行创作的文学家却很少。
值得一提的是,一方面,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不是对自己以及历史上一些先哲们创作经验的简单概括,而是饱含着斑斑血泪对自己痛苦心灵的抒写。这就使他的理论主张显得与众不同,闪现着耀眼光芒。孔子虽然也提出了“诗可以怨”,对当时不良的文学风气或社会风尚报有鲜明的批判态度。但孔子的删编《诗经》,是为了“修齐礼乐”。使《雅》 《颂》各得其所。而且他本人并没有遭受什么奇耻大辱,对统治者也没有司马迁那般决绝。因而他的“诗可以怨”虽然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其所具有的批判性显然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司马迁对自己的理论主张付诸全部精力以至生命,为了著书,他忍受了世人的嘲讽,从“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的悲愤状态中振作起来,终于写成了《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
五、“发愤著书”说的余波
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汉赋占据着主导地位,汉赋虽然提倡“劝百讽一”,但大多数汉赋作品都是一些歌功颂德之作,并不长于讽,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显然是独树一帜的,它不仅具有丰富理论的内涵,而且对后世作家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创作的优良传统。
到了唐代,有着“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对“发愤著书”说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的“不平”既包括司马迁所说的愤怨又包括欢乐等情绪。宋代,欧阳修提出了“穷而后工”说,是对“发愤著书”说的进一步发展,“穷”的范围更大,不仅包括政治上受到的挫折,也包括生活中遭遇的不幸;明代李贽把“发愤著书”说这一理论运用到小说批评上,他指出施耐庵、罗贯中“虽生元日,实愤宋事”[13],怨恨封建统治者的无能,创作《水浒》来发泄内心的怨愤,至此,“发愤著书”说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完成了新的突破。
六、结语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孔子的“诗可以怨”。孔子的“诗可以怨”更多地表现在政治功用上;到了屈原则发展成为“发愤以抒情”,用诗歌来寄托情感;到了司马迁诗怨传统仍然贯穿在整个社会当中,不过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说则是有别于孔子的“诗可以怨”的。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更多地关注个人情感的抒发;情感强度更加激烈;更加注重“诗怨”的文学功用,使得“诗怨”这一命题从讽刺上政这一单一社会功用发展到文学的创作论上来。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提出不仅与其从小接触道家思想以及传习《鲁诗》有关,道家思想和鲁诗中的批判精神为司马迁所继承,所以我们读《太史公书》可以读出字里行间所饱含的作者的批判与愤懑。更为重要的是与其遭受的经历息息相关,“腐刑”不仅是对身体的重创,更是对尊严、人格的践踏。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将这种内心的极度愤懑宣泄在文学的创作中,由此也形成了后世所说的“发愤著书”这一文学理论命题。从孔子“诗可以怨”到司马迁“发愤著书”,中国“诗怨”传统在不断地继承与发展,对后世文学理论以及文学实践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