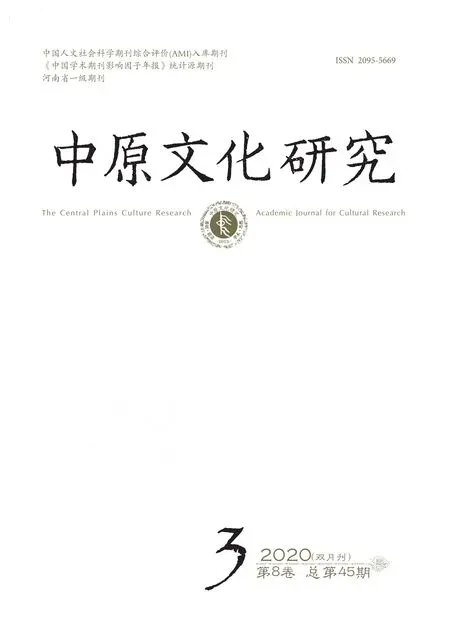明清运河区域的徽商及其社会活动研究*
郑民德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成了南北之间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通道,在满足国家漕粮供给、军事征伐、交通运输的同时,运河区域还以强大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吸引了晋商、徽商、江右、洞庭、闽等商帮的聚集。他们或在运河城市开设店铺,或以运河为转输枢纽,操奇计赢、获取利益,为运河区域市场的繁荣、商业层级的构建、市民生活的丰富、国家财库的充裕发挥了巨大作用。徽商作为明清重要的商业力量,又称徽州商人或新安商人,包括明清徽州府的歙、休宁、祁门、婺源、黟、绩溪等县商人。明清运河区域的徽商具有分布范围广、综合实力强、商儒相结合等特点。他们以运河水道作为商货物资运输的主要路径;把船只当作日常经营、出行的重要工具,南北转运博弈;并以“诚信”为经营理念,通过同乡互助、修造会馆、扶危济困等社会行为,实现了徽商个人理想与国家信念的结合。目前关于运河区域徽商的研究主要关注于某一省份徽商的经营活动及其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对整个运河区域徽商的分布规律、经营状况、社会活动尚未进行全面研究。本文拟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徽商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进一步探讨徽商在运河区域经营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时就其会馆文化、慈善文化、桑梓文化、科举文化进行分析。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徽商在运河区域的分布及商业经营
明清两朝,徽州民众经商比例之高冠绝全国,他们遍布大江南北,从事各种商货的转运与销售活动,从繁华都市到乡村僻野,从沿海地区到内陆腹地,随处可见徽商们的经营足迹,甚至形成了“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的俗语。这种全民经商的模式既是徽州当地的自然状况所导致的结果,同时也与徽商诚信经营、以商裕国的经营理念有着很大关系。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1]卷103《荒政部》,83258。可见生活与生存的压力是徽州民众外出经商的直接原因。除却“徽地多山少田”的自然环境外,悠久的经商传统与“儒商”的文化影响也是徽商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徽地号称“东南邹鲁”,自唐朝黄巢起义后,“中原衣冠避地于此,益尚文雅,宋名臣辈出,多为御史谏官者,自朱子而后为士者多,明义理之学。……读书力田,间事商贾”[2]卷1《风俗》,儒家思想成为了徽商重要的文化内核。正是靠着坚忍不拔的毅力与儒商文化的传承,至明清时期“徽商之足迹,殆将遍于国中”[3]7,而且他们实力雄厚“徽州六县客商遍天下,家家巨万”[4]卷10《艺文志》,尤其是在典当、盐业贸易上“大者千万,少亦万金,此皆有力者”[5]卷7《艺文》。作为明清商业文化最为繁荣的运河区域,尤受徽商关注,他们以北京、天津、临清、济宁、扬州、苏州、杭州等大城市作为商业经营的据点,辐射至沿河城镇与乡村,建构起了大城市、中等城市、市镇与村落的市场网络层级与体系,在运河区域形成了北至京津,南至宁绍的商业经营范围,不断强化徽商的综合实力与影响力,与其他商帮进行竞争。
(一)徽商在运河区域的分布
徽商在华北运河区域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特点①,其商业势力主要集中于运河沿线的大中型城市,其中北京的徽商多与徽籍官员、赴京士子相结合,具有官商结合的性质。他们修建会馆,一方面增强在京徽籍人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另一方面也利用桑梓之情扩大徽商在京城中的影响力,从而在与其他商帮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其他如临清、济宁等运河商埠,也是徽商的集中地,有大量的徽州商人在此经营贸易,在城市商业力量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明清经营于燕冀、齐鲁的徽商以歙县人为主,他们依赖强大的宗族凝聚力与合作共赢精神,纵横运河沿线,“徽歙以富雄江左,而豪商大贾往往挟厚赀驰千里”[6]288,歙商所居“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6]288,成为了华北运河区域重要的商业力量。
北京号称运河上“漂来的城市”,大量漕粮与商货通过京杭大运河输往北京,以满足皇室、官僚、驻军的需要,全国各地的商人也希望在京城占据一席之地,其中徽州籍商人不但在京城建有规模最大的徽宁会馆,且商业实力也不容小觑。明正德、嘉靖时歙县人王茂棨善于经营,“综理甚密,商于京浙,虽豪商大贾无不推尊,善观时变,以此赀用日饶,而基产日盛,盖亦商之杰出者矣”[7]卷4。又如吴永评“少服贾燕京,捐费助建会馆及置义冢”[8]1526,通过互助与义行以增强徽商之间的凝聚力。至嘉靖四十年(1561年)歙县诸商已在京城设置义庄,创办会馆,“隆庆中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乾隆中则茶行七家,银行业之列名捐册者十七人,茶商各字号共一百六十六家,银楼六家,小茶店数千,其时商业之盛,约略可考”[9]357。可见明清徽商在京人员数量众多,经营范围广泛,实力雄厚。其他经营于燕冀等地的徽商也不胜枚举。
山东运河区域也是徽商分布的要地,尤以临清、济宁数量最多。临清踞会通、漳卫诸河,有户部钞关与仓厂、工部砖厂与船厂,为著名商埠与码头,号称“富庶甲齐郡”[10]卷11《艺文志三·诗词》,有着吸引商人的政治、交通优势。徽商在临清诸商中占有绝对优势,据明谢肇淛《五杂俎》载“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11]289,他们长期在临清经营,甚至加入了当地户籍,融入了临清地方社会,成为了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歙县人黄文茂,“善于治生,商游清源(临清),清源北临燕赵,西接三晋,为都会地,亦多大贾。大贾人争务奢侈,公折节为俭,任人择时,以此起富。公又勤力,……赀日饶,益业日丰,大雄于齐鲁、新安间矣”[3]87。济宁为山东另一著名商埠,“正当南北要冲,人民殷富,户口繁庶,比临清更胜”[12]260,不但是明清河道总督驻地,而且交通发达,居全河中枢,南北商贾汇聚于此。徽商在济宁建有会馆,有七进院落,房间八十余间,用于日常的商业交流与生活娱乐。他们在济宁长期经营,从事诸多行业,形成了强大的商业实力,对济宁城市的市场网络与商业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临清、济宁外,张秋镇也是徽商的一处重要据点,张秋夹河为城,为明清北河工部分司衙署驻所,既是河工要地,又是商业枢纽,为“河济一都会”,镇内有南京店街,“盛时江宁、凤阳、徽州诸缎铺比屋居焉”[13]卷2《街市》,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山东运河南部城市峄县也有徽商驻足,如歙县人徐平仲“因族之商峄县者,遂起家峄”[14]卷68《礼部仪制司主事徐平仲墓志铭》。不过总体看来,明清徽商在山东运河区域的力量是弱于晋商的,德州、聊城、张秋、宁阳、汶上都有山西会馆的分布,而徽商则主要占据临清、济宁等大城市,在一般的县或镇分布不多,无法与江南地区形成的从上到下的市场网络体系相提并论。
江南地区的苏浙两省是徽商在运河区域最主要的分布地。首先,在地理位置上,徽州离江南更近,方便人员、商货的往来;其次,苏浙两省交通发达,运河畅通,加上与运河相贯通的自然河道众多,有大量的码头与港口;最后,江南地区早在唐代其经济发展程度就已超过北方,该区域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一般的市镇,其商业的规模均高于江北地区,有着吸聚商人、货物的优势。正是靠着这些便利,徽商遍布于江南地区的城市、镇集,甚至村落,“徽为富郡,商贾遍天下”[15]卷7《人物》,“徽州人以商贾为业,宏村名望族为贾于浙之杭、绍间者尤多”[16]卷15《艺文》。在淮安、扬州、苏州、杭州等运河名城,聚集了大量的徽商,成为了影响区域社会经济的重要力量。《从政录》亦载:“向来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数十户,蓄赀以七八千万计。”[17]卷2《姚司马德政图叙》扬州临长江、运河,交通发达,“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3]109,徽商对于扬州的崛起与繁荣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苏州自古繁盛,阊门为苏州门户,“上津桥去城一里许,闽、粤、徽商杂处,户口繁庶,市廛栉比,尺寸之地值几十金,筑室者争其址”[18]卷5《坊巷》,整座城市的兴旺可见一斑。杭州是徽商较早踏足的城市,“今钱塘江滨,徽商登岸之所,即谓之徽州塘也”[19]卷5《市镇》,“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20]卷2《风俗》。除京杭运河城市外,绍兴、宁波等浙东运河城市也有相当数量的徽商分布,商业影响力也很巨大。
与华北运河区域徽商主要集中于中大型城市不同,江南地区的县城、市镇受到大城市商业的辐射,同时自身经济也很发达,也是徽商重要的商业据点,其建构起了大小结合、层次清晰、相互影响的市场网络体系。如苏州府嘉定县南翔镇“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21]卷1《市镇》。嘉兴府平湖县新带镇“有中市、东市、西市,有花街,有上塘、下塘,饶鱼米、花布之属,徽商麇至”[22]卷1《舆地四·都会》。杭州府于潜县“铺路左达杭湖,右通徽歙,商旅往来,络绎不绝”[23]卷1《铺站》,塘栖镇“去武林关四十五里,长河之水一环汇焉。东至崇德五十四里,俱一水直达,而镇居其中,官舫、运艘、商旅之舶,日夜联络不绝,屹然巨镇也,财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24]卷18《风俗》。江南市镇兴盛的推动力除拥有交通方面的优势外,自身经济力量的雄厚及不同产业的合理布局,也是吸纳各地商帮、商货集聚的重要因素。
(二)徽商在运河区域的商业经营
在中国古代社会,盐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为官营物品,属国家财政收入重要组成部分,徽商能够取得盐的经销权,除其官方背景强大外,还与其雄厚的实力密不可分。徽商盐业活动的主要区域在淮扬一带,属两淮盐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食盐产区之一,大量食盐通过运河与长江水道销往两湖、安徽、江苏、江西等地。明嘉靖年间商人分为边商、内商、水商,其中内商“多徽歙及山陕之寓籍淮扬者,专买边引,下场支盐,过桥坝,上堆候掣,亦官为定盐价,以转卖于水商”[25]卷11《盐法志上》。万历《歙志》也载“邑中以盐策、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递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者”[26]卷10《货殖》。可见徽商在两淮盐业中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属执牛耳者。著名的盐业商人如:歙人黄五保“挟赀治鹾淮阴间,善察盈缩,与时低昂,以累奇赢致饶裕”[3]110;休宁人汪福光“贾盐于江淮间,艘至千只,率子弟贸易往来,如履平地,择人任时,恒得上算,用是赀至巨万”[3]118。诸多徽商凭借着精明的商业头脑,加上长期商业经验的积累,成为了淮扬盐业的操控者。不过随着清代中后期运河的淤塞、战乱的频兴,两淮徽商的盐业经营也陷入了困境,“徽、西大商,昔日数百万之赀者,今无一人,百计招徕,小商仅足应课,又为积残滞引,侵占新纲,故完课不能如额,此商之绌也”[27]《文后集》卷8《赠汪孟慈序》,“乃纲盐改票,昔之甲旅夷为编氓,漕运改途,昔之之巨商去而他适,百事罢废,生计萧然”[28]卷1《疆域·风俗·物产》,可见传统漕运的衰落对盐业也产生了巨大冲击。
明清饮茶之风盛行,徽商中有大量人员从事茶叶贸易,同时徽地的黄山、六安、祁门、霍山等地也盛产名茶,从而为茶的运销提供了地利之便。徽商贩茶路途遥远,“歙之巨业商盐而外,惟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3]171,其中运河区域的北京、临清、济宁等地均为较大的茶叶转销枢纽。至清乾隆间,徽州茶商聚集京城者有一百六十六家,小茶店不计其数,在京城茶叶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临清、济宁两地位居运河中枢,商贩云集,大量安徽茶商在两地或设店经营,或以此为转运枢纽,通过水路销茶至河北、京津等地,甚至有远销至口外者。
明清运河区域的布业市场也很兴盛,临清有大量徽州布商,他们不但经营贸易,而且积极参与公共事业,如从事临清布业的徽商王道济曾参与修建舍利塔。另一城市无锡盛产布匹,“坐贾收之,捆帮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尝有徽人言,汉口为船码头,镇江为银码头,无锡为布码头”[29]卷1《备参上》。无锡与淮安、扬州、高邮、宝应等地以运河相贯通,布匹通过水道运输不但省时省力,而且这些区域人口密集、商业发达,对于布匹的需求量巨大。新安汪氏设布店于苏州,巧为居奇,“用者竞市,计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30]80,积累了巨额财富。
明清徽商从事典当行业的人员众多,万历时河南巡抚沈季文曾言“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赀数千金”[31]卷434,万历三十五年六月丁酉条,“典商大多休宁人,……治典者亦惟休称能,凡典肆无不有休人者,以专业易精也”[3]155。运河区域作为商贾云集、人烟辐辏之处,对于金钱的需求甚于别处,加之货物交易需要资本支撑,所以典当行业异常兴盛。休宁人孙从理在浙江吴兴县经营典当业,“什一取赢,矜取予必以道,以质及门者,踵相及,趋之也如从流”[32]卷52《南石孙处士墓志铭》,汪栋治典业于吴江县平望镇“典业则择贤能者委之,因材授事,咸得其宜”[3]163。嘉兴为江南富地,赋多役繁,居南北孔道,“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又以田农为拙业,每以质库居积自润,产无多田”[33]卷22《艺文志》,临清“两省典当,旧有百余家,皆徽浙人为之”[34]卷11《市廛志》。其他如北京、扬州、泰州、苏州等运河城市也有着大量徽州典当商人,他们几乎垄断了部分运河城市的金融市场,在当地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木材业也是徽商从事的重要行业,从业者多来自婺源,“徽多木商,贩自川广,集于江宁之上河,资本非巨万不可。……然皆婺人,近惟歙北乡村,偶有托业者,不若婺之盛也”[3]179。早在明永乐年间,徽州、处州两地商人就已通过运河贩运木材。徽商所贩木材除来自川、广等边远省份外,徽州本土也出产良材,休宁“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35]卷1《风俗》,“徽处万山中,每年木商于冬时砍倒,候至五六月,梅水泛涨,出浙江者,由严州;出江南者,由绩溪顺流而下,为力甚易”[36]906,所贩木材除作为建筑材料外,还经常用来修造漕船。通过以京杭大运河为枢纽的水路贩运木材,不但省时省力,而且直达著名商埠杭州、苏州、南京、扬州、淮安等地,无论对于当地公共设施建设,还是国家漕船修造,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上述经营的主要行业外,徽商足迹遍天下,在粮食业、刻书业、颜料业、锻造业、陶瓷业、药材业等行业也屡有建树,他们以大运河、官道作为交通线路,以车船作为交通工具,将不同区域的货物贩销到全国市场,一方面促进了人口、经济、文化的流动,刺激了城市的崛起与市场网络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也使徽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运河区域独擅其美,成为了影响国家与区域社会经济的重要商业群体。
(三)运河区域的徽商会馆
商业会馆是同省商帮、商人联系的纽带,也是商业经营群体在实体建筑上的标志与符号。徽商在运河区域的重要节点城市建有大量的会馆,这些会馆不但是商人聚会、娱乐的公共空间,对于增进乡情、乡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商业交流的重要场所。
4)经验总结。根据枝条强弱,使用不同的稀释倍数处理。对于强枝条,土壤持水量高,空气湿度大,在果粒增大处理时,每10 mL吡效隆对水 9.5~10 kg;中等枝条,每 10 mL吡效隆对水8~8.5 kg;弱枝条,每10 mL吡效隆对水7.5~8 kg处理。
江北地区徽商会馆主要集中于北京、天津、济宁等运河重镇。如清代李虹若《都市丛载》载,北京有徽籍会馆二十余所,其中安徽会馆在琉璃厂南后孙公园路北、徽州会馆在前门外繇儿胡同、歙县会馆两所在宣武门大街路西与南半截胡同、黟县会馆在南半截胡同、绩溪会馆在椿树头条胡同路北、休宁会馆两所在绳匠胡同路西与长巷上四条胡同、婺源会馆两所在石猴街路西与大耳胡同路南[37]卷3《安徽》,其他还有庐州会馆、颍州会馆、泾县会馆、旌德会馆、太平会馆等,分布于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这些会馆既有商人商业会馆,也有供赴京考试徽籍学子食宿的会馆,甚至某些会馆有着综合性的功能与作用,常有达官贵人在此聚会宴饮。天津也有安徽会馆,位于李公祠旁。济宁徽商云集,亦建有会馆,房屋八十余间。
江苏运河区域商业发达,徽商数量众多,会馆分布也最为广泛。苏州有安徽、江西、广东、岭南、新安、宝安、潮州、浙宁等会馆二十余处,其中安徽会馆在南显子巷,新安会馆在五图义慈巷东[38]卷30《舆地考·公署三》。江都县有徽国文公祠,又名徽州府六邑公馆。徽国公朱熹被徽州诸商视为乡土神,在异地经商时,为朱熹塑像并祭祀,一方面可以利用其号召力,树立徽商“儒商”的形象,增强文化上的感染力;另一方面对于团结人心,以桑梓之情作为联系纽带,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建于清嘉庆年间,有正殿三间,分供协天大帝关羽、忠烈王汪公大帝、东平王张公大帝,同时建有殡舍、义冢、行馆、驳岸,购有公置田产,“会馆自创始以来,暨堂中一切公需资费较巨,皆赖同乡竭力襄助”[39]355-357。浙江杭州柴垛桥有安徽会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为旅浙全皖高等小学,从会馆改制为新式学堂,为徽籍子弟接受新式教育提供了场所与经费[40]卷17《学校四》。乌程县朱文公祠在眺谷铺,“乾隆二十八年徽人汪堂巴、钟灏、戴永标等建,名新安乡祠,余屋为徽州会馆”[41]卷40《祀典》,在这里乡祠与会馆合为一体,更增强了乡土文化的凝聚力。
明清运河区域的徽商会馆在分布数量上江苏最多,浙江、北京次之,山东再次之,天津、河北较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商业的发展程度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与地理上距离的长短也密不可分。江苏运河畅通、商埠数量众多,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徽商前来经营,浙江距徽州较近,有水路相通,所以也是徽商的重要聚集地。而北京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有着广阔的市场,自然吸引着徽商的注意力。山东、天津、河北等运河区域虽然也有着较为发达的商业城镇,但在密集程度、商品的专业分工上不如江浙地区,同时这些省份晋商的实力超过徽商,所以徽商会馆的数量不多。
二、徽商与运河区域社会的互动
明清时期徽商之所以能够立足运河区域,除精明的商业头脑外,还与其积极融入地方社会、投身公益事业有着密切关系。通过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徽商树立了良好的商业形象,赢得了土著百姓的承认与接纳,从而为商业规模的扩大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们修建庙宇、桥梁、公共墓地等,并以赈灾、入籍等方式,获得了当地政府与群众的认可,使徽商“好义”“仁德”“为公”的形象深入人心,为扎根运河区域、增强商业影响力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第一,徽商在运河区域修建了大量的寺庙,满足了信教群众的精神需求。庙宇、寺观在中国古代社会属重要的公共空间,对于人群的思想有着重要影响。徽商通过修建寺庙建筑,一方面将自己获得的部分利润回馈运河区域社会,得到了当地百姓的认同与肯定;另一方面通过自身信仰与区域社会信仰的结合,强化了信仰的共同体,使文化的认同感得到了提升,减轻了商人重利轻义的传统形象。如乌程县有报恩光孝观,始建于梁代,后渐废,“万历四十七年徽商吴维祯、方嘉礼重修,俗名小宫”[42]卷8《观》。又如如皋县雨香庵,“今为徽商会馆,内奉关圣帝君,国朝康熙十八年吴公达始、黄元灿、汪之珩等捐田祭祀”[43]卷3《建置》。盱眙县三元宫在县治西南,“徽、苏各商建”[44]卷11《古迹》。仪征县有两座昆庐庵,“一在八字桥南,一在西门外老虎山左米市,徽籍典商吴永隆建,后渐倾圮。乾隆丙子岁,曾孙志高继葺,规制重新”[45]卷2《建置》,吴氏世代经商于仪征,甚至在公益事业上都具有延续性,体现了徽商与运河区域社会关系的密切。
第二,热衷于运河区域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以修桥、铺路、筑堤、置闸、建仓的方式,便利民众,造福乡里。古代公共设施因耗资巨大,资金多源于官府与地方精英人士的筹资,普通百姓难以承担大型工程的资金投入。面对困境,徽商以大量公共工程设施的修建作为融入地方社会的手段。歙人汪应庚营盐业于扬州,“居家素丰,好施与,如煮赈、施药、修文庙、资助贫生、赞襄育儿、激扬节烈、建造船桥、济行旅、拯覆溺之类,动以十数万计”[46]372-373。吴江县有饮马桥,明洪武年间里人陆仲和建,“国朝康熙三十三年徽商程栋重建”[47]卷6《桥梁》。临清通济善桥,由徽商汪保所建,“侨寓清源,乐善好施,兹桥其所建也。桥当鳌头矶之东,往来充斥”[47]卷6《桥梁》。徽商吴瀛,实力雄厚,面对嘉兴财力匮乏、民生凋敝的现状,“造便民仓三十间,以宽民力”[33]卷11《官师》。休宁人姚柱于高邮经商,“议筑堤,因水涝易砖以石,岁久不圮,遂成沃壤,邮人尸祝之”[49]卷6《人物》。
第三,扶危济困凸显“义商”形象。作为常年奔波于运河区域的徽商,在经商途中经常遇到突发的危难、紧急事件,他们不顾自身安危,以“义”为先,进行救助与帮扶。在兵燹、灾荒时节,他们又施钱、施棺、放粮,收纳灾民、赈济穷黎,使徽商“善”的文化辐射于运河区域。明万历年间,某徽商过九江,“见江干有舟被劫,舟中人群裸号泣,商泊而救焉,内有孝廉七人,各给衣食,且赠路资以去”[33]卷17《果报》,这种见义勇为、见义必为的精神,对于徽商整体形象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赈灾也是徽商与区域社会互动的重要表现之一。万历年间大灾,歙人毕懋尝贾于浙江杭州府于潜县,“睹饥馁状,心矜之,有持质丐米者,倍所予,不责其偿,日给数千人”[50]卷9《人物》,赈济了大量灾民,助他们渡过了难关。崇祯时松江府大饥,歙人吴邦瞻贩麦经此,“见之恻然,尽以舟麦散饥人,人各给一斗,得延旬日以待食新,所活无算”[3]319。顺治年间常州大水,他又治粥以活灾民。在战乱、兵燹时接济难民,也体现了徽商的仁义之心。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婺源人程开纯避难苏州,“所识穷乏者,必款留之,晨起炊米,非数斗不能周给,或曰‘尔独不自为计乎?'笑曰:‘贼至,身且不保,遑他顾耶!'生平济人急,无德色;许人言,无宿诺”[51]卷34《人物》,为乡里所赞。
第四,通过“入籍”的方式,将“他乡”变“故乡”,彻底融入当地社会。诸多的徽商常年,甚至累世经营于运河区域,早已熟悉了当地的生活与民风习俗,同时这里是他们产业的根基所在,加上在此通婚、科举,再也无法返回故乡,逐渐融入了当地社会。山东临清为徽商重要聚集地,由于长时期在此居住、经营,所以大量徽商入籍临清,成为了临清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扬州为运河名城,“多寓公,久而占籍遂为土人,而以徽人之来为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汪、程、江、洪诸姓皆徽人流寓而占籍者也,故丧祭有徽礼、扬礼之殊,而食物中如徽面、徽饼、徽包,至今犹以徽为名”[52]卷30《杂录》,大量徽商在扬州定居,影响了区域社会的风俗与饮食习惯。
总之,徽商作为明清时期重要的商业力量,其商业形象的塑造和树立除了与其艰苦创业、诚信经营、勤俭务实的经商作风密不可分外,还在于其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通过与运河区域社会的良性互动,将徽商“仁”“善”“义”的美好品德进行传播,并使这一形象不断扩张与辐射,在无形中提高了徽商的地位,增强了商业竞争力。同时,运河区域徽商的公益投资具有自身的特点,那就是修建桥梁、闸坝、堤岸的比例较高,运河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与其相关的水利设施数量众多,运河区域徽商经商的重要工具也为船只,所以通过大量水利设施的修建,一方面便利了自身与民众的通行,另一方面对于提升徽商商业品牌,塑造良好的商业形象也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徽商的同乡互助与重儒情结
徽商作为明清全国性的商业群体,其商业影响力辐射于整个运河区域。作为异地经商者,为增强商业竞争力、提高同省商人的归属感,他们经常互帮互助,相互扶持,以“抱团”经营的模式,与经商区域的社会进行合作或对抗,以此维护徽商群体的利益。同时,作为“东南邹鲁”的徽州,科举文化始终影响着徽州商人,他们在秉持“诚信经营”的道德理念外,还将儒家的诸多观念渗透到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中,如喜好读书,积极入仕。这种情况说明在明清传统社会中,徽商更多的是将商业经营作为一种谋生与积累财富的手段,而通过科举实现人生价值的提升则是根本目的。
徽商在运河区域的互帮互助,在生与死两个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晰。徽商作为远离故土的群体,有着很深的乡土情结,尤其是在异地遭遇挫折、困难时,他们就会通过同乡互助的方式寻求解决之道,而这种互助在面临生存、死亡的时候体现得尤为明显。徽地宗族观念浓厚,“家乡故旧,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所在村落,家构祠宇,岁时俎豆”[53]卷2《风俗》。这种敬宗收族,重桑梓之谊的传统不但在徽州本地延续,而且也在异地经商区域得到了传播。徽商在外经商,最重乡情,“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己身地也。近江右出外,亦多效之”[54]卷2《两都》,通过团结一致,强化徽商在经营地的力量。婺源人王悠经商于苏杭之间,积有余金,邻乡潘某“贷四百金商于苏,未几亏蚀,竟不欲归。悠复贷之银两,俾归里。又闻归后迫债成疾,造其门取券焚之”[51]卷33《人物》。歙人汪朔周亦治盐业于江都,“党中有急难,解推不少吝”[55]卷32《人物》。对困境中的同乡商人施以援手,救助其于危难之中,体现了徽商的互助精神。
除日常的困境扶持与接济外,面对死亡时,在心灵悲痛之余,徽商们更多的是希望在遥远的异地能有一个归葬的场所,从而使灵魂得到安息,而在墓地的选择上,徽商除正常购买外,其土地的获得也并非一帆风顺。娄县有新安义园在谷阳门外护龙桥北,“徽人之商贾力作于松江者众,病故后,旅榇所在暴露,程师义、查家驹、汪绳蕙、黄楚珍、黄德达、程诗嘉募建是所,停厝掩盖,集有公款,存典生息,咸丰年间司事程礼智将公款置田一百七十余亩,以期久远”[56]卷2《建置》,义园用以埋葬在异地去世的徽州客商,并有专人管理相关款项,通过存典、置田等方式,以保障资金的延续与积累。杭州是徽商的聚集地之一,万历年间有大量徽商购置土地,引起了当地民众的不满,“南北二山风气盘结,实城廊之护龙,百万居民坟墓之所在也。往时徽商无在此图葬地者,迩来冒籍占产,巧生盗心,或毁人之护沙,或断人之来脉,至于涉讼群起。……罪同杀人而恶深掘冢矣。隆庆六年有士民傅成等呈鸣上司,严行禁约,不许奸商越占坟山”[57]卷19《风俗》。因为坟地的占有关系,徽商与杭州土著民众产生了大量纠纷与矛盾,其核心就在于土地产权与葬地的归属问题。北京有歙县义庄,位于永定门外石榴庄,“旧名下马社,规制甚宏,厅事高敞,周垣缭之,丛冢殆六七千,累累相次”[9]357。在北京长期经营的徽商,很多死后葬于此地,形成了大规模的墓园,从本质上讲是徽商利用集体力量,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长期购置土地形成的结果。
虽然徽州经商人员众多,但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贾而好儒”,力求仕进。在中国古代社会,“士农工商”等级森严,商人往往被其他社会群体所轻视,而在徽州区域社会则有所差异。徽州地狭,“民不容居,故逐末以外食,商之外富,民之内贫也”[58]卷154《徽守南侯复役记》,“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20]卷8《蠲赈》,可见徽人外出经商与其贫瘠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随着经商人群的不断扩大,经商之气蔚然成风,形成了“徽之俗重商而贱农工,有志者生其间,不为士则为商,商而能尽商之职”的风俗[59]卷7《东泉金处士传》。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读书入仕的地位依然超过经商,从事商业经营是很多徽人读书而未有成就后不得已的做法。如婺源“吾邑习俗每喜远商异地,岂果轻弃其乡哉!亦以山多田寡,耕种为难,而苦志读书者又不可多得”[3]53,“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驰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乃为子孙计,宁驰贾而张儒”[3]438。像休宁人陈祖相就“七岁能书,十岁能文,壮志不遂,乃事贾”[60]卷3。这种因读书未成而从商的例子还有很多,说明在徽人眼中,“士”的地位还是高于“商”的。如果说外出经商是因为自然环境与生计所迫,那么读书与好儒,则源自徽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新安为朱子阙里,而儒风独茂,岂非得诸私淑者深欤”[61]卷3《硕行》,“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62]3,可见徽州好儒之风与这一地域长期受朱子理学的影响密不可分。而外出经商的徽州人,带有明显的“儒商”性质,经商闲暇时读书,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如歙人方宏基,“占临清籍,生而整肃,知读书即以圣贤为己任,弱冠为诸生食廪,学问渊博,驰骋于韩苏诸大家”[63]卷8 上《人物》,休宁汪志德“年十五能服父劳事,贾江湖,有倜傥之才,所谋所施,绰有大过人者,人不敢以年少目之。虽寄迹于商,尤潜心于学问无虚日,琴棋书画不离左右,尤熟于经鉴,凡言古今治乱得失,能历历如指诸掌”[64]卷42《行状》。而诸多经商有成就者,也激励子孙弃商从儒,“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着。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宏儒,则其躬行彰彰矣。临河程次公升、槐塘程次公与,与先司马并以盐策贾浙东西,命诸子姓悉归儒”[3]485。以经商而富家,积累财富后,让子孙读书仕进而光耀门楣,是诸多徽商经营的最终目的。
明清时期运河区域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集聚了大量的商人、商货,徽商作为其中重要的力量,其之所以能够立足运河沿岸城市,是与互帮互助的桑梓文化、团结一致的宗族观念、合作共赢的商业精神分不开的,靠着这些商业文化的支持,加上徽商的诚信经营、勤于商事,才使徽商的品牌与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了运河区域的著名商业力量。而“贾而好儒”则是徽州“东南邹鲁”乡土文化的外在体现,无论是经商途中儒家文化的发扬,还是勉励子孙读书入仕,这说明在徽州“重商”的外表下,商业经营获得利益只是维持较好生活的物质基础,而最根本的目的则是通过“好儒”而进入权力阶层,从而实现家族荣誉与人生理想的双重辉煌。
结 语
明清两朝,徽商在运河区域数百年的经营,一方面积聚了巨额的财富,成为全国著名的商业力量;另一方面也影响了运河区域城市的兴衰、市场的建构、国家物资的需求。徽商的崛起,除得益于其从商人员众多、实力雄厚、官方扶持外,还与其艰苦创业、诚信经营的商业理念密不可分,通过多种经营,转运南北,互助合作,徽商在运河区域站稳了脚跟,并且在与其他商帮的竞争中逐渐占据了优势,他们通过运河水路贩运商货,辗转于北京、临清、扬州、杭州等大城市,甚至连江南部分市镇也是他们重要的经营场所,正是靠着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徽商形成了著名的商业品牌。而正确的义利观及对经商所在地的利益回馈,加上大量慈善工作的进行,使徽商在经营地树立了良好的影响,被当地民众所接纳,逐渐融入了运河沿线社会。而“贾而好儒”与“力求仕进”则是徽商商业理念的继续与延伸,即经商除满足生存、生活外,还可以为子孙后代科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实现身份与地位的飞跃,进入传统社会中的权力阶层,实现人生理想与社会价值。
注释
①传统意义上的华北运河区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四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