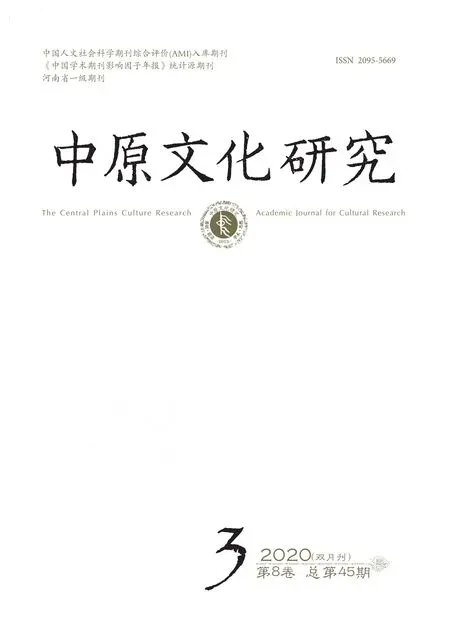宋代植物崇拜中的神秘感应与神话传说
郭幼为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其所著的《原始思维》中开篇便解释了一种被称为“集体表象”的观念形态,即它是世代相传的,且使集体之中的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某种感情[1]5。加注了特征的“集体表象”还是让人觉得似懂非懂。奥地利心理学家G·贾霍达便直言这种集体表象“或多或少类似于今天的‘文化'”[2]175注释。而结合美国人类学家威廉·A·哈维兰对文化所下的言简意赅的定义则可证明贾霍达的解释不虚,“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为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如果文化能够保证社会的延存并合理满足其成员的需求,那么它就可称为是成功的”[3]242,261-262。中国古时先民在驯化植物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情感、观念意识便有上述集体表象的影子①。先民们很早便通过植物的忽生或变异来揣度天意,预测吉凶;但吉凶不定,未来不可测,加之植物变异后千奇百怪的形状使得认识水平还很有限的先民往往以“草妖”“木怪”来笼统解释其中的奥秘。到了宋朝,万紫千红的花卉、千奇百怪的树木在时人的精神世界里仍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记。但也要看到这种植物崇拜的信仰传承之中亦有裂变。王利华曾认为:“人类适应生态环境、利用自然资源,是以一定的经验知识和思想态度为基础的。”而这些经验知识和思想态度构成了古代的“生态认知系统”,该系统包括了“实用理性认知”“神话宗教认知”“道德伦理认知”和“诗性审美认知”等四个主要认知方式[4]381-382。宋人驯化植物过程中所形成的植物崇拜或可归为“神话宗教认知”范畴②。对这种认知进行解读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宋代民间社会,而且对了解宋人的精神世界,从而窥视自然事物之于古人的文化烙印也有助益。
一、宋人与植物的交互影响
宋代笔记小说《墨客挥犀》中有一则故事,大意是:寇准迭遭贬黜,后死于海康,朝廷诏许榇还洛阳。当寇准的棺椁路过公安县时,当地人自发送葬,以竹插地,挂物为祭。孰料竹无根而茂,百姓以为神,立庙于侧,祀奉甚谨[5]5。该故事也先后被《类说》《竹谱祥录》《倦游杂录》《青琐高议》《渑水燕谈录》《麈史》节引以及被时人刘敞、王陶“各为文刻石志其事”[6]1366。可见该故事在当时的影响较大。更为重要的是,“立庙于侧,祀奉甚谨”的公安县百姓相信上天的旨意会通过世间万物的变异或反常来昭示。这反映了宋民赋予植物以生命,让具有人格的植物替己立言,来表达自身的价值取向和是非观念。
陈涛曾以牡丹为例,推测人工栽培牡丹出现的大致时间,得出“唐代是栽培牡丹发展的关键时期,宋代是牡丹栽培技术体系发展的完备阶段”[7]。事实上,宋时以牡丹为代表的观赏类植物开始进入种植的繁盛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独立的种植行业[8]。当时的花卉种植技术日益精湛,花匠对培育、嫁接等技术已驾轻就熟;品种渐趋增多,一些名贵花卉如牡丹、菊花之类品种已达百余种。品种的日新月异带来的是花卉数量的与日俱增,动以亩计的种植面积在一些花卉主产区已屡见不鲜[9]15,18。观赏类植物的大面积种植使得像牡丹、芍药等草、木本植物广泛地进入人们的生活,对时人的思想观念亦产生影响。
观赏类植物品种的日趋多样,使得宋人有底气对其进行优劣划分,宋人龚明之便将花喻作客,贵客、清客与佞客、恶客之分亦能看出植物在时人心中已有好坏之别[10]240。人世间,芸芸众生有优劣之分,所以古人认为植物的大千世界里也讲究尊卑顺序。邱濬将牡丹的各个品种按后宫嫔妃等级进行排序,撰成《牡丹荣辱志》[9]9-14。人有七情六欲,爱恨情仇。先民们认为植物亦具有爱憎之情绪。宋人张功甫在《玉照堂梅品》中便为读者勾勒了一枝爱憎分明的梅花[11]5617-5618。无独有偶,邱濬在《牡丹荣辱志》中亦描述了泾渭分明的牡丹花[9]13-14。
具有人格的植物亦为宋人鸣冤叫屈。如前述寇准的故事,《青琐高议》便记录了其他版本[12]1030-1031。该版本虽与实际不符,但既然能被士人记录在册,想必流传甚广。在这个杜撰的故事中,竹子变成了昭雪洗冤的关键。而南宋洪迈所记亦是对之前流传故事的改良[13]3041-3042[14]364-365。说的是有一个孝敬老人的儿媳却遭人诬陷下狱,屈打成招后秋后问斩,行刑之时将簪在髻上的石榴花交于行刑者,令其为她取此花插坡上石缝中,指天立誓,“我实不杀姑,天若监之,愿使花成树。我若有罪,则花即日萎死”。后石榴花“已生新叶,遂成树,高三尺许,至今每岁结实”[15]647,为妇洗刷了冤屈。此故事随时代的变迁被加入了植物的元素,却演绎出相同的结果,表达不同朝代中人们相似的是非观念。
二、宋代植物的神秘感应
布留尔将“‘原始'思维所特有的支配这些表象的关联和前关联的原则叫做‘互渗律'”[1]69。马伯英先生也详细解释了上述“互渗律”的概念[16]44。何裕民等则更进一步,认为布留尔的“互渗”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感应相类同[17]19。本文特采用何氏所解,即将互渗与感应相类同。纵观宋代史料,就有许多植物感应的记载。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完整记录了史上有名的“四相簪花”。该典故被宋代典籍《后山谈丛》《清波杂志》《墨客挥犀》《丞相魏公谭训》《西畲琐录》等转录,可见影响深远。故事中“芍药一干,分四岐,岐各一花,”与《宋书·符瑞志》中“芙蓉二花一蒂”等较为相似[18]834-836,均显符瑞之像,所以也就有了韩琦(魏国公)“开一会,欲招四客以赏之,以应四花之瑞”的雅事[19]241。该典故也反映了当时士人阶层借花卉的变异来对未来命运予以美好期许,反映出该阶层追求富贵的期盼和封侯拜相的愿望。事实上,宋人将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等诸种期许渗透在植物的变异之中。上层统治者也自然是将四海升平、皇权永固孕育在植物世界的特殊变化之中。《宋史·五行志》中此类记述不绝如缕[20]1415,1416,1417,宋人笔记小说中亦有不少记载[21]399[22]1848[23]5[24]240。在宋时植物变异引来嘉祥的记录中,士人的价值观表达的也最为充分。士人多借池中“莲生花双头”[15]738-739“松颠生二毬”[15]270等植物变异来表达科举中第的美好愿望。当然,士人更希望到更大的舞台一展宏图,所以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也就成了士人价值取向中的不二之选,也就有了:地中忽生莲,后莲生不已,遂成大池,芡荷甚茂,“入 为 大理评事”[25]183;杏树之上忽开蔷薇花,一年之间,“四迁轶”[26]4122;梅接桃枝,无水自繁,“有闺门之戚”“明年为淮漕”[15]627。
上述故事中的主人公,其心理行为是今天大加挞伐的迷信心理,但正如贾霍达所言:“迷信的信仰和行为是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无意识心理过程中,并且都认为迷信不是一种昔日的事物,或仅限于受较少教育的人们之中——它事实上被看作每个人心理构造的一部分,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很容易浮在表面。”[2]122迷信也可算作一种心理行为,是时人“无意识深层结构中透露出来的文化意识和因由”[27]序言2。此类社会心理行为不是即兴而发,而是经历上千年形成的趋吉避凶观念印刻在时人的头脑中所形成的某种触发机制,在某一时间点受某物(比如某类植物的忽生、变异等)的触动而开启。
三、宋代植物的神话传说
宋人王巩在《闻见近录》中录有千年树精显身拜谒吕洞宾的桥段[28]21。该故事在宋人范致明的《岳阳风土记》中也能见到,只不过范氏又加入了树精求丹、洞宾赐诗的桥段,也就有了“旧松枯槁,今复郁茂,得非丹饵之力邪”的猜想。到了南宋,洪迈又在此基础上为该故事编撰续集,让吕洞宾故地重游,造福人间[15]1415。当然,树精不可见,但“惟有千年老树精,分明知是神仙过”的题壁诗确实存在过[29]80[30]336。至于题壁诗的作者究竟是不是吕洞宾,已无从考证,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的作者见参天古松而想到树神,这种联想或是受泛灵信仰的影响③。关于树神崇拜,林惠祥在其所著《文化人类学》中便有一些介绍[31]293。这种包括植物在内的万物有灵经草妖、木怪等观念的渲染渐渐向精怪方向发展。先民对树神敬畏与崇拜的观念源远流长,乌丙安先生说:“在植物中最直接的崇拜主要表现在对森林、树木崇拜方面最为突出,其次是花草、谷物崇拜。”[32]91王子今先生也发现秦汉民间对社树的崇拜,使树木“兼有宗教的权威和宗法的权威的意义”[33]358。魏晋时期树神的人格化更加明显,出现了能兴风雨的树神黄祖[34]。唐时人们对森林神的崇拜通常是和山神崇拜结合在一起称为山林神。而纵览宋人玄怪小说中关于树神的记载,其人格化形象更为明显,年寿长久的树木多被塑造为老者形象④。既然是老者,慈眉善目、脾气温和是其示人的一贯形象,他们对于人类的初次冒犯还是讲究先礼后兵,往往先是托梦晓以利害,希望人类能够幡然悔悟、迷途知返[15]2,154,234-235。若人不听劝阻,一意孤行,则会触怒树神,招致血光之灾[15]578-579,938-939,1529[35]187[36]158。从托梦求救、促人悔悟到树颜震怒、降灾于人,宋人不吝笔墨、近乎重复的记录关于树神的传说,其目的或是想向世人灌输因果轮回、生死报应的禁忌观念。树神于此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信仰世界为爱惜树木、禁止乱伐筑起了一座道德大闸⑤。
与树神出现的时间相似,木怪在秦汉时期已有记录。王子今先生说,秦汉时期被大量记录于史册的木妖跟农耕社会关系密切[33]357-369。魏晋南北朝时期,木怪植物崇拜向精怪化方向发展,出现许多动物化树木精怪[37]。唐以后人格化的树木精怪成为主体。唐人诗文笔记小说中有诸如“杨树精”“橘树精”“松树精”“柳树精”等树精木怪的记录。宋代以沙木、杉木、桐树、槐树、皂角、杨树等为原型的沙木怪[38]160、杉木怪[15]305、桐郎[15]421、槐树精[15]1312、皂角鬼[15]1756-1757、杨树精[15]1804等也大量活跃在宋人的笔记小说中。而以草本植物为原型的花妖、草怪出现的时间较晚,约在唐以后才大量出现。唐时有杨花、李花等“众花精”以及蓬蔓等草怪[39]。宋时亦有酴醾妖[35]187、芭蕉精[15]152、红梅仙[15]374、玫瑰鬼[15]774、菊花仙[15]1572-1573等花妖与草精。
关于神话,一些人类学家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一些解释[3]530[31]340[40]17。这些神话的定义虽略有不同,但都在说明神话是在为现实服务,“以各种方式说明了该社会的行为道德准则”[3]523。结合神话的社会功能,可以看到披上神话传说外衣的宋代植物被附着了更多的社会属性,反映了该时社会的一些情况。首先,植物的神鬼化有了明显的性别归属,树神因其法力高强而多具男性的阳刚之气,而鬼怪尤其是花草精多怀女性的阴柔之姿,法力几乎为零,这与古时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社会观念以及宋代较为重视“男女之别”的伦常规范有关。其次,植物的神、人、鬼之间,按照能量大小已现强弱之分,神仍居首位,与其他领域的诸神地位相似,植物的鬼怪在与人的角力中全面落于下风,即使做些魅惑凡人的勾当,也被人伐树除根,轻取性命,可见宋人普遍认为精怪一般没有强鬼那样可怕,“往往是正面应对或采取某些禳除方法即可战而胜之”[41]264。最后,前文所举的十余种精怪,有近一半事例发生在伦理场域中,如因贪色而亡的杨树精、魅惑少女的桐郎、以色诱人的酴醾妖、玫瑰鬼、芭蕉精等。事实上,鬼怪本就是阴暗的代名词,所干勾当令人不齿,人与鬼怪发生的男欢女爱也定是不伦。所以无论是男人心猿意马,还是女人寂寞难耐,偷食禁果的下场便是惙然疲痿甚至一命呜呼。说明宋代国家为维护家庭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对各阶层民众的性越轨行为进行了规范[42]。
四、宋代植物崇拜的传承与罅隙
植物崇拜的对象虽时有增减,但其观念的支撑却是一以贯之,即多将植物的变异与妖、怪相勾连。先秦时期就有人将植物的忽生归为妖的范畴[43]卷三100,汉时亦有将植物的更生与变形定义为木怪的记载[13]1319,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晋书》《南齐书》《宋书》中的五行志都会专列一卷详记木怪或草妖。进入中古以后此类记录更多,王永平就详列史料说明类似“草妖”“木怪”在唐代非常普遍。到了宋朝,时人多用“地反物为妖”来作为论断的结语,如北宋欧阳修便以牡丹为例,解释了自然物成灾和变妖的区别,而花卉变异显然属于后者,“凡物不常有而为害乎人者曰灾,不常有而徒可怪骇不为害者曰妖。语曰‘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此亦草木之妖,而万物之一怪也”[9]3。南宋时,陆游也在描述“数百房,皆并蒂”的百合花后也发出“乃知草木之妖,无世无之”的感叹[44]3479。
先秦时期形成的草妖、木怪观念在宋朝继续影响着时人的吉凶观念。但其中也出现了质疑的人群,孔平仲以唐朝事例验证“祥瑞之不可凭也”[45]250,周密则举当朝事例亦在告诫“世有喜言祥瑞之人,观此亦可以少悟矣”[46]5505。而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人为的假造祥瑞则让时人进一步看清此类吉凶是无中生有的虚造。似成“万宋年岁”[20]卷六十五1417“天太下赵”[20]卷六十五1418“上天大国”[19]160字样的木连理被屡次记录应是受宋真宗时期伪造天书、大兴祥瑞的影响[47],以此来寻求统治的合法性。这种做法亦被南宋上层统治者拿来粉饰太平[20]卷六十五1417-1418。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人揣度君意假借植物的奇特现象,投君所好、寓意嘉祥,只不过碰上不以其为祥瑞的宋仁宗,并遭其训斥[48]4604。更有人伪造祥瑞,自造蟾芝,落得欺君罔上,贬官放逐的下场[49]5131。媚上的伪造、虚假的祥兆使崇拜的幻象破灭。
在古代,人们的认识水平较低,对自然的认识往往求助于神人(巫术)或神灵(宗教),再加上先民信仰中实用功利,使得古人极易将自然界的许多奇异现象与吉凶勾连,并幻想成一个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对其产生敬畏与崇拜心理。这也是中国民间信仰中万物有灵意识和灵魂不灭观念的社会思想基础。植物崇拜孕育的观念与人们认识自然的过程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紧密相连。一旦人类将具有超自然力量的自然崇拜“还原成正常自然运动和力量的认识”[16]63,这些观念也就势必被打破。从这点来看,对植物的变异或突生,宋人仍会受前朝观念的影响而做出趋吉避凶的表现,但更多的是赋予植物更多的社会属性,用树神、花妖、草怪等神话传说来反衬社会的种种面相,目的是建构一个有序的社会。这或是宋代的植物崇拜与前朝的不同,抑或是当时社会向近代转型的缩影。
结 语
植物与人的交互影响是人类认识、利用和保护植物的实践经验积累的历史过程。在民族植物学的视域中植物不仅仅是构成自然界的生物体,还因对社会结构、群体行为产生某种特别的生理或精神功能而具有特别的社会和文化价值[50]。王子今先生曾说:“与树木有关的异象往往被理解为吉凶的征兆,也透露出值得注意的社会心理倾向。”[33]358宋人与生活在之前朝代的人们一样无法完全理解植物世界的种种变异,只能借助神人(巫师)或神怪来诠释其中的奥秘,从而在精神层面对植物进行驯化,形成了植物崇拜的观念基础。弗雷泽解释巫术、宗教、科学依次出现的原因[51]370-371,实际上就是人类逐渐认识自然及其所蕴含规律的过程。一旦人们认识到了其中的逻辑关系,像自然崇拜这样带有宗教意味的观念则会瓦解,泛着理性思维之光的科学观念则会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借由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向外延展,来看待源远流长并继续传承的植物世界中的种种文化景观,“推测文化的起源并解释历史上的事实及现代社会状况”,我们可以窥探各种自然事物如何影响古人的精神情感,先民又是如何认识和理解自然,进而“利用这种知识以促进现代的文化并开导现存的蛮族”[31]19,最终为当代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家园提供启示。
注释
①本文所考察植物多为观赏类植物,一些蔬菜、瓜果、菌蕈等植物则不在考察范围之内。②从神话宗教角度来认知植物,今人学者或著书涉及或专门撰文,参见: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99 页。王永平:《论唐代民间信仰中的植物崇拜》,《唐史论丛》2006年期。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8-373 页。王利华:《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62-373 页。张黎明:《中国文化中树木精怪嬗变源流辨析》,《古代文明》2013年第4 期;《魏晋志怪故事<树神黄祖>的民俗文化阐释》,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 期;《原始信仰中的植物文化》,选自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会议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6-172 页。③哈维兰的泛灵信仰与我们所说的万物有灵较为一致。见威廉·A·哈维兰,王铭铭等译:《当代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6页。马伯英先生也详细论述了原始人万物有灵观念出现的原因,见马伯英著:《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8 页。④此较为符合人类学学者对自然物神话性质的概括。见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1 页。⑤这种砍树活动引发树神震怒的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或具有文化共性。见J.G.弗雷泽著,耿丽编译:《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第5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