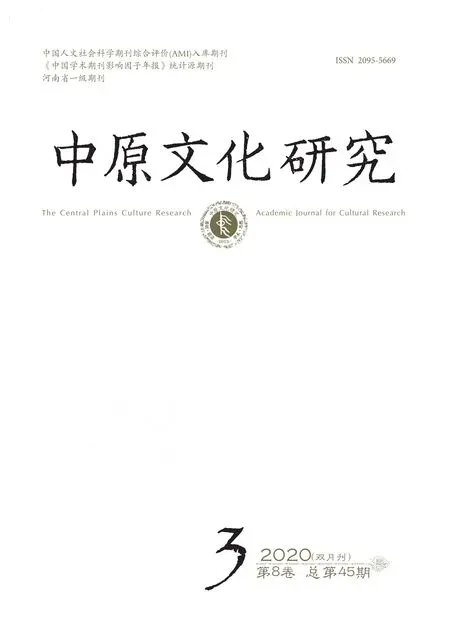“学”与孔子的话语体系建构*
宋 宁
“学”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如《论语》之《学而》,《荀子》之《劝学》,这种文献的编排反映了儒家的重学思想。金圣叹在点评《孟子》时说:“大凡一部书初开卷,必有压面第一章,如织锦人,先呈花样;如拳棒人,先吐门户。”[1]761可谓一语中的。在《论语》中,“学”字共出现了65 次之多。结合《论语》言“学”的不同语境来看,它的含义较为复杂。通过对“学”义的梳理,可以呈现出不同历史阶段“学”的思想文化内涵,这有助于理解孔子重学思想的话语体系及其阐释路径,并对孔子为学、为文、为道、治世之间的关联有进一步了解。
一、“学”义探析
从字源学的角度来看,“学”义的产生与古人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结合相关文献,至迟在三代时期,“学”字就已经出现了。许慎认为“學”是从篆文(“斆”)简化而来的[2]505。“斆”在甲骨文中有近10 种写法,其字形为:(合952 一期),(粹425 三期),(花东473 一期),(合30827 三期)等,从字符中大体可以看出其中包含有“双手”和“爻”的象形符号,“学”的原初意义可能与算筹(或占筮)活动相关。到了金文的写作中,“学”的字形变为:(沈子它簋 周早),(静簋 周中)[3]438等,增加了“子”和“攴”等象形符号,其意义可能带有了教育、指导等。
对“学”的释义,较为通行的观点是《说文解字》中释为“觉悟也”,段玉裁注:“斆觉叠韵。《学记》曰:‘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按:知不足所谓觉悟也……教人谓之‘学'者,学所以自觉,下之效也;教人所以觉人,上之施也。故古统谓之学也。”[2]505段玉裁认同许慎的观点,学即是自觉、觉悟。同时段氏提出了“教学同源”①的看法,教、学两字本来是不作区分的,都作“学”(斆),是后来逐渐分化为两字的。段氏的注解符合古代汉字“施受同词”的观点。杨树达曾说过:“古人言语,施受不分,如买和卖、受和授、籴与粜,本皆一词,后乃分化耳。教与学亦然。”[4]191。何琳仪在《战国古文字典》中解释“斆”时也认为:“教与斆(学)一字孽乳。”[5]174从基源意义上理解,学与教的含义是相通的。这种现象在传世文献中可得到印证。如《尚书·盘庚上》有言:“盘庚学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孔安国注:“学,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6]169《礼记·文王世子》中云:“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郑玄注:“学谓教也,言三王教世子及学士等,必各逐四时所宜。”[7]1404-1405。不难看出,这种学教同义,以学论教的情形是广泛存在的。
自春秋以降,社会动乱,礼坏乐崩,周初形成的“学在官府”局面被打破,执掌典籍文化的官员多因战乱散入民间。《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8]2114随着王官之学的衰落,文化知识的下移,“天子失官,学在四夷”[8]2084,社会上的私学逐渐兴起,教和学的含义也在不断地分化发展。如《左传·闵公二年》:“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8]1786《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8]2015《礼记·学记》:“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7]1524可知,“教”和“学”已经不再混为一谈了,“学”的社会性价值取向日渐突显。这在随后的孔子处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孔子继承了三代以来“尚学”的思想传统和精神内涵,提出了“志于学”“好学”“乐学”等一系列的重学思想。从《论语》中来看,孔子言“学”时,主张学、习结合,强调学、思并重,赞同学、问兼顾,倡导学、行并施,追求学、仕一体。显然,孔子言“学”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也更为具体,既体现在对广博历史文化传统的学习、思考,又反映在个体内在德性的修养,还指向了教人入仕从政。这也是儒家论“学”的独特传统。孔子有言:“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这种强烈的为学热情经过了孔子及其后学的倡导,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浓厚的重学风气,从教学方法、学习方式、处事原则等层面赋予了“学”社会伦理道德的内涵,使儒家重学思想得到了更为多元的阐释和呈现。
结合上面的分析,从“学”的原初意义上理解,“学”源于人的心理本能,是心理获得的一种理性自觉,“学之为言觉也,悟所不知也”[9]253。随着历史的发展,“学”逐渐由感性的心理活动过渡到了理性的人伦道德层面,以致“学”的知识层面内涵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被伦理道德的价值内涵所遮掩。孔子论“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学”复杂、宽泛的内涵,如《论语》中对“学”与“文”、“学”与“道”、“学”与“政”等问题的思考,突显了个体在为学过程中自我实现的价值和意义。西方汉学家指出“学”是“直接关涉‘觉'(be-coming aware)的过程”,是“通过‘闻'(教与学的相互作用和交流)而拥有和体现文化传统(‘文')的意义”,是需要个体全身心地投入的事业[10]47-48。在孔子那里,“学”是自觉的、主动的、终身的追求,是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
二、孔子话语体系中的“学”
在孔子的话语体系中,“学”与“文”是内在贯通的。需要明确的是,“文”不仅是三代之“遗文”,是“五经六籍”,是“文不在兹乎”的文,还是“天之未丧斯文”的文。朱熹注曰:“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11]110显然,“文”包含着更大的义项,与三代以来的礼乐文化制度及其相关的礼仪形式相贯通。如清代学者刘沅在《论语恒解》中所言:“礼乐法度,圣人所垂,一一实践于身心,此学也。”[12]205可以看出,孔子的“为学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西周“王官之学”的范围,侧重以经典知识的学习为基础,进而发展为一种广博的、全面的人格修养。故夏静认为,孔子《先进》篇所谓的“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学',即以‘文'为‘学',是指对三代礼乐文化为主题的古典知识有广博的学养”[13]207。可谓知言之论。进一步而言,孔子的“以文为学”是将所学之“文”经由“习—思—行”三个阶段层层深入,从而逐渐深化“学”的发展进路。如《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中记载:“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贵其能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14]69故简要从“学与习”“学与思”及“学与行”三对关系中探究孔子话语体系中的“学”范畴。
学与习。《论语》开篇言:“学而时习之。”马融释为:“学者以时诵习之,诵习以时,学无废业。”[15]2457显然“学”与“习”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对“习”的经典释义,见于许慎《说文解字·羽部》:“习,鸟数飞也。从羽、白声。”[2]549即“习”是鸟类反复鼓动翅膀,尝试飞翔,有重复练习的意义。近人对此说法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数飞”并不是习的本义②。综合近人的研究来看,“习”的初始意义有重、惯等,后逐渐引申出“重叠”“反复地学”“熟悉”“习惯”等意义。《学而》篇中两处“习”的意义相近,可理解为是一种重复、反复的学习活动,以期熟练掌握所学内容。有学者认为:“‘学'总是内含着某种自我生命实践的意向,‘习'则是在这种意向中展开的个体生命实践。”[16]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孔子的“生命实践”并不是单纯性的重复,而是在反复“习”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质,使习在保持原有的重复之外,多了一层规定性——思考[17]25。如《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18]1925正是这种新的“规定性”,让孔子在反复学乐的过程中,由“习其曲”“习其数”升华到“得其志”“得其为人”的境界,可谓“不亦说乎”。正如康有为所言:“凡学至熟习,则观止神行,怡然理顺,逢源自得。”[19]1可以说,“思”使“习”有了质的飞跃,“习”又与“思”共同建构了孔子“学”范畴的话语体系。
学与思。如上所言,思作为一种“新的规定性”,是对所习之文的提升。同样,思也是衡量学生善学、好学的重要标识。孔子重思,主张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王夫之总结道:“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助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20]301这是符合孔子原意的。孔子认为获取“致知之途”需要求知者积极主动地“愤”和“悱”,这样才能有所领悟,做到“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告诸往而知来者”。故孔子对子夏、颜回等大加赞赏。如《论语·八佾》篇云: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15]2466
子夏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思考、追问,给了孔子很大的启发。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是孔子所赞赏的。又如《论语·为政》篇载:“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颜回的“退而省”让他对孔子之“学”有了深刻的领悟。颜回曾赞叹道:“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遂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从颜回的感叹中可以看出,孔子之“学”虽看似平易近人,实则高深莫测。只有经过不断地反思、内省,才能自觉地将所学的知识由外转化为内,逐步摒除心中的忧虑和恐惧,然后借助知识的“起”“发”进入自得之域,实现通其变化,行其所知的目的。正如《四书训义》所述:“夫学何为也?非侈诵习之博也,非摹仿古人之迹以自表异为君子也……则其于学也,日有作,月有省,瞬有养,息有存,以遇古人于心,而复吾性之知能也。必无不尽也,而后可以集于吾心,而行焉皆得也。不然,慕道而无致道之功,何足以为君子乎?”[20]966可谓颇得要领。故不难理解曾子有言“吾日三省”,孔子有云“君子九思”。
学与行。在孔子话语体系中,行也是学的一部分。程子解释“学”时言“学者,将以行之也”[11]47。匡亚明在《孔子评传》中说道:“孔子所谓学,本身即包括实践——行的内容。”[21]245“行”在《论语》里被看作比“忠、信”更为难得的品质。刘宝楠解释道:“‘忠信'者,质之至美者也。然有美质,必济之以学,斯可祛其所蔽而进于知仁之道,故子以四教先文行于忠信,行即行其所学也。”[22]207这里的“行”(或“行其所学”)更近于一种道德实践,是将所“学—习—思”之“文”,经由内而转向外的过程。《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7]1632荀子曰:“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23]142可以说,“好学”“躬行”反映了内在的自然天性与外在的道德理性间的协调融合,是谓孔子所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是在礼乐教化的背景下,孔子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典范。所以孔子对颜回、孔圉的“好学”给予了高度评价,“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相应,孔子对宰予的“昼寝”给予了严厉批评,“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论语·公冶长》),对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作出“恶夫佞者”的评价(《论语·先进》),又对孔鲤“不学诗”“不学礼”(《论语·季氏》)进行了劝导。在孔子那里,“学”与“知”“行”一起,强化了求学者的道德品格,彰显了为学之人的存在意义,使为学之人“由本然的、自在的形态,提升为自觉的存在”[24]201。可以说,“学”既涵盖了单纯的知识性学习,也是与“知”“行”一起贯穿了个体德性修养的整个过程。孔子语子路的“六言六蔽”便是最好的例证。
由上观之,经过“习—思—行”的“学”是一个不断积累、层层深入的过程。它是对三代以来礼乐文化的传承,是理想人格塑造的重要途径。但是孔子话语体系中的“学”,不仅体现在文化传承与身心修养,还指向了教人入仕从政。面对动荡的社会局势,孔子深刻地认识到了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论语·子张》)。孔子尝试将知识学习与教育活动融合起来,以求实现为学由立己到立人、成物的转化,期望借助文化、教育的力量来扭转礼坏乐崩下混乱的社会秩序。这样一来,“学”便与社会政治生活与意识形态相联系,成为儒家论“学”的独特传统。
三、孔子重学思想的深层内涵
孔子重学,倡导“为己”之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这里的“为己”是君子“美身”之学,是“欲得之于己”而非“见知于人也”。对此,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认为孔子充分发展了自我意识,肯定自我是“一个能实现自己意志的个体自我”[25]130。如《论语》有言:“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但孔子的“为己”之学并不是强调“个人的”“孤立的”自我之学,他强调的是各种关系的连接点或汇聚点[26]39。孔子很清楚人是社会的关系性的存在,只有在社会的相互作用下,人的独特性与自我的价值才能得以呈现。正如《中庸》所载:“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7]1633可以说,孔子的“为己”之学既是发掘自我潜能,也是将自我融入到复杂的社会行为当中,遵循“道”,尽为人之道。如柳诒徵所说:“孔子为学之目的,在先成己而后成物。其成己之法,在充满其心性之本能,至于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境,而一切牖世觉民之方,乃从此中自然发现于外。”“孔子所学,首重者曰成几,曰成人,曰克己,曰修身,曰尽己……孔子之学,亦非徒为自了汉,不计身外之事也。成己必成物,立己必立人。”[27]274-275概言之,孔子论“学”是“为己”与“为人”相统一的,是借助“学”将“文”“道”“政”内在贯通起来,形成了孔门论学的独特传统。
具体来看,孔子论“学”有着更高的理想追求。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此处的“一以贯之”与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相关联。汉学家史华兹(Benjamin I.Schwartz)认为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实质上是一种潜在的“统一性通见”[28]132,这种潜在“通见”的显现,需要通过对三代礼乐文化知识的学习,领悟深藏于这些历史经验、历史知识中的“道”,进而掌握运用这种文化传统来评判、介入当前社会生活的能力。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余英时曾指出:“中国的‘道'源于古代的礼乐传统,这基本上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29]107可谓一语言中。儒家一向认为“学”与“道”内在相通,道寓于学中,学以体现道。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
进一步而言,孔子论“学”还蕴含着更深刻的社会追求。上文分析,“学”与“道”是内在统一的。借助“学”,孔子自觉到自己已成为“道”的现实体现者,“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并认为自己得到了天命的承认,“天生德于予”“知我者其天乎”。所以,他带着强烈的信念践行“天道”赋予他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他相信“通过自我努力人性可以得到完善,固有的美德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天人有可能合一,使他能够对握有权力、拥有影响的人保持批评的态度”[26]11。实质上,孔子眼中的“道”不是绝对形而上的、非人事的、远世间的,而是带有世俗化、人间化品格的存在。我们知道,孔子一直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论语·公冶长》)等作为其社会理想追求,他期望通过“为学”等手段来“修己”,实现“以敬”“以安人”“以安百姓”的治世理念。从这一角度来看,孔子重“学”和正“道”的最终指向——“政”(或“仕”)。孔子期望通过对“文”的重新阐释,担负起“道”的历史使命,进而借助教育的方式成为社会中意义的传播者和价值的引导者,以期实现“施于有政”“化民成俗”等社会理想。而入“仕”(从“政”)正是介入并实现这一社会追求的重要手段。由此,“学”与“仕”便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来了。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朱熹《论语集注》云:“仕与学理同而事异……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11]190实质上,仕与学在古义上也是相通的。“仕”在《说文解字·人部》中释为:“学也。”段玉裁注云:“训仕为入官,此今义也。古义宦训仕,仕训学。故《毛诗传五》言:士,事也。而《文王有声传》亦言:仕,事也。是仕与士皆事其事之谓。学者,觉悟也,事其事则日就于觉悟也。”[2]1461段玉裁以古义释仕,提出仕与学相依相通,认为实践政事而有所觉悟,便是一种学习。有学者研究指出:“孔子把从仕看作是实践所学的一个过程,因此,从仕就不是作为学习目的出现,而学也不仅仅是从仕的一个先决条件了。从仕无非是学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说,学和仕是一个整体过程表现出来的两个方面……既然学仕一体,那么,‘学而优则仕'就不能作为选拔人材的原则来看待,应当把它们看作是学习过程。”[30]268-269正如《为政》篇所言:“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儒家将这种政治上的责任意识内化为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为学、为文、为道、为仕正是践行生命形式的重要途径。在这个过程中,为学、为文与为道可以丰富个体的知识系统,提升个体的德性修养,从而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入仕的选择。从这一角度来看,孔子的“谋道”“忧道”“志于道”“死守善道”指向的是社会秩序的重建,带有一种普遍的人伦思考。“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
综上所述,在孔子的话语体系中,“学”有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在于传承三代以来的礼乐文化传统,而且也通过为学修身与儒家的为道、治世理念相契合,形成了儒家论学的独特传统。诚然,孔子生活的时代,社会动乱,礼坏乐崩。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尝试从内部着手转变混乱的社会现实,实现“施于有政”“化民成俗”等社会理想,也注定是失败的。但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诸子却借助教育的手段有效地控制了文化系统,凭借对传统经典文献的阐释,儒家诸子“将生命力注入其中,并将之作为神圣使命,担负在自己肩上”[26]19,成为三代礼乐文化精神的传承者,成了社会中意义的提供者,以及政治权威合法性的辩护者[29]47。从这一角度看,他们又是成功的。概言之,在早期儒家的话语体系中,“学”“文”“道”“政”间是错综复杂的关系存在,“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纽带,在传承三代礼乐文化精神,确认知识分子政治身份,以及构建儒家的文学传统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注释
①从目前学界研究来看,就学源于教,还是教出于学,尚存有争论。如王凤阳在《汉字学》的《象形字释例》中说:“学,教的同源分化字,教训之使之有所觉悟也。”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高华平《由楚简中“教”族字的使用看楚人的辩证“教学”观》也认为学源于教,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年第1 期。杜成宪则持相反的观点,他在《早期儒家学习范畴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中明确提出教是由学而来的。对此,本文暂不讨论。②唐兰认为“鸟数飞也”,不是习的本义,“疑习之本训当为暴乾矣……习声与叠袭相近,故有重义、惯义,引申之乃有学义,本无飞义也”。见《殷墟文字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杨树达指出:“习与易坎卦习坎之习义同,重也。”见《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54年版。这一点也得到了饶宗颐、裘锡圭等先生的赞同。如饶宗颐在《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卷二》中明确说道:“习,即袭,重也。”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2·甲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