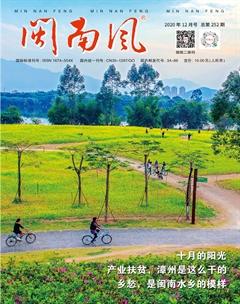父亲与芗剧
庄北阳
金师傅的理发店就在菜市场一隅,那里经常会有一些丝竹发烧友,咿咿呀呀地演奏芗剧曲调,来理发的人可以一边理发一边欣赏奏乐。我路过那里,也常常坐一会儿,聊聊天。
金师傅每次见到我,总会提起我的父亲,说他曾经也是那里的常客,而且,壳弦、三弦演奏芗剧曲调水平不低,还带个老徒弟(我叫他阿智兄),却老是弹不好三弦,我父亲很耐心地指导他。我父亲人缘好,乐友们对他印象颇佳。
金师傅还说,有一天,我父亲的老徒弟,独自一人来到理发店,泪眼迷蒙地对他说,我的师傅过世了,我以后没人教乐器,也没人相伴谈心,日子要怎样度啊!话语中竟带着哭腔。
我听了以后很感动,勾起了无限的思念之情。
父亲是新千年伊始那年的六月十八日离去的。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愿意和弱小无助的人做朋友。
就说他这个老徒弟吧,六十多岁了,同一村的,年轻时长得帅气,心高气傲,追他的姑娘有好几个!可是性格固执,常爱跟人争论高低,爱发牢骚。他的家庭出身不好,遭遇可想而知。大小队的头儿们常拿他做出气筒,经常挨骂挨批挨斗,干最重最累的活。时光流逝,一转眼,他就成了生产队里的第一老光棍,终身难娶。
我父亲没有疏远他,轻视他,相反,经常安慰、开导他,还教他学弹三弦,内容都是芗剧曲调,引领他在音乐中寻找乐趣。他在我家才感到温暖,才感到被尊重,一直对我父亲心存感激。
父亲的朋友不少,都是老实忠厚的平头百姓,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爱好弦乐的乐友!
有一个叫阿寿的,解放初期十四、五岁,无家可归,与我父亲同在村中创办的芗剧团学艺。父亲大他十多岁,一段时间,常带阿寿到家里来吃饭、住宿,与他共同切磋芗剧。父亲与奶奶待他很好,家里虽穷,也让他感到温暖。阿寿很聪明,没几年时间,学会了芗剧的大部分艺术,编导演奏,样样精通,出师以后,独当一面,能到外地教戏了。
阿寿叔后来到外地成家,二十多年后,回家乡探望我父亲,阿寿叔称父亲为老大哥。阿寿叔此时今非昔比,因为有华侨关系,在县里的侨联任职。对我的父亲及奶奶,在他最无依无靠、飘泊流浪、苦学芗剧的日子里,经常管饭留宿,一再表示心存感激!阿寿叔还把他戴了多年的心爱手表,送给我父亲,留作纪念,父亲甚是高兴。老朋友相见,分外亲切,把盏叙旧,情意浓浓。父亲离世后,我把手表转送给阿智兄,作为人世间纯厚情谊的延续。
父亲一生喜爱芗剧,喜爱演奏芗剧曲调,常常以乐会友,奏乐自娱。即使是在经济极端困难,文化生活极端缺乏的年代,也不例外。是芗剧使他对生活充满信心,对人生有种朴实坦然的感悟,是芗剧音乐陶冶造就了他善良温和、宽厚待人、忍让谦逊,随缘恬淡、与世无争的性格。
父亲对芗剧的喜爱很早就开始了。
早年听说,民国初期,老家奎洋顶圩汪洋甲,就有一个民间剧团,因为只有七个角色,号称“七角仔戏”,演员演技出众,演出内容通俗有趣,闻名遐迩。
父亲从小受到村里演戏气氛的熏陶,对民间戏剧产生了兴趣。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漳州城里有几位芗剧艺人到家乡教戏,父亲与一批有兴趣爱好的男女青年,一起学习,接受培训。
父親学习演奏乐器,角弦、壳弦、广弦、三弦、月琴、唢呐,都有涉及。他学习很刻苦,很虚心。少时,因家里穷,只上过几天的私塾读书,却因记性好,悟性高,加上勤奋,认了一些字。这对记乐谱唱词很有帮助。各种芗剧曲调,很快就背得滚瓜烂熟了。同时,用心观察、揣摩、领会老师演奏的指法,弓法及其技巧。走路时,吃饭中,睡觉前,口必哼曲调之音,手必做拉弹之势。经过刻苦训练,反复实践,慢慢地,掌握了演奏的技巧和本领。还认真钻研、收集整理芗剧曲谱,供自己及同伴学习使用。
不久,乡村里组建了业余芗剧团,演员队伍人才济济,排练了一批传统剧目。偏僻、闭塞、落后的乡村开始活跃了。一到夜晚,山村的道路上,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步履轻快,打着松明火、手电筒赶往排练场(借用祠堂),一路欢声笑语,一路引吭高歌,好不热闹。
父亲在剧团渐露头角,拉二手弦,一段时间拉过头手弦。他为人低调,从不张扬个性。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队成立的美声芗剧团,排演了一批古装戏,如《桃花搭渡》《知县斩案司》《沉香扇》《五女拜寿》《十五贯》……还有一些我叫不上来的剧目,准备在春节期间演出。
那时候我七、八岁,粗懂事,听说演戏,整天高兴得像过年似的。通常,排练时不准外人参观,特别是小孩。因为父亲是剧团的人,我不上学时,就到剧团找父亲,目的是看热闹,看叔叔、阿姨们怎样排练节目。
演出当晚,我早早吃好饭,便随父亲到大队的剧场。剧团团长是父亲的同庚要好朋友,他特许我到戏台上的边厢寻个座位,但嘱咐我别乱跑动。一般无关人员是不能上台挤占位子的,我沾了父亲的光,觉得特自豪。
锣鼓响了二通后,台下观众已是黑压压一片,翘首以待了。
布幕徐徐拉开,弦管齐奏,美妙悦耳。女演员踩着碎步登台了,到台中一亮相,嘿!台下嘈杂声立即静了下来。
我坐在乐队后面,看着父亲他们忙碌起来。父亲右手有节奏地长舒短摆,轻松自如地拉着弦弓,左手在弦线上按压揉弹,上下滑动,侧身坐着,眼睛专注地看着台中演员的表演。
整个乐队人人精神振作,各自操弄着拿手的乐器,通力配合,悠扬的乐曲在剧场里弥漫开来。那乐曲,时而如清亮山泉叮咚流淌,时而如高山瀑布奔泻而下,时而如宽阔江河平缓舒展;那乐曲,有如春风的温暖和煦,夏日的炽热高亢,秋雨的缠绵缱绻,冬雪的凛然奇寒。
随着剧情的展开,父亲更加忙碌着。一会儿换上三弦,熟练地弹拨起来,乐曲里传出急切紧张的气氛;待到剧情高潮时,父亲又换上唢呐,嘀嘀嗒嗒地鼓吹起来,高昂的声调响彻整个剧场。
父老乡亲们,平日里在田间辛勤劳作,难得有机会享受文化生活,只有在节日里,才能品赏到这美好的文化盛宴。喜闻乐见,通俗易懂,乡土气息浓厚,便于吟唱传播的芗剧,给大家带来了笑声,带来了愉悦,带来了欢畅的心情。看戏的机会,也是亲朋好友见面聚会、畅谈交流的良时佳辰,整个剧场充满着温馨、祥和、亲切、欢乐的气氛。
剧终了,幕谢了。大家依依道别,带着满足和惬意,回家去了。
我家所在的生产队,跟我父亲一样会乐器的有好几位。每年农活轻松时节的夜晚,他们相聚一起,演奏娱乐。演奏的最好场所,是生产队仓库的顶棚上。这是座水泥钢筋青砖楼(通常称为番仔楼,为早年本地财主所建),楼下的石埕也不错。
大家拎着乐器,拿上茶水、烟丝、椅凳,排列坐定。调好弦音,扬琴叮叮咚咚开了头,接着丝弦拉动,箫笛和鸣,一场简易的演奏会便开始了。
只见:兆伯敲扬琴,两片薄竹片,上下左右,轻捷敲打;福伯拉大广弦,娴熟自如,闭目晃头,渐入梦境;文兄吹洞箫,气沉丹田,舒缓婉转,荡气回肠;智兄弹三弦,由于初学,不太跟拍,只能轻轻弹拨;古兄跟着音乐拍子,敲打响板,恰到好处;父亲拉着六角弦,运弓按弦,灵活熟练,眼睛微启,忘情地融入佳境。
他们沉醉在音乐的世界里,沉醉在芗剧优美亲切的曲调中,忘却了繁重劳作的苦累,忘却了艰辛生活的苦涩,忘却了漫漫人世间的烦恼,尽情地体会人生的乐趣,寻求精神上的快慰。
有时候,同在业余剧团的老戏骨们,还会赶来凑凑热闹,畅喉高歌,过过芗剧瘾。现场气氛热烈高涨,其乐融融。
事隔几十年,至今回想起来,印象是那么清晰,那么深刻,那么美妙。这也是闭塞山村唯一的文化娱乐活动。
可惜,在“文革”中,因为怕被扣上传播资产阶级思想,传播封建文化艺术,演奏活动停止了。父亲那把心爱的六角弦,还有壳弦、三弦,用袋子装着,悬挂在房梁上,束之高阁,只有在心情愉快时,时间又充裕,才偷偷取下来,检查一下,轻轻地拉几段熟悉的曲调。
直到1980年以后,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土地承包,父亲才有心情重新操弄乐器。
以乐会友,奏乐为媒。父亲他们组织了新的演奏娱乐小组,成员中有爱好芗剧的,有爱好潮剧的,也有爱好南音的,总之,以乐为乐。
大家约定,每逢五天一圩之期,到奎洋大圩场边的山伯家集中。山伯热情好客,家中乐器、牌桌,一应俱全,是个理想的聚会娱乐场所。常到人员七、八位,多者十多位,吹拉弹唱,风光热闹,惹得赶集的人,趋前探看聆听,称羡不已。演奏累了,还可打牌讲古,老伙伴们自然玩得开开心心。
中午用餐时,大家自掏腰包,花上一两块钱,购些面条、猪肉、葱蒜、蔬菜,煮着一块吃,乐乐陶陶。圩集散了,那些老伙伴们心满意足,悠哉游哉地走在返家路上。
父亲的一位老乐友叫庚伯,酷爱弹三弦和月琴,已经到了非常痴迷的地步。他平时在家做木桶手艺,干活间隙,操起琴弦拨弄一番,权当休息,然后才重新操斧弄锯。有乐友来访,即刻放下手中活儿,泡茶入座,和弦弹奏尽兴。有一次没米下锅,也不去设法借米,坐在灶间叮叮当当弹琴,聊以充饥。此事邻居一传扬,成为佳话。我曾经好奇,问其本人:阿庚伯,听说有一次你没米煮饭,饿着肚子在弹琴,有这回事么?阿庚伯听后,嘿嘿地笑笑作答:大家爱说话。
这些老伙伴们,还有惊人的壮举呢!他们都是六十岁上下的人了,娱乐之余,还组织上山造林,挣些钱,除贴补家用外,自己留一些钱作为娱乐活动费用。父亲人缘好,被推举为这小集体的“小头目”,分配工种,安排伙食,管理账务。
许多六十岁的老人,在家里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可他们却老当益壮,上山造林,發挥余热,精神实在可嘉。
早上,他们一行十多人,肩扛锄头,劈刀,腰扎柴刀,挑着米菜、茶水、铁锅,头戴斗笠,足穿胶鞋,精神抖擞上山去。攀登山路,动作虽慢却有说有笑,气喘吁吁却坚持不懈。艰苦的劳作打造了他们坚韧的性格,生活的磨难炼就了他们顽强的精神,集体的活动又使他们找到了快乐,焕发了活力。
老大伯造林队成了山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赞许。乡亲们见了他们就说:“哇,老阿伯个个都是老愚公,真出力啊!”老伯们连忙说:“夸奖了!夸奖了!”谦虚、害羞、自豪的表情写在他们的脸上。
那些老伯们善良勤劳,乐观豁达,都有一副热心肠。
说来有趣,那时我二十六、七岁还没结婚,老伯们就集体行动给我物色对象,说我人太老实,应找一个性格、人品较般配的。为此,他们议论了好一阵子,有时还争论不休呢!
其实此前,我因处境困逆,心情不畅,不想找对象,不知不觉间已到“大龄”。现在老伯们这么热心帮忙,不好拒绝,自然心存感激,最后,我首肯了门伯给我介绍的对象。
真得感谢父亲的朋友,那些可亲可敬的老伯们。
这是闲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老家奎洋造水库,我们搬家了。父亲与那些好伙伴们分离了。这是多么伤心和无奈的事啊!一段日子,父亲闷闷不乐,老是惦记着昔日的老朋友们。想当下,迁居异处,人地生疏,居所简陋,生活窘迫;时过境迁,物事皆非,昔日的乐友,剧团的戏友,散离的散离,谢世的谢世。重新相聚,奏乐纵歌,已不可能,悲凉之情,一时难于排遣。好在父亲能够及时调整心态,随遇而安,淡定从容,勤劳坚韧,开始新的生活。
搬到马山新家后,得益于芗剧音乐牵线,父亲又结识了一批新朋友。
在菜市场金师傅的理发店里,圩场江师傅的理发店里,父亲与一群乐友,抬手弄弓弦,奏乐觅知音,又是一番热闹欢乐的景象。
但更多时候,父亲却潜身侍弄菜园,提供全家人饭桌上的新鲜蔬菜。夜晚空闲,父亲独自坐在自家门口,拉奏弦乐,沉默不语,神色凝重。在美妙的芗剧声乐里,流露出对昔日时光的无限怀念,对诚挚老友们的深深思念,倾诉着生活中的孤单和失落,人世间的沧桑和无奈,也表达了人生的满足和希望……
多年以后,我在奎洋村,碰到依然健在、年近九十的山伯,山伯亲切地拉着我的手,动情地说:“你父亲是我最好的老友,却离我先去,真可惜!我做梦都经常梦到他!”说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混浊的眼睛中泪光闪闪。我紧握着山伯的手,久久没有分开,激动难言。
现在我也有一大把年纪了,想学习拉胡琴,奏弦乐,丰富一下业余生活,可拉起弓弦,奏响的乐曲,实在不雅听,用邻居的话说,拉弦像是锯木头!这才叹惜,以前没有认真向父亲讨教学习弦技。
父亲走后,我在他的画像上写了一副对联,以示怀念:
七四华龄,勤奋聪灵知器乐;
一生善德,谦和忠厚守仁心。
父亲善良的人品,对芗剧音乐的挚爱,永远烙印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