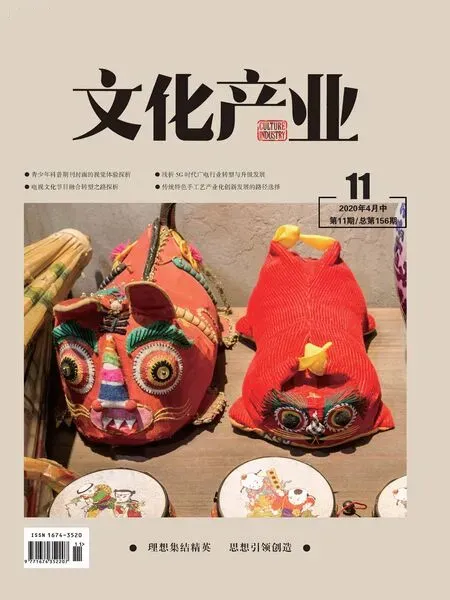基于Instagram进行对外汉语教学的分析探究
◎姚美先
(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 100000)
移动互联和大数据技术突破Web2.0时代,电脑作为唯一硬件端的限制,使得信息入口小屏化、信息形式碎片化、信息内容自媒体化。国际中文教育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挑战和机遇,对外汉语的教学形式也在不断创新。在风行全球的移动社交媒体应用软件Instagram上,对外汉语教学账号于近几年集中兴起,就是一个典型现象。
一、研究背景
(一)行业背景
世界格局的变化,使汉语学习需求有了前所未有的高涨,这是促成对外汉语教学队伍不断壮大的内在动因。在2019年12月份召开的国际中文教育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发言指出,师资是开展语言教育的关键,现在各国中文教育机构的突出问题是师资不足。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明确表示,未来2-3年中国教育部将重点采取6项新举措,支持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这其中,就有多条涉及教师培养,比如大幅增加专业博士名额,重点录取中外优秀青年中文教师;既招收学历生,又开展各种专业化培训,提升各国中文教师的语言教学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本土工作适应能力;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提高中方外派中文教师及志愿者待遇的政策,进一步增强外派中文教师岗位的吸引力,同时支持各国孔子学院选拔聘用更多的本土中文教师。
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是对外汉语教学形式取得突破的重要土壤,语言教学类自媒体因此得以崭露头角。它们有的由汉语教学机构开设,有的只是中文教学爱好者自己运营的业余平台,但都在各类网络平台上得到迅猛发展。本文关注的Instagram就是对外汉语教学账号蓬勃兴起的平台之一。根据Quintly发布的“2019年Instagram调查报告”,全球范围内平均10个成年网民中,就有6个人拥有Instagram账户。
首先,Instagram的主要用户为母语非汉语的人,他们是对外汉语教学天然的教学对象。其次,Instagram支持文字、图片、视频、直播、表情、网页链接等几乎所有内容形式,且仍在不断研发新的形式,例如Story。Story是一个独立于主页时间流之外的竖屏分享界面,同样兼容图片、视频、文字等几乎所有的传播形式,手机屏幕就像一块画布,用户可以自行调动内置的各类元素进行创作,但会在发布后的24小时内消失。此外,Instagram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社交媒体的优势,在熟人社交之外同样支持陌生人社交,用户发布的内容可以被任何人看见,这是十分有利于知识科普教学类账号的。Instagram还会通过一系列的机制帮助用户发现可能感兴趣的账号,比如标签功能可以引导用户主动标注,一个标签就能集纳一个类型的内容,从而被更多的陌生用户看到。
(二)学术背景
笔者首先以社交媒体、自媒体、汉语教学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此前的研究大多关注社交媒体上中文教学的传播效果,以及由此带来的构建国家形象的效果,还未有人对利用平台和技术本身进行实质的汉语教学进行探讨。比如,黄鸿业认为社交能力和传统文化素养是决定汉语国际教育跨文化交流效果的两大重要因素,因此应培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大学生正确使用社交媒体的能力。陈珂忆与辜亿珈做过中文社交媒体在对外汉语修辞教学中的运用及影响研究,不过其实验所用数据来自中文社交媒体,与本文探讨的Instagram仍有不同。
笔者再次以Instagram、Chinese为关键词进行检索。Veronika Seroshtan进行过基于Instagram汉语教学中的视觉辅助方面的研究,他认为社交媒体(Instagram)是支持非正式汉语学习的有效方式。然而局限性在于,Veronika的研究是通过实验进行的,而社交媒体的特点决定了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孵化影响力的平台,实验与实际运营依然存在差异。
笔者再将关键词进行发散,发现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各类新技术被学界关注已久且十分重视。吴瑛就认为中国文化传播应该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的文化传播经验,借助多种传播媒介,拓宽传播渠道,并且要密切关注、及时评估对外传播的效果。郑艳群提到:“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汉字的读音需要声音媒体支持,汉字的笔顺书写作为动作,技能的教学理应用动画或影像技术支持,汉字的义项和构词等用法信息离不开文字技术的支持。”这些特性都与Instagram不谋而合。但郑艳群同时认为,深入研究信息技术与汉语课程整合的论文相对匮乏,如什么类型的汉语知识适合或需要用什么样的媒体或它们的组合形式来表现?什么样的汉语技能适合或需要用什么样的媒体或它们的组合形式开展训练?祝智庭等指出,教育技术研究方法越来越趋向实证的趋势,这方面的研究应加紧开展。也就是说,学界对于理论和效果的研究都展开了,但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的分析尚匮乏。这正是本文将采用的研究方法,即针对账号本身进行探究。
二、研究过程与结论
(一)明确有效研究对象
研究第一步是建立Instagram上的汉语教学账号库。笔者分别以Chinese(59个),Mandarin(67个)、中文(63个)、汉语(68)、hanyu(58)、普通话(65)、putonghua(37)为关键词进行账户(Accounts)搜索,删除重复项与非相关项后,得到个与中文学习有关的账号123个。考虑到并非所有的汉语教学账号都一定会在命名中加入上述关键词,笔者又使用了Instagram里的相似账号推荐功能,即每一个账号下面都有为你推荐(Suggested for you)按钮,点击所有(All),就能看到系统对所有类似账号的推荐。最终共得到账号125个。
研究第二步是筛选用于案例分析的账号。本文设立了三个筛选标准:粉丝数超过1万、截笔日的一周内有内容更新、有点赞和互动。这三个数据指标都很客观,且共同构成了社交媒体账号的活跃度和影响力。笔者发现,粉丝数超过50k的账号有两个,超过30k的有5个,接着,随着粉丝数的递减,账号的更新频率以及互动率也随之递减。同时,一些账号的内容形式雷同,彼此“模仿”。最终,在粉丝数超过10k+以上且近期有更新的账号中,选取了14个账号进行研究。
(二)分析研究结果
建立账号库的过程也帮助笔者建立了宏观观察,因此分析结果将从账号本身与账号内容两个角度展开。
1.对账号本身的分析
首先,账号命名中含有Chinese和Mandarin有助于获得更多关注,含有中文、汉语、普通话、hanyu、putonghua的则效果不明显,这表明了外国人对中文教学的第一关联关键词是Chinese和Mandarin。14个账号均为英文命名,有的强调学习效果,比如Chinese zero to hero、Learn real Chinese;有的明确指出账号定 位,比如 Bite-sized Chinese、Chinese link words、Chinese readers'guild-CRG;有的将账号运营者包含在内,比如汉语学习网站Chinese class 101,个人运营者Jen的账号Chinese with Jen。其次,14个账号中,9个账号由面向外国人的汉语教学网站或APP官方运营,3个账号由个人运营,2个账号由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运营。这表明有扩大影响力和招生需求的机构,更有动力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最后,这些账号中全部创立在2015至2109年间,这佐证了本文前部分对于行业现象的描述。Instagram本身成立于2010年且流行已久,汉语教学账号的兴起确实是近五年间的新现象。
2.对内容风格的分析
尽管自媒体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新形式,但内容风格存在趋同的现象,制作精美的字、词、句卡片,是被普遍采用的形式,在由中国人运营的账号中尤其明显,两个外国人运营的账号没有采用这种方式。不过,尽管都使用汉语卡片,个人运营的账号与机构运营的账号还是有明显差异。个人账号习惯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来总结汉语词汇。比如目前粉丝数最多的chilling Chinese,206条字词卡片类短视频内容中,格式均为拍下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名词或短语场景,在封面上写上这个词,内容包括软件、东北菜、月饼、震惊、肯德基、电动车、取钱、打卡、软、糯米糍、咬手指等等,所有的场景都来自博主的生活。但机构账号倾向于做总结型的字词卡片,比如食物名称合集、常用动词合集、洗衣类词语合集等等,与汉语教材相似。
个人出镜很受欢迎,亲和的教师或博主形象是学生或受众与教学平台的强连接。Chilling Chinese、Chinese with Jen、East west Chinese、Learn real Chinese 都有博主出镜来讲解教学点。Chilling和Jen是中国人,二者都会录制一种属于自己的视频风格来进行教学。East west Chinese 和 Learn real Chinese 都是外籍博主,他们选择录制自己生活中的场景,通常是用英文视频来讲一个中文的场景。比如East west Chinese一人分式两角,模仿奶茶店点奶茶、买煎饼果子等场景。
汉语教学账号的点赞数和评论数,相较于Instagram上的其他类型内容都不算多,除了有社交媒体本不是专门用于知识科普的平台这一个原因外,也说明了对外汉语教学自媒体账号的内容依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学生或受众更多地流于观看,还没有进入到思考和提问的程度,导致与博主的交流欲望并不强烈。Chinese class 101注意到了互动环节,会专门发布提问卡片,比如你如何练习你的中文发音?你到过中国吗?你如何学习中国语法?你通常在什么时候会用到中文?这类型的帖子下就会形成讨论。
与传统教学不同,社交媒体既可以成为教汉语的平台,同时也是一个展示汉字魅力与中华文化的平台。East west Chinese 和 learn real Chinese 从个人生活视角拍摄的中国生活视频,风格轻快诙谐,无形中就向受众传达了当代中国形象。比如疫情期间east west Chinese拍摄的模拟买口罩视频,就反映了一种日常、真实但可爱的中国生活。
三、结语
如上是针对Instagram对外汉语教学账号进行统计观察所得出的思考,但这些显然是不够的。小屏、竖屏时代改变信息传播方式,也给“三教”问题带来新思路,中文教材如何编写能更好与移动互联结合?如何利用非正式学习空间建立更完善的语言学习环境?教师的技能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拓展?此外,我们也不能一味认为新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还需思考社交媒体进行辅助中文教学的利和弊分别是什么。笔者将继续关注,与学界同仁共同为国际中文教育带来更多思考。